 四时殊气
四时殊气学术大咖齐现身!《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系列专著首发式暨研讨会举行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 通讯员 杨希林暑假到了,但杭州老师的暑期生活却并不像爸妈们想得那么轻松:除了做好备课工作,他们还要抽空研读暑假作业单上的阅读作业,方便和学生讨论、交流读后感。鲜为人知的是,不少一线高中语文老师在研读外国文学经典时,心中一直有个烦恼: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凸显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作用?“原来,很多人认为外国文学就是外国的文学,但是我们现在阅读的译文版,其实是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单纯作为外国的文学来阅读。”一名教龄20余年的高中语文老师告诉钱报记者:“比如《堂吉诃德》、《红与黑》等作品,不少人都读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在源语国的生成情况。”关于这个问题,记者在7月12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八卷集系列专著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上,找到了答案——“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强调在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生成、演变与传播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实情,关注外国文学经典在我国传播演变过程中凸显的中外文化交流、民族文化身份建构和民族形象重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外国文学经典的源语生成当做可资借鉴的宝贵文化财富,为我国文化建设服务。会上,系列专著总主编,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教授回顾了10年来项目从申报到立项,从研讨到结题,再到成果出版的全过程。“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结合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以及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及其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一视野来考察经典的译介与传播。应着眼于外国文学经典在原生地的生成和变异,汲取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的经验,为祖国的文化事业服务。”吴教授还补充道,通过外国文学经典的中国传播,以及面向世界的学术环境和行之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将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看成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发展历程的折射,进而重塑文化中国的宏大形象。“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绝对不是为了宣扬外国文化。我们是把外国文化普及起来,为我所用。外国文学,它绝对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项目,也是浙江省最早获得的人文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在研讨会现场,其他专家学者也分享了自己在探索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中的领悟。“外国文学,它绝对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外国文学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还是重要的学术资源。将学术的发展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需要以及学科原有的基础,有助于外国文学学科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促进各个二级学科以及三级学科之间的协调发展,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赢得世界学界的尊重。” 系列专著分卷主编、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温州大学傅守祥教授总结道。“翻开这套丛书,我感到特别惊喜。我从小就热爱读外国文学经典名著,但囿于国别和时代背景,觉得西方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各有特点,无法进行系统性研究。而这套丛书将西方经典文学作为整个文学系统整体图景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流动性环节来进行研究,打通艺术门类、国别和时代划分,通过纵横交错的多方位考察,展现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西方文学经典独特的生成方式,以及这些文学经典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描绘出了历史文化变迁在文学中留下的轨迹以及这些文学经典生成后的运行轨迹。不仅是关于文学经典生存与传播的研究,它本身已经成为经典生成与传播的一部分。无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研究方法都富有创新,成果突出,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拓展了空间。”研讨会嘉宾之一,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胡可先教授表示。
 蝴蝶鱼
蝴蝶鱼陈众议:新世纪外国文学与研究点厾
编者按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陆续推出,敬请关注)“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之三:让蝴蝶飞一会儿 新世纪外国文学与研究点厾文 | 陈众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之一是市场趋于成熟和稳定,追风和迷信明显消退,这主要归功于“四个自信”和拿来的从容,次之是外国文学本身呈现出空前的多维发散状态,同某些政治经济单边主义适成反差。在文学这个天平上,“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譬如自然界的“蝴蝶效应”,任何事件、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学书写对象,任何写手也可能成为潜在和显在的作家。此在彼在,你写我、我写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业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常态。之二是无论国内、国外,出版和接受日趋理性;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这两者自然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之三是外国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反过来助推了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多样化趋势,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了解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当然,这也充分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下仅就学界广泛关注的“世界文学”问题略呈管见。首先,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客观存在。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舞和口传文学;从共时性角度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皆有文学。因此。世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和丰富多彩的呈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学》,就像《文艺报》有一个“世界文坛”版面。前者最早由鲁迅和茅盾创刊,是为《译文》;上世纪50年代末改称《世界文学》,而且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其天平甚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倾斜。《译文》(《世界文学》前身)创刊号 其次,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既是古来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也是现实主义者无如之何的选择。19世纪初,歌德萌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时代”的预想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而是出于对《玉娇梨》《好逑传》或《沙恭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举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早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这一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种“世界文学”。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再次,迄今为止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夏志清还是马悦然,大抵对我国“四大名著”评价不高,《红楼梦》也远未进入“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和凤毛麟角的蠹书虫,西方读者鲜有知道《红楼梦》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单就读者数量而言,《金瓶梅》和《聊斋志异》远超《红楼梦》。至于我国当代文学,则大抵还是西人文化猎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质。平心静气的理解尚须假以时日,一视同仁的欣赏却必得我国全面崛起。19世纪的英、法文学和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其所以风行,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圭臬,除了文学本身带有某些超前基因,背后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自不待言。如今,作为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文学,却也不再沉默,其生命力和艺术价值更是不容小觑。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已经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个全球化时代摆正了位置。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像对待美欧文学那样对待过巴基斯坦文学?因此,国内外达姆罗什们、卡萨诺瓦们的所谓“世界文学”果真是对世界文学一视同仁的接受与赞美吗?当然不是。但我们不应该顾此失彼,甚至戴上有色眼镜。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愿景、一个问题甚或一种审视文学的方法,恰恰是在全球化时代被重新提出并得以广泛讨论的。各民族文学的共性也是的确存在于兹,从文学的起源到体裁的发生可见一斑。文学内部的诸多题材的、内容的、人物的、意象的、情愫的相似也是实实在在可视可感的。因此,姑且让这个带引号的“世界文学”问题暂时悬置吧!让蝴蝶飞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应如何。好在杂事倥偬、时光倏忽,我辈之后,还有来者;也好在世界一日千里,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后人很快就会得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近年来风气乃变,多数学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马首是瞻。学术史研究、伦理学研究、历史社会学蔚然成风。如此等等,并不排斥纷纷嚷嚷的主义、思潮,但基本视野却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资源”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下我仅举三个例子:先说学术史研究。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自然也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武器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且说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多少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自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之后。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显借鉴学术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再说伦理学研究。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同样起始于“维新变法”之后,尽管伦理学资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在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由于唯洋人、唯文本,在较长一个时期,伦理学这个常规武器彷佛被付之阙如,甚至被当作冬扇夏炉。近十余年来,在学者聂珍钊的带领下,我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早已蔚然成风。然后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它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这在学者王守仁和杨金才以及蒋承勇等引领或主编的现实主义再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印证,同时也在吴笛主编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无论是学术史研究、伦理学批评还是历史社会学,归根结底都立足于新时代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方法。它们虽然是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无不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适当地回到常识,同时兼及当代范式,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因此,上述常规武器重现“江湖”至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藉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社会历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三)适当阻断现代主义以来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当然,其他还有诸多可圈可点的新探索、新尝试,遗憾这里只能挂一漏万,无法面面俱到。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几大外国文学研究刊物几乎无不彰显了主体意识。由此催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和认同是:从小看外国动漫和从小读经典的结果一定不同。这好比童年的味蕾,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同时,二十年前的互联网巨头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文化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原动力。从布热津斯基的“奶嘴战略”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人们大抵看清了文化产品的厉害。林林总总、潮起潮落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也不再紧张到老死不相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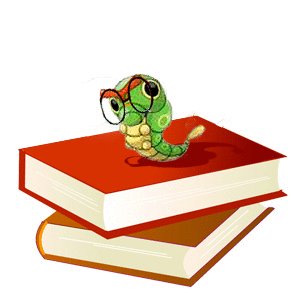 伊甸木
伊甸木“新中国70年外国文学研究”研讨会在长举行
华声在线6月3日讯(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蔡颂 黄林键)6月1日至2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双年会暨“新中国70年外国文学研究”研讨会在长沙举行。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知名专家欢聚一堂,共同研讨中国外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现状和未来。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洪新说,新时代外国文学工作者要为文学而文学,关注文学本身发展,透过文学探索人类未来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说,我们既要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又必须以我为主、从我出发、为我所用,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和“二为方针”,继承五四精神,参与到中国文学母体中,建立起三大体系和同心圆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80余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150余名知名专家参会。与会专家研究的领域囊括了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等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学。会议期间,专家们对新中国70年外国文学研究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对当下的现状进行总结与研讨,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与规划。
 两展其足
两展其足他是外国文学研究泰斗,却不怕被嘲笑,主动称读不懂德国顶尖诗歌
“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你那彩霞般的影儿/竟也同幻散了的彩霞一样!”这是一首题为《我是一条小河》的爱情诗,作者是诗人冯至。冯至在艺术上的天资是毋庸置疑的,他的诗作明净、清丽、韵味悠长,鲁迅曾经称赞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学识也非常渊博,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0年赴德国留学,1935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他凭着一部《杜甫传》,成为我国社科界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学部委员”;20世纪80年代,他又写出了学术力作《论歌德》,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界的泰斗。当然,成就冯至那种非同一般的才气的,绝不只是天资和学识。作家叶廷芳《缅先生》一文,其中提到冯至做事业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廷芳想主编一部论文集,邀请一些人撰写有关现代主义作家的论文,每篇三四万字。冯至在德国留学时受到奥地利作家里尔克的影响,叶廷芳觉得冯至是写里尔克最合适的人选。刚开始时,冯至不肯答应。叶廷芳动员他:“您是以‘学贯中西’著称的学者,国外的您抓了顶尖的诗人歌德,国内的您抓了顶尖的诗人杜甫,这是您学术战略上的横向平衡。而在德语文学领域,您抓的里尔克在德语诗人中也是顶尖的,这是纵向的协调。只是您关于里尔克写得还不够多,如果能通过这篇长文充实一下,这对后辈也是一种欣慰。”他这才答应了。但截稿时间到了,冯至未能交稿。叶廷芳于是给他宽限三个月,但他还是不能交稿。叶廷芳又往后推三个月,去找冯至要稿,冯至却抱歉地说:“我跟你说实话,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没有搞懂。”叶廷芳听了十分震惊,宽慰他:“现代派的作品看不懂是常事,但资料那么多,您参考一下别人的就可以了。”冯至马上反驳说:“诗歌主要靠理解,别人写的是别人的看法。不知为不知,人云亦云那是问心有愧的!”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泰斗和社科界的“院士”,冯至主动承认自己对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没有读懂,一点也不顾及此事传出去之后的“负面影响”,表现了他的务实精神。而对没有看懂的作品,他不予置评,免得误导他人,让自己良心不安,这又是可贵的自省态度。因为务实,冯至的才气有了踏实的基础;因为自省,他在诗歌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说,真正的才气永远不只是来源于一个人的客观优势,而是贵在自省。
 烽火台
烽火台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热点与趋势
2016—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目录索引库共收录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论文8970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论文392篇,转载率约为4%。全文转载的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3年里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广受关注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讨论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界的热点问题。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的两个发展阶段。法国学派开创了影响研究范式,主要从事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学派则主张平行研究,认为文学比较不必有事实影响,即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意。美国学派因不满于法国学派机械强调影响源头而提出平行研究,但平行研究的弊端是会出现很多硬比、乱比和随意比较,有学者甚至因此而将平行研究“妖魔化”。是否需要提出“中国学派”,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从逻辑上说,关注不同国家文学间的事实影响关系的法国学派和认为文学比较不必有事实影响的美国学派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没有必要提出新的学派。但是事实并非这么简单。近3年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转载的比较文学论文,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影响研究,也没有纯粹的平行研究,而是集中于以下方面。首先是探讨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如陈兵的《清教徒笛福笔下的中国》、赵学勇和王鑫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邹雅艳的《16世纪末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为例》、侯铁军的《中国的瓷器化——瓷器与18世纪英国的中国观》等。其次是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与误读。如徐勇的《外国文学选本编纂与“现代派”的接受及其合法性问题》、汪介之的《文学接受的不同文化模式——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为例》、谭渊的《“名哲”还是“诗伯”?——晚清学人视野中歌德形象的变迁》、张强的《意图的挪用:奥登在中国》等。再次是海外汉学研究,如季进的《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刘耘华的《欧美汉学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建构》等。而上述内容正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上述对形象学、译介学、接受学和海外汉学的研究,突显了中国比较文学不同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新特点。女性文学研究引人注目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热点。2016—2018年被研究最多的外国作家前20名依次为(括号中为研究论文篇数):莎士比亚(222)、托妮·莫里森(153)、福克纳(89)、伍尔夫(79)、爱丽丝·门罗(78)、艾米莉·勃朗特和夏洛蒂·勃朗特姐妹(76)、卡夫卡(72)、海明威(72)、托马斯·哈代(69)、简·奥斯汀(65)、D·H·劳伦斯(65)、石黑一雄(63)、多丽丝·莱辛(59)、纳博科夫(59)、赛珍珠(58)、伊恩·麦克尤恩(55)、菲茨杰拉德(54)、陀思妥耶夫斯基(52)、爱丽丝·沃克(52)。上述被中国学者研究最多的20位外国作家中,女性作家有9位,几乎占一半。而现今得到研究界广泛关注的托妮·莫里森、爱丽丝·沃克、纳博科夫、石黑一雄等都是少数族裔作家。但是,女性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在热闹的外表下也隐藏着危机,大量论文是对女性理论、后殖民理论或离散理论的简单套用。以女性文学研究为例,仅近3年外国文学领域就发表了女性文学研究论文近千篇。但是以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的论文数量来看,女性文学研究在近3年中的转载数量并不多,仅十几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文学研究存在缺乏新视角、大量研究类同等问题。空间批评与空间叙事研究持续升温从空间批评的角度研究外国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热点。20世纪末,西方理论界经历了一次空间转向。一般认为,这一理论转向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首开其端,之后有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菲利普·韦格纳的《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以及爱德华·苏贾的“空间三部曲”等众多理论家的研究,遂使空间理论蔚为大观。空间理论不满于传统理论对空间的忽视,深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往对“时间”的关注转移到“空间”上来。在空间理论的烛照之下,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环境、城市景观等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从国内的论文发表情况看,以“空间”为主题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在2000年之前极为少见,2000年之后空间理论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2010年后相关研究大量出现,近年呈持续增长的态势。2016—2018年复印资料目录索引库收录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中与空间研究相关的有293篇,其中19篇被全文转载,转载率比较高。所转载论文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作品呈现的城市空间的研究,如傅星寰的《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的代码系统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城市空间》等;其次是对作品描绘的地域景观或故事发生的空间环境的研究,如杨曼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空间批评》等;再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作品文本空间结构的研究,如包慧怡的《感官地图上的灵魂朝圣之旅——中古英语长诗〈珍珠〉的空间结构》等。“诺奖”作家研究异军突起近年来,“诺奖”作家备受外国文学研究界关注。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本上都会引起研究热潮。2013—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分别是:爱丽丝·门罗、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鲍勃·迪伦、石黑一雄。五位“诺奖”得主都经历了一个得奖前研究较少,或根本没有研究(如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得“诺奖”后研究论文猛增,再到研究论文数量回落的过程。只有石黑一雄稍有不同,中国学界在其得奖前即对他有较多的研究,但是在他获得“诺奖”后相关研究也有明显增长。除上述四个研究热点之外,生态文学研究、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美国“911文学”、老年书写、数字人文等研究也新见迭出,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原标题: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热点与趋势——以2016—201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为依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曹世瑞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红高粱
红高粱研究外国文学志在增益中国
我国的外国文学学科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其中有收获,也有偏颇,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时至今日,我们的“拿来”必须建立在自信和互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妄自菲薄或盲目自大。然而,在大量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为激活思辨能力、拓展文学视野、推动中国文学多维发展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淹没在林林总总的其他主义之中?有没有忘却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终究或者主要是为了繁荣、发展和强健中国文学这个母体?颠倒的次序:先外国后中国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本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先有外国文学学科,后有中国文学学科。这是因为我国文学古来无史。《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常常彼此割裂、不相杂厕。再则,在古代即或诗词歌赋稍有地位,戏剧和小说也是不登大雅的“倡优之术”,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援引孔子曰:“是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国人真正看重文学、视文学为学科则是在“百日维新”,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首先,“百日维新”“托洋改制”的“体”“用”(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思想的一个显证。1898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力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梁启超的小说群治论更是振聋发聩,令时人耳目一新。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1904)。其次是五四运动。如果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了。同时,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作为中国文学学科基础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由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之后又有了日本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等分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或文学史纲。而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文学史一直到1904年方始现身,它便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不仅不包括戏曲和小说,而且与其说它是文学史,不如说它是国学史。除了诗词歌赋,它还包括群经文体、诸史文体、诸子文体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修辞学等错位的关系:偏废拒斥与饥不择食且说中学和广义的西学(外学)不可偏废。这本应成为常识,但事实并非如此。综观70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第一,苏联模式影响了前3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从而使我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后40年又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来者不拒地拥抱西方,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范式,其中包括苏联东欧文学文化和自身的红色文学文化,而且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所在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借冯至先生的话说,我们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但否定中也有肯定”。第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必要的总结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中国文学学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派,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同心圆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大有裨益。具体说来,我们的问题是引进照搬多,分析甄别少;学科壁垒高,“拿来”门槛低。换言之,西方文学和学术思潮潮起潮落,迅速推搡我国相关主义和学术方法的顺化。从叙事学、符号学、心理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生态批评、后人道主义到后之后,以及身份、身体、创伤、流散、空间等等,心潮逐浪,衍生出海量的论文和专著。尽管近年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审美批评的复归明显改变了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格局,但有理有节、既坚定又包容地避免机械唯物主义,确立相对独立的审美维度,依然是我国人文知识分子亲历时代变迁、参与学科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也是时代精神的定海神针和价值平衡器。南朝有《述异记》,谓“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这个寓言犹如“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之说,逐渐成就了一个典故,后人遂以“烂柯”指时间倏忽,喻时移世易,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犹麻姑往复。于是,我们也便有了诗人刘禹锡“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这样的名句。而今,世界正以空前的加速度一日千里地飞跃、奔腾,蓦然回首,恍若隔世,须臾之间就换了人间。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敢懈怠,更不敢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夜郎自大、淡忘了道光年间以及之后的血的教训。忘却的传统:研究外国文学志在中国文学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彷佛是对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隔世回应。面对人类的无数危机和劫难,后者曾经不无感慨地叹惋:“也许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却了出发的初衷。”作为外国语言文学工作者,我们义不容辞,肩负着交流互鉴的责任。“人文化成”(《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诗性的滋润、诗意的化合,更需要大家的参与和奉献,否则我等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新时代的“烂柯人”。而我们的服务对象首先是中国文学这个母体。曾几何时,我们的前辈们,无论是“鲁郭茅”“巴老曹”还是冯至、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等,都是“双枪将”。他们一手是外国文学,另一手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在学科越分越细的背景下,他们还念念不忘“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钱杨伉俪甚至连“做游戏”都不忘拿中国文学起手。譬如他们用一个字概括一个作家,谓鲁迅的作品是“挤”出来的,郭沫若的作品是“唱”出来的,巴金的作品是“说”出来的,朱自清的作品是“做”出来的,如此等等。而这一个“挤”字了得,盖因它既是风格,也是内容:谓作品凝练,犹挤出一半;做人纯粹,则像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反躬自问,当下我国外国文学学者对中国文学母体的关心和参与明显不足。这固然有学科发展自身的问题,但不能否认的首先是我们自觉的关怀少了。我们在潜心关注外国文学,甚至追捧外国文学的同时,是否无意间成了“烂柯人”呢?面对海量的中国文学(年产纸质长篇小说就超过万部、网络长篇小说逾200万部),我们是否已经恍然若梦、无从下手?己犹不擅,何以善人?人类大同的怀想必须建立在民族复兴的基础上,否则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一定会把世界引向歧途、引向末日。而文学无疑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协调道器和内外左右的有效平衡器。原标题:研究外国文学志在增益中国——我辈学人有责任中外兼修,像前辈们那样成为“双枪将”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众议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梦不落
梦不落广外刘波教授优秀成果荣获首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
3月30日,首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颁奖典礼暨外国文学研究高端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广外刘波教授的优秀成果《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荣获首届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一等奖。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副校长孙有中以及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典礼。彭龙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北外“双一流”建设和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更为了弘扬北外老一辈学者的优秀治学传统,学校于2016年纪念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成立了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设立了“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彭龙指出,我们要弘扬王佐良先生的学术精神,并以获奖学者们为榜样,潜心研究,奋发进取,为我国外国文学和文化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孙有中宣布了首届“外国文学研究奖”的获奖作品。刘波教授的《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荣获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一等奖,陆建德教授主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上、下)、申丹教授和王邦维教授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六卷本)、陈明教授的《印度佛教神话:书写与流传》分别荣获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二等奖,王卓教授的《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美国族裔诗歌研究》、杨金才教授的《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分别荣获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提名奖。据悉,“王佐良外国文学研究奖”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秉持科学、公正、公开原则,面向全国,每两年评选一次。该奖项旨在纪念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王佐良先生,鼓励本领域学者潜心探索,推动我国外国文学界的学术大发展。(中国日报广东记者站)
 愿
愿新时代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宁海举办
央广网宁波10月24日消息(记者杜金明 通讯员徐铭怿 项麟寓)10月23日,新时代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叶水夫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在宁海举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全国各地高校和出版社的40余位专家、教授缅怀了叶水夫先生,并深入探讨了新时代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叶水夫,原名叶源朝,笔名水夫,宁波宁海力洋镇力洋村人,是我国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开创者之一,曾长期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领导工作。叶水夫的译作有皮萨列夫的《现实主义者》、柯涅楚克的《赴苏使命》、葛罗斯曼的《生命》、田德里亚科夫的《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等。他还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俄苏文学》等,为我国新时期苏联文学研究的起步提供了最基本最急需的资料。“译者是文明的驿马”,叶水夫数十年坚持致力于俄苏文学的介绍与研究,为世人堆积起一座座丰富的精神矿山。2018年,宁海为进一步增进中俄之间的交流,纪念叶水夫先生,投资120余万元,建成叶水夫纪念馆,馆内收藏了叶水夫和其夫人的手稿、翻译著作及物品等,并围绕叶水夫和他夫人的作品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和学术活动,成为了青少年教育和学习的第二课堂,水夫精神得以发扬光大。现场,专家、教授们结合自身体会,围绕叶水夫的生平事迹以及中国文学外译的传播与接受、新时代外国文学翻译、外国文学格局等,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国文学译介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叶水夫之子许佶表示,父亲毕生精力都花在了从事俄文翻译工作上,间接推动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发展,未来,他会继续整理父亲的手稿、物品和书籍,把曾经的记忆定格下来,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学走出去,展现文化自信。叶水夫的成就和事迹深深感动着国外的教授。“这是水夫先生从故乡走向世界的出发地。”常住中国的乌克兰教授布鲁克·伊戈尔对一生奉献在中俄翻译工作,为中俄两国的友好交往作出巨大贡献的叶水夫先生表示崇敬并表示,他非常喜欢拜读叶水夫翻译的作品,在宁海他近距离接触了养育水夫先生的这片山水,感受滋养了水夫先生心灵的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文化底蕴,未来他将带着朋友一起到宁海力洋感受中国文化。
 不形之形
不形之形社科专访|正确把握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实践向度
外国文学是高校文学院与外国语学院的骨干课程之一。在当今网络已广泛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如何更高效地进行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经典作家作品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如何对其加以鉴别认定?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围绕以上文学研究界较为关注的问题,笔者专访了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建军教授。 从单纯知识传授向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高照成:作为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您是否感到在当前网络普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时代背景下,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也面临着一种挑战?刘建军:在当前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深入到各个领域的新形势下,教育领域也面临巨大挑战。挑战之一是,来自世界范围内新知识、新信息的几何式增长。这样的现实,使得我们每个人,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甚至难以掌握某一学科领域内的新知识和新信息。挑战之二是,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知识和信息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进入了学习者的大脑。这也对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严酷的挑战,使得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模式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以上两大挑战,在教学领域,说到底,是对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原有关系的颠覆。就此而言,我认为,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需要改进:一个是更新观念,一个是更新方法。在知识爆炸和信息几何数增长的今天,以讲授知识为主要目标的课堂教学需要改进。因为在今天,无论用多长的时间来传授知识,都不会追赶上知识和信息的增长速度。随着教育手段的进步,我们虽然已经采用了很多现代的技术手段,如ppt、网络课程、公众号、慕课等形式,但目前采用的很多新的现代教育手段,仍然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换言之,很多现代技术使用的目的仍然是希望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方便地掌握各种知识。假如运用这些所谓新方法和新手段的目的,仍然还是以传授知识为主,那不过是穿新鞋走老路而已。我们要明确知道,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从单纯的知识传输向通过知识讲授从而向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能力方向转变。这是一种教学观念的巨大转换。以问题意识为先,以培养学生和教师提出问题的能力为先,才能应对当前信息时代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高照成:外国文学含量非常巨大,但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授很多国家、很多作家也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内目前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和教材选用,一般涉及的只是欧洲(含苏俄)和美国的作家作品。对此您如何看待?又有哪些改进建议?刘建军:这个问题与你上面提出的问题联系紧密。外国文学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和民族从古到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数量十分庞大。而高校的课时又非常有限。那么,长期以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靠减少作家和作品的讲授数量来应对。这其实是个最无奈的办法。如前所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改革教学观念入手。首先要明确,让高校学生掌握外国文学知识,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知道或掌握过去不知道或不了解的东西,诚然是目的之一。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知识性的问题,一定要在课堂上讲授吗?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乃至博生研究生,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学积累和文化知识积累,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著作来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在课堂上讲授呢?我认为,作为大学课堂上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也就是说,要把教学的重点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向度转换。这里,我要特别指出,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该是在教学中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过去说到课程设置目的时,总是强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认为,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应得到更优先地强调。因为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换言之,学习外国文学的学生只有能够依据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提出有效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做到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外国文学教学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时,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步骤。第一,对本科生而言,必须注重和强调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并引导学生在文本的阅读中提出问题。比如某个细节或场景的价值,某个人物描写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深层问题,等等。这样,既符合大学生要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的实际需要,同样也对这些刚进入外国文学之门的大学生,有具体的问题对象可以把握,从而教师能够对其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的初步训练。第二,对硕士研究生而言,他们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主要应该集中在学科领域,应该重点培养他们提出外国文学学科领域问题的能力。比如,有些文学史的观点是否合适,有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否需要重估,有些作品的理解是否得当以及是否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解,等等。这样,既符合硕士研究生专业培养的要求,也为他们在阅读的基础上为进入专业系统学习拓宽眼界,走向深入。第三,到了博生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时,应该在前两个提出问题能力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结合专业知识去提出和思考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相关方面的问题。这样,在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中,以培养提出问题为核心,分阶段地不断拓展和深化其提出问题的能力,就会得到更好地培养效果。也可以说,一个学生只有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才可以去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问题都提不出来,所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一句空话。从上述的前提出发,我以为,我们对教材中和课堂上选取哪些作品,讲授哪些作品,应该依据的是如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原则,而不是根据主观上认为的知识或文学现象所谓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原则。因为在学生的学习阶段,知识的重要性与否并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通过这些知识去培养训练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为此,我理想中的外国文学史,应该是按照不同时代提出了哪些问题和当时急需解决哪些问题所编撰而成的文学史,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文学史,而不是那种单一的按历史年代顺序讲述纯知识的文学史。在课程讲授上,应该围绕一些大的时代问题和时代精神需要来重新构建课堂讲述。这样,围绕着某些重要问题去讲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就不必纠缠于哪一个知识点没讲到,哪个作家或作品没有讲到了。因为学生只要明白了此时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会据此来举一反三地来理解其他作家的作品。还需指出的是,现在之所以欧美文学和俄苏文学在教材和教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本质上是研究现状和思维局限所决定的。现状是我国欧美、俄苏文学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成果数量也较多,研究的也比较深入。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思维上的局限:就是翻遍现有的外国文学史,就会发现,现有的外国文学教材编写和课堂讲述,几乎已被分析西方文学的模式框定住了,并且把西方文学的研究书写模式和讲授方法照搬到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上来了。例如对东方文学的分期,缺少东方特色;对东方作家作品的讲授,仍然采用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大多数外国文学通史类教材中,东方文学的介绍完全是按照我们对西方文学研究和讲授的模式来进行的,致使东方文学不过成了西方文学价值导向和西方文学评判模式的一个例证而已。倘若从问题意识出发,即从不同时期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解决的问题出发,就完全可以寻找出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学解决各自问题的不同审美路径和不同文化类型的发展特征。倘若能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方文学之间在课时上的平衡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经典外国文学作品与人生智慧高照成:我注意到,作为长期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您对西方国家的经典作家非常关注。请列举几个您尤为喜爱的作家及其最重要的作品,并谈谈原因。刘建军:我喜欢的西方文学作家很多,也比较关注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品,首推德国作家歌德以及他的作品《浮士德》。因为这部作品不仅体现出主人公积极进取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强大的象征精神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这一切又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例如歌德在古老的中世纪故事中,通过创造的《天上序幕》一场,就彻底改变了一个中世纪德国民间故事的面目,艺术地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象图景。这一场主要描绘的是发生在天庭里天帝与魔鬼靡非斯特之间的赌赛。即作品伊始,歌德就告诉读者,在浩瀚的宇宙中,天帝(“至善”)是“第一”和“最高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本原之一。同样,在这场序幕中,作家也交代了天帝的对立面魔鬼靡非斯特“至恶”的内涵特征。由于他所代表的“至恶”与天帝所代表的“至善”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与“至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这样,中世纪神学观念中的天使与魔鬼之间的矛盾斗争,被歌德置换成了“至善与至恶”的斗争。《天上序幕》中出现的第三个人物是浮士德。他是天帝与魔鬼用来赌赛的人物,是至善与至恶之争的对象。天帝认为,虽然“人在努力中,总有错妄”,但无论如何,“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并不会迷失正途”。而靡非斯特却断言,人总是贪图小利,无所成就。那么,情况究竟会怎样,浮士德作为人类代表的出现,将通过自己的一生追求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正是作品中的三个形象的相互关系,不仅构成了《浮士德》全剧最基本的结构方式,而且也使善恶斗争作用于人,而人不断克服恶向善飞升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形象化了。我们知道,17—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在借用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歌德正是艺术地把中世纪神学的“上帝”本原变成了“善”是本原,把中世纪神学体系中的上帝与恶魔之间的矛盾斗争置换成了至善和至恶之间的斗争,从而完成了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反映。歌德的《浮士德》其实就是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艺术化反映,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艺术写照。悟透了《浮士德》,其实也就知道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除了强烈的象征性之外,《浮士德》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例如,“浮士德精神”体现出一种看待追求进取的辩证精神。作家通过戏剧情节的安排,在深刻地展示追求进取精神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所带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了与这种追求精神和进取行动相伴而生的各种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的。所谓的“浮士德精神”也不例外。例如今天进行的现代化建设,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民追求进取的伟大壮举,它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人们生活的极大提高。但这种伟大的追求和探索也同样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问题和新的弊端,如自然环境的破坏、道德感的淡漠、诚信的缺失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追求相伴而生的东西,即是人们所说的“现代化代价”。这和浮士德的追求进取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深谙辩证法思想的伟大作家,歌德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类的每一次伟大的进步,都是和新的问题出现密切相关的。善恶相依,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在“浮士德精神”上的艺术体现。此外,我也喜爱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其实,老人桑提亚哥打鱼的故事平淡无奇,但其中包含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无比丰富。这既可以解读出老人在无奈的现实困境中超迈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也可以从“老人八十四天打不到鱼”和作品结尾处“一个女人在海滩上行走”等情节,解读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极度隔膜的困境。再如,卡夫卡和他的《城堡》也是我喜欢的作品之一。这是因为“城堡”的意象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过自己的“城堡”——即渴望得到却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不管你做过多少努力和挣扎。我之所以喜欢这样的作品,因为在这些作品的故事背后深藏着深刻的哲理和生活的智慧。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在2017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经典中的人生智慧》一书中,曾对此做过较为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经典文学作品的三种品格高照成: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最初接触的一般是自己国家的文学,请您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这三十几年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刘建军: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对此没有发言权。至于做总体性的评价,更不具备这个资格。但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学,所以我愿谈一点关于我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理解。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是经典,自身必须具备三种品格,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必须要有引人入胜的细节和经典性的场景。文学作品本质上是生活的艺术性反映。人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当一个读者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最先让其记住并长久不忘的,常常是一些经典型的细节或经典的场景。这些细节不仅让人总是随口道出,随时使用,而且还能够经得住反复咀嚼,回味无穷。更重要的是很多细节和场景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语言,如我们说到“替罪羊”,就来自《圣经·旧约》中的经典细节。再如人们形容某个人耽于幻想,不切实际,常常脱口而出“真是个堂吉诃德”或“又在大战风车了”。由此可见,经典的细节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作家人生智慧和艺术智慧最集中的体现。除了叙事作品中的细节和典型化场景之外,一首诗歌中的名句,一出戏剧中的“戏眼”,也是如此。这里我要对一个误解进行澄清。恩格斯在给哈卡奈斯的信中曾有一段名言。他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们很多人在理解这句话时,都认为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高于细节的真实。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恩格斯强调的恰恰是细节真实的重要性大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换言之,没有细节的真实,就不会有典型的环境与人物。更进一步说,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是通过典型细节和经典型场景表现出来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二是,一部好的作品必须包括丰富的时代性尤其是地域性知识。也就是说,文学的经典文本必须要具有知识的丰富性。《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乃至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荒原》《尤利西斯》《百年孤独》,以及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乃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作品,它们都是当时人类各种知识,尤其是特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知识的“百科全书”。以巴尔扎克为例,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就说过,他从其作品中所学到的关于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社会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政治斗争知识等比一切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统计学家告诉他的全部东西都要多。至于《红楼梦》其中所包含的时代性、地方性知识,如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的政治结构、家族状况、阶层构成、人际关系乃至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绘画技法等,更可称为一个集封建社会丰富知识百科全书。甚至一首诗歌,只要称为经典,也能在短短的几行诗句中,包含着时代性的知识,例如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艾略特的《荒原》就是经典范例。现在一些文学作品只有故事,只有自己的个人琐细的体验和肤浅的生活感受,却缺少时代性、地方性的知识内蕴,因此其价值是大打折扣的。三是,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邃的哲理性。文学经典文本一般说来都是指向哲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具体道理的传递。从中外文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不是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类著作,它不以讲述某种道理和宣传某种观念见长,而是以形象和情感来表现某种哲理。可以说,一个以讲道理见长的作家,或者一个作家试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讲述某个具体的道理,哪怕是最深刻的道理,那也是创作不出经典作品的。因为任何道理都是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特定性的,从来没有哪个具体的道理,尤其是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道理,可以适应一切时代和一切人。一个只知道讲某一个具体道理的作家,阐释的丰富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同样,若一个文本体现出了某种哲理,就使它具有了多元阐释的可能,即具备了阐释的无限性。我说这些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我所认定好的作品的标准,若读者认为我说的标准有道理,那就请读者们据此来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和不足吧。未来外国文学史的教材编写高照成:未来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应该如何编写?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刘建军:如何编写一本外国文学史教材,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我先说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当说到编写文学史的时候,要首先想到有两种文学史,一个是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文学史,类似于学术著作、参考书或工具书,另一种是为教学使用的文学史教材。现在出版的很多外国文学史著作都是二者不分的。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才可以说未来的外国文学史该如何编写。就前者而言,应该体现出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的探索性。就学生使用的外国文学教科书而言,以下几方面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教学型的外国文学史编写,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学史,中心线索应该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在面临不同时代主要问题时文学作家们的精神发展历程,是不同时期的文学对所面临问题的独特美学感悟和艺术性回答,以便为学生能认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特点服务。至于具体内容,可以根据问题的需要与否进行统筹取舍。其次,未来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必须是富有启发性的文学史,而不是灌输性的文学史。启发性文学史,并非不顾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在文学现象和文本真实的基础上,不仅要告诉学生“是什么”,更是要让学生学会“为什么”。最后,新的文学史必须是以文本和史料为主要内容的外国文学史,而不是编写者所认知的文学史。也就是说,新的外国文学教材的编撰,应该把最重要的史料和文本作为编写内容的重点,而不是把编者自己的思辨过程和看法让学生去接受。我们现在的很多外国文学史,由于缺少文本的进入和材料的出现,只是讲一些编写者的认识和体会,这其实是剥夺了学习者乃至讲授者的学习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我认为这也是当今我国的外国文学教材需要注意的领域之一。当前的普遍现状是,讲西方文论的人很少涉及外国的文学现象与作品,而讲文学史的人很少涉及文论。因此,必须要做好二者的结合。其实这二者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来看,我讲西方文论,总是先从作品入手,然后引入理论并说明理论。我认为,理论是通过文本表现出来的。而我讲文学史的时候,由于从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出发,所以文论思想也就能在解读文学现象和文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灌注到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讲述之中了。这样,学生学起来就不再是两层皮,而是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我始终认为,教师讲文论、学生学文论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若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学再多的理论也是没用的。这里有一个关键之处要注意:这就是二者结合一定在在问题意识中进行。我前面说过,外国文学的讲授要有问题意识。我们若以问题为导向,那么理论和文本二者就会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些人之所以愿意套用理论,就是因为没有问题意识,或者说问题意识缺乏。例如,在讲述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时候,如果你要解决的是“莎剧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究竟是个什么形象”这个问题的时候,假如你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你就可以采用文艺社会学理论;假若你从心理学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就可以采用现代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理论去解决这个问题。若说理论与作品二者孰轻孰重,还是那句话,两者并重,辩证统一。高照成:非常感谢您谈了这么多富有创见的学理逻辑和具体建议!最后请举出几位您认为值得推荐阅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并谈谈推荐理由吧。刘建军:又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不是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可能很难给你满意的回答。若非要指出几个作家,我首推鲁迅。尤其是鲁迅的《阿Q正传》。我喜欢鲁迅,是因为他的小说对普通中国人灵魂的以及他对这些普通人历史命运的关怀。同时,他的小说《阿Q正传》也具有深刻的常读常新的哲理魅力和艺术魅力。以阿Q的名字为例,可以看出,Q首先是个○,是个圆。这个圆包含着三重含义:第一,这个圆是阿Q一生“不觉悟—想觉悟—最终没有觉悟”的循环命运的写照;二是这个圆也是对辛亥革命从不革命到革命,再到失败这一循环过程的写照;第三,这个圆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循环命运的象征。所以,鲁迅才借阿Q之口,说出了“孙子画圈才画得圆”的话。其实,《阿Q正传》中的这种原型意象,在鲁迅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如《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轨迹,《故乡》中的闰土的命运变化乃至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无不体现着这种圆的意象。鲁迅的小说就超越了一般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单一主题,成了一种超越故事本身的对中国人精神困境的哲理反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鲁迅先生为什么不把阿Q直接称为阿○呢?其实,这显示出了鲁迅的敏锐,因为阿Q毕竟已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民了,他毕竟要“革命”了。但是由于当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没有出现,所以他也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革命者,因此,他的“革命”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样,圆上的这个小尾巴就显示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贫苦农民的新特征。第二个我推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是周立波和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这部作品的价值,必须要从建国后“革命与建设”两大任务叠加的特定的历史需要谈起。我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结项成果中曾说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革命和建设两大任务的叠加时期,也是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农民与千百年来旧思想、旧观念决裂的主要历史阶段。由于这部小说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和广大农民的独特精神风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所以具有史诗的性质。在艺术上,作家不论是人物描写,还是矛盾设置与场景刻画,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有着特定时期的历史气息,都有着由衷地流诸笔端的对社会主义的赞美之情,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作者简介:刘建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高教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高照成,文学博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第二博士学位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高照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大搜捕
大搜捕秦川、王子成:“日本红学”由热到冷原因探析
经典《红楼梦》在日本颇受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那已经是上世纪的事情了。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经典名著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研究,依然呈现盛况,但对于《红楼梦》的传播和研究已是今非昔比了。日本图画刊行会1916年刊本《红楼梦图咏》相对于明清“四大名著”的小说甚或其它古代小说戏曲来看,在日本的《红楼梦》阅读和研究正呈冷寂状态。至于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就日本“红学”研究现状,进行一些客观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一、日本红学研究现状概述《红楼梦》自1793年被传到日本,到日本学者森槐南于1892年的翻译和发表在《早稻田文学》上的《红楼梦论评》一文,再到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上世纪末,《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研究实况,可谓一路走高,形成了读红热和研红热。所谓读红热,如《红楼梦》这部小说一传到日本,就被读者抢购一空,四方书店无以为售①,这是读红热的体现。至于研红热,也就是笔者所谓的“日本红学”,它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始,直到上世纪末,几达八十年的历程,可谓盛世空前。如百数十人的研究队伍,数百篇的研究论文以及为数不少的高质量红学专著,足以证明日本红学的盛况。这“双热”现象,不仅使得《红楼梦》在日本曾走向了经典化,而且也促进了日本红学自身的经典化。至于经典《红楼梦》在日本的经典化以及日本红学自身的经典化现象,笔者已有专论另外发表,故此不赘。《日本红学史稿》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对于《红楼梦》的阅读和研究已是明显冷静了下来,几乎呈现冷寂状态。从《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学》、《集刊 东洋学》、《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以及多家大学学术杂志如东京大学的《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神奈川大学的《人文研究》,《庆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埼玉大学纪要(教养学部)》以及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論集》所登载或转载的学术成果来看,其冷寂状态十分明显。下面将分列上述10家期刊自2015至2018年(少数刊物的时间范围略大一些)所登载或转载的论文,及其“学术动态”栏目介绍的学术信息进行分析。(一)《日本中国学会报》该刊一年一集,2015年为第67集至2018第70集,四集共刊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文17篇,分别为2015年2篇,2016年4篇,2017年7篇,2018年4篇,但没有一篇属“红学”论文。该报所设“汇报”专栏,是对头一年学术专著包括译著情况的介绍。而该专栏介绍的四年共计24部,其中2部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专著信息,如2015年“汇报”报道了2014年井波陵一新译《红楼梦》(第七册由岩波书店发行)的信息,而2016年“汇报”又介绍了2015年由广濑玲子翻译的《石の物語:中国の石伝説と<紅楼夢><水滸伝><西遊記>を読む》的信息,而该书由法政大学出版局刊行,其原著系杜克大学王瑾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因英文名称太长,故略)。井波陵一译本《红楼梦》其它论文论著译著皆涉及《太平广记》《夷坚志》《三国志演义》《三国志平话》《西游记》《西游补》《水浒传》《封神演义》《杨家将演义》《扬州梦》《梧桐雨》《西厢记》“元杂剧”以及其它小说戏曲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二)《东方学》该刊系由日本东方学会主办,为半年刊,一年两集,分别为1月和7月出刊。2015年两集仅刊登古代文学的论文1篇,即7月第130集里的竹村则行《弘治本<西厢記>に付載する明·張楷<蒲東崔張珠玉詩集>について》(p53-67)。另有个“学术动态”栏目,提供了2014年静永健在“第五十九回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第六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上,所做的题为“洪邁《夷堅志》の世界”主题报告的信息。2016年1月份即第131辑有中国古代文学的论文2篇,但内容皆与《红楼梦》无关。而“学术动态”栏目所介绍的是有关《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方面的信息,而7月份即第132辑没有刊登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却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信息,如田仲一成为已故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撰写的纪念文章《“先学を語る―伊藤漱平先生―”》,此外杂志还对日本红学大家伊藤漱平的生平著述进行了整理汇总推介,如专著或主编书籍10部,翻译著作12部,论文61篇,基本上是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的成果,而“红学”方面的占主流地位。《日本红学研究最新成果简介》2017年1月没有相关研究论文,而“学术动态”也与《红楼梦》无关;7月即第134辑有一篇“红学”论文,如船越达志《<紅樓夢>后四十囘における<五兒“復活”>と太虛幻境》(p80-110)。“学术动态”则无任何相关信息。2018年1月份亦无相关论文,而6条“学术动态”皆与《红楼梦》无关。而7月有两篇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和众多学术信息,但都与“红学”无关。(三)《集刊 东洋学》该刊系由日本中国文史研究会主办,也属半年刊,一年两期。2015至2016年自112号至115号4集各刊论文1篇,皆与“红学”无关.而“学术动态”提供的信息也与红学无关。2017年116-117号皆无古代文学方面的相关内容。2018年118号和119号各收论文1篇,与“红学”无关,而学术动态“汇报”栏目的信息亦与“红学”无关。(四)《中国研究》该刊系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主办,属该校《日吉纪要》里的组成部分,系年刊,即一年一期。该刊创刊于2008年,第1期为创刊号,发表了渡边良惠《森槐南の中国小説史研究について—唐代以前を中心に》(p33-68)。森槐南书法自2009-2011年即第2-4期无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而2012年第5期发表了渡边良惠《顧況<戴氏広異記序>について》(p65-112)。2013-2016年即第6至第9期皆无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2017年第10期发表了渡边良惠《明治期の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小説史研究について—文学史における記述を中心に》(p109-140),2018年第11期亦无相关内容。2019年第12期发表了渡边良惠《家族の元へ戻る鬼の話—<広異記><薛万石>と<李覇>を中心に》(p1-24)。可见,该刊所刊论文皆与“红学”无关。(五)《埼玉大学纪要(教养学部)》该刊系由埼玉大学主办,亦系半年刊,即一年一卷两号,发表少量文学类论文,但自2013年第48卷第2号至2019年第54卷第2号,内容皆与“红学”无关。(六)《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该刊显然系由东京大学主办,为年刊,即一年一期。自2015年第18号至2018年第21号,发表少量有关古典文学的论文,但都与“红学”无关。(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该刊显系东京大学主办,一年一册或二册不定,但大多是一年一册。自2015年第167册至2019年第175册,共发表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5篇,皆与“红学”无关。《小说的读法:铃木阳一文论集》(八)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该刊显系神奈川大学主办,半年刊,即一年二期。自2015年NO.186号至2019年197号共发表相关论文3篇,如2015年NO.186号有王子成《<三言>と江西省の地域文化——水神信仰に注目して》(p111-142);2017年NO.190日高昭二教授退职記念号上有铃木阳一《<白蛇伝>の解読補遺(一)》(p95-116);2018年NO.194马兴国先生追悼号上有铃木阳一《<白蛇伝>の解読補遺(二)》(p1-20)等,皆与“红学”无关。(九)《中国古典小説研究》该刊系中国古典小説研究会编的年刊,即一年一期,但2015年停刊1年。自2014年第18号至2018年第21号,共发表相关论文包括学术会议论文27篇,仅2篇“红学”论文,即2016年第19号上所刊宋丹《<紅楼夢>日本伝来時期の再検証―村上文書「差出帳」の「寅弐番船南京」について―》,和2018年第21号上所刊涩井君也《清代の<紅楼夢>続書における「姻縁」の枠組み——<紅楼夢>戯曲との比較から―》。u2028(十)《中国文学論集》该刊系由九州大学主编,系年刊,即一年一期。除论文外,也有“学术动态”和“学术著作”的信息栏目。自2015年第44号至2018年第47号,发表少量相关论文,但皆与“红学”无关,仅2017年第46号“会员著书介绍”栏目里推介了合山究著、陈翀译《〈紅樓夢〉新解——一部“性別認同障礙者”的烏托邦小說》的书评信息,而该译著系台北联经出版社于2017年4月出版的图书。《红楼梦新解——一部性别认同障碍者的乌托邦小说》中译本由此可见,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在这十家期刊或报刊所刊载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说日本“红学”在新世纪以来处于冷寂状态,并非臆测。二、新世纪以来,日本“红学”处于冷寂状态的原因探析由上可知,新世纪以来,《红楼梦》在日本的接受及其研究,相对于中国其它几部小说名著乃至其它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情况,显得冷静多了。究其主要原因,大概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接受的冷寂在于观念的转变与兴趣的转移新世界以来,日本读者对于我国经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喜爱程度,相比于上世纪初的情况来看,热情明显减退,远不如对中国其它小说戏曲的兴致浓厚。虽然我们无法统计到日本今人阅读《红楼梦》的具体情况,但我们可以通过日本学者的研究来反观其阅读信息。本文以日本学界刊发的相关研究论文为例,分析其阅读的兴趣和范围。如下文将及的十家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非常少,而大多数是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杨家将演义》“三言二拍”《太平广记》《夷坚志》《西厢记》《梧桐雨》等一大批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成果。日本汲古书院影印程乙本《红楼梦》这已充分说明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的《红楼梦》在当代日本,确实不及上世纪那样受欢迎,尽管在上世纪也存在着阶段性的冷热之分②。那么作为曾经受到世界瞩目、日本读者喜爱的《红楼梦》,如今却受到日本读者的如此冷落,也是有其原因的。1、紫式部《源氏物语》与其爱情观民族化的冲击以爱情为内容的小说,在日本已有其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流播。所谓日本民族的特点之一,是以欲望的达成为其目的的心理满足。《源氏物语》是日本作家紫式部创作的经典名著,其爱情观带有明显的日本民族特征,而作为日本的读者自然更加习惯其本民族风格特征的文学作品。虽然《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二书中皆具对爱情的理想追求,皆为爱情悲剧,皆属“梦幻”;但《红楼梦》中的“梦幻爱情‘在现实中体现为梦幻的破灭,而《源氏物语》中的”梦幻爱情“则体现为“梦幻”的实现(即以“替身”来满足愿望)。因此,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比起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来,更能满足人的心理欲求。所以说,《红楼梦》如今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是紫式部《源氏物语》与爱情观民族化的冲击所致。而当代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戏曲《西厢记》《梧桐雨》产生浓厚兴趣并致力研究,正是因为二剧皆能满足其欲望的达成。《源氏物语》如《西厢记》“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主题,以及莺莺张生爱情的喜剧结局,符合日本读者的心理欲求和阅读满足;即使像颇带悲剧色彩的《梧桐雨》同样受到日本今人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因为该剧通过梦幻实现了主人公的心理愿望。2、日益扩大的日中交流与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在日本传播所产生的影响中日交流历史悠久,中国文化包括古典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日益广泛。日本读者或学者接触到更多的中国其他经典名著后,其原来的阅读兴趣自然转移到更多更为广阔的领域,诸如对战争描写的《三国志演义》《杨家将演义》之类的小说、对神魔描写的《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的小说、对神怪描写的《太平广记》《夷坚志》之类小说、对社会世情做现实描写的《金瓶梅》“三言二拍”之类的小说,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因而《红楼梦》不再热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二)研究的冷寂在于“日本红学”已达顶峰,超越顶峰既无可能亦无必要“日本红学”在上世纪已达顶峰,《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经典化以及“日本红学”的经典化已经完成,再要超越顶峰的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限于篇幅,仅以《东方学》平成二十八年(2016年)七月第132辑,对上世纪“日本红学大家”伊藤漱平生平著述整理的情况为例进行分析。从其著述、主编的情况来看,上世纪“日本红学”已经达到一个高峰,而且从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论著来看,日本红学研究完全属于少数学者的个人兴趣。日本学者因为日本人的“匠人精神”,往往一个领域牛角尖钻到底,这个领域某个学者占据了,研究出了很多成果,别人也自觉地不会去和他争,那是他的地盘,有话语权。伊藤漱平译本《红楼梦》可见,伊藤漱平的个人著述对日本红学研究具有总结性意义。如伊藤漱平主编的《中国の八大小説》(于1965年6月由平凡社出版)的,其中五部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内容。伊藤漱平于2005年至2008年出版的《红楼梦编》(上中下),皆由汲古书院出版,分别是《紅楼夢編(上)》于2005年10月出版,《紅楼夢編(中)》于2008年6月出版,《紅楼夢編(下)》于2008年9月出版,这对日本“红学”来说,显系总结性的研究成果。从其翻译的角度看,《红楼梦》研究的平台也已完备。如日本平凡社分别于1958年12月、1959年10月、1960年10月在《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二四、二五、二六里出版了伊藤漱平翻译的《红楼梦》(上中下),又分别于1969年1月、1969年7月、1970年2月在《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四四、四五、四六里出版了伊藤漱平翻译的《红楼梦》(上中下),又由平凡社于1996年9月至1997年12月陆续出版的伊藤漱平译著《紅楼夢(全十二巻)》。另外,还有1963年8月由平凡社出版的伊藤漱平的译著《奇書系列<紅楼夢>(上中下)》、1963年7月由平凡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一)》里所收伊藤漱平翻译的徐怀中的《我們播種愛情》以及1963年8月由平凡社于《中国現代文学選集(一)》里所收《清末五四前夜集》之《王国維<紅楼夢評論>》等,再加上由汲古书院自2011年刊行伊藤漱平著作集中所收录的《红楼梦》旧译,伊藤漱平旧藏的程甲本、程乙本影印本,还有井波陵一新译《红楼梦》第七册(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以及2017年4月由台北聯經出版社出版的合山究著、陈翀译《〈紅樓夢〉新解》等,至此《红楼梦》日译本已全部出版完毕。可见,日本《红楼梦》研究的平台构建已基本完备。《阐释的演化: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研究》,吴珺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3月版。从其对《红楼梦》的相关研究来看,可谓深入细致,面面俱到,颇具总结性特征。如伊藤漱平61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中,就有45篇“红学”论文,内容涉及版本研究、作者研究、思想内容以及艺术成就研究、文学形象研究、中日“红学”研究、中国红学家及其相关研究以及相关的考证等。另外还有大量“红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现分列于下:有关《红楼梦》的介绍和传播的成果如《紅楼夢》(勁草書房《中国の名著》,1961年10月),《世界文学における<紅楼夢>》(岩波書店《文学》五五巻三号,1987年3月)等。有关作者研究的成果如《曹沾と高鶚に関する試論》(《北海道大学外国語外国文学研究》二号,1954年10月),《李漁と曹沾——その作品に表はれたる一面(上)――》(《島根大学論集》六号,1956年2月),《李漁と曹沾——その作品に表はれたる一面(下)――》(《島根大学論集》七号,1957年3月)以及《晩年の曹沾の(佚著)について——<廃芸斎集稿>等の真贗をめぐる覚書――》(講談社《加賀博士退官記念中国文史哲学論集》,1979年3月)等;《曲亭馬琴と曹雪芹と——和漢の二大小説家を対比して論ず――》(二松学舎大学大学院《二松》八集,1994年3月)有关版本研究的成果如《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一)》(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二巻九号,1961年10月),《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二)》(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三巻八号,1962年9月),《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三)》(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四巻七号,1963年8月),《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四)》(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五巻六号,1964年7月),以及《脂硯齋脂と脂硯齋評本に関する覚書(五)》(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一七巻四号,1966年5月)等。《红楼梦》颂枝茂夫日文译本有关中国“红学”带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如《王国維の<紅楼夢評論>と雑誌『教育世界』について(上)》(《清末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一号,1962年9月),《王国維の<紅楼夢評論>と雑誌<教育世界>について(中)》(《清末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二号,1962年10月),《王国維の<紅楼夢評論>と雑誌『教育世界』について(下)》(《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四号,1963年10月),《胡適と古典――旧小説、特に<紅楼夢>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た覚書(上)》(大修館書店《漢文教室》一二六号,1978年6月),《胡適と古典——旧小説、特に<紅楼夢>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た覚書(中)》(大修館書店《漢文教室》一二七号,1978年10月),《胡適と古典——旧小説、特に<紅楼夢>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た覚書(下)》(大修館書店《漢文教室》一二八号,1979年2月),以及《胡適と古典——旧小説、特に<紅楼夢>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た覚書(補)》(大修館書店《漢文教室》一二九号,1979年5月)和《王国維と兪平伯の一面(覚書)——「皇帝」との距離、その他――》(大安書店《近代の思想と文学》,1967年7月)等;《<世界文庫>覚書——鄭振鐸と魯迅――》(《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八号,1942年1月)有关日本“红学”带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如《日本における<紅楼夢>の流行(上)》(大安書店《大安》一一巻一号,1965年1月),《日本における<紅楼夢>の流行(中)》(大安書店《大安》一一巻三号,1965年3月),《日本における<紅楼夢>の流行(下)》(大安書店《大安》一一巻五号,1965年5月), 《日本における<紅楼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汲古書院《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1986年3月)《红楼梦杀人》有关考证方面带总结性的成果如《程偉元刊<新全部繡像紅楼夢>小考》(鳥居久靖先生華甲記念会《中国の言語と文学》,1973年3月),《程偉元刊<新全部繡像紅楼夢>小考補説》(《東方学》五十三輯,1977年1月),《程偉元刊<新全部繡像紅楼夢>小考 餘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五八号,1978年3月)等;《<紅楼夢>的甄(真)賈(假)の問題——二人寳玉の設定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学中哲文学会《中哲文学会報》四号,1979年6月),《<紅楼夢>的甄(真)賈(假)の問題——林黛玉と薛寳釵の設定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学中哲文学会《中哲文学会報》六号,1981年6月)等。《<紅楼夢>成立史臆説——七十回稿本存在の可能性をめぐって――》(《東方学》八三輯,1992年1月)有关内容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紅楼夢>首回、冒頭部分の筆者についての疑問》(《東京シナ学報》四号,1961年6月),《<紅楼夢>首回、冒頭部分の筆者についての疑問(続)》(《東京シナ学報》五号,1962年6月),以及《<紅楼夢>首回、冒頭部分の筆者についての疑問(続)訂補》(《東京シナ学報》一○号,1964年6月)等;有关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研究成果如《<紅楼夢>に見る女人像および女人観(序説)——金陵十二釵を中心として――》(汲古書院《中国文学の女性像》,1982年3月),《金陵十二釵と<紅楼夢>十二支曲》(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人文研究》一九卷一○号,1968年3月),《<紅楼夢>の脇役たち——王熙鳳の娘およびその他の諸人物に就いての覚書――》(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人文研究》二○卷一○号,1969年2月),以及《<紅楼夢>に於ける象徴としての芙蓉と蓮と——林黛玉、晴雯并び香菱の場合――》,(汲古書院《日本中国学会創立五十周年記念論文集》,1998年10月)等。日本1964年刊印《红楼梦展》有关带总结性的研究资料如《<紅楼夢>研究日本語文献資料目録(付索引)》(《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単刊)六,1964年12月),《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紅楼夢>版本研究書略解(上)》(極東書店《書報》六二号,1964年12月),《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紅楼夢>版本研究書略解(中)》(極東書店《書報》六三号,1965年3月),以及《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紅楼夢>版本研究書略解(下)》(極東書店《書報》六四号,1965年4月)等。其它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近世食文化管窺——<金瓶梅><紅楼夢>を材料として――》(《食と近世食文化管窺——日本中国法国》,1992年5月),《紅楼夢図画——改埼<紅楼夢図咏>を中心に――》(《二松学舎大学東洋学研究所集刊》二六集,1995年3月),《二十一世紀紅学展望(中国文)》(一九九七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1997年8月)等。可见,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已成为“日本红学”顶峰中的顶峰,系上个世纪带总结性的成果。作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达到如此境地,再要超越它实属不易。然而作为新时代的日本学者,转向去领略甚至挖掘中国古典文学宝藏中的其它珍宝,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在“红学”顶峰上去做无效的努力,于是在日本出现“红学”的冷寂状态也就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伊藤漱平译本《红楼梦》总之,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日本的接受传播以及“日本红学”已今非昔比,明显处于冷寂状态,已是无须回避的客观事实。形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当为:一是观念的转变和兴趣的转移;另一是以伊藤漱平为代表的“日本红学”已经达到顶峰的境地,要想超越其顶峰,既无可能亦无必要。注释:①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页。②孙玉明《日本〈红楼梦〉研究略史》,《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