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尾猫
八尾猫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2019届毕业生发表46篇SCI文章?
作为不同学校同一专业的医学生,也参加了一些科研工作。对于三年46篇SCI的事情,不想吹也不想黑,这样宣传只是在服从游戏规则罢了。认为这是灌水也没有错,但不能否认这一数量可以反映出这位同学的科研能力,起码是努力程度的事实。考虑到现行国内研究生毕业评价体系的导向,这一做法可以理解,我与他易地而处,可能也不会做的比他高尚。当然从科学价值来看,这些大量的低分文章大部分时候产生不了任何科学价值(其实对于分数稍高的期刊这一事实也没有太多的改变)。在这里我只想要解释一下一些事实。SCI杂志的文章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文章内容差异很大,周期也完全不一样。Original article:属于一般人常规意义上理解的“论文”,即用自己得到的实验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包括full-length和brief report(brief communication)两种,前者长度长更严谨,后者较短更注重新颖性。这类文章需要经过peer review,审稿周期较长,哪怕是低分杂志,从投稿到录用半年多是家常便饭。Review:也就是综述,是对某一主题的论文进行系统性检索并整理论文提供的证据后,撰写的对某一主题的研究进展或现状的描述性文章。同上,需要经过peer review。Meta-analysis/Systematic review:meta分析及系统性综述,针对一个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利用统计学方法将这些研究(以RCT为主)的结果放在一起,得出结论的文章。这类文章工作量小,只要有好的选点,从设计到成文,两周左右即可完成。需要经过peer review。Case report:病例报告,是对一个或数个典型或罕见病例进行描述。需要经过peer review,但录用周期较短。Case series:病例系列,对多个病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类似于original article中的回顾性研究,但对研究设计的要求较低,属于单臂研究。需要经过peer review。Comments/letters to the editor:评论性文章,是对于某篇文章提出自己的评论和意见,少数有原始数据,但大部分为单纯的意见。不需要经过peer review,虽然较高分(IF > 10)刊物会有比较高要求,但接受率总体较高,录用周期往往只有几天。到这里情况已经很明了了,占大部分的Comments, letters to the editor, meta-analyses工作量其实并不大,前二者严格来讲不能算是SCI论文,也不会计入期刊的IF,近年来各大院校也不再将低分的meta分析纳入毕业考评和职称评定。还有十几篇original article,也是大家质疑的焦点。通常的基础研究,不管分再低,从设计到实验再到写作投稿,三四个月总是要的。但也不是没有快速刷文章的办法,例如同一个回顾性队列把数据拆成几部分分开发文章等(仅举一例,毕竟还有很多人要恰饭的)。综上所述,三年,不造假,发46篇SCI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如何评价实在见仁见智,我在此不想做任何评价。很多时候,这种新闻出来,我们看到的都是学生,而不是背后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的那些东西。——————————分割线——————————感谢大家关注,看了一些其他回答之后我觉得还有两点事实我不得不补充:1.唯影响因子论的片面性:IF,即impact factor,是杂志三年以来该杂志每一篇original article和review平均被引用次数,例如Cancer Medicine这一期刊三年来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平均被引用了3.3次,其IF就是3.3,俗称该杂志为3.3分,或某人发了一篇文章在这个杂志上,就称他发了篇3.3分的文章。从这一俗称可以看出,IF是我们常用于评判一本期刊好坏的指标,然而唯IF论也是不可取的。期刊的IF有很多影响因素,例如杂志相关领域近年来是否够热,杂志每年发文量多少,自引率多少,杂志发文覆盖面大小,杂志发表综述的比例高低(综述通常被引量远高于original article)等等。因此即使在同一领域,IF也无法直接比较两本杂志质量的高低。而在不同领域,IF几乎完全无法说明问题。胸外科领域顶刊的IF也很低,即使讨论外科学大类,公认的外科学神刊Annals of surgery的影响因子也才9左右,与Oncotarget被移出SCI前最高的8相差无几(笑)。而肿瘤相关的杂志近年来影响因子暴涨,原本5.6分的超过10分比比皆是。2.科研成果的影响因素:一个教授、医生、学生能做出的科研成果受到大量因素影响,努力和能力只是其中两个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已。基础研究受限于经费,仪器以及运气。临床回顾性研究受限于数据的accessibility(很多医院和科室只有主任级的大佬才有权处置数据,因此在这样的单位中,一来普通医生和教授无法获取这些数据用于科研;二来各自为政数据分散导致无法形成大文章)。临床前瞻性研究一来动辄需要数年乃至十几年之功,二来门槛极高,单中心的往往需要院长级的领导牵头才便于组织协调各科室工作,解决(恰饭)矛盾;而多中心的则需要业内屈指可数的负有盛名的大佬来牵头才能避免引起authorship的争端(到了这个层次才可能谈得上发表于知乎er们认可的国际顶级刊物如BMJ PNAS Lancet和NEJM等上)。除了这些客观条件的影响外,评价体系也会影响科研人员们选择课题,很多时候会存在“我想认真做研究但是我还是学生还是先搞个短平快的课题满足毕业要求再说”“我想认真做研究但是我还是个小主治还是先搞个短平快的课题评职称再说”“我想认真做研究但是我只是个普通小博导学生还要毕业我还是想几个短平快的课题把他们打发走再说”等等的尴尬。而对于绝大部分研究者来说,这样的尴尬就是他们科研生涯从开始到结束的三个阶段。
 面包师
面包师中国首个癌症早筛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结果出炉,进展期腺瘤筛查实现国内临床检测性能重大突破
9月25日,诺辉健康在2020年CSCO学术年会上正式发布中国首个癌症早筛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Clear-C)的重要数据结果。CSCO学术年会是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举办的权威肿瘤学术盛会,聚焦肿瘤临床最前沿的创新和实践。“Clear-C”(Colorectal Cancer Early Screening in China)注册临床试验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作为牵头研究单位,联合江苏省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湖北省肿瘤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8家大型三甲医院共同开展,历时16个月,旨在研究结直肠癌早筛的创新技术对降低中国结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临床价值。此次试验于2018年9月正式启动,累计入组数据近6,000例,实际纳入统计分析数据4,758例,目前已向国家药监局正式完成全部临床数据的提交。“诺辉健康见证了中国癌症早期筛查居家检测领域的开创和发展,和中国百万战斗在一线的临床医生一样,我们深知严谨负责的态度和专业精准的技术是医疗产品研发与创新不可动摇的基础。”诺辉健康联合创始人兼CEO朱叶青表示,“‘Clear-C’是诺辉健康过去七年投入最大的临床试验,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国最重要的肿瘤学术论坛CSCO上发布,也期待和业内专家一起共同探讨降低中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精准筛查手段。”“Clear-C”临床研究的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国家十三五重大专项结直肠癌专病队列研究首席科学家丁克峰教授代表试验项目组公布了“Clear-C”的重要数据结果。“‘Clear-C’是中国首个癌症早筛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此次试验全面达到临床研究目标,对结直肠癌早期筛查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丁教授表示,“此次试验有三个特点。一是我国此前从未有过有关肠癌早筛的前瞻性注册临床试验,二是入组样本量大,三是试验结果优异。所有入组人群均要求在常卫清检测同时完成肠镜检查,对比肠镜检查和病理的金标准验证常卫清的筛查结果。此外,该大规模前瞻性试验设计,贴近筛查的实际应用场景,有利于早期筛查,达到预防肠癌发生的目的;有利于早期诊断,有利于提升肠癌早期治疗效果,临床意义明确,可以极大改进早期治疗效果,预防肠癌的发生。”丁克峰教授表示,我国的肠癌筛查目前主要依靠问卷、便潜血和肠镜等手段,高危人群只有40%愿意做肠镜,顺应性差。常卫清作为精筛手段,对肠癌的灵敏度高达95.5%,与问卷及便潜血的初筛相结合,可以有效地浓缩高危人群,显著提升肠镜检出率。“Clear-C”试验数据结果表明,常卫清对进展期腺瘤的检测灵敏度为63.5%。“Clear-C”的研究者之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癌多学科协作组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大肠癌诊治中心主任蔡三军教授表示,对进展期腺瘤及早发现并干预,能够在临床上达到最理想的肠癌防治效果,也是通过筛查降低肠癌发病率的关键。“Clear-C”的试验中,常卫清对结直肠癌的阴性预测值达到了99.6%。阴性预测值(NPV)指待评价诊断方法判断为健康的被测者中,真正未患病的比例,也是国际广泛认可用以衡量早筛产品的权威指标之一。“Clear-C”研究者之一,江苏省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顾艳宏教授表示,临床上看筛查和体检有相似的目的,最核心的功能帮助被检者排除健康风险,最大程度的保证阴性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敦促阳性检测结果的被检者到医院就医。“Clear-C”采用了前瞻性的实验设计,其数据结果的可靠性远高于回顾性研究,能够为被检者提供更高的可信度。【来源:都市快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火弗能热
火弗能热华西博士3年发表46篇SCI排第一16篇论著,这怎么做到的?
在国内以SCI论英雄的大环境下,盛产SCI的神人不在少数,今天看到这个我真的惊呆了,虽然之前也看到过不少某某博士发表很多SCI的新闻,但是大多数都是材料专业的,临床医学专业的真的不多。四川大学华西的科研氛围我是见识过的,但是遇到这样的神人还是要感叹一下,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当无数人都憋不出1篇论文的时候,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2019届毕业生邓博士在3年时间里累积发表了46篇SCI !邓博士,2011年考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硕博连读,自2016年至今,累计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46篇,其中第一作者41篇(是的,你没有看错,自己第一作者排名第一就有41篇,这可是实打实自己写的,不像很多人虽然文章数量很多,但是很多都是共一),共同第一作者5篇,累计影响因子大于120分!!如果是基础试验,我觉得一篇完全自己做完的SCI差不多需要耗费一个普通研究生1到2年的工作量,如果前瞻性的临床试验,光收集病例+随访也要2年时间吧,当然如果都是回顾性的临床研究就比较快了。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成绩肯定会有一些质疑,我也比较好奇邓博士发了什么样的文章,有人也去挖了一下,发现在这么多文章中,其中Original research 16篇(仅仅原创论著就有16篇,也足够秒杀很多人了),其它Comments 9篇,Meta分析10篇,另很多篇letter,这些文章平均IF都是2-3分之间。邓博士本人也对网络上的质疑做出了回复。咱先不评论邓博士的论文有没有灌水的嫌疑,这样高产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很多人为啥1篇也写不出来呢?我觉得能做到这样,估计有以下几点:1. 对科研和专业的热爱不喜欢科研,不喜欢写文章的人,不喜欢自己所学专业的人肯定是做不到这些的。2.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不管是以拿奖学金,拿荣誉称号,还是以成为学术大牛为目标,这里面肯定有他的奋斗目标。4.合作能力强能发这么多原创论著,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是基础试验,我猜这离不开导师课题组团队的协作。5.依托平台强大华西医院的科研氛围很好,硬件软件实力在国内都是顶尖的,所以基于高平台能高产论文也不奇怪。6.数据资源充足华西这样的顶尖平台一般资源和数据来源都比较充沛,所以也比较容易写文章。7.导师指导有方优秀的学生肯定不乏优秀的老师,能出这样的学生导师功不可没。8.超出常人的勤奋勤能补拙,这样的学生从小就是学霸,学习非常努力,所以在科研上也不会差。就是发46篇中文核心也得费点功夫,就是46篇统计源也TM得码字啊,想发46篇SCI,阅读文献基本破千了,说他非常努力没什么好说的。9.善于思考能写这么多Comments和Letter就说明平时看文献会经常思考,不然也找不到文献里的错误,更写不出Comments。10.不刷抖音,不看电视,不打游戏,不逛街,不睡觉这条是我胡乱想的,能写这么多文章,差不多几天就出1篇SCI的速度,那么每天应该没有那么时间干这些事情的吧,也应该没有不相干的事情来干扰。回想起我读硕士搞第一篇SCI的那时候,为了学做实验,巴结讨好人,感觉实验没学会我可以卖保险了。每天闷头看文献,设计实验,不知不觉趴实验室桌子上睡着了,再一抬头卧槽天亮了?在实验室养细胞的时候,细胞污染是常态,常年是凌晨1两点还在做实验,那时候有个女同学也做实验到很晚,因为她害怕,每天要我等她做完我才能走。所以我经常是最后一个从实验室离开的人。到了写文章的时候因为没写过SCI,就先写中文,然后自己翻译,绞尽脑汁在啃,写完以后再让老板求人给我改,别人每一句都能指出一个错误。投文章时候,隔几天邮箱里的回复都是“I regeret……”开头,我都快绝望了。终于熬到接收那一天,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然而现在回看,真的是一篇水的不能再水的垃圾文章了,要是现在,我分分钟就能想到类似的idea,1个月之内就能把实验做完。哎,现在老了,精力不足,乱七八糟的事情干扰也比较多,已经缺少年轻时的那股冲劲了,现在1年搞出来一两篇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哈哈哈!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
 伦勃朗
伦勃朗岑少宇:详解钟南山领衔的连花清瘟论文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岑少宇】之前做了几期视频,希望每次通过小段子讲一个小观点,不过很多朋友都极有求知欲,觉得太不满足了。今天我们干脆大干一场:钟南山领衔的关于连花清瘟胶囊的论文,最近正式发表了,不妨把每一部分都好好学习一下。最后也会提到一些热点问题,比如连花清瘟的应用是否不讲辨证?这样的研究是否存在“废医验药”的嫌疑?以及研究人员与连花清瘟胶囊的制造商以岭药业的关系等等,辨析下某些人的质疑是否有道理。如果对论文本身不大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看。论文题目很长,叫《中草药连花清瘟胶囊改变用途后,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Efficacy and safety of Lianhuaqingwen capsules, a repurposed Chinese herb, in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A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光题目里,就有几个关键点。首先是“胶囊”。中草药因为有效成分不明确,研究结果有时会受到质疑,比方说你拿这批药材熬药做的研究结论是“无效”,他拿那批药材做的“有效”,两边到底谁更准确,是不是因为药材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或者处理方法的差异造成的?即使有同样的处理流程,多了这么个环节,多少也会增加出现偏差的风险,有时候就说不清楚了。“胶囊”作为一个标准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制剂,可以减少这方面的质疑。第二个关键词是多中心。就是说这项研究是多个试验点同时进行的,参与的研究者不同,按照相同的方法试验。虽然影响因素可能更多了,难度更大,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依然得出有效的结论,那就更为可信了。我国1985年的《新药审批办法》里就规定,“每一种新药的临床研究医院不得少于3个”,而“增加适应症的中成药”,也是《新药审批办法》规定的新药。现在用的是2007年通过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里面有专门一章是“多中心试验”。可见我国对临床试验的重视。第三个关键词是前瞻性。与前瞻性相对应的,是回顾性。前瞻性就是先设计试验,再搜集资料,回顾性是搜集已经有的临床资料,总结总结。临床问题比较复杂,非研究人员之前搜集的资料,未必完整,你想要这个,他搜集的是那个,所以回顾性研究往往被认为质量相对较低,前瞻性的质量相对更有保证。导言部分下面我们来看看正文。在导言里,论文特别提及新冠病毒会造成“肺部炎症和浸润,以及全身炎症细胞因子风暴,及时治疗是治疗Covid-19的关键”。作者还说“传统医药经过了长期的演化”,“被证明对流感有效”,“受此启发,传统中药被改变用途,用于新冠治疗”。这里还没有明确提及连花清瘟,句末引用的文献来源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但在句中说对“流感有效”时,引用了一项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的2011年的双盲研究,正是连花清瘟胶囊治疗H1N1的。这项研究是北京佑安医院与以岭医药研究院下面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络病重点研究室等机构共同完成的。研究虽然没有设置空白对照,但与奥司他韦相比,病程中位数、病毒脱落时间中位数都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发热、咳嗽、咽喉疼痛、乏力的持续时间,以及靠打分计算的病情严重性上,则显著改善。下一句,作者引用别人的研究说,对几种候选药物已有所探究。这里说得稍微有点模糊,因为紧接着上面的“传统中药”,我一开始以为是几种中药候选者。不过仔细看引用的文献,其实是武汉病毒所和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表在《细胞研究》上的“给编辑的信”。他们通过体外试验,研究了一批现代药物,包括利巴韦林、喷昔洛韦、法匹拉韦、萘莫司他、硝唑尼特、瑞德西韦和氯喹,结论是瑞德西韦和氯喹可以有效抑制病毒。这说明,看论文不能想当然,毕竟现在和几十年前不同,文章都是惜字如金,难免有模糊的地方,一定要再去看看引用的文献。作者随后说,“在最近发表的文献中,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胶囊可以在体外显著抑制新冠病毒复制,改变病毒形态,显示出抗炎症的活性”。这项体外研究也是由钟南山团队完成的。当然,不管是瑞德西韦、氯喹,还是连花清瘟,体外研究确实不能真正作数,主要的意义在于启发人们进行下一步的临床研究,或者机理研究。可以说,它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论文接着提出,“连花清瘟胶囊可能显著(could significantly)改善主要症状(如发热、咳嗽、乏力),缩短病程”。此处引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中文杂志《世界中医药》上的《连花清瘟颗粒治疗54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分析及典型病例报道》,另一篇也是中文文献,发表在《中医杂志》上的《中药连花清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63例临床观察》。这两篇文章都基于连花清瘟颗粒,质量不算高,都是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样本数量也偏低。而且前一篇没有对照,当然也没有显著性检验,原话也比较谨慎,是“明显改善”,其实没有提“显著”这样的术语。后一篇虽然有对照,有显著性检验,但病人收入时按照当时的第四版诊疗标准只是疑似病例,由于试剂盒供应等问题,没有纳入核酸标准,作者解释说,按第五版“现均为临床诊断病例”。但我们在第七版里可以看到,确诊病例还是要核酸或抗体检测,所以这样的研究存在非常大的漏洞。回到钟南山他们的论文,接着就提到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也有连花清瘟胶囊,不过没有具体展开。我们回顾下,方案仅仅是在“医学观察期”,临床表现“乏力伴发热”时,推荐了连花清瘟胶囊或颗粒,是三种药物中的一种。有这些铺垫,也就引出了新研究的必要性。方法部分下面我们进入“方法”部分。论文开篇就明确,这是项“开放性研究”(open-label),也就是“非盲法”,没有什么“单盲”“双盲”。在“方法”部分比较后面的地方,作者回过头来,简单解释了下不采用“盲法”的原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有紧急性。我认为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今年1月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传统医学理应有自己的位置》,提到“现在很多中医论文质量不高也是实情,但在防治疫情方面的研究有其特殊性。”我还引用了世卫组织非典报告里的一段话:“专家认识到,当非典这一新的流行病正在传播时,对治疗手段进行研究有着重重困难与挑战。由于医疗资源的相对稀缺,以及临床工作之繁重,对非典的临床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如此,研究人员为改进研究设计,确保质量,减少误差,已竭尽全力。”面对新冠,情况也是类似的。回到论文,作者接着报告了临床试验注册情况,根据注册号2000029434,可以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检索到“连花清瘟胶囊/颗粒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申请人韩硕龙所在单位是以岭药业,研究负责人是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等。研究实施负责单位则是河北以岭医院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经费或物资来源”填的也是以岭药业。再看病患的选择,试验申请时是两组各120人,现在总共284名病人,因为考虑了一个“脱落率”的概念,就是有些病人即使进组了,也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中途“脱离”,论文里给出的估计是10%以内。最初纳入评估的病人则高达480名,可见入组淘汰之严格。没有核酸检测,就刷掉了140人,CT上没有肺炎症状,又刷掉21人,同时,患者必须有发热、咳嗽、乏力中的任一症状。论文还写明了许多其他排除因素,这在试验申请页面上能看到中文版。下一小节是“疗法”,介绍了连花清瘟胶囊的主要成分,并指明试验用药是由制造商提供的。常规疗法基于第七版诊疗方案,主要是支持性治疗,包括氧疗、抗病毒治疗和对症治疗。在流程中讲了一组是只用常规疗法,另一组加上连花清瘟胶囊,一日3次,每次4粒,总共14天。不过在试验注册时,还提了“或颗粒每次1袋”。可能是为了提高研究质量,在实际操作中也许统一用了胶囊。“症状恢复”或说改善的标准,是至少有一项主要症状,也就是咳嗽、发热或乏力,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临床治愈的标准,则要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体温恢复3天以上,症状恢复,胸部CT有明显改善,连续两次病毒RNA测试阴性(间隔至少一天)。试验的主要终点也就是主要的观察指标,是症状恢复率,次要终点是症状恢复的时间、单一症状的恢复率和时间、CT改善的比例、临床治愈的比例、核酸检测改善率与时间。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标准、终点呢?因为它们挺重要的。比如之前号称“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韦,中美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别,引发了到底有效无效的争议。中国研究团队的曹彬教授就谈到了终点问题,他的“研究终点采用了国际公认的六等级复合终点指标。NIH一开始的设计和我们一样,也是复合终点指标,但是后来进行了修改。”另外,曹彬还提到“我们的研究更严格,要求入组病人必须在发病的12天以内,而NIH的研究没有做这方面的限制。”确实,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冠病毒的临床试验,像曹彬教授这样更为细致的设计,还是比较少的。在“终点”这一小节里,还有一句比较重要的话。“乏力和咳嗽的强度是由病人自己报告的。”也就是病人主诉。这里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争议,因为没有盲法,如果不像发热那样,规定37.3度以上算发热,选择的终点只能靠病人主诉的信息来衡量,那么这些单项数据发生偏差的可能还是不小的。但我们也要考虑到疫情期间实际条件的限制,虽然有像曹彬教授那样的双盲试验,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无法强求每个研究都能做到双盲。在循证医学中,双盲比起非盲是等级更高的证据,但在连花清瘟没有更高等级证据的时候,也可以参考相对低等级的证据。循证医学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体系,不是说必须有双盲,如果全世界真的什么高等级证据都没有,只有“专家意见”说有效,那也是循证医学的一部分。有些人对循证医学的排斥根本没有道理。至少,研究者们是不排除“盲法”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引入了盲法。比如在这篇论文里,CT的检查就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专家做的,这位专家身上就用了“盲法”,他对手头病例的分组情况不知情。统计分析里面提到了FAS和PPS的概念,前者是全分析集,后者是符合方案集,就是剔除一些偏离方案的病例。在这项研究中,影响不大,因为两组都恰好各只剔除了3例。结果与讨论部分下面再简单谈谈结果。很多媒体都已经报道过了。主要终点,也就是症状恢复率或说改善率是显著提高的,其他包括症状恢复的中位时间,以及发热、乏力、咳嗽的单项改善时间,临床治愈率,CT等指标也都有显著差异。至于对病毒直接的作用,之前有报道引用钟南山的话,“连花清瘟胶囊对病毒抑制作用有一些,但是很弱。”而在论文中的说法是,连花清瘟与病毒转阴率的改善“无关”(not associated with),转重症的比例用的是两组“类似”(similar)。虽然说用什么语言来表述差异不显著的结论,并没有定规,但多少也可以反映出作者们的态度。结果还有一部分是安全性分析,连花清瘟作为一个上市已久的药品,确实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结果。主要的不良反应是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升高。在讨论部分,作者们谈到了新冠与SARS的一些相似性,指出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引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献表明,患者入院后统计,88.7%有发热,67.8%有咳嗽。因此,突出了连花清瘟面对这些占比很高的病例时,可能很有价值。随后讨论的是炎症风暴,引用了多篇体外研究的论文,指出连花清瘟可以在体外抑制一些炎症因子的释放。不过体外试验毕竟有局限性,而作者们的临床试验确实也没有直接检测炎症相关的指标,因此他们比较含蓄地说:“更高的临床治愈率和CT恢复率也可能与抗病毒的活性有关(could also be associated with),或许(probably)也与抗炎症效应相关”。反正“讨论”部分本来就是可以探讨一些间接的联系或推测,提到这些可能的相关性也是惯例。另一方面,作者明确指出了,关于病毒转阴的临床结果,与体外的抗病毒结果不符合。之后作者引用了《中国中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基于临床经验和分子对接技术的抗新型冠状病毒中医组方快速筛选模式及应用》,认为连花清瘟的关键成分连翘和金银花可以阻断新冠病毒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也就是ACE2的结合。这项筛选研究选取了“2003年国家公布的中医药防治SARS方案,以及近期国家、各省市和知名专家公布的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方案的中医方剂”,把里面已知的主要成分的结构和ACE2去匹配,如果结合能力强,就有可能阻断病毒的结合。《基于临床经验和分子对接技术的抗新型冠状病毒中医组方快速筛选模式及应用》中的配图其他几篇被引用的文献,则提到广藿香缓解腹泻,改善宿主胃肠道的防御能力;红景天有缓解肺部损伤的功能;大黄可以有效拮抗刺突蛋白与ACE的结合,并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缓解肺部损伤。这些都是连花清瘟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基本都是动物试验,如小鼠、大鼠、兔等,或是生化研究,离临床都还很远。另一个有趣的点是,所引文献里的是红景天(Rhodiola rosea),而作者在之前介绍主要成分时提到的是大花红景天(Rhodiola crenulata)。最后,作者们指出,在只有血浆疗法有效的情况下,连花清瘟或许可以推荐给病人,用以减轻症状,改善临床结果。但是作者们也坦诚,试验设计有局限性,再次说明因为事态紧急,需要及时治疗患者,没有采用盲法。在结论部分,作者也说未来要全面评估疗效,双盲试验还是有必要的。至于没有使用安慰剂对照,作者们解释,在传染病迅猛爆发时,用安慰剂是不合医学伦理的。另外,作者们认为治疗时长的确定是基于经验,但延长治疗时间是否能达成更好的疗效,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他们在这里保留了一些不确定性,在这些不确定性中,甚至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治疗时间延长,两种疗法的效果没有拉开、反而趋近。新冠已知有相当多患者可以自愈,出现这种疗法随时长趋近的可能性到底多大,难以断言,就见仁见智吧。几个热点问题的探讨· 连花清瘟能有多大作用?疫情期间,一些关于尸体解剖的新闻里突出了“痰栓”,有些人就将某些药物、设备与此相联系。等到连花清瘟的报道多了后,也有人脱离论文与作者们自己的表述,对其改善症状的意义,与痰栓、炎症等的关联过度联想。其实作者们在“讨论”部分提到的与炎症相关的信息,基本都是很松散的,离临床也很远,因此推断也留有极大的余地,这是学术论文里常见的现象。关于“痰栓”,不妨引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2月28日在武汉写下的诊疗笔记:2月28日:关于尸体解剖出现痰栓国家有难、有疫情,应该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救治患者。可每每这个时候牛鬼蛇神都跑出来,心怀鬼胎地推荐各种离奇的治疗方案、不着边际的药品、设备。尸体解剖出现痰栓、出现化脓性改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尸体解剖的都是病情很重死亡的患者,这些患者往往在后期合并有细菌或者真菌。其实新冠病毒肺炎(呼吸衰竭,ARDS)的尸体解剖发现的是病理改变和之前的病毒肺炎包括SARS等大同小异,主要是肺水肿、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改变。一些不良厂商抓住痰栓、炎症反应等,就大肆鼓吹自己的药品,鼓吹吸痰机。在临床上,病毒肺炎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患者在合并细菌和真菌感染之前痰还是比较少,气道还是比较干。ARDS患者如果不给充分氧疗,不给正压通气就用吸痰机吸痰,那几乎100%死亡,你自己试试。要想做好呼吸支持,就要求做好吸痰、气道管理等,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连花清瘟的应用是否不讲辨证?在钟南山多次提及连花清瘟后,有些中医爱好者发出了一些质疑,认为连花清瘟这样的药不讲究辨证,不能体现中医的精髓。证与症状不同,辨证试图把握病理变化的本质,确实不是症状的简单堆积。但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有些人为了突显中医的特色与价值,过于强调“辨证”“一人一方”等概念。然而,只讲辨证和不讲辨证,是两个极端,都是对中医的片面认识。在实际运用中,有大量只需对症,不需辨证的情况。就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为例,其中在临床治疗期,也就是针对确诊病例,固然列了许多如“寒湿郁肺证”“湿热蕴肺证”等证型,但在“医学观察期”,只举了两类临床表现的症状,一是乏力伴胃肠不适,二是乏力伴发热。作为全国中医药力量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说,这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界主流的认识,并非什么都要提“证”。一说中医就是辨证,和一说现代医学就是双盲,在思维方式上倒有相似之处。遇到那些只会把“辨证”两个字挂在嘴边,甚至说得神乎其神的“爱好者”,我们反倒要长个心眼,怕不是遇到了什么江湖骗子。· 钟南山的研究是否存在“废医验药”的嫌疑?有些“中医爱好者”甚至从“不讲辨证”,进而引申到“废医验药”这样的大帽子。诚然,作者们使用了现代的临床试验方法,虽然整体没有使用盲法,但看CT的放射科医生用了盲法,而且作者在结尾也强调了将来使用双盲的必要性。此外,作者引用的文献还采用了很多现代药学的手段,比如之前提到的对中药成分的结构筛查等。从这些表面现象看,似乎是有种只在“验药”的感觉。然而,“验药”始终是主流的目标之一,虽然困难重重,有些药厂也有惰性,但总体上在往这个方向走。归根结底,“验药”与“废医”完全是两码事,从科学上讲,“废医”根本是个伪命题(这点以后有机会再详谈)。我们从作者引用的那些与药学相关的参考文献中,还可以看出现代科学对药方改进的重大价值。比如前面提到的红景天与大花红景天,或许可以尝试改变药方中红景天的具体种类;又如,可以参考作者引用的药物筛选文章,根据药材主要分子与受体结合的能力,在原有配伍的基础上,尝试调整具体的配方比例。当然,药物筛选等方法和体外实验一样,都只是一种提示,实际效果还是要临床检验,也要考虑到临床检验需要的人力、物力,和可能取得的效果,判断是否值得进行这样的改进。· 药品说明书和研究为何完美对应?有人质疑说,论文的“指标也很怪,主要指标就是后来药品说明书增加的那三个症状,但这三症状在诊疗方案里根本没提对应的治疗”。言下之意,似乎研究是为了在新冠疫情下推广药物“量身定做”的。我查了下,以岭药业确实在4月14日就发布公告,称新说明书获批。说明书中的【功能主治】项增加“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常规治疗中,可用于轻型、普通型引起的发热、咳嗽、乏力”。媒体报道此事时说,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连花清瘟”,结果显示仅有以岭药业获批。当时论文还没有正式发表,审批也需要时间,申请肯定要早得多,应该是基于刚完成的研究申请的。3月,钟南山等已经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及连花清瘟,主要也是基于这项临床研究。从时间上看,2月15日完成试验,到3月前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初步结果。根据研究结果,申请新的说明书,一一对应也很正常,并没有先上车后补票的嫌疑。前面提到过,“乏力和咳嗽的强度由病人主诉”,在没有盲法的情况下,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只是研究者们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的选择,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和说明书修改有什么关系。至于诊疗方案里没有专门提及这三个症状,也很容易解释,毕竟诊疗方案的制定者们,与审批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不是一套班子。· 研究人员与连花清瘟胶囊的制造商以岭药业是何关系?之前我们提到,在临床试验注册表上,申请人韩硕龙所在单位是以岭药业,“经费或物资来源”填的也是以岭药业。不过,看正式发表的论文中,“资金”部分里写的是,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冠肺炎应急项目”和广东省中医药局等提供资金,以及一些北京、河北、澳门大学等项目的资金。可见,就像作者在论文中所说的,以岭药业提供的应该只是试验药物。因此,在“利益冲突声明”部分,作者简单地写了“无”(None)。还有人挖出钟南山曾与以岭药业的创始人吴以岭院士,曾共建“南山-以岭肺络联合研究中心”等等。然而,吴以岭、钟南山都是院士,研究中心很可能只是学术合作,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商业行为。论文里已经写明了由以岭药业提供药物,通讯作者之一还是以岭医院院长贾振华,引用的文章也有与以岭研究院相关的,根本没有要隐藏与以岭药业或以岭集团的关系。如果真要隐瞒什么利益冲突,谁会这么操作呢?而且,论文里还写了“无”利益冲突,可谓白纸黑字,如果真有利益冲突,哪天曝光了岂不是加倍的丑闻?谁会这么傻,给自己挖坑呢?从医学上讲,试验设计、临床意义当然可以探讨,捕风捉影实在是没有必要吧。
 上征武士
上征武士中国COVID-19的回顾性研究:其他汀药物可降低亡率
任冉/卫生部门He汀是一种具有良好抗炎作用的降脂药物,被认为是COVID-19的辅助治疗药物。然而研究表明他的汀药物可能通过诱导ACE2表达而增加风险。新型冠状病毒Castiglione和他类汀类药物的免疫调节作用表明,他们可能有助于对抗新的冠状病毒感染,Castiglione,等等;抗炎,哈利利,Fedson,等等。。然而这些药物已经被证明可以增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的表达。因此迫切需要直接的临床证据来回答his汀类药物对住院COVID-19患者是否有害或有益的问题。的研究表明,感染ACEI抑制剂或ARB(ACEi/ARB)的患者比没有ACEI抑制剂或ARB的患者有更低的28天全死亡风险(Zhang等人,)。然而联合治疗对COVID-19个体的影响尚未被研究。为了解决这些重要的临床问题,我们进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之一,作者强调这是一个回顾性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其局限性,为了前瞻性地研究其他汀药物对COVID-19结果的影响,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首先,结论如下对13981例COVID-19例中国湖北省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其中1219例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根据倾向评分匹配后的混合效应Cox模型,我们发现匹配他汀类和非他汀类药物组28天全的死亡率分别为5.2%和9.4%,风险比调整为0.58。在Cox时变模型和边缘结构模型分析中也观察到他汀类药物的低死亡风险。研究概况:图1,概述参与者参与、排除和纳入标准的示意图。297名没有高血压病史或有高血压但没有服用抗高血压药物的参与者被排除在亚组分析之外。分析包括来自中国湖北省21家医院的13981例确诊病例。其中1219人在医院使用了他的汀药物组,其余12762人没有接受他的汀药物治疗(非他汀药物组)胸部CT显示汀组双侧病变较非汀组更常见(89.5%比83.7%,P入院时,his汀组的LDL(LDL-C)和总胆固醇(TC)比非他汀组更频繁地增加。在整个住院期间,两组的血脂水平相似。与非汀组相比,使用其他汀药物治疗的患者从症状出现到住院的天数更长,平均随访天数也更长。图2,PSM和非汀组的生存曲线在PSM队列中,汀组的死亡率(IR,0.20例/100人日;死亡率5.2%)显著低于IR,0.37100人·天)。死亡率为9.4%。对于COVID-19的次要终点,我们分析了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与有创机械通气、ICU、ARDS、感染性休克、急性肝损伤、急性肾损伤和急性心脏损伤的发生率之间的关系。经PSM校正基线差异后,his汀组有创机械通气发生率仍低于非他汀组(aHR,0.51;95%CI,0.34-0.78,P=0.002)。在PSM队列中,他的汀类治疗与其他次要结果(如急性肾损伤、肝损伤和心脏损伤)和血清CK或转氨酶水平升高无关。图3住院期间他汀类与非他汀类炎症因子的动态变化在基线差异匹配的受试者中,CRP的动态轨迹在入院后均呈下降趋势,在整个住院期间,his汀吸毒者的CRP动态水平较低。在整个随访期间,his汀组的IL-6水平低于非他汀组。同时,在住院期间,his汀药物组中性粒细胞计数动态曲线较非汀组有更显著的下降趋势。此外,为了消除审查制度或死亡造成的任何文物,对活着的参与者进行了分析。当在28天的随访期内死亡的人被排除在每组之外时,这种趋势是相似的。
 柏瞳
柏瞳川大荣誉毕业生46篇SCI背后是真优秀还是为了优秀而“优秀”?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019 届荣誉毕业生发表 46 篇 SCI 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其中讨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在读博期间发表如此多的SCI论文?全都是刻苦钻研所撰写还是为了数量而灌水?针对目前争议较大的两个问题,网友们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当事人答复(图片来源于网络)其中网友A认为:灌水毫无疑问助长了华西及全国sci泛滥,唯文章论的风气,因为打败灌水的最好方法就是灌更多的水。但是我也算理解这种行为。相比于其他办法来讲,这其实是最简单稳妥的取胜方法。打个比方,你今年和一个10篇sci,IF平均1分(记为10*1)的竞争留院,你想胜出,你手里有12分,可能是1*12、2*6、3*4、6*2、12*1,哪个胜面大,哪个更稳妥,哪个能做到?网友通过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来描述了这种量产的可能。有利益就必然存在着竞争。就拿网友列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发表一篇12分SCI的难度远远大于发表12篇1分SCI论文的难度,所以为了“取胜”,那么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那么论文灌水现象便随之发生。而对于为何会写这些总体影响因子低的文章,网友B分析了几个原因:第一:绝大部分博士没有条件(钱、精力、时间、关系)去做多中心RCT甚至是前瞻性研究;第二:有关于重要方向的回顾性研究(例如手术与否,术式选择、A药与B药等),数据难以全取,分组难以平衡、偏移难以把控,结果难以接受。用心筛,就是总样本小;往大做,就是漏洞多,所以只有扣细枝末节的问题,而不敢讨论重要争议所在;第三:即使是meta,也很少有人认真筛文献。其实meta的证据等级是最高的,但是因为meta用心做和不用心付出的努力差别很大,而且记工作量直接折半(博士后时期),自然没人认真写meta;第四:letter和comment也不是没意义,德布罗意靠letter就能得诺贝尔奖。但是和meta一样,这两个记分时折到1/3甚至1/6,所以很多时候的做法是盯着稍好一点的杂志找茬,大多言之无物,而不是真的有感而发。另外,对于如此高产的SCI论文,也有网友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位同学如此高产,至少证明他有异于常人的体力和精力,而且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归纳手段——他没整出模板我是不信的。具有这等素质的学生,在正确的引导下,是具备很大潜力的。胸外科尤其是肺癌领域近些年的突破可以说是极为震撼的,而这位同学把自己的才华、潜力和宝贵的时间挥霍于一些价值可能极其有限的研究,实在是太可惜。作为一个外科博士,博士在读期间以及进入临床工作3年内是决定他在学术道路上能走多远的关键时期,一旦没利用好,就会陷入没成果-拿不到项目-没钱做研究-没成果的死循环,而下一轮学术机遇期至少要到等同于副高阶段才会出现,空窗期长达近10年甚至更久。再回到这件事,为何现在存在如此多的学术造假或者文章灌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博士毕业机制、科研经费申请机制、职称评级机制等。既然定了标准,那么想要获得对应的荣誉、经费就得想办法去满足条件。不排除部分博士、教授确实凭借着自己多年的研究心血总结出高质量论文,实打实地满足相应条件。但是更多的是部分博士、教授为了优秀而“优秀”,为了符合条件而想办法符合条件,于是就衍生了众多的学术造假,学术灌水。对于学术灌水而言,没有学术造假那么严重,只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去发表一些价值不大的论文或者说水文,无疑是对自身实力、科研经费的浪费。为了避免类似乱象,那么像之前提到的相应机制是否需要修改,完善?总的来说,博士期间能够发表46篇SCI确实了不起,但是如果能更加专注于文章质量而不是数量,那么可能网络上的这些质疑声就会随之烟消云散。不知道对于此事,大家怎么看呢?
 吾岂
吾岂有趣的研究:近视眼患者不易“中招”新冠?
近日,发表在《JAMA Ophthalmology(美国医学会眼科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来自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调查新冠疫情早期的住院患者发现,日常佩戴眼镜与新冠病毒低感染率存在相关性。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将2020年1月27日至3月13日在中国随州市增都医院(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所有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纳入研究。该团队收集了所有病例的信息,包括湖北省的接触史、临床症状、潜在疾病、视力状况和佩戴眼镜的时间等。在276名接受新冠肺炎治疗的患者中(男性155人,中位年龄51岁),只有16人(5.8%)每天戴眼镜时间超过8小时。患者中没有人戴隐形眼镜或曾进行过屈光手术。研究人员在确定这些患者都是近视眼后,又调查了湖北省的近视眼患者比例。他们在一项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这一比例要高得多,达到了31.5%。因此得出结论:近视眼患者发展为住院患者的比例比预期要低5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性研究结果,与所有单一的研究一样,必须要谨慎对待。虽然在大流行中,眼睛的防护一直是个人防护装备(PPE)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项研究报告的差异程度令人惊叹。这并不是说研究结果可能是不真实的,而是在得到独立证实之前,我们不建议人们做出任何有悖于常识的行为改变。眼睛是病毒的窗口吗?任何病毒感染的关键步骤之一都是先试图进入人体。我们身体的大部分都被具有保护性功能的皮肤屏障所覆盖,以阻止病毒或细菌进入我们的身体;但覆盖在呼吸道、消化系统和眼睛上的屏障要薄得多,它们就是一层薄薄的薄膜。这些薄膜的作用是让氧气、食物以及光线等外部物质进入我们的身体。然而不幸的是,病毒已经学会利用这些“薄弱的环节”。这就是佩戴口罩、护目镜,以及穿防护服来保护这些“环节”的原因。尽管我们可以想象到,对这些“薄弱环节”的主要攻击来自于以气溶胶形式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颗粒,但它们到达这些地方的主要途径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手。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健委的建议都在反复强调经常洗手,以避免接触我们的口鼻眼。因此,眼睛前架一副眼镜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是有道理的,不仅可以防止他人呼出的病毒颗粒,还可以防止佩戴者触摸自己的眼睛。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就有报告在医院环境中因没有适当保护眼睛而感染上新冠肺炎的案例。我们也知道,新冠病毒偏爱的ACE2受体也存在于眼睛中。但作者表示该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这是一项单中心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戴眼镜和长期佩戴眼镜的患者数量有限,这限制了将结果扩展到更大的人群。因此,该研究结果需要通过大样本多中心研究进行验证。随这篇研究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传染病科的Lisa Maragakis指出,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得出相关性结论的观察性研究,并不一定意味着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而且作者也列出了一些局限性,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结果。研究人员对普通人群的数据来自一项更早的研究,该研究的样本(在年龄、人口学和其他因素方面)与因新冠肺炎而入院的样本并不完全匹配。他们也不能保证一般人群中所有近视的人每天戴眼镜的时间都超过8小时。虽然眼镜不能提供与护目镜相同的保护程度,但它们可以充当部分屏障,类似于布口罩的方式减少病毒载量。Maragakis表示,这项研究具有启发性,并提出了这样的可能,即公众佩戴眼镜可能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使其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但需要进行更多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以确认本研究中观察到的关联性。论文链接: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ophthalmology/fullarticle/2770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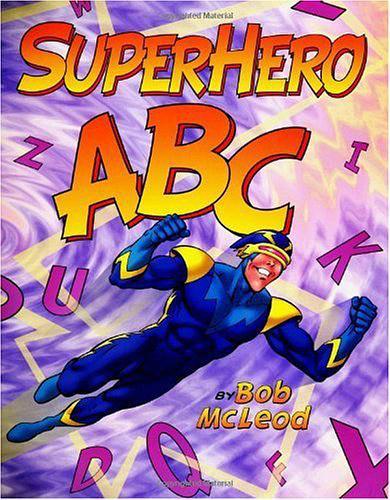 田猎毕弋
田猎毕弋在医学科研和医学写作中如何正确运用统计学
科学研究是人类探索未知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重要活动,而这些规律的发现,要靠科学的统计研究设计为指导,长期的观察和大量的实验为前提,对实验数据进行合理的分析和处理为依据,从而作出科学的推断和结论。在这个过程中,通常都需要借助统计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得力助手,它使科学研究工作者头脑更清醒、智力更超常、眼睛更明亮、手段更有力。一项科研工作,原本需要统计研究设计,但有些研究者由于轻视或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未用或误用了统计研究设计方法,要么浪费人力、物力和时间,要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那么,在医学科研和医学写作中,如何才算正确地运用了统计学?在医刊汇编译看来,无论是运用还是表述,一般来说,都要涉及“统计研究设计、资料的收集和表达、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和结果的解释”等内容。如果在这几个方面,都很少或几乎不犯统计学错误,才算正确地运用了统计学。事实上,在研究阶段,用统计学主要体现在“统计研究设计与具体实施”和“资料的收集”两个方面;而在写作阶段,用统计学主要体现在“关于统计学处理部分的表述”、“统计分析方法的合理选择及实现”和“结果的解释及结论的陈述”等方面。为此,我们建议在医学科研和医学写作中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重视树立正确的统计思想。不能把统计学视为获得高等级科研成果和发表学术论文的敲门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统计学是帮助科研工作者揭示客观事物内在规律性的重要工具之一,它可以使研究工作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以理服人、多快好省。第二,应重视统计研究设计。不仅在科研工作开始之前就要制定完善的统计研究设计方案,而且一定要自始至终地按方案认真实施,还要在成果报告或学术论文中,明确交代所采用的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如本研究采用的是前瞻性调查研究设计还是回顾性调查研究设计、本研究采用的是观察性研究设计还是实验性研究设计,具体地说,还有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多因素析因设计和具有重复测量的多因素设计等。第三,应重视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与描述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成果报告或学术论文中,通常都有一段关于作者如何进行统计学处理的描述。它反映了作者是如何选用以及如何描述统计分析方法的。有些作者仅说自己使用的是何种统计软件,这种种描述实在太空洞了,根本不够,最主要的是要交代所使用的统计研究设计类型和统计分析方法。因为统计软件只是实现数据处理的一种工具,如果使用不当,再高级的统计软件也会给出错误的分析结果。第四,应重视结果的解释与结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结果解释也时常会出错。一种是关于无显著性意义的结果的解释,一种是关于有显著性意义的结果的解释。特别是关于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解释和关于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的解释,很容易出错。一般来说,统计学假设检验的结果,并不能得出两组之间的差别大到了何种程度,它仅仅说明两组之间的差别在统计学上有没有意义,有些差别即使在统计学上有意义,而在专业上却没有意义。
 八恶人
八恶人有趣的研究!中国科研团队:近视眼患者不易“中招”新冠
近日,发表在《JAMA Ophthalmology(美国医学会眼科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来自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调查新冠疫情早期的住院患者发现,日常佩戴眼镜与新冠病毒低感染率存在相关性。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将2020年1月27日至3月13日在中国随州市增都医院(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所有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纳入研究。该团队收集了所有病例的信息,包括湖北省的接触史、临床症状、潜在疾病、视力状况和佩戴眼镜的时间等。在276名接受新冠肺炎治疗的患者中(男性155人,中位年龄51岁),只有16人(5.8%)每天戴眼镜时间超过8小时。患者中没有人戴隐形眼镜或曾进行过屈光手术。研究人员在确定这些患者都是近视眼后,又调查了湖北省的近视眼患者比例。他们在一项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这一比例要高得多,达到了31.5%。因此得出结论:近视眼患者发展为住院患者的比例比预期要低5倍以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性研究结果,与所有单一的研究一样,必须要谨慎对待。虽然在大流行中,眼睛的防护一直是个人防护装备(PPE)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项研究报告的差异程度令人惊叹。这并不是说研究结果可能是不真实的,而是在得到独立证实之前,我们不建议人们做出任何有悖于常识的行为改变。眼睛是病毒的窗口吗?任何病毒感染的关键步骤之一都是先试图进入人体。我们身体的大部分都被具有保护性功能的皮肤屏障所覆盖,以阻止病毒或细菌进入我们的身体;但覆盖在呼吸道、消化系统和眼睛上的屏障要薄得多,它们就是一层薄薄的薄膜。这些薄膜的作用是让氧气、食物以及光线等外部物质进入我们的身体。然而不幸的是,病毒已经学会利用这些“薄弱的环节”。这就是佩戴口罩、护目镜,以及穿防护服来保护这些“环节”的原因。尽管我们可以想象到,对这些“薄弱环节”的主要攻击来自于以气溶胶形式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颗粒,但它们到达这些地方的主要途径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手。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健委的建议都在反复强调经常洗手,以避免接触我们的口鼻眼。因此,眼睛前架一副眼镜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是有道理的,不仅可以防止他人呼出的病毒颗粒,还可以防止佩戴者触摸自己的眼睛。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就有报告在医院环境中因没有适当保护眼睛而感染上新冠肺炎的案例。我们也知道,新冠病毒偏爱的ACE2受体也存在于眼睛中。但作者表示该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这是一项单中心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戴眼镜和长期佩戴眼镜的患者数量有限,这限制了将结果扩展到更大的人群。因此,该研究结果需要通过大样本多中心研究进行验证。随这篇研究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传染病科的Lisa Maragakis指出,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得出相关性结论的观察性研究,并不一定意味着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而且作者也列出了一些局限性,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结果。研究人员对普通人群的数据来自一项更早的研究,该研究的样本(在年龄、人口学和其他因素方面)与因新冠肺炎而入院的样本并不完全匹配。他们也不能保证一般人群中所有近视的人每天戴眼镜的时间都超过8小时。虽然眼镜不能提供与护目镜相同的保护程度,但它们可以充当部分屏障,类似于布口罩的方式减少病毒载量。Maragakis表示,这项研究具有启发性,并提出了这样的可能,即公众佩戴眼镜可能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使其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但需要进行更多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以确认本研究中观察到的关联性。论文链接: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ophthalmology/fullarticle/2770872
 杨何
杨何樊代明院士:用医学的反向研究探索创新药发展
12月14日,首届中国(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科技发展论坛在石家庄以岭健康城举行。本次论坛由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主办,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承办。论坛以“为生命、一起赢”为主题,包括高峰论坛和五个不同主题的平行论坛。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多位国内外专家、院士、领军企业代表,千余位嘉宾汇聚石家庄,就生物医药产业的趋势与机会、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全球竞争等话题展开对话交流。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医药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樊代明以“医学的反向研究”为题目,为现场的千余嘉宾带来了精彩的主旨演讲。樊代明指出,当今的医学界在基础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医学界以发表论文作为前进的标志和结果,但只有3%具有参考价值。“2013年美国FDA发布了一则消息,最好的药品是抗抑郁症的药,40%没有效果,最差的抗癌药有75%没有效果,而美国只有30%有效果就可以进入到临床了。”樊代明说,“现在诊断出来的病例比过去十年翻了一番,但是治疗并没有跟上,究其原因,一部分来源于经验主义,用医学上的同质性来分析病人的异质性。”“在医学界普遍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前瞻性研究更加科学。”樊代明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前瞻性研究是随意的可由人为控制,“它固然有一定的真理,但并不是高于回顾性研究。”樊代明指出,指南作为医生看病的参考,但每个病人是独立的个体,并不能用一种方法来解决,参考指南的方法是“蔑视和抹煞了高级医生的能力和经验”。谈到医学的反向研究,樊代明说:“经验是经历了实践的东西,经验到临床到机制,找得出机制是机制,找不出机制以效果说了算。所谓的反向是指前后反向左右反向,上下反向,顺时针和逆时针反向,以及对现有已经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是更大的反向。”针对市面上出现的老药新用,以及药品出现的副作用的现象,樊代明都以医学上的反向研究思维进行了分析,发挥每一个药的若干的作用来取代创新药品。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立刻删除。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