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湛青天
湛湛青天逻辑学:《悖论研究》
逻辑学:《悖论研究》作者:陈波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悖论起源很早,如古希腊的“说谎者悖论”、中国的“白马非马”说等。历史上,众多的哲学家、数学家对悖论进行了探索,带给他们成功的快乐和失败的苦痛,并且不断推进了人类智慧的进展,引发哲学和数学的革命。悖论之所以存在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人类思维深处的矛盾和裂隙,在对悖论漫长的探索过程中,我们不断攀升人类智慧的高度。艺术史:《再读睢阳五老》编者:上海博物馆《睢阳五老图》是北宋时期画作。所谓“五老”,是指杜衍、王涣、毕世长、冯平、朱贯,皆大宋朝中重臣,辞官后寓居南京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颐养天年。该画是一部国宝级画作。本书收入靳尚谊、吕胜中、徐冰、吕澎、尹吉男等当代艺术家对自己艺术创作中传统与创新的阐释的文章,各自提供40幅作品,充分展示各自对艺术的理解。历史:《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作者:高晔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荷兰汉学家高罗佩颇具知名度,缘于其狄公案系列小说的创作及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开拓性研究。但高氏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更广。本书致力于对高罗佩生平经历、汉学研究、小说创作、藏品藏书的综合研究,在详实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学、史学、语言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学科知识,深入考察高罗佩推动华风西被的诸多贡献。社会学:《攀登劳累尔山》作者:(美)梅西等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本书对埃塞尔·劳伦斯家园——劳雷尔山决议产生的一个住房开发项目——进行了系统的评估。作者们评估了这个项目的影响,揭示了被社会科学家称为居民区效应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居民区可以形塑居民的生活轨迹。本书证明修建保障性住房项目是达致整合及改善穷人生活状况的有效的、划算的途径,这种途径成本合理,且对社区整体没有负面影响。小说:《大街》作者:(美)辛克莱·路易斯出版:漓江出版社主人公卡罗尔是个女文青,大学毕业后嫁给乡镇医生肯尼科特,随夫来到囊地鼠草原镇。在试图改革重建的道路上,卡罗尔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特别是小镇上流社会保守势力的反对。深感孤独的卡罗尔选择逃离“大街”前往华盛顿独自谋生,却在两年后不得不重回丈夫身边,因为华盛顿不过是放大的囊地鼠草原镇,是另一条“大街”罢了。
 鼻彻为颤
鼻彻为颤毛泽东的逻辑学之旅:他为何喜爱章士钊的“叛书”,两人啥关系?
在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关系,可以说最为特殊。这一特殊的关系,表现在毛与章之间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上。诸如:毛泽东“还钱”、毛泽东批准出版章的《柳文指要》等等。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生活方面的关心,同时,还表现在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毛泽东突然问章士钊,能否借您的逻辑学著作一阅?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毛泽东见到章士钊忽然问道:“听说您在逻辑方面有著作,能否给我一阅?”章士钊的这本著作,正是他于1943年在重庆出版的《逻辑指要》,但章士钊却十分踌躇,他犹豫了一番,说道:这本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由此呈现给您,怕是对您的侮辱。为什么章士钊要这样说呢?原来,章在这本书的序章里,迎逢了蒋介石,因此蒋介石请他到国民党陆军大学里讲授这本书。毛泽东当然知道其中缘由,但也只是呵呵一笑:“这是学问上的事情,个人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话虽如此,但其实毛泽东与章士钊很早就相识了。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与章士钊有了一段“特殊”的关系。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在李大钊的介绍之下,才在北大图书馆中入职,做了一名小小的“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曾经回忆那段经历时直言,“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人看”。因此在毛泽东的心中,对知识分子虽然敬重,但多少是提不起什么好感的。但章士钊,却是一个例外。在毛泽东困难的时候,章士钊这个当时的知名人物,在北大任教授,却给予了毛泽东这名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2万银元的资助,因此毛泽东对他一直是心有感激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章士钊的《逻辑指要》这样的感兴趣呢?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兴趣和关注;二是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与争鸣有关;三是与章士钊此书在中国逻辑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有关。原来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读过有关逻辑方面的书籍。据《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利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了1905年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穆勒名学》(直译名为《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和斯宾塞的《逻辑》等书。这位作者是继承了培根哲学的,他在培根的基础上,他还富有创新精神的自创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的理论偏向于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强调兼容并包,他指出:新的逻辑学不应简单反对旧的逻辑学。毛泽东通过读这《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学知识,同时也深刻地掌握了良好的逻辑性思维与表达能力,这为毛泽东的理论水平,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由于客观条件相对地稳定了下来,毛泽东能够集中精力读他所要读的书。这期间,毛泽东读得最多的书籍,就是哲学方面的书籍。《辩证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大纲》,以及战争哲学著作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1937年,毛泽东刚写完《矛盾论》,便于1938年春天读到了刚出版的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这可能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所读到的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关于逻辑学方面的专门著作。这本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并下了很大的精力来读它,并对其中的许多地方“颇感新鲜”。但这一时期,应该说毛泽东对逻辑学本身方面的认识和掌握的深度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而更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投入更多的精力的是50年代我国国内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和争鸣的时期。延安时期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在在中国理论基础上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国内的哲学,逻辑学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译自苏联。所以苏联理论界与学术界的一些成功与观点,在当时的国内占有了一定的地位,甚至到了与苏联关系交好时,中央主张学习苏联”老大哥”,因此这些观点,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逻辑学在这方面,则更加的突出了。由于中国自民国以来便饱受战火,而哲学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环境,中国之前的逻辑学研究,比较有价值性和代表性的,就只有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了。在个大前提,大背景下。中国方面的逻辑学观点,长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当时中国学术界对待哲学的态度,也是与苏联“一脉相承”的。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相比,有阶级性,有党性,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形式。它与辩证逻辑相比,是低级与高级的区别。二: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毛泽东支持周谷城然而,这种一家独占的形势并没有持续多久,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国的学术界不久便迎来了一场争论,逻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终于到来了。1956年,《新建设》杂志二月号(总第89期)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这篇文章里,对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造成了一种挑战当时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马上注意到了。毛泽东读的书很多,尤其书有关于逻辑学与哲学的书籍,周谷城的观点既新颖,又深得毛泽东的认可。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开会。他们谈天说地,讨论如何让批评更加有说服力。而这时,毛泽东想起了周谷城,他说:周谷城写了一篇关于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对了,是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毛泽东非常支持这场围绕着逻辑问题的争论,提倡学术争鸣。有一次毛泽东正中央领导人开会,会议之后,一群人正在会议室楼下的西厅准备就餐,这时毛泽东想到了周谷城也正在附件,他便把周谷城也叫了过去。刚一进屋的周谷城,便与毛泽东开始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拿着《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嘛,要继续争鸣下去。”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感慨地说:“我这个观点始终是太过于新颖独立了。只有我一人持此观点,学术界多数都在反对。火箭炮冲起来就不能落地了,我现在的局面有些被动”。毛泽东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理始终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有新的观点,适当地提出们,这才是学者应该有的态度,我看啊,辩论就是嘛。毛泽东还说:在人大办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就有与你文章相同观点的文章,还引用了你的意见。周谷城说:我没有看见。毛泽东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毛泽东还对周谷城说,大胆地写,不要怕,有观点就亮出来给大家看看,真理嘛,总是越辩越明的。周谷城受到毛主席的鼓励之后。信心大增。不久便再次发表了文章。而周谷城的这篇逻辑学文章,刚一发表,便引起了理论界的轩然大波。许多杂志社的编辑找到了周谷城:你这篇文章一出来,反对你的文章更是多了起来,周同志你准备怎么办呢?压力来到了周谷城这边。但是压力带来的更多的是动力。周谷城对杂志社的编辑们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主席也说,真理越辩越明,身为学者我是不怕有反对意见的。这件事很快让毛泽东知道了。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他们谈到哲学界正在讨论逻辑学。毛泽东说:问看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在此次思想争辩中,毛泽东几次给周谷城吃下了定心丸。他为了让周谷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特意告诉他:“人大有个王方明,他的观点和你相同。”这次谈话,除了论及个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毛泽东这番话对于周谷城、王方明当时尚属“少数派”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马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马特虽然在文章中进行了对讨论情况的综合叙述,但是对周谷城、王方明的观点,是带有批判性质的。他说这个争论是“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将学术问题,看成了斗争问题。还称周谷城、王方明“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周谷城的一篇文章,毛泽东便看到了,非常高兴,他对这篇题目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很感兴趣。还特意用长途电话召周谷城从上海来北京中南海。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门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问题十分关注。毛泽东对他说:“问题移到 《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周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连在一起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毛泽东用夹杂着英语的话风趣地说:“formal logic 本来说是formal的,要把它与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儿。”“中学高中班、大学初级班学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毛泽东说:“懂不懂,当然也有感觉是问题。但是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这时期,毛泽东投入许多精力关注着这场争论,对有关报纸、杂志登载的文章也都研究、阅读,对这场争论始终是比较重视的,并密切注视着各种观点。毛泽东所借的《新建设》和《哲学研究》,也正是用来查我有关于逻辑学相关的文章。而20世纪50年代,这场关于逻辑学问题的争论,首先便是在《新建设》杂志上展开的。而《哲学研究》,则一直以来都是毛泽东必读的杂志。1958年7月1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上面赫然写着:要该年“一至六月的《哲学研究》”,关注着论战的毛泽东,一直借助相关的杂志和期刊,来关注理论界的最新发展。而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有关于逻辑学方面的文章,登录的也比以往要多了一些。三:毛泽东出版哲学图书,毛泽东为何喜欢”叛书”?1958年,正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毛泽东,再一次的聚谈逻辑问题,其中参加的便有周谷城。他们从下午5时起,一直谈到11点半,毛泽东对哲学的热爱,显然是独有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列出了许多哲学与逻辑学的书单,供中央领导人们认真研读。其中《哲学研究》这个期刊,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青睐。他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们,人人都订上一本《哲学研究》。建国之后的毛泽东,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习哲学尤其是有关于逻辑学的知识,他深刻地意识到,逻辑学知识需要进行普及,逻辑学的研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需要继续发展。为了进行普及,并且理清楚中国逻辑学发展的情况,毛泽东下了一个决定:编辑出版有关逻辑和逻辑学方面的论文以及相关的著作。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7月以前就有过类似的想法。一次,毛泽东曾对周谷城说过:“ 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个系统的叙述。还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学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分丛书,在前面写上几向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出关于逻辑学方面的论文集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是个妥妥的行动派,1959年5月左右,毛泽东将这个问题正式纳入了议事日程。开始组织人力着手编印论文集和专著。从青年时期便对逻辑学感兴趣的毛泽东,在这次编辑出版时期,就更加注重各方面的意见,各种观点,以及关于逻辑学书籍的收集上。力求做到:做成一个一个相当于比较完善的丛书系列。出版后,毛泽东便一直将这套《逻辑丛刊物》放在身边。不过由于时代的限制,以及环境问题,毛泽东在建国以前只读过《穆勒名学》和《逻辑与逻辑学》,而他在这套《逻辑丛刊》出版之前,他只读过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为了再次出版这本书,章士钊还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书做了很多次的修改。毛泽东得知还为此还写信给予称赞。那么,毛泽东为何对他的这部书这么感兴趣呢?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逻辑指要》在中国近代逻辑研究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对于这一点,正如章士钊在为此书写的那个序言(未用)中所说:毛泽东“然相谓日:吾公见此书已,字不遗者阅通。 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伙矣,然大抵从西籍得来,不足称为专著,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指出《逻辑指要》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逻辑指要》“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以排,以成一学,蔚成一学,为此科开一生面”。(《逻辑指要》(自序)),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章士钊写作《逻辑指要》“志在灌输逻辑恒识取便广泛读者”。章谦称为国人讲逻辑,仅执翻译之劳。章士钊认为:“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此学宜当融贯中西,独树一帜”。(章士钊:《逻辑指要》<例言>)“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者,言也。其谓人不重逻辑之名,而即未解逻辑之理者,尤妄说也。且欧洲逻辑外籀部分,自亚里士多德以至17世纪,沉滞不进;内籀则里诸贤,未或道及。自培根著《新贝经》,此一部分渐开发,逻辑以有今日之仪容。然而,不难发现《逻辑指要》一书有些史料不乏牵强之处,但它另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晚清时节,西方的逻辑学对于中国人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20世纪10年代情况虽大有好转,但开设逻辑学课的却并非很多。至于20世纪40年代能够写出逻辑学专著的更是前无古人之举。而章土钊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无疑是一件空前的事情。当然,《逻辑指要》一书也并非十全十美,其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正如后来章士钊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但是,正如首先吃螃蟹的人是最勇敢的人一样,对于开拓的人也不应该求全责备。其二,从章士钊自身在逻辑学领域所有的经历看来,毛泽东看《逻辑指要》和选为逻辑学的“专著”之列也是当然的。章士钊在逻辑学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章士钊是国内最早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研究的人。1907年4月,他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后,他就用所得稿费离开日本,经上海前往英国,进入苏格兰大学攻读法政兼逻辑。“自是践履逻辑途径,步步深入,兴会亦相而高。那时出洋留学者,攻读逻辑的人是极少的。回国后,在北京大学(1917年秋推荐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以后),曾专任教授,讲授逻辑学。他在北京大学(主要是1918年)所讲授过的逻辑学,影响很大,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会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辑指要》即是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对于这段经历,章士钊在1939年5月12日为重庆版所写的《自序》中曾作记载:千九百十八年,余以此科都讲北京大学,时同僚陈独秀、陶孟辈,主学生自为笔录,不顾讲章,吾亦疏于记,逻辑未有专著。讲授名理,以墨辩也许正是由于章士钊在逻辑学领域的造诣和成绩,使他的这部著作在重庆出版之后被荐送到蒋介石处,于是蒋让章士钊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讲演,前前后后约一年光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部书是一部蒋介石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书。毛泽东对章士钊的这部《逻辑指要》的评价也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应该承认章的这部《逻辑指要》的价值是不应低估的。第一是它在中国关于逻辑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第二是在中国关于逻辑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作用。而这部书得以重版,应该说与毛泽东对该书的充分肯定和对章士钊的信任及他们之间“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
 藍鬍子
藍鬍子《何谓逻辑学》:有人认为逻辑学就是研究思维…
有人认为逻辑学就是研究思维的科学,我们没有学习逻辑学照样能够进行思考,所以学习逻辑学是没有必要的。其实不然,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习工作中,逻辑学无处不在,学习逻辑学非常有意义。
 固不及质
固不及质潘梓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诚捍卫者与无私奉献者
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他创办了《新华日报》被毛泽东称为“中共第一报人”他就是我校前身中原大学的校长潘梓年作为一名中南大人你对潘梓年的了解有多少呢?今天的这篇文章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冯颜利让我们跟随他的文字一起深入认识一下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卓越先驱个人简介潘梓年又名宰木、定思、弱水、任庵,1893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38年负责创办《新华日报》,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第一任学部副主任(主持学部常务工作),也是哲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筹备创办了学术杂志《哲学研究》。潘梓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是我党在新闻、教育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和卓越先驱,为推动哲学研究事业不遗余力,作出了杰出贡献。不同出版社出版的《逻辑与逻辑学》封面书影(资料图片)一片丹心: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从北京大学旁听生到一名共产党员。潘梓年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在父亲的私塾中学习“四书五经”。受辛亥革命影响,潘梓年对新知识和新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迫切想要外出求学,先后到上海的私立大同学校和龙门师范就读。但作为长子的家族责任感使潘梓年牺牲自己的前途,在读完书后回到家乡任教,一边照顾老人,一边为二弟潘菽挣取学费,使二弟有了读书的机会。1920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潘梓年通过半工半读的形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了三年的旁听生,主要攻读哲学、逻辑学和新文学,为后来的革命之路和学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开启了他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序幕。3年后,潘梓年被介绍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教书,他为学生作的新文学讲演深受欢迎,讲演稿被整理成册并出版,即后来的《文学概论》。1926年,在大革命的召唤下,潘梓年决心从北京奔赴广州直接参加革命,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和身体原因,遗憾未能如愿参与北伐。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毅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献身革命的精神开启了其一生忠诚为党的革命生涯。从普通的共产党员到顽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入党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潘梓年回到家乡宜兴任县教育局局长,暗中担任中共宜兴县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利用合法身份不断奔走于南京和宜兴之间,发起广泛的思想动员工作,为宜兴起义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1927年9月,潘梓年返回上海负责《北新》《洪荒》等进步刊物的主编工作,发表了多篇社论,为日后的办报办刊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在斗争中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自1929年到1933年,潘梓年在党的指示下多次易职,历任华南大学创办者、“社联”(社会科学联盟)负责人、“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真话报》总编辑。由于叛徒出卖,潘梓年和文学家丁玲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经历了特务们的辣椒水灌喉、电刑等多种严刑逼供,仍如“入定老僧”般泰然自若,对国民党蓄意散布的谣言置之不理,甚至写下了《咏雪》诗激励狱中难友坚定理想信念:“一片一片又一片,飞上河山皆不见;前消后继更凶猛,终把河山全改变。”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被囚4年有余的潘梓年才被营救出狱。狱中4年,他尽管身心饱受摧残,但仍然保持着积极的学习状态,撰写了三十多万字的《矛盾逻辑》(出版时改名为《逻辑与逻辑学》,1938年再版曾改名为《逻辑学与逻辑术》,后仍沿用原名),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潘梓年与艾思奇、李达等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普及、创新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共产主义战士到党在新闻、教育战线上的卓越先驱。潘梓年出狱后,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开始与章汉夫筹办《新华日报》,后经党中央批准被任命为新华日报社社长。《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从报纸筹办开始,他辗转南京、武汉、重庆等地,为争取出版和言论公开不断与国民党进行拼死斗争:在率领工作人员向重庆撤退时受日机袭击,他亲眼看到25名同伴不幸遇难,并饱受失去至亲胞弟之痛。在《新华日报》办刊的九年多时间里,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写下数百篇社论、短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纲领,广泛报道中国共产党在生产建设中的成就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革命中取得的赫赫战绩,深刻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出尔反尔的丑恶行径。在潘梓年的全力推动和努力下,《新华日报》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扩大统一战线的强大舆论宣传阵地,在战争年代教育了整整一代人。1948年12月,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停刊一年多之后被组织派往河南筹办中原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49年5月调到武汉,历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等职位。直到1954年,潘梓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建工作。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第一本哲学理论刊物《哲学研究》于1955年3月创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于同年6月和9月成立,潘梓年任学部副主任和哲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在担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的十多年里,除了行政工作和领导工作之外,仍尽心竭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传播,积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问题,撰写了《大家来学点儿哲学》《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最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专著。1958年,年近古稀的潘梓年不顾自身年事已高,与助手、研究生一道,赴郑州、开封、洛阳等市县郊区开展农村调查,历时长达两个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现实问题,正确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上下求索:勇于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潘梓年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之一,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创新、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国学界围绕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主张辩证逻辑是适应于更高社会形态的高等逻辑,形式逻辑是低等逻辑,辩证逻辑应该取代形式逻辑。早年间潘梓年在狱中拟定了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矛盾逻辑》一书,1937年出狱后“将私意轮廓写成一小册子发表”,命名为《逻辑与逻辑学》,意在解决和回答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此书是他一生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和逻辑学著作。潘梓年在此书中强调:“辩证唯物论是现代劳动阶级的哲学,它以改造自然存在,尤其是改造社会存在的各种实践为基础,同时也就以这些实践为归宿,看出了思维的真面目是通过行动去改造世界。”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思维不仅是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由此层层深入阐明辩证唯物论的真理性。在上篇“方法论(逻辑学)”中,他全面阐述了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以及辩证法中的几对范畴,包括本质与现象、根据与条件、必然性与偶然性、法则与因果性、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他认为应当“扬弃”形式逻辑,即并不是全盘否定并取代形式逻辑,而是将形式逻辑中有益之处挑拣出来,以技术的形式服务于辩证逻辑这一主体。这种“扬弃”的做法十分具有进步意义。此书出版不久便寄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此颇为赞赏,表示:“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九十三页,颇为新鲜。”这表明,潘梓年尽管将形式逻辑从“方法”降位为“技术”继而沿用,但仍然肯定了其价值及地位,在近代逻辑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看法是新颖独特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学术界的逻辑争论中,毛泽东同志多次赞赏学界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探索,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主从、高低之分。潘梓年在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上下求索过程中,为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梳理贡献了新的观点和智慧。《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为日后科学理解辩证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勇敢探索的重要学术成果,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此书是他独立思考和勇于开拓的结果,其表述精辟、观点新颖;其次,在抗日战争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苏联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思考对我国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辩证法如何引入中国国内”“如何引起大众的共鸣”是彼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和使命,此书是继艾思奇《大众哲学》(1936年)之后另一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著作,潘梓年在其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思想,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辩证法乃至运用辩证法解决现实问题;最后,此书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益探索,其中独特的观点和深刻的论证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使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道路。除此之外,潘梓年还发表了《关于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同一问题》(1941年)、《关于“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律》(1941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1943年)、《新哲学研究的方向》(1951年)、《否定之否定——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之一》(1956年)、《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方面对毛主席两类矛盾学说的一点体会》(1958年)、《大家来学点儿哲学》(1958年)、《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1959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演讲,深入浅出地阐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将手中的笔化作捍卫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学性的有力武器。在《新哲学研究的方向》一文中,他回答了“什么是哲学”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哲学是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思维科学的共同的规律总结起来,得出总的规律,而这总的规律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则。”在《关于“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律》一文中,他通过回顾恩格斯对量变质变的表述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抨击了“‘质量律’已经是落伍了的‘机械论’”的错误言论,重申量变与质变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辩证律对中国发展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潘梓年几经学术争论浪潮,始终坚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难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武器一一击碎意图动摇我党根基的错误思潮和不当言论,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与此同时不断向世人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和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潘梓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在1956年撰写了《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怎样进行研究》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把一切都当作发展过程来看待的,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对于人民还是有利的东西,还有它的积极作用的东西,我们就要发展它,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发展它,使它的积极作用获得充分的发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肯定了我国在过渡时期应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并且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包括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更进一步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中的不同经济成分不是杂凑在一起的混合体,而是按照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有机组织在一起的统一而完整的集体。除此之外,他认为复杂的经济基础将有复杂的上层建筑与之相对应,主张厘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1958年写作的《宏伟的远景规划,卓越的科学理论》一文中,潘梓年强调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两种优良作风,要求在实事求是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贯彻群众路线。潘梓年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独到看法,对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高度重视,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贡献的宝贵财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潘梓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注重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特别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发表论著。潘梓年尽管长年承担着极为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仍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了多部专著、多篇社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运用到中国革命及建设实际中来,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我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实践经验,是中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和回答中国问题的典范,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及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一方面,他在所发表的专著及论文中,十分注重将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例如,在《逻辑与逻辑学》中将唯物辩证法的论述与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相结合,通过总结提升自然科学的规律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本质及其规律;另一方面,潘梓年在行政工作中鼓励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融合,极力支持并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参加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与自然科学研究者结成学术联盟。第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具体的社会实践调查相结合。潘梓年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时,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既注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现实难题,又注重从现实调查中发现问题、从实践中检验理论成果。1958年,潘梓年率领一行人开展历时2个月的调查研究,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在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及方法,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术成果通过论文和报告的形式与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分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中,潘梓年虚怀若谷、谦逊恭谨的治学态度,也让人肃然起敬。潘梓年在1937年出版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中强调,“作者敢提出一己之见,就正于明达”“希望能引起一般人的讨论与批评,以求个人的进步”。在1961年再版时,他表示此书是匆促写成的,“至多只是敢想敢说的成果”“里面幼稚可笑之处甚多”,最后强调“敬请同志们鞭策”。这种治学态度始终贯穿着潘梓年的整个学术生涯,例如在《新哲学研究的方向》一文中,他两次表示:“我还没跟旁的朋友谈过,所以是个人的意见。”潘梓年这种谦逊恭谨的治学态度,展示了一代哲学宗师的大家风范。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潘梓年是一名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他穷其一生都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办报办刊的过程中,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身体力行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潘梓年通过畅通传播渠道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办报办刊方面,他一生创办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哲学研究》等一系列刊物,负责过《北新》《洪荒》《真话报》等刊物的主编工作,积极创建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渠道,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从而正确阐明中国共产党斗争的宗旨和目标,对抗歪曲事实、鼓动反动的思想观点,通过纸质媒介赢得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支持和拥护,团结一切可团结的群众,被誉为“中共第一报人”。第一,潘梓年明确了办刊的原则。一是党性原则。他曾提出:“党报要加强‘党性锻炼’。”只要是他经手的报刊,党性原则一直贯穿着办报办刊的整个过程,上至整个报刊的办刊宗旨、办刊方向,下至报刊刊登的每项内容、每则消息,都无一不体现着党的立场和使命,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二是以团结人民为己任。《新华日报》发刊词中庄严宣告:“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本报力求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报刊在他的领导下以团结人民为己任的决心和使命。在创办《哲学研究》杂志时,他一方面团结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组成刊物编委会,定期召开会议;另一方面重视各学科的建议,多次召开会议征求意见,将以团结人民为己任的决心和使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办报办刊中。第二,潘梓年创新了报刊管理方法。在《新华日报》办刊中提出“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口号,在纸张管理上精心改进技术工艺,提高纸张质量,使得刊物销量更多,从而提高了报刊的传播广度。总而言之,潘梓年在办报办刊期间,始终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使报刊杂志成为宣传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阵地,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在战争时期有效地引导了舆论方向,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巩固了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开辟了重要的舆论阵地。在教育教学方面,潘梓年曾历任县教育局局长、中原大学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位,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历,在教育界不留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更多青年学者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接班人。潘梓年在学术交流传播中从不以专家自居,也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总是谦虚地向别人请教。他每写一篇文章,都要向许多专家、学者征求意见,高度重视并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建议。在实际工作中,他经常主动向专家学者请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工作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认可。潘梓年还致力于培育新人。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认真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积极培育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锋力量,经常组织、主持各项学术讨论会,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开展对外交流。与此同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扶植群众性的哲学研究队伍,鼓励群众加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中来。正是因为潘梓年谦卑待人、团结众人,并致力于培育新人,使之成为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在他的影响下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深刻认识到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潘梓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内容上根据不同的行政岗位展现不同的侧重点。任报社社长时,他侧重从宣传的有效性出发,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具体的中国革命中,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抨击歪曲中国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当言论,或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及宗旨,受众群体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文章多数为报刊服务,篇幅较短,讲究时效性,重在宣传;任哲学研究所所长时,他侧重从教育的深刻性出发,将视野拓宽到提升全国哲学研究水平的高度,更加强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受众群体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外,还有大批专家、学者,文章讲究学术性,重在教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斗争中,潘梓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实践。回顾潘梓年的一生,他对党和国家赤胆忠心,“共产党员”这一称号是他至高无上的荣耀、重于泰山的责任。他用自己的矢志不渝和无私奉献,诠释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情怀和担当。他的战友石西民在1982年《学者与战士——回忆潘梓年同志》一文中谈及:“1966年初,有一次我到他家看望,他是那样恳挚地向我表示,很怕因为年老迟钝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而有违共产党员的称号。”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同时,应永远铭记这样一位终身为后人开山造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永葆初心,不负韶华!(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03月15日 15版)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娜塔莎
娜塔莎南哲研究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连发两篇文章
南哲新闻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陈佳与其导师潘天群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Studia Logica上连续发表两篇关于分歧主题的论文:“Logic for Describing Strong Belief Disagreement between Agents”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1225-017-9724-1“Logics for Moderate Belief-Disagreement Between Agents”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1225-018-9790-z其中第二篇论文为国际会议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gic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ame and Decision Theory (LOFT 12)的接受论文。这两篇论文分别描述了关于双主体间的温和信念分歧与强信念分歧的几种逻辑,构建了相应的公理系统并证明了其可靠性和完全性,讨论了信念分歧逻辑在哲学和博弈论上的应用。分歧是一个涉及到哲学(认识论)、逻辑学、博弈论等多个学科的热点话题,该论文的发表对于这些学科的发展有推动作用。Studia Logica由波兰科学院的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与斯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是著名的符号逻辑国际性期刊,为A&HCI(web of science艺术人文索引)来源期刊。编辑/段玉蕊
 瞳亮
瞳亮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
来源:科学大院(ID:kexuedayuan)作者:王贻芳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华为、阿里、腾讯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图片来源:央视、澎湃等网络截图)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耗时耗力研究基础科学真的值得吗?大院er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图片来源:必应图库)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本文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图片来源:veer图库)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 “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而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出现了几何学、逻辑学等科学,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发展出一整套科学体系。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西方的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基础科学水平提升 欧美国家的崛起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Tevatron粒子加速器(图片来源:必应图库)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图片来源:https://news.cnblogs.com/n/180532/)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给西方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西方的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目前,在我国社会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1. 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2. 中国古往今来的基础科学的水平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3. 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处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了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均衡支持基础研究 发展大科学装置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的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图片来源:人民网)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s://ke.sogou.com/v224241.htm)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建设中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1/420228.shtm)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图源片来:中青在线)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二十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
 对待
对待王贻芳院士: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
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华为、阿里、腾讯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图片来源:央视、澎湃等网络截图)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耗时耗力研究基础科学真的值得吗?大院er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图片来源:必应图库)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本文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图片来源:veer图库)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 “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而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出现了几何学、逻辑学等科学,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发展出一整套科学体系。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西方的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基础科学水平提升 欧美国家的崛起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Tevatron粒子加速器(图片来源:必应图库)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图片来源:https://news.cnblogs.com/n/180532/)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给西方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西方的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目前,在我国社会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1. 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2. 中国古往今来的基础科学的水平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3. 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处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了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均衡支持基础研究 发展大科学装置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的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图片来源:人民网)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s://ke.sogou.com/v224241.htm)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建设中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1/420228.shtm)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图源片来:中青在线)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二十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
 柏油路
柏油路在发展与繁荣之间
应用逻辑是与纯逻辑相对而言的。逻辑可以分为纯逻辑和应用逻辑两大类,前者研究的是只涉及形式的、抽象的推理结构;后者研究的是涉及实质内容的、某一特殊领域的推理结构。应用逻辑涉及的具体学科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验科学,甚至生活常识,是某一具体领域推理规律的系统化理论形式。应用逻辑逐渐兴起康德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最早提出“应用逻辑”一词,至20世纪初,应用逻辑研究始呈现规模性兴起趋势。此后,由于逻辑学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应用逻辑自20世纪80年代起获得了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相当有价值的应用逻辑论著,如彻尼沃斯基(J. C. Cherniavski)等人出版的系列丛书《计算机科学与应用逻辑进展》(Progress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ed Logic)、李未院士出版的《数学逻辑:信息科学的基础》(Mathematical Logic:Foundations for Information Science)和加贝(Gabbay)等人出版的《应用逻辑丛书》(Applied Logic Series),这些应用逻辑的代表著作得到广泛认可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应用逻辑在20世纪后期获得了迅速发展,充分重视应用逻辑研究已成为国际逻辑学界一个更加自觉的意识。《纯逻辑和应用逻辑年鉴》(Annals of Pure and Applied Logic)和《应用逻辑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Logic)先后创刊于1983年和2003年,每年都汇集、发表不少应用逻辑各领域的高质量论文。另外,加贝等逻辑学者编写出版了两卷本的《应用逻辑的数学问题:21世纪的逻辑》(Mathematical Problems from Applied Logic:Logics for the XXIst Century),由此书的标题我们不难看出应用逻辑在21世纪激动人心的宏伟前景。我国在应用逻辑研究方面业已取得不少成果,如胡泽洪编写的《逻辑:纯逻辑与应用逻辑》(1991)、张锦文编写的《数理和应用逻辑文集》(1992)、朱武编写的《论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秦豪编写的《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2004)、南旭耀编写的《法律应用逻辑教程》(2005)等,既有应用逻辑基本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有致力于应用逻辑理论体系的建设。近年来,我国的应用逻辑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张建军、杜国平等进一步探讨了应用逻辑的学科性质,杜国平主持的“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资助。邹崇理、刘奋荣、任晓明、周北海、徐明、唐晓嘉、黄华新、李小五、鞠实儿、赵希顺、何向东、潘天群、熊明辉等在自然语言逻辑、认知逻辑、归纳逻辑、人工智能逻辑、模态逻辑、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科学逻辑、法律逻辑等应用逻辑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果。此外,2009年6月在北京首次召开了应用逻辑学术研讨会,之后又于次年10月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应用逻辑专业委员会。可见,应用逻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此领域深入耕耘是大有作为的。 应用逻辑研究热点近年来,应用逻辑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应用逻辑前沿问题研究。近年来,应用逻辑涉及的前沿议题比较多,如量子逻辑、混合逻辑、范畴逻辑、逻辑和人工智能、动态逻辑、逻辑和认知、概率逻辑、逻辑和计算、自动推理、人工规范体系、逻辑和网络、神经系统等。可见,应用逻辑涉及的学科领域非常广泛,其发展也紧跟时代的脚步,并以贯通性、交叉性、综合性研究为特色。在新兴学科理论研究中,应用逻辑研究是不可缺少的。正如杜国平所说,“我们要抓住应用逻辑飞速发展的契机,积极开展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逻辑研究,特别是新兴学科的应用逻辑研究,实现我国的逻辑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认知逻辑研究。认知逻辑一直是国际应用逻辑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当信息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逻辑学者开始研究信息给我们的认知带来的变化,以及如何对此类现象进行逻辑的抽象刻画。动态认知逻辑、信念修正逻辑、偏好逻辑、不可能世界的认知状态、克里普克信念之谜等问题已经成为学者的研究热点。近年来,来自语言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们对认知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知逻辑已经成为一种方法论,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今天,随着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应用逻辑与认知逻辑不断相互影响和汇合,其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语言逻辑研究。语言逻辑是应用逻辑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逻辑研究领域发生了所谓的“动态转向”。这一逻辑立场认为,相对于静态地描述主体的认知状态,为了更好地描述知识和信息更新所引起的变化,我们需要动态地把行为变化等因素考虑进来。如动态认知逻辑就是认知逻辑和动态逻辑的融合,可以分析主体之间交往中的信息流动以及所引发的主体认知的变化。因此,相对于“静态”,“动态”可以更好地刻画信息的更新和认知的变化。大多数学者都支持自然语言研究的动态趋势,对自然语言动态性的研究构成了逻辑学家最感兴趣的挑战。拉兹洛·波罗斯(László Pólos)和迈克尔·马西(László Pólos)编辑出版了《应用逻辑:如何,什么和为什么:自然语言的逻辑方法》(Applied Logic: How, What and Why: Logical Approaches to Natural Language,1995),这是一本将动态语义学应用于新议题的论文选集。我国学者目前主要把研究重心聚焦于自然语言的范畴语法、蒙塔古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用逻辑和认知语用学等,以及结合人工智能研究自然语言论辩,这些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我国逻辑理论的范围,对应用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推动作用。应用逻辑研究前景展望应用逻辑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拓展,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亟待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尽管学界对应用逻辑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脉络有所论述,但是这些论述既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因而需要对应用逻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更加系统、科学的分析和考察,以为今后应用逻辑的学科建设奠定可靠基础。应用逻辑之所以得到如此广泛的研究,得益于它具有多方面的实际应用功能。这些应用不是局限于已有的逻辑方法,而是在逻辑理论和问题之间进行双向回应与调适,且最终可能会改变逻辑本身的面貌。各种形式的非标准逻辑,如模态逻辑、时间逻辑和直觉逻辑越来越受到关注,动态逻辑、非单调逻辑等也已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以一种简单而笼统的方式来阐释和处理问题。换言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用逻辑的研究更要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要在积极探索和启发借鉴中不断完善与超越。经过多年演化,应用逻辑研究已发展成为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合力攻关的研究领域,涉及数学、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杜国平对于应用逻辑的发展前景持有乐观态度,他认为:“应用逻辑已经成为逻辑学的研究主流,国内逻辑学界要着眼于未来,要关注国际应用逻辑研究的前沿问题,努力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毋庸置疑,应用逻辑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契机,当代中国逻辑学者对此应有所准备,并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积极推动应用逻辑的发展。比如搭建应用逻辑共享平台、建立应用逻辑网站、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或翻译先进的应用逻辑论文和著作等,争取在应用逻辑的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方面能有新的发现;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周易逻辑、墨家逻辑和道家逻辑等研究领域。由此可见,应用逻辑的发展、提升和创新前景是令人期待的,我国学者要把握机遇挑战、积极探索借鉴、敢于突破创新,努力攀登逻辑学研究的高峰,赋予新时代逻辑学更鲜明的特色。总而言之,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应用逻辑的发展也是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在庆祝首个“世界逻辑日”(Word Logic Day)时致辞说:“逻辑切实推动了思想变革,是许多创新的源泉,在当今21世纪,逻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切合时宜且不可或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14ZDB014)、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拔尖人才项目(BJ2019080)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孙雯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奥菲斯
奥菲斯明治人对逻辑学的期待
(图片来源:全景网)【文化好东西】对逻辑学的期待与命名“论理学”(Logic逻辑学)首先出现在日本,中国古汉语里虽有“论理”一词,但它并不意味“论理学”。如《史记·李斯列传》里有 “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这里说的“论理”,指辩论是非之理,具有辨理的意思,这一约定俗成的“定义”,在将“逻辑学”译成“论理学”时,虽然有时也会模糊译意,但日本人还是坚守了“论理学”之“论理”,与传统汉语之“论理”的不同立场,中国则将Logic译为“名学”。欧洲学术传统,非常重视Logic,日本人在翻译西学中意识到这一重要性,于是作为应对新时代学问的手段,日本人开始重视学习新Logic。西方逻辑学的日本导入者是西周,他把Logic翻译成“致知学”。“致知学”之源,始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而近代逻辑学作为应对新学问的方法论,西周又称之为“新格致学”。在其《百学连环》一书中,已出现穆勒的“SystemofLogic”(逻辑学体系),后来严复翻译为《穆勒名学》。西周在书中介绍了古希腊的七种学术:以往西洋之古,将学术分为七种科学 (SevenSciences),即Grammar(语法学)、Logic(致知学)、Rhetoric(文章学)、Arithmetics(算术)、Geometry(几何学)、Astronomy(量学)、Music(音乐学)。这七种科学,成为人们发现真理的手段。但怎样使用这些手段、为什么是这些手段,以及应该怎样发现这些手段,正是“新致知学”所探求的。如果把“新致知学”翻译成英语,西周认为应该是“AMethodoftheNewLogic”。“致知”一词,出自中国古籍《礼记·大学》,所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宋代学者朱熹在他的《大学章句》中,将“格物致知”活用于他的“穷理”之学。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句话竟然启发了西周,他把“格物学”想象成现代物理学(Physics),并使它与“致知学”成为一个对子。顺着西周这种直接比对的东方式思维,我们也会很自然地得出另一个对子,即出自《易经·系辞》篇的形而上下的对子,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许受此句启发,西周给予了具有形而上气质的Logic以“致知学”的名誉,同时将Physics(物理学)作为形而下之器予以“格物学”之名。西周在1861年(日本文久元年),为津田真道《性论理》一书作跋时,使用了“论理”一词,他将西方古典哲学一分为二,即“论理”与“论气”,恐怕是受宋儒主张的“理气二元论”的影响。“论理”为形而上者,“论气”为形而下者。津田真道的《性论理》,可说是日本最早的哲学读物。那时日本还未摆脱中国治学的传统,有关物性和心性的区别还未明朗。西周在此只能把关于物性的名之为“论气”,把关于心性的称为“论理”。1862年,江户幕府的洋书调所出版了《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其中收入以Logic为核心的“论理术”以及之后的“论理学”等词语。说起来,幕府的行动力也还算敏捷,洋书调所的前身,始于1855年在江户九段坂下创立的洋学所,1856年改称番书调所,至1862年改为洋书调所时,教授洋学,翻译洋书,兴旺如“幕府大学”。由于无限定的使用,“论理”一词泛滥,在江户末期被日本社会上下广为应用。西周在翻译Logic时,竟也不回避地使用了“论理学”,不过,他很快以“致知学”取代了“论理学”。无疑,构筑日本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人是西周。回顾初始,于筚路蓝缕之际,绞尽脑汁的首先是对Logic概念的翻译。1874年明治七年,他在写作关于论理学解说书时,仍以《致知启蒙》为题。同年,他寄稿给《明六社杂志》,题为“知说”,其中对“文学”的解释颇具逻辑学的意味,在这里,他赋予“文学”以修辞学或雄辩术的功能性品格。他使用了“Logic”一词解释“文学”,为了避免误解,并对“Logic”做了“致知学”的注释。《明六社杂志》时代,中村正直将Logic译为“明论之法”或“推论明理之学”。随后,中村正直将明治时代的新学问,分为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并以“无所争子”为笔名发文。把学问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大块的,还有梁启超。那已是1902年以后的事了。梁在《格致学沿革考略》的《导言》中说,“形而上”和“形而下”来自《周易·系辞传》,是有着很了不起的来历的词汇。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在宋代理学家程颐那里,已经发展为带有明显等级分别的“理气二元论”。“理”为“形而上”,“气”为“形而下”。江户时代,顺着理学思维的惯性,日本人也普遍认为欧洲学术为“形而下”之物,相反,亚洲学问则为“形而上”。当然,今天作为常识,形而上学指Metaphysics,而形而下学指Physicalscience,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同。Logic以“论理学”之名进入学校教育,始于明治文部省。明治初期,在人们对“科学”的渴望与学习中,意识到新论理学作为思想方法的无可取代性,日本人还将“论理学”比喻横卧在科学根底的基础学科,并对“论理学”给予了非常的期待。“演绎”与“归纳”在整个明治时代,西周几乎是所有领域执先鞭的先觉者。同样,作为论理学的基础概念,如“演绎”、“归纳”,也是西周创造的日本新汉语。首先,他将穆勒的“新论理学”命名为“新致知学”。他说:“新致知学,原义为AMethodofNewLogic,由一名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英国人所发明,他著述的SystemofLogic,是个大部头。这一方法论的出现,是对学术领域的大大改革。”那么改革之法是什么呢?曰in-ction(归纳之法)。而欲知此归纳之法,则必先知dection(演绎之法);什么是演绎法?所谓演绎犹如字义,演为陈述之义,绎为找到线头引出丝线。再譬之为猫吃鼠,先从头部开始——大前提,然后次第于胴体、四足——小前提,及于鼠尾——结论。总之,从所重之所开始,引出种种道理,即是猫吃鼠的演绎法;什么又是归纳法?Inction,即归纳之法,与演绎相反,譬之人吃佳肴,一点点地品其美味儿,最终所食殆尽。如此,从小的真理出发,涉猎所有,由外而集聚于内。要想了解此归纳之法,不可不知真理无二,大凡宇宙间的真理不存在有二之事;什么是“致知学”?兹有subjective(此观)和objective(彼观),两个概念彼此相关。所谓此观,并非就物而论,而是独居个体的立场,去探求真理的主观意志。所谓彼观,是指根据客观事物而研究其理。大凡学问皆与此二观相关,无外于此。“致知学”,即此观,是思考还未及观察事物之前的先验之理,此观皆由语言中来。西周把subjective译成“此观”、ob-jective译成“彼观”,但他意不在“此观”,也不在“彼观”,而是用这两个概念解释“致知学”,同时还创造了“主位”、“属位”的译语。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哲学字汇》中,将subjective译作“主观”、objective译作“客观”,西周并未使用“主观”和“客观”概念。对于学术用语规范化,明治时期的知识人如同大渡海一样各显神通,不过,说西周的贡献最大并不为过。《百学连环》中,他规范了“演绎”、“归纳”并奠定了论理学的其他相关基本用语,强调只有以“归纳”(inction)的推论方法,沿着穆勒提示的新方向,今后的学问必定能深入下去。唯有in-ction的方向,才是逼近onlytruth(真理无二)的方法。“演绎”一词,古汉语有用例。朱熹《中庸章句》序:“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昭后之学者。”宋学教养深厚的西周,也许忽然记起年轻时学习《中庸章句》,朱熹的“演绎”一词给了他灵感,用来作为dection的译语。朱熹“演绎”,是以古之尧舜之道与今之父师之言为前提进行推导,西周据此发展一下,的确与dection相称。“归纳”在中国古典里却不曾见过,无论《佩文韵府》,还是《大汉和辞典》均不见载,恐怕是西周造语。西周在写作《百学连环觉书》时,特别留下了备忘录,并以“觉书”为《百学连环》全集冠名,宣喻该书是一名觉者所作的“觉书”。谈到“归纳法”时,他说:归纳乃引类入一而求其同一之法。“演绎”与“归纳”作为近世学术的研究方法,西周已经运用自如。他在寄给《明六社杂志》的“知说”中说到:此二法术之差,演绎法如富豪之子弟费资本金,归纳法如贫人之子蓄资本金。演绎法,譬如限定百万两资本金,将它分配至各自应用领域承担费用。演绎以至高至善之原理,并将此一原理推广为万事万物。因此,其原理若至善,就会至当,苟若有谬,则致毫厘有千里之误,譬若百万资金投资不当,付之东流。归纳法,譬如一钱两钱之积攒,日蓄月累,终致巨万之资。由层层积累的过程得一贯之真理,如贫人亦可得富资,积累深厚而发明新真理。将事实归纳为一贯之真理,又将这一揭示真理的逻辑过程,构成一种显著的范式,才可称之为学;再因这一门学问使真理了然普及并活用以方便人间万般事物,方可称之为术。西周在穆勒“新致知学”中看到了“归纳法”的方向。他断言,“归纳法”才是最迫近“学”的推论方法,由“归纳法”也才有可能获得“一贯之真理”。中国学者译介西学穆勒 (JohnStuartMill1806-1873),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根据经验论完成了“归纳法”,是实证社会科学理论的奠基人,著有《自由论》(OnLiberty)。日本明治时代学者中村正直于1872年明治四年翻译为《自由之理》刊行。严复于1903年将穆勒的《论理学》译为《穆勒名学》、《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出版。严复在译介西学时所历的种种艰难,他能与日本启蒙学者共鸣的,皆因重新造种的使命感。日本语的“论理学”或“致知学”,在中国被称作“名学”,或音译“逻辑”、“络集克”,严复在《穆勒名学》引论中提到了“逻辑”是Logic的音译。在他将穆勒的Systemoflogic译为《穆勒名学》之后,1909年又将耶方斯 (William StanleyJevons,1835-1882,为19世纪英国经济学、逻辑学者)的PrimerofLogic(《逻辑学入门》)译成《名学浅说》出版,成为中国最早的逻辑学教材。严复从《天演论》开始,就将Logic译作“名学”或“名理”。1901年《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除了沿用“名学”、“名理”之外,还使用了“洛集克”音译语。“名学”、“名理”之“名”,是中国战国诸子百家之一的名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名家”擅长论理,以概念论辩闻名于世,惠施和公孙龙为代表,有智者风范,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学派。著名命题有“白马非马论”和“坚石非石论”。可见,严复以“名”冠之的来历与出处,来源于先秦诸子的形名之学,显然,严复比西周更懂得中国古典,当西周还在从宋代理学寻找解读西方逻辑的语词时,晚于西周的严复已深入到中国名学的根底,用中国传统名学来解读西方逻辑,这是严复比西周的深刻的地方。但是这种深刻性,也带有某种局限性,沉浸于文明传统而生成的无比自豪感的中国人,势必不能简单地抛弃其传统性,因此,在翻译穆勒的逻辑学著作之际,严复几乎无法拒绝中国名学的传统魅力。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重镇,除严复外,当然不能忘记康有为和梁启超。关于逻辑学,此二人似乎也并非随意使用日语的“论理学”译词。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尚未找出“论理学”的蛛丝马迹。梁启超提到过“论理”,但是此“论理”非彼“论理”,它与中国古典用例一样,是“论理”,但并不意味Logic。如梁启超在《清议报》发文,“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其中有一句“今且不论理而专论势。”当日本人看到“论理”文字时,轻而易举就理解成推理、论证之理,或是思考的法则。中国人直觉则必然是关于“理学”之论,而“理学”一词,自宋学以来有着顽固的传统。因此,“理学”之“理”作为另一种立场的词汇,一旦遭遇具有逻辑学意味的、日本新汉语“论理”一词,就会产生很大的抵触。宋代“理学”是一个有着怎样传统的词汇呢?要而言之,如日本人常言的“万有哲学”,就是中国的“理学”。“理”在中国,它包括人伦之理、自然社会之理、宇宙万物之理等等,所有都在一“理”中。不过,日本人没有这一庞大沉重的传统,可以很轻松地把“理”作为“理论”之理来理解,于是使用“论理学”这一词汇翻译逻辑学,便不会有拖泥带水的纠结感。而在中国,“理”则带着传统训诫的权威悬垂于众人思维之上,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不那么能容易诞生与其传统性相异的另一个世界的“论理学”一词。现代之中国怎样呢?作为逻辑学的学术规范用语,“名学”与“名理”被逐渐淘汰,相应的,从论理学到逻辑学则开始普及,表明逻辑学的确带来了新思维的出现。如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严译名著丛刊》的《天演论》,就为Logic译语的“名学”特别作了注释:“名学”即“一名论理学、一名逻辑学”。《原富》一书也为Logic译语“名理之学”特别作注为“论理学或逻辑学”。1902年,亦即光绪28年、明治35年前后,大量的日本学术书籍被翻译到中国,日本学术用语多半原封不动地传播到中国,成为此后中国学术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关“论理学”的日本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是富山房、范迪吉等译的《论理学问答》,由上海会文学社出版,据云从此“论理学”之日本语,取代“名学”、“名理”而广为中国学术界通用。关于“命题”一词,古汉语中很难找出使用的例子,因此,可以说这个词是日本人的造语。将它作为论理学的用语,则是出自西周的苦思冥想。西周将proposition翻译为“命题”,严复则译成“词”。如今,“命题”一词在中国普及;严译universalproposition为“全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为“全称命题”;又,关于particularproposition,严译“偏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为“特称命题”;而indefinitiveproposition一词,严译“诨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不定称命题”;严译singularproposition为“独谓之词”,同上书卷末注“单称命题”。如此繁复注释案例,显示了中国商务印书时代关于逻辑学的译介用语,基本采用了日本语的译法。1881年明治十四年出版的《哲学字汇》中,已经收入与“论理学”相关的译语有:Proposition命题、Universal全称、Particular特称、Indefinite不定、Sin-gular单称。这些译语在日本诞生,以此而明。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及观西人之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途术也。”这里使用的“内籀”相当于日本译语的“归纳”,“外籀”相当于日本译语的“演绎”。“内籀”是严复翻译inction的译语,“外籀”是de-ction的译语。两者在《穆勒名学》与《原富》中,均有卷末注释,今译为“归纳”与“演绎”。“内籀”与“外籀”在当时也是颇具影响的名译,但还是因晦涩费解而被淘汰,而日译“归纳”以及“演绎”则广为普及。梁启超在文章中使用的是“归纳”与“演绎”,而不是“内籀”与“外籀”。“演绎”是中国古典词汇,梁启超用起来或许比较容易,此不列举。至于“归纳”一词,则创自日本语,梁启超应用起来也得心应手,他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说:“欧洲自希腊、罗马以来,即有民选代议之政体,而我中国绝无闻焉。此又其最疑之点而绝奇之事也。中国之无此政体何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也。民何以不求自伸其权?不见他人之权,故不求也。因一统闭关之故也。不知己之失权,故不求也。因无阶级自安之故也。故吾仍以归纳之于前两者之一点也。”可以说将“归纳”与“演绎”之日本新汉语传达到中国的,仍然是梁启超。其实,有关西方逻辑学的知识,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大部分来自于英国19世纪最有影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著Asystemoflogic的启蒙,这部“逻辑学体系”为新时代东方学术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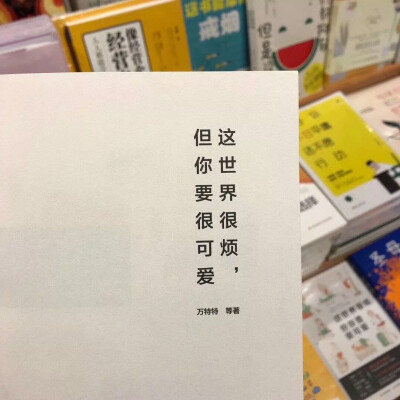 鬼磨坊
鬼磨坊他大三时证明了西塔潘猜想,获得了100万奖金,后破格成为985教授
大学可以说是我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阶段之一,对我们的一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大学期间,我们开始渐渐变得懂事,开始学会独立,开始慢慢接触社会,不少人就是在大学期间迅速成长起来的,也有很多人大学期间在自己的领域崭露头角。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一位在大学期间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学生,他在大三的时候破解了一道困扰数学家们多年的世界难题。刘路是一名毕业于中南大学数学科学与计算技术学院的学生,中南大学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是一所以工学和医学为特长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位列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中南大学在国内的排名也非常靠前,在985院校中都能排在中游位置。中南大学还入选了一系列重点教育培养计划,是中国百强企业最欢迎的10所大学之一。刘路作为中南大学数学科学与计算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成绩自然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刘路在大三的时候,还做了一件轰动了半个数学圈的事情——证明西塔潘猜想。西塔潘猜想是由英国数理逻辑学家西塔潘于上个世纪提出的一个反推数学领域关于拉姆齐二染色定理证明强度的猜想,这一猜想在提出之后立即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困扰了数学家们十多年之久。据了解,刘路在大学的时候就对数学非常感兴趣,他在学校的时候经常去图书馆借阅相关的数学书籍,常常看到深夜。在大二的时候,刘路就开始学习数理逻辑,他对数理逻辑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路在学习自学反推数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西塔潘猜想,刘路当即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在接触到问题两个月后的一天,刘路突然想到利用之前的一个方法稍作修改便可以证明这一结论,于是他连夜将这一证明写了出来,并用名“刘嘉忆”将证明过程投给了数理逻辑国际权威杂志《符号逻辑杂志》。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时任《符号逻辑杂志》编辑的汉斯杰弗德看到了刘路的论文,他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而感到高兴,亲自写信向刘路表示祝贺。后来,还是大三学生的刘路受邀参加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逻辑学术会议,在会议上,刘路报告了他对目前反推数学中的拉姆齐二染色定理的证明论强度的研究,刘路的报告给了这一难题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也标志着西塔潘猜想的彻底解决。后来,刘路又作为亚洲高校的唯一代表参加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理逻辑学术会议,在会议上作了40分钟的报告。在被证实解决了西塔潘猜想后,刘路成为了国内数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中南大学颁发给刘路100万元的奖励,同时,为了让刘路尽快进入相关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中南大学决定让刘路提前毕业,并破格聘任再度的刘路为中南大学正教授级研究员。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年仅23岁的刘路与各领域的精英一起摘取了凤凰卫视授予的“影响世界华人”奖杯。对于解答西塔潘猜想的过程,刘路本人则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过程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像是灵光一现。其实,在小编看来,所谓的灵光一现或许是平常积累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要注意平时的积累,很多时候看似突然而来的灵感其实是一种厚积薄发。网友们,你们怎么看待刘路解决西塔潘猜想的事情?欢迎在文章下方留言讨论!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