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瓜祭
瓜祭杭州一所新学校招老师 剑桥博士来了好几个
2018-01-23 07:21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梁建伟“又来了一位,而且非常优秀,基本上能确定下来,这个人我们要定了。”前两天,杭州育海外国语学校的学术指导周凡之对记者说,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女孩通过了试讲,马上就将成为学校的一名美术老师。再早些时候,该校初中部刚招进两名英语老师,也都有国外名校背景。而周凡之本人,就是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是一位心理学专家。作为一所去年才开办的民办学校,杭州育海外国语学校的老师中,有海外求学经历的已经占到了约三分之一,其中有两个是剑桥大学的博士。“这些海归老师绝大多数毕业于名校,大部分是硕士学位,有些还是双硕士。”周凡之说,包括她自己在内,几乎是“毫不犹豫就选择当了老师”。寒窗苦读十数载,好不容易在海外名校拿到了博士、硕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为什么甘愿当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呢?温州小伙放弃剑桥在读博士回杭州当了一名小学英语老师小练是去年3月份到杭州育海外国语学校当初中英语老师的。这个来自温州的帅小伙,头上顶着两个惹眼的硕士学位:伦敦大学东亚研究专业硕士,剑桥大学历史专业硕士。实际上,在决定回国前,他甚至在剑桥读了一年的博士。为什么要回来当老师?因为没有申请到奖学金。“这个博士我以后还会回去读的,不过那得等积累了一些经济基础。”小练对记者说,“在英国,攻读文科博士耗时较长,起码要5到7年,如果是工科博士,相对会快一些。”这么长时间在英国读书,没有奖学金,没有收入来源,经济压力会非常大。其实,回国后,毕竟履历摆在那里,小练的就业机会挺多。“有所高校邀请我去教书,我考虑再三拒绝了。”小练说,除了大学老师工资相对较低,他还嫌评职称太麻烦。在大学任教,职称往往和收入、地位挂勾。“我对评职称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如果进了大学,就不可能绕过去。”小练选择当一名初中老师,主要是从兴趣出发,他喜欢这一行,想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这种兴趣,在大学时就开始了。在国内读本科时,他给一些孩子做家教,学生的英语成绩上升非常快,让他颇有成就感。到英国后,他又给老外教中文,算是从教经验丰富。在杭州当上老师后,学校交给小练一个任务,和一些同样有海外求学经历的老师一起,研发国际课程。“素质教育不等于不考试,但素质教育需要提供给学生更多动手操作、体验社会的课程,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小伙子说。她在英国拿了双硕士还考出了注册会计师证小王也是一位海归,2013年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应用语言学硕士毕业,她还有一个该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学位。而且,在英国期间,她还考出了十分难考的皇家注册会计师证。有这么亮眼的简历,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当一名英语老师呢?小王毕业后,在英国留校工作了两年,专门负责给海外留学生审核材料、注册等。回国后,她又到一家知名培训机构教了两年英语。去年考出教师资格证,小王毫不犹豫到杭州育海应聘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其实,在培训机构教书收入并不低,每年有20多万元。“我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是从小的热爱。”小王说,她的外公就是当老师的。“从小我就觉得这个职业特别崇高,长大后当一名老师的想法就更清晰了。”自从当上“正规”的老师,收入虽然比以前少了些,但成就感、幸福感却强多了。“培训机构的学生流动性大,课程周期短,跟学生还没混熟,新面孔就来了。在学校当老师就不同啦,每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学生从一个单词都不会说,到后来能简单地对话,说一长串的句子,我就非常开心。”当光环不再耀眼海归们择业更趋理性在杭州育海外国语学校负责老师招聘的周凡之,自己就是一名海归。她在英国整整待了12年,从高中一直读到剑桥大学的博士,是一位心理学专家。“这些年,海外学成后选择回国的人越来越多。实际上,有些海归不一定比国内院校的毕业生优秀。”周凡之说,“海归派的光环不再那么耀眼了,他们回国后在择业时也变得越来越理性。”周凡之说,她所在的学校今年招聘老师,一共收到近千份简历,经过一轮筛选后,剩下的重点考察对象,有三分之一有海外求学背景。那么,海归派在向学校求职时,有没有什么优势呢?“主要是在英语方面,毕竟都在海外待过一段时间,口语的纯正度肯定比国内毕业的要好。”周凡之说,不过,学校选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求职者是否适合当老师。如果求职者履历再漂亮,不适合当老师,学校也不会要的。“前几天刚面试一位女老师,是国内大学毕业的,后来去英国一所小学当了一年的汉语老师,英语口语非常好。虽然没有国外大学学历,但我们当即决定要她。”【浙江新闻+】中国正迎最大规模“海归潮”据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中国政府支持创新创业力度空前,越来越多海外留学人员选择“海归”。10年前,中国每送出3个人出国留学,只能迎回1人;如今,出国与回国人数比例已从2006年的3.15∶1下降到2015年的1.28∶1,且呈现人才加速回流态势。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回流占比明显提升,中国正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1978-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处于学习研究阶段,221.86万人选择学成回国,学成回国学生占已完成学业学生群体的79.87%。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2015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达40.91万,较2014年增加4.43万,增幅为12.14%。而2016年,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增幅明显。有报道说,“海归潮”的到来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狂风沙
狂风沙扒一扒新冠病毒家族的“子子孙孙”,英国这项研究信息量不小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卞英豪当地时间4月9日,英国剑桥大学在其官网公布了一项关于新冠病毒研究。研究显示,目前,新冠病毒已在全球变异成3种毒株。最接近于蝙蝠身上的“原始病毒”,主要出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患者,在中国武汉流行的则是其另一类变种。新冠病毒已变异成3种不同毒株?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了解到,该项研究使用的新冠病毒数据,来自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从世界各地采集的病毒样本。报告中,研究人员将与新冠病毒的同源性高达96.2%的蝙蝠冠状病毒,设定为新冠病毒的“原始版”。该病毒即中国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团队发现的BatCovRaTG13病毒,也是目前所公认的同源性最高的,宿主为动物的病毒之一。根据以上数据,研究人员按照病毒进化的关系,将目前全球传播的新冠病毒分为了A、B、C三个类型。A类,即在人类身上传播的新冠病毒的“原始”类型,从遗传学角度,A类也最接近动物宿主体发现的病毒。 B类,则是从A类变异而来,相比A类病毒,其序列已在多处发生了变异。 C类,科研人员将其称为“B类病毒的子女”,其源自B类病毒。但与B类病毒相比,也已是一个不同的变种。 研究称,A、B、C三类新冠病毒是三个截然不同,但密切相关的变体。 三类病毒如何进行传播?那么,这三类病毒的传播情况究竟如何?数据显示,在该研究选取的160例确诊病例病毒样本中,A类病毒共33例,B类共93例,C类共34例。 研究指出,最接近动物体内病毒的A类病毒,更多地发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病例,而不是中国武汉。33例A类病毒样本中,至少有15例来自东亚以外的地区。在中国,也发现了少量的A型病毒,包括5名武汉病例和4名广东病例。然而,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传播更广泛的是B类病毒。在武汉就至少有19例B类病毒。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广泛流行的均为B类病毒。研究人员称,B类病毒此前的主要传播范围为东亚地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变异,新冠病毒不太可能在东亚以外的地方大规模传播。然而不幸的是,B类病毒变异成了C类病毒。而C类病毒主要流行于欧洲。在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等地的患者中均发现了C类病毒。但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大陆并发现C类病毒。研究分析称,在C类病毒肆虐最严重的意大利,病毒进入该国的途径之一,是1月27日通过首例记录在案的德国患者感染。而另一条早期的意大利感染途径,则与“新加坡聚集性病例”有关。图:3种不同类型的新冠病毒的传播情况 制图 刘嘉仪这是一篇什么样的论文? 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全球顶尖科学家在不同平台发布了难以计数的论文。那么,这篇研究又是什么来头?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了解到,剑桥大学官网公布的这份研究报告,源自该校科研专家彼得·福斯特博士(Peter Forster)和德国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论文题目中文译为《新冠病毒的变种分析》。据悉,该论文已刊载于《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这一份是与Nature、Science齐名的全球著名科学类期刊,也是当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学科文献之一。论文的第一作者,正是来自剑桥大学的英国遗传学家福斯特。 值得一提的是,3月中下旬,剑桥大学已和“英国新冠肺炎基因组学联盟”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工作。据英国媒体报道,确诊新冠肺炎病患的病毒样本,将被送往“测序中心”,该网络目前囊括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在内的13所大学。剑桥大学在其官网表示,其正在进行的全基因组测序,包括读取病毒的完整遗传密码,研究病毒基因组,这将协助科学家更好更快地了解病毒的传播方式,变化情况,帮助改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 不难看出,无论是从专业性还是针对性的角度出发,这项研究均具有相当的可讨论性。论文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论文的第一作者英国专家福斯特在文中指出,该研究旨在通过对新冠病毒的基因进行分析,以求解开病毒变异的密码,同时找到病毒在全球扩散的路径。从论文的结果中不难发现,最接近原始病毒的A类病毒,在中国出现过,但并没有在中国大规模流传。在武汉等地广泛传播的则是“原始病毒”的变种B类病毒。从该研究结果来看,“原始病毒”真正扩散的地区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而目前欧洲地区备受折磨的病毒中,有一部分已变异成C类病毒。相较A类病毒,C类病毒已完成多次“进化”。 那么,这样的结论与全球争论病毒“发源地”问题有何关系?福斯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仍无法就病毒的来源地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其研究发现,新冠病毒最初感染人类的时间大致在2019年9月13日至2019年12月7日这个区间。福斯特表示,A类病毒之所以没有在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城市内大范围出现,可能是因为A类病毒并不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也因此变异成了B类。同样的道理,A类更多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可能也是因为A类更适应这一群体的免疫系统。此前,福斯特在剑桥大学官方网站表示,病毒有太多的快速突变,无法完整地追踪病毒全部的家谱。简言之,新冠病毒变异而来的“子子孙孙”,暂时仍然无法一一追溯。福斯特提醒,目前,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快速变异,以适应不同人群中的免疫系统抵抗力,各方必须加以警惕。
 名士
名士剑桥大学新冠病毒变种报告作者:武汉首被发现的B型病毒非原始病毒
04:304月8日,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发表文章“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论文由来自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第一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日前,CGTN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就研究内容进行了解答。↓↓↓福斯特介绍,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原始病毒类型”。因为有太多的快速突变,传统手段很难清晰地追踪COVID-19家族树,研究人员专门使用了一种“数学网络算法”技术。此前,该技术主要用于分析DNA以绘制史前人类种群活动图。这是其第一次被用来追踪冠状病毒的感染途径。研究人员分析了自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160个新冠病毒(SARS-Cov-2)基因组的数据,发现了三个主要SARS-Cov-2变体,并根据氨基酸变化不同将其命名为A、B和C型。其中A型病毒与蝙蝠及穿山甲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最为接近,为原始病毒类型,B型衍生自A型,C型衍生自B型。此外,三类变体在全球的分布范围不同,差异极大。A和C型多发现于欧洲人和美国人中,B型是东亚最常见的类型。福斯特说,在武汉疫情明显时首先被发现的一个基因组是B型病毒。研究人员当时误以为B型是原始病毒,但事实并非如此,A型才是原始病毒,当时在武汉只是少数,不过B型之后成了武汉疫情暴发期间的主要病毒类,并且进一步突变为C型。研究发现,感染A型的样本将近一半来自东亚以外地区,主要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且三分之二美国样本感染的是A型。此外,A型虽然最早出现在武汉,但武汉只有极少的感染病例。有些曾在武汉生活过的美国人被发现携带A型病毒基因组。而B型主要分布于中国及东亚地区,亚洲以外的B型基因组都发生了突变。C型是在欧洲传播的主要病毒类型,在美国和巴西也都有发现;但在中国大陆的感染样本中未被发现,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皆有分布。福斯特表示,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的首例感染病例可能是由蝙蝠传到人,并发生在2019年9月13日到12月7日之间。因此2019年12月24日从武汉采样的病毒基因组根本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疾病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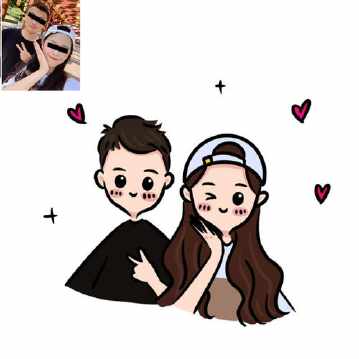 唐
唐如何评价剑桥大学研究称新冠病毒分三个变种?
剑桥大学4月9日发表关于新冠病毒的几个变种和传播路径的研究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分为A、B、C三个变种,而不少人据此推出了一系列阴谋论。我觉得有点过早了。因为,这个结论,上个月,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就发表过这个结论了。写在篇前的话0,数量不代表起源有个很大的歧义点,一些人一看到A型更古老,且美国更多,就直接像打鸡血了。数量多,更多的是传播问题。你们还记得把病毒分为S和L型的NSR文章没?S型古老,L型年轻,结果在武汉L型占了96%多,而其原因在于L型更具有侵略性。而作者对于哪型在哪个区域更多也指出了,这是进化选择的结果,不同类型适合不同的宿主。These genome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under evolutionary selection in their human hosts, sometimes with parallel evolution events, that is, the same virus mutation emerges in two different human hosts1、这篇文章最大的亮点是算法上,用了人类学里的算法去尝试病毒。毕竟论文的主要贡献者就是那个唯一不是foster的人目前兴趣之一是人类学。通过新的算法发现了病毒的平行进化现象(parallel evolution),也就是病毒的不同类型适合不同的人群,A类型适合北美,B类型适合东亚。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和病毒的奠基者效应(所谓奠基者就是后代群体的样子很大程度取决于祖先)2、病毒多样化和病毒源头是两码事。很多时候我们容易产生一种看法,就是你看xx地方的多样性更高,那么它就更可能是起源。包括之前的那个广为流传的某视频。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简单直白的, 美国的族群规模复杂程度很高,但是你肯定不认为美国是人类起源吧?同样,数量最多也不能代表源头。3,文章使用的参考基因组依然是最早发布的武汉测序的那一个这一点倒是业内通用的,毕竟第一条上传的序列,往往会被当做参考序列,剩下的序列会和它比。The sequence range under consideration is 56 to 29,797, with nucleotide position (np) numbering according to the Wuhan 1 reference sequence这里其实有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事实上默认了这个早了,后面的所有病毒都是由这个变异来的,但是有的时候,或许换个参考,或许不一样,不过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蝙蝠的序列。所以,如果能够找到更古老的病毒序列,甚至直接找到个可以把现在病毒都当做姊妹群的病毒,或许整个状况都要被改写,毕竟根序列变了,那很多东西都要变。4,还是一个样本规模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讨论过很多了,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分析,全是依赖于最开始的那一波数据,然而我们都知道,那一波数据是有源头性问题的,因为我们直接默认了华南海鲜市场,而后来证实,华南海鲜市场并非最早起源,顶多是个爆发点事实上,理论上,如果我们对武汉当地的病毒进行更多的全基因组测序,或许发现更多精彩的东西,不过我们早就停下来了,毕竟这东西做了对抗疫也没啥用,还花钱贻人口实,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哈哈。5,文中看了会有不少可能很多读者会直接想说“你行你上”的内容。首先我是不太认可“你行你上”这种理论,否则论坛有啥存在意义呢?直接崇拜权威罢了,其次PNAS这个期刊一直有个备受诟病的问题就是,如果它本身是美国科学院院刊,你只要是院士,哪怕你在上面夸师母,一样可以发表(有没有想到冰川冻土哈哈?),这就是院士特权,特征之一就是写的contribute。包括当年venter写的用基因算长相被science 拒掉的时候,他也动用了这个权利把文章丢到了pnas上,然后那个science评委(当然也是大牛Yaniv Erlich)还很愤怒的和venter两人大战300回合(当然结果就是每人都发了一堆文章~毕竟大牛打架都是要用论文的哈哈哈)事实上,关于这篇文章,砖头早就飞了。比如Andrew Rambaut,进化领域的超级巨佬就指出文章有严重错误。微博上一些相关领域人士的评价polyhedron,复旦的严实博士,做分子人类学的。fengfeixue0219,中科院的郗旺 ,也就是飞雪之灵,做植物分子遗传的————正文部分————首先,当我看到这篇论文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这又充值了。因为当时一看作者,4个作者,3个foster,这就是一家子发论文,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可能是水文。而且还真的不是我随便说的,1和4是亲兄弟哦,据说2是1的老婆~真是foster承包了好吧,唯一例外的是第三个,但是更是让我惊呆了,因为这个人是整个论文的主要推动者一看到contributed,我瞬间就明白了,这群院士又开始水了,这个院士是做啥的呢?答案是考古学研究欧洲史前内容,比如希腊基克拉迪群岛的史前历史,基克拉迪文化与东南欧和西南欧的关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传播等等,当然后期对分子人类学感兴趣。特别说明:我对colin Renfrew是没有意见的,人家是考古学的顶级专家,能够当院士,肯定是实力超群PNAS是美国科学院院刊,他的文章有两种,一种是认真submit的文章,一种就是contribute,后者的文章,就是哪怕你去写一篇夸师娘,只要你是院士,也可以发表出来。所以pnas影响因子不高,备受诟病,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些院士去contribute了,院士们有优先发表且不受限制的权利。特别说明:并非所有的contribute都是水文,但是在pnas里,contribute水文比例的确很高。好吧, 不管怎么说,虽然心里预期自己又要看一篇渣文了,但是还是咬着牙看下去,万一有惊喜呢。结果从头看到尾,最后证明,我还是想多了,真的没惊喜。全文核心就是这张图(是的,其他图是附件的图)给大家瞅一眼全文,3页就是大家熟悉的进化树,长的表示进化距离远,短的表示进化距离近。仔细一看,这图早就看了很多次了,就比如大家熟悉的这张图。本质上都一样。很古老的祖宗bat,然后就是武汉的病毒。然后继续分为ABC。A是从武汉回去的美国人,B是武汉型,C是欧洲型。这东西老早就知道了,为啥他们还是重复一遍呢?我就去看了下数据来源we here present a phylogenetic network of 160 largely complete SARS-Cov-2 genomes160?怪哉,都是来自GISAID database,的确少了,咋还是160个数据呢?为啥不多点?注:文章写的时候是4 March 2020,投稿是March 17, 2020,发出来是昨天,但是那个时候其实gisaid数据已经不少了。作者也说了,3月4号的时候都已经有254 coronavirus genomes了。不过reviewer真的是太好了,我最近就碰到了一个认(bian)真(tai)审稿人,让我用他的建议重新计算了一次三代基因组,然后一个小修折腾了3个月了(中间不断让变动十几次了)我还专门登入gisaid去看了,你瞅瞅人家的数据,这么多点点呢。或者看看这图Full genome treesof S clade或者这种Full genome treesof G clade既然发文章,能真的加点数据吗?尤其是送审都3月17了,发出来是4月份,中间的新数据哗啦啦的,补充点数据很有必要的。当然,文章中还是有些内容的。比如南美洲的巴西病毒是属于C的,从意大利传过去的(废话,人家报道的就是去意大利旅行了)比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的那一例,是有武汉/广东旅行史,分类也自然属于这一支了。墨西哥倒是例外,他的病毒是B家族的,而且和意大利/德国比较近这个人去过意大利,其实也说明了,意大利这地方,早就是各种感染混杂了。这张图倒是说明了一点,就是基因组信息和采样信息很对应,说明这些日子,这些病毒还是比较单纯,输入了,大家就检测到了,所以时间和基因组信息对的上。到此为止,全文结束。基本上就是老瓶子老酒,要不是院士contribute,这文章很难发到PNAS。当然,文章最大的新意是:使用了character-based phylogenetic networks,这是分子人类学里常用的办法,搁到病毒里去用了。———后续———一篇文章水不水,其实读者是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这篇文章的确是有点水了,那大家一定会问,那你举个不水的,其实就有啊,比如NSR那篇把病毒分为L型和S型的,明显质量要高出一大截。如何看待中国科研团队发现新冠病毒已突变,演化出两个亚型,且传染力或有差异?发生了哪些变化?www.hu.com当然,我还是要说:水文,那也是有价值的!
 好经大事
好经大事剑桥大学汉学研究的见证人——访英国著名汉学家鲁惟一教授
■3月10日下午,鲁惟一教授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接受访谈。 作者/供图鲁惟一(Michael Loewe,1922— ),英国著名汉学家、秦汉史专家、剑桥大学荣休教授。他先后就读于剑桥珀斯中学、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51年因其出色的中国汉代史研究而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本科一等荣誉学位,并于1963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同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东亚系执教,直至1990年退休。其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前史、秦汉史等,代表作有《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1967)、《剑桥中国秦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I: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B.C.221-A.D.220,1986)、《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1999)和《中国的早期帝国:一种重估》(China's Early Empires:A Re-appraisal, 2010)等。1月31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在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一楼会议室,我有幸聆听了著名汉学家鲁惟一教授的主题演讲:汉代的“孔子”与“儒生”。这是我初到剑桥出席的首场学术讲座。看着眼前这位98岁高龄的演讲者,我心中很是感慨和感动。自1990年退休以来,鲁惟一教授就这样孜孜不倦于自己的汉学研究,乐而忘忧而不知老之将至!这才是吾辈治学的楷模,这才是学者的价值所系。台下不乏七八十岁的老友听众,他们就这样携手乐游于汉学的海洋。3月10日下午三点的预约访谈,我们一起回顾了鲁教授的汉学研究历程。访谈结束后,面对1992年才参加工作的后学,鲁教授深情而感慨地说:“你这么年轻,前途可期,要加油啊!” 家学渊源 喜读日汉 孙继成: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访谈。请谈谈您的家学渊源,您又是如何开始自己的汉语学习的?鲁惟一:我的祖先是德国犹太人,19世纪20年代移民来到英国。曾祖父路易·罗威(Louis Loewe)是希伯来学的著名学者,也是最早钻研古埃及学的学者之一。我父亲赫伯特·罗威(Herbert Martin James Loewe,1882—1940)是犹太教法典的教授,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父亲本科就读于剑桥大学皇后学院(Queens’College),先后获得东方研究专业和神学学位的第一名,是当年在剑桥大学攻读神学学位唯一的犹太人。毕业后他留校工作,其间曾担任过剑桥大学图书馆东方文献馆馆长。1913年,他成为牛津大学的讲师,后于1931年又回到剑桥大学担任教授,先后在三一学院和格顿学院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二战时期,他因尽力帮助欧洲犹太学者逃离纳粹迫害而深受大家尊敬。父亲为人宽容、思想开放,是一个内心坚定的正统犹太教教徒,一生都致力于构建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桥梁”。父亲的为人与学问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我早年就读于剑桥的珀斯中学(The Perse School)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二战前夕,我正在莫德林学院学习西方古典语言。二战开始后,我应征入伍去学习日语,后来被分到外交部工作,担任日语翻译。二战结束后,我作为一名特殊学生去伦敦大学学习汉语,攻读学士学位。其间,我学的是现代汉语,业余时间自学古代汉语。 孙继成:当年服役期间破译军事密码的训练,对您后来的汉学研究有何影响?鲁惟一:二战服役期间,我曾效力于英国政府设立的秘密情报所,其官方名称是“政府代码与编码训练学校”(GCCS),对外戏称“高尔夫俱乐部与象棋协会”(GCCS),后又以“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为世人所知(因其地点在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园)。它在二战期间为击败德日轴心国作出了卓越贡献。破解德日军事密码需要智商很高的译员,所以这一机构吸纳了许多学术型人才。我们首先进行了6个月的日语强化学习,接下来就是数周的密码破解课程,然后进行密码破译的实际操作。这一经历对我之后汉语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习过程中强有力的纪律保障,以及所承受的压力和使命感,这些都是一个杰出学者的基本素质与业务要求。孙继成:您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于1947年在北平的英国驻华领事馆工作过,这段经历对您的汉语学习有何影响?鲁惟一:1947年,我在英国驻华领事馆担任秘书。我的中文名字“鲁惟一”就是在那时起的。根据英文发音,我把“Loewe”置换成了“鲁惟一”,由此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我。在华工作这六个月里,我曾拜师学习汉语。我的老师大约45岁,可以用他的长指甲蘸墨写字。他不管我是否听得懂,每天都会给我讲授《道德经》和《论语》。但半年后,我就返回了英国,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活。 问学伦大 细研汉简孙继成:1951年,您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本科一等荣誉学位,当时有哪些老师影响了您以后的学术研究?鲁惟一:进入伦敦大学学习时,我是作为特殊学生入校的,仍然是外交部公务人员。学习期间,学校对我没有上课的硬性要求,因此,我与任课老师的交往不多。记得当时我与蒲立本(E. G. Pulleyblank)老师见过一两面。给我真正上过课的有莱德敖(J. K. Rideout)老师,可惜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另一位老师是西门华德(Walter Simon)教授。20世纪30年代,作为德裔学者的华德老师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移居英国。自40年代开始,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积极推动汉语教学。从他那儿我了解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及相关书目,他对我进入汉学研究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孙继成:1956年,您留校任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您是如何进行汉语教学的?当年亚非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大致如何? 鲁惟一:在伦敦大学的汉语教学中,我给学生开设过“中国历史概论”、个别朝代的专门史等课程,还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辅导、学位论文写作指导等常规性工作。1956年,在伦敦大学学习汉语的本科生对汉语知之甚少,关于中国历史的教材也多采用英语、德语和法语版教材,所以我当时不能奢望学生会有很高的汉语水平。在教学过程中,我会训练学生去撰写论文,有时也为他们提供论文题目。我记得最初学习汉语的学生有两位华人,还有两个英国学生。据我所知,他们后来都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当时同在亚非学院任教的师资队伍可谓阵容强大,有刘殿爵(D. C. Lau)教授、葛瑞汉(A. C. Graham)教授、乔治·韦斯(George Weys)、戈拉·唐纳(Gorla Downer)、杰克·格雷(Jack Gray)等,他们的教学与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考古等。其中刘殿爵和葛瑞汉两位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他们都是研究中国早期思想的学者。刘殿爵教授英译的《论语》《道德经》和《孟子》水平很高,他的清儒学问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葛瑞汉教授的《庄子》思想研究见解独到。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是古代汉语,但当时的学生都很喜欢学习现代汉语,以便毕业后能到外交部门任职。20世纪50—60年代,伦敦大学的汉语教学团队不断扩大,研究发展势头也日益向好。 孙继成:1963年,您凭借自己的居延汉简(指1930年在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城障、烽燧、关塞遗址发掘出的1万余枚汉简,别称“居延旧简”)研究,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博士学位。请问您当年研究居延汉简的资料来自何处?在研究过程中,您得到过哪些师友的帮助?您的研究方法有何独特之处? 鲁惟一:继敦煌汉简之后,居延汉简是考古发现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它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者,为汉代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当我开始研究居延汉简时,能够使用的研究材料非常有限。那时,我无法去中国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除了查阅西欧各国的图书馆外,我还不得不借助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开展自己的研究。在居延汉简的研究过程中,我主要参考了中国学者劳榦(1907—2003)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敦煌汉简研究成果。尤其是劳榦对我的研究起到了巨大作用。劳榦将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事项分别从文献中提炼出来,再把它们与简牍归纳出的记事内容进行比对考证,他所撰写的《居延汉简考释》及相关文章代表了当时简牍研究的最高水平。根据内容,劳榦对居延汉简进行了分类整理,他所依据的分类方法继承了王国维汉晋木简的研究成果。在1944年的考证中,他根据汉简的性质和用途把它们分为五类:文书、簿册、信札、经籍和杂类。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把简牍重分为七大类66项。在《汉代行政记录》一书中,我主要采用了文书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所谓文书学的方法,就是根据简牍的出土地点、大小和形制,简册的编联方式、笔迹,文书的布局及内容,结合汉代行政实践的特点,将零散的简牍及其残片加以集成;在所集成的同类简中,通过完整的木简标准,找出残简究竟残缺了哪些部分,而残缺部分又相当于完整木简的哪些内容,借以恢复简册文书的本来面目。有些简牍支离破碎,文字不全,乍看好像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借助于文书学的研究方法,把它们与相关的简牍排列在一起,往往就会凸显其独特的研究价值。简单地说,就是“首先要进行证据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其次是罗列出这些证据本身”。这一思路与我当年从事军事密码的破译工作有类似之处。在内容上,第一卷主要回顾了居延汉简发现、保存和整理公布的历史,从考古学和古文书学的角度阐释了简牍文书复原的依据和标准,考察了汉代行政机构的运行方式、汉代兵役的征发与管理、汉代的边防和汉代戍卒的工作与生活等。第二卷是对43组简牍原文的翻译,并对每组文书的形式以及它们在汉代制度实际运行中的作用给予相应的阐释。我所依据的汉简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于沙畹的几百件敦煌汉简和劳榦考证的1万多件居延汉简。我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过劳榦本人,并与他进行过简短交流。 任教剑桥 致力秦汉 孙继成:1963年,您调入剑桥大学担任汉学讲师。在剑桥您开设了哪些课程?当时剑桥大学教授汉语的有哪些同事?他们的研究重点有何不同?请问剑桥大学与伦敦大学在汉学研究传统上有何异同?鲁惟一:剑桥大学与伦敦大学在教学上起初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校的汉语教学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在伦敦大学,你所接触的学者都是教授汉语、日语、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的,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具体,也比较狭窄;但在剑桥大学,你可以接触到科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等,接触的人群会比较广博,这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更多的是来自于汉学以外的收获。剑桥大学的汉语教学安排与伦敦大学的也有所不同。前者本科生的四年汉学教学一般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两年的教学内容多集中于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史,而后两年会引导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比如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语言学等。而后者的汉语专业分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方向,分别授予学位,我在伦敦大学拿到的学位就是古代汉语专业的。剑桥大学教授汉语的同事有从伦敦大学调过来的蒲立本教授,他是中国历史、现代汉语的专家;捷克籍保罗·克拉托奇维尔(Paul Kratochvil)讲师,他是教授现代汉语的专家,著有《现代汉语》(The Chinese Language Today,1968),还曾去北京给毛泽东做过口译员。崔瑞德(又译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chett,1925—2006)教授,他是著名的隋唐史专家,也是《剑桥中国史》主编之一。还有一位老师教授中国现代史,但在剑桥的时间不是很长,他就是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著有《中国过去的模式:一种社会经济的解释》(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1973)等。当时剑桥大学资金雄厚,汉学教学师资配备较为完善,教学与科研进展比较顺利。 孙继成:您在剑桥大学培养的学生中比较知名的都有哪些?鲁惟一:1963年,我来剑桥大学教书时,圣约翰学院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刚好是本科毕业,他是剑桥大学自己培养的学生,后来,他致力于中国思想史与制度史研究,成了唐史专家,著有《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士人》(1988)等。另外,巴雷特(Timothy H.Barrett)是我教过的学生,他现在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著有《中国佛性论》。 孙继成: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如何编写《剑桥中国秦汉史》(即《剑桥中国史》第1卷)的。鲁惟一:因秦汉史被《剑桥中国史》主编列为这一丛书的开篇,而没有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所以,当年我们编写《剑桥中国秦汉史》时压力很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深受当时中国考古发现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发现几乎改变了中国史前史乃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当时的学界未能与传统文献记载进行比对考证,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研究成果,所以《剑桥中国史》只好改从秦汉史开始写起,因为撰写秦汉史所能依据的文献较多,也都比较可靠。另外,我被委任为《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主编也事出偶然。我本来只是负责撰写其中的相关章节,只不过当时我给丛书主编崔瑞德教授按时交了稿。后来有一天,崔瑞德教授指定我来承担第一卷的主编工作。参与编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团队集结了当时欧美等地著名的秦汉史学者,主要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1909—2003)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荷兰莱顿大学的何四维(A.F.P.Hulsewé,1910—1993)教授,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西嶋定生(Sa Nishijima,1919—1998)教授等。由于写作进度不太一致,交稿早的学者都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团队协作精神,大家合作得比较愉快。孙继成:您能谈一谈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和2010年出版的《中国的早期帝国:一种重估》吗?鲁惟一:1999年,我与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等人合作编著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参与编写的有哈佛大学与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专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华盛顿大学的威廉·博尔茨(William G. Boltz)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卫·奈特利(David N.Keigbtley)教授,牛津默顿学院的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以及同时供职于匹兹堡大学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华人学者许倬云等。这本书在内容上将传世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资料互证互补,对中国先秦时代的史前史背景,商代考古、商代政治、语言文字,西周政治、西周考古,春秋考古、春秋政治,战国政治,先秦思想史、先秦科技思想史,战国美术史、草原文化等主要领域和研究动态都作了具体描述。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新资料和新研究的大量积累,我们对秦汉史的总体认识也有了较大的改观,我感到有必要对原来的《剑桥中国秦汉史》进行一些内容上的补充,于是我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合编了《中国的早期帝国:一种重估》。这算是我们对《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补充与拓展,其内容涵盖的范围更广。 东学西研 蹊径独辟孙继成:作为西方历史学家,你觉得研究中国历史有哪些方法?又有哪些困难?鲁惟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首先,每个历史学家都在历史研究中设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和学术问题,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结果就会出现很大差异。其次,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慎重地选择自己所关注的时代、地域、主题、时间或者人物,无论他是不是愿意接受“比较文化学者”这一称号,其实他都在进行着比较研究的工作。在比较研究中,他们都会受到很多基本要素带来的限制:如果比较研究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易被界定出来的独特历史事件之中,那么这类比较研究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在宏观范围内,运用比较方法的最著名例子就是“李约瑟难题”。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像“李约瑟之问”这类问题就很难得到一个彻底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选择一个介于这两者之间、中等难度的研究主题来进行比较研究,也许会取得较大的收获,并且还有希望得出一个有效而又合理的普适结论。再次,就是对于历史资源的使用。在甄别和评估史料时,鉴别哪些内容是被后人添加进去的,这才是最有必要的研究;要注意将这些添加内容与编纂者最初所写的文本区分开来。最后,就是批判的方法。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学者运用批判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历史记录;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也许会从检视历史著作的写作动机开始研究,然后检视其中存在的偏见,进而确定现在人们所看到的物质证据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对史料本身所进行的文本批评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步骤。至于说到研究困难,西方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正史中所提供的信息也许并不完整,或许正史并不是它所记述的那个时代必要的参考文献。例如《新唐书》中就没有关注佛教的论述,而对佛教的关注在其他资料中却到处可见。历史学家还都面临着一个特别而又普遍的困境:也就是他们会忍不住把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假设和思想置入过去的某个时代中去。另外,中国的历史学家对汉语史料及其相关事实的娴熟,也是西方历史学家所无法达到的。由于无力运用如此丰富的信息资源,西方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分析他们所知道的文献,尝试理解与此相关的问题,他们会做编年笔记,尝试在时间的长河中去发现问题的发展与变化,并且研究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偶然所致或有意所为。孙继成:在秦汉史的编写过程中,官衔术语的翻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官衔没有系统性,级别和职责还常会发生变化,不能用同一个英文译名来翻译不同时期的中国官职名称。对于中国的官职,有人按字面直译,但对西方读者来说,直译会显得拙劣,有时还会引起误解。您在历史著作中对汉代官职的英语翻译是如何处理的? 鲁惟一:在翻译中国历史上的官衔时,我们的译文大多参考了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翻译《汉书》时的英语译文,还有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又译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编写的《西汉的官衔》(Official Titles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67)上的译名。但是这些译名并不太理想,因为它们没有反映出汉代文官制度的内部等级差异,也没有明确官衔的主要职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译名是从欧洲社会借用来的,其含义与中国的制度并不相符;如果照着字面意思直译过来,对西方读者来说,沟通效果并不太好。另外,我们还参考了毕汉思教授的《汉代的官僚制度》(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1980)。他在这本书中首次论述了汉代的官僚政治,并以命名学为基础,详细论述了各官署的历史、隶属关系以及官员的具体职责等,这是一部很好的官衔翻译参考书。我们知道,有时候,同一个官职名称在西汉与东汉会发生职能变化,因此相应的译文就要作相应的调整;同样,有些官职名称发生了变化,但其职能或地位却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我们就可使用同一个译名。总之,在官职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力求译名译得准确而具体,能够让读者读得懂、看得明白。孙继成:您是卡莱尔学院(Clare Hall)的终身院士,也是李约瑟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您如何评价李约瑟教授?鲁惟一:卡莱尔学院是剑桥大学系统里较为年轻的学院,学院的学术视野比较开阔,对当时的边缘学科也比较重视,汉学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卡莱尔学院延续了这一开放办学的优势,才使得我有幸与东亚学者展开广泛的学术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们陆续邀请了许多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国学者来剑桥访问学习,其中李学勤教授就是最早来访合作的中国学者之一。我所了解的李约瑟教授是位充满矛盾的学界巨人,他既有恪守学术规则的古板,也有突破各种社会规范的非凡勇气。李约瑟一生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学科之间跨度很大,难度很高,但他凭着自己的严格学术训练都取得成功;个人生活方面,他也很勇敢,突破了当时世俗观念的束缚,敢于坚持自己,勇气可嘉。 孙继成:你对西方历史学家未来的汉学研究有何看法?也请您总结一下自己的治学心得。 鲁惟一:西方历史学家可以承担研究中国文明特征的出现、增长、变化过程的历史任务。他们可以将更多的中国文化特征与其他文化特征进行比较;另外,中西方历史学家都倾向于研究持续时间较长的王朝,如对汉、唐、宋、明、清的研究,而较少关注那些持续时间相对短暂的王朝,如秦、晋、隋或者元朝。同样也不太关注那些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的分裂时期,其实,加深研究这些分裂的历史时期也许会有更高的研究回报,也可能更有意义。在中国撰写历史的传统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原则限制了人们对那些短命王朝成就的正确评价。这主要是因为后代的历史撰写者已经将这些短命王朝的统治实践描写得没有借鉴价值。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也许正是这些短命王朝促成了中国历史实践中的一些重要变化,而随后的政权只不过更有能力以更加持久的方式发展了这类思想,并且将之拓展到更广范围。至于我自己,我觉得历史学者都肩负着两种不同的使命,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出版学术著作,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借鉴;二是面向大众,引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话题产生兴趣,为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做好引领。多年来,我自己关于秦汉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早期历史,让更多的专家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早期古代史,以便给他们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文化视角,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治学过程中,我认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担当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你远离学术功利化的诱惑,也可让你更加安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英语系副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1日第1945期 作者:孙继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番木瓜
番木瓜新冠病毒究竟源于何处,剑桥大学最新论文分析清楚了!
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始于2019年年底,结束似乎还遥遥无期,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这次疫情源头是哪儿,一直备受关注。近日,一项来自剑桥大学遗传学家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团队的研究引发热议,他们从新冠患者分离的第一批160个完整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新冠病毒起源可能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而不是中国武汉患者。(剑桥大学新冠病毒进化研究引发争议。来源:剑桥大学官网)无独有偶。4月1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接受媒体采访,谈及海外疫情时也表示:“如果(疫情)没有控制住,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可能除了武汉以外,还有别的源地,我们没有发现,也许在国外还有;另一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防疫措施不到位。”(曾光教授判断,病毒源头不排除来自国外的可能性。来源:中新视频)新冠病毒的来源,已经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它到底来自哪里,我们一起来看看。新冠病毒源自哪里?3月30日,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ANS)以“Contributed”( 注:Contributed的一种机制,即可通过院士内推发表论文。)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针对病毒溯源的研究,他们发现全球的新冠病毒已经变异为A、B、C三种类型,并且这三种类型的病毒在全球分布范围各不相同[1]。(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关于新冠病毒进化的研究快速发表。来源:PNAS官网)仔细看来,这篇论文沿用了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现的BatCovRaTG13病毒[2](即新冠病毒在动物中的”祖先”)作为源头,从“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中提取了160个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组成了系统进化网络。(通过全球不同地区来源新冠病毒基因组做出的进化树。来源:剑桥团队研究[1])A群新冠病毒,是在人类社会里传播的最原始的病毒,上图可以看出:A群在中国、东亚、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均有分布。这项进化分析研究的作者将A群分为了两个亚群:T-等位基因亚群中,有4个中国人(来自中国广东省)带有祖先基因组,而3名日本人和两名美国病人则有许多突变,据报道,这些美国患者有曾在武汉疑似疫情暴发地的居住史;C-等位基因亚群,其中包括来自武汉的5个人(有两个携带祖先基因),另外8个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和邻近国家的东亚人,该亚群有近一半(15/33)主要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剑桥新冠病毒进化研究对病毒起源的分析。来源:剑桥团队研究[1])B群新冠病毒,被认为是通过A群突变而来,分布以亚洲为主(93个里面占74个),中国武汉22例,东部其他地区31例。较早的B群完全在东亚传播(共26个),但是亚洲以外的每个B群都进化出了突变(共19个),作者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不是因为B群在中国传播而自然发生的突变导致的,而是因为B群本身适应了亚洲人群,需要再次突变以适应欧美人群。而C群冠状病毒被认为是B群突变而来,在中国大陆不存在,主要在欧洲分布(11例),新加坡有5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也有。该论文作者还讨论了病毒在欧美的传播链条:巴西的第一例病人是访问意大利后感染的,其病毒属于C群;墨西哥的病毒也是意大利起源的,是2020年2月28日在墨西哥的意大利旅行者身上被检测出来;意大利的病毒源头是德国,一位在慕尼黑Webasto公司工作的员工。结合上述信息,这篇论文本身并没有回复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新冠病毒是起源于美国,还是中国”。据悉,作者已经更新了他们的样本至1000例,但目前尚未通过同行评议发表出来。而后,论文作者Peter Forster博士接受了环球时报耿直哥采访表示[3],不论是哪篇论文,目前仍无法就病毒的来源地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对A族群的分布问题,也做出了回应:“为何A型病毒并没有在武汉和中国大范围地出现,这可能是因为A型并不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所以才变异成了B型。但也可能是因为,武汉当地更多的病例是由B型感染者传染出去的,即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至于A型为何更多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他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A型更适应那里人的免疫系统。但是,A型在武汉出现过,感染过一些武汉人,也感染过有武汉居住旅行史的美国人。所以,从现有证据来看,美国的A型病毒仍然可能是从武汉居住史这个途径过去的。而并不是有些人猜测的“起源于美国”。(Peter Forster博士回应耿直哥采访原文。来源:环球时报评论[3])“病毒源自美国”真的实锤了吗?事实上,关于病毒的起源,我国的学者也发布过不少论文,剑桥大学这篇研究几乎是在重复我国学者的工作。正如欧美的防疫,一步步验证了我国已经验证过的问题(比如戴口罩、加强隔离等)。2月21日,国内的预印本网站ChinaXiv上曾发表过一篇论文,也是将新冠病毒分为了三个族群。(国内学者2月份发表的新冠病毒进化传播研究。来源:ChinaXiv[4])当时,这篇论文主要的热点集中在破除了“病毒源自华南海鲜市场”的认知,但我们仔细阅读下来就会发现,剑桥大学的研究几乎和该论文如出一辙。(国内学者2月份新冠病毒进化传播研究里的全球分布地图。来源:ChinaXiv[4])可以看到,同样的有A、B、C三个族群,不过我国学者是以B群为最早期的病毒群;而后来我国学者这篇论文,被台湾某节目引用论述是否源自美国而大火,腾讯医典此前也曾专门做过解读:美国虽然有更多的病毒种类,但是基本上都与中国患者有关:患者要么到过中国,要么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接触过中国的患者。(美国确诊病例分布和溯源。来源:美国CDC[5])因此,分析了这么多,源头到底是哪儿?目前暂未可知。不过,从越来越多的研究追溯发现,中间宿主可能是分布在东南亚国家的马来西亚穿山甲,病毒的起源可能不是中国。寻找真正的源头是科学问题,也是让类似的疫情不会再次上演的重要因素,我们就让子弹再继续飞一会吧。
 金环蚀
金环蚀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博士: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
央视网消息:4 月 8 号,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了德国和英国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的有关新冠病毒变种的报告。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该报告的第一作者英国剑桥大学彼得 · 福斯特博士。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彼得 · 福斯特博士介绍说,研究人员分析了自 2019 年 12 月 24 号至 2020 年 3 月 4 号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 160 个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数据,发现了三个主要变体,并根据氨基酸变化不同将其命名为 A、B 和 C 型。其中,A 型病毒与蝙蝠及穿山甲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最为接近,是原始病毒类型,B 型衍生自 A 型,C 型衍生自 B 型。三类变体病毒在全球的分布范围不同,差异极大。英国剑桥大学新冠病毒变种报告第一作者彼得 · 福斯特:"A 型病毒就是我们所说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原始病毒,经过突变后出现了 B 型病毒。此前疫情在武汉显现时,B 型病毒的基因组被最早发现。研究人员当时误以为 B 型病毒就是原始病毒,但事实上不是,A 型病毒才是原始病毒。疫情暴发之初,武汉只有少数群体被 A 型病毒感染,随着疫情的蔓延,B 型病毒在武汉发展成为了主要病毒,经过突变后 B 型病毒产生了 C 型病毒。中国疫情初期阶段,中国大陆地区都没有发现 C 型病毒,而是在其他地区发现,比如说在新加坡就有很多被 C 型病毒感染的病例。"研究发现,感染 A 型的病例样本近一半来自东亚以外地区,主要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且三分之二美国样本感染的是 A 型。此外,A 型虽然最早出现在武汉,但武汉只有极少的感染病例。有些曾在武汉生活过的美国人被发现携带 A 型病毒基因组。而 B 型主要分布于中国及东亚地区,亚洲以外的 B 型基因组都发生了突变。C 型是在欧洲传播的主要病毒类型,在美国和巴西也都有发现;但在中国大陆的感染样本中未被发现。福斯特表示,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的首例感染病例可能是由蝙蝠传到人,发生时间在 2019 年 9 月 13 号到 12 月 7 号之间。因此 2019 年 12 月 24 号从武汉采样的病毒基因组无法准确地告诉证实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来源:央视网【来源:ZAKER潇湘】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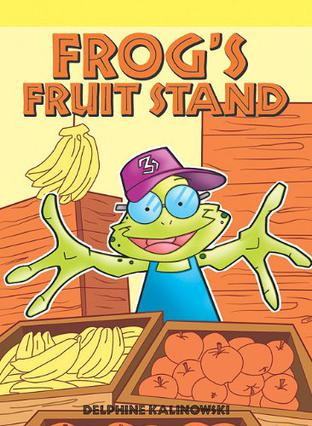 夫若然者
夫若然者剑桥大学新冠病毒变种报告第一作者: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
4月8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了德国和英国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的有关新冠病毒变种的报告。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该报告的第一作者英国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博士。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彼得·福斯特博士介绍说,研究人员分析了自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160个新冠病毒基因组的数据,发现了三个主要变体,并根据氨基酸变化不同将其命名为A、B和C型。其中,A型病毒与蝙蝠及穿山甲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最为接近,是原始病毒类型,B型衍生自A型,C型衍生自B型。三类变体病毒在全球的分布范围不同,差异极大。英国剑桥大学新冠病毒变种报告第一作者 彼得·福斯特:A型病毒就是我们所说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原始病毒,经过突变后出现了B型病毒。此前疫情在武汉显现时,B型病毒的基因组被最早发现,研究人员当时误以为B型病毒就是原始病毒,但事实上不是,A型病毒才是原始病毒。疫情暴发之初,武汉只有少数群体被A型病毒感染,随着疫情的蔓延,B型病毒在武汉发展成为了主要病毒,经过突变后B型病毒产生了C型病毒。中国疫情初期阶段,中国大陆地区都没有发现C型病毒,而是在其他地区发现,比如在新加坡就有很多被C型病毒感染的病例。 研究发现,感染A型的病例样本近一半来自东亚以外地区,主要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且三分之二美国样本感染的是A型。此外,A型虽然最早出现在武汉,但武汉只有极少的感染病例,有些曾在武汉生活过的美国人被发现携带A型病毒基因组。而B型主要分布于中国及东亚地区,亚洲以外的B型基因组都发生了突变。C型是在欧洲传播的主要病毒类型,在美国和巴西也都有发现;但在中国大陆的感染样本中未被发现。福斯特表示,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的首例感染病例可能是由蝙蝠传到人,发生时间在2019年9月13日到12月7日之间。因此,2019年12月24日从武汉采集的病毒基因组无法准确地证实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来源:央视财经
 卡琳顿
卡琳顿CGTN独家专访剑桥大学新冠病毒变种报告第一作者: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
04:304月8日,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发表文章“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论文由来自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第一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日前,CGTN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就研究内容进行了解答。福斯特介绍,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原始病毒类型”。因为有太多的快速突变,传统手段很难清晰地追踪COVID-19家族树,研究人员专门使用了一种“数学网络算法”技术。此前,该技术主要用于分析DNA以绘制史前人类种群活动图。这是其第一次被用来追踪冠状病毒的感染途径。研究人员分析了自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160个新冠病毒(SARS-Cov-2)基因组的数据,发现了三个主要SARS-Cov-2变体,并根据氨基酸变化不同将其命名为A、B和C型。其中A型病毒与蝙蝠及穿山甲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最为接近,为原始病毒类型,B型衍生自A型,C型衍生自B型。此外,三类变体在全球的分布范围不同,差异极大。A和C型多发现于欧洲人和美国人中,B型是东亚最常见的类型。福斯特说,在武汉疫情明显时首先被发现的一个基因组是B型病毒。研究人员当时误以为B型是原始病毒,但事实并非如此,A型才是原始病毒,当时在武汉只是少数,不过B型之后成了武汉疫情暴发期间的主要病毒类,并且进一步突变为C型。研究发现,感染A型的样本将近一半来自东亚以外地区,主要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且三分之二美国样本感染的是A型。此外,A型虽然最早出现在武汉,但武汉只有极少的感染病例。有些曾在武汉生活过的美国人被发现携带A型病毒基因组。而B型主要分布于中国及东亚地区,亚洲以外的B型基因组都发生了突变。C型是在欧洲传播的主要病毒类型,在美国和巴西也都有发现;但在中国大陆的感染样本中未被发现,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皆有分布。福斯特表示,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的首例感染病例可能是由蝙蝠传到人,并发生在2019年9月13日到12月7日之间。因此2019年12月24日从武汉采样的病毒基因组根本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疾病的起源。
 古镇情
古镇情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教会你:用兴趣爱好做科研原来这么爽!
提到阿加莎,大家会想到她的《无人生还》、《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等被编排成无数影视作品的经典推理小说。但你相信,一个喜欢阿加莎的经济学博士,竟然可以靠研究阿加莎,发表了论文参加了会议,并且还从中找到了学习经济学的灵感?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魏仪老师在看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电影中发现了一名不起眼的列车员Pierre Michel。作为阿加莎的铁杆书迷,她发现这个列车员也曾出现在另一本小说《蓝色列车之谜》中。从这名列车员开始,魏仪老师开始了她关于阿加莎的研究。她发现除了Pierre Michel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人物,频繁的重复的出现在阿加莎的各种作品中。她发现这些小人物其实都具有他们的原因和作用。在阿加莎不同的创作阶段,这些小人物的出现也具备他们的意义。在研究的过程中,魏仪老师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于阿加莎作品甚至对阿加莎本人生平的理解,更是发现,对阿加莎的研究在自己经济学博弈论的研究方向上也十分有帮助。大部分的小伙伴,在听到“研究”、“科研”等等,都会觉得这会是一个枯燥而漫长的过程。然而魏仪老师的例子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爱好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研究这个爱好,也会在无形中帮助我们主业的学习。不管你的爱好是玩游戏、吃东西、还是看书看电影,其实只要你细心研究,他们中都有大大的学问。比如说,因为爱玩《刺客信条》,开始研究起了古埃及,发现古埃及历史上各种有趣的事情;因为爱吃地三鲜,开始研究起了天体物理,发现茄子土豆和青椒在一千年前其实是一种生物;因为爱看鬼故事,研究起了各种女鬼形象所代表的东亚文化。如果你也对阿加莎和魏仪老师的研究充满兴趣,或者你有一个想要深入研究的爱好,却不知道该如何入手,那就不要错过这次的讲座!在讲座中,魏仪老师将会分享自己关于阿加莎的“冷门发现”,还会分享自己研究阿加莎的方法和经验,以及自己在关于阿加莎的研究是如何帮助自己学习经济的。参与方式请见下方海报: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