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冲
威冲贵州作家·微刊|此生,与书为伴(随笔)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管【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每周一、三、五更新 NO·642贵州作家·百花园地此生,与书为伴作者:张再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书增长知识,对于我来说,读书改变了人生。书是我的命运之源,是我的立身之本。已经中年的我,没有什么爱好,不会下棋,不会钓鱼,不会打麻将,也不唱歌跳舞,也不善交朋结友,更不喜喝酒聚会。唯一的爱好是读书,书是我长期的不变的伴侣,成了我一生不变的嗜好。生命中,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书,还有许多和书有关的故事。1、《三国演义》影响我的一生。这是影响我人生的第一本书。1981年,我12岁。那是我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在家的第二年。没有上学的我,白天跟父母下地干活,每天一早一晚上山放牛。云贵高原的偏远山区农村,冬天一般没有什么活儿,而我的任务就只剩下上山放牛。那时家里非常穷,一家九人里,我们兄妹七人,每年每人只能穿一双鞋子。这双鞋子,既要穿着上山砍柴、割草、放牛,还要下地薅包谷、挖洋芋、打猪草、铲灰施肥,一年四季的农活都要穿上它。实际上,往往一般不到两个月,我们就会把它穿烂了,三四个月后,直到头通底落。用母亲的话说,我们能“把鞋子穿得连尸首都找不到。”因此每到年末的冬天放牛,就成为一件辛苦的事,因为那得光脚出门上山。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刺骨的北风,冰冷的小雨,长时间不化的雪堆覆盖着山林草地。由于给牛儿过冬的草存得有限,冬天的顶风放牛,对于我来说在所难免,只要不是大雪封山,我都得要骑牛出门上山。母亲不忍心看到我的受冻,打算提前给我买一双球鞋放牛过冬。由于天气干旱,那年的收成并不好,包谷歉收,养猪生病,家里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母亲想来想去,决定把仅有的一只公鸡背到20余公里以外的小镇上去卖。便和父亲商量此事,得到了父亲的同意。由于几个弟妹都没有这份“待遇”,让他们很是羡慕。当时,家里农活较忙,父亲母亲都不去镇里,卖鸡买鞋的事就交由我自己去办。30 多里以外的牛场镇,是附近几个乡镇的中心集市,要走近三个小时。路上泥泞阴雨,自不必说。到市场后,通过一番讨价还价,我很快把那只鸡以4块5毛的价钱卖给了一个穿着讲究却语言生硬的青年男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城里人,有钱人,细皮嫩肉,举止优雅,和我们这些乡下人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得到钱后的我激动得全身发抖,我对这个买了我的鸡的中年男人充满感激,他使我变 “有钱人”了。4块5角啊!我的兜里从来没有装过这么多钱,我走路也像只公鸡似的昂首挺胸,很是自豪;同时我还用手紧紧捏着,生怕钱会忽然间就不在了,被人偷走了。冬天的小镇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非常热闹。我想在买鞋之前先四处看看,想象那种城里有钱人的感觉。走着走着,鬼使神差来到了新华书店,我便走了进去。我在书店的柜台前站定,看到了那些我在家里辍学后四到八处去借阅的连环画,东周列国故事、隋唐英雄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等等,它们安静地躺在隔有玻璃的橱柜里,一本本的摆开去,红红绿绿,整整齐齐而又修然高贵,仿佛在等着我去翻阅那精美的插图,简洁而明了的文字,让我留连忘返。辍学两年的我,在家的我冬天除了放牛几乎无事可做,我把看书当成了消磨时光的唯一手段。但家里穷,没有什么书,我看的书都是去邻村的小舅和小叔那里借来的。这时,柜台最高一层的一排一色的麦绿色的书吸引了我,那是《三国演义》!那时,我已从一个一起去寻找野生天麻的大哥哥那里知道,有关《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共计48本,我几乎找来一大半看了,其余的找不到。我断定这是真正的小说,连环画里的东西这里面一定都有,如果一旦拥有了它,就可以完全不用四处找其他连环画来看了。我对站在柜台里的那个中年女人说:“同志,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也许是我的身体太矮了,她没有看见我。见她没有反应,我又说了一遍。“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同志。”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答话,而是自顾张罗那些大人带着小孩子要的书。冬天的书店里有很多人,大人居多,小孩子很少。我以为我的声音太低了,又过了一分钟,我指着书架的最高层大声说:“老师,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这时,她从柜台里偏过头转过脸来,眼睛似乎专注地对着我足足十秒钟,“哪一本?”她问。我又用手指了指那本书的位置。“两块三。”她对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买,我就上去拿,你如果不要,就只远远的看一眼就得了。”她说完又自己照顾别的客人,嘴里还咕隆了一句:“一个小屁娃儿,看什么《三国演义》啊?”她的话激怒了我。我大声说:“我要买。”我说出这句话时,周围的看书买书的人都安静下来,怔怔地看着我。我已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我并不知道,那个年代,花两块多钱去买一本书,别说是小孩,就是大人,也得掂量掂量,当时的大米也只是7块多钱100斤。买书,是有钱人的游戏,买这种书,更是奢侈的活儿。她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过来。对着我,认真地说:“那,开钱吧。”书店里的人惊奇地看着我,看着我这个冬天里衣衫褴褛、光着脚丫、嘴唇发青、浑身发抖的小孩。可能是我当时十分想读到这本书,或者是她的表情激怒了我,我想都没有想,就掏出了那四块五毛钱,摊在齐我脖子高的柜台上,从里面捡了两张一元的,又抽出一张五毛的推到她的面前。多年以后,读到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有“排除九文大钱。”觉得就和我当时的情形差不多。见到钱,这个穿着干净、冷面高傲的女人立刻露出温和的笑容。她看了柜台上的钱,没有直接去接,而是再看了看我,狐疑而又温和地说:“孩子,你决定要了?”“是的。”我坚定地说。其实我已没有选择。“好!我给你去取。”她说着,然后转过身去,在柜台里面一扇门的背后杠出一个黑色木梯,小心的搭在书架上,慢慢爬上去。我看到她努力伸展身子,用两根手指在书脊上向下一扣,两本一样的书就倾斜出来,她用五根手指把书捏住,并在书背面看看,嘴里说“没有错,书价就是二块三,分上下两册。” 然后把书取下来,另一只手弯曲着,把书抱在胸前,然后下了木梯,她在能翻转的柜台面上取出一个椭圆形的图书章来,在一个红色的盒子了压了压,印上印泥,当着我的面,认认真真地在一本书的背面封底盖上印章,看了看,大概是看盖得正不正。然后又在另一本书的背面又盖了一下,对着盖的地方吹一吹,最后合上封底,满面笑容地递到我的手里。大声说,“拿好了,小伙。”我接过两本厚厚的书,感觉到它沉沉的分量,小学未毕业就辍学的我,除了《新华字典》而外,我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厚的书,何况是小说!如今这书是我的了,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摩挲着书的墨绿色的封面,看到上面的毛笔繁体行书核桃大的“三国演义”几个字,旁边竖起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楷体字样,深灰的暗色花纹,亮亮的封面,打开书的扉页,一股细细的墨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让我精神一振,久久不散。我没有来得及看周围的人的表情,就抱着书匆匆忙忙的走出书店。一出店门,一阵刺骨的北风吹来,我的脸上身上一阵凉意。这时的我,突然间清醒过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一只鸡的价钱大概刚好是一对球鞋的价格,我用买过冬鞋子的钱给花掉一半多,意味着我买不到球鞋了!我一路走,一路想,脑袋里一时是书的内容,一时又是一片空白,我看着手中的书,来来回回地想这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最后天色渐晚,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是想自己如何才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而是想晚上回到家后怎样向爸爸和妈妈作出说明和交代。事实正像我预想的那样。光着脚丫回到家里时,天早已黑下来。当爸爸知道这件事时,足足有一分钟看着我,不知是高兴,还是愤怒,但看得出,他被我的行为震动了。好久时间后,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了句:“书呆子啊,老子看你就光脚板过冬吧。”而妈妈气得一个晚上没吃饭,几天不和我说话。不几天,爸妈变卖了一些包谷也给几个弟妹买了过冬的鞋,但已经没有我的份了。为了表示惩罚,父亲还故意约了寨子里几个家庭一起到岩山上去砍柴,让我和穿上鞋子的其他孩子们一起翻山越岭,在荆棘草丛里穿行。他逢人就说,“呵呵,看我家这个书呆子,一点都不怕冷的。”那个冬天的寒冬腊月,我光着脚丫在山坡上放牛砍柴。没有鞋子穿,冬天的风象锋利的刀子从我的身上刮过,我的脚生起了紫色的冻疮。每天回家后,母亲都要叫我用萝卜在火炕里烧烫后给压在冻疮上面,说这样可以治疗冻疮,不至于化脓。萝卜钻心的烫使我龇牙咧嘴,大喊大叫。这样的土办法治疗效果当然有限,最后冻疮全都变成乌黑色,我的光脚在风中往往疼痛直到麻木。但我心里一点也不后悔。我用旧报纸小心地把书皮包起来,以免弄脏了他。在深冬的晴天里,我在不再有庄稼的土地上放牛时,我怀里多了一本书,我童稚的心里走进了那个风起云涌、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大时代。由于小学未毕业,语言功底差,知识又有限,很多字都是连猜带想。但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我就只能天天看这套书,并把看后的情节拿去与山村的孩子们分享。大家都知道我有一部《三国演义》,很是羡慕,我也在其中得到了莫大的虚荣心和满足感。三年半的辍学,我在这段时间把书上的情节熟悉了,连细节都能说出来,最后连诗词都全部背下来。更可喜的事,由于天天看书,感动了母亲,她虽然是文盲,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个,但却从我买书的这件事情上看到了我与别人家的孩子不同之处。在那个没有一个农村家庭重视孩子读书的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她开始意识到要对我这个大儿子今后的人生道路进行别样的规划。1983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个乡里小升初的考试机会,就偷偷跑出来参加了,一个月后我得到了乡中学的录取通知。由于没有事先得到许可,父亲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而母亲却坚决赞成我去读书并瞒着父亲为我到外面借了报名用的7.2元钱,在那个山村里第一个让我走上了复学的道路。母亲说,“孩子,既然你喜欢书得很,那就去读吧。”重新上学后,因为有书读,我格外勤奋努力,每天步行34公里,天未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回到家,日日坚持,从不迟到。而先前对《三国演义》的烂熟于心和一知半解,竟成了我学习古文的坚实基础,很多课外书都是在遥远的路上边走边看的,后来,在高考时我成了我们班上唯一一个进大学的人,并且选择了中文系。至今,我仍然对书中的很多诗词、情节甚至人物对话也烂熟于心,连读初中的女儿也惊讶我对《三国演义》的特殊记忆力。家里现在已有五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有的还装帧得很漂亮。但是由于有特殊的经历,只有这一部是我想永远珍藏的。书虽已破旧,我却一直留在身边。几次搬家,我都要特别检查一下,怕因为书的破旧被家人扔了。我在书的扉页上,加进一张纸片,写下当时购书的情景,以便时刻提醒自己,曾于失学的年代对于读书的极端渴望,以及对命运的不甘寂寞。2、《传统与变革丛书》对我中学时代影响最大的书,要算“传统与变革丛书”。这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后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润生主编的一套丛书。印象中这套丛书共出版了三批,第一批的书目有《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向》《中国意识的危机》《决策学的新视野》《日本之谜》和《家庭的明天》;第二批书目有《我们性格中的悲剧》《新波斯人信札》《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的演进》;第三批书目有《经济行为与人》《文学的绿色革命》《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等。这些书,几乎我都看过,有些还不只看一遍。那时,刚读高中,对书中反传统的观点很感兴趣,认为针砭时弊,思想深刻。但是,由于知识面和认识程度有限,对其中的一些思想其实只是一知半解。由于别的同学很少接触这种理论性的观点较深的书,我在同学们中就显得鹤立鸡群。在与别人交谈时就会拿出其中的观点来说问题,弄得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我的带动下,班上有李景长、胡辉戎等也去买。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商量,错位购买,你买这本,我买那本,加起来能把书目全部买来,并交换阅读。这种方法果然有效,在我们那个农村学校,我们省下的有限饭菜钱,就能拥有全部书目的书籍。因此,我们几乎全部看完了这些书目。到90年代初期,我上了大学中文系,继续购买和阅读了丛书的后几批书目。在大学里重读这些书,才在一个合理的大背景下接近准确地理解书中的内容。1985年后,传统和变革,逐渐成为一个思想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传统与变革,这是两个密切相联的话题。所有变革都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在本质上是对传统的一种破坏和再创造。此其一。然而情况的复杂在于所有的变革都必须在传统中进行,不仅变革的行为处身于传统规范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呼吁并从事变革的精英及群体自身也带有不可摆脱的传统。这即是问题的另一面。对于古老的东方民族,则问题有其更为复杂、特殊的性质。因为变革的指向是现代化,而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化其实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为标志的,这样,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就是将现代化看作为西方文化传播的结果,从而产生“激烈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语)。20世纪以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与变革的关系在认识上所不断陷入的困境常常即由此产生。传统又是不断生成的,变革是要对传统的东西进行修正、改进和完善。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这些观点成为我的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的研究对象和思考的主题,不断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丛书编委会集聚一批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作一番描述,对传统文化万里长城的砖块进行一次清点,以期回答五个问题:一是传统是什么?二是传统的成因在哪里?三是传统对现代的影响方式?四是传统的功过是非;五是传统在当代的转换趋势。丛书选题精致,结构井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对传统与变革这一时代主题反思的理论深度。需要提及的是,作为经济并不发达、思想并不前沿的贵州,其出版社同志对社会思潮的敏锐感受,对民族振兴的深刻焦虑已经跃然其中,这其实并不是碰巧,在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规模宏大的工程中,编辑付出的艰辛和拥有的胆略,大大超出的我们这些读书人的预期。之后还出版了《山坳上的中国》等名著,轰动一时,使读书界无不见之而动容。因为有这批学者以及这批编辑,贵州人民出版社迎来了一段非常辉煌的黄金时期。3、《不列颠百科全书》及《傅雷译文集》我的书架上,与生命和家庭相关的还有两套书,一套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十一本,是在1994年3月,我大学即将毕业时,女友出钱买来送给我的。那时的我迷上了民族学和人类学,装模作样的搞起了研究,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写作时要查阅了很多资料,撰写了很多风物日记,自己也购买了《中国风俗词典》《风物掌故大全》及《金枝》等读物,因为要写作,觉得经常需要更多的资料,我想,如果有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好了。这个想法,在回乡看望已经参加工作的女友时无意间说出来了。她二话不说,在我离开她回贵阳学校时,她把三百元钱放在我的包里,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不是要买那套什么《不列颠百科全书》吗?只要用得着,再贵的书我也舍得买给你的。”那时,刚参加工作的她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200多元,她需要两个月的收入才能维持这笔开支。回学校后,在师大门口的文人书店里,我购买了这套书,还夸张地请寝室的大哥陈孟前、四哥潘绍辉两个同学一起,在校园熙熙攘攘的同学的众目睽睽之下搬回宿舍,引起很多旁观者的赞叹。而同寝室的其他同学,则直接羡慕得连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他真是太夸张了,幸福啊”他们说。可惜这套书买来后,我并没有认真地翻阅多少。彼时,我已获省教委和计委批准留在贵阳工作。由于工作的性质远离了文化人类学,也远离了哲学社科研究,书上架后很少翻阅。在这个电子图书的时代,各类资料网上随处可寻,这套书只是成了撑门面、衬托书架的东西了。但是这套书却成了我和女友爱的见证,后来女友成了老婆,我们成了家,有了孩子,并把这套书立于书架中最显眼的位置。另一套书是《傅雷译文集》,包含了大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服尔德、梅里美、罗曼罗兰、丹纳和罗素等的代表作品,共计15卷,500余万字。那是我和爱人结婚的时候买了。1997年,我在贵阳市小河镇,她在福泉的一个小镇上工作。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我们感情弥坚。元旦前夕,秋声渐远,冬天来临,恋爱了8年的我们,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在我工作的政府大院民政科领取了结婚证。我们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大摆筵席,没有车辆接送。她花了300多元为我买了这套15卷的红、白、蓝三色从书;我为她买了一件600元的红色尼子大衣,算是彼此对对方的承诺。1998年,她的家人知道此事后,趁我春节期间回去看她的时候,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她家所在的村里不多的几户寨邻前来恭喜祝贺。我们是初恋,也是最后一恋。这两套书,成了我们爱的见证。妻子对于我,犹如现今一段微信里的诗句:你进,我陪你出生入死;你退,我陪你颐养天年。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你赢,我陪你君临天下。偶尔,看着那些书,想起那些年我们曾经有过的追求,心里充满了进取的自豪和温馨。4、几个和购书有关的故事一是高一时读的第一本理论书。书中谈到小说创作的十个问题,如情节、人物、语言、节奏、细节等,其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细节。为此我天天写日记,就是为了练习写细节,我把生动细腻的细节当成了我的最高要求。当我跟一个语文成绩较好的人说作文心得时,这让他大吃一惊,之后在与别的同学说起作文时,他把我当成了比老师还要高明的人。这本书我看了几遍,但是被人借去后再没有还回来,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卖的。但对于自己读过的第一本文艺理论书,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是我两个星期不吃早餐,省下的钱买的,至今记得书的价格,0.82元。这本书有一个普通的名字《小说创作十谈》,作者彭嘉锡。二是大学中文系的课本。我不知道,当时我所就读的大学中文系是一个以读书著称的地方。进校门的第二天,系里通知同学们去库房领书,我以为像高中时那样,只要一个小书包就可以装下几本课本了。和同寝室的几个农村同学嘻嘻哈哈来到书库时,见四到八处全堆满了书,几个班干部已经把书分好,当班长说起每一堆书都是一个同学的时,我们的眼睛都瞪大了。天啊,足有100多本,其中有必须上的课本,有要选修的课本,有要求课外阅读的书籍,古典文学作品选、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文学作品选、西方文学作品选、东方文学作品选等等,我感觉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典籍全在里面了。大家兴奋得一会儿看这本,一会儿翻翻那一本,象孙悟空进了蟠桃园一样,把书搬来搬去,我掏出笔来,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大大的写上“读尽天下好书,争做天下好人。”以示决心。而外系的同学也领到书本,但却远远没有我们中文系的多。有人说,进了中文系,看什么书都是你的专业,无论是哲学、文艺理论、数理逻辑,特别是小说,都是专业需要。我为当初的选择这样的专业而暗自高兴,我觉得把这些书读完就是一个优秀的中文系大学生了。可是,第一节课上的是《文学概论》,上课是图书馆的馆长任洪文老师,他告诉我们,发给我们的这些书只是中文系的人所读的书的一个引子而已,原因不光是这些书目有限,九牛一毛,远远不够;而且选的书目也不尽合理,比较保守,观念陈旧,篇目偏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人性的关注由于远远不够,还必须广泛涉及大量的课外读物,才能学好《文学概论》这门课。这使我们感到昨天的无知和可笑,同时又感到读好中文系的巨大压力。因此大学期间,不管别人怎样,我都对读书如饥似渴,不光看完所有发下来的书,还在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书,也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买了很多书。毫无例外的是,买来的借来的这些书几乎都会认真地读完。以至于我们班主任封孝伦,后来是贵州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他开玩笑似的跟其他同学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张再杰,现在你们还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学四年后,张再杰就可以当很多同学的老师了。”三是一本《沈从文短评小说选》。这本集子是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买的,当时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小镇上工作,工资才215元。由于家庭情况困难,我还承担还刚进初中三弟和四弟的读书费用,一个月下来,经常是入不敷出。那个夏天,天气正好,阳光明媚,空气干燥。我从小镇进城,在贵阳市区办完事后,我包里已经没有几个钱,但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想去逛逛书店。那时的大南门,有一排卖鲜花的店,店面整齐,名称各异,都对着河岸开放着百合、玫瑰、菊花等,从甲秀楼一直延伸到大南门去。但花店从其中的一个地方断开一个缺口,那里独独的一个书店,显得突兀,店面用黄漆黑木,隶书一匾曰“帕尼书店”。我走进店里,看到很多新书,其中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居多,还有贾平凹的文集,那时贾平凹因为《废都》的事在文坛上已是沸沸扬扬。在小说类,看到一排绿色的小开本小说,其中的一本映入我的眼帘《沈从文短篇小说选》,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贾平凹的风格是学习汪曾祺的,而汪曾祺的风格是学习沈从文的,沈从文之前,是清末的散文集张岱。由于自己一直喜欢沈从文的小说,在从事民俗研究后还知道他是民族文化特别是服饰文化研究的大家,见到了他的书就格外亲切。我取下书,一看书价是4.9元。我一摸包里,还有5块钱,刚好够买这本书。我不假思索,让店员给我盖了书店的章。然后拿着书,走出书店,步行回家。从市里到小河,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为一本书走两个小时,当时想来,值。多年以后我开车从小河去省委上班,(省委刚好离那里不远),我用车的路码表量了距离,不多不少刚好10公里。四是一套”四大名著”八本版的连环画册,那是我2006年从山西太原买回来的。之所以要提起这套书,是因为买这套书让我的书呆子气暴露无遗。当时我已是一个区教育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并在区里两个正科级的单位作过了一把手。那时,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就读MPA结束课程,在参加完毕业典礼后,我和省信息产业厅的薛艳桃、贵定县国土局副局长周尔春等几个同学相约,选择了去山西平遥和五台山旅游。在结束那里的旅程后,周尔春去了广东,薛大姐还要去甘肃敦煌,而我要赶回单位。在送走他们后,我留下来,乘还有一点时间,在市里看了几个小的景点,第二天的飞机是下午三点。可是,在中午退掉酒店的房卡后,我变得无所事事,打算逛一会儿街后去机场,在公园的门口我看到了那套长时间以来想拥有的四大名著连环画,现代的出版社把它合并成横翻的八册,平均每部两册,价格140元,买书的人说一分不少。等我把钱给他把书打包以后,发现身上除了已经订好的机票外,只有40元钱的现金了,倒霉的是那个街区离机场50多公里,打的至少需要50块钱。我有些后悔,见到书商已经给我打好了包,不好开口,于是在旁边打听,怎样才能用最节约车费到机场。当被告知附近2公里远的地方有一路公交车,可以坐到机场大巴的停车点,那里的机场大巴只需要30元钱时,我采纳了这个人的建议。提着沉重的书在7月的太阳底下步行到公交车站,挤上了那辆路过机场大巴车站的公交车,当我重新坐上机场大巴车时,问到机场多少钱,他要收的车费不是30元,而是40元。由于之前挤公交车时已开去两元,兜里只剩下38元。我给大巴车师傅说,我只有38元钱,能不能让我坐车,他看着我的一身打扮,又望着那打了包的书,怀疑我是骗钱的,硬是不让我上车。当着大伙乘客的面,我只好打开包裹亮出图书,解释这里面的书,好说歹说,足足用了三分钟,旁边的人都笑起来,“见过爱书的,但没有你这么爱书的,连赶路飞机的都钱敢花!”最后他终于勉强让我上车。一路上,我都低着头,觉得有人在看我,嘲笑我是书呆子,因此一路上我都面红耳赤,狼狈不堪。5、书房由于对书的特殊经历和特殊情感,每次定居,我都是首先考虑书的问题。我平生干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是高中毕业时,由于高考没有考到理想的状态,加上在与同学们对答案时,大多数答题都和大伙的不一样,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大学没有希望,悔恨之余,把装满整个箱子的高中时代的课本和笔记从四楼的寝室门前直接扔下去,在一声巨响中解脱了高考的苦闷和整个高中时代压抑。待得到大学通知书后,整理家中的书时也仅剩下原来购买的课外书了。之后,非常珍爱这些书,进了大学后,这些书被我一本不剩地带往大学校园。1994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贵阳市郊区小河镇工作,报道时,我除了一床破被子外,就是四大箱书。由于镇里工作岗位一直定不下来,住所也无法落实,我的行李只好放在当时教办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到安排了工作落实了住宿后,我才把书整理出来,有些书在纸箱底下已被拖地的水腐烂了。让我非常心疼。之后,我一直盼望有一个完整的放书的地方,先是想有一个小的书架,有了小书架后又想有大书架,最后想要一个书房,最大的愿望是在一个读书人聚居的地方开一个能看书、能买书、能聊天、能写作的小店。这个愿望现在都没有实现。第一个书架是结婚时买的,有两米长,一米八高,那是我和妻子两个共同凑钱订做的,把它放在一间房子的中央,正好把睡觉的床和煮饭用的炉子隔开,形成一个屏障,也是我们结婚以后家里唯一的固定财产。对当时农村来的我们来说,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家具了,小镇上的人不知道,我们对书架的满足和开心,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我们觉得已经足够“高端。大气。上档次。”那是在1996年,我刚参加工作两年的事。1998年,小镇上政府集资建房,我终于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房子虽然不大,52.24平方米,两室一厅,但是我把最大的一间做成了书房,还隔成两半,一半是一壁通顶的书架,背面另一半是书桌,书桌旁边有一铺床的位子,铺上一张活动的沙发,放下后就是一张简易床,以备老家来客人时用。在那里我写过很多社会新闻评论和很多官样文章。多年以后,我已调到省委某个部门工作,这些文章成了我的基础。在一次小河镇老朋友的聚会中,原乡镇企业局的老局长无意中说起一个关于我读书的故事。他说,也许你不知道,以前区委书记王亚光,你和他接触不多,也不太主动找他汇报工作,他却对了关爱有加。他说,有又一次,你生病时来他你家里探看,无意看到你当时搞的书房,他吃了一惊,之后多次跟其他的副书记副区长等等一干人说,“真没有想到,他妈的这个张再杰,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农村娃娃,一套小小的房子,竟然搞了这么大一个书房,很多好书,是一个爱读书人。令我刮目相看。”可惜,我当时从未听到这话,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区委书记,是一个喜欢读书、自己还写书的官场文人,他从政的水平不怎么样,喜欢感情用事,又爱朝令夕改,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但是,他写的书,却是文采飞扬,散文字字珠玑,小说结构恢弘,时代性强,还语言朴实,富有生活况味。可惜他从政时间太久,忙碌公务,作品不多,至今,我只记得他的《那年那月》、《躁动》极少数的几本。我错过了一个同样把我作为读书人的领导交流的大好机会。但是,如果我当时就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那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也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了。那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搬家,每一次看房、装修和搬家,我都没有其他别的要求,只要有一间大得容得下我全部书籍的书房就行。我妻子也知道我的性格,每到一处,全部由她说了算,但书房除外。因此,我能在一次一次的搬家中,保住我的书房,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的空间还大。别人换大房为的舒适,我换大房为的书房,别人成为房屋的奴隶,简称“房奴”,而我则成了书房的奴隶,可以简称为“书奴”。读书是我当时离开农村出门远行的理由,书箱是我参加工作时唯一的行李,书架是我结婚时唯一的家具,书房是我有房时觉得唯一需要装修的地方。如今,书房成了我下班回家后呆得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有人说,家有500册书,即可算得上藏书,现在我家里已有各类书籍5000余本,超过了10倍,有各类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民族学,其中文学类最多,占60%,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文艺理论、文人传记等等,几乎可以不出门就能看一辈子,可以算名副其实的藏书了。我在成为书奴的同时,也成了书主。坐在书房里,灯光融融,书香墨味,环视四周,图书林立,熟陌相应,如朋满座,历经千古,遍阅中外,大师莅临,鸿儒聚集,谈笑风生。看着这些从书店里买来的、从地摊上淘来的一册册书,我心里感觉到很充实,我能感觉到书中的精彩内容,或深深印象,或浅浅一笑;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交流,或同感共鸣,或引发思考。每一本书都有来历,每一本书都有故事。我能清楚的记得我在把他们买回来的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场景,清楚的记得每一部书后面与我相关的生动故事,或欢呼雀跃,或失魂落魄;或如获至宝,或故人相遇。我是我的这些书的主人,我的生命与他们交融一体。书成为我工作的基础,成为生活的内容,也成为我思想的灵光。此生,与书为伴。作者简介张再杰:在乡镇区县和省委机关工作多年。在人民网、光明网、《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党刊网》《人民音乐》《统计与决策》《情报学报》《贵州民族研究》等发表文章100余篇,参与编辑书籍和出版专著10余部。系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共贵州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精彩回顾欢迎关注贵州作家文学贵州贵州文房三宝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主管:贵州省作家协会编辑:何冲 魏昉 蔡国云野老 老八 黄 勇编辑部主任:黄山主编:魏尔锅微信号:gzzjwx投稿邮箱:gzzjwx@qq.com
 活地图
活地图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高层论坛召开
7月24日至26日,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高层论坛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主办,《小说评论》编辑部、《网络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葛建军,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绪晃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总议题举行了1场主论坛发言和2场专题研讨,就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顶层设计、基础理论和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血红小说及相关作品等话题论道亮剑、竞相发言,以推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大数据产业堪称是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的最新形态。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文化生态建设的大数据开发利用大有可为。大数据产业在给网络传媒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可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艺术生产、传播、消费方面大显身手。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为独特的一脉不容忽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1990年代末产生,历经萌芽、发展和转型三个阶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效应。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培育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还传承和发展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一全新的草根文学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新的精神家园。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指出此次论坛是全国首个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讨会,具有开创性、突破性、基础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他从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层面强调了研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醒研究者们应当注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从研究少数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题材中去寻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在网络文学中得以体现。他提出,网络作家在创作中应当树立一体多元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以客观地、历史地眼光书写文学,防止大汉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倾向,并表示今后将加大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扶持力度,争取尽快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的短板补上。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并作闭幕式总结发言。他指出我国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几乎是和网络文学同步联动发展起来的。经过20余年的努力,已经从文学网站、作家作品以及理论批评等方面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学特色和网络文学的民族阵营,成为中国文学大格局中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劲旅,构成中国网络文学极具特色的一个重要板块。具有民族特色的网络文学已打造出少数民族作家新的精神家园,是文学新秀诞生和成长的摇篮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力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网络写手多,知名作家有待成长;作品丰富,但精品力作不多;理论研究稀缺,批评成果薄弱等不足。这表明,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从创作实践到理论评论,都还处于蓄势待发的创生期和成长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编审庄庸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志雄教授、湖南省委讲师团干部辅导处处长欧阳文风教授、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周兴杰教授等分别就网络文学的“贵州模式”、中华文化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产业IP开发以及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等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北京大学邵燕君副教授担任评议人。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顾雪松教授、《小说评论》杂志主编李国平先生、《贵州民族研究》杂志副主编周真刚先生、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袁星洁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张邦卫教授等分别担任主持人、评议人,出席了专题研讨环节。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网络文学研究基地,此次论坛是该基地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贺予飞 张若玉)[责编:李婷婷]
 万物一齐
万物一齐王成志:哈佛大学藏中国贵州苗族稿本源流考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本首页。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笔者数年前发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龙里定水垻海(左“貝”右“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一册,27厘米,单页10行,红格稿纸,毛笔端正小楷;含当地苗人书信和手绘海“貝巴”苗分布图等总共约80页,简单纸捻装订,封面封底仅为与正文所用一样的额外的一张的空白红格稿纸,稿本没有页码;署民国38年(1949)。多年来,该著的图书馆编目只有标题和作者。编目记录中的作者仅为汉先二字,没有生卒年月等信息。民国晚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中,做海“貝巴”苗族田野调查而出版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不多。笔者仔细查找民国人物,包括民族研究学者,但不见名为汉先的踪迹。倒是有位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先生(1913-1998),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苗族调查的报告和研究成果;他于1949年以汉先为作者名发表过苗蛮调查文章,并涉及“海蚆苗”。作者汉先是不是杨汉先?调查情况如何?这份珍贵稿本如何得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何为海蚆苗?1949年有“汉先”为名发表的“龙里苗夷民族杂记”(《贵州民意》1949年第5卷第4-5期,第21-22页)考察了“海蚆苗”。“海蚆苗”应该就是该稿本中“海‘貝巴’苗”。但更早的1942年,吴泽霖有考察“海‘貝巴’苗”的专文“海‘貝巴’苗中的斗牛”(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硏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第228-232页)。其实,该稿本比较明确地调查确定海“貝巴”苗地理分布和历史发展等。海“貝巴”苗具有明显的服饰特征:“当地的汉人都称这种苗叫海‘貝巴’苗。原因是他们的女子所着的衣服背面挂着很多的海‘貝巴’,这些海‘貝巴’是用线穿好然后连在一快四方布的底边,方布的上一边连有两根带子,可以套在颈项上的,这真是海‘貝巴’苗女子衣服的特别标记,所以这种苗也才得这样的名称。”而苗族服饰正是该稿本作者之一的美国人类学家要收集和研究的内容。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苗族研著述中,包括杨汉先自己的作品中,“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逐渐演变成“海肥苗”或“海巴苗”。比如,史继忠用“海肥苗”一词(史继忠,《民族识别文献资料汇编》,贵州省民族硏究所,1982,第42页)。杨汉先用“海巴苗”(回顾我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贵州省龙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里县志》使用“海巴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侯清泉也用“海巴苗”(《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续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第78页,“杨汉先”条目)。龙基成的“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国苗族知识分子——苗族学者杨汉先传略”(《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50-158页,第156页)写道:杨“曾与美国学者李桂英(P.M. Mickey)一道到贵州龙里一带调查海肥苗。杨汉先自己也搜集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可惜杨氏的调查笔记后来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了。”最近的石朝江和石莉的研究认为美国学者1947年调查“海肥苗”,特别指出:“米凯,美国民族学者,她曾到贵州省贵定县、龙里县一带调查,著有《贵州的海肥苗》(1947)”(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及学术研讨会“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谐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2009年年会,http://www.mpsc.org.cn/ShowNews.asp?id=256)。如果1949年后早期可能由于汉字简化的需要和植字的困难,使用“海巴苗”代替“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那么后来民族研究学者使用“海肥苗”很可能是因为粗心不查所致,进而普遍以讹传讹。汉先是谁?该稿本开篇有“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目次”,具体如下:引言一. 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二. 海“貝巴”苗分布大概三. 籍载上所见海“貝巴”苗的痕迹四. 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五. 海“貝巴”苗的习俗“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含三节:龙里;龙耸;定水坝。“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含两节:名称;移徙历史与住局年代。“海‘貝巴’苗的习俗”一章最长,为全书重点,含九节:椎牛;订婚;结婚;巫女治病;杀过年猪;新年禁忌;除夕邀牛;新年小孩拜年;除夕与新年时青年男女的活动。该书的引言简短,引言全文引述如下:三十八年元月,奉张校长与任教务长命,随桂玉芳女士去龙里调查海“貝巴”苗。我们是元月四日离校,七日到龙里,八日到择定的地点定水坝工作,直到二月四日离开定水坝返花溪。前后计时有一月之久。在定水坝时因要事,故汉先曾回校一次,所以在工作地点时间约二十日。这次的调查费用是由桂女士担负,工作计划则颇得鲍克兰夫人指示,这是应当特别提出感激的。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汉先识于花溪不难看出,首先作者的机构为位于花溪的贵州大学。1949年,校长为张廷休(1898-1961),教务长为曾先后留学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哈佛大学的任泰。引言中特别感谢的鲍克兰夫人为德裔Inez de Beauclair博士(1897-1981),人类学家。自1941年始,在贵州、云南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苗族和仡佬族的研究。在贵州大学教德、法和拉丁文,同时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用中英文发表多篇研究论文。1951年离开贵州大学;1952年离开中国。鲍克兰夫人后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达18年之久。单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上就发表多篇英文论文。1956年与芮逸夫合著《仡佬的族属问题》。1970年在台北出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鲍克兰夫人在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1946年杨汉先被录用到文科研究所工作时,他发现鲍克兰夫人和自己是仅有的正常上班工作的研究人员。鲍克兰夫人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和著述,学术影响很大。费孝通在其“少数中的少数——《兄弟民族在贵州》之七”一文中承认:“关于仡佬的历史现在还不免多属猜测性质,我把这有些地方似乎牵强的推想都写了下来,目的只在指出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的历史材料很多是得自贵州大学鲍克兰教授,一并志谢。”(1951年3月31日《新观察》第2卷第12期)可以确定稿本的作者汉先是杨汉先。杨汉先,苗族,1913年出生于贵州威宁,1998年去世,为著名的民族志学者。1933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主修社会学。次年因家贫休学一年,1938年毕业。1941年,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重要论文“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同年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贵州大学任教。1946年7月与鲍克兰夫人到黔西调查苗族;1947年又独自去大定、黔西、赫章补充调查。1948年写出《黔西南苗族调查报告》。1949年初与美国学者去龙里调查海蚆苗。1959年至1966年,杨汉先任贵州大学副校长。他兼任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多年。杨汉先1949年与美国学者去龙里做调查的美国学者是谁?杨汉先1986年在贵州文史资料民族史料专辑上发表“回顾我的历程”。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元月,学校要我同美国人李桂英去龙里调查海巴苗,我们住在苗寨。不久就到农历年节了,我乘此机会到许多苗族家中了解情况,并看到了他们跳舞、唱歌。”(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龙基成1997年发表的杨汉先传略一文明显参考引用《回顾我的历程》,虽所提杨汉先陪的美国人英文名大体不错,但也认为是李桂英。美国学者是谁?“美国人李桂英”明显与实际不符。写回忆文章时,杨汉先七十多岁,不排除他回忆有误。事实是,1949年1月4日至2月4日,杨汉先陪美国人类学家桂玉芳到龙里做苗族田野调查研究工作。据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档案:桂玉芳(Margaret Portia Mickey,1889-1988),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人,1912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数学专业毕业。多次到中国,是调查研究中国苗族和仡佬族的著名学者。如不少奥柏林学院毕业生赴华传教一样,桂玉芳大学毕业首先任奥柏林学院院长秘书,不久也赴华传教。1914-1920年,任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华北教区传教教师和秘书。她在中国第一所女子高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Woman's Union College)教数学,并任校长麦美德(Luella Miner,1861-1936)的秘书。桂玉芳1920返美国照顾生病的父母,同时做秘书工作,包括1931至1935年任奥柏林学院图书馆馆长秘书。1935年她又回到华北教区,在通州教会医院工作;次年到日本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教一年英语。后再返美,这期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学习人类学、中文和日文研究生课程。桂玉芳。来源: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于1939年至1944年间第三次到中国,在贵州调查研究苗族。1944到1946年她转到印度北方邦的马苏里(Mussoorie, Uttar Pradesh),任教会寄宿学校伍德斯托克学校(Woodstock School)的学籍管理员。1946年她到后来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读研究生课程深造,同时继续进行人类学研究。1946年她发表贵州的海“貝巴”苗的学术论文。1947年,桂玉芳将贵州苗族田野调查成果“Cowrie Shell Miao of Kweichow”(《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于哈佛大学《皮博迪美国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刊(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以九十多页单册出版。皮博迪博物馆的创始人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为美国新英格兰棉商,1866年捐15万美元由哈佛大学创建博物馆,1877年落成开放。皮博迪博物馆为美国最早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 1907–1997)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上专门写书评,大赞其优点,但也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韦慕庭的父亲也到中国传教多年,在上海、东北等地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韦慕庭幼时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和成长;1931年从奥柏林学院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桂玉芳也在哥伦比亚大读研究生课程。《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中夹有一封当地杨家寨的苗人乡长杨正湘致桂玉芳的信。从信中看出,桂玉芳上次调查来到杨正湘家,与杨家人成为好朋友。桂玉芳第四次来贵州,于12月初给杨正湘写信,杨于12月28日回信。从该信看出,杨正湘非常高兴、期待老朋友到来,同时谈到家里人和自己的情况。这封信随没有注明年份,但很可能是1948年12月28日。信中也提到自上次桂玉芳离开已四五年没有通音讯。1949年一月的调查中,桂玉芳很可能又来到杨家寨杨正湘家。这封信也说明该调查报告稿本是桂玉芳拥有、源于桂玉芳处。1948年到1950年间,桂玉芳第四次到中国,由美国赖特学者项目(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资助,继续做研究中国苗族的调查研究。美国国务院下面的富布赖特学者项目于1946年成立,1948-1949年成功获得此项目资助的赴华交流学者有21人。当时为中国内战时期,九人“由于中国情况没有成行而取消”。能成行的12人当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和宾州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二人的“海外联系机构”项下分别为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的“专业”分别为历史和中文。桂玉芳的“海外联系机构”为华西协和大学及其华西边疆研究所(West China Frontier Institute),专业为“人类学”。美国“国内机构”列为“无”的桂玉芳为1948-1950年赴华学者,1948年8月获得资助。1941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1900-1985)任社会学系主任和副所长,校长张凌高(1890-1955)任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虽然经费一直不足,但研究所成员精干,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生机勃勃,成果斐然。 桂玉芳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工作,她花很多时间做苗族服饰图案式样的研究。1948年,桂玉芳非正式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目录学著作一部“A Bibliography of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n-Chinese Peop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s of Adjacent Areas: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国华南和西南:非汉民族及其与邻近地区民族关系西文目录》)。1949年元月,她与杨汉先到贵州龙里定水坝做田野调查。根据二人调查结果,杨汉先于1949年三月完成调查报告的稿本。因此,该报告的资助单位应该是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项目,作者应该是桂玉芳和杨汉先两个人。1950年她应该利用了1949年她与杨汉先一起合作进行的田野调查结果,非正式出版56页的《贵州的海“貝巴”苗:增补和订正》,对1947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论文专册《贵州的海“貝巴”苗》做适当的增订。1951年至1954年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工具书出版公司G.& C.韦氏公司(G. & C. Merriam Company)编辑部工作。后退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国会图书馆研究苗族服饰女性服饰图案式样中体现的象征主义。最后定居于加州的波莫纳(Pomona),利用之前在中国收集的苗族资料继续做研究。如何到哈佛大学?据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的桂玉芳档案,1976年,已87岁高龄的桂玉芳视力明显转差,她与哈佛校友朋友任北亚利桑那博物馆(Museum of Northern Arizona)馆长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内德丹森(Edward Bridge “Ned”Danson,1916-2000)商量她的收藏的可能去向。自三月始,他们致信给当时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馆长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1926-2017),希望将桂玉芳收藏的苗族研究文献、实物、图书、手稿、信函和照片等捐赠给皮博迪博物馆。五月,威廉姆斯馆长回信同意桂玉芳的收藏比较独特,欣然接受捐赠。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桂玉芳档案含等数百种苗族女性服饰、刺绣图案临摹稿及其说明,中国神话故事和传奇的翻译,中英文图书、中国国画和苗族宗教、音乐和工作有关的实物等。信函包括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葛维汉(David C. Graham, 1884-1961)和1948到1950年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白天宝(J. Calvin Bright,1915-?)等人的信件。1976年6月12日,在给威廉姆斯的信中,桂玉芳回忆她对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研究的缘起,与葛维汉有关:1941年12月,我到华西协和大学校园中浸信会的葛维汉夫妇家里做客。他当时是该大学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他把自己收藏的100件文物和川苗女性的900种刺绣服饰捐给该馆。我对这些服饰的图案设计特别感兴趣。1949到1950年,我又到华西校园。1949年12月,中共已到成都。在任命新官员之前,他们不许美国人离开成都,所以我一直在那里住到1950年8月才离开。在这7个月左右,我把这些苗族服饰的十字绣图案,全部快速临摹下来。这些服饰由深蓝棉布以以及白色和彩色丝织刺绣组成。我不得不使用在成都能找到的任何有白底、能画出图案的图纸和中国(印度)墨料和彩色颜料。我没有时间临摹缎织品的图案式样。她写到,回美国“在克莱蒙特(Claremont)安顿下来后,为让这些图案式样保持一致和减少我之前匆忙临摹的错误,我花一年半时间再次仔细转画。我有一箱这样的图案式样。”同时桂玉芳介绍自己对这些服饰图案式样进行深入研究。成都解放时,华西协和大学一位杨姓中国艺术教授由于所教的课程不能继续,向当时博物馆馆长白天宝建议,由杨教授为她讲解和分析这些服饰图案的象征意义。二人一起分门别类整理出30多种图案主题,并做详细笔记。1954年,桂玉芳花四个月时间到国会图书馆全面研究西文文献中图案式样的象征主义,并做了三本活页笔记。然而,由于年岁已高、视力下降严重,无人协助的话桂玉芳打字已经很困难。她出版研究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的著作的想法就没有实现。但她深信这些苗族文献在美国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在捐赠时,她要保证邮寄运输这些文献到万无一失。颇费一番周折后,皮博迪博物馆通知她档案收到无虞。其实早在1946年,国立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和西南文化研究所致信皮博迪博物馆等,希望建立国际学术合作交换关系。1946年5月9日皮博迪博物馆唐纳德斯科特(Donald Scott,1879-1967)馆长写信给桂玉芳转述贵州大学的来函:“敝省的原始部落快速采用汉语和汉人风俗,将导致土著民族文化很快消失。可是,目前贵州本地民族文化实物甚丰,比如各种装饰精美的民族服装和纺织、蜡染和刺绣服饰,以及仍在使用的如芦笙、竹笛和铜鼓等各种民族乐器。敝所愿意向海外博物馆提供这些实物样本以供收藏。作为交换,期待贵方提供图书馆所需的书刊以及人类学工具和照相器材为感。地址是,贵州省贵阳附近花溪。”斯科特馆长就此事请教桂玉芳:“你知道,博物馆收藏特种实物或有展览价值的物品的兴趣,远不及对民族部落使用的日用品的完整收藏。我们愿向贵州的西南文化研究所建议是否可能建立这样的收藏,若可能,费用如何。在贵州何地、何民族部落获得这些藏品。你对贵州深为了解,我现特向你征求高见。我很感谢你的帮助。等收到你的回信后,我再回复贵州大学。”至于随后桂玉芳如何帮助贵州大学和皮博迪博物馆建立合作交换关系,皮博迪博物馆档案中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1946年八、九和十一月,以及后来1948年的八月,皮博迪博物馆收到桂玉芳捐赠的贵州苗族以及日本人的服饰、吉祥物等物品。而且,1947年皮博迪博物馆向代表贵州大学的鲍克兰夫人顺利购买一些代表贵州和贵州苗族民族物品和照片,1948年博物馆收到。如何转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经桂玉芳同意,她捐赠的图书部分可根据图书的性质由皮博迪博物馆的档案馆确定分别转送该博物馆的托泽图书馆(Tozzer Library)、哈佛大学的佛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图书馆和燕京图书馆保存。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877年皮博迪博物馆落成时,其图书馆也同时落成开放。托泽博士(Alfred Marston Tozzer,1877-1954)于1934年至1947年间任皮博迪博物馆的图书馆馆长。1973年主要利用托泽家人的捐款,该图书馆的新楼建成,为纪念托泽博士而冠名该馆为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于1979年正式转隶于哈佛学院图书馆系统(Harvard College Library),但仍与皮博迪博物馆保持密切关系。佛格艺术博物馆的成立与中国有渊源。十九世纪中后期源于波士顿、后迁至纽约的著名对华贸易商佛格(William Hayes Fogg)去世后,其妻佛格夫人(Elizabeth Perkins Fogg)1891年将佛格生前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和20万美元巨资捐赠给哈佛大学创建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佛格艺术博物馆于1895年落成开放。1927年佛格博物馆的维修实验室和研究图书馆等成立。1962年佛格博物馆的图书馆正式并入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与其艺术图书文献馆藏合并而成为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Fine Arts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受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基金资助于1928年成立。其同时成立的图书馆名为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改隶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但与哈佛燕京学社依然保留密切的关系。哈佛燕京学社及其图书馆对中国现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细查《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第一页也就是目录页,在含有地址的英语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章下,有手写铅笔字迹两行,不大清晰。仔细辨认后可以确定为Gift of Portia Mickey (桂玉芳捐赠)和Trans from Tozzer(托泽馆转来)。紧接下面,盖有日期章:Nov 9, 1976。很明显,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收到该稿本后,先转送给哈佛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再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11月9日正式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结语《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是1949年初华西协和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桂玉芳和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汉先合作对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进行田野调查的中文报告,由杨汉先执笔撰写。该稿本由桂玉芳从贵州带到四川,再带回美国。1976年她捐赠给哈佛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转送哈佛托泽图书馆后,最后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保存。《黔苗图说》图片来自网络皮博迪博物馆及其档案馆除藏有桂玉芳和鲍克兰夫人有关的中国苗族实物和档案文献外,还收藏有很多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藏品和档案文献,比如以照片为主的、反映中国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伍尔辛(Frederick Roelker Wulsin,1891-1961)特藏和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特藏。同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的善本书和档案特藏,比如,非常稀见的《黔苗图说》《苗蛮图说》《滇苗图说》,以及源于洛克的纳西族东巴文手稿收藏。此外,以照片和书刊为主的毕敬士牧师中国穆斯林特藏(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和以蒙文晚清和民国图书为主的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特藏,都非常丰富和珍贵。近年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化扫描工作,与国内不少机构合作,系统地将大量珍稀图书和特藏文献进行数字化,对外线上免费开放使用,真正使哈佛燕京的善本和特藏成为天下公器。这是让哈佛之外的研究者尤其感到方便和高兴的事。(致谢:非常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特别感谢中文部主任马小鹤老师、古籍善本部王系老师、哈佛皮博迪博物馆Katherine Meyers Satriano和奥柏林大学图书馆朱润晓老师提供的帮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气之聚也
气之聚也《贵州民族研究》再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近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版),由贵州省民族研究院主办的《贵州民族研究》再次入选。这是《贵州民族研究》第9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期刊工作者和学术界权威专家开展的中文核心期刊评价研究项目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采用定量筛选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分学科研究方法,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了1990种核心期刊。【来源:贵州省人民政府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千织
千织贵州作家·微刊|此生,与书为伴(随笔)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管【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每周一、三、五更新 NO·642贵州作家·百花园地此生,与书为伴作者:张再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书增长知识,对于我来说,读书改变了人生。书是我的命运之源,是我的立身之本。已经中年的我,没有什么爱好,不会下棋,不会钓鱼,不会打麻将,也不唱歌跳舞,也不善交朋结友,更不喜喝酒聚会。唯一的爱好是读书,书是我长期的不变的伴侣,成了我一生不变的嗜好。生命中,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书,还有许多和书有关的故事。1、《三国演义》影响我的一生。这是影响我人生的第一本书。1981年,我12岁。那是我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在家的第二年。没有上学的我,白天跟父母下地干活,每天一早一晚上山放牛。云贵高原的偏远山区农村,冬天一般没有什么活儿,而我的任务就只剩下上山放牛。那时家里非常穷,一家九人里,我们兄妹七人,每年每人只能穿一双鞋子。这双鞋子,既要穿着上山砍柴、割草、放牛,还要下地薅包谷、挖洋芋、打猪草、铲灰施肥,一年四季的农活都要穿上它。实际上,往往一般不到两个月,我们就会把它穿烂了,三四个月后,直到头通底落。用母亲的话说,我们能“把鞋子穿得连尸首都找不到。”因此每到年末的冬天放牛,就成为一件辛苦的事,因为那得光脚出门上山。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刺骨的北风,冰冷的小雨,长时间不化的雪堆覆盖着山林草地。由于给牛儿过冬的草存得有限,冬天的顶风放牛,对于我来说在所难免,只要不是大雪封山,我都得要骑牛出门上山。母亲不忍心看到我的受冻,打算提前给我买一双球鞋放牛过冬。由于天气干旱,那年的收成并不好,包谷歉收,养猪生病,家里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母亲想来想去,决定把仅有的一只公鸡背到20余公里以外的小镇上去卖。便和父亲商量此事,得到了父亲的同意。由于几个弟妹都没有这份“待遇”,让他们很是羡慕。当时,家里农活较忙,父亲母亲都不去镇里,卖鸡买鞋的事就交由我自己去办。30 多里以外的牛场镇,是附近几个乡镇的中心集市,要走近三个小时。路上泥泞阴雨,自不必说。到市场后,通过一番讨价还价,我很快把那只鸡以4块5毛的价钱卖给了一个穿着讲究却语言生硬的青年男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城里人,有钱人,细皮嫩肉,举止优雅,和我们这些乡下人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得到钱后的我激动得全身发抖,我对这个买了我的鸡的中年男人充满感激,他使我变 “有钱人”了。4块5角啊!我的兜里从来没有装过这么多钱,我走路也像只公鸡似的昂首挺胸,很是自豪;同时我还用手紧紧捏着,生怕钱会忽然间就不在了,被人偷走了。冬天的小镇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非常热闹。我想在买鞋之前先四处看看,想象那种城里有钱人的感觉。走着走着,鬼使神差来到了新华书店,我便走了进去。我在书店的柜台前站定,看到了那些我在家里辍学后四到八处去借阅的连环画,东周列国故事、隋唐英雄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等等,它们安静地躺在隔有玻璃的橱柜里,一本本的摆开去,红红绿绿,整整齐齐而又修然高贵,仿佛在等着我去翻阅那精美的插图,简洁而明了的文字,让我留连忘返。辍学两年的我,在家的我冬天除了放牛几乎无事可做,我把看书当成了消磨时光的唯一手段。但家里穷,没有什么书,我看的书都是去邻村的小舅和小叔那里借来的。这时,柜台最高一层的一排一色的麦绿色的书吸引了我,那是《三国演义》!那时,我已从一个一起去寻找野生天麻的大哥哥那里知道,有关《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共计48本,我几乎找来一大半看了,其余的找不到。我断定这是真正的小说,连环画里的东西这里面一定都有,如果一旦拥有了它,就可以完全不用四处找其他连环画来看了。我对站在柜台里的那个中年女人说:“同志,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也许是我的身体太矮了,她没有看见我。见她没有反应,我又说了一遍。“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同志。”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答话,而是自顾张罗那些大人带着小孩子要的书。冬天的书店里有很多人,大人居多,小孩子很少。我以为我的声音太低了,又过了一分钟,我指着书架的最高层大声说:“老师,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这时,她从柜台里偏过头转过脸来,眼睛似乎专注地对着我足足十秒钟,“哪一本?”她问。我又用手指了指那本书的位置。“两块三。”她对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买,我就上去拿,你如果不要,就只远远的看一眼就得了。”她说完又自己照顾别的客人,嘴里还咕隆了一句:“一个小屁娃儿,看什么《三国演义》啊?”她的话激怒了我。我大声说:“我要买。”我说出这句话时,周围的看书买书的人都安静下来,怔怔地看着我。我已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我并不知道,那个年代,花两块多钱去买一本书,别说是小孩,就是大人,也得掂量掂量,当时的大米也只是7块多钱100斤。买书,是有钱人的游戏,买这种书,更是奢侈的活儿。她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过来。对着我,认真地说:“那,开钱吧。”书店里的人惊奇地看着我,看着我这个冬天里衣衫褴褛、光着脚丫、嘴唇发青、浑身发抖的小孩。可能是我当时十分想读到这本书,或者是她的表情激怒了我,我想都没有想,就掏出了那四块五毛钱,摊在齐我脖子高的柜台上,从里面捡了两张一元的,又抽出一张五毛的推到她的面前。多年以后,读到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有“排除九文大钱。”觉得就和我当时的情形差不多。见到钱,这个穿着干净、冷面高傲的女人立刻露出温和的笑容。她看了柜台上的钱,没有直接去接,而是再看了看我,狐疑而又温和地说:“孩子,你决定要了?”“是的。”我坚定地说。其实我已没有选择。“好!我给你去取。”她说着,然后转过身去,在柜台里面一扇门的背后杠出一个黑色木梯,小心的搭在书架上,慢慢爬上去。我看到她努力伸展身子,用两根手指在书脊上向下一扣,两本一样的书就倾斜出来,她用五根手指把书捏住,并在书背面看看,嘴里说“没有错,书价就是二块三,分上下两册。” 然后把书取下来,另一只手弯曲着,把书抱在胸前,然后下了木梯,她在能翻转的柜台面上取出一个椭圆形的图书章来,在一个红色的盒子了压了压,印上印泥,当着我的面,认认真真地在一本书的背面封底盖上印章,看了看,大概是看盖得正不正。然后又在另一本书的背面又盖了一下,对着盖的地方吹一吹,最后合上封底,满面笑容地递到我的手里。大声说,“拿好了,小伙。”我接过两本厚厚的书,感觉到它沉沉的分量,小学未毕业就辍学的我,除了《新华字典》而外,我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厚的书,何况是小说!如今这书是我的了,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摩挲着书的墨绿色的封面,看到上面的毛笔繁体行书核桃大的“三国演义”几个字,旁边竖起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楷体字样,深灰的暗色花纹,亮亮的封面,打开书的扉页,一股细细的墨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让我精神一振,久久不散。我没有来得及看周围的人的表情,就抱着书匆匆忙忙的走出书店。一出店门,一阵刺骨的北风吹来,我的脸上身上一阵凉意。这时的我,突然间清醒过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一只鸡的价钱大概刚好是一对球鞋的价格,我用买过冬鞋子的钱给花掉一半多,意味着我买不到球鞋了!我一路走,一路想,脑袋里一时是书的内容,一时又是一片空白,我看着手中的书,来来回回地想这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最后天色渐晚,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是想自己如何才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而是想晚上回到家后怎样向爸爸和妈妈作出说明和交代。事实正像我预想的那样。光着脚丫回到家里时,天早已黑下来。当爸爸知道这件事时,足足有一分钟看着我,不知是高兴,还是愤怒,但看得出,他被我的行为震动了。好久时间后,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了句:“书呆子啊,老子看你就光脚板过冬吧。”而妈妈气得一个晚上没吃饭,几天不和我说话。不几天,爸妈变卖了一些包谷也给几个弟妹买了过冬的鞋,但已经没有我的份了。为了表示惩罚,父亲还故意约了寨子里几个家庭一起到岩山上去砍柴,让我和穿上鞋子的其他孩子们一起翻山越岭,在荆棘草丛里穿行。他逢人就说,“呵呵,看我家这个书呆子,一点都不怕冷的。”那个冬天的寒冬腊月,我光着脚丫在山坡上放牛砍柴。没有鞋子穿,冬天的风象锋利的刀子从我的身上刮过,我的脚生起了紫色的冻疮。每天回家后,母亲都要叫我用萝卜在火炕里烧烫后给压在冻疮上面,说这样可以治疗冻疮,不至于化脓。萝卜钻心的烫使我龇牙咧嘴,大喊大叫。这样的土办法治疗效果当然有限,最后冻疮全都变成乌黑色,我的光脚在风中往往疼痛直到麻木。但我心里一点也不后悔。我用旧报纸小心地把书皮包起来,以免弄脏了他。在深冬的晴天里,我在不再有庄稼的土地上放牛时,我怀里多了一本书,我童稚的心里走进了那个风起云涌、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大时代。由于小学未毕业,语言功底差,知识又有限,很多字都是连猜带想。但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我就只能天天看这套书,并把看后的情节拿去与山村的孩子们分享。大家都知道我有一部《三国演义》,很是羡慕,我也在其中得到了莫大的虚荣心和满足感。三年半的辍学,我在这段时间把书上的情节熟悉了,连细节都能说出来,最后连诗词都全部背下来。更可喜的事,由于天天看书,感动了母亲,她虽然是文盲,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个,但却从我买书的这件事情上看到了我与别人家的孩子不同之处。在那个没有一个农村家庭重视孩子读书的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她开始意识到要对我这个大儿子今后的人生道路进行别样的规划。1983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个乡里小升初的考试机会,就偷偷跑出来参加了,一个月后我得到了乡中学的录取通知。由于没有事先得到许可,父亲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而母亲却坚决赞成我去读书并瞒着父亲为我到外面借了报名用的7.2元钱,在那个山村里第一个让我走上了复学的道路。母亲说,“孩子,既然你喜欢书得很,那就去读吧。”重新上学后,因为有书读,我格外勤奋努力,每天步行34公里,天未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回到家,日日坚持,从不迟到。而先前对《三国演义》的烂熟于心和一知半解,竟成了我学习古文的坚实基础,很多课外书都是在遥远的路上边走边看的,后来,在高考时我成了我们班上唯一一个进大学的人,并且选择了中文系。至今,我仍然对书中的很多诗词、情节甚至人物对话也烂熟于心,连读初中的女儿也惊讶我对《三国演义》的特殊记忆力。家里现在已有五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有的还装帧得很漂亮。但是由于有特殊的经历,只有这一部是我想永远珍藏的。书虽已破旧,我却一直留在身边。几次搬家,我都要特别检查一下,怕因为书的破旧被家人扔了。我在书的扉页上,加进一张纸片,写下当时购书的情景,以便时刻提醒自己,曾于失学的年代对于读书的极端渴望,以及对命运的不甘寂寞。2、《传统与变革丛书》对我中学时代影响最大的书,要算“传统与变革丛书”。这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后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润生主编的一套丛书。印象中这套丛书共出版了三批,第一批的书目有《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向》《中国意识的危机》《决策学的新视野》《日本之谜》和《家庭的明天》;第二批书目有《我们性格中的悲剧》《新波斯人信札》《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的演进》;第三批书目有《经济行为与人》《文学的绿色革命》《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等。这些书,几乎我都看过,有些还不只看一遍。那时,刚读高中,对书中反传统的观点很感兴趣,认为针砭时弊,思想深刻。但是,由于知识面和认识程度有限,对其中的一些思想其实只是一知半解。由于别的同学很少接触这种理论性的观点较深的书,我在同学们中就显得鹤立鸡群。在与别人交谈时就会拿出其中的观点来说问题,弄得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我的带动下,班上有李景长、胡辉戎等也去买。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商量,错位购买,你买这本,我买那本,加起来能把书目全部买来,并交换阅读。这种方法果然有效,在我们那个农村学校,我们省下的有限饭菜钱,就能拥有全部书目的书籍。因此,我们几乎全部看完了这些书目。到90年代初期,我上了大学中文系,继续购买和阅读了丛书的后几批书目。在大学里重读这些书,才在一个合理的大背景下接近准确地理解书中的内容。1985年后,传统和变革,逐渐成为一个思想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传统与变革,这是两个密切相联的话题。所有变革都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在本质上是对传统的一种破坏和再创造。此其一。然而情况的复杂在于所有的变革都必须在传统中进行,不仅变革的行为处身于传统规范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呼吁并从事变革的精英及群体自身也带有不可摆脱的传统。这即是问题的另一面。对于古老的东方民族,则问题有其更为复杂、特殊的性质。因为变革的指向是现代化,而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化其实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为标志的,这样,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就是将现代化看作为西方文化传播的结果,从而产生“激烈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语)。20世纪以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与变革的关系在认识上所不断陷入的困境常常即由此产生。传统又是不断生成的,变革是要对传统的东西进行修正、改进和完善。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这些观点成为我的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的研究对象和思考的主题,不断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丛书编委会集聚一批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作一番描述,对传统文化万里长城的砖块进行一次清点,以期回答五个问题:一是传统是什么?二是传统的成因在哪里?三是传统对现代的影响方式?四是传统的功过是非;五是传统在当代的转换趋势。丛书选题精致,结构井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对传统与变革这一时代主题反思的理论深度。需要提及的是,作为经济并不发达、思想并不前沿的贵州,其出版社同志对社会思潮的敏锐感受,对民族振兴的深刻焦虑已经跃然其中,这其实并不是碰巧,在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规模宏大的工程中,编辑付出的艰辛和拥有的胆略,大大超出的我们这些读书人的预期。之后还出版了《山坳上的中国》等名著,轰动一时,使读书界无不见之而动容。因为有这批学者以及这批编辑,贵州人民出版社迎来了一段非常辉煌的黄金时期。3、《不列颠百科全书》及《傅雷译文集》我的书架上,与生命和家庭相关的还有两套书,一套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十一本,是在1994年3月,我大学即将毕业时,女友出钱买来送给我的。那时的我迷上了民族学和人类学,装模作样的搞起了研究,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写作时要查阅了很多资料,撰写了很多风物日记,自己也购买了《中国风俗词典》《风物掌故大全》及《金枝》等读物,因为要写作,觉得经常需要更多的资料,我想,如果有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好了。这个想法,在回乡看望已经参加工作的女友时无意间说出来了。她二话不说,在我离开她回贵阳学校时,她把三百元钱放在我的包里,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不是要买那套什么《不列颠百科全书》吗?只要用得着,再贵的书我也舍得买给你的。”那时,刚参加工作的她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200多元,她需要两个月的收入才能维持这笔开支。回学校后,在师大门口的文人书店里,我购买了这套书,还夸张地请寝室的大哥陈孟前、四哥潘绍辉两个同学一起,在校园熙熙攘攘的同学的众目睽睽之下搬回宿舍,引起很多旁观者的赞叹。而同寝室的其他同学,则直接羡慕得连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他真是太夸张了,幸福啊”他们说。可惜这套书买来后,我并没有认真地翻阅多少。彼时,我已获省教委和计委批准留在贵阳工作。由于工作的性质远离了文化人类学,也远离了哲学社科研究,书上架后很少翻阅。在这个电子图书的时代,各类资料网上随处可寻,这套书只是成了撑门面、衬托书架的东西了。但是这套书却成了我和女友爱的见证,后来女友成了老婆,我们成了家,有了孩子,并把这套书立于书架中最显眼的位置。另一套书是《傅雷译文集》,包含了大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服尔德、梅里美、罗曼罗兰、丹纳和罗素等的代表作品,共计15卷,500余万字。那是我和爱人结婚的时候买了。1997年,我在贵阳市小河镇,她在福泉的一个小镇上工作。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我们感情弥坚。元旦前夕,秋声渐远,冬天来临,恋爱了8年的我们,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在我工作的政府大院民政科领取了结婚证。我们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大摆筵席,没有车辆接送。她花了300多元为我买了这套15卷的红、白、蓝三色从书;我为她买了一件600元的红色尼子大衣,算是彼此对对方的承诺。1998年,她的家人知道此事后,趁我春节期间回去看她的时候,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她家所在的村里不多的几户寨邻前来恭喜祝贺。我们是初恋,也是最后一恋。这两套书,成了我们爱的见证。妻子对于我,犹如现今一段微信里的诗句:你进,我陪你出生入死;你退,我陪你颐养天年。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你赢,我陪你君临天下。偶尔,看着那些书,想起那些年我们曾经有过的追求,心里充满了进取的自豪和温馨。4、几个和购书有关的故事一是高一时读的第一本理论书。书中谈到小说创作的十个问题,如情节、人物、语言、节奏、细节等,其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细节。为此我天天写日记,就是为了练习写细节,我把生动细腻的细节当成了我的最高要求。当我跟一个语文成绩较好的人说作文心得时,这让他大吃一惊,之后在与别的同学说起作文时,他把我当成了比老师还要高明的人。这本书我看了几遍,但是被人借去后再没有还回来,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卖的。但对于自己读过的第一本文艺理论书,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是我两个星期不吃早餐,省下的钱买的,至今记得书的价格,0.82元。这本书有一个普通的名字《小说创作十谈》,作者彭嘉锡。二是大学中文系的课本。我不知道,当时我所就读的大学中文系是一个以读书著称的地方。进校门的第二天,系里通知同学们去库房领书,我以为像高中时那样,只要一个小书包就可以装下几本课本了。和同寝室的几个农村同学嘻嘻哈哈来到书库时,见四到八处全堆满了书,几个班干部已经把书分好,当班长说起每一堆书都是一个同学的时,我们的眼睛都瞪大了。天啊,足有100多本,其中有必须上的课本,有要选修的课本,有要求课外阅读的书籍,古典文学作品选、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文学作品选、西方文学作品选、东方文学作品选等等,我感觉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典籍全在里面了。大家兴奋得一会儿看这本,一会儿翻翻那一本,象孙悟空进了蟠桃园一样,把书搬来搬去,我掏出笔来,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大大的写上“读尽天下好书,争做天下好人。”以示决心。而外系的同学也领到书本,但却远远没有我们中文系的多。有人说,进了中文系,看什么书都是你的专业,无论是哲学、文艺理论、数理逻辑,特别是小说,都是专业需要。我为当初的选择这样的专业而暗自高兴,我觉得把这些书读完就是一个优秀的中文系大学生了。可是,第一节课上的是《文学概论》,上课是图书馆的馆长任洪文老师,他告诉我们,发给我们的这些书只是中文系的人所读的书的一个引子而已,原因不光是这些书目有限,九牛一毛,远远不够;而且选的书目也不尽合理,比较保守,观念陈旧,篇目偏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人性的关注由于远远不够,还必须广泛涉及大量的课外读物,才能学好《文学概论》这门课。这使我们感到昨天的无知和可笑,同时又感到读好中文系的巨大压力。因此大学期间,不管别人怎样,我都对读书如饥似渴,不光看完所有发下来的书,还在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书,也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买了很多书。毫无例外的是,买来的借来的这些书几乎都会认真地读完。以至于我们班主任封孝伦,后来是贵州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他开玩笑似的跟其他同学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张再杰,现在你们还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学四年后,张再杰就可以当很多同学的老师了。”三是一本《沈从文短评小说选》。这本集子是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买的,当时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小镇上工作,工资才215元。由于家庭情况困难,我还承担还刚进初中三弟和四弟的读书费用,一个月下来,经常是入不敷出。那个夏天,天气正好,阳光明媚,空气干燥。我从小镇进城,在贵阳市区办完事后,我包里已经没有几个钱,但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想去逛逛书店。那时的大南门,有一排卖鲜花的店,店面整齐,名称各异,都对着河岸开放着百合、玫瑰、菊花等,从甲秀楼一直延伸到大南门去。但花店从其中的一个地方断开一个缺口,那里独独的一个书店,显得突兀,店面用黄漆黑木,隶书一匾曰“帕尼书店”。我走进店里,看到很多新书,其中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居多,还有贾平凹的文集,那时贾平凹因为《废都》的事在文坛上已是沸沸扬扬。在小说类,看到一排绿色的小开本小说,其中的一本映入我的眼帘《沈从文短篇小说选》,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贾平凹的风格是学习汪曾祺的,而汪曾祺的风格是学习沈从文的,沈从文之前,是清末的散文集张岱。由于自己一直喜欢沈从文的小说,在从事民俗研究后还知道他是民族文化特别是服饰文化研究的大家,见到了他的书就格外亲切。我取下书,一看书价是4.9元。我一摸包里,还有5块钱,刚好够买这本书。我不假思索,让店员给我盖了书店的章。然后拿着书,走出书店,步行回家。从市里到小河,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为一本书走两个小时,当时想来,值。多年以后我开车从小河去省委上班,(省委刚好离那里不远),我用车的路码表量了距离,不多不少刚好10公里。四是一套”四大名著”八本版的连环画册,那是我2006年从山西太原买回来的。之所以要提起这套书,是因为买这套书让我的书呆子气暴露无遗。当时我已是一个区教育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并在区里两个正科级的单位作过了一把手。那时,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就读MPA结束课程,在参加完毕业典礼后,我和省信息产业厅的薛艳桃、贵定县国土局副局长周尔春等几个同学相约,选择了去山西平遥和五台山旅游。在结束那里的旅程后,周尔春去了广东,薛大姐还要去甘肃敦煌,而我要赶回单位。在送走他们后,我留下来,乘还有一点时间,在市里看了几个小的景点,第二天的飞机是下午三点。可是,在中午退掉酒店的房卡后,我变得无所事事,打算逛一会儿街后去机场,在公园的门口我看到了那套长时间以来想拥有的四大名著连环画,现代的出版社把它合并成横翻的八册,平均每部两册,价格140元,买书的人说一分不少。等我把钱给他把书打包以后,发现身上除了已经订好的机票外,只有40元钱的现金了,倒霉的是那个街区离机场50多公里,打的至少需要50块钱。我有些后悔,见到书商已经给我打好了包,不好开口,于是在旁边打听,怎样才能用最节约车费到机场。当被告知附近2公里远的地方有一路公交车,可以坐到机场大巴的停车点,那里的机场大巴只需要30元钱时,我采纳了这个人的建议。提着沉重的书在7月的太阳底下步行到公交车站,挤上了那辆路过机场大巴车站的公交车,当我重新坐上机场大巴车时,问到机场多少钱,他要收的车费不是30元,而是40元。由于之前挤公交车时已开去两元,兜里只剩下38元。我给大巴车师傅说,我只有38元钱,能不能让我坐车,他看着我的一身打扮,又望着那打了包的书,怀疑我是骗钱的,硬是不让我上车。当着大伙乘客的面,我只好打开包裹亮出图书,解释这里面的书,好说歹说,足足用了三分钟,旁边的人都笑起来,“见过爱书的,但没有你这么爱书的,连赶路飞机的都钱敢花!”最后他终于勉强让我上车。一路上,我都低着头,觉得有人在看我,嘲笑我是书呆子,因此一路上我都面红耳赤,狼狈不堪。5、书房由于对书的特殊经历和特殊情感,每次定居,我都是首先考虑书的问题。我平生干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是高中毕业时,由于高考没有考到理想的状态,加上在与同学们对答案时,大多数答题都和大伙的不一样,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大学没有希望,悔恨之余,把装满整个箱子的高中时代的课本和笔记从四楼的寝室门前直接扔下去,在一声巨响中解脱了高考的苦闷和整个高中时代压抑。待得到大学通知书后,整理家中的书时也仅剩下原来购买的课外书了。之后,非常珍爱这些书,进了大学后,这些书被我一本不剩地带往大学校园。1994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贵阳市郊区小河镇工作,报道时,我除了一床破被子外,就是四大箱书。由于镇里工作岗位一直定不下来,住所也无法落实,我的行李只好放在当时教办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到安排了工作落实了住宿后,我才把书整理出来,有些书在纸箱底下已被拖地的水腐烂了。让我非常心疼。之后,我一直盼望有一个完整的放书的地方,先是想有一个小的书架,有了小书架后又想有大书架,最后想要一个书房,最大的愿望是在一个读书人聚居的地方开一个能看书、能买书、能聊天、能写作的小店。这个愿望现在都没有实现。第一个书架是结婚时买的,有两米长,一米八高,那是我和妻子两个共同凑钱订做的,把它放在一间房子的中央,正好把睡觉的床和煮饭用的炉子隔开,形成一个屏障,也是我们结婚以后家里唯一的固定财产。对当时农村来的我们来说,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家具了,小镇上的人不知道,我们对书架的满足和开心,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我们觉得已经足够“高端。大气。上档次。”那是在1996年,我刚参加工作两年的事。1998年,小镇上政府集资建房,我终于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房子虽然不大,52.24平方米,两室一厅,但是我把最大的一间做成了书房,还隔成两半,一半是一壁通顶的书架,背面另一半是书桌,书桌旁边有一铺床的位子,铺上一张活动的沙发,放下后就是一张简易床,以备老家来客人时用。在那里我写过很多社会新闻评论和很多官样文章。多年以后,我已调到省委某个部门工作,这些文章成了我的基础。在一次小河镇老朋友的聚会中,原乡镇企业局的老局长无意中说起一个关于我读书的故事。他说,也许你不知道,以前区委书记王亚光,你和他接触不多,也不太主动找他汇报工作,他却对了关爱有加。他说,有又一次,你生病时来他你家里探看,无意看到你当时搞的书房,他吃了一惊,之后多次跟其他的副书记副区长等等一干人说,“真没有想到,他妈的这个张再杰,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农村娃娃,一套小小的房子,竟然搞了这么大一个书房,很多好书,是一个爱读书人。令我刮目相看。”可惜,我当时从未听到这话,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区委书记,是一个喜欢读书、自己还写书的官场文人,他从政的水平不怎么样,喜欢感情用事,又爱朝令夕改,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但是,他写的书,却是文采飞扬,散文字字珠玑,小说结构恢弘,时代性强,还语言朴实,富有生活况味。可惜他从政时间太久,忙碌公务,作品不多,至今,我只记得他的《那年那月》、《躁动》极少数的几本。我错过了一个同样把我作为读书人的领导交流的大好机会。但是,如果我当时就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那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也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了。那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搬家,每一次看房、装修和搬家,我都没有其他别的要求,只要有一间大得容得下我全部书籍的书房就行。我妻子也知道我的性格,每到一处,全部由她说了算,但书房除外。因此,我能在一次一次的搬家中,保住我的书房,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的空间还大。别人换大房为的舒适,我换大房为的书房,别人成为房屋的奴隶,简称“房奴”,而我则成了书房的奴隶,可以简称为“书奴”。读书是我当时离开农村出门远行的理由,书箱是我参加工作时唯一的行李,书架是我结婚时唯一的家具,书房是我有房时觉得唯一需要装修的地方。如今,书房成了我下班回家后呆得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有人说,家有500册书,即可算得上藏书,现在我家里已有各类书籍5000余本,超过了10倍,有各类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民族学,其中文学类最多,占60%,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文艺理论、文人传记等等,几乎可以不出门就能看一辈子,可以算名副其实的藏书了。我在成为书奴的同时,也成了书主。坐在书房里,灯光融融,书香墨味,环视四周,图书林立,熟陌相应,如朋满座,历经千古,遍阅中外,大师莅临,鸿儒聚集,谈笑风生。看着这些从书店里买来的、从地摊上淘来的一册册书,我心里感觉到很充实,我能感觉到书中的精彩内容,或深深印象,或浅浅一笑;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交流,或同感共鸣,或引发思考。每一本书都有来历,每一本书都有故事。我能清楚的记得我在把他们买回来的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场景,清楚的记得每一部书后面与我相关的生动故事,或欢呼雀跃,或失魂落魄;或如获至宝,或故人相遇。我是我的这些书的主人,我的生命与他们交融一体。书成为我工作的基础,成为生活的内容,也成为我思想的灵光。此生,与书为伴。作者简介张再杰:在乡镇区县和省委机关工作多年。在人民网、光明网、《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党刊网》《人民音乐》《统计与决策》《情报学报》《贵州民族研究》等发表文章100余篇,参与编辑书籍和出版专著10余部。系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共贵州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精彩回顾欢迎关注贵州作家文学贵州贵州文房三宝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主管:贵州省作家协会编辑:何冲 魏昉 蔡国云野老 老八 黄 勇编辑部主任:黄山主编:魏尔锅微信号:gzzjwx投稿邮箱:gzzjwx@qq.com
 彼教不学
彼教不学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高层论坛召开
7月24日至26日,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高层论坛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主办,《小说评论》编辑部、《网络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葛建军,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绪晃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总议题举行了1场主论坛发言和2场专题研讨,就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顶层设计、基础理论和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血红小说及相关作品等话题论道亮剑、竞相发言,以推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大数据产业堪称是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的最新形态。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文化生态建设的大数据开发利用大有可为。大数据产业在给网络传媒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可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艺术生产、传播、消费方面大显身手。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为独特的一脉不容忽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1990年代末产生,历经萌芽、发展和转型三个阶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效应。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培育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还传承和发展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一全新的草根文学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新的精神家园。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指出此次论坛是全国首个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讨会,具有开创性、突破性、基础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他从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层面强调了研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醒研究者们应当注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从研究少数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题材中去寻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在网络文学中得以体现。他提出,网络作家在创作中应当树立一体多元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以客观地、历史地眼光书写文学,防止大汉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倾向,并表示今后将加大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扶持力度,争取尽快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的短板补上。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并作闭幕式总结发言。他指出我国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几乎是和网络文学同步联动发展起来的。经过20余年的努力,已经从文学网站、作家作品以及理论批评等方面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学特色和网络文学的民族阵营,成为中国文学大格局中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劲旅,构成中国网络文学极具特色的一个重要板块。具有民族特色的网络文学已打造出少数民族作家新的精神家园,是文学新秀诞生和成长的摇篮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力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网络写手多,知名作家有待成长;作品丰富,但精品力作不多;理论研究稀缺,批评成果薄弱等不足。这表明,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从创作实践到理论评论,都还处于蓄势待发的创生期和成长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编审庄庸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志雄教授、湖南省委讲师团干部辅导处处长欧阳文风教授、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周兴杰教授等分别就网络文学的“贵州模式”、中华文化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产业IP开发以及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等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北京大学邵燕君副教授担任评议人。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顾雪松教授、《小说评论》杂志主编李国平先生、《贵州民族研究》杂志副主编周真刚先生、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袁星洁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张邦卫教授等分别担任主持人、评议人,出席了专题研讨环节。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网络文学研究基地,此次论坛是该基地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贺予飞 张若玉)[责编:李婷婷]
 恐惧症
恐惧症王成志:哈佛大学藏中国贵州苗族稿本源流考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本首页。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笔者数年前发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龙里定水垻海(左“貝”右“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一册,27厘米,单页10行,红格稿纸,毛笔端正小楷;含当地苗人书信和手绘海“貝巴”苗分布图等总共约80页,简单纸捻装订,封面封底仅为与正文所用一样的额外的一张的空白红格稿纸,稿本没有页码;署民国38年(1949)。多年来,该著的图书馆编目只有标题和作者。编目记录中的作者仅为汉先二字,没有生卒年月等信息。民国晚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中,做海“貝巴”苗族田野调查而出版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不多。笔者仔细查找民国人物,包括民族研究学者,但不见名为汉先的踪迹。倒是有位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先生(1913-1998),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苗族调查的报告和研究成果;他于1949年以汉先为作者名发表过苗蛮调查文章,并涉及“海蚆苗”。作者汉先是不是杨汉先?调查情况如何?这份珍贵稿本如何得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何为海蚆苗?1949年有“汉先”为名发表的“龙里苗夷民族杂记”(《贵州民意》1949年第5卷第4-5期,第21-22页)考察了“海蚆苗”。“海蚆苗”应该就是该稿本中“海‘貝巴’苗”。但更早的1942年,吴泽霖有考察“海‘貝巴’苗”的专文“海‘貝巴’苗中的斗牛”(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硏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第228-232页)。其实,该稿本比较明确地调查确定海“貝巴”苗地理分布和历史发展等。海“貝巴”苗具有明显的服饰特征:“当地的汉人都称这种苗叫海‘貝巴’苗。原因是他们的女子所着的衣服背面挂着很多的海‘貝巴’,这些海‘貝巴’是用线穿好然后连在一快四方布的底边,方布的上一边连有两根带子,可以套在颈项上的,这真是海‘貝巴’苗女子衣服的特别标记,所以这种苗也才得这样的名称。”而苗族服饰正是该稿本作者之一的美国人类学家要收集和研究的内容。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苗族研著述中,包括杨汉先自己的作品中,“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逐渐演变成“海肥苗”或“海巴苗”。比如,史继忠用“海肥苗”一词(史继忠,《民族识别文献资料汇编》,贵州省民族硏究所,1982,第42页)。杨汉先用“海巴苗”(回顾我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贵州省龙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里县志》使用“海巴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侯清泉也用“海巴苗”(《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续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第78页,“杨汉先”条目)。龙基成的“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国苗族知识分子——苗族学者杨汉先传略”(《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50-158页,第156页)写道:杨“曾与美国学者李桂英(P.M. Mickey)一道到贵州龙里一带调查海肥苗。杨汉先自己也搜集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可惜杨氏的调查笔记后来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了。”最近的石朝江和石莉的研究认为美国学者1947年调查“海肥苗”,特别指出:“米凯,美国民族学者,她曾到贵州省贵定县、龙里县一带调查,著有《贵州的海肥苗》(1947)”(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及学术研讨会“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谐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2009年年会,http://www.mpsc.org.cn/ShowNews.asp?id=256)。如果1949年后早期可能由于汉字简化的需要和植字的困难,使用“海巴苗”代替“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那么后来民族研究学者使用“海肥苗”很可能是因为粗心不查所致,进而普遍以讹传讹。汉先是谁?该稿本开篇有“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目次”,具体如下:引言一. 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二. 海“貝巴”苗分布大概三. 籍载上所见海“貝巴”苗的痕迹四. 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五. 海“貝巴”苗的习俗“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含三节:龙里;龙耸;定水坝。“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含两节:名称;移徙历史与住局年代。“海‘貝巴’苗的习俗”一章最长,为全书重点,含九节:椎牛;订婚;结婚;巫女治病;杀过年猪;新年禁忌;除夕邀牛;新年小孩拜年;除夕与新年时青年男女的活动。该书的引言简短,引言全文引述如下:三十八年元月,奉张校长与任教务长命,随桂玉芳女士去龙里调查海“貝巴”苗。我们是元月四日离校,七日到龙里,八日到择定的地点定水坝工作,直到二月四日离开定水坝返花溪。前后计时有一月之久。在定水坝时因要事,故汉先曾回校一次,所以在工作地点时间约二十日。这次的调查费用是由桂女士担负,工作计划则颇得鲍克兰夫人指示,这是应当特别提出感激的。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汉先识于花溪不难看出,首先作者的机构为位于花溪的贵州大学。1949年,校长为张廷休(1898-1961),教务长为曾先后留学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哈佛大学的任泰。引言中特别感谢的鲍克兰夫人为德裔Inez de Beauclair博士(1897-1981),人类学家。自1941年始,在贵州、云南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苗族和仡佬族的研究。在贵州大学教德、法和拉丁文,同时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用中英文发表多篇研究论文。1951年离开贵州大学;1952年离开中国。鲍克兰夫人后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达18年之久。单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上就发表多篇英文论文。1956年与芮逸夫合著《仡佬的族属问题》。1970年在台北出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鲍克兰夫人在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1946年杨汉先被录用到文科研究所工作时,他发现鲍克兰夫人和自己是仅有的正常上班工作的研究人员。鲍克兰夫人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和著述,学术影响很大。费孝通在其“少数中的少数——《兄弟民族在贵州》之七”一文中承认:“关于仡佬的历史现在还不免多属猜测性质,我把这有些地方似乎牵强的推想都写了下来,目的只在指出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的历史材料很多是得自贵州大学鲍克兰教授,一并志谢。”(1951年3月31日《新观察》第2卷第12期)可以确定稿本的作者汉先是杨汉先。杨汉先,苗族,1913年出生于贵州威宁,1998年去世,为著名的民族志学者。1933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主修社会学。次年因家贫休学一年,1938年毕业。1941年,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重要论文“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同年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贵州大学任教。1946年7月与鲍克兰夫人到黔西调查苗族;1947年又独自去大定、黔西、赫章补充调查。1948年写出《黔西南苗族调查报告》。1949年初与美国学者去龙里调查海蚆苗。1959年至1966年,杨汉先任贵州大学副校长。他兼任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多年。杨汉先1949年与美国学者去龙里做调查的美国学者是谁?杨汉先1986年在贵州文史资料民族史料专辑上发表“回顾我的历程”。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元月,学校要我同美国人李桂英去龙里调查海巴苗,我们住在苗寨。不久就到农历年节了,我乘此机会到许多苗族家中了解情况,并看到了他们跳舞、唱歌。”(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龙基成1997年发表的杨汉先传略一文明显参考引用《回顾我的历程》,虽所提杨汉先陪的美国人英文名大体不错,但也认为是李桂英。美国学者是谁?“美国人李桂英”明显与实际不符。写回忆文章时,杨汉先七十多岁,不排除他回忆有误。事实是,1949年1月4日至2月4日,杨汉先陪美国人类学家桂玉芳到龙里做苗族田野调查研究工作。据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档案:桂玉芳(Margaret Portia Mickey,1889-1988),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人,1912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数学专业毕业。多次到中国,是调查研究中国苗族和仡佬族的著名学者。如不少奥柏林学院毕业生赴华传教一样,桂玉芳大学毕业首先任奥柏林学院院长秘书,不久也赴华传教。1914-1920年,任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华北教区传教教师和秘书。她在中国第一所女子高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Woman's Union College)教数学,并任校长麦美德(Luella Miner,1861-1936)的秘书。桂玉芳1920返美国照顾生病的父母,同时做秘书工作,包括1931至1935年任奥柏林学院图书馆馆长秘书。1935年她又回到华北教区,在通州教会医院工作;次年到日本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教一年英语。后再返美,这期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学习人类学、中文和日文研究生课程。桂玉芳。来源: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于1939年至1944年间第三次到中国,在贵州调查研究苗族。1944到1946年她转到印度北方邦的马苏里(Mussoorie, Uttar Pradesh),任教会寄宿学校伍德斯托克学校(Woodstock School)的学籍管理员。1946年她到后来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读研究生课程深造,同时继续进行人类学研究。1946年她发表贵州的海“貝巴”苗的学术论文。1947年,桂玉芳将贵州苗族田野调查成果“Cowrie Shell Miao of Kweichow”(《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于哈佛大学《皮博迪美国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刊(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以九十多页单册出版。皮博迪博物馆的创始人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为美国新英格兰棉商,1866年捐15万美元由哈佛大学创建博物馆,1877年落成开放。皮博迪博物馆为美国最早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 1907–1997)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上专门写书评,大赞其优点,但也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韦慕庭的父亲也到中国传教多年,在上海、东北等地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韦慕庭幼时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和成长;1931年从奥柏林学院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桂玉芳也在哥伦比亚大读研究生课程。《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中夹有一封当地杨家寨的苗人乡长杨正湘致桂玉芳的信。从信中看出,桂玉芳上次调查来到杨正湘家,与杨家人成为好朋友。桂玉芳第四次来贵州,于12月初给杨正湘写信,杨于12月28日回信。从该信看出,杨正湘非常高兴、期待老朋友到来,同时谈到家里人和自己的情况。这封信随没有注明年份,但很可能是1948年12月28日。信中也提到自上次桂玉芳离开已四五年没有通音讯。1949年一月的调查中,桂玉芳很可能又来到杨家寨杨正湘家。这封信也说明该调查报告稿本是桂玉芳拥有、源于桂玉芳处。1948年到1950年间,桂玉芳第四次到中国,由美国赖特学者项目(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资助,继续做研究中国苗族的调查研究。美国国务院下面的富布赖特学者项目于1946年成立,1948-1949年成功获得此项目资助的赴华交流学者有21人。当时为中国内战时期,九人“由于中国情况没有成行而取消”。能成行的12人当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和宾州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二人的“海外联系机构”项下分别为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的“专业”分别为历史和中文。桂玉芳的“海外联系机构”为华西协和大学及其华西边疆研究所(West China Frontier Institute),专业为“人类学”。美国“国内机构”列为“无”的桂玉芳为1948-1950年赴华学者,1948年8月获得资助。1941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1900-1985)任社会学系主任和副所长,校长张凌高(1890-1955)任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虽然经费一直不足,但研究所成员精干,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生机勃勃,成果斐然。 桂玉芳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工作,她花很多时间做苗族服饰图案式样的研究。1948年,桂玉芳非正式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目录学著作一部“A Bibliography of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n-Chinese Peop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s of Adjacent Areas: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国华南和西南:非汉民族及其与邻近地区民族关系西文目录》)。1949年元月,她与杨汉先到贵州龙里定水坝做田野调查。根据二人调查结果,杨汉先于1949年三月完成调查报告的稿本。因此,该报告的资助单位应该是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项目,作者应该是桂玉芳和杨汉先两个人。1950年她应该利用了1949年她与杨汉先一起合作进行的田野调查结果,非正式出版56页的《贵州的海“貝巴”苗:增补和订正》,对1947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论文专册《贵州的海“貝巴”苗》做适当的增订。1951年至1954年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工具书出版公司G.& C.韦氏公司(G. & C. Merriam Company)编辑部工作。后退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国会图书馆研究苗族服饰女性服饰图案式样中体现的象征主义。最后定居于加州的波莫纳(Pomona),利用之前在中国收集的苗族资料继续做研究。如何到哈佛大学?据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的桂玉芳档案,1976年,已87岁高龄的桂玉芳视力明显转差,她与哈佛校友朋友任北亚利桑那博物馆(Museum of Northern Arizona)馆长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内德丹森(Edward Bridge “Ned”Danson,1916-2000)商量她的收藏的可能去向。自三月始,他们致信给当时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馆长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1926-2017),希望将桂玉芳收藏的苗族研究文献、实物、图书、手稿、信函和照片等捐赠给皮博迪博物馆。五月,威廉姆斯馆长回信同意桂玉芳的收藏比较独特,欣然接受捐赠。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桂玉芳档案含等数百种苗族女性服饰、刺绣图案临摹稿及其说明,中国神话故事和传奇的翻译,中英文图书、中国国画和苗族宗教、音乐和工作有关的实物等。信函包括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葛维汉(David C. Graham, 1884-1961)和1948到1950年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白天宝(J. Calvin Bright,1915-?)等人的信件。1976年6月12日,在给威廉姆斯的信中,桂玉芳回忆她对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研究的缘起,与葛维汉有关:1941年12月,我到华西协和大学校园中浸信会的葛维汉夫妇家里做客。他当时是该大学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他把自己收藏的100件文物和川苗女性的900种刺绣服饰捐给该馆。我对这些服饰的图案设计特别感兴趣。1949到1950年,我又到华西校园。1949年12月,中共已到成都。在任命新官员之前,他们不许美国人离开成都,所以我一直在那里住到1950年8月才离开。在这7个月左右,我把这些苗族服饰的十字绣图案,全部快速临摹下来。这些服饰由深蓝棉布以以及白色和彩色丝织刺绣组成。我不得不使用在成都能找到的任何有白底、能画出图案的图纸和中国(印度)墨料和彩色颜料。我没有时间临摹缎织品的图案式样。她写到,回美国“在克莱蒙特(Claremont)安顿下来后,为让这些图案式样保持一致和减少我之前匆忙临摹的错误,我花一年半时间再次仔细转画。我有一箱这样的图案式样。”同时桂玉芳介绍自己对这些服饰图案式样进行深入研究。成都解放时,华西协和大学一位杨姓中国艺术教授由于所教的课程不能继续,向当时博物馆馆长白天宝建议,由杨教授为她讲解和分析这些服饰图案的象征意义。二人一起分门别类整理出30多种图案主题,并做详细笔记。1954年,桂玉芳花四个月时间到国会图书馆全面研究西文文献中图案式样的象征主义,并做了三本活页笔记。然而,由于年岁已高、视力下降严重,无人协助的话桂玉芳打字已经很困难。她出版研究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的著作的想法就没有实现。但她深信这些苗族文献在美国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在捐赠时,她要保证邮寄运输这些文献到万无一失。颇费一番周折后,皮博迪博物馆通知她档案收到无虞。其实早在1946年,国立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和西南文化研究所致信皮博迪博物馆等,希望建立国际学术合作交换关系。1946年5月9日皮博迪博物馆唐纳德斯科特(Donald Scott,1879-1967)馆长写信给桂玉芳转述贵州大学的来函:“敝省的原始部落快速采用汉语和汉人风俗,将导致土著民族文化很快消失。可是,目前贵州本地民族文化实物甚丰,比如各种装饰精美的民族服装和纺织、蜡染和刺绣服饰,以及仍在使用的如芦笙、竹笛和铜鼓等各种民族乐器。敝所愿意向海外博物馆提供这些实物样本以供收藏。作为交换,期待贵方提供图书馆所需的书刊以及人类学工具和照相器材为感。地址是,贵州省贵阳附近花溪。”斯科特馆长就此事请教桂玉芳:“你知道,博物馆收藏特种实物或有展览价值的物品的兴趣,远不及对民族部落使用的日用品的完整收藏。我们愿向贵州的西南文化研究所建议是否可能建立这样的收藏,若可能,费用如何。在贵州何地、何民族部落获得这些藏品。你对贵州深为了解,我现特向你征求高见。我很感谢你的帮助。等收到你的回信后,我再回复贵州大学。”至于随后桂玉芳如何帮助贵州大学和皮博迪博物馆建立合作交换关系,皮博迪博物馆档案中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1946年八、九和十一月,以及后来1948年的八月,皮博迪博物馆收到桂玉芳捐赠的贵州苗族以及日本人的服饰、吉祥物等物品。而且,1947年皮博迪博物馆向代表贵州大学的鲍克兰夫人顺利购买一些代表贵州和贵州苗族民族物品和照片,1948年博物馆收到。如何转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经桂玉芳同意,她捐赠的图书部分可根据图书的性质由皮博迪博物馆的档案馆确定分别转送该博物馆的托泽图书馆(Tozzer Library)、哈佛大学的佛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图书馆和燕京图书馆保存。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877年皮博迪博物馆落成时,其图书馆也同时落成开放。托泽博士(Alfred Marston Tozzer,1877-1954)于1934年至1947年间任皮博迪博物馆的图书馆馆长。1973年主要利用托泽家人的捐款,该图书馆的新楼建成,为纪念托泽博士而冠名该馆为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于1979年正式转隶于哈佛学院图书馆系统(Harvard College Library),但仍与皮博迪博物馆保持密切关系。佛格艺术博物馆的成立与中国有渊源。十九世纪中后期源于波士顿、后迁至纽约的著名对华贸易商佛格(William Hayes Fogg)去世后,其妻佛格夫人(Elizabeth Perkins Fogg)1891年将佛格生前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和20万美元巨资捐赠给哈佛大学创建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佛格艺术博物馆于1895年落成开放。1927年佛格博物馆的维修实验室和研究图书馆等成立。1962年佛格博物馆的图书馆正式并入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与其艺术图书文献馆藏合并而成为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Fine Arts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受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基金资助于1928年成立。其同时成立的图书馆名为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改隶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但与哈佛燕京学社依然保留密切的关系。哈佛燕京学社及其图书馆对中国现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细查《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第一页也就是目录页,在含有地址的英语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章下,有手写铅笔字迹两行,不大清晰。仔细辨认后可以确定为Gift of Portia Mickey (桂玉芳捐赠)和Trans from Tozzer(托泽馆转来)。紧接下面,盖有日期章:Nov 9, 1976。很明显,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收到该稿本后,先转送给哈佛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再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11月9日正式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结语《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是1949年初华西协和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桂玉芳和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汉先合作对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进行田野调查的中文报告,由杨汉先执笔撰写。该稿本由桂玉芳从贵州带到四川,再带回美国。1976年她捐赠给哈佛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转送哈佛托泽图书馆后,最后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保存。《黔苗图说》图片来自网络皮博迪博物馆及其档案馆除藏有桂玉芳和鲍克兰夫人有关的中国苗族实物和档案文献外,还收藏有很多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藏品和档案文献,比如以照片为主的、反映中国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伍尔辛(Frederick Roelker Wulsin,1891-1961)特藏和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特藏。同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的善本书和档案特藏,比如,非常稀见的《黔苗图说》《苗蛮图说》《滇苗图说》,以及源于洛克的纳西族东巴文手稿收藏。此外,以照片和书刊为主的毕敬士牧师中国穆斯林特藏(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和以蒙文晚清和民国图书为主的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特藏,都非常丰富和珍贵。近年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化扫描工作,与国内不少机构合作,系统地将大量珍稀图书和特藏文献进行数字化,对外线上免费开放使用,真正使哈佛燕京的善本和特藏成为天下公器。这是让哈佛之外的研究者尤其感到方便和高兴的事。(致谢:非常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特别感谢中文部主任马小鹤老师、古籍善本部王系老师、哈佛皮博迪博物馆Katherine Meyers Satriano和奥柏林大学图书馆朱润晓老师提供的帮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鄙哉
鄙哉贵州作家·微刊|此生,与书为伴(随笔)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管【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每周一、三、五更新 NO·642贵州作家·百花园地此生,与书为伴作者:张再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书增长知识,对于我来说,读书改变了人生。书是我的命运之源,是我的立身之本。已经中年的我,没有什么爱好,不会下棋,不会钓鱼,不会打麻将,也不唱歌跳舞,也不善交朋结友,更不喜喝酒聚会。唯一的爱好是读书,书是我长期的不变的伴侣,成了我一生不变的嗜好。生命中,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书,还有许多和书有关的故事。1、《三国演义》影响我的一生。这是影响我人生的第一本书。1981年,我12岁。那是我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在家的第二年。没有上学的我,白天跟父母下地干活,每天一早一晚上山放牛。云贵高原的偏远山区农村,冬天一般没有什么活儿,而我的任务就只剩下上山放牛。那时家里非常穷,一家九人里,我们兄妹七人,每年每人只能穿一双鞋子。这双鞋子,既要穿着上山砍柴、割草、放牛,还要下地薅包谷、挖洋芋、打猪草、铲灰施肥,一年四季的农活都要穿上它。实际上,往往一般不到两个月,我们就会把它穿烂了,三四个月后,直到头通底落。用母亲的话说,我们能“把鞋子穿得连尸首都找不到。”因此每到年末的冬天放牛,就成为一件辛苦的事,因为那得光脚出门上山。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刺骨的北风,冰冷的小雨,长时间不化的雪堆覆盖着山林草地。由于给牛儿过冬的草存得有限,冬天的顶风放牛,对于我来说在所难免,只要不是大雪封山,我都得要骑牛出门上山。母亲不忍心看到我的受冻,打算提前给我买一双球鞋放牛过冬。由于天气干旱,那年的收成并不好,包谷歉收,养猪生病,家里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母亲想来想去,决定把仅有的一只公鸡背到20余公里以外的小镇上去卖。便和父亲商量此事,得到了父亲的同意。由于几个弟妹都没有这份“待遇”,让他们很是羡慕。当时,家里农活较忙,父亲母亲都不去镇里,卖鸡买鞋的事就交由我自己去办。30 多里以外的牛场镇,是附近几个乡镇的中心集市,要走近三个小时。路上泥泞阴雨,自不必说。到市场后,通过一番讨价还价,我很快把那只鸡以4块5毛的价钱卖给了一个穿着讲究却语言生硬的青年男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城里人,有钱人,细皮嫩肉,举止优雅,和我们这些乡下人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得到钱后的我激动得全身发抖,我对这个买了我的鸡的中年男人充满感激,他使我变 “有钱人”了。4块5角啊!我的兜里从来没有装过这么多钱,我走路也像只公鸡似的昂首挺胸,很是自豪;同时我还用手紧紧捏着,生怕钱会忽然间就不在了,被人偷走了。冬天的小镇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非常热闹。我想在买鞋之前先四处看看,想象那种城里有钱人的感觉。走着走着,鬼使神差来到了新华书店,我便走了进去。我在书店的柜台前站定,看到了那些我在家里辍学后四到八处去借阅的连环画,东周列国故事、隋唐英雄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等等,它们安静地躺在隔有玻璃的橱柜里,一本本的摆开去,红红绿绿,整整齐齐而又修然高贵,仿佛在等着我去翻阅那精美的插图,简洁而明了的文字,让我留连忘返。辍学两年的我,在家的我冬天除了放牛几乎无事可做,我把看书当成了消磨时光的唯一手段。但家里穷,没有什么书,我看的书都是去邻村的小舅和小叔那里借来的。这时,柜台最高一层的一排一色的麦绿色的书吸引了我,那是《三国演义》!那时,我已从一个一起去寻找野生天麻的大哥哥那里知道,有关《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共计48本,我几乎找来一大半看了,其余的找不到。我断定这是真正的小说,连环画里的东西这里面一定都有,如果一旦拥有了它,就可以完全不用四处找其他连环画来看了。我对站在柜台里的那个中年女人说:“同志,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也许是我的身体太矮了,她没有看见我。见她没有反应,我又说了一遍。“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同志。”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答话,而是自顾张罗那些大人带着小孩子要的书。冬天的书店里有很多人,大人居多,小孩子很少。我以为我的声音太低了,又过了一分钟,我指着书架的最高层大声说:“老师,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这时,她从柜台里偏过头转过脸来,眼睛似乎专注地对着我足足十秒钟,“哪一本?”她问。我又用手指了指那本书的位置。“两块三。”她对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买,我就上去拿,你如果不要,就只远远的看一眼就得了。”她说完又自己照顾别的客人,嘴里还咕隆了一句:“一个小屁娃儿,看什么《三国演义》啊?”她的话激怒了我。我大声说:“我要买。”我说出这句话时,周围的看书买书的人都安静下来,怔怔地看着我。我已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我并不知道,那个年代,花两块多钱去买一本书,别说是小孩,就是大人,也得掂量掂量,当时的大米也只是7块多钱100斤。买书,是有钱人的游戏,买这种书,更是奢侈的活儿。她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过来。对着我,认真地说:“那,开钱吧。”书店里的人惊奇地看着我,看着我这个冬天里衣衫褴褛、光着脚丫、嘴唇发青、浑身发抖的小孩。可能是我当时十分想读到这本书,或者是她的表情激怒了我,我想都没有想,就掏出了那四块五毛钱,摊在齐我脖子高的柜台上,从里面捡了两张一元的,又抽出一张五毛的推到她的面前。多年以后,读到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有“排除九文大钱。”觉得就和我当时的情形差不多。见到钱,这个穿着干净、冷面高傲的女人立刻露出温和的笑容。她看了柜台上的钱,没有直接去接,而是再看了看我,狐疑而又温和地说:“孩子,你决定要了?”“是的。”我坚定地说。其实我已没有选择。“好!我给你去取。”她说着,然后转过身去,在柜台里面一扇门的背后杠出一个黑色木梯,小心的搭在书架上,慢慢爬上去。我看到她努力伸展身子,用两根手指在书脊上向下一扣,两本一样的书就倾斜出来,她用五根手指把书捏住,并在书背面看看,嘴里说“没有错,书价就是二块三,分上下两册。” 然后把书取下来,另一只手弯曲着,把书抱在胸前,然后下了木梯,她在能翻转的柜台面上取出一个椭圆形的图书章来,在一个红色的盒子了压了压,印上印泥,当着我的面,认认真真地在一本书的背面封底盖上印章,看了看,大概是看盖得正不正。然后又在另一本书的背面又盖了一下,对着盖的地方吹一吹,最后合上封底,满面笑容地递到我的手里。大声说,“拿好了,小伙。”我接过两本厚厚的书,感觉到它沉沉的分量,小学未毕业就辍学的我,除了《新华字典》而外,我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厚的书,何况是小说!如今这书是我的了,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摩挲着书的墨绿色的封面,看到上面的毛笔繁体行书核桃大的“三国演义”几个字,旁边竖起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楷体字样,深灰的暗色花纹,亮亮的封面,打开书的扉页,一股细细的墨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让我精神一振,久久不散。我没有来得及看周围的人的表情,就抱着书匆匆忙忙的走出书店。一出店门,一阵刺骨的北风吹来,我的脸上身上一阵凉意。这时的我,突然间清醒过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一只鸡的价钱大概刚好是一对球鞋的价格,我用买过冬鞋子的钱给花掉一半多,意味着我买不到球鞋了!我一路走,一路想,脑袋里一时是书的内容,一时又是一片空白,我看着手中的书,来来回回地想这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最后天色渐晚,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是想自己如何才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而是想晚上回到家后怎样向爸爸和妈妈作出说明和交代。事实正像我预想的那样。光着脚丫回到家里时,天早已黑下来。当爸爸知道这件事时,足足有一分钟看着我,不知是高兴,还是愤怒,但看得出,他被我的行为震动了。好久时间后,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了句:“书呆子啊,老子看你就光脚板过冬吧。”而妈妈气得一个晚上没吃饭,几天不和我说话。不几天,爸妈变卖了一些包谷也给几个弟妹买了过冬的鞋,但已经没有我的份了。为了表示惩罚,父亲还故意约了寨子里几个家庭一起到岩山上去砍柴,让我和穿上鞋子的其他孩子们一起翻山越岭,在荆棘草丛里穿行。他逢人就说,“呵呵,看我家这个书呆子,一点都不怕冷的。”那个冬天的寒冬腊月,我光着脚丫在山坡上放牛砍柴。没有鞋子穿,冬天的风象锋利的刀子从我的身上刮过,我的脚生起了紫色的冻疮。每天回家后,母亲都要叫我用萝卜在火炕里烧烫后给压在冻疮上面,说这样可以治疗冻疮,不至于化脓。萝卜钻心的烫使我龇牙咧嘴,大喊大叫。这样的土办法治疗效果当然有限,最后冻疮全都变成乌黑色,我的光脚在风中往往疼痛直到麻木。但我心里一点也不后悔。我用旧报纸小心地把书皮包起来,以免弄脏了他。在深冬的晴天里,我在不再有庄稼的土地上放牛时,我怀里多了一本书,我童稚的心里走进了那个风起云涌、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大时代。由于小学未毕业,语言功底差,知识又有限,很多字都是连猜带想。但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我就只能天天看这套书,并把看后的情节拿去与山村的孩子们分享。大家都知道我有一部《三国演义》,很是羡慕,我也在其中得到了莫大的虚荣心和满足感。三年半的辍学,我在这段时间把书上的情节熟悉了,连细节都能说出来,最后连诗词都全部背下来。更可喜的事,由于天天看书,感动了母亲,她虽然是文盲,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个,但却从我买书的这件事情上看到了我与别人家的孩子不同之处。在那个没有一个农村家庭重视孩子读书的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她开始意识到要对我这个大儿子今后的人生道路进行别样的规划。1983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个乡里小升初的考试机会,就偷偷跑出来参加了,一个月后我得到了乡中学的录取通知。由于没有事先得到许可,父亲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而母亲却坚决赞成我去读书并瞒着父亲为我到外面借了报名用的7.2元钱,在那个山村里第一个让我走上了复学的道路。母亲说,“孩子,既然你喜欢书得很,那就去读吧。”重新上学后,因为有书读,我格外勤奋努力,每天步行34公里,天未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回到家,日日坚持,从不迟到。而先前对《三国演义》的烂熟于心和一知半解,竟成了我学习古文的坚实基础,很多课外书都是在遥远的路上边走边看的,后来,在高考时我成了我们班上唯一一个进大学的人,并且选择了中文系。至今,我仍然对书中的很多诗词、情节甚至人物对话也烂熟于心,连读初中的女儿也惊讶我对《三国演义》的特殊记忆力。家里现在已有五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有的还装帧得很漂亮。但是由于有特殊的经历,只有这一部是我想永远珍藏的。书虽已破旧,我却一直留在身边。几次搬家,我都要特别检查一下,怕因为书的破旧被家人扔了。我在书的扉页上,加进一张纸片,写下当时购书的情景,以便时刻提醒自己,曾于失学的年代对于读书的极端渴望,以及对命运的不甘寂寞。2、《传统与变革丛书》对我中学时代影响最大的书,要算“传统与变革丛书”。这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后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润生主编的一套丛书。印象中这套丛书共出版了三批,第一批的书目有《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向》《中国意识的危机》《决策学的新视野》《日本之谜》和《家庭的明天》;第二批书目有《我们性格中的悲剧》《新波斯人信札》《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的演进》;第三批书目有《经济行为与人》《文学的绿色革命》《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等。这些书,几乎我都看过,有些还不只看一遍。那时,刚读高中,对书中反传统的观点很感兴趣,认为针砭时弊,思想深刻。但是,由于知识面和认识程度有限,对其中的一些思想其实只是一知半解。由于别的同学很少接触这种理论性的观点较深的书,我在同学们中就显得鹤立鸡群。在与别人交谈时就会拿出其中的观点来说问题,弄得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我的带动下,班上有李景长、胡辉戎等也去买。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商量,错位购买,你买这本,我买那本,加起来能把书目全部买来,并交换阅读。这种方法果然有效,在我们那个农村学校,我们省下的有限饭菜钱,就能拥有全部书目的书籍。因此,我们几乎全部看完了这些书目。到90年代初期,我上了大学中文系,继续购买和阅读了丛书的后几批书目。在大学里重读这些书,才在一个合理的大背景下接近准确地理解书中的内容。1985年后,传统和变革,逐渐成为一个思想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传统与变革,这是两个密切相联的话题。所有变革都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在本质上是对传统的一种破坏和再创造。此其一。然而情况的复杂在于所有的变革都必须在传统中进行,不仅变革的行为处身于传统规范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呼吁并从事变革的精英及群体自身也带有不可摆脱的传统。这即是问题的另一面。对于古老的东方民族,则问题有其更为复杂、特殊的性质。因为变革的指向是现代化,而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化其实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为标志的,这样,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就是将现代化看作为西方文化传播的结果,从而产生“激烈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语)。20世纪以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与变革的关系在认识上所不断陷入的困境常常即由此产生。传统又是不断生成的,变革是要对传统的东西进行修正、改进和完善。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这些观点成为我的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的研究对象和思考的主题,不断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丛书编委会集聚一批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作一番描述,对传统文化万里长城的砖块进行一次清点,以期回答五个问题:一是传统是什么?二是传统的成因在哪里?三是传统对现代的影响方式?四是传统的功过是非;五是传统在当代的转换趋势。丛书选题精致,结构井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对传统与变革这一时代主题反思的理论深度。需要提及的是,作为经济并不发达、思想并不前沿的贵州,其出版社同志对社会思潮的敏锐感受,对民族振兴的深刻焦虑已经跃然其中,这其实并不是碰巧,在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规模宏大的工程中,编辑付出的艰辛和拥有的胆略,大大超出的我们这些读书人的预期。之后还出版了《山坳上的中国》等名著,轰动一时,使读书界无不见之而动容。因为有这批学者以及这批编辑,贵州人民出版社迎来了一段非常辉煌的黄金时期。3、《不列颠百科全书》及《傅雷译文集》我的书架上,与生命和家庭相关的还有两套书,一套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十一本,是在1994年3月,我大学即将毕业时,女友出钱买来送给我的。那时的我迷上了民族学和人类学,装模作样的搞起了研究,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写作时要查阅了很多资料,撰写了很多风物日记,自己也购买了《中国风俗词典》《风物掌故大全》及《金枝》等读物,因为要写作,觉得经常需要更多的资料,我想,如果有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好了。这个想法,在回乡看望已经参加工作的女友时无意间说出来了。她二话不说,在我离开她回贵阳学校时,她把三百元钱放在我的包里,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不是要买那套什么《不列颠百科全书》吗?只要用得着,再贵的书我也舍得买给你的。”那时,刚参加工作的她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200多元,她需要两个月的收入才能维持这笔开支。回学校后,在师大门口的文人书店里,我购买了这套书,还夸张地请寝室的大哥陈孟前、四哥潘绍辉两个同学一起,在校园熙熙攘攘的同学的众目睽睽之下搬回宿舍,引起很多旁观者的赞叹。而同寝室的其他同学,则直接羡慕得连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他真是太夸张了,幸福啊”他们说。可惜这套书买来后,我并没有认真地翻阅多少。彼时,我已获省教委和计委批准留在贵阳工作。由于工作的性质远离了文化人类学,也远离了哲学社科研究,书上架后很少翻阅。在这个电子图书的时代,各类资料网上随处可寻,这套书只是成了撑门面、衬托书架的东西了。但是这套书却成了我和女友爱的见证,后来女友成了老婆,我们成了家,有了孩子,并把这套书立于书架中最显眼的位置。另一套书是《傅雷译文集》,包含了大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服尔德、梅里美、罗曼罗兰、丹纳和罗素等的代表作品,共计15卷,500余万字。那是我和爱人结婚的时候买了。1997年,我在贵阳市小河镇,她在福泉的一个小镇上工作。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我们感情弥坚。元旦前夕,秋声渐远,冬天来临,恋爱了8年的我们,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在我工作的政府大院民政科领取了结婚证。我们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大摆筵席,没有车辆接送。她花了300多元为我买了这套15卷的红、白、蓝三色从书;我为她买了一件600元的红色尼子大衣,算是彼此对对方的承诺。1998年,她的家人知道此事后,趁我春节期间回去看她的时候,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她家所在的村里不多的几户寨邻前来恭喜祝贺。我们是初恋,也是最后一恋。这两套书,成了我们爱的见证。妻子对于我,犹如现今一段微信里的诗句:你进,我陪你出生入死;你退,我陪你颐养天年。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你赢,我陪你君临天下。偶尔,看着那些书,想起那些年我们曾经有过的追求,心里充满了进取的自豪和温馨。4、几个和购书有关的故事一是高一时读的第一本理论书。书中谈到小说创作的十个问题,如情节、人物、语言、节奏、细节等,其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细节。为此我天天写日记,就是为了练习写细节,我把生动细腻的细节当成了我的最高要求。当我跟一个语文成绩较好的人说作文心得时,这让他大吃一惊,之后在与别的同学说起作文时,他把我当成了比老师还要高明的人。这本书我看了几遍,但是被人借去后再没有还回来,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卖的。但对于自己读过的第一本文艺理论书,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是我两个星期不吃早餐,省下的钱买的,至今记得书的价格,0.82元。这本书有一个普通的名字《小说创作十谈》,作者彭嘉锡。二是大学中文系的课本。我不知道,当时我所就读的大学中文系是一个以读书著称的地方。进校门的第二天,系里通知同学们去库房领书,我以为像高中时那样,只要一个小书包就可以装下几本课本了。和同寝室的几个农村同学嘻嘻哈哈来到书库时,见四到八处全堆满了书,几个班干部已经把书分好,当班长说起每一堆书都是一个同学的时,我们的眼睛都瞪大了。天啊,足有100多本,其中有必须上的课本,有要选修的课本,有要求课外阅读的书籍,古典文学作品选、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文学作品选、西方文学作品选、东方文学作品选等等,我感觉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典籍全在里面了。大家兴奋得一会儿看这本,一会儿翻翻那一本,象孙悟空进了蟠桃园一样,把书搬来搬去,我掏出笔来,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大大的写上“读尽天下好书,争做天下好人。”以示决心。而外系的同学也领到书本,但却远远没有我们中文系的多。有人说,进了中文系,看什么书都是你的专业,无论是哲学、文艺理论、数理逻辑,特别是小说,都是专业需要。我为当初的选择这样的专业而暗自高兴,我觉得把这些书读完就是一个优秀的中文系大学生了。可是,第一节课上的是《文学概论》,上课是图书馆的馆长任洪文老师,他告诉我们,发给我们的这些书只是中文系的人所读的书的一个引子而已,原因不光是这些书目有限,九牛一毛,远远不够;而且选的书目也不尽合理,比较保守,观念陈旧,篇目偏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人性的关注由于远远不够,还必须广泛涉及大量的课外读物,才能学好《文学概论》这门课。这使我们感到昨天的无知和可笑,同时又感到读好中文系的巨大压力。因此大学期间,不管别人怎样,我都对读书如饥似渴,不光看完所有发下来的书,还在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书,也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买了很多书。毫无例外的是,买来的借来的这些书几乎都会认真地读完。以至于我们班主任封孝伦,后来是贵州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他开玩笑似的跟其他同学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张再杰,现在你们还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学四年后,张再杰就可以当很多同学的老师了。”三是一本《沈从文短评小说选》。这本集子是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买的,当时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小镇上工作,工资才215元。由于家庭情况困难,我还承担还刚进初中三弟和四弟的读书费用,一个月下来,经常是入不敷出。那个夏天,天气正好,阳光明媚,空气干燥。我从小镇进城,在贵阳市区办完事后,我包里已经没有几个钱,但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想去逛逛书店。那时的大南门,有一排卖鲜花的店,店面整齐,名称各异,都对着河岸开放着百合、玫瑰、菊花等,从甲秀楼一直延伸到大南门去。但花店从其中的一个地方断开一个缺口,那里独独的一个书店,显得突兀,店面用黄漆黑木,隶书一匾曰“帕尼书店”。我走进店里,看到很多新书,其中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居多,还有贾平凹的文集,那时贾平凹因为《废都》的事在文坛上已是沸沸扬扬。在小说类,看到一排绿色的小开本小说,其中的一本映入我的眼帘《沈从文短篇小说选》,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贾平凹的风格是学习汪曾祺的,而汪曾祺的风格是学习沈从文的,沈从文之前,是清末的散文集张岱。由于自己一直喜欢沈从文的小说,在从事民俗研究后还知道他是民族文化特别是服饰文化研究的大家,见到了他的书就格外亲切。我取下书,一看书价是4.9元。我一摸包里,还有5块钱,刚好够买这本书。我不假思索,让店员给我盖了书店的章。然后拿着书,走出书店,步行回家。从市里到小河,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为一本书走两个小时,当时想来,值。多年以后我开车从小河去省委上班,(省委刚好离那里不远),我用车的路码表量了距离,不多不少刚好10公里。四是一套”四大名著”八本版的连环画册,那是我2006年从山西太原买回来的。之所以要提起这套书,是因为买这套书让我的书呆子气暴露无遗。当时我已是一个区教育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并在区里两个正科级的单位作过了一把手。那时,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就读MPA结束课程,在参加完毕业典礼后,我和省信息产业厅的薛艳桃、贵定县国土局副局长周尔春等几个同学相约,选择了去山西平遥和五台山旅游。在结束那里的旅程后,周尔春去了广东,薛大姐还要去甘肃敦煌,而我要赶回单位。在送走他们后,我留下来,乘还有一点时间,在市里看了几个小的景点,第二天的飞机是下午三点。可是,在中午退掉酒店的房卡后,我变得无所事事,打算逛一会儿街后去机场,在公园的门口我看到了那套长时间以来想拥有的四大名著连环画,现代的出版社把它合并成横翻的八册,平均每部两册,价格140元,买书的人说一分不少。等我把钱给他把书打包以后,发现身上除了已经订好的机票外,只有40元钱的现金了,倒霉的是那个街区离机场50多公里,打的至少需要50块钱。我有些后悔,见到书商已经给我打好了包,不好开口,于是在旁边打听,怎样才能用最节约车费到机场。当被告知附近2公里远的地方有一路公交车,可以坐到机场大巴的停车点,那里的机场大巴只需要30元钱时,我采纳了这个人的建议。提着沉重的书在7月的太阳底下步行到公交车站,挤上了那辆路过机场大巴车站的公交车,当我重新坐上机场大巴车时,问到机场多少钱,他要收的车费不是30元,而是40元。由于之前挤公交车时已开去两元,兜里只剩下38元。我给大巴车师傅说,我只有38元钱,能不能让我坐车,他看着我的一身打扮,又望着那打了包的书,怀疑我是骗钱的,硬是不让我上车。当着大伙乘客的面,我只好打开包裹亮出图书,解释这里面的书,好说歹说,足足用了三分钟,旁边的人都笑起来,“见过爱书的,但没有你这么爱书的,连赶路飞机的都钱敢花!”最后他终于勉强让我上车。一路上,我都低着头,觉得有人在看我,嘲笑我是书呆子,因此一路上我都面红耳赤,狼狈不堪。5、书房由于对书的特殊经历和特殊情感,每次定居,我都是首先考虑书的问题。我平生干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是高中毕业时,由于高考没有考到理想的状态,加上在与同学们对答案时,大多数答题都和大伙的不一样,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大学没有希望,悔恨之余,把装满整个箱子的高中时代的课本和笔记从四楼的寝室门前直接扔下去,在一声巨响中解脱了高考的苦闷和整个高中时代压抑。待得到大学通知书后,整理家中的书时也仅剩下原来购买的课外书了。之后,非常珍爱这些书,进了大学后,这些书被我一本不剩地带往大学校园。1994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贵阳市郊区小河镇工作,报道时,我除了一床破被子外,就是四大箱书。由于镇里工作岗位一直定不下来,住所也无法落实,我的行李只好放在当时教办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到安排了工作落实了住宿后,我才把书整理出来,有些书在纸箱底下已被拖地的水腐烂了。让我非常心疼。之后,我一直盼望有一个完整的放书的地方,先是想有一个小的书架,有了小书架后又想有大书架,最后想要一个书房,最大的愿望是在一个读书人聚居的地方开一个能看书、能买书、能聊天、能写作的小店。这个愿望现在都没有实现。第一个书架是结婚时买的,有两米长,一米八高,那是我和妻子两个共同凑钱订做的,把它放在一间房子的中央,正好把睡觉的床和煮饭用的炉子隔开,形成一个屏障,也是我们结婚以后家里唯一的固定财产。对当时农村来的我们来说,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家具了,小镇上的人不知道,我们对书架的满足和开心,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我们觉得已经足够“高端。大气。上档次。”那是在1996年,我刚参加工作两年的事。1998年,小镇上政府集资建房,我终于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房子虽然不大,52.24平方米,两室一厅,但是我把最大的一间做成了书房,还隔成两半,一半是一壁通顶的书架,背面另一半是书桌,书桌旁边有一铺床的位子,铺上一张活动的沙发,放下后就是一张简易床,以备老家来客人时用。在那里我写过很多社会新闻评论和很多官样文章。多年以后,我已调到省委某个部门工作,这些文章成了我的基础。在一次小河镇老朋友的聚会中,原乡镇企业局的老局长无意中说起一个关于我读书的故事。他说,也许你不知道,以前区委书记王亚光,你和他接触不多,也不太主动找他汇报工作,他却对了关爱有加。他说,有又一次,你生病时来他你家里探看,无意看到你当时搞的书房,他吃了一惊,之后多次跟其他的副书记副区长等等一干人说,“真没有想到,他妈的这个张再杰,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农村娃娃,一套小小的房子,竟然搞了这么大一个书房,很多好书,是一个爱读书人。令我刮目相看。”可惜,我当时从未听到这话,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区委书记,是一个喜欢读书、自己还写书的官场文人,他从政的水平不怎么样,喜欢感情用事,又爱朝令夕改,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但是,他写的书,却是文采飞扬,散文字字珠玑,小说结构恢弘,时代性强,还语言朴实,富有生活况味。可惜他从政时间太久,忙碌公务,作品不多,至今,我只记得他的《那年那月》、《躁动》极少数的几本。我错过了一个同样把我作为读书人的领导交流的大好机会。但是,如果我当时就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那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也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了。那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搬家,每一次看房、装修和搬家,我都没有其他别的要求,只要有一间大得容得下我全部书籍的书房就行。我妻子也知道我的性格,每到一处,全部由她说了算,但书房除外。因此,我能在一次一次的搬家中,保住我的书房,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的空间还大。别人换大房为的舒适,我换大房为的书房,别人成为房屋的奴隶,简称“房奴”,而我则成了书房的奴隶,可以简称为“书奴”。读书是我当时离开农村出门远行的理由,书箱是我参加工作时唯一的行李,书架是我结婚时唯一的家具,书房是我有房时觉得唯一需要装修的地方。如今,书房成了我下班回家后呆得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有人说,家有500册书,即可算得上藏书,现在我家里已有各类书籍5000余本,超过了10倍,有各类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民族学,其中文学类最多,占60%,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文艺理论、文人传记等等,几乎可以不出门就能看一辈子,可以算名副其实的藏书了。我在成为书奴的同时,也成了书主。坐在书房里,灯光融融,书香墨味,环视四周,图书林立,熟陌相应,如朋满座,历经千古,遍阅中外,大师莅临,鸿儒聚集,谈笑风生。看着这些从书店里买来的、从地摊上淘来的一册册书,我心里感觉到很充实,我能感觉到书中的精彩内容,或深深印象,或浅浅一笑;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交流,或同感共鸣,或引发思考。每一本书都有来历,每一本书都有故事。我能清楚的记得我在把他们买回来的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场景,清楚的记得每一部书后面与我相关的生动故事,或欢呼雀跃,或失魂落魄;或如获至宝,或故人相遇。我是我的这些书的主人,我的生命与他们交融一体。书成为我工作的基础,成为生活的内容,也成为我思想的灵光。此生,与书为伴。作者简介张再杰:在乡镇区县和省委机关工作多年。在人民网、光明网、《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党刊网》《人民音乐》《统计与决策》《情报学报》《贵州民族研究》等发表文章100余篇,参与编辑书籍和出版专著10余部。系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共贵州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精彩回顾欢迎关注贵州作家文学贵州贵州文房三宝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主管:贵州省作家协会编辑:何冲 魏昉 蔡国云野老 老八 黄 勇编辑部主任:黄山主编:魏尔锅微信号:gzzjwx投稿邮箱:gzzjwx@qq.com
 笛吹川
笛吹川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高层论坛召开
7月24日至26日,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高层论坛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主办,《小说评论》编辑部、《网络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葛建军,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张绪晃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总议题举行了1场主论坛发言和2场专题研讨,就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顶层设计、基础理论和少数民族网络作家血红小说及相关作品等话题论道亮剑、竞相发言,以推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大数据产业堪称是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的最新形态。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文化生态建设的大数据开发利用大有可为。大数据产业在给网络传媒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空间的同时,也可在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艺术生产、传播、消费方面大显身手。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中,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为独特的一脉不容忽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自1990年代末产生,历经萌芽、发展和转型三个阶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效应。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培育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还传承和发展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一全新的草根文学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新的精神家园。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指出此次论坛是全国首个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讨会,具有开创性、突破性、基础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他从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层面强调了研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醒研究者们应当注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从研究少数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题材中去寻找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特点,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在网络文学中得以体现。他提出,网络作家在创作中应当树立一体多元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以客观地、历史地眼光书写文学,防止大汉族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倾向,并表示今后将加大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扶持力度,争取尽快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的短板补上。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并作闭幕式总结发言。他指出我国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几乎是和网络文学同步联动发展起来的。经过20余年的努力,已经从文学网站、作家作品以及理论批评等方面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学特色和网络文学的民族阵营,成为中国文学大格局中一支不可小觑的文学劲旅,构成中国网络文学极具特色的一个重要板块。具有民族特色的网络文学已打造出少数民族作家新的精神家园,是文学新秀诞生和成长的摇篮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力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网络写手多,知名作家有待成长;作品丰富,但精品力作不多;理论研究稀缺,批评成果薄弱等不足。这表明,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从创作实践到理论评论,都还处于蓄势待发的创生期和成长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编审庄庸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志雄教授、湖南省委讲师团干部辅导处处长欧阳文风教授、中南大学禹建湘教授、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周兴杰教授等分别就网络文学的“贵州模式”、中华文化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产业IP开发以及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等论题作大会主题发言,北京大学邵燕君副教授担任评议人。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顾雪松教授、《小说评论》杂志主编李国平先生、《贵州民族研究》杂志副主编周真刚先生、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袁星洁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张邦卫教授等分别担任主持人、评议人,出席了专题研讨环节。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南大学研究基地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网络文学研究基地,此次论坛是该基地向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贺予飞 张若玉)[责编:李婷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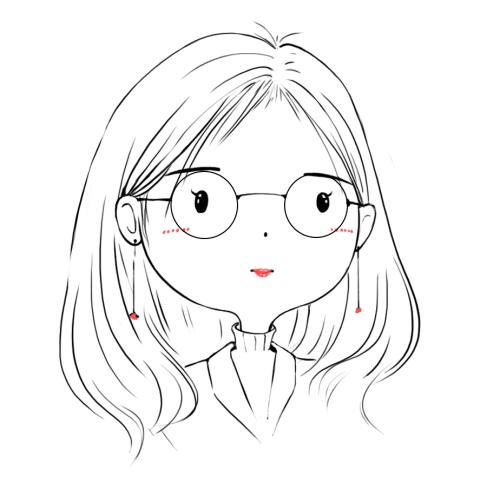 健一
健一王成志:哈佛大学藏中国贵州苗族稿本源流考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本首页。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笔者数年前发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龙里定水垻海(左“貝”右“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一册,27厘米,单页10行,红格稿纸,毛笔端正小楷;含当地苗人书信和手绘海“貝巴”苗分布图等总共约80页,简单纸捻装订,封面封底仅为与正文所用一样的额外的一张的空白红格稿纸,稿本没有页码;署民国38年(1949)。多年来,该著的图书馆编目只有标题和作者。编目记录中的作者仅为汉先二字,没有生卒年月等信息。民国晚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中,做海“貝巴”苗族田野调查而出版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不多。笔者仔细查找民国人物,包括民族研究学者,但不见名为汉先的踪迹。倒是有位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先生(1913-1998),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苗族调查的报告和研究成果;他于1949年以汉先为作者名发表过苗蛮调查文章,并涉及“海蚆苗”。作者汉先是不是杨汉先?调查情况如何?这份珍贵稿本如何得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何为海蚆苗?1949年有“汉先”为名发表的“龙里苗夷民族杂记”(《贵州民意》1949年第5卷第4-5期,第21-22页)考察了“海蚆苗”。“海蚆苗”应该就是该稿本中“海‘貝巴’苗”。但更早的1942年,吴泽霖有考察“海‘貝巴’苗”的专文“海‘貝巴’苗中的斗牛”(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硏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第228-232页)。其实,该稿本比较明确地调查确定海“貝巴”苗地理分布和历史发展等。海“貝巴”苗具有明显的服饰特征:“当地的汉人都称这种苗叫海‘貝巴’苗。原因是他们的女子所着的衣服背面挂着很多的海‘貝巴’,这些海‘貝巴’是用线穿好然后连在一快四方布的底边,方布的上一边连有两根带子,可以套在颈项上的,这真是海‘貝巴’苗女子衣服的特别标记,所以这种苗也才得这样的名称。”而苗族服饰正是该稿本作者之一的美国人类学家要收集和研究的内容。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苗族研著述中,包括杨汉先自己的作品中,“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逐渐演变成“海肥苗”或“海巴苗”。比如,史继忠用“海肥苗”一词(史继忠,《民族识别文献资料汇编》,贵州省民族硏究所,1982,第42页)。杨汉先用“海巴苗”(回顾我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贵州省龙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里县志》使用“海巴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侯清泉也用“海巴苗”(《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续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第78页,“杨汉先”条目)。龙基成的“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国苗族知识分子——苗族学者杨汉先传略”(《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50-158页,第156页)写道:杨“曾与美国学者李桂英(P.M. Mickey)一道到贵州龙里一带调查海肥苗。杨汉先自己也搜集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可惜杨氏的调查笔记后来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了。”最近的石朝江和石莉的研究认为美国学者1947年调查“海肥苗”,特别指出:“米凯,美国民族学者,她曾到贵州省贵定县、龙里县一带调查,著有《贵州的海肥苗》(1947)”(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及学术研讨会“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谐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2009年年会,http://www.mpsc.org.cn/ShowNews.asp?id=256)。如果1949年后早期可能由于汉字简化的需要和植字的困难,使用“海巴苗”代替“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那么后来民族研究学者使用“海肥苗”很可能是因为粗心不查所致,进而普遍以讹传讹。汉先是谁?该稿本开篇有“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目次”,具体如下:引言一. 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二. 海“貝巴”苗分布大概三. 籍载上所见海“貝巴”苗的痕迹四. 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五. 海“貝巴”苗的习俗“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含三节:龙里;龙耸;定水坝。“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含两节:名称;移徙历史与住局年代。“海‘貝巴’苗的习俗”一章最长,为全书重点,含九节:椎牛;订婚;结婚;巫女治病;杀过年猪;新年禁忌;除夕邀牛;新年小孩拜年;除夕与新年时青年男女的活动。该书的引言简短,引言全文引述如下:三十八年元月,奉张校长与任教务长命,随桂玉芳女士去龙里调查海“貝巴”苗。我们是元月四日离校,七日到龙里,八日到择定的地点定水坝工作,直到二月四日离开定水坝返花溪。前后计时有一月之久。在定水坝时因要事,故汉先曾回校一次,所以在工作地点时间约二十日。这次的调查费用是由桂女士担负,工作计划则颇得鲍克兰夫人指示,这是应当特别提出感激的。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汉先识于花溪不难看出,首先作者的机构为位于花溪的贵州大学。1949年,校长为张廷休(1898-1961),教务长为曾先后留学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哈佛大学的任泰。引言中特别感谢的鲍克兰夫人为德裔Inez de Beauclair博士(1897-1981),人类学家。自1941年始,在贵州、云南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苗族和仡佬族的研究。在贵州大学教德、法和拉丁文,同时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用中英文发表多篇研究论文。1951年离开贵州大学;1952年离开中国。鲍克兰夫人后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达18年之久。单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上就发表多篇英文论文。1956年与芮逸夫合著《仡佬的族属问题》。1970年在台北出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鲍克兰夫人在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1946年杨汉先被录用到文科研究所工作时,他发现鲍克兰夫人和自己是仅有的正常上班工作的研究人员。鲍克兰夫人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和著述,学术影响很大。费孝通在其“少数中的少数——《兄弟民族在贵州》之七”一文中承认:“关于仡佬的历史现在还不免多属猜测性质,我把这有些地方似乎牵强的推想都写了下来,目的只在指出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的历史材料很多是得自贵州大学鲍克兰教授,一并志谢。”(1951年3月31日《新观察》第2卷第12期)可以确定稿本的作者汉先是杨汉先。杨汉先,苗族,1913年出生于贵州威宁,1998年去世,为著名的民族志学者。1933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主修社会学。次年因家贫休学一年,1938年毕业。1941年,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重要论文“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同年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贵州大学任教。1946年7月与鲍克兰夫人到黔西调查苗族;1947年又独自去大定、黔西、赫章补充调查。1948年写出《黔西南苗族调查报告》。1949年初与美国学者去龙里调查海蚆苗。1959年至1966年,杨汉先任贵州大学副校长。他兼任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多年。杨汉先1949年与美国学者去龙里做调查的美国学者是谁?杨汉先1986年在贵州文史资料民族史料专辑上发表“回顾我的历程”。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元月,学校要我同美国人李桂英去龙里调查海巴苗,我们住在苗寨。不久就到农历年节了,我乘此机会到许多苗族家中了解情况,并看到了他们跳舞、唱歌。”(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龙基成1997年发表的杨汉先传略一文明显参考引用《回顾我的历程》,虽所提杨汉先陪的美国人英文名大体不错,但也认为是李桂英。美国学者是谁?“美国人李桂英”明显与实际不符。写回忆文章时,杨汉先七十多岁,不排除他回忆有误。事实是,1949年1月4日至2月4日,杨汉先陪美国人类学家桂玉芳到龙里做苗族田野调查研究工作。据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档案:桂玉芳(Margaret Portia Mickey,1889-1988),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人,1912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数学专业毕业。多次到中国,是调查研究中国苗族和仡佬族的著名学者。如不少奥柏林学院毕业生赴华传教一样,桂玉芳大学毕业首先任奥柏林学院院长秘书,不久也赴华传教。1914-1920年,任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华北教区传教教师和秘书。她在中国第一所女子高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Woman's Union College)教数学,并任校长麦美德(Luella Miner,1861-1936)的秘书。桂玉芳1920返美国照顾生病的父母,同时做秘书工作,包括1931至1935年任奥柏林学院图书馆馆长秘书。1935年她又回到华北教区,在通州教会医院工作;次年到日本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教一年英语。后再返美,这期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学习人类学、中文和日文研究生课程。桂玉芳。来源: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于1939年至1944年间第三次到中国,在贵州调查研究苗族。1944到1946年她转到印度北方邦的马苏里(Mussoorie, Uttar Pradesh),任教会寄宿学校伍德斯托克学校(Woodstock School)的学籍管理员。1946年她到后来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读研究生课程深造,同时继续进行人类学研究。1946年她发表贵州的海“貝巴”苗的学术论文。1947年,桂玉芳将贵州苗族田野调查成果“Cowrie Shell Miao of Kweichow”(《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于哈佛大学《皮博迪美国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刊(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以九十多页单册出版。皮博迪博物馆的创始人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为美国新英格兰棉商,1866年捐15万美元由哈佛大学创建博物馆,1877年落成开放。皮博迪博物馆为美国最早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 1907–1997)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上专门写书评,大赞其优点,但也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韦慕庭的父亲也到中国传教多年,在上海、东北等地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韦慕庭幼时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和成长;1931年从奥柏林学院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桂玉芳也在哥伦比亚大读研究生课程。《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中夹有一封当地杨家寨的苗人乡长杨正湘致桂玉芳的信。从信中看出,桂玉芳上次调查来到杨正湘家,与杨家人成为好朋友。桂玉芳第四次来贵州,于12月初给杨正湘写信,杨于12月28日回信。从该信看出,杨正湘非常高兴、期待老朋友到来,同时谈到家里人和自己的情况。这封信随没有注明年份,但很可能是1948年12月28日。信中也提到自上次桂玉芳离开已四五年没有通音讯。1949年一月的调查中,桂玉芳很可能又来到杨家寨杨正湘家。这封信也说明该调查报告稿本是桂玉芳拥有、源于桂玉芳处。1948年到1950年间,桂玉芳第四次到中国,由美国赖特学者项目(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资助,继续做研究中国苗族的调查研究。美国国务院下面的富布赖特学者项目于1946年成立,1948-1949年成功获得此项目资助的赴华交流学者有21人。当时为中国内战时期,九人“由于中国情况没有成行而取消”。能成行的12人当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和宾州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二人的“海外联系机构”项下分别为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的“专业”分别为历史和中文。桂玉芳的“海外联系机构”为华西协和大学及其华西边疆研究所(West China Frontier Institute),专业为“人类学”。美国“国内机构”列为“无”的桂玉芳为1948-1950年赴华学者,1948年8月获得资助。1941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1900-1985)任社会学系主任和副所长,校长张凌高(1890-1955)任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虽然经费一直不足,但研究所成员精干,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生机勃勃,成果斐然。 桂玉芳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工作,她花很多时间做苗族服饰图案式样的研究。1948年,桂玉芳非正式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目录学著作一部“A Bibliography of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n-Chinese Peop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s of Adjacent Areas: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国华南和西南:非汉民族及其与邻近地区民族关系西文目录》)。1949年元月,她与杨汉先到贵州龙里定水坝做田野调查。根据二人调查结果,杨汉先于1949年三月完成调查报告的稿本。因此,该报告的资助单位应该是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项目,作者应该是桂玉芳和杨汉先两个人。1950年她应该利用了1949年她与杨汉先一起合作进行的田野调查结果,非正式出版56页的《贵州的海“貝巴”苗:增补和订正》,对1947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论文专册《贵州的海“貝巴”苗》做适当的增订。1951年至1954年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工具书出版公司G.& C.韦氏公司(G. & C. Merriam Company)编辑部工作。后退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国会图书馆研究苗族服饰女性服饰图案式样中体现的象征主义。最后定居于加州的波莫纳(Pomona),利用之前在中国收集的苗族资料继续做研究。如何到哈佛大学?据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的桂玉芳档案,1976年,已87岁高龄的桂玉芳视力明显转差,她与哈佛校友朋友任北亚利桑那博物馆(Museum of Northern Arizona)馆长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内德丹森(Edward Bridge “Ned”Danson,1916-2000)商量她的收藏的可能去向。自三月始,他们致信给当时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馆长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1926-2017),希望将桂玉芳收藏的苗族研究文献、实物、图书、手稿、信函和照片等捐赠给皮博迪博物馆。五月,威廉姆斯馆长回信同意桂玉芳的收藏比较独特,欣然接受捐赠。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桂玉芳档案含等数百种苗族女性服饰、刺绣图案临摹稿及其说明,中国神话故事和传奇的翻译,中英文图书、中国国画和苗族宗教、音乐和工作有关的实物等。信函包括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葛维汉(David C. Graham, 1884-1961)和1948到1950年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白天宝(J. Calvin Bright,1915-?)等人的信件。1976年6月12日,在给威廉姆斯的信中,桂玉芳回忆她对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研究的缘起,与葛维汉有关:1941年12月,我到华西协和大学校园中浸信会的葛维汉夫妇家里做客。他当时是该大学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他把自己收藏的100件文物和川苗女性的900种刺绣服饰捐给该馆。我对这些服饰的图案设计特别感兴趣。1949到1950年,我又到华西校园。1949年12月,中共已到成都。在任命新官员之前,他们不许美国人离开成都,所以我一直在那里住到1950年8月才离开。在这7个月左右,我把这些苗族服饰的十字绣图案,全部快速临摹下来。这些服饰由深蓝棉布以以及白色和彩色丝织刺绣组成。我不得不使用在成都能找到的任何有白底、能画出图案的图纸和中国(印度)墨料和彩色颜料。我没有时间临摹缎织品的图案式样。她写到,回美国“在克莱蒙特(Claremont)安顿下来后,为让这些图案式样保持一致和减少我之前匆忙临摹的错误,我花一年半时间再次仔细转画。我有一箱这样的图案式样。”同时桂玉芳介绍自己对这些服饰图案式样进行深入研究。成都解放时,华西协和大学一位杨姓中国艺术教授由于所教的课程不能继续,向当时博物馆馆长白天宝建议,由杨教授为她讲解和分析这些服饰图案的象征意义。二人一起分门别类整理出30多种图案主题,并做详细笔记。1954年,桂玉芳花四个月时间到国会图书馆全面研究西文文献中图案式样的象征主义,并做了三本活页笔记。然而,由于年岁已高、视力下降严重,无人协助的话桂玉芳打字已经很困难。她出版研究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的著作的想法就没有实现。但她深信这些苗族文献在美国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在捐赠时,她要保证邮寄运输这些文献到万无一失。颇费一番周折后,皮博迪博物馆通知她档案收到无虞。其实早在1946年,国立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和西南文化研究所致信皮博迪博物馆等,希望建立国际学术合作交换关系。1946年5月9日皮博迪博物馆唐纳德斯科特(Donald Scott,1879-1967)馆长写信给桂玉芳转述贵州大学的来函:“敝省的原始部落快速采用汉语和汉人风俗,将导致土著民族文化很快消失。可是,目前贵州本地民族文化实物甚丰,比如各种装饰精美的民族服装和纺织、蜡染和刺绣服饰,以及仍在使用的如芦笙、竹笛和铜鼓等各种民族乐器。敝所愿意向海外博物馆提供这些实物样本以供收藏。作为交换,期待贵方提供图书馆所需的书刊以及人类学工具和照相器材为感。地址是,贵州省贵阳附近花溪。”斯科特馆长就此事请教桂玉芳:“你知道,博物馆收藏特种实物或有展览价值的物品的兴趣,远不及对民族部落使用的日用品的完整收藏。我们愿向贵州的西南文化研究所建议是否可能建立这样的收藏,若可能,费用如何。在贵州何地、何民族部落获得这些藏品。你对贵州深为了解,我现特向你征求高见。我很感谢你的帮助。等收到你的回信后,我再回复贵州大学。”至于随后桂玉芳如何帮助贵州大学和皮博迪博物馆建立合作交换关系,皮博迪博物馆档案中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1946年八、九和十一月,以及后来1948年的八月,皮博迪博物馆收到桂玉芳捐赠的贵州苗族以及日本人的服饰、吉祥物等物品。而且,1947年皮博迪博物馆向代表贵州大学的鲍克兰夫人顺利购买一些代表贵州和贵州苗族民族物品和照片,1948年博物馆收到。如何转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经桂玉芳同意,她捐赠的图书部分可根据图书的性质由皮博迪博物馆的档案馆确定分别转送该博物馆的托泽图书馆(Tozzer Library)、哈佛大学的佛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图书馆和燕京图书馆保存。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877年皮博迪博物馆落成时,其图书馆也同时落成开放。托泽博士(Alfred Marston Tozzer,1877-1954)于1934年至1947年间任皮博迪博物馆的图书馆馆长。1973年主要利用托泽家人的捐款,该图书馆的新楼建成,为纪念托泽博士而冠名该馆为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于1979年正式转隶于哈佛学院图书馆系统(Harvard College Library),但仍与皮博迪博物馆保持密切关系。佛格艺术博物馆的成立与中国有渊源。十九世纪中后期源于波士顿、后迁至纽约的著名对华贸易商佛格(William Hayes Fogg)去世后,其妻佛格夫人(Elizabeth Perkins Fogg)1891年将佛格生前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和20万美元巨资捐赠给哈佛大学创建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佛格艺术博物馆于1895年落成开放。1927年佛格博物馆的维修实验室和研究图书馆等成立。1962年佛格博物馆的图书馆正式并入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与其艺术图书文献馆藏合并而成为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Fine Arts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受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基金资助于1928年成立。其同时成立的图书馆名为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改隶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但与哈佛燕京学社依然保留密切的关系。哈佛燕京学社及其图书馆对中国现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细查《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第一页也就是目录页,在含有地址的英语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章下,有手写铅笔字迹两行,不大清晰。仔细辨认后可以确定为Gift of Portia Mickey (桂玉芳捐赠)和Trans from Tozzer(托泽馆转来)。紧接下面,盖有日期章:Nov 9, 1976。很明显,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收到该稿本后,先转送给哈佛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再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11月9日正式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结语《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是1949年初华西协和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桂玉芳和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汉先合作对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进行田野调查的中文报告,由杨汉先执笔撰写。该稿本由桂玉芳从贵州带到四川,再带回美国。1976年她捐赠给哈佛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转送哈佛托泽图书馆后,最后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保存。《黔苗图说》图片来自网络皮博迪博物馆及其档案馆除藏有桂玉芳和鲍克兰夫人有关的中国苗族实物和档案文献外,还收藏有很多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藏品和档案文献,比如以照片为主的、反映中国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伍尔辛(Frederick Roelker Wulsin,1891-1961)特藏和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特藏。同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的善本书和档案特藏,比如,非常稀见的《黔苗图说》《苗蛮图说》《滇苗图说》,以及源于洛克的纳西族东巴文手稿收藏。此外,以照片和书刊为主的毕敬士牧师中国穆斯林特藏(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和以蒙文晚清和民国图书为主的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特藏,都非常丰富和珍贵。近年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化扫描工作,与国内不少机构合作,系统地将大量珍稀图书和特藏文献进行数字化,对外线上免费开放使用,真正使哈佛燕京的善本和特藏成为天下公器。这是让哈佛之外的研究者尤其感到方便和高兴的事。(致谢:非常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特别感谢中文部主任马小鹤老师、古籍善本部王系老师、哈佛皮博迪博物馆Katherine Meyers Satriano和奥柏林大学图书馆朱润晓老师提供的帮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