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在
实在中国法院改革的内部治理转向——基于法官辞职原因的再评析
来源:基层法治,原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6期摘要:在有关法官和法院的议题设定中,法官流失是一个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主题。研究者多将法官流失归因于法官待遇差、法院机构地位低,但是实际上,法官流失的原因多种多样。法官货币和非货币收益的大幅度改善,证伪了法官辞职与法官整体福利指标之间正相关性。法官辞职的真正原因在于法院内部晋升的各种非正式规则严重影响到正式职务晋升制度发挥作用。法院职级晋升上的异化,导致优秀法官相对剥夺感增强,因而以选择离开的方式表达不满。法院改革的中心在于内部治理,而主要不在于外部对法院人财物的制约。法院改革应进行内部治理转向。关键词:法官辞职 法官待遇 法院改革 内部治理本文提交2017年11月18日第二届法律社会学青年学术论坛,发表于《法商研究》2019年第6期。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现代西方诉讼构造的观念体系下,司法体制改革的中心议程被设定为法官中心、法院至上。为实现此目标,研究者集中论证法院机构地位应拔高,法官待遇应提升,如此才能吸引法学精英、律政先锋进入法院,法院的公共信任度和民众认同才能改善。由此为导向,多年来颁布的众多方案,都以扩大法院干部职级比例、提升法官福利水平为真实内涵。法院的机构地位、法官的福利水平,从历时性看,获得巨大提高;从共时性分析,较之许多同级党政机关和律师都有较大超出。但是,在有关法院的作品中,以法院福利待遇低为主题的研究始终弥散。晚近,“法官流失”一词开始被高频使用。这些研究的归因逻辑线路是:法官流失→法官待遇差→法官缺乏职业保障→司法的人财物受制于外部。本文对此归因路线进行拆解,对于法官辞职和由此牵引出的法院内部晋升中的积弊,重新进行分析。如何实现良好的法官晋升激励机制,应是法院改革的中心之一。将司法改革集中于去除人财物受制于外部的定位,遮蔽了真实的痼疾所在。本文使用的“转向”(turn)一词为借用。西方哲学先后经历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每次都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哲学的内容。“转向”并非否定先前,而是自我更新。对法院改革进行内部转向,建立一个优良的法院内部治理,与践行系于司法的政策目标具有更紧密的关系。一对法官“流失”相关数据的精细拆解何谓法官流失?定义域内的“法官”,是指中央政法编制内助审员以上人员;“流失”指法院统计报表中,中央政法编制内助审员以上人数减少。两者都须辨析。其一,不包括非中央政法编制人员。从“一五纲要”开始,法院书记员被要求实行合同聘任制。2004年之后试点法官助理的法院,部分法官助理也临时聘任。这两类人员,非中央政法编制。大量刚毕业学生,应聘担任合同书记员、法官助理,目的在于积累司法经验(俗称“刷履历”),三年合同期满即转考公务员、进律所或升学,人员流转极快。部分律所合伙人、学者见求职、考研者中有法院经历者日益增多,错以为大面积法官离职。其二,同样是中央政法编制内法官离开法院,须细致区分以下各类情形。第一类,并非“我要离开”,而是“要我离开”,是有意驱离。包括:(1)清理调出。如最高法院规定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情形应予清退。(2)精简。如2000年中央编委要求法院在政法编制控制数基础上,按10%比例精简,部分法官“提退”。(3)因违纪被处分、双开,因犯罪被判刑。2003年,全国法院处理违法违纪案件1297人,其中法官794人。第二类,自然减少。包括:(4)正常年龄退休;(5)任职期间病故。第三类,(6)职务晋升或交流至其他机关任职。第四类,离职。2014年,中央决定法院保留39%的员额。但与历次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时,干部向行业协会、企业分流不同,法院未入额人员并不分流到法院之外,仍保有公务员身份,只是不再担任法官。少数未入额法官因失落而离职,出现:(7)离职升学、转考其他公务员。(8)辞职做律师、法务。由上可见,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法官离开法院这一行为每个个体意义各不相同,计量法学偏爱的大规模数量统计结果,在此没有一个统一意义。“流失”一词,仅增加了思维成本,属于奥卡姆剃刀所称“如非必要,勿增实体”的赘词。真正为普通公众关注,纳入本文讨论对象者,只有第8类。但是,作为一种宣传策略,媒体并不仔细提供每一个数字指向的个体事实,而是采用典型事例加一般数据的手法,即:通过简单枚举,将最突出的法官辞职转做律师的例子进行放大,然后再给出一个规模数据。给外部观察者传递的印象即是:法官离职,都系法官待遇差和无司法自主权,导致留不住人。如果不是从强烈意识形态前见出发,当代人对公务员离职都有平和的心态。现世的人追求的目标日益多样,尤其在当代电子、网络、交通条件下,时间感、空间感较此前大不同,人的心理体验异于以前,各种抱负多元。没有任何一个职位,能安放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心灵。即使在世俗者眼中身处高不可及职位的官员,都有辞职转做律师者。但对党政机关人员分流和辞职从事律师,部分研究者认为是解决机关臃肿、克服官僚化的治本之策,媒体的方向是鼓与呼,不会将之与待遇进行勾连。但一到法院,整个舆论被引导到法院待遇低、法官收入差,直至司法受制于人等大叙事。法院将部分研究者对法官辞职原因的归纳,援为根据,将之作为诉求更多待遇改善的根由。2000年,中央编委部署全国法院减编10%,但编制返还,用于书记员改革。然而,在次年最高法院给中组部的报告中称:“审判人员的职级配备偏低、社会地位没有很好得到保障,影响了审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致使审判队伍不稳,业务骨干外流,仅2000年一年之间全国四级法院共外流2017名干部。这也是造成法院取证难、办案难、执行难的客观原因之一,势必影响人民法院裁判的严肃性和法律的权威,也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将法官辞职进行单一归因,归结为法官待遇差的断言,首先遭遇比较法证伪。部分研究者对中国四级法院,包括对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法官进行制度设计,原型都出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美国有联邦和州两套司法系统,各州法院芜杂,州法官有任期限制、非终身,非任命制,而是选举,职权、声望远不及联邦法官。1789年宪法第3条规定,只要联邦法官行为端正(ring good behavior)就可以保住职位(hold their offices),也就是除非渎职,哪怕重病至不能履职,如晚年的道格拉斯大法官,只要自己不离职,无法将其免职。对整个联邦法院,按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说法,2000-2005年有38位法官离开法院。波斯纳的数据是:这六年间,总数1200位现职和资深联邦法官中,有12位辞职;1969-1974年,总数720位法官中,有10位辞职。1981年到2007年,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也有8位辞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2000年流失2017人的数据,以当时中国法院政法编制30万人计算,流失比例0.7%。相比美国联邦法院,罗伯茨的数据为3.6%,即使按波斯纳的数据,比例也为1%。因法官待遇差、法院没有吸引力而选择辞职,这种看法也与普通公众日常经验发生矛盾。普通公众对职业选择热点的观察,有两个风向标:一是军转干部。在1980年代前票证经济下的物资紧缺时代,军转干部最中意择业方向是百货公司、供销社等商业批发、零售单位。去公检法的人员,各方面能力要次一级。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商业凋零后,公检法,尤其法院,是工作能力强的军转干部的首选。另一个是领导干部子女。一些地市、县区负责人在解决子女就业时,首选进政法机关。在通过公开招考录用法院公务员之前,一些人能进入法院,是基于家庭背景。“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各部门岗位的高低优劣,深深浸于体制内的亲历、参与者,其体验和判断必定胜于通过键盘、屏幕了解世界的书斋摇椅上的研究者。如果说法院待遇差、法官收入低,导致大批法官辞职,那么军转干部、领导干部子女的选择就是非理性的。这显然与经验抵牾。当然,在离职法官中,并非政策性分流、退休、交流任职等情形,而是从事律师等市场职业者,有一定数量。但是,中组部等主管部门查知不少公务员辞职,目的是“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断言法官辞职从事律师即是福利待遇差,而不剔除目的是为了给权力贴现从事居间、中介的情形,难以服人。对此,最高法院政治部亦承认“实践中,确实存在极少数法院工作人员辞职后从事与原职务有经常性直接关联的业务活动,利用曾在法院工作的便利条件与法院内部人员进行利益输送,或借助自身的影响力扰乱正当的法律服务竞争环境等问题,引起社会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议论和反感,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对于法官辞职后的行为进行具体限制。经过以上精算,“流失”法官至少有8种情形,仅第8种为主动辞职从事律师、法务者,其中再剔除目的就是为了中组部等部门察觉的“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剩下的动机单纯从事律师者,所占比例并不大。那么,仅就这一部分辞职法官的行为作根据,是否即可断言法院机构地位低、法官福利待遇差?假设是,那么,此意味着法官福利与离职之间具有一个正比例函数关系,如果法官福利改善,辞职即会减少,相应法院就福利改善,向媒体造势和决策层的吁请也会减弱。谱绘近年法院、法官货币和非货币收益的图景之后,发现这一函数关系并不成立。二法官福利指数的改善证伪了其与法官辞职之间的正相关性较之马斯洛心理层次说,极为直白的表达是俗语所称的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列入法官个人福利多目标追求集合U=(a1,a2,an-1,an)中最重要的四个项目是:职级、个人货币收入(工资福利、个人住房等)、非货币收入(与职权相关的的职业尊严、办公场所条件等)、悠闲(工作负担等)。对法官福利指数改善的测评,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向度。(一)历时性向度1.职级分两种,一个是职,习惯称“实职”。另一个是级,习惯称“虚职”。如,地市级中院的庭长,是正科职位干部,但是区分资历,法院党组会与地方党委沟通,将部分任职年久者安排为副县级审判员。从中发1979年64号文件开始,法院院长级别被高配1985年,中办又发文重申。1987年,进一步对地方各级法院审判员、助审员级别给与规定。为避免僧多粥少,1987年对法院各级别干部的比例进行了固定。2001年,又对比例进行了提高。不仅在“虚职”上不断提高,对“实职”,中央和地方党委,通过给法院不断增设庭室、先后增加政治部主任、执行局长进党组、增设2-3名专委等职务新品种,给予倾斜性照顾。[5]2014年起,为最高法院先后增设六个巡回法庭,每个法庭设两名副庭长,每个副庭长都是正厅职。虽然庭长由本部副院长、专委兼任,副庭长由本部审判庭庭长调任,但是院本部提升部分干部补了审判庭庭长原位。通过增设机构、增加职数比例的多年掘进,法院的职位数量激增。在广东高院,2013年,不到500名中央政法编制的规模内,领导班子成员20人,另有副厅级干部8人。不包括数量较多的处级、副处级审判员,实职副处以上共117人。2.工资福利等待遇1998年,中央要求对政法机关的行政办公经费,按照高于当地一般行政机关一倍以上标准予以安排。按照财政部的数据,1995年,全国公检法支出298.84亿元,是1990年的3倍;人均公用经费支出11284元,比一般行政机关人均公用经费支出高5658元,基本达到一般行政机关的2倍。这种优先保障,一直持续,尤其在2009年后,政法经费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级分类全额保障,更加强化。具体至法官个人,《法官法》仿照军衔、警衔,给法官设置了衔级制度。为其建立一个类似军衔、警衔的衔级制度,目的只在于效仿军队、公安增发薪酬。对于标准,最高法院提出“审判津贴标准本着与工资之和高于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20%-25%确定。” 中央在2007年,同意最高法院要求,继军队军衔和公安、安全机关的警衔补贴后,根据法官等级每月发放180-340元的审判津贴。3.个人住房2003年,著名的国发18号文件对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意义进行提示,此后房地产业发展迅速,许多人的收入赶不上飞涨的房价。但是,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国家机关,财政部门颁发了各种补贴。各地法院也多以集资合作建房等方式,以低价格解决本院干警住房。在北京,房价上涨迅猛,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国光讲述: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亲自找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基本解决了正局级和部分审判骨干的住房。”4.与职权相关的职业尊严在以法官个体独立为基本观念的思潮熏染下,2015年“四五纲要”推进法官个人责任制,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对大多数案件,庭长、主管副院长、院长不再批案,具体案件的承办人自由裁量权日益扩大。按最高法院的数据,改革后,“取消行政化的案件审批制,确立合议庭、法官办案主体地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全国法院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直接签发裁判文书的案件数量占到案件总数98%以上。”法官的职务获得感线性增长。5.办公场所门楼高低、办公场所的优劣,构成人员非货币待遇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最高法院数字:“十五期间”,全国70%以上法院改建、新建了人民法庭、审判法庭和办公用房。全国法院新增车辆2万多辆。五年间,全国法院物质装备建设共投入资金近200亿元。在各种激励作用下,法院办公场所建设在近三十年,获得极大发展。6.工作负担法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文书撰写。传统上,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审理报告、各种笔录等文书制作完全依赖手写,手写文书的审批、传递、打印、校改也耗用大量精力。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判例检索也极为辛苦。晚近,办公用计算机、数据库、办公局域网络、语音转换、电子卷宗等手段使用之后,相关工作负担大为减轻。在实行人员分类制改革后,合同制法官助理、书记员大量聘用,审理案件的法官主要精力集中在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事务性工作负担减轻。当然,各地案件负担极为不均衡,2017上半年全国法院受案数量排名前三位即是上海浦东新区、北京朝阳、广州越秀。在受众印象中,抱怨案多人少、待遇差和法官辞职比例最高的主要是京沪穗三市。为解决三市的案件负担,中央决策层给与了积极应对,方式之一是增设新法院。在京沪,一个中院在1995年拆分为一中、二中院。1998年上海、广州两个海事法院分别由交通部移交两市。2012年,驻在京沪穗的铁路运输中院及基层院,分别由对应的路局、分局划归三市。2013年增设北京三中院。2014年增设北京四中院(铁路),上海三中院(铁路),另为京沪穗增设三个中院级别的知识产权法院。2018年再为上海增设一所中院级别的专门法院上海金融法院,为京穗两市各增设一所基层院级别的专门法院:北京和广州互联网法院。加上司法改革后管辖跨辖区案件的专门法院北京、上海、广州、广州第二铁路运输法院,北京有5个中院,2个基层法院级别的专门法院;上海有5个中院,1个(基层法院级别的)专门法院;广州有4个中院,3个(基层法院级别的)专门法院。数量极大超出其他城市。此政策效应溢出,产生正外部性,不仅为这三市法官实际减少了负担,更极大增加了职级比例。增设一个法院,需从全市调配法官,激活了全市法院职级调整,整个干部职级都动态提升。由上可见,以历时性眼光看,在1979年中发64号文件三十多年以来,以干部职级和货币收入两项为核心的法院、法官整体福利待遇水平不断提高,整个曲线方向向右上倾斜。(二)共时性向度前部分通过历时性方式查勘了法官收益效用由多个参数构成,通过法官收益变化,证伪了法官离职与福利待遇低有关。再以律师、公司法务、其他政法机关人员作映衬,以共时性方式,对法官福利效用函数查勘,从对比中尤可看清真实状态:1.职级考评法院职级待遇,常被研究者作为参照物的是党委和行政机关。但中央组织工作文件,在对法院干部的职务配备上,明确要求“法院审判业务人员的职务配备规格和职数比例略高于同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尤能体现法院职级待遇优越的是与检察院的对比。检察院反贪反渎和预防机构转隶之前,“一府两院”中,两院历来被等量齐观,但在实际职级待遇上,法院高于检察院。1996年机构改革,中央批准的方案中,高院内部机构为15至17个,对应的省级检察院为14至16个;中院为14个,对应的市级检察院为13个;基层法院设置9个,对应的县检察院为8个。2001年机构改革,法院同样保持了对检察院的超出。2.工资福利等待遇列入中央政法编制保障的法官,不仅是当期现金收入高且稳定,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还有完全可预期的退休收入,无生存压力之感。在律所工作,收入完全无预期,常有基本意义上的生存压力;在丧失劳动能力后,完全无退休工资;在任何公司工作,都会有破产、失业或被减裁之虞。3.个人住房1994年律师制度大变革之后,律师“不再使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和行政管理模式界定律师机构的性质”,而是“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律师自嘲是法律个体户,不存在机关优惠集资建房和财政补贴等福利。4.与职权相关的职业尊严法官坐在法庭正中、高于检察官席的审判席上,面对站立侧旁接受质证的出庭侦查人员,以及需举手示意才能发言的公诉人、律师和各种诉讼参与人,法官有强烈的自我实现感和职业愉悦。从事律师,生存依赖于案源,拓展案源面临激烈竞争,需要加强社交和形象塑造,法官做久之后,角色转换并不容易。将检察官和法官的职业尊严感进行对比,尤有说服力。检察工作基本以刑事案件侦查、批捕和起诉为主,法院更多是自然人、公司等私主体之间适用“处分原则”的民商事纠纷,不仅案件性质不同,而且人均案件负担差异极大,加之强调法官自主,所以在案件决定权的层级分布上,同为案件承办人,普通法官职权较之普通检察官大的多。虽然在2018年反贪反渎和预防三个机构职能转隶监察委之前,作为一个机构整体的检察院,在职权上与法院并无大的差距,但检察院奉行上下一体原则,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和同一检察院内都是上级领导下级。检察权分布为倒金字塔型,大要案权力集中于上级检察院;在每一检察院内部,事权又集中于检察长、副检察长,承办人决定权极小。[23]因此,普通法官的自我认同要远高于普通检察官。此外,随着可诉性、诉权的日益扩大,法官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不断趋强。5.办公场所法院基本都有良好办公环境,设施维护运转,由财政和法院经费负担,无需法官个人承担任何费用。法官办公场所条件的优良,虽然不是直接注入的货币,但是作为非货币收入,实实在在地转换成了健康和幸福感。许多律所也有豪华办公场所,原因在于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是一种信用品、经验品,而不是搜寻品,客户筛选律师只能依赖服务品质信号。所以,律所多使用资产符号传递品质信息,高端律所都租用豪华写字楼作为办公场所。但律所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个人集合,律所各种费用由合伙人分摊,每个独立结算律师都根据自己使用律所场地的方位优劣和大小支付费用。做律师如逆水行舟,不管当期有无收益,租金和各种费用催收不免,压力、焦虑无时不在。6.工作负担与行政权的积极、主动相比,司法权被给出的职责是消极、被动。这决定了法官工作方式应当是在审判庭内听审,或是办公室阅读文书材料,基本不需要野外工作,尤其是审判工作性质不具有突发性、应急性,不需要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作出应对,拿出工作实效。仅就工作负担最重的刑事公诉案件而言,按照刑诉法156、202条规定,审限也有三个月,如果“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等情况,审限还可延长到6个月。在如此长审限内,法官可以自己调节工作节奏。对比公安人员,一线民警每四天一次24小时在单位备勤值班;不论酷暑的正午、严寒的深夜和节假日,不管潜在危险多大,值勤的男女民警,接到110出警通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出警。而律师,不论时间早晚,更是要被委托人、客户随时电话备讯,被大客户召之即来,否则可能在当期会被投诉,更无法得到下阶段的委托和收费。由此看,单独拆出来法官福利指标体系中某一个,与同级党委、行政机关中刻意选出的指标比较,法院可能不占优,以各项指标总和,以整体福利来比,法院具有最大优势。2017年员额制完成后,全国不少法官就地躺倒成为法官助理,但绝大多数都不选择辞职。最高法院公布了近年辞职法官的比例,仅在0.35%以下,这对本文的论断进行了补注。此外,作为不带偏见的学术研究,在方式上,以整体主义方式论证,会产生精准度欠缺,应将法官与律师进行个体主义比较。律师内部,收入水平悬殊,阶级、阶层分化严重。在职级晋升上,升至厅级以上高级法官者固然是少数,但年收入千万级以上的“大par”(业内对高收入的高伙partner的习称)更是少数。作为研究者,不能隐匿律师业最大的制约条件——“案源”,否则,即会误导旁观者,给局外人带来一个错误印象,似乎是:法官转做律师,客户即扑面而来,“无边案源萧萧下,不尽收费滚滚来”。行业内人士都知道,在法律服务市场,拓展案源如任何有形商品市场一样残酷艰难。律师收入有名、暗收入之分,部分诉讼律师灰黑收入极高,原因在于有特殊通道,如黄松有、奚晓明案件中的律师。这种收入模式,非其他律师能移用复制。2018年底,全国律师数量近40万人,大部分律师在从事收费低的简单业务。在访谈中,当初“冲冠一怒为待遇”而从法院离职做律师却案源匮乏,坦承后悔者不在少数。但是,将法官和律师收入进行比对的研究者,其策略实际是一种变形后的“田忌赛马”。对律师序列,排序是:A京沪穗年收入千万级的律师;B京沪穗年收入五百万级的律师;C收入百万级的律师;D中西部年收十万元以下的律师。对法官序列:甲:县区法院院长、中院副院长以上法官;乙:中西部县区法院副院长;丙:中西部县区法院庭长;丁:中西部县区法院普通审判员、助审员。对比策略是:A —乙;B—丙;C—丁。但是,在律师群体中占最高比例的D,被弃置不提。而且,对比例不超过律师总数10%左右的ABC三类人,在媒体聚光下过度渲染,在报道上无限放大。实际上,“一五纲要”以来历次司法改革,都以增大法院权力,扩大法院干部职级,提高法官福利待遇,为公开的或隐蔽的真实内涵。虽然在研究手段上,外部观察者极难获得一个较长时段内全国或一个省法官流失的数量和具体详情,仅以法院和媒体给出的数据片段,传递的图景是法院和法官的福利不断增强,而法官流失越来越严重。这即证明法官离职与福利指数没有正相关性。以整体主义方法论,将法院待遇差、法官福利低,作为法官离职原因,无法成立。那么,实践中,确实有不少法官离职,原因何在?三法院内部职级晋升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细析本文作为分析根据的各项指标体系,其中办公场所、人员经费、福利等要素,对在同一个法院工作的法官群体来说,不因人员编制增长而边际收益明显降低,属于类公共品,所以在成员内部之间不具有竞争性。本文认为,测评“流失”法官中离职单纯从事律师那一部分人的离职原因,职级晋升是最值得关注的变量。理由如下:(1)财政供养官员的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在现代官僚制建立后,都与个人职务职级正相关,福利目标集合中的其他各项条件,都与职务职级有对应关系;(2)职级具有稀缺性。在科层制社会构成单元中,职务分布为金字塔型,对应的是差异性分布的人数,愈向上,人数越少,稀缺性愈强;(3)人非索群独居,如亚里士多德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与蚂蚁、蜂群等集群动物不同的是,作为城邦/社会集群中的人,建立了一种自我认同,即“我是谁?”。这在库利的“镜中之我”理论看来,取决于“我”投射于外部后,别人的判断。在职务高度稀缺的给定条件下,获得晋升,意味着能力、水平被认可,社交圈、被媒体关注度更高,自己抱负施展、自我认同的实现期许也更强。从而,职级一方面具有直接货币收入差异属性,另外则具有非货币意义上的尊严和认同属性,具有独立变量意义。因此,职级晋升成为公务机关内许多人的竞逐目标。由于职级晋升引发竞争,职级差等成为撬动法官行为最有力的杠杆,法院因此刻意构建一个差异性的职级序列,利用职级对法官行为进行诱导和控制。之所以如此,因为在法院内部另具有不同于其他公务机关的特殊性:(1)法官有最后裁断权,裁断之上无裁断,而大量诱致法官做出裁判的行动不可查测,据以做出裁判的内心纤细意志无法以外显方式展示;(2)实体法、程序法、证据规则,对于法律适用具有约束力,但都无法完全禁绝法官在事实认定上的心证空间;(3)为遏制法官寻租、权力贴现,通过事先规制、事中约束、事后监督,都只能起部分作用。不滥用自由裁量权,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法官个人的自我内敛。因此,建立一个晋升阶梯,通过职级晋升,保持对法官行为的激励,诱导法官对可能偏移的行为进行自我规训。在法官数量庞大的现实状况下,法院尤其需要一种控制机制实现内部秩序,细密的职级分层从而成为手段之一。由上可见,个人的追求和法院的有意诱导,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得职级晋升成为法院内部秩序中的中枢问题。职级晋升也因此成为微观政治中最复杂的现象。之所以复杂,因为在各种政治机体内,都多少存在着职级晋升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规则。职级晋升,标准应当是能力、业绩和政治忠诚。不管是现代国家还是前现代家产制下的政治体,正式制度的要求都如此。但是,在历来的政治中都存在各种非正式规则,对官员的升迁,具有实际影响力。非正式规则,不见于文,只可从现象中查知;非正式也不意味着不占支配地位。相反,非正式规则常能抑制正式制度。职级晋升中的非正式规则,为西方研究者所过度关注的是所谓站队、派系、山头(factionalism)等行为,但在法院内,另有不为正式制度研究者所瞩目的许多微小却具有作用力的行动。例如:(1)在后勤设施陈旧时代的许多法院,早晨上班第一件事是内部勤务,包括拖地板,到单位的锅炉房给办公室的暖水瓶灌满开水。坚持这样做的普通干警,都会给其他人留下良好印象。(2)笔录和判决书、裁定书的稿本、审理报告以及各种文书都是手写,而一个人字写得好坏,影响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对一个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的评价。一些干部通过这样的方式,长期的自我“印象管理”,多会将一个勤勉的形象沉淀在领导和同事印象中。各种法官职级晋升中的非正式规则能够畅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低度的司法知识专业化。中国大规模民商经济立法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此前,法院审判工作所需各种专业知识,基本流于粗放,案件主要是自然犯类型的刑事案件和婚姻家事案件以及简单民间债务纠纷等。其中多数案件,仅凭人生阅历和日常朴素的伦理观念即可裁断,法学科班出身与未受过学院内法学知识训练的法官,在专业能力上的位差,远无理工科、医学等门类那么明显。通过前述印象管理方式,非科班出身干警,也能在提拔时获得青睐。本文例举的这两种非正式规则也在近年失去依托。原因不是来自强制规范的禁止,而是社会经济演化释放出的转变。多年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法院“两庭”建设投入,法院都兴建新办公楼,使用了自动热水器、饮水机,机关清洁多外包给物业公司;办公用电脑普及,司法文书都在各自电脑上敲击,部分“智慧法院”已实现裁判文书自动生成,通过办公系统传输审批、打印。通过打开水、拖地板、苦练硬笔书法等对形象塑造,在法官晋升中的意义淡化。但是,包括地域、山头、职业出身和各种单位政治等在内的干部晋升中的更多的各种非正式规则,实际被压制,来自于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这一正式制度的颁布实施。从1982年开始,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标准,中共中央对各级干部大力更新换代。在四项指标中:(1)革命化,主要是看文革期间的表现。但不属于“三种人”,而是所谓随大流的“观潮派”和普通群众,数量庞大。(2)年轻化。中央对省部、厅局、县处等不同级别拟选任干部年龄设定了上限,如省部级干部,“掌握在四十岁左右和四十五岁左右这样两批人”。以中国人口基数规模,符合这两个年龄段的人,群体数量同样庞大。(3)知识化。建国三十年,全国大学毕业生只有30万人左右。作为知识化表征的文凭以其稀缺性成为强有力条件。(4)专业化。1980年全国仅4所政法学院、22个大学法律系,在校学生占高校学生总数0.5%,1949年到1978年毕业政法学生2.9万人,占同期大学毕业生总数的0.9%。。因此,以同时符合这四项指标作为根据选拔干部,实际上是最具有稀缺性的法律本科文凭,成为杠杠支点意义的变量。俗称“文凭是个宝,年龄少不了”,“以文凭一刀切”,成为这一时期干部选用最大特点。除了1980年代初中期破格提拔文革前大学生之外,在随后的干部提拔中,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大学生迅速进入干部培养梯队。这与当时法官学历状况有关。从1984年统计看,全国法院15万人,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为3%。1990年,全国法院22.54万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4.9%,地方法院审判员和正副庭长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3.2万人。直到2002年《法官法》之前,法院大多数人都是“业大”专业证书文凭。法院统计数据内获得本科学历的,也基本是党校函授、电大、自考等成人教育形式。2001年,即使在文化教育水平相当发达的上海,规定选任审判长资格的学历条件时规定:一般应具有法律本科以上学历(含在读本科)。鉴于符合条件的人可能较少,放宽规定特别优秀的业务骨干须具有法律专科学历(含专业证书)。经过多年文凭政治演生历程后,决策层和组织部门有越来越多经验,逐渐不再以单一的文凭选拔干部。原因:其一、由于文凭附加值极高,在局部地方诱发入门壁垒松弛。1980年代中期之后,已可通过委培、定向等方式进入大学,文凭逐渐不必然证明较强知识能力。其二、知识与美德无关。原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黄松有都是科班出身,而且都是法学博士。以文凭做“一刀切”式干部提拔,遭致实践中各种否证。根本导致传统干部晋升制度崩解的是,干部选拔四项指标中最具有自然稀缺性的普通高校文凭学历形态激变。1999年后高校扩招,法学学科设置泛化,法学本科学历供给量激增。稍后的研究生扩招,再次将学历稀缺性打破,研究生品种不仅有法学硕士,还增加了非法本法硕,又增加法本法硕。2015年,有权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单位有186个。高学历也加速量化生成,截止到2017年,全国有48个一级法学博士点。二级法学博士点和挂靠其他专业招收法学博士的难以计数。仅以西南政法为例,1979年招首届研究生11人,2009年为4679人。三十年膨胀了425倍。由于总供给巨幅增加,在学历供需上,卖方市场逆转为买方市场,作为学历颁发者的大学,处于激烈竞争生源状态,部分法学院为争抢法硕生源,竞相降低条件,如降总分、降单科分、免试先入学听课再补入学资格等。对于法官来说,拿到一个法律硕士文凭并不困难。读一个学士学位,还是继续读硕士、博士学位,逐渐成为个人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不再具有直接附加、可兑换的政治资本。在加大的学历教育供给洪峰持续下,各层次的法学文凭稀缺依次被冲垮。此前仅靠一个文凭即能获得提拔重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不管多高的洋学历、土学历,必须参与竞争,以实际能力获得认证。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结果即是:以文凭为轴心的单一晋升规则崩解,机关政治内容发生巨变,另一种干部提拔使用的非正式规则逐渐抬头,再次扭偏了正式制度。怀抱旧有的“文凭大树下好乘凉”观念的一些法官,开始无荫可乘。四职级晋升规则的异化折射出法院内部治理的积弊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项指标都逐渐虚化后,如何建立一个形式理性化、可测评的标准根据,成为法官选任中一个突出问题。一些法院在竞争上岗中,曾实行过简单以票取人做法。这遭致一些经验质疑,因为实践中常见部分工作能力强、坚持原则的法官,在票选政治下得票率并不高。反而个别工作能力一般,常以原则做交易,或者从不得罪人的老好人,会有极好的票面。对此,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林说:“应注意防止在决定干部任用时‘一切由群众说了算’的现象”,“党管干部和走群众路线都是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在竞争上岗中要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通过竞争上岗确定有关职位的人选,要充分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把群众对竞争人员的评价作为决定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党委(党组)要牢牢掌握竞争上岗工作的主动权,从制定方案、设计程序到具体组织实施的整个过程,都要在党委(党组)的领导下,由组织人事部门具体承办。”原本从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开始,到2002年正式颁布、2014年《条例》修正,干部选任的基础条件和资格、程序都有规定。但由于党委、人大、政府、两院等各机关人员差异性大,《条例》不可能具体规范至每个职位,对具体人员专业能力的识别,势必由本机关裁量。在干部选任“红”与“专”协调时,以专业性强或不足,作为干部任用或否决的理由,成为业务性强的机关自主决定权日益加重的根据之一。在法院,亦为突出。法院干部任用分为三个层级:1.法院院长,由上级党委主管,上级法院党组协管,任免决定权在上级党委,但是“任免、调动,应征得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同意”。1998年之后,上级法院党组利用组工制度赋予的这一正式权力,在人选建议和任用上,具有极大分量。2.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专委这一级干部,由同级地方党委主管,任免征求上级法院党组意见。虽然决定权不在本院,但本院具有强大的人选提名建议权,尤其对非中意人选,具有极强否决权。从日后工作协调、班子团结和全局工作出发,地方党委都会充分尊重、吸纳作为“一把手”的院长对副院长人选的意见。即使有院长不便直接拒绝的人选,在与上级法院汇报后,上级法院党组、政治部都会支持自己的下级法院,出面与地方党委协调,建议改变任命。实践中,将院长对副院长任用上有力的建议权和强硬的否决权,戏称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3.法院内设机构正副职(俗称的中层),由本院党组主管。对所有中层,最后决定权在院党组会。在实际产生形态上,对中层副职,主管副院长即具有较大决定分量。对中层正职,主管副院长具有建议权,主要取决于作为党组书记的院长的态度。由此可知,法院职级提升,决定力量不在于外部,而在法院自身。在学历条件消散后,以工作能力、业绩为选拔根据,很难建立可计算、可操作的测评根据,尤其是在边缘处界限模糊不清。这即为主观评测留下极大空间,为各种非正式规则的潜入,提供了通道。一些自生自发的非正式规则,再次处于超越正式制度的支配性地位,成为建立职级提升的新秩序规则。法官职务晋升,在部分法院,更多依靠裙带关系或者贿买。在部分法院,法官谋取晋升,依靠激烈的行贿竞争,贿金最高者胜出。近年判决的法院院长职务案件,受贿犯罪事实基本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利用审判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部分是在干部调整、晋升中,收受贿赂。如原任深圳龙岗区法院院长、深圳中院副院长黄常青,2015年因受贿400万元被查处,除收受律师贿赂外,另外收受下属买官行贿款近百万,在收受贿赂后,将一些法官提拔为业务庭长、副处级干部。2018年被立案查处的副省级城市长春中院院长张德友是法学博士,“他在担任吉林、长春两市法院院长期间,在干部任用工作中,利用职权,先后为多名基层法院院长在职级晋升中提供帮助,从中收受现金、高档烟酒等‘感谢’。”以上晋升方式,在部分地区的部分法院,成为常态。缺乏裙带关系,又不愿堕入行贿竞争者,或流于边缘化,或自我放逐,选择离职。在基层法院,职级晋升尤为艰难。基层法院,院长为副县职,其他副院长是副科职、高配为正科级审判员。庭长基本是科员,或地方上称谓的股级,老资格的庭长会解决科级审判员。但因为县区法院人数相对较少,而且个人认同都是基于对比本人所在群体产生,如果公平晋升,并不会产生反向激励。而且全国80%的案件初审集中在基层法院,事权分量极重。但是,1998年以来,法院纵向一体化现象严重。上级法院向下派院长、副院长数量日益增多。基层法院职级晋升艰难,主要不是职位少,而是来自于上级法院挤占。不仅中院不断将自己的庭长下派到基层院任院长,或副庭长担任副院长,连高院也加入其中,将普通的正科级助审员下派到条件好的县区法院任副院长。吉林即规定:省法院40岁左右的中层干部可选派到中院任副院长;省法院和中院35岁左右的正科级以上干部可以选派到基层法院任副院长。这极大地挤压了下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晋升通道。一方面,中国法院是一种锥形设置,平均12 个中院对一个高院,7.8个基层法院对一个中院,97.9个基层法院对1个高院。因此,每一个下级法院院长,要升任到上一级法院任党组成员,都有多个来自平行职位的竞争者,晋升极为困难。另一方面,与法院数量锥形分布相反,法院内设机构则是倒锥形,越往上越宽厚。按最近一次地方法院机构改革方案:高院设置15至18个机构;中院设置14至16个机构;基层法院设置9至12个机构。这些内部机构不包括与审判庭平级的纪检、监察,也不包括中院以上政治部内设的3-5个处和执行局内设的3-5个庭室。此外,在中院以上,另设有基层院不设立的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处,以及法官学院等事业编制机构。高院以上多有期刊,最高院另还有报社、出版社、应用法学研究所等事业单位和司改办等临时机构。法院内设事业单位的普通人员为事业编,但机构的正副职都是政法编制。由审判庭普通人员调到事业单位任正副职,即迈上了职级晋升和下派的台阶。这种内设机构的倒锥性设置,对法院内部晋升的影响是:上级法院内设机构不断膨大,具有下派任职资格的正副职也随之倍增,上级法院又具有最强劲的干部任用支配权,有能力不断将自己的干部下派下级法院任职,四级法院层层挤压传递,一直掼到最底层,结果即是占全国法官人数80%的基层法院法官提拔最艰难,基本是至副院长即到天花板。晋升院长如此,副院长及以下干部晋升也同样艰难。实践中,四级法院中央政法编制内人员,熬时间资历,从书记员到助审员再到审判员,都不会有障碍,只是迟早几年问题,但要担任副庭长、庭长,则面临激烈竞争。再向上晋升,则有诸多困难。原本一个副院长出缺,本院通过内部晋升可获得整体的最大福利改善,如将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提拔,出任党组成员、副院长。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留下的位置,可由作为专委的执行局长升任。执行局长空出的专委职位,可由办公室主任升任,还可再提拔两名干部任执行局长、办公室主任。依次跟进,全院实现动态的跟序晋升。但上级法院下派一人,将一个位置堵塞,整个法院晋升链的通道即停滞。职级晋升的自变量意义,对纯粹的学院研究者而言可能会被认为分量过大。但实际上,对法官而言,昔日学生时代并无强烈的官职进取心,但处于机关氛围濡化日久,基础性导向即是以职级评价个人成功。一个双一流A类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毕业,到法院工作,公认的业务骨干,但工作十年,仍只是普通审判员,而只是“业大”专业证书结业、网络教育函授本科毕业,曾做过自己书记员的人,业务一般,仅因有特殊渠道,就被提拔为领导自己的庭长甚至副院长,该审判员即会因严重不公而情感受挫。河南辉县法院民庭庭长刘建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在法院工作14年,干部调整竞聘副院长失败,随即选择辞职做律师。2016年,原本本职工作即是与媒体打交道,深为媒体熟悉的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任新闻局副局长七年后,辞职去了阿里巴巴公司。这一行为本身,而不是对着麦克风的发言,成为作为前发言人燃爆舆论的最后一次发言。每个离职法官的内心体验都未必愿与他人道来,要获得大规模公开数据统计支持极为困难,但逻辑和公开的个例指向一致。五法院改革的重新定向由上可见,并不是决策层给予法院整体职级比例不足,更不是法官货币、非货币福利水平不高,而是以晋升为中心的法院内部治理需要重新设计。职级晋升,在政治内部治理中,原本是为了给公务员中的优秀者以回报,并通过提升优秀者传递出信号,激励其他人员检视自己的行为,矫正可能的行为偏差。如果那些不依赖贿买或特殊关系渠道,而寄希望于业务精良、工作勤勉的人员,因无法获得相应职级回报,而不断选择辞职,公务员群体即会逐层劣化。虽然单纯转做律师的法官比例极小,但由此折射出的是整个法院内部治理的积弊。那么,扩大法院职数,是否可能消解法官离职?这种策论也被证明只是一种无效应答式反应。因为职务和级别设立,都只能是少数人享有。在法官数量众多、案件数量众多的法院,以业务相同、相近为分类标准,设立多个次级管理单元(庭、处、室),由一人担当负责职务,目的在于效率。如每人都有独立意志,众声喧哗,效率尽失。基于“类案同判”朴素意识的当事人,也会因此怀疑公正。2017年,最高法院编制总数有1300人之多,入额法官高达367人,不计算审委会委员、巡回法庭主审法官,刑事岗位151人,民事岗位99人,行政赔偿岗位19人。2018年11月第二批又入额法官40人。如此多法官,如何统一审判尺度;如此多人员,如何对其行为进行管理,法院内部势必会发育出一套机制。任何体制下的负责机制,依然只能是一两人承担。另外,级别(虚职)设立,是为了奖掖先进,激励有为者,因此也只能是分配给少数人。如果无差别的由所有人齐平享有,南郭先生大行其道,则无以在内部实现有效秩序。因此,职务获得擢升者只能是少数,失意者常在。从近年经验看,亦支持了这一看法。在职级上,最高法院院长是副总理级,各副院长只是副部级。决策层通过增设常务副院长(正部级)这一做法,拉升了法院职级。地方党委对地方法院也相继比照增设了常务副职。如前述,政治部主任、执行局长进党组,允许增设2-3名专委作为院领导等做法,也拉高了法院领导职数。通过增设更多法院、巡回法庭、内设庭室,更极大增加了干部职级比例。但是,因为职级晋升机制出现局部偏差,导致提高职级比例和增加职数,出现反向激励:在一些时候不仅未平息不满,反而诱发内部矛盾和不满。研究二战期间士兵满意度的学者发现,美国空军比其他军警晋升要快,而且更可预期。但是,由于大多数空军人员都觉得自己比其他成员更为出色,所期望的要比实际获得的更多,反而有更强烈挫折感。研究者名之为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感。对中国法官离职现象进行深描,可查知这一诠释,同样对本文主题具有解释力。如前述,四级法院内中央政法编制法官,解决审判员都不存在问题。作为普通审判员,最高院是副厅级,高院为副处级,中院为副科级。但是高院的副处级审判员不会与中院副科级审判员相比而沾沾自喜。辞职法官的相对剥夺感,是基于自我设定的同一个群体——本院具有可比性的同辈人而滋生。不仅导致未晋升者不满,这种内部晋升上的不公导致的反向激励,在获得晋升者中也被展示出来。因为原本因优秀而被晋升的干部,看到能力、美德远不及自己的人竟与自己平行,亦会滋生不满。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企图达到优越(不平等)的境界。——这些情况也许都有道理,也许都不应该——较低的人们为了求得平等而成为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了取得优越(不平等)也成为革命家。”此情形与金属铸币时代劣币驱逐良币一样:成色不足、重量不够的铸币进入流通,导致优良铸币的实际兑换价值被压低,最后只好退出市场。那么,通过提高法官货币收入,是否能消解法官离职?时下,法院改革一个中心议程被部分研究者设定为提高法官待遇。最新理由是既然“以审判为中心”,就应给出与法官权力对应的报酬。根据仍是相沿多年的高薪养廉说:通过高薪,让法官意识到贪腐导致机会成本、预期收益损失过大,从而不想贪腐。但是,高薪与“以审判为中心”之间并没有直接相关。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目的是“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意味着:证据质证在法庭,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判决根据形成在法庭。没有更多含义。而且,这种以高薪谋取清廉的策论,遭遇两个方面的否证:其一,反向经验。意欲贪腐的个别法官对高薪丧失的顾虑,不抵一单大额受贿的激励。何况还有被查获的低几率,壮大了收益预期。其二,司改不内部转向,继续通过外部注入福利,提高法官的货币收入福利指数,无法降低被剥夺感和减少辞职。在货币收益和福利待遇上,与前述职级上的相对剥夺感一样,离职法官的心理体验,不是在拿自己的优越与公安检察院对比,而是与自我设定的参照系——与自己年龄、学历、资历相当的本院法官对比。因此,无差别地提升法官的整体福利指数,而非公正地解决法院内的二次分配问题,并不能消除其差异感。通过无限制抬升法官职级和货币福利及其他非货币收入,以挽留优秀法官的做法,之所以不被支持,更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扬汤止沸的做法,遮蔽了合法性危机。传统上,司法制度研究者中的浪漫派总期待法官只服从自己的良心,而不服从任何派别、舆论、民意、其他法官的干预,也因此认为只要通过在高学历、法学科班出身、律师中选拔并给予高薪等手段守护好法官的良心,就会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冷静的现实观察者并不这么看待。对法官进行行为经济分析的研究即认为:“许多传统法律学者关于法官行为的理论并不符合实际,却有着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并且得到了法官群体的支持。在他们的理论中,对名利的追求以及意识形态在司法决策中并不产生影响。”按照还原论观念,司法组织设计是司法的中枢设计,其在整个司法结构中的位置是:实体法受制于程序法,程序法受制于司法体制,而司法组织设计又在司法体制内处于基础决定位置,是司法内部秩序构建的柱梁。因不满而辞职从事律师的法官,虽比例极小,但这种行为表达出的信号内容清晰:(1)不公正的晋升机制损伤了法院内部秩序。如果晋升与业绩、个人品行无关,只与贿金多少有关,那么,就可以不理会任何司法伦理和制度约束。(2)作为一种微观政治异化,不公正晋升征表的是政治治理结构性危机。对于政治治理者而言,职位晋升激励的正式制度,如何能够有效践行,是关系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问题。官员因自己的优秀获得了正当晋升,使得官员对所处其中的国家机构形成高度认同;官员获得了国家机构内职级晋升的回报,也带来收入和各种福利的改善,从而使个体的利益与国家政治紧密相关。法院内部不适当的晋升机制,会颠覆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政治的信心。由此可见,在法院内部职务晋升中感到不满而离职,只是法院内部治理中大量反向激励、反效率做法这一最应予以改革的总病灶的病症之一,这一病灶真正破坏伤害的是公众的司法信任和政治正当。先前部分研究对于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外部给予了过度的倾注,对于原本是法院内部治理中积存的痼疾,也习惯于归结为外部的人财物供给不足。对于更应给予优先性考量的法院职级晋升,却丢在观察的视域之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倒转望远镜看——物体虽近在咫尺但同时又远在天边。与部分研究者的认知偏差不同,中央有关部门则对此问题始终有清晰认识。2014年,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河南后向河南省委反馈巡视情况:“组织人事、法院系统等领域腐败案件增多。”“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2017年2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在巡视最高法院后的反馈意见中也尖锐的提出:“选人用人不够规范,干部管理不够严格,一些领域存在廉洁风险。”为此,要求最高法院“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好干部’ 标准,严把选人用人关,严格干部选任程序,坚决防止带病提拔、违规使用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用人环境。”最高法院党组随后关于巡视整改情况进行通报,其中提出要“着力解决‘选人用人问题突出’问题”,“ 着力解决“廉洁风险不容忽视”问题”。本文由此认为,以法官晋升作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是较大而化之的法院外部人财物约束边界更重要的问题域。在法院改革这一主题上,从关注外部到进行内部治理转向,中心问题是职级晋升。在制度上,如何对法院进行深层次改革,需要纵深推进。2018年5月中央政法委即提出要“统筹推进政法组织体系改革”,“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和综合配套改革”,“形成全方位深层次的政法改革新格局”。政策研究者提出解决内部晋升的对策是对行政事务与审判事务进行二分。另外的建议是消解科层制。在手段上,研究者关注两个,其一,自然科技的深度运用,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各种网络、信息化手段在法院中的运用。技术约束条件给定的行为边界得到变化之后,法院内部人员构成会相应松动。其二,对司法化、可诉性等命题进行深度的调整。对这两种远端对策的实效,有待深度学术分析和经验中渐进的检验。来源:法治宣传网智库 编辑:陕西法制网 孙钰颖
 卫玠
卫玠《政法论坛》主编:办刊物的都想发好文章,但问题是哪有好文章可发?
文章 |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来源 | 麦读今天我来这里主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不是聊法学,而是聊法学期刊。刚才王教授也介绍了,我本人除了教书之外,还兼做法学刊物的编辑。我今天不是以一个教授的身份而是一个编辑的身份来谈谈中国法学期刊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话题呢?话题选择的动机和初衷非常简单。在座的各位,咱们学法学的,老师是研究法学的,我们做一个研究,研究成果就要发表。很多的论文因为投错了地方,你论文的风格和某些法学杂志的风格不相适应的时候,可能没有被采用。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我把在座的各位都看成我们《政法论坛》这样一个法学学术期刊的潜在作者,从这个角度我想告诉大家,咱们的法学期刊登载的论文有什么样不同的风格和品位。大家如果要发表论文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我们要发表,按照法学期刊的编辑角度,和大家提供一点参考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和初衷,我想讲这样一个话题。今天的讲演分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学期刊的现状,一个是走向。特别是走向很重要。大家不管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法学老师,要专门地进行法学研究和发表论文,你要知道往哪走,我们有我们的行规和规矩,作为期刊有它的规矩。咱们中国在法律类期刊上应该在全世界来讲是个大国,有600多种。分三个类别,一个是法律文化生活类的,像法制新闻、法制文学,这类我归为法律生活类。大家都知道《民主与法制》这是另外一个期刊,在座年轻的后生和老师、同行一般不可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论文。这是一个消费型的,消费法律文化的刊物,这类刊物在中国比重比较大,大概有400多种,这是非常大类别的期刊。第二类期刊是部门实务为主,大概有100种,《公安大学学报》《检察官学院学报》《中国监狱学刊》《中国版权》《中国公证》等,这些都是部门行业为主的期刊。在座的各位和这些期刊关系也不是很大,我们一般也不会给这类杂志发论文。第三类是以法学学术为主要的期刊,这和我们有关系,我着重讲这类期刊,这在我们国家大约有180多种。法学学术期刊以刊物的主办单位来分,大体上可以分三类:第一是以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社联以及下属单位为主办单位的期刊。这是我们法学学术期刊的主流。主要有:中国法学会主办的《中国法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主办的《法学研究》和《环球法律评论》,地方社科院和地方研究机构主办的刊物,历史比较老的是上海社科院主办的《政治与法律》、北京法学会主办的《法学杂志》、山东法学会主办的《法学论坛》,我们的叫《政法论坛》。《法学论坛》是山东省法学会主办的。还有河北省法学会主办的《河北法学》。这类期刊是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和社联、独立研究机构主办的刊物。这类刊物里最有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法学研究》,一个是《中国法学》。这是法学期刊的大户。我们的老师和同学能够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发文章,肯定是一个非常光彩的事情而不是丢人的事情。这类期刊是比较重要的。第二类是政法专业院校所主办的期刊,这个就谈到我们了。比如说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政法论坛》,西南政法大学的《现代法学》、西北政法大学的《法律科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商研究》、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第三类是高校法学院系所主办的学术期刊。这类期刊也比较多,上面那一类,社会科学院、地方社科院以及独立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大概有30多种,政法院校所主办的期刊,这里的类别大约有10来种。第三类高校法学院系的期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学法学的人都知道的,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学评论》、北京大学的《中外法学》、清华大学的《清华法学》。《清华法学》是新增加的由高校法学院主办的刊物,到目前为止办得还不错。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学家》、吉林大学法学院的《法制与社会发展》、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行政法研究》、苏州大学法学院的《东吴法律评论》、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南京大学法律评论》、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北大法律评论》、南京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主办的《金陵法律评论》等等。这包括了以书代刊、季刊等,大约有20来种。这基本上是我们目前的现状,基本上分独立的研究机构的、政法院校的期刊、高等院校法学院主办的期刊。全部加起来是180种,大家要写论文发表论文只能在这180种里选,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现状。配图来自《边走边唱》,王人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现在法学期刊的格局是什么呢?很简单,最大的一个格局,中国法学学术期刊的重心肯定在北京。在这180种里,北京占的比重应该是一半,六七十种左右,中国法学期刊的重心仍然在北京。以北京为主的这样一个法学期刊的格局,在中国基本上就形成了。在这些刊物里,在北京为核心的法学期刊的格局里,从一个刊物办刊的特色,以及这个刊物采用论文的偏好来分,大家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现在法学学术期刊基本上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类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法学学术期刊。比如说《法学研究》,法学研究很少登单纯介绍国外的论文,它对这个不感兴趣。同样,我们的《政法论坛》一般也不发表单纯介绍国外某一个法律制度、某一个法律规则、某一个法学流派、某一个法学思想家的法学思想。这些我们肯定不登。这个格局基本形成了。这些是主要登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法学期刊。从这个类别来分,《中国法学》也属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期刊。相反,有些刊物可能是以发表研究国外为比较主要的内容的刊物。像《中外法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比较法研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环球法律评论》,这就是登研究国外为主的法学期刊。也就是说,对国外的法律、法学的研究,在这些刊物上占比较大的篇幅。但是法学研究、政法论坛这样的刊物,我们基本上是不做这方面的设计的。但是不是说,我们不登任何涉及国外的文章?我告诉大家,《政法论坛》有这样一个风格,要读一本西方法律著作,这类文章我们登。因为我们为了鼓励读书。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学知识是传授过来的,我们是继受的,中国没有法学知识传统。整个的法学体系和知识是来自西方的,我们追根溯源,这方面一点不涉及肯定不行。你要搞国际经济法肯定是西方的法律知识体系,中国的国际经济法不可能是主流化的。法学的话语肯定是以西方为主流,这样的话刊物不涉及西方是没有情理的。我们为了鼓励博士生、硕士生、青年教师去读书,我们专门开了栏目《读书札记》,你可以发表读了某一本书,你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你的札记可以发表,这是纯粹法学知识的话语而不是法律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我们两个栏目是登有关西方的,一个是《读书札记》,还有一个就是书评。前不久,发表了北京大学一个教授的很长的书评,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如果你写《试论卢梭的社会思想》,我绝对不登。他换了一个角度,每一个大学或者国家的学术期刊肯定有一个栏目书评。我们国家的学术期刊之所以办得不如人意,进不了一流期刊,就是我们的书评不够。因为中国的学者基本上不读书,怎么能写出好的书评呢?而要发表书评,那基本上不是书评,完全是广告。有什么创新,这哪是书评?!这是广告。广告我们也登,海淀工商管理局给我们批了广告的许可证,但是我们不可能给你稿费而是要收你钱的。我们封二封三专门给你登,一版一万元。我们不发这样的书评,要有真正的学术书评。要有两个标准,这本书要是经典,值得评。如果你写《评王人博的书》,对不起,你这是给我做广告呢,不能登。陈端洪教授评卢梭的书确实下了工夫,读出了感觉。在座各位年轻的后生和同行,我想《政法论坛》的大门向各位敞开,其他地方我不敢讲,书评和读书札记是永远向大家敞开的,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文章。我们很多人会写论文,但是很少写书评和札记,因为他们不懂书,博士不读书了,教授更不读书。你可以写很长的论文,比如《试论公司法的完善》。这样的论文一天可以写两篇,但是书评不容易。我们是外行,但也不是外到大家认为的那样。一本杂志是登中国的为主,我们也登国外的,在这两个栏目里。我想通过这样的努力,鼓励年轻的法学后生去读书、去思考,养成读书的习惯。你不读书怎么做学问?读书札记是你做论文的前期工作。你连一个札记都写不出来,怎么写论文呢?现在好了,我们从农业社会一步到了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写札记而直接写博士论文,那能成什么样的?很多刊物是不登载单纯研究国外的东西的,而有些刊物是专门做对国外研究的选题的。《政法论坛》还有一个例外,我告诉大家,你要登国外的,除了读书札记和书评之外,还有一个可以登的。比如说,研究美国的死刑问题,但是必须挂一点。《试论美国的死刑制度》我绝对不登,但是你说《美国死刑制度对中国的启示》,这就登了,这是中美比较。单纯介绍国外的制度有学术价值吗?既没有学术价值又没有实践意义。你以为中国的立法者都不懂国外?都懂啊。我给他们下了定义,法学的海归有两个价值,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以介绍中国法为饭碗。海归了学成回国了,以介绍外国法为职业。这样的文章一般我们不登的。这是以研究问题为根据的刊物。再一个,从法学学术期刊的品格和品位来分类,我认为可以分三类。一类特别注重意识形态,跟形势跟得特别紧的。比如说,登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讲话,比如《中国法学》。如果你要发表什么讲话,最好在《中国法学》登,我们不发这样的论文。还有一个是研究和中国社会官方最密切最热的问题,这类刊物有,他不注重学术性而注重前沿性。《中国法学》在这方面是老大,你写这方面的论文最好往《中国法学》投。还有一类刊物特别注重技术,我称之为“技术法学”,以《法学研究》为代表。《法学研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它不登宏大叙述的论文,它不太重视理论和思想,它注重技术。你把一个东西做得很精细,这符合《法学研究》的风格。大家不信打开法学研究看看。当然美国的学者、行业对《法学研究》提出了批评。来自于哈佛大学的,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顺便说一句,哈佛大学教授过来讲座的时候,说哈佛大学法学院只收了中国三家期刊,一家是《法学研究》,一家是《中国法学》,另一家是《政法论坛》。而按照哈佛大学的教授评论,美国人更喜欢《政法论坛》这样的风格。《法学研究》很精细,但是眼界太窄,它不注重理论和思想,你不注重这样的刊物,上不了这个档次。做这样评价那些同行会有意见,但是我很注重这本杂志,因为它很精细,如同把一个女人做得很有品位。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翁就是《法学研究》,小女人味很浓,或者说小资,但是缺少大视野。而《法学研究》是社科院法学所的,做得很精细,很用工,技术性很强,但是理论和思想性不强。第三类刊物偏重理论和思想,这不是《政法论坛》,我想做但不是很成功。相反是我们自己学生办的刊物,像《北大法律评论》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它进不了我们的评价系统,大家当教授、当博导、考核,先看发的哪个期刊。但《北大法律评论》,因为是学生刊物,如同哈佛大学法律评论,进不了我们的系统。我们的名家能够写出一流作品的法学家不给北大法律评论,可能给《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这是他们遇到的很大的困难。作为办期刊的人,我一直呼吁要把《北大法律评论》纳入到我们的系统中去,那是学生办的刊物。这是在中国的第一次让学生来评价老师的东西。结果,很多老师的稿件被学生否定掉了。他们说,这写的是什么?!退稿!说实话,在座的各位,法学的地位不是以老师和学生来分类的。我说的直白点,我也带博士、硕士。我认为很多硕士、博士的水平是超过了博导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评价体系不一样,无法衡量真正的学术氛围。而《北大法律评论》偏重这方面。我们《政法论坛》也在努力。一个学术刊物一定要偏重理论和思想。如果你的论文写得比较玄,就往这些杂志上投,写得很扎实、很精细的,往《法学研究》投。配图来自《边走边唱》,王人博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目前法学期刊存在的问题。说实话,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中国法学期刊都遇到了头号的问题,套用红色电影《南征北战》来讲,“不是兄弟无能,是共军太狡猾”。我们办刊物的都想发好文章,但是问题是哪有好文章可发?这是最大的问题。不要误认为我们这些编辑和主编都是吃干饭不识货的。有人说,我这么好的论文都给我退稿?!说实话,真正好论文不可能退稿的。这是中国法学期刊所面临的最尴尬的形势,也是中国法学研究最令人担忧的一个事情。中国法学研究表面化,大家表面化到什么程度,你们并不知道。我们一个编辑一个月要处理三百篇稿件,他们多痛苦,最痛苦的职业就是法学编辑,我称之为“垃圾处理”。这个话可能不恭敬,我用官方的话来讲,按照教育部社科司统计,高校和独立的研究机构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的论文有十万篇。按照这个说法,80%以上都是垃圾。所以中国是生产垃圾的大国,环境污染的大国。我在一个讲演中讲过,中国是资源非常贫乏的,这样的浪费,法学生产的浪费,不但造成了垃圾污染,更重要的是掏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让你解读中国,就要有一个视角,不能仅拿着问题去写,必须要有一个视角。我举个例子,我要把中国定义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一个视角。你说你从中国男足进去,你愣说中国是个体育大国。你说从中国乒乓球、跳水、体操来解读中国,说中国是个体育大国,没问题。因为你视角不一样。但是你从中国男足来看,中国是个体育大国,这不笑掉大牙。如果你从法学来定义中国是个法学大国,和男足一样,会被世人笑掉大牙的。各位,我真不夸张。我这样表达大家就听懂了,讲这些话中国人不太有脸面。中国13亿人的大国,五千年历史的文明,能够建成鸟巢、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大国,但是法学能够成为大国吗?中国是个法学大国?谁信啊?!在世界法学的主流话语里,你的话语权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法学的主流话语是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现在世界的法学格局里,主流的法学格局是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来自中国法学界的学者怎么能够和来自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法学家有一个平等的对话呢?很多中国的学者很牛的:哈佛大学请我去讲过学,耶鲁大学请我讲学。你问他,请你谈的题目是什么?这些中国的学者被西方主流话语请过去讲的都是中国问题,老外很好奇。你到美国哈佛大学聊聊人类的未来,人家说别别,走吧,研究人类的问题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责任。在主流法学话语之下,什么是中国法学的真正地位?刚才这位同行说了,你们编辑有很大的权力,这个话没错。我们有毙你的权力,把你毙了可以,这本身就是一个法学刊物非常不正常的。中国有匿名评审的制度吗?怎么可能?谁不知道谁。匿名评审是美国的期刊发表的制度。美国的匿名评审有一个前提,是洲际的。同样一篇论文,匿名评审必须有三个专家来进行,一个是来自欧洲的,一个来自美洲的,一个来自亚洲的。三个来自不同洲际的同行专家认为这个很牛,那肯定牛。中国的匿名评审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匿名。你不知道吗?所以中国的很多刊物说,我们实行匿名评审,人们会笑掉大牙的。中国这个社会怎么能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匿名评审制度。我们的博士论文是不是匿名评审?怎么可能真正用匿名?一看来自经贸大学的写的什么东西,那是王军的学生,我对王军有看法,把他毙掉。我们的学科评审也一样,都用无记名投票而且是保密制度的。我们没散会,那边就知道了,谁得了多少票。中国不是一个保密大国而是一个泄密大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匿名评审,是学术体系、评价体制决定的。只要没有真正的匿名评审,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到公正?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做刊物的人的责任来总结,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中国在这样一个法学知识生产的机制下,你即便做得像美国那样的匿名评审也没有用,因为你的论文不值得这样去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论文不能用。我们做的不是研究,这就是我们法学类期刊所遇到的同类问题。没有真正的好稿子,这是最恼火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流于形式,面孔千篇一律,这都是表象。根子就是中国的法学者,特别是成了名的法学者,特别是当了教授的法学者,他不搞知识生产而是知识消费,怎么写论文?我认为,教授的论文可以不好好看,但是副教授的论文要好好看,因为他要评教授。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法学期刊的现状。可能我说的有点极端和绝对。但是极端可能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也就是目前期刊的现状。讲到这里,我希望各位来自外经贸大学的同行和年轻的后生们,你们能够把最好的科研成果,不要交给《中国法学》,交给我们《政法论坛》。我最反感的,有些哥们,他认为我们挺傻的,他说把最好的文章交给你了。我说真够意思,给他发了。其实,同一期他还有一篇论文。结果,是把最好的给了《中国法学》,把次的给我们。我们也不是次品处理厂啊!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支持《政法论坛》,把你们最好的给我们。这是对兄弟的抬举。但是说实话,现在确实法学期刊令人担忧,大家做论文的很少。他们说,我忙,太忙了;今天全国人大又叫我去参加什么论证会;昨天我刚给国务院法制局写了报告,哪有时间读书啊。我在我的小书里写的,这是一个瞎忙的时代,我们忙得没有时间去读书没有时间做学问了。我也是学法史出身的,中国的学问有一个规律,板凳十年冷。不坐冷板凳怎么写好论文。在座的法学后生,你在读书吗?你在应付各种考试,在找工作,很难静下心来思考。最令人反感的是,法大的博士硕士和我讲,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你给我指正一下,我花了很多心血,我认为有很多创新哦。这样的论文不能看,他说有创新就不能看了,因为肯定没有创新,有创新用你说吗?你认为我没有眼力,你的创新我发现不了?说大点你在欺骗我。在座的各位,我真是在约稿子,而我很少给教授约稿子。我给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04级本科生约的稿子我发了,一个叫羽戈的。给法大的一个本科生约过稿子。羽戈是我在西南教过的一个本科生,现在文集都出版了。他是04年毕业的本科生,现在是无业游民。他写了几篇文章,我好多年没有看文章觉得拍案叫绝了。他是写柳如是的。他写了《柳如是暗地妖娆》,我看了题目就觉得很有才学。这样的文章写出来,我们的教授感到很汗颜,但是我很庆幸的是我教过他。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博士硕士,论文不一定谈得上。不一定在哪个栏目,真正的论文我们未必能做得出来,我相信你做不出来。现在写了读书札记和书评,既是练笔也是把自己的读书思考整理一下,挺好的。第二,中国法学期刊的走向。有这么三个问题,时间关系我点到为止。中国的法学期刊必须强调学术性,中国法学期刊离开了学术两个字就没有生命了,没有厚重感。学术和政治、学术和实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学者是做学术的,什么叫学术?行话可以说是黑话,出了这个圈你听不懂。牙医的术语我们不知道,我们给一个医生说什么叫要约?他们也不懂。一个法学期刊必须强调学术性,要增加学术厚重感。这有两个方面的来源,要以西学为原则,不读西书肯定不可能把法学做得很学术。第二以中国古典为原点,邓正来教授一直提倡回到孔子,回到柏拉图。这样的提法可能值得商榷,但是动机我们认同。再有,中国的法学学术期刊一定要形成法学的谱系。我们法学人应该在哪一个谱系上找到我们的角色。我在很多地方做过讲演,就是中国法学的谱系的问题。法学如果没有流派哪称得上法学。法学期刊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和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中国法学》所属的流派就是意识形态派,以学习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讲话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流派。以《法学研究》为代表的属于技术派。总之,法学一定要有自己的谱系和流派。还有,中国的法学期刊,包括做研究的人,应该处理好几个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想,一个是理论与实践。这话说起来很老套,我们一直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如果过于联系实际可能缺乏了学术性,如果理论过于漠视实践,那可能就是玄学。你和实践之间太紧也不行,你仅仅梳理这个事件也不行。我一直提倡说,中国的法学家应该关心政治、关心现实,但是又必须和政治和现实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中国的很多法学者非常热衷关注现实,但是距离感不够,太近了。但是学术又不能不关心现实和实际,我说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关注现实,但是要保留一个适当的距离,要有距离感,这是一个学人应该做的。法学期刊也要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法论坛》不能登社论某一个领导人讲话。甚至我告诉大家,今年五四青年节的时候,温总理视察过中国政法大学,他留下了很多的照片。对于《政法论坛》的封二封三刊要不要登温总理视察政法大学的问题,我说不行,这不是学术活动。如果你说温总理视察了政法大学的某个国际研讨会,那肯定要登的。我们很关注温家宝视察政法大学,但要有距离。我们不是不登温总理的讲话,但是我们级别还不够呢!我们可以转载,但我想也别转了。也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和学术,在国外这不是个大事,而在中国,引用舒国滢教授的话来讲,不要过分强调法律是一门科学,如果过分强调法学是一门科学的时候,可能不太利于法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咱们法学家中有的人,对某些敏感的问题,特别喜欢直白的表达,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套用解释学的话来讲,不在乎你说什么,只在乎你怎么说。说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怎么说。你说“中国要实现多党制”“要搞三权分立”。这样讲是不行的。我们对三权分立也可以谈,关键在怎么说。一句话,中国的法学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很重要。最后结语一句话,希望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能够支持我们《政法论坛》,讲得不好。谢谢各位!
 造人
造人线上+线下,首届中国会展法治论坛精彩呈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7月30日讯 首届中国会展法治论坛暨中国会展法律与政策委员会成立大会于7月29日以广东东莞为线下主会场,通过国家级经济移动云平台——中经网会iCE Meeting进行了独家直播。13位国内外会展、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在线分享后疫情时代会展业创新、责任与多元共治。论坛在线观看人数已达到 11万+。首届中国法治论坛线上+线下现场。袁梓 摄 首届中国会展法治论坛暨中国会展法律与政策委员会成立大会由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广东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法律与政策工作委员会、北京叒比邻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首届中国法治论坛直播间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袁再青致开幕词,并宣布研究会法律与政策工作委员会成立。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书记、院长、教授 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张宝秀为大会致开幕词。首届中国会展法治论坛现场嘉宾。袁梓 摄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陈泽炎宣布《中国会展法治报告》编辑启动,《中国会展法治报告》是中国的第一份在会展法治方面的专业报告,具有国内绝对领先性,引领潮流。是引导会展企业会展活动,对中国各地市会展法律与政策的提供独立评估,可以促进会展业健康发展,为会展业及相关产业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建议。长沙市会展办党组书记、主任陈树中发表演讲。袁梓 摄长沙市会展办党组书记、主任陈树中发表了“会展主办方的法律困境与会展立法前瞻”主旨演讲,谁是真正的展会主办方?发起者?投资者?运营者?直接收益者?风险承担者?在此过程中,需要厘清会展立法上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会展业范围及会展主办方参与方界定;二是展会名称及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三是政府对于会展业行政管理的界限。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展法律与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张万春发表了“后疫情时代中国会展立法探讨”主旨演讲,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是一个大事件,不仅是法学界的大事件,更是备受社会关注。对会展业立法更具指导意义,如倡导绿色发展观念,会议、会展及场馆建设在未来发展更趋向于绿色发展,面对疫情,会展活动延期,会展合同如何践行,如何保护会展业的知识产权,会展法律责任承担等需要会展业立法。未来很长时间内,疫情防控是常态,会展活动属地负责是常态,因此,后疫情时代,地方会展立法过程中,需明确主办方、协办方、承办方的责任,为会展活动创造健康、宽松的发展环境。 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代柏发表了 “澳门会展业发展:政策及其优化分析”主旨演讲,澳门发展会展业有政府、地理位置、交通等便利,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专章阐释支持港澳发展的重大举措: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积极发展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商务部积极支持澳门发展会展业、特色金融、跨境电子商务。政策措施包括:支持澳门会展业向优质化品牌化发展,为重点展会活动提供出入境签注便利,推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等大型国际品牌展会落户澳门。澳门会展活动的增加值总额2015年至2017年期间由14.4亿澳门元上升至35亿澳门元,占所有行业增加值的比重由0.4%上升至0.9%。 亚太盛会活动管理协会产业联系副会长林冠文发表了“台湾会展活动产业的复苏之路”主旨演讲,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动观光会展行业在线培训、转型、做政策指导。发放消费券促消费,推动京剧等文化产业发展,举办线上艺术博览会,吸引到了全球各地的关注,提高了人民生活。 中国商务会展联盟副主席姚红和国际会议中心协会 CEO Sven Bossu 发表了“迎接挑战时代的变化”主旨演讲,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地的会展活动场所都因业务关闭而处于“生存模式”,据国际会议中心协会(AIPC)统计,全球6290个展览活动取消,6660个展览活动推迟。在此情况下,需要全球合作以分享知识,准则和经验教训,AIPC与UFI(全球展览业协会)和ICCA(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一起,已向整个会展活动行业提供了3份会展业实践指南。在9月之前将发布的新版《商务会展重启指南》,针对全行业收录经验教训和新的会展信息。未来,会展活动场地也需要为客户提供线下和线上两种服务,以提供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以真正满足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 随后,英国博尔顿大学国际小组组长 Ben Chen 发表了“从欧盟的视角看,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融合”的主旨演讲,《法商研究》资深编辑、副编审、编辑主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理事翟中鞠发表了“法学研究如何选题:方法与热点”主旨演讲。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展览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大可为本次会议总结发言,宏观政策如何惠及会展企业?政府要有担当,积极推动复工复产,要在严格防控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复工复产,防控工作到位了,即使出现局部疫情,不能简单追责。因为经济政策只有在复工复产中,才会发挥作用;加强政府部门间政策协调,形成部门联动;政策要有针对性,帮扶对象要精准定义,这既涉及到公平问题,也涉及到效率问题,措施要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如税收返回,贴息贷款等等,当前,首先需要启动市场。 (王俊杰/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博览会
博览会石一峰: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民商辛说
作者按:对于善意问题的关注源于现实生活中的观察,在现今的时代善意似乎愈发稀缺,同时也越发难以界定。这其中引发的思考是善意者在最低限度的法律上该如何保护,善意的认定又该遵循怎样的规则体系。本文只是这些议题的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法学研究能关注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展开更多有温度的理论研究。本文的写作也得益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民商法研究所同仁的支持和帮助,正是民商法研究所的“神仙”氛围,让那些看似不着边际的思考和讨论能展现在大家面前。注:本文发表于《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转自《法学研究》公众号。本文共计24,504字,建议阅读时间50分钟摘要:私法中适用信赖保护之善意普遍存在且多样。究其本质,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这一认知状态是私法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不知悉。对于此种不知悉的评价,依善意的发展历史及其认定的特性,应属于法律价值判断,并可通过过失要件进行利益衡量。鉴于善意及其认定的共性,为化解善意认定规则上的争议,可以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为主线脉络,对善意的认定进行体系化的规则建构。其中,一般可信赖程度是善意认定类型的层级区分依据,依此形成的规范标准以过失作为层级协调因素。一般可信赖程度加上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决定了具体认定善意中的实体考量因素和程序方式选择。依此,可形成“非为明知”和“非因过失而不知”的实体标准判断要素,以及一般性推定与有条件推定的程序展开方式,最终构建起以体系思维为引导的善意认定规则体系。关键词:善意认定;可信赖事实;一般可信赖性;特定可信赖性目录一、问题的提出二、善意及其认定的本质(一)作为认知状态评价结果的善意(二)作为法律价值判断的善意认定三、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一)可信赖程度作为类型区分之标准(二)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区分(三)依可信赖程度的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区分四、善意的具体认定(一)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二)善意认定的程序方式结论一、问题的提出善意,系私法中普遍存在之表述与要求,各类规定纷繁复杂,其中最值研究者,当属信赖保护中之善意。[1]有些规范有关于“善意”之明确表述,如物权法第106条(民法典第311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2]物权法第24条、第129条、第158条(民法典第225条、第335条、第374条)等规定的特殊物权变动规则中的善意,[3]民法总则(民法典)第65条规定的商事登记不得对抗规则中的善意。[4]有些规范则隐含着“善意”之要求,如民法总则(民法典)第172条中的“有理由相信”,[5]合同法第50条(民法典第504条)中的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等。[6]然而,各善意之规定散置于私法的不同条文中,致使现有研究偏重于在其所附制度中一笔带过,至今未有体系而全面的整体研究。[7]虽然第三人之善意系指“不知悉”已属通说,[8]但何谓“不知悉”以及如何判断“不知悉”,却未有定论。首先,对于同一制度内的善意采何认定标准,仍有争议。如针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有论者从善意的主观属性出发,认为“不知悉”与过失无关;[9]或认为虽与过失无关,但依客观情势,判断交易经验上一般人均可知悉时,则为非善意;[10]也有观点认为,善意乃“非为明知且非可得而知”(即“非因过失而不知”)。[11]我国法以德国民法典第932条为借鉴,认为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系“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12]但却未如德国法那样区分不动产与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认定标准。[13]其次,不同制度间的善意认定标准存有差异的原因未被揭示,善意认定不同标准的相互关系和判断层级,均未得到重视和阐释。我国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与表见代理中善意第三人的善意即采不同认定标准,前者乃“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后者乃“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14]现有的分散性研究并未明晰此种差异的缘由,体系思考之不足亦导致善意认定的相关争议不断。[15]除实体认定标准外,善意的程序认定方式亦有争议。因善意多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非善意”的反面表述,故在程序上一般采推定模式。[16]然而,推定是否一定导致证明责任倒置,对于私法中的善意是一律采取推定还是有其他认定方式,也未有定论。[17]可见,私法中善意的实体认定标准与程序认定方式均存有争议。涉及善意的各制度虽各有其特定目的,但背后均共享对善意者予以信赖保护之思想,[18]因而各善意认定实际上相互关联,只有在体系中确立认定的标准和方式,并将实体与程序相融合,才能使善意的认定更具说服力。鉴此,本文拟对私法中善意之认定进行体系化研究,并由此构建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19]二、善意及其认定的本质(一)作为认知状态评价结果的善意1.可信赖事实作为认知对象善意有积极观念与消极观念之区分,后者只需不知他人非为权利人,前者须有以他人为权利人之积极信念。[20]一般认为,积极观念的要求过于苛刻,[21]因而各国立法例均以“消极观念说”为主。[22]我国通说亦采“消极观念说”。[23]从词源上看,善意起源于拉丁文“bona fides”,意为“不知情”,[24]但并未有积极确信事实为真的意思。在规范表达上,也通常以“知道与否”来界定善意,且从反面表述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非为善意,如我国合同法第50条、第151条、第158条第3款(民法典第504条、第613条、第621条第3款)等,德国民法典第122条、第173条、第405条、第932条第2款等。由此,善意仅表达了“不知悉”的消极观念。“不知悉”依其字义,系一种认知状态。法律上以善意表“不知悉”,实际上是将私法主体的这一认知状态评价为善意。然而,作为对一种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善意必然要求私法主体有特定的认知对象,私法主体是以何种情事为认知对象进而被评价为善意的,仍需进一步界定。从认知论的角度看,人们通过观察事物的表象完成对事物本质的认知。表象乃事物所展现的外在现象,是事物之真实情况的表征,我们只能借助对外在表象的观察来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25]观察是人的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表象输入到自身的感知系统中,并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反应。私法主体也是从各类表象来判断真实的法律关系,如代理关系中,交易相对人仅能从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书等表象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有代理权。换言之,私法主体对事实的认知其实都是以对事实之表象的认知为基础的。一般而言,若表象与真实情况一致,则不会发生法律纠纷;仅当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时,才需要判断私法主体对该不一致是否知悉并用善意与否来评价这种认知状况。法律上,善意的拉丁文“bona fides”,相当于英文的“good faith”,[26]并与德语中的“guter Glaube”一致,字面上均为“好的信任”之义。这意味着信任并非建于虚无之上,有信任的基础,才能成为“好的”信任,即善意。“好的”信任意味着私法主体所认知的事实至少在表象上是值得信任的。若所有人均可轻易分辨真伪而得出表象不值得信任的结论,自无善意可言。某一表象之所以无法被轻易分辨真伪,是因为在相应制度供给之下,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同步一致性,即表象通常揭示了真实情况,由此表象才有被信任的可能。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同步一致性的事实,因存在同步一致性的制度保障而具有可信赖性,被称为可信赖事实(Vertrauenstatbestand)。基于此,可信赖事实成为私法主体表现为善意时的认知对象。2.可信赖事实的特性作为人们行为的信任基础,可信赖事实首先应当具有可信赖性,同时,它也应当是人们交往中可认识的重要事实。但对于哪些事实能成为可信赖事实,学说有争议。有仅限于“交易当事人之行为外观”者,[27]有扩充为“主体资格、权利状态和表意行为等法律上视为重要因素之外部要件事实”者,[28]有笼统概括为“表见事实”者。[29]对此,需结合可信赖事实的特性作进一步分析。第一,可信赖事实应当具有可信赖性,这意味着存在使可信赖事实的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同步一致性的保障。此类保障源于可信赖事实相关制度的内在逻辑,如将不动产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由此激励交易当事人主动且正确地登记,以保障不动产登记情况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可信赖事实的此种一致性保障机制,在法律上均以规范化的制度存在,但不同可信赖事实之一致性保障机制在规范供给上存在差异,由此会导致其同步一致性存在差异,从而形成可信赖程度不同的可信赖事实。此外,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性除了受内在规范制度的影响外,还受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所、相关交易的时机等。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性影响着善意的认定,并是善意规则体系构建的核心基础。第二,可信赖事实是一种外部事实,但并非一切可感知的事实都可成为可信赖事实。可信赖事实产生于一定的法律关系中,其指向某一相对人,如甲对乙宣称丙是A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此时对于丙而言未有可信赖事实,在丙知悉或容忍甲的言词时,对于乙而言就存在“丙为表见合伙人”之可信赖事实。因此,可信赖事实具有指向性,并非单纯的“行为外观”或“表见事实”。第三,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具有持续性。此种不一致至少持续到相对人已完成相关行为时,才可使得可信赖事实对相对人发挥作用。如股权转让人登记于商事登记簿中之事实,致使相对人依此表象认为转让人与真实权利人一致,在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后,相对人才知悉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不一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才可主张依股权工商登记之事实获得保护。第四,可信赖事实作为法律关系中的事实,须对相对人具有法律意义,即该事实获得法律上重视的原因,在于其足以影响交易等行为。但这一事实不单单涉及行为、主体资格、权利状态或表意等事实,通常还是与法律行为一般成立要件相关的事实,并已被法律定型。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包括: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30]可信赖事实可从这些角度进行归纳:(1)与当事人身份有关的事实,如组织成员权;(2)与当事人权限有关的事实,包括处分权(含对标的的要求)、代表权、经营范围权限等;(3)与意思表示有关的事实,包括明确的言词、可推断的行为以及交易习惯下的行为,如代理权授予的书面言词、对他人为代理的容忍行为以及商事惯例中沉默视为同意等;(4)其他足以影响相对人行为的事实,如上市公司公告、一般的公司公告,商事登记中的组织形式、经营场所等。[31]由于交易及相关行为的差异,对于何为可信赖事实仍需进行个案判断。例如,在一般交易中,当事人并不关注对方的身份,但另一些(如涉及身份行为或偿付能力的)交易中,身份外观可能影响相对人的行为(如与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就存在合伙人或股东承担无限责任还是有限责任的不同)。(二)作为法律价值判断的善意认定1.善意认定的价值判断属性第一,从善意的历史发展来看,善意发源于罗马法上的诚信观念,具有伦理道德属性,其中“fides”和“bonus”本身就是伦理概念,前者指“信”的德,后者是“善”的意思。[32]因而,从词源上,其本就暗含价值判断的属性。同时,历史上,诚信被区分为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善意源于其中的主观诚信概念,针对的是主体的内部心理,与针对主体外部行为的客观诚信相区分。[33]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同源于社会生活中的信赖(信任)这一社会伦理因素,基于伦理因素的考量,两者均考虑主体是否具备故意和过失等主观因素,[34]因而只有基于可原谅错误的不知悉才为善意。[35]错误是否可原谅,已经从单纯的事实判断转向价值判断,并与过错概念紧密相连。第二,从善意的认定过程来看,其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很难进行完全客观化的认定。与对所有事物的认知一样,人的主观心理只能从外在的表现来判断。由此,善意的认定过程也只能从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来判断其主观心理状态。但是,要从客观事实判断主观心理状态,仍需基于法律所确立的原则进行价值判断。第三,从善意认定的实体考量因素来看,其不仅考量单个的外在客观事实,还需综合当事人的行为、所处的环境等相关因素来认定;[36]或结合个案中的交易场所、有关处分人、标的物、市场信息等有关交易背景进行考量。[37]综合认定已不再是单纯的事实认定,而是融合诸多因素依据法律上的价值取向来判断是否构成善意。由此,善意认定的性质也从事实认定转化为法律价值判断。[38]此与过失等主观心理判断的客观化一脉相承。[39]第四,从善意认定的程序展开方式来看,其是以推定的方式进行,故善意不是被直接发现的事实,而是依据一系列事实所作出的判断。此种判断需要有参照的基准,即依据一般理性人或通常情形来判断行为人是否知悉。但这些判断基准并非现实存在,而是裁判者通过对以往案例及自身知识经验的总结得出的结论。由此,善意认定的程序展开中所依据的参照基准并非客观事实,其认定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的价值判断。综上,善意与否,即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是否一致的认知状态的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核心在于,对私法主体的何种认知状态应予保护,需进行利益衡量。明确善意认定的价值判断属性,提示我们认识到善意认定背后蕴含着对诸如交易安全和效率等价值的利益衡量。进行利益衡量需有具体的衡平因素,善意认定过程中的利益衡平因素即是与这种认定密切相关的过失要件。2.过失作为价值判断的衡平因素过失之所以可作为善意认定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的衡平因素,除了善意的历史发展揭示善意作为主观诚信时已包含对过失的考量外,更重要的是过失要件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当事人之间的信息成本与风险,从而实现对交易安全和效率的利益衡量。作为认知状态评价结果的善意,其认定核心在于判断民事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是否知悉。知悉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显然的知悉,乃明知之状态;二是依据交易经验、常识等综合判断下应当知悉,乃盖然性的知悉。[40]在明知情形下,第三人无需花费成本核实即可避免不当交易,相较于保障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相一致者(潜在责任者)的监管成本,明知不一致的第三人所需付出的成本更低,故应排除对此类第三人的善意保护,由其承受风险。但若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并非明知,而是仅有怀疑,其需付出相应成本核实,此时由谁承担风险,取决于第三人的注意义务程度,以此来分配风险更为合理。[41]当第三人负有核实的注意义务时,其就应当知悉。“应当知悉”在德国法上的表述是“kennen musste”,字义上已蕴含着必须知悉的注意义务,违反该注意义务而不知,则非为善意。注意义务之违反乃过失问题,因而德国民法典第122条中,“应当知悉”与“因过失而不知”(infolge von Fahrlssigkeitnicht kannte)等同;德国民法典第173条标题中的“fahrlssiger Unkenntnis”与法条中的“kennen muss”对应,也表明两者应同等对待。综上,“应当知悉”本身蕴含着注意义务的要求,乃过失判断之问题。过失要件使得善意认定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得以更好地展开。当客观情事为第三人提供了足够的“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可能不一致”的警示时,第三人就应尽到起码的注意义务以防止自身的认知出现偏差。第三人未关注相应的警示而使自己陷于认知错误时,若仍认定其为善意,则将在利益衡量上过分保护第三人而导致利益失衡。[42]由此,过失要件能够合理分配信息成本的负担,[43]使得善意保护中的利益衡量更为合理。不同情形下的善意认定对过失程度的要求也不同,过失程度可成为善意认定不同标准的区分标志。三、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一)可信赖程度作为类型区分之标准私法中的善意有不同的认定标准。一般而言,不动产登记作为认知对象时,仅要求“非为明知”即可,而动产占有作为认知对象时,则还需“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44]商事登记作为认知对象时,善意需“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45]代理委托授权书等代理权外观作为认知对象时,则需“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46]之所以出现此种差异,是因为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此种评价必然受制于认知对象之状况。善意评价是基于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若某事实显不具有可信赖性,即其表象与真实情况之不一致显而易见时,自不具有不知悉此种不一致之可能,因而也不能评价为善意。可信赖性源于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但不同可信赖事实的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程度存在差异,由此,可信赖程度也存在差异,如不动产登记的可信赖程度最高、商事登记次之、登记之外的授权委托书最低。正是基于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程度的不同,才会出现针对不同可信赖事实之善意认定要求的变化。比较法上,也有学者以商事登记与非商事登记事实之可信赖程度不同,而提高对非商事登记事实的善意认定标准。[47]针对不动产登记与动产占有的善意认定标准不同,也是因为土地登记簿相较于占有,存在更为坚实的信赖基础。[48]由此,不同的可信赖事实呈现差异化的可信赖程度,善意认定也随之而变化。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高的可信赖事实,善意者所负的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就会下降,此时对于善意的认定标准随之下降;反之,则加重善意者的负担,提高善意的认定标准。[49]善意的认定随着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变化,而可区分不同标准并由此形成善意认定的类型区分。(二)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区分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性与“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程度有关,但此种判断仅源于可信赖事实制度本身的内在逻辑,影响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的还包括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这样,从认识的角度来看,就形成了一般可信赖性与特定可信赖性的区分。其中,一般可信赖性源于可信赖事实本身的规范化制度逻辑,是一种一般性认知;特定可信赖性源于可信赖事实所处的变化的外部环境,是一种特定性认知。特定可信赖性受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域、针对对象、存续时间、与其他可信赖事实的结合等因素影响,随个案情形而变化。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因素所改变的是可信赖事实的外部认知环境,并未改变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的内在逻辑,因而特定可信赖性是对一般可信赖性的具体修正,并不改变可信赖程度的层级。[50]同时,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因素一般在善意的具体认定中予以考量,如“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确定了善意的认定标准后,分别在第16条和第17条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善意认定进行了具体规定。从此角度而言,特定可信赖性是对善意认定更为细化的影响,而一般可信赖性是对善意认定的根本性影响。为此,一般可信赖性可作为善意认定的规范性标准类型层级区分的依据。可信赖事实既可以是权利信息的展示,也可以是状态信息的展示,同时还存在不同的信息展示载体。通过对现行法的梳理,依其信息载体不同,可信赖事实可分为登记(包括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等)、状态(占有)、类商事登记(上市公司公告、一般公司公告等)、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言词(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会议记录等;口头形式)与行为(各类表征代理或代表的行为、各类表征合伙人等成员权的行为、符合交易习惯的行为)等。这些可信赖事实的制度逻辑中均存在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的机制。以不动产登记为参照模板,其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的具体制度可区分为内在保障与外在保障。其中,内在保障关注的是可信赖事实是否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生效要件,或者是否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对抗要件,是否具有推定效力等;外在保障关注的是可信赖事实是否有国家强制及其审查力度,是否因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而受到惩戒(公法的惩戒与私法的惩戒)等。各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的制度保障程度不同,就构成了其一般可信赖程度的不同,对此可作以下类型区分:1.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在内在保障机制上,是权利生效要件并具有推定效力。[51]当不动产登记是权利变动生效要件时,交易当事人会积极主动地登记以确保权利的移转和获取。同时,基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力,真实权利人亦会积极关注不动产登记之状况,确保自己享有之权利已被正确登记。由此,能够鼓励真实权利人积极登记并确保登记之正确性。[52]在外在保障机制上,不动产登记有国家统一登记的强制要求,且登记机关采取实质审查模式,登记不正确也将使得真实权利人的权利因不动产善意取得等受到私法上的不利益。为此,不动产登记具有最全面的制度保障,因具有较高的可信赖程度而被称为具有公信力。[53]其制度保障机制可作为判断其他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程度的参照模板,可标记为最高档。2.动产占有占有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权状态,也具有表征其背后权利的特性。通常认为,占有之外观状态与实际情形,具有“八九不离十”的盖然性,[54]其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同步一致性。这背后的内在保障机制,一方面在于占有及其移转(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另一方面在于占有也具有推定效力。[55]作为生效要件,其促使当事人积极移转占有以确保权利已有效变动;又因其具有推定效力,使得真实权利人也积极关注占有的状况,确保其控制力或选任正直的直接占有人。如此,占有也具有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的制度供给。但由于对物之利用需求旺盛,占有与所有的分离已成常态。[56]同时,占有毕竟不同于登记,外在保障机制上缺乏国家强制力的支撑,未有必要的核验与监督,因而其虽也可称为具有公信力,但可信赖程度已有所下降,可标记为中档偏上。3.商事登记商事登记在内在保障机制上,仅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对抗要件,所具有的推定效力也弱于不动产登记和占有。[57]在外在保障机制上,商事登记虽然具有国家强制要求,但偏重于形式审查。[58]商事登记不当也将受到私法上和公法上的惩戒,如《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了对企业法人在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行政处罚,此外,还将追究其法定代表人的行政和刑事责任。但因为内在保障机制上的弱化,外在审查力度的下降,商事登记的可信赖程度亦下降。然而,考虑到商事登记仍具有强制登记属性,且商事登记义务主体对登记正确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其可信赖程度相较于占有也并未大幅下降,可标记为中档。4.类商事登记事实商事登记之外,还存在商事公告类的信息传递机制,典型的如上市公司公告和一般的公司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进行清算的公告。在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的内部保障机制上,上市公司公告不是权利或状态变动的生效(或对抗)要件,也不具有推定效力,仅为信息公示方式。在外部保障机制上,证券法第78条第2款规定了通过上市公司公告披露的信息应真实、准确、完整,否则依据证券法第181条以下条文和证监会的各类监管规范,上市公司将受到一系列行政和刑事处罚。[59]除此之外,依据证券法第9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以下简称“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规定”),上市公司公告瑕疵还会引发民事赔偿等私法惩戒。为此,上市公司存在及时公告的强制要求,若公告不当也将受到公法上的处罚和私法上的惩戒。但由于缺乏国家力量支撑,所有信息均由公告主体自身审核,从而在确保公告信息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上,较登记弱。因而,可推论上市公司公告的可信赖程度应低于商事登记。但由于证券监管的持续性以及信息披露内容的专业性,相较于投资者,公告主体更有动力和能力进行充分审核来保障公告信息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由此,其可信赖程度仍可保持与商事登记相当,仅略偏低,可标记为中档偏下。与上市公司公告类似的还有一般的公司公告,主要涉及公司的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此种公告也仅为信息公示方式,不存在强有力的内部保障机制。但在外部保障机制上,公司法第204条规定了不依法公告的行政处罚。理论上,公告不当也可能基于违反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忠实和勤勉义务”和公司法第189条规定的“清算义务”而使相关主体承担私法责任。但一般公司公告针对特定债权人,亦可通过通知完成信息传递,在确保公告正确性上的激励小于上市公司公告。为此,一般公司公告的可信赖程度弱于上市公司公告。但考虑到它们的信息展示逻辑相同,一般公司公告的可信赖程度可属于同一层级,只是其属于该层级中的最低层级,可标记为中档最低。5.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事实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言词和行为也可成为可信赖事实,但其缺乏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的内部保障机制,如授权委托书等代理权外观事实并非代理权授予的生效或对抗要件,且不具有推定效力,也不存在国家强制和公法上的直接惩戒。但在外部保障机制上,其至少存在私法上惩戒的可能,如因选任代理人或代表人不当而需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因此,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事实仅能通过私法上的惩戒来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其可信赖程度最低,可标记为最低档。即使如此,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事实内部也存在差异,可进一步区分为书面言词(书证型)、可推断行为、口头言词等。三者因证据效力(私法惩戒可能性)的递减而在可信赖程度上亦递减。(三)依可信赖程度的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区分依据上述可信赖事实之一般可信赖程度,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在理论和实证法上可通过过失程度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层级。第一,针对不动产登记的善意,仅要求“非为明知”即可,而针对动产占有的善意,则还需“非因重大过失不知”。如前所述,此为德国通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不动产登记之可信赖程度强于动产占有。我国实务中也认为,“由于占有的公信力低于登记,因而两者需差别对待”。[60]但我国“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将针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善意统一为“不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之所以如此规定,首先在于“物权法解释一”第2条基于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实情,[61]妥协性地降低了不动产登记之公信力。其次,根据《德国土地登记条例》第36条、第37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需以公证证书的形式提供申请材料。公证环节增强了对登记状况与真实情况相一致的保障。我国法并无此要求,不动产登记的可信赖程度相比而言下降。最后,“物权法解释一”第16条第2款和第17条中对于不动产和动产情形下的重大过失进行了分别规定,两者在重大过失之注意义务上有明显差异,从而形成了内部的善意认定类型层级。第二,针对商事登记的善意,民法总则(民法典)第65条等并未明确善意的认定标准。比较法上,德国商法典第15条第1款和第3款对商事登记的善意均采取“非为明知”的标准。[62]理论上也认为,此时第三人的非善意不包括因重大过失而不知。[63]但此与德国的商事登记制度有关。根据德国商法典第12条和《德国商事登记规定》第8条的规定,商事登记的申请材料一般须经公证才能提交,从而提高了登记状况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因此,德国法上才会对商事登记的善意信赖采取“非为明知”的标准。反观我国,并未有对商事登记材料的公证要求,因而对商事登记的善意不能仅要求“非为明知”。另一方面,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6条第3款对股东名册的善意采“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标准。股东名册虽然不是直接的商事登记事项,但从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表述来看,股东名册是“列入”商事登记簿的。在商事登记已电子化的今日,股东名册与商事登记其他事项一样,收录于平行的登记文件夹(Registrierordner)。由此,股东名册在形式上与商事组织提交的其他登记事项类似。此外,根据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5条第3款、第40条第2款的规定,股东名册也需公证后提交,且通过董事责任来保证股东名册变更的及时和正确,此与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对抗要件等内部保障机制在效果上相当。但股东名册并不会被登记机关更深入地审查,由此导致德国法上股东名册虽与商事登记类似,但可信赖程度下降。对比而言,我国商事登记在可信赖性保障上与德国法上的股东名册在程度上更为接近。因此,我国法上对商事登记的善意也应增加“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要求。第三,针对类商事登记事实的善意,“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19条将“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作为排除“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但该条忽视了因果关系仅为客观判断,“明知”指向的是主观方面,即善意的要求。投资者主观方面的非善意不在于排除因果关系,而是会导致保护基础的丧失。[64]该司法解释对类商事登记的善意仅要求“非为明知”,与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形并不符合。一方面,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应明知投资有风险,其具有相应的信息识别注意义务;另一方面,类商事登记的可信赖程度也并未因监管的持续性而大幅提高,其仅与商事登记的可信赖程度相当。为此,针对上市公司公告的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也应要求“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但在具体的认定规则上应与对商事登记之善意有差异。就非上市公司公告而言,其可信赖程度虽比上市公司公告要低,但较之登记之外的事实,仍与上市公司公告处于同一个层级。因而,对非上市公司公告的善意认定标准仍采取“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但在重大过失的判断上会有差异,即第三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上有差异。这与“物权法解释一”第15—17条中针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善意在规范标准上相同,但对重大过失的认定予以差异化规定的做法一致。第四,针对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现行法一般采取“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标准。如表见代理中的善意,通说认为应采“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及实务也采相同见解。[65]此外,依合同法第50条(民法典第504条),商事表见代表中的善意也采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标准,其中“应当知道”即“因过失而不知”。[66]比较法上,我国台湾民法第107条、第169条,日本民法第122条亦采相同标准。实际上,实证法上针对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居多,如民法总则(民法典)第149条中,合同相对方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第三人欺诈的,即为善意,合同另一方丧失对于因受欺诈而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撤销权;[67]民法总则(民法典)第167条中,代理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的,即为善意,代理人无须承担连带责任等。[68]其他如民法总则(民法典)第145条、第170条,合同法第74条、第169条(民法典第539条、[69]第636条)等,也均为针对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但登记之外事实本身仍存在可信赖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需要通过具体案件中过失的认定标准来体现,同时也需要程序法上的善意认定方式来衡平。综上,在可信赖事实的一般可信赖程度下,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以过失作为协调因素,形成一定的类型层级。但是,善意的具体认定还受制于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此时,这些因素除了对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判断产生影响外,还将影响善意认定的程序方式,即通过一般性推定和有条件推定的区分来完成对各类善意认定更为细化的平衡。四、善意的具体认定善意的具体认定中,首先要定位善意所针对的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处于上述何种类型层级,进而明确其规范标准,其后再进行具体的认定。因善意通常采取反面规定,即通过“知悉”来排除善意,所以善意的具体认定一方面是在实体上判断何谓明知,及因何种过失程度而不知;另一方面是在程序上明确以何种方式进行具体的判断。两者除受一般可信赖性影响外,还受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通过分析一般可信赖性和特定可信赖性对善意认定的影响,可挖掘善意认定实体标准的判断要素和程序方式的选择依据,进而以此构建起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一)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1.“非为明知”的认定(1)信息类型的影响“非为明知”是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未有明确的认知。因善意的认定往往从其反面进行,故具体的实体认定也从何谓“明知”展开。“明知”的认定首先受第三人能获得的信息类型的影响,信息类型的不同将影响第三人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是否一致的判断。第三人能获得的第一种类型的信息是可信赖事实本身所展现的信息,这部分信息区分为两种亚类型:(1)可信赖事实中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如不动产登记簿中的登记主体的信息或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人信息明显有误。若存在直接证明第三人知悉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证据,如第三人已对他人明示自己知悉,自可证明。若直接证明困难,则只能以推定的方式完成,如依一般理性人之标准可发现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或者受让人本身就是登记错误的参与者,受让人当然了解登记错误的发生过程,即可推定为明知。[70](2)可信赖事实中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典型的如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异议登记、预告登记以及查封登记等提示性登记;上市公司公告中的财务报表已经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等。可信赖事实本身存在这些提示性信息,即可推定第三人知悉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第一种类型的信息更容易在一般可信赖程度较高的可信赖事实中获得,如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公司公告等。对于一般可信赖程度较低的可信赖事实,更容易获取的是第二种类型的信息,即可信赖事实之外的信息。此亦可区分两种亚类型:(1)可信赖事实之外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这些具有直接证明效力的外在信息必须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可作为第三人认知的基础,如真实权利人以生效判决进行的通知、[71]企业撤销代表人的通知、[72]企业更正公告信息的通知[73]等。(2)可信赖事实之外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这些信息既可能是第三人直接知悉的,也可能是第三人间接知悉的,如通过非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知悉不动产登记簿中的权利主体错误、通过媒体的报道知悉上市公司公告有瑕疵等。[74]相较于可信赖事实本身的提示性信息,可信赖事实之外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说服力有限,第三人需要去核实调查才能判断信息的可信度。此时,第三人是否具有核实调查义务及其义务程度,就成为考量的核心。这本质上关涉的是注意义务的程度及其违反问题,将之纳入“因过失而不知”中进行认定,更为合理。(2)信息状况的影响“明知”的认定还受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如第三人了解的关于可信赖事实的额外信息、可信赖事实针对的交易对象等,均可在个案中影响对“明知”的判断。其判断基准是可信赖事实的外在状况(即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是否已经对上述信息类型产生影响。例如,第三人可能获得了可信赖事实之外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因而“明知”的标准降低。如第三人就是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知悉甲乙夫妻共有房屋仅登记于甲名下,在甲未出示乙授权时,仍与甲进行交易,应认定为“明知”。又如,可信赖事实针对的交易对象是金钱或无记名证券时,由于交易效率和安全的要求,必须强调其流通性,[75]提高对其之占有的可信赖程度。[76]在此情形下,第三人获取可信赖事实中直接或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的难度增加,“明知”的标准应提高。对于其他的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遵循相同的分析路径。2.“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同样,“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也是从其反面即何谓“因过失而不知”展开,其核心是过失及其与“不知”之间关系的认定。传统上,过失区分为重过失和轻过失,[77]但两者区分标准模糊。前者采取普通人标准,[78]后者采取一般理性人标准。[79]但此两种标准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理性人与普通之人的标准争议颇多。[80]究其本质,重大过失是作为普通之人已意识到某种风险,但并未引起其必要的注意,强调的是行为人应具备某种认知,但却未对该种认知加以注意而仍然行为。因此,重大过失是一种有认知的过失,即认知到了某事实发生或存在的风险。[81]轻过失则并未有对于风险的明确认知,需要去调查核验才可能认知风险并放弃行为。具体到“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是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已有明确认知,即有高度怀疑时仍然行为;因轻过失而不知,是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只有模糊认知,即有轻度怀疑时却未尽到核实调查义务。至于如何判断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状态,一般可信赖程度仅能提供一般性指引,即一般可信赖程度越高,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可能性越低,但具体的判断仍需在个案中考量可信赖事实之特定可信赖性的各影响因素,以此指导具体的认定。[82]基于此,“因过失而不知”的具体认定要素可区分为以下类型:(1)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域交易场域包括交易场所,交易的时机、方式、价格,以及第三人针对可信赖事实的额外信息等。第一,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所通常划分为公开市场和非公开市场。公开市场如拍卖等情形,除了公开性外,还受资质、特殊交易程序等限制,因而增强了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使得第三人无需付出过多的成本去核实调查,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认知能力就会下降,由此导致过失的判断标准提高。第二,交易时机、方式、价格等,也会影响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此时需要借助交易习惯进行判定,若交易方式不符合交易习惯或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都应提高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从而要求其尽到更多注意义务去核实调查。在此,区分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的标准,是对不符合交易习惯或价格不合理所产生的风险的认知状态及由此产生的怀疑程度。不符合交易习惯或价格不合理将使得第三人认知到有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其应有较高程度的怀疑而进行调查核实,否则构成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此时,交易习惯应作一般习惯和商事习惯之区分,因为商人的风险认知能力强于非商人,应当遵循要求更高的商事习惯。[83]第三,第三人针对可信赖事实获知的额外信息,也会影响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如在善意取得中,第三人曾与转让人进行过系列交易或与之非常熟悉,就更应当知道转让人是否有处分权。[84]又如股权转让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股东应知道股权转让的情形,因而其若以商事登记簿未变更为由而轻信,即构成重大过失。(2)可信赖事实针对的对象可信赖事实针对的对象不同,也会影响其可信赖程度,从而导致第三人注意义务的变化。当可信赖事实针对的交易对象是金钱或无记名证券时,基于交易效率的需要,占有金钱等即有处分权的可信赖程度提高,使得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下降,从而应降低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当可信赖事实针对的是代表权限时,一般交易权限与特别交易权限也应作区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10条的规定,限营、特营情形下,交易权限不能仅依据商事登记簿记载的经营范围,还需要相应的许可证明。在无许可证明时,第三人应有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而须尽到相应注意义务,否则构成重大过失。(3)可信赖事实的存续时间信息传递中,人们会根据迄今为止的状态作出判断,[85]所以若可信赖事实存续时间很长,则可能造成“现存的事实状态与真实状态一致”的印象。由此,一项长期存在的可信赖事实,其可信赖程度更高,因为迄今为止的状态提高了外观状态与真实状态同步一致的概率。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6条第3款规定,股权登记错误若存在超过一定的期限(3年),则责任者的可归责性下降,此时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可能性也相应降低,除非存在新的风险认知因素,否则第三人不构成因重大过失而不知。(4)可信赖事实的混合增强实务中,第三人的认知基础可能并非单一可信赖事实,潜在责任者也往往通过可信赖事实的混合来增强其可信赖程度。[86]这一方面可能是通过高层级的可信赖事实来增加低层级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如通过商事登记增强自己书面言词的可信赖程度。此时,由于跨越了层级,应当按高层级可信赖事实调低第三人善意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可能是通过同一层级的可信赖事实的相互印证来增强其可信赖程度。此时,善意的规范标准不变,但具体认定上,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下降,应当提高过失的认定标准。(二)善意认定的程序方式善意的具体认定需通过一定的程序方式实现对实体标准的判断,不同一般可信赖程度及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下的善意认定差异亦需通过程序方式的选择予以体现。不同难易程度的程序方式选择展现了善意认定在程序法操作上的精细化,亦衔接了善意认定的实体与程序规则。从私法各具体制度中善意认定的一般规则来看,无论我国法还是比较法,均采取推定的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从正面证明自己善意是一个“魔鬼证明”(probatio diabolica);[87]另一方面,实体法中的善意一般是通过其反面来加以规定,这其实已为程序法上善意的证明方式指明了方向,即需要主张非善意者从反面来证明第三人非善意。但此种推定在程序法上以什么方式展开,仍有疑问:首先,善意推定是否导致了证明责任倒置;其次,是否所有层级的善意认定一律采取直接推定。1.善意推定的基本原理对于善意推定是否导致了证明责任倒置,比较法和我国法上素有争论。[88]从善意推定的具体过程来看,第一,善意推定并非法律的直接规定,法律中并未有善意(或非善意)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规定,这与诸如侵权责任法第6条(民法典第1165条)中的过错推定导致证明责任倒置不同。证明责任倒置需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善意推定是在诉讼程序中形成的规则。第二,善意推定的功能在于减轻程序上的证明难度,此点可参照德国法上关于其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中过错证明难度的减轻机制,该机制一般以运用表面证据规则(Anscheinsbeweise)为通说,[89]并不需要证明责任倒置。第三,表面证据规则的运用实际上弱化了主张善意者提出证据的义务,但对于主张善意者提出表面证据的要求存在不同情形。在一般性推定中,由对方首先提出非善意的证据,己方主张善意本身就被看作是一项表面证据;在有条件推定中,己方除主张善意外,还需先提出初步的表面证据,以完成提出证据义务,此后才进入推定,并允许对方提出反证对推定予以反驳。可信赖事实在可信赖程度上存在差异,使得对善意的认定亦随之改变,此种改变不仅导致实体认定标准的变化,而且涉及程序方式上整体证明难易度的调节,即在运用表面证据规则进行善意推定时,对表面证据的强弱要求不同,并由此区分为善意的一般性推定与有条件推定。2.善意的一般性推定规则一般情形下,表面证据的要求低,提出主张的陈述本身也可构成一项证据,此为一般性推定。但此种主张至少应包括善意行为的具体事实和过程。例如,善意取得中,善意取得人通常对从何处受让及在何种情形之下取得某物,应有记忆。如经原告要求,被告拒绝为此项陈述时,其未完成表面证据的举证,不能推定其为善意。[90]在善意的一般性推定中,主张善意者提出了善意主张后,反对者可对此进行反驳性举证,即通过举证第三人是明知或因过失而不知而证明其非善意。此时,非善意的证明包括明知的证明与因过失而不知的证明。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明知的证明存在直接证明的可能,如在笔录或庭审中第三人自我供述已明知,或查明第三人交易时随身携带着对不动产登记真伪的查询结果,即可认定为明知。相反,对于因过失而不知,由于过失本身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判断,因而很难说存在直接证明因过失而不知的可能。(1)“非为明知”的推定由于“非为明知”乃内心事实,依经验观之,诉讼程序中极难证明,一般推定第三人“非为明知”,但允许反对者通过证明第三人“明知”来进行反驳。可信赖事实中直接或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以及可信赖事实之外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均可成为判断第三人是否明知的基础,如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异议登记、存在生效的判决文书等。此外,影响可信赖事实之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也会影响第三人获取相关基础事实的难易度,因而上述关于可信赖事实的信息状况的分析,也可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明知时的进一步考量要素。(2)“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推定“非因过失而不知”存在同样的证明困境,因此,也只能推定之,反对者可通过证明因过失而不知进行反驳。其中的核心在于证明过失,但过失已采客观化认定,即通过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来判断。需注意的是,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与因一般过失而不知的认定,并不相同。前者需同时证明存在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和未尽到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后者仅需证明未尽到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由此,“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推定与其反驳的核心在于证明是否具有注意义务、是否有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以及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其中,是否有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需结合前述“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要素,除一般可信赖程度的影响外,应着重考察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区分各种情形进行认定。3.善意的有条件推定规则善意的一般性推定虽为原则,但随着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下降,尤其是因存在影响特定可信赖的因素而在同一层级存在可信赖程度的差异时,需进行有条件的推定。典型的如特别交易权限的事项,法律已规定不能由代表人单独实施的行为(如合伙人一致决事项),以及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禁止经营的事项,第三人须先证明存在股东会决议、内部一致同意书或者特许、许可等文件。实务中已有判决认识到此点,要求第三人不能仅信赖对方的承诺、保证以及相关公章签订合同,而是还需对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合伙人一致同意书等进行审查。[91]但此种审查仅为形式审查,因为第三人缺乏实质审查的技术能力,决议或特许、许可的真伪不在审查范围之内,除非是明显的伪造。[92]一旦第三人举证证明决议或特许、许可存在,善意的认定又进入一般推定模式,即主张非善意者要依据上述一般性推定规则举证证明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已有认知及未尽到合理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93]区分哪些情形是有条件的推定,一方面是依据可信赖事实的一般可信赖程度来认定。言词或简单书面材料等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最低,第三人的信赖基础过于薄弱,其主张自己善意即进入推定并不合理。此时,第三人至少应先行提出这些可信赖事实展现的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实质关联等证据,才能进入推定模式。若第三人不能提出相关证据,则只能认定其非为善意。这与让主张非善意者进行反驳相比,更为节省诉讼资源,也避免因内心事实问题的证明而产生不必要的争论。另一方面,同一层级的可信赖事实因影响其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内部认定的差异。如上述同为商事登记的可信赖事实,若针对一般权限事项,采取一般性推定即可;若针对特别权限事项,则应先证明享有特别权限,从而需进行有条件的推定。其他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也会导致推定的有条件化,但并非所有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都会导致有条件推定。只有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增加了可信赖事实之外的信赖基础时,才会导致有条件的推定。例如,可信赖事实针对特别权限增加了特别权限的信赖基础,可信赖事实混合增强时增加了其他可信赖事实的信赖基础。[94]其他影响因素如在非公开市场,交易时机、方式、价格等不合理或不符合交易习惯,可信赖事实与第三人较近,可信赖事实存续时间较长等,一般并未增加新的信赖基础,仅使得原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发生变化,可采取一般性推定并通过“非为明知”与“非因过失而不知”的不同认定标准来体现差异。结论私法中存在众多关于信赖保护的善意,通过对其进行体系化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认知的对象是可信赖事实。当私法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并不知悉时,这一认知状态在法律上可被评价为善意。善意的认定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其中过失是价值判断中利益平衡的要件。2.鉴于善意与可信赖事实的关系,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在实证法和理论上可作为善意认定的“体系轴”。其中,一般可信赖程度使得善意认定区分为以过失为协调因素的类型层级,从而形成善意认定在实体法上的规范标准。3.一般可信赖程度加上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将影响善意具体认定中的实体标准判断和程序方式选择。在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判断上,“非为明知”以信息类型(一般可信赖程度影响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和信息状况(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导致信息状况不同)作为判断要素;“非因过失而不知”以特定可信赖性各影响因素为判断要素。在程序方式的具体展开上,因一般可信赖程度的不同使得针对不同可信赖事实之善意的推定方式不同,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的不同使得针对同一层级不同可信赖事实之善意的推定方式也不同,从而形成对表面证据强弱要求不同的一般性推定和有条件推定。由此形成的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首先形成了善意认定的一般类型层级供裁判者进行“定位”,以明确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再根据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判断要素和程序展开方式进行具体的认定。其次,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起到了衔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作用,为善意的认定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引,增强了善意认定的可操作性。最后,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体现了体系化思维,有助于在理论上厘清私法之内在体系。体系化思维也有助于具体规范解释适用时的说理论证,为司法裁判提供支撑。注释:*本文的写作特别要感谢张谷老师、周江洪老师、张家勇老师、张继成老师、陈信勇老师、韩家勇老师,以及时常讨论的伙伴们:陆青、章程、周淳和林洹民。也要感谢冯珏编辑和外审专家,冯老师对学术的较真和细致,乃我辈楷模。*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商事习惯司法适用问题研究”(20YJC820040)、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商事信用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9SFB3030)的资助。[1] 与善意相对的,还有恶意的表述,如合同法第42条(民法典第500条)中的“恶意进行磋商”,合同法第52条(民法典第154条)中的“恶意串通”等。这些关于恶意的规定,规制的是基于恶意而为的客观行为,已被纳入诚信要求中予以考量,本文则侧重于信赖者主观“不知悉”的善意。关于诚信与善意的区分,参见董学立:《论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恶意》,《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第65页;甄增水:《民法中的善意》,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9页以下。关于善意的历史发展,参见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97页以下。[2] 关于善意取得中的善意分析,参见叶金强:《论善意取得构成中的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要件》,《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第31页以下。[3] 参见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6页以下。[4] 该条文义上针对法人登记,但登记不得对抗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内外部法律关系的区分,商事主体因其对外经营特性而符合内外法律关系区分的前提,所以在解释上,一方面要限缩该条适用的法人类型,另一方面要扩张适用至非法人的商事组织。参见石一峰:《论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第57页。[5] 参见杨芳:《〈合同法〉第49条(表见代理规则)评注》,《法学家》2017年第6期,第170页。[6] 参见石一峰:《商事表见代表责任的类型与适用》,《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144页。[7] 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8] 参见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吴国喆:《善意认定的属性及反推技术》,《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18页。[9] 参见李光夏:《民法物权新论》,上海书报社1955年版,第83页;前引[2],叶金强文,第82页。[10] 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4页。[11] 1982年台上字第2819号判决。[12] 参见前引[8],尹田书,第204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6〕5号,以下简称“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也规定,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乃“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13] 对于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认定应采何种标准,我国学说与实务也有差异。通说认为是“非为明知”,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王利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0期,第6页;程啸:《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与动产善意取得的区分》,《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第531页。反对意见认为不动产和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应统一为“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14] 参见史浩明:《论表见代理》,《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第70页;曹新明:《论表见代理》,《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第65页;江帆、孙鹏主编:《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15] 关于无权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标准就有三种观点。参见夏昊晗:《无权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法学》2018年第6期,第104页以下。[16] Vgl.Wolf/Wellenhofer, Sachenrecht,30.Aufl.2015,§8 Rn.16; Baur/Stürner, Sachenrecht,18.Aufl.2009,§52Rn.25, S.673; Hübner, Handelsrecht,5. Aufl.2004, S.59;Canaris,Handelsrecht,24. Aufl.2006, S.66;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页以下;刘家安:《物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17] 参见徐涤宇:《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之解释基准——以物权法第106条为分析文本》,《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98页以下;吴泽勇:《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149页以下。[18] Vgl.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7. Aufl.1989, S.43.当然,善意只是信赖保护的构成之一。对信赖者信赖的判断,需要综合信赖者的善意、信赖者对可信赖事实的知悉、信赖者的信赖处置行为以及信赖处置行为与信赖之间具备因果关系。Vgl. Canaris, 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eutschen Privatrecht,1971,S.503ff.[19] 诚如曾世雄所言:善意恶意等因广泛附随于各种制度而存在,彼此有其共通,俨然自成一体系,故有特予讨论之必要。参见前引[7],曾世雄书,第227页。[20] 参见前引[10],史尚宽书,第564页。[21] 参见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22] 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2款、日本民法第192条、瑞士民法典第714条等,通说均认为采消极观念说。参见前引[10],史尚宽书,第564页。[23] 参见前引[16],梁慧星等书,第194页;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第108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物权法解释一”第15条亦采消极观念说。[24] 参见王利明、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第11页。徐国栋将“bonafides”译为诚信,并区分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其中主观诚信在现今法律文本中对应的表述就是善意。参见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二题》,《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80页以下。[25] 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页。[26] 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缩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27] 参见张国建:《商事法论》,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45页;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以下。[28] 参见田土诚主编:《交易安全的法律保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29] 参见李井杓:《韩国商法上的表见责任制度之研究》,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30]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页。[31] 影响相对人对最终责任人是否承担有限责任的判断以及合同履行地的判断。[32] Cfr.Pietro Bonfante, Essenza della bona fides e suo rapporto colla teorica dierrore, Bulletino dell’ istituto di diritto romano, Vol. VI (1894), p.91.转引自徐国栋:《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的分合与更名问题比较法考察——兼论中国的诚信立法向何处去》,《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13页。[33] 参见前引[24],徐国栋文,第80页;前引[1],徐国栋文,第98页。[34] 参见前引[1],徐国栋文,第98页。[35] Vgl. Carl Georg Bruns, Das Wesen der bonafides bei der Ersitzung: ein praktisches Gutachten nebst einem theoretischen Nachtrage,1872, S.79f.[36] 参见王利明:《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以我国物权法草案第111条为分析对象》,《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82页。[37] 参见前引[2],叶金强文,第84页。[38] 参见前引[8],吴国喆文,第23页。[39]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过失也被认为是一种主观心理,在判断上也转向以“注意义务”为基础的客观化综合判断,故也涉及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参见陈聪富:《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40] 参见前引[10],史尚宽书,第564页。[41] Vgl.Schfer/Ott, Lehrbuch der konomischen Analyse des Zivilrechts,2. Aufl.1995,Berlin, S.472ff.[42] 参见前引[8],吴国喆文,第21页。[43] 参见前引[13],王泽鉴书,第486页。[44] 此为德国通说,参见前引[16],Baur/Stürner书,第300页,第673页;前引[16],Wolf/Wellenhofer书,第8节边码17,第19节边码21。[45] 参见前引[4],石一峰文,第57页。[46] 参见杨代雄:《表见代理的特别构成要件》,《法学》2013年第2期,第65页以下。[47] 参见前引[16],Canaris书,第92页。[48] 参见前引[16],Baur/Stürner书,第300页。[49] Vgl.Wiegand,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2011,§932,Rn.37.[50] 如不动产登记在一般可信赖程度上肯定强于登记之外的言词,不能因为登记之外的言词处于公开市场、存续时间长等外部因素,而使其可信赖程度跨越层级、超过不动产登记。[51] 德国民法典第873条规定了因合意和登记而取得土地的登记生效主义,第891条规定了土地登记簿的推定效力,第892条规定了土地登记簿的公信力(依此可善意取得不动产)。我国物权法第9条(民法典第209条)、第14条(民法典第214条)规定了登记生效主义,第16条、第17条(民法典第216条、第217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力,第106条(民法典第311条)统一规定了不动产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52] 参见前引[49],Wiegand评注书,第408页以下。[53] 参见前引[16],Baur/Stürner书,第169页;前引[16],Wolf/Wellenhofer书,第19节,边码1以下。[54] 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页。[55] 我国物权法第23条(民法典第224条)规定了交付生效主义,占有的推定效力虽未明文规定,但为学理所承认;物权法第106条(民法典第311条)统一规定了不动产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关于占有的推定效力,参见庄加园、李昊:《论动产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以〈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为借鉴》,《清华法学》2011年第3期,第123页以下。[56] 参见温世扬:《物权法要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57] 参见前引[4],石一峰文,第54页。[58]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4条第2款和实务判决均确认此点。实务判决参见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4)温瑞行初字第130号行政判决书;甘肃省庆阳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4)庆中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59] 刑法第160条、第161条分别规定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60] 参见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2013)金商初字第0498号判决书。[61] 实践中,登记不当情形仍不在少数,如房改房、继承等或为规避税费而不进行登记。参见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62] 德国民法典第68条对于社团登记簿的善意,也采取了“非为明知”的表述,与商事登记相同;商事登记与社团登记的情形也类似,因此下文的分析也适用于社团登记。[63] 参见前引[16],Canaris书,第55页。[64] 参见石一峰:《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中的交易因果关系认定》,《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第85页。[6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013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43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第93号民事裁定书。[66] 此处的商事表见代表既可能基于商事登记产生,也可能基于登记之外的事实而发生,前者仍采“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标准,后者才采“非因过失而不知”标准。具体分析可参见前引[6],石一峰文,第137页以下。因而,需注意的是具体规范中的善意可能针对的可信赖事实具有多样性。诸如善意占有、善意不当得利等制度,亦因占有与得利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复杂多样性,其所针对的可信赖事实也具有多样性,需依据具体情形分析到底是对不动产登记、占有还是商事登记或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67]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14045号民事判决书。[68] 参见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3民终628号民事判决书。[69] 民法典第539条已将合同法第74条中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本文分析所得的善意要求相符。[70] 参见前引[13],王利明文,第7页。[71] 参见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2行终6号行政裁定书;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7)吉2401行初99号行政判决书。[72]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2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20民终4862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再72号民事判决书。[73]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鲁民二终字第287号民事判决书。[74]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75] 参见前引[13],王泽鉴书,第503页。[76] 参见[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78页。[77] 参见黄风:《罗马私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78]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79] 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以下。[80] 参见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79页。[81] 同上文,第89页。[82] 有学者指出,重大过失的判断需要根据交易场所、有关处分人、标的物、市场信息等有关交易背景信息来考虑。参见前引[2],叶金强文,第84页。比较法上,相同见解参见Schwab/Prütting, Sachenrecht,29 Aufl.2000,S.181。[83] 参见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2013)金商初字第0498号判决书。[84] 参见前引[36],王利明文,第83页。[85] 参见前引[16],Canaris书,第50页以下。[86] 此与潜在责任者的可归责性亦相关。[87] 德国商法典第15条第2款要求第三人自己证明其既不明知也不应知此种事实,此被学者认为是不可能的。参见前引[16],Canaris书,第61页。[88] 采举证责任倒置者有前引[16],Canaris书,第93页以下;Roth, in:Koller/Kindler/Roth/Morck, Handelsgesetzbuch(Kommentar),8. Aufl.2015,§15 Rn.57采取事实推定的有Rhricht/Grafvon Westphalen/Haas (Hrsg.),Handelsgesetzbuch,4. Aufl.2014, Anhang zu§5 Rn.34。我国相关争论可参见前引[17],徐涤宇文,第98页以下;前引[17],吴泽勇文,第149页以下。[89] Vgl.Wagner,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823,7. Aufl.2017,Rn.87ff.; Hager,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823,2017,Rn. G34.[90] 参见前引[10],史尚宽书,第565页。[9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终字第00560号民事判决书。[9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93]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84号民事判决书。[94] 如果第三人不先举证证明其他可信赖事实的存在,则仍按照单一可信赖事实的标准认定,此时主张非善意者更易进行反驳。因而,欲主张自己是对混合可信赖事实的信赖,以降低自己的注意义务要求的,需先举证证明其他可信赖事实的存在。
 哪出儿
哪出儿武汉大学成功举办法学期刊与新时代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研讨会
人民日报人民周刊讯(统筹:秦前松):2019年9月28日,正值金秋时节,桂子飘香,“法学期刊与新时代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系武汉大学恢复法科教育40周年纪念学术活动之一,由武汉大学法学院与《法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环球法律评论》主编周汉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马长山、《当代法学》主编李建华、《中国法律评论》主编袁芳、《法制日报》理论部主任蒋安杰、《法商研究》常务副主编温世扬、《比较法研究》副主编丁洁琳、《法学》副主编于改之、《法学家》副主编尤陈俊、《现代法学》副主编董彦斌、《法学论坛》副主编吴岩、《法学家》编辑高圣平、《中外法学》编辑杨明、《法律科学》编辑焦和平、《法制与社会发展》编辑郑怀宇等各大法学期刊报社的主编和编辑拨冗莅临珞珈山,同时参会的还有校内外师生代表四十余人。开幕式由《法学评论》秦前红主编主持。武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夏义堃副院长和武大法学院冯果院长分别致辞。夏义堃副院长介绍了武汉大学文科期刊的办刊历史和现状,对如何办好专业期刊提出了建议和期冀。她认为,学术期刊承载着促进学术交流、提升学术传播以及进行学术品鉴的重要功能,高校期刊的办刊水平反映了高校的学术面貌和学术发展态势。冯果院长介绍了武大法学院的学科建设情况。他提到:今年正是武大法科重建40周年,我们院里也在总结历史,展望未来,40年风雨历程,我们一代代珞珈法律人不断进行耕耘,逐步形成了具有武大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武大法学院的成绩取得不容易,学术成果的传递、学术群体的形成、学术风格的养成都有赖于各大期刊的栽培与支持,借此机会向大家通报一下法学院目前的状况,更想表达的是对大家的敬意和谢意。《环球法律评论》主编周汉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马长山、《当代法学》主编李建华、《中国法律评论》主编袁芳分别进行了主旨发言。周汉华主编首先回忆了自己在武大求学的美好经历,表达了对母校法科建设如此出色的骄傲自豪之感。随后他谈到,近几年C刊的发文量都在缩减,因为好文章少之又少,而《环球法律评论》的高标准高要求也从未放低,始终坚持学术的创新性,推崇文章理论观点要创新,方法要创新。同时他还表达了对年轻学者的关怀,要重视对年轻学者的培养和发掘,但不能拔苗助长,要尊重学术规律。马长山主编从三个方面展开阐述。1.期刊偏好与成果发表。期刊和作者要保持沟通对话。2.办刊的动力和压力。严格控制学术底线。3.办刊方向与学术研究。办刊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又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纯洁性和自主性。李建华主编对办好期刊需要把握的几对关系做了解读。在法学期刊与法学创新的关系上,二者相辅相成,法学创新的发展为法学期刊提供素材,法学期刊推动法学的创新发展。在法学期刊与期刊办刊单位的关系上,好的法学期刊离不开办刊单位的支持,办刊单位也通过期刊展示科研实力、学科特色,对此应公正评价。因此有关于自发率问题,只要控制在合适比例,应当予以理解。在法学期刊的办刊特色与交流合作问题上,既追求自己的办刊特色,也重视法学期刊间的交流互动。袁芳主编向大家分享了中法评办刊的一些心得体会。她指出,受益于法律出版社的品牌资源、资金支持和放权管理,中法评在办刊方面没有太多负担,能够专心做学术。在办刊理念上,一是把刊物当产品来做,注重内容的思想性、评论性和策略性,突出问题意识、担当意识、传播意识和政治意识;二是注重品牌的推广和维护,通过主办、协办、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通过利用好新媒体平台,提升刊物的影响力,并以最好的服务回馈作者的支持。此次研讨会上,与会期刊编辑与作者进行了精彩的学术对话。与谈编辑听取作者的论文汇报后,根据具体情况从选题、标题、研究方法、结构安排、文献引用、投稿策略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各项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对于作者的一些质疑和求教,编辑们也耐心地予以解释和指导。现场时而剑拔弩张,时而欢声笑语,各方代表精彩的发言与踊跃的讨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热烈的气氛、高昂的情绪,令这次编辑作者对话交流会几度延时。在法学院大楼走廊回响的讨论声中,法学期刊与新时代中国法学创新发展研讨会圆满落幕。编辑:法评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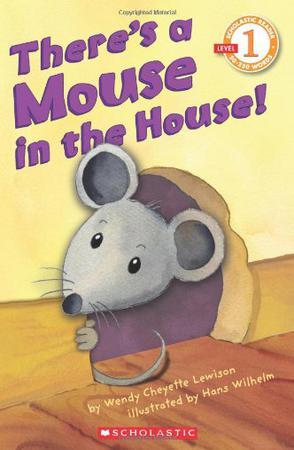 浮业镇
浮业镇华东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
华东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12月20日揭牌成立。这是华东政法大学发挥法学专业和人才优势成立的上海高校首个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将立足上海,与全国一流法学专家和理论骨干携手合作开展相关研究、阐释工作;中心将在广泛汲取各方面智慧和资源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理论研究,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工作,把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效融入课程思政建设,选拔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教学能力突出、建言献策踊跃的专家学者,更好地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和阐释的共同体。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上海市教卫党委书记沈炜,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解超,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曾峻,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丕祥教授,原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上海交通大学沈国明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商研究》主编姚莉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党委副书记、校长叶青,教育部、市教卫委党委、全国各高校法学院领导、专家和教师代表参会。据悉,研究中心由郭为禄和叶青担任中心主任,由著名法理学专家、《法学》杂志主编胡玉鸿教授担任执行主任,同时设顾问委员会和学术委员,张文显、徐显明、公丕祥、李林、沈国明等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付子堂担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宗科、姚莉等知名学者专家担任副主任委员,全国各知名院校法学院所专家担任委员。当天还举办了一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理论研讨会,来自教育部、上海市委党校、三十二所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专题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运用问题, 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学术阐释。(看看新闻Knews记者:朱玫 编辑:小真)
 美人关
美人关第二届“全国民商法博士生论坛”将举行
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承办,《法商研究》编辑部 、《法学》编辑部 、《比较法研究》编辑部 、2020年第二届“全国民商法博士生论坛”将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以“民法典时代民商法解释论的新发展”为主题,论坛设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2名,奖金各10000元;二等奖5名,奖金各5000元;三等奖8名,奖金各2000元。据了解,2019年10月12日至13日,首届“全国民商法博士生论坛”在华东政法大学举办。在此之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已连续举办了九届“全国民商法博士生论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也举办了首届“全国民商经济法博士生论坛”,以上论坛均旨在为全国民商法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提供学术成长的机会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求学术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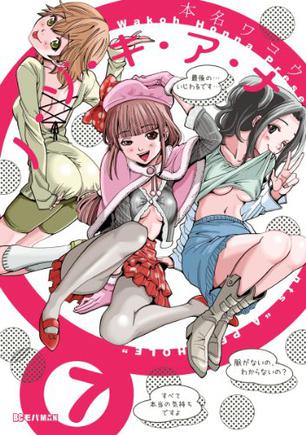 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博览天下|杨东、徐信予:区块链与法院工作创新——构建数据共享的司法信用体系
作者简介:杨 东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徐信予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共票与公共数据开放”(项目编号:19XNQ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载于《法律适用》2020第一期内容摘要数据作为司法审判中语音识别、区块链存证、人工智能等辅助技术发展的“原材料”,也是全流程在线审理机制建设的核心要素。而区块链技术的去中介、分布式、防篡改等特点给数据的利用方式、价值体现提供了新的选择,特别是区块链存证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使数据脱离了纸质文本的“形式束缚”与第三方中介的“效力依附”,为重构数字经济时代的信任模式打下了坚实基础。数据的顺畅流动是走向信用司法体系的应有之义,但囿于数据流动的制度成本大且激励不足而存在“数据滞流”现象,需要区块链技术和“共票”机制在司法机构之间构建对等的平台和有效激励机制,构建属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司法信用体系。关键词:数据滞流智能合约共票一、问题的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抓住区块链技术融合、功能拓展、产业细分的契机,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这一讲话明确了区块链技术在我国技术发展和产业变革中的地位,也为国家治理与司法审判工作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机遇、新挑战指明了方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大潮流下,既产生了数字货币、区块链存证、农产品溯源、身份认证、护照办理、时间银行、政府管理、档案验证等创新应用,也出现了利用区块链、数字货币进行传销诈骗,利用区块链分布式、跨国界等特点进行金融犯罪等问题。急速到来的数字经济时代并未给司法的应对预留太多时间,新型案件数量剧增、电子证据形式复杂化和执行难度增大是司法必须直面的燃眉之急。互联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人们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又将面临新型案件剧增的现实压力。各级法院在解决区块链带来的新问题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司法数字化中的创新应用,全国诸多法院已选择了区块链技术作为其数字化业务发展的底层技术之一。截至2019年6月,已有杭州互联网法院主打的“司法区块链”“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北京互联网法院打造的“天平链”,广州互联网法院推出的包括司法区块链、可信电子证据平台、司法信用共治平台“一链两平台”的“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此外吉林、山东、天津、河南、四川等12个省(市)的高院、中院、基层法院均已上线了区块链电子证据平台。[1]这标志着摸索区块链在司法中应用的哨声已经吹响,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有望成为未来司法变革的底层技术。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应当如何解决层出不穷的司法问题?如何应对司法审判中面临的种种数字化挑战?更为紧迫的是,以金融为主要应用场景、以比特币闻名的区块链技术应如何嵌入我国司法数字化运行之中?二、司法的“数据滞留”困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断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分配合理有序。”这是中央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数据的助推下,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不断涌现,人类活动在现实与虚拟的交织中得以无限延展。[2]而体现个人的个性表达和言论等数据在一定程度体现个人心理和情感,[3]也因此个人的浏览记录、交易记录等数据被企业广泛收集形成数据画像用以精准营销。[4]数据的累加使得算法得以拟制出一个个“数据人”。更进一步说,现实生活中的数据由政府、企业、个人等主体的各种行为交互而形成,[5]因此数据不仅能忠实地拟制“人类”,也能反映其他更复杂的自然与社会情况,甚至可对未来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高度数字化的“数据地球”。(一)数据补位:司法人力资源错配数据是这一轮技术集群涌现的“驱动原料”,在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技术的发展中发挥“原材料”的作用。从生产要素理论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会存在主导性生产要素,该要素代表着某一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能够成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6]不同于工业时代石油的相对稀缺性,数字时代的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具有可复制、易增殖性,其价值随着人类的二次使用、交互等行为不断增加;更加关键的是,数据的非排他性使数据共享成为可能。[7]数据也是司法审判中各项辅助技术发展的“原材料”。当前,语音识别、区块链存证、人工智能等技术都在不同程度上嵌入了司法审判的各个流程之中,但这些技术离开了数据供给将形同虚设。比如当前智能化司法中存在的概率建模下的司法要素限缩、裁决算法的价值偏见、裁决算法黑箱等问题的解决,[8] 都依赖数据的大量供给。只有源源不断地向算法模型进行数据投入,才能使人工智能算法不断自我演化,更加符合人类的社会行为规范,在司法审判中更显“智能”。司法人力资源配置错位需要数据补位。司法审判中事务性工作繁重已被诟病许久,案件繁多现象与司法工作如影随形, [9]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文书传递成本高,证据验证和审查复杂,司法执行难度大,大量司法资源不得不被投入到包括填写传票、证据辨认、起草文书、送达文书、归档等琐碎的程序性事务。[10]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法律文书的送达问题,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流动规模大,这就给法院的文书送达增加了压力。司法文书传递的本质是信息传递,如果可以实现数据在司法中多方触达,足以填补传统人力资源错配的困境。当前各类区块链司法创新的本质都是推动数据在司法中的功能补位。当前存在的区块链司法创新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北京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将各类电子数据通过区块链技术保证了真实性;另一类是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移动微法院”为代表的,将线下诉讼转移至线上,使得审判等司法活动可以借助现有的通讯技术突破空间的障碍,例如广州互联网法院推出的“网通法链”依托智慧司法政务云、百度超级链,联合“法院+检察院+仲裁+公证”多主体数据调用方,集聚“运营商+金融机构+企业”跨领域数据提供方,为智慧信用生态系统提供多方可查、安全可控、中立可信、负载均衡的区块链技术支撑;“移动微法院”利用区块链技术,在线对标准签名进行验证,确认当事人身份。上述法院在司法审判创新中都积极地应用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新技术,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可触达性,局部完成司法程序的优化,实现了数据在司法中的功能补位。(二)现实之困:数据滞流于何处机构和平台是承载数据的重要主体,也是决定数据流动模式的关键。《电子商务法》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电子商务经营者”等表述强调了平台在电子商务中的重要地位。数据存储具有相当的资金、技术、政策门槛,只有具有一定规模与相关产业支撑的企业才能作为数据库建设、管理者。[11]数据主体的门槛也决定了推动数据流动过程中必须考量机构和平台的相互关系与运作流程。根据数据承载主体之间的关系,数据流动可以分为纵向流动与横向流动。由于纵向的数据流动往往发生在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机构之间,所以数据流动相对顺畅。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建立的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庭审公开网及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司法公开系统,“移动微法院”诉讼平台和以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专业法院建设,是对构建全流程在线审理机制的有益探索,有效解决了法院系统内的数据纵向流通问题。而横向数据流动往往发生在互不隶属的机构或平台之间,往往会出现“全频带阻塞”。[12]全频带阻塞,是指在战争情况下所采用的一种极端性质的电信号频带干扰。通常情况下战场通信采用算法加密,然后分频带阻塞,全频带阻塞的情况一般是在受压制的一方孤注一掷索性将所有通信频带通通强制干扰从而使整个战场交战各方通信完全中断的一种情况。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各类数据包涵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数据对外流转可能产生安全风险以及因用户信息泄露招致的行政处罚与公关危机。从客观方面看,不同机构的数据库建设标准不同,数据的收集与分类各有异同,加之缺乏对外数据开放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SDK(软件工具包)端口,使得数据流动在客观上也内含技术性障碍。市场机构之间的横向数据流动尚可通过市场交易、机构兼并和爬虫技术等实现。现行法中也存在一系列制度可以调整和保护数据所负载的利益,[13]比如近些年出现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开放银行”,就是通过开放金融机构的API或SDK端口,将金融数据与第三方进行共享,实现金融消费者的数据转移。[14]非市场机构之间的横向数据流动则由于共享激励长期缺位等原因而举步维艰。非市场机构往往是行政或者司法机构,其数据横向流动不足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是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而拒绝进行分享,数据共享带来的信息泄漏往往会造成相关机构的责任承担;第二是数据本身质量参差不齐,数据共享将会暴露机构对数据库的管理问题;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激励。数据存储在不同机构的中心化数据库中,向外传送的数据就会成为对其他数据库的“无偿奉献”。市场手段往往难以实现对互不隶属机构之间数据共享的正向激励,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机关,其最大的激励手段是行政的升迁。[15]这就使得数据共享往往流于形式,停留于“运动式治理”状态,[16]也因此难以形成数据流动的长效机制。沉疴需猛药,司法资源的错配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数据滞流”背后的激励机制的构建问题。而在传统路径乏力的背景下,化解“数据滞流”之痼疾更要另辟蹊径;选择以区块链技术为内核驱动的数据治理之道,或可成为解决司法数据触达难题的另一种选择。三、区块链撬动司法数据流动“移动微法院”和以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专业法院建设,对构建全流程在线审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从数据真实性角度有效解决了司法数据纵向流通问题。不论是以三大互联网法院为代表的区块链存证创新,还是以“移动微法院”为代表的诉讼流程创新,都仅是在有限的民事法律领域对相关证据规则和司法程序进行优化,建立在法院和当事人关系相对简单的基础上,该过程中不必涉及其他司法、行政机关。而在超出这一范畴的刑事乃至行政领域则缺乏具体的场景应用,仍待进一步探索。(一)区块链:分布式的对等平台区块链根据其开放程度可以分为公有链、私有链和联盟链。公有链具有参与门槛低、参与者数量多的特点,只要具备一定资质即可加入,其大量应用于数字货币等领域,例如比特币(BTC)和以太坊(ETH)。私有链则是某一单位内部使用的区块链,不对外部开放,因而具有速度快的优点。而联盟链是介于公有链和私有链之间、偏向于私有链范畴的区块链。联盟链主要有以下特点:1不完全分布式;2可控性较强;3数据的有限访问;4交易速度快。当前对联盟链青睐有加的大多是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较为著名的有R3区块链联盟、 R3区块链联盟于2015年9月份成立,目前已经有大约40多家国际银行组织加入,成员几乎遍布全球。其主要致力于为银行提供探索区块链技术的渠道以及建立区块链概念性产品。R3使用以太坊和微软Azure技术,将11家银行连接至分布式账本。超级账本(Hyperledger) 超级账本(Hyperledger)是Linux基金会于2015年发起的推进区块链数字技术和交易验证的开源项目,加入成员包括:荷兰银行(ABN AMRO)、埃森哲(Accenture)等十几个不同利益体,目标是让成员共同合作,共建开放平台,并简化业务流程。目前已经有北京AiYi数字金融技术公司、Belink(数贝荷包)、BitSE和Onchain共4家中国公司加入。和俄罗斯区块链联盟。俄罗斯区块链联盟也被称为“俄罗斯版R3”,正式成立于2016年7月1日,其成员包括支付公司QIWI、B&N银行、汉特-曼西斯克银行(Khanty-Mansiysk Otkritie Bank)、盛宝银行(Tinkoff Bank)、莫斯科商业世界银行(MDM Bank)以及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联盟链可以在技术上实现节点之间地位的完全平等。联盟链更类似一种分布式的数据库技术,联盟链与公有链的差别在于它只对特定的组织团体开放,因此联盟链的共识过程受到预选节点控制。也就是说,联盟链上的节点都受到一定资格限制。简单来说,联盟链上的信息对每个人都是只读的,只有节点有权利进行验证或发布交易,这些节点组成了一个联盟,普通用户如果想发布或者验证交易,则需获得联盟的许可。在联盟链中诸多机构可以联盟链为基础平等地开展工作,各个节点数据库也保持一致。诸多加入的机构将会接受统一的数据标准,多数据库同步记录,这就减少了不同机构之间数据录入的成本。如果数据记录不准确,也可以在联盟链上发起“异议”,通过多个数据的对比和“投票”机制纠正数据库记录。与传统集中式数据库之间数据流动的“零和游戏”不同,联盟链之间的数据库建设改变了传统集中式数据库数据有去无回的数据共享方式,在理论上可以实现“1+1≥2”的效果。联盟链可以兼顾数据开放与信息保密,满足司法数据的保密性要求。首先,数据开放往往与信息保密不可兼得,但在联盟链上可以设置相应权限,只有在该联盟链上的节点数据库才可以进行读取、上传和发起修改。其次是在数据库中应用“零知识证明”, 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是由SGoldwasser、SMicali及CRackoff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它指的是证明者能够在不向验证者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的情况下,使验证者相信某个论断是正确的。零知识证明实质上是一种涉及两方或更多方的协议,即两方或更多方完成一项任务所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可以实现最小泄露证明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联盟链中的每个节点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私钥,每个节点产生的数据信息只有该节点知道。如果节点与节点之间需要进行信息交换和数据交流,就必须知道对方节点私钥,这能够在保证信息流通的同时,避免节点隐私泄露的问题。最后,对于私钥的获取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甚至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在要式条件达成情况下自动获取,这在司法等具有一定保密性的领域具有极高的价值。全国范围内部分司法机关和机构已经先行试用了联盟链,联盟链有望成为司法机关共建数据库的基础支撑。杭州互联网法院主打的“司法区块链”“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广州互联网法院推出的包括司法区块链、可信电子证据平台、司法信用共治平台“一链两平台”的“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将电信、移动、联通等三大运营商,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仲裁委、南方公证处和广州公证处等司法机构,腾讯、平安、华为、百度、阿里、京东等30余家企业纳入智慧信用生态系统。北京互联网法院打造的“业务链、管理链、生态链”三链合一“天平链2.0版本”,已完成跨链接入区块链节点19个,已完成版权、著作权、互联网金融等9类25个应用节点数据对接,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4万件案件全部上链,上链电子数据超过1000万条,跨链存证数据量已达上亿条。[17]除互联网法院外,截至2019年10月31日,全国已完成北京、上海、天津、吉林、山东、陕西、河南、浙江、广东、湖北等省、直辖市的22家法院及国家授时中心、多元纠纷调解平台、公证处、司法鉴定中心,共计27个联盟链节点建设,共完成超过194亿条数据上链存证固证,支持链上取证核验。[18](二)“共票”:数据流动的激励机制数据在实现技术上的平等共享之后,还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各个机构上传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共票”(Coken)是实现利益分配的机制,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机制创新。[19]对于共票制度,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众筹是核心制度,区块链是基础技术,‘共票’是共享权益。”[20] 数据与“共票”的关系是共票制度的核心,区块链技术是“共票”理论的技术基础。[21]区块链为数据赋权,让每个数据贡献者都有参与数据共享的权利;“共票”为数据赋能,旨在实现两大功能:第一是价值发现,锁定高价值数据;第二是让每个参与者分享数据共享的红利,调动数据共享的积极性。共票制度的核心在于构建内生激励机制,以促进司法诚信体系的良性运转。区块链为数据共享提供了底层技术。基于区块链技术,数据可以实现在多个数据库(节点)之间的同步;甚至从理论上说,以区块链为根本,有望实现对于数据共享这一行为的有效激励。[22]“共票”对于激励制度影响之大,与其说是一场技术革命,毋宁说是一次制度革命。“共票”是一种权益凭证,在数据流动中,可以根据不同机构所贡献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向其反馈作为激励凭证的“共票”。一方面,可以“共票”衡量相关机构所提供数据的质量并作为其业务的考核凭据之一,甚至形成共同建设司法诚信体系的“锦标赛体制”;缺乏术语解释,[23]另一方面,“共票”作为一种权益凭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流通,兑换一定的实物或公共服务。通过“共票”可以激发司法机关等的数据共享热情,产生数据共享的内生动力。四、重构数据时代的信任机制信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没有信任也就没有了社会,[24] 而区块链被誉为数字时代改变信任的“工具”,其将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交往习惯和社会形态。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通道把全球70多亿人类连接起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活动的便利性;而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物联网等技术变革正在逐渐向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25]信任的建立与维系也经历了瓦解与重构,单纯的信息互联网已向人类可以互相信任的价值互联网演变。(一)铺垫:司法电子化从历史发展看,司法从纸质到电子,从电子到数字是发展的必然进程。早在1983年,龚祥瑞和李克强就借鉴了美国、欧洲和前苏联在司法电子化建设方面的成果而提出法律工作的电子化(计算机化)对中国司法具有重大意义。[26]从2007年到2017年,全国各级法院都在快速进入信息化时代,“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诉讼服务网”“律师服务网络平台”“最高人民法院域外法查明统一平台”等一系列网站也相继开通。[27]被“禁锢”于各个机构、大学、图书馆的以纸质文本呈现的法律文件、资料被转化为电子形式,从而实现快速检索。法律文本与资料的电子化为司法审判的数字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审判将会顺理成章地实现数字化。司法数字化意味着案件起诉、立案、调解、举证、质证、庭审、宣判、执行等诉讼环节全部在线完成,这就要求在信息传递中实现“数据库→数据库”的直接数据转移,而非“数据库→纸质文本→数据库”的模式。由于电子化是纸质文本上传至各自孤立的数据库中,数据库的建设标准不同意味着不同机构的数据库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数据交流,数据入口缺乏与格式不兼容使得数据在不同数据库之间的转移存在巨大的技术障碍。只有从根本上脱离纸质文本的“效力”束缚,司法审判才能真正走向数字化。电子化和数字化的根本区别在于文件效力来源不同,电子化的效力来源于第三方机构的背书,而数字化意味着数据本身就具有效力。电子化是纸质文本的电子化,在这一过程中,第三方机构的法律效力是不可替代的,比如庭审中提交的电子证据往往是纸质版文件的扫描件或是相关页面的截图,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纸质文件的电子化,依然需要第三方的“公证”。以二进制代码形式呈现的数据本身就具有不必假借于外物的法律效力,这才是司法数字化所要达至的目标。(二)先声:区块链存证法律和技术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在许多领域两者具有可替代性。[28]由于可以对电子化的证据进行篡改和伪造,仅仅是电子化的证据无法自证其“真”,数字化仍需区块链技术实现证据的不可篡改性。正如单个人无法实现对微信群聊天记录的篡改,区块链也通过众多“节点”形式的数据库保存了记录,这就防止了数据在上传之后被篡改,保证了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天平链的技术架构分为应用层、管理层、服务层、核心层和基础层。其中,应用层即为天平链电子存证平台,主要有用户功能、业务功能和管理功能。在管理层有接入功能节点功能,北京互联网法院积极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公证处、行业组织、大型央企、大型金融机构、大型互联网平台等,使其作为“天平链”的节点。基于区块链可以实现去中介化认证,大量区块链存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法大大、法链存证等区块链存证平台都在分布式记账的基础上保持节点的相对数量,既提高了司法存证的共识效率,也确保了司法存证内容的可信度;不同机构间数据的同步有效解决了传统流程复杂、公信力不足、信息不对称、传递效率低的痛点。比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建设的“天平链”,利用区块链技术多方参与、防篡改、可追溯的特点,实现了“数据生成”、数据存证、数据取证、数据采取的全流程上链,解决了审判当中电子证据的取证难、存证难、认定难“三难”问题,是区块链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典型应用。广州互联网法院的“网通法链”的事前存证,自动验证系统也实现了证据的全流程数字可信化。具体而言,在这一场景中,司法区块链、广州互联网法院电子证据平台、互联网应用平台、广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之间,通过事前对相关合同和证据进行保存,在诉讼发生时,快速提取司法区块链上存证的证据,实现了快速无争议的证据提取、验证,通过九个步骤的无缝衔接,有效地从根本上提高了司法效率。图1网通法链的事前存证,自动验证系统区块链存证的应用改变了传统证据结构,也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方式认可了区块链证据的合法性。[29]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通过私力取证获得的电子证据往往要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全面说明,而电子证据的技术化程度越高对于缺乏相应技术水平的当事人而言取证难度也越高,以至于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虽种类繁多却难以自证其效力,[30] 特别是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的“真实性”审查,往往要耗费法官大量时间进行甄别和判断。而就登记在区块链上的证据而言,其真实性不需要其他证据补强和链式论证,本身就代表了真实性。因此在2018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确认了在符合真实性的条件下,区块链存储的电子证据可以作为有效证据被法院采纳。区块链存证是司法数字化的先声,提高了个人与审判机关之间的数据流动效率,使得在诉讼中不必纠结证据的“真实性”,这意味着一套合适的诉讼系统足以“解放”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的人力资源。广州互联网法院在2019年8月探索“互联网+”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并成功研发在线纠纷“类案批量智审系统”。当事人可通过该系统,在线批量提交证据、发起立案申请。法官可批量实现立案审查、排期、在线庭审、生成裁判文书、送达。与传统送达不同的是,送达全程区块链留痕,可实时追踪送达时间、地点、签收人等关键节点信息。同时,对于代表性强、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件,法官可以通过发送邀请码等形式,实现同类型案件当事人在线旁听,举一反三,推动平行案件达成和解、调解协议或自动履行。随着在网络世界嵌入程度的进一步攀升,区块链也将从当前的数字货币交易、存证、不动产登记、发票、产品溯源等领域走向更多的社会应用场景。(三)目标:信用司法体系司法变革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轫于技术创新,滥觞于制度变革。[31]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时序数据、集体维护、可编程和安全可信等特点,特别适合构建可编程的货币系统、金融系统乃至宏观社会系统。[32]对于司法而言,其意味着可以构建基于区块链的信用司法体系。区块链存证有助于解决数据从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传递过程中的真实性问题,数字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从“数据库→纸质文本→数据库”的信息传递到“数据库→数据库”的数据转移,从点到面,从起诉到执行的司法全流程数字化。未来更是需要拓展数据触达的深度,延伸数据流动的广度,打造以数据为驱动的信用司法体系是未来司法建设的主攻方向。区块链的2.0形式——智能合约被视为数字世界运行的齿轮和未来信用系统中可运行的诉源治理新模式。[33]智能合约最早由Nick Szabo博士提出,它被认为是以数字形式定义的能够自动执行条款的合约。[34]在未来大量的合同可以转至区块链上,对于违反合同条款的行为一般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直接进行处置,只有出现智能合约无法处理的纠纷时,法院才予以介入。可以假设这样的一种场景,当事人对智能合约中约定的事项产生纠纷,无法通过预先设定的条款进行解决,那么法院将介入处理,而后在全网“广播”判决结果,并在区块链上直接执行诉讼标的。在2019年10月24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上线了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打造“自愿签署-自动履约-履行不能智能立案-智能审判-智能执行”的闭环司法体系,这一体系旨在高效处理违约行为,并通过智能合约减少了不可控因素的发生,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实现数据可信化全记录,多部门协作,全节点见证,是智能合约在信用司法体系应用的先驱。在司法中对于智能合约的广泛应用有赖于相关成就条件的“上链”——广泛的现实资产的数字化和法律行为的数字化。目前在不动产、学历登记、农产品溯源、遗嘱、发票、门票、债券发行、身份验证、遗嘱继承、合同订立等领域都出现了区块链的落地应用。以娄底市不动产区块链信息共享平台为例,传统的法院判决与执行之间存在一定时间差,这就给诉讼标的的转移留下了违法操作空间。特别是在现有的各个数据库系统分割的状态下,房管部门与法院对于不动产的登记记录不一致,甚至可能现实情况和登记情况也存在不一致,在执行中发现不动产产权已经转移等情况。区块链不动产登记就是在这一情况下,打通了不动产的数据登记,解决了执行中存在的标的不符状况。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多元统一的信用司法体系。我国各地应用区块链技术有快有慢,特别是在证据提取和执行层面需要社会治理手段的配合,各地区也会因本地化色彩产生创新的“地方特色”,形成各地具有一定差异的信用司法生态。比如广州互联网法院利用区块链技术,在保证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基础上形成的“五色信用”评价体系、“网通法链”智慧信用生态系统、“E法亭”便民诉讼服务设施、“E链智执”执行工作平台等立足于广东地区的信用司法小生态。要鼓励司法与基层治理创新有机融合,在证据保存提取、执行财产网络处置等方面形成多元并存、良性促进的格局,最后在互相补充的基础上构建拓展至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信用司法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传统的司法体系和构筑于区块链技术之上的信用司法体系将同时并存,对于这两种体系的长期并存中,司法创新不断发挥“扬弃”的作用,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中国司法的革新,而两者的动态变化将会最终孕育生成契约化的法治秩序。[35]五、结论与展望对于区块链技术创新到底会将未来的司法引向何处仍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这是法律秩序的产生是由人类理性决定还是由社会实践决定两种观点碰撞的当代重现。哈耶克将人类秩序分为“自生秩序”和“建构秩序”,[36] 西方法学家针对法律秩序的产生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讨,特别是19世纪初德国海德堡大学罗马法教授蒂堡(AFThibaut)与法学家萨维尼(KVSavigny)关于统一民法的“建构主义与自然生成路径之争”。[37]就区块链在司法中的创新而论,发挥植根于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创新潜力,结合各个地区现实情况的多样性,探索符合我国国情、民情、社情的区块链司法应用之路,这是新时代以区块链技术变革为契机推动信用司法体系构建的必然选择。在司法工作中对区块链技术的重视,不仅是对其本身技术特征的推崇,更是应当把握技术革新带来的制度变革契机,进一步打通司法领域的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在区块链嵌入司法审判的同时,关注区块链司法创新与社会基层治理的有机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制度张力和生命力的多元社会信用司法体系,回应人民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司法工作中具体落实的殷切期盼。注释:[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编:《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2] 参见马长山:“‘互联网+时代’法治秩序的解组与重建”,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3] 参见贺栩栩:“比较法上的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载《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2期。[4] 参见丁晓东:“用户画像、个性化推荐与个人信息保护”,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5] 参见龙卫球:“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6] 参见岳佐华、李录堂:“生产要素演进规律及其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启示”,载《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7] 参见胡贝贝、王胜光:“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产函数”,载《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9期。[8] 参见马靖云:“智慧司法的难题及其破解”,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9] 参见尤陈俊:“‘案多人少’的应对之道:清代、民国与当代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10] 参见周迅:“当前基层法院人案现状的主要特点及对策分析——以溧水法院的调查为样本”,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11] 参见杨东:“‘二选一’是否垄断不可一概而论”,载《经济参考报》2019年10月28日第7版。[12] 参见刘慈欣:《流浪地球·刘慈欣短篇小说精选》,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309-352页。[13] 参见纪海龙:“数据的私法定位与保护”,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14] 参见杨东、程向文:“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开放银行数据共享机制研究”,载《金融监管研究》2019年第10期。[15] 参见周飞舟:“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及范式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16] 参见周雪光:“寻找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17] 徐伟伦:“北京互联网法院打造‘天平链20’”,载《法制日报》2019年12月9日第3版。[1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编:《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19] 参见杨东:“Libra:数字货币型跨境支付清算模式与治理”,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20] 参见杨东:《区块链+监管=法链》,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21] 参见杨东:“‘共票’:区块链治理新维度”,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22] See Yang Dong,Blockchain and Coken Economics:A New Economic Era,Author House UK 2019p5-16[23] 参见周飞舟:“锦标赛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24] 参见翟学伟:“从社会流动看中国信任结构的变迁”,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25] Swan Melanie,Blockchain:Blueprint For A New EconomyO'Reilly Media Inc,2015p16[26] 参见龚祥瑞、李克强:“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载《法学杂志》1983年第3期。[27] 参见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3期。[28] 参见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29] 参见张玉洁:“区块链技术的司法适用、体系难题与证据法革新”,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3期。[30] 参见刘显鹏:“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关系探析——以两大诉讼法修改为背景”,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31] 参见杨东:“论金融领域的颠覆式创新与监管重构”,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1期,第30页。[32] 参见袁勇、王飞跃:“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载《自动化学报》2016年第4期。[33] 参见杜前:“智能合约,让纠纷解决更高效”,载《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7日第7版。[34] Nick Szabo,Smart Contract:Building Blocks for Digital Markets1996载http://wwwfonhumuvanl/rob/Courses/InformationInSpeech/CDROM/Literature/LOTwinterschool2006/szabobestvwhnet/smartcontractshtml,2019年12月4日访问。[35] 参见梁平、冯兆蕙:“基层治理的法治秩序与生成路径”,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6期。[36]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37] 参见梁平:“基层非正式治理的法治化路径”,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10期。来源:《法律适用》2020第一期编辑:杜绮祺
 猎天下
猎天下公示公告!这77篇论文拟获奖
第26次山东省法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公示公告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展示近年来山东省法学法律研究丰硕成果,激励更多优秀法学法律工作者脱颖而出,近日,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厅、省法学会组织开展第26次全省法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经由山东政法智库、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等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匿名严格公正评选、认真研究,共评选出获奖优秀成果77项。其中,一等奖15项,二等奖24项,三等奖38项。现将拟获奖的名单予以公示。一、一等奖(15项)1.论宪法与国际法的互动作者单位:王德志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2.广义抑或狭义:身份犯中身份概念的再界定——以身份的本质为中心作者单位:周啸天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人大法律评论》2017年卷第3辑3.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及其完善作者单位:孙光宁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4.论司法过程中的案件事实论证作者单位:武飞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家》2019年第6期5.《合同法》第167条(分期付款买卖)评注作者单位:郝丽燕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家》2019年第5期6.终身监禁之立法解读、法律性质及溯及力作者单位:吴玉萍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2017年第10期7.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路径作者单位:苗红培 山东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发表期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8.构成要件保护目的与过失犯结果不法的规范限缩作者单位:李波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家》2017年第5期9.公司法民事责任的解释方法——以公司股东、内部法律责任分析为视角作者单位:杨志壮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律科学》2019年第6期10.中国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演进趋势与改革走向——基于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作者单位:管金平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11.从私法范畴到政策维度——当代物权变动制度的哲学反思作者单位:刘经靖 烟台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12.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作者单位:李克杰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13.日本宗教法人制度作者单位:黄晓林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出版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14.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研究作者单位:徐丽枝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法律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15.比较法视角下我国农业补贴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作者单位:王维芳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结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9年10月结项二、二等奖(24项)1.警察即时强制权的规范化行使——以公民权利保护为线索作者单位:刘军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东方法学》2019年第6期2.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虚无陷阱及其化解——兼评法释〔2017〕20号第12条作者单位:满洪杰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2018年第7期3.犯罪学视角下校园暴力的预防与处理作者单位:侯艳芳(第一作者)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9年第5期4.法律漏洞补充行为的失范与规制作者单位:曹磊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5.立法解释的学理解构与制度重建——以刑法为视角作者单位:马凤春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发表期刊:《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6.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规制作者单位:张爱艳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陈 灿 山东郓城法院法官助理发表期刊:《刑法论丛》2019年第1卷7.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法教义学分析作者单位:安 然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8.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模式构建作者单位:王占启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杂志》2019年第9期9.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内涵与表达思路作者单位:管洪彦(第一作者)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发表期刊:《江汉论坛》(CSSCI)2017年第4期10.人工智能风险规制的困境与出路作者单位:郭传凯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9年第6期11.论法律解释的目标作者单位:解永照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发表期刊:《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12.我国绝对确定法定刑立法模式的历史考证及其现代意蕴作者单位:黄春燕《政法论丛》编辑部发表期刊:《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13.更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刑法评价作者单位:孙 杰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法论丛》2018年第2期14.继承人有无不明时的继承法完善作者单位:于 晓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法论丛》2017年第6期15.自动驾驶汽车风险的立法规制研究作者单位:侯郭垒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8年第5期16.论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从人类基因编辑事件切入作者单位:钱继磊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政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5期17.检察机关检察权制度研究作者单位:李 震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马建华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18.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实证研究—以S省H市两级法院为例作者单位:王 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版单位:法律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19.英国普通法权利保护研究作者单位:刘吉涛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20.论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限制及其正当性作者单位:罗亚海 临沂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21.明代监察御史巡按职责研究作者单位:陶道强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出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22.乡村振兴战略法律问题研究作者单位:王淑华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结项课题:山东省法学会2018年度“民营经济法治保障十大课题”2019年7月结项23.国有企业类型化改革与监管的法律体系重构作者单位:封延会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结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2019年12月结项 24.法治中国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建设研究作者单位:韩 慧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结项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2019年9月结项三、三等奖(38项)1.法律漏洞的特征与填补路径作者单位:李秀芬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2.“立法”和“行政”概念的宪法解释作者单位:门中敬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3.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治的困境与对策作者单位:范冠峰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发表期刊:《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4.合宪性审查与法律规范审查体系的裂隙与衔接作者单位:张栋祥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5.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ublic-interest Litigants in China: Evolution, Obstacles and Solutions(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演进、困境及应对)作者单位:翟甜甜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张晏瑲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SSCI一区,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年第3期6.两汉经律融合视域下“比”的法律意义作者单位:林 丛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7.论澳大利亚家庭法审查中的儿童程序参与作者单位:齐凯悦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民商法论丛》2019年第2期8.论新时代公安组织文化的再塑造作者单位:石 嵩(第一作者)青岛市市南区委政法委发表期刊:《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9.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作者单位:姜爱丽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10.终止追究并不等同免予追究作者单位:祖丙山 平原县人民检察院发表期刊:《检察日报》2019年5月26日第三版11.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探析作者单位:冷 帅(第一作者)山东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发表期刊:《中国律师》2017年第5期、第6期12.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的替代性解决方法研究作者单位:刘万啸 山东政法学院经贸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杂志》2017年第10期13.法教义学视角下的交通法学教材建设的问题与举措作者单位:张志文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学院发表期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14.论“三权分置”下农村承包地上的权利体系配置作者单位:肖立梅 山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处发表期刊:《法学杂志》2019年第4期15.法国破产重整方案中的债转股问题研究(译文)作者单位:种 林(第一作者)山东政法学院经贸法学院发表期刊:《政法论丛》2019年第1期16.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研究—基于 s 省试点实践调查作者单位:伊庆山 山东政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发表期刊:《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17.中国近代遗产税立法及司法实践研究作者单位:郑显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法学院王 蕾(第二作者)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发表期刊:《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1期18.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作者单位:张亚丽(第一作者)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19.专利权的所有权构造方式及其功能作者单位:郭雪军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发表期刊:《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10期20.亲属法价值取向中的人性根基作者单位:李 伟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杂志》2017年第9期21.广播组织权客体研究作者单位:崔立红(第一作者)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22.“认罪认罚从宽”内涵再辨析作者单位:赵 恒 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23.行政救济考核指标如何设计—以地权保护为例的分析作者单位:章彦英(第一作者)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 24.经济刑法机能的重塑:从管制主义迈向自治主义作者单位:张小宁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发表期刊:《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25.Growth and Innovation of Land Trust System in China(中国土地信托制度的成长路径与创新实践)作者单位:于朝印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China Legal Science》(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26.乡村法治社会建设研究的四重哲学维度作者单位:张 强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7日27.当代新法家研究及其主要价值作者单位:赵玉增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4期28.二审民事案件适用独任制审理的理性逻辑与进路探索作者单位:荣明潇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表期刊:《法律适用》2017年第9期29.论正犯与共犯区分之中国选择作者单位:马 聪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发表期刊:《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30.涉外足球劳动合同争议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的特殊性作者单位:董金鑫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法学系发表期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31.法律硕士人才培养中的六大关系研究作者单位:窦衍瑞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32.个人金融信息管理:隐私保护与金融交易作者单位:朱宝丽(第一作者)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33.预防犯罪与矫正罪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者单位:王立军(主编)山东省监狱学会出版单位:法律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34.山东省地理标志保护发展作者单位:杨 永 菏泽学院政法学院出版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5.要素式审判权运行机制研究作者单位:胡发胜(主编)莒南县人民法院出版单位: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36.保障性住房地方立法及实践研究作者单位:李会勋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7.多维视角下的诉权保障研究作者单位:王岩云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出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38.美国私人养老金法律制度研究作者单位:周 煜 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出版单位:法律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对上述名单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间内向省委政法委、省法学会反映(信函以当地邮戳时间为准)。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地址。对线索不清的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函,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公示期限至3月10日。受理单位:山东省法学会研究部受理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00-5:00受理电话:0531-82923349通讯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5743号邮政编码:250014来源: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山东省法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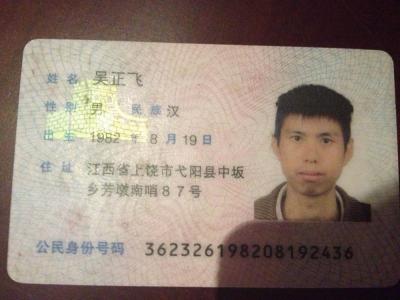 王浮
王浮第七届天山法学论坛:武大新大携手为丝绸之路贡献法治新智慧
人民日报客户端政经视窗讯(法治观察员 一舟)2019年8月6-9日,第七届天山法学论坛在新疆大学成功举行。论坛由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给予指导,武汉大学法学院、新疆大学法学院、新疆党内法规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学会、国家知识产权培训(新疆)基地、新疆稳定与地区经济发展保障基地、自治区专利信息中心、新疆大学图书馆、新疆大学知识产权信息中心承办,新疆元正盛业律师事务所协办。天山法学论坛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在落实中央援疆工作中,与新疆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的法学论坛,是新疆法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盛会。从2005年第一届联合举办以来,至今已经举办七届。本届论坛,武汉大学法学院派出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江学者、院长冯果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江学者秦前红教授,副院长祝捷教授以及孙晋教授、段磊副研究员、苏绍龙助理研究员等重量级学术阵容参与了论坛的组织和研讨;《法学评论》给予了学术支持。同时,论坛还邀请到了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同济大学李明德教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曹新明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易继明教授;国家法官学院施新洲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弘弘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姬亚平教授、内蒙古大学杨凯民教授等,以及《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张广兴教授;《法学》、《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商研究》、《清华法学》、《政法论坛》、《法制日报》、《江海学刊》等期刊杂志的主编、编审、编辑等50余名疆外专家学者和50余名疆内学者,还特邀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杨翔科长和外事办李保全主任。参加会议的疆内外学者达100余人,是历届天山法学论坛参会人数最多、规格最高、议题最多、提交论文最多的一次盛会。论坛开幕式上,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介绍了武汉大学法学院对口支援新疆大学法学院的情况和取得的成就。从2005年武汉大学对口支援新疆大学法学院以来,已经为新疆大学法学院培养了16名博士,占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三分之二。在武汉大学交流的师生达到20人次,派出援疆干部4人。经过十多年的持续支援,新疆大学法学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7年在教育部法学评估中获得C+,进入全国法学学科前50名。2008年获批西北地区唯一一个法学一级博士点。冯果教授对新疆大学法学院取得的骄人成绩表示祝贺,并表示武汉大学法学院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大学法学学科的发展,通过设立科研平台加强双方的合作交流。并对武汉大学法学院第九批援疆干部邓社民副教授出色的工作表示感谢。为了加强双方的紧密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贡献法治新智慧,武汉大学法学院与新疆大学法学院联合设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法律研究中心”。此外,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疆大学设立“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新疆分院”,并为两个科研平台举行了揭牌仪式。新疆大学党委副书记罗旭,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事办主任李保全、新疆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李军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法律研究中心”揭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孙晋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网信办杨翔科长和新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青松为“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新疆分院”揭牌。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展现了武汉大学法学院落实中央援疆工作的积极态度和取得的实效,进一步加强了武汉大学法学院与新疆大学法学院的合作交流和对口支援工作。编辑:赵欣、主编:秦前松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