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山号
横山号每日一校推荐: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在三环路两侧分设东、西两个校区,是教育部直属、首批“211工程”高校、“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北外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高等学校,前身是1941年成立于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建校始隶属于党中央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归外交部领导,195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1959年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80年后直属教育部领导,1994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获批开设101种外国语言,欧洲语种群和亚非语种群是目前我国覆盖面最大的非通用语建设基地,是教育部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学校形成了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文、法、经、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按照时间先后,学校开设语种包括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日语、阿拉伯语、柬埔寨语、老挝语、僧伽罗语、马来语、瑞典语、葡萄牙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斯瓦希里语、缅甸语、印尼语、意大利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豪萨语、越南语、泰语、土耳其语、朝鲜语、斯洛伐克语、芬兰语、乌克兰语、荷兰语、挪威语、冰岛语、丹麦语、希腊语、菲律宾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斯洛文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爱尔兰语、马耳他语、孟加拉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拉丁语、祖鲁语、吉尔吉斯语、普什图语、梵语、巴利语、阿姆哈拉语、尼泊尔语、索马里语、泰米尔语、土库曼语、加泰罗尼亚语、约鲁巴语、蒙古语、亚美尼亚语、马达加斯加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阿非利卡语、马其顿语、塔吉克语、茨瓦纳语、恩得贝莱语、科摩罗语、克里奥尔语、绍纳语、提格雷尼亚语、白俄罗斯语、毛利语、汤加语、萨摩亚语、库尔德语、比斯拉马语、达里语、德顿语、迪维希语、斐济语、库克群岛毛利语、隆迪语、卢森堡语、卢旺达语、纽埃语、皮金语、切瓦语、塞苏陀语、桑戈语、塔玛齐格特语、爪哇语、旁遮普语。学校秉承延安精神,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目前已开齐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用语。北外现有33个教学科研单位,近年来,学校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成立国际研究生院,陆续成立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等众多特色研究机构;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北外学院、国际组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在原亚非学院基础上,扩建为亚洲学院、非洲学院。学校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委科研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4个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中东欧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以及37个教育部备案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3个教育部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学校编辑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国际论坛》《国际汉学》四种CSSCI来源刊物,一种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出版《中国俄语教学》《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国际汉语教育》《英语学习》《欧亚人文研究》《德语人文研究》《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区域与全球发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等刊物。学校有全国最大的外语类书籍、音像和电子产品出版基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外开设本科专业121个,其中44个专业是全国唯一专业点。学校现有4个国家重点学科(含培育学科),7个北京市重点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11个(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教育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点8个(金融、国际商务、汉语国际教育、翻译、新闻与传播、法律、会计、工商管理硕士),涵盖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六大学科门类。在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学校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评级为A+,位居全国榜首。2018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发布,学校语言学、现代语言2门学科再次进入全球前100强,居国内同类院校之首。学校本科在校生5600人,研究生(硕士、博士)3100人,留学生1600人。北外注重创新人才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现有在职在编教职工1200余人,另有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教师近200人。学校拥有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家百万千万人才工程、国家“四个一批”人才、青年“长江学者”等高水平师资。教师中超过90%拥有海外学习经历。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师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北外坚持高端引领、整体推进的国际化办学思路,与世界上91个国家和地区的313所高校和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匈牙利罗兰大学、波兰雅盖隆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学校承办了23所海外孔子学院,位于亚、欧、美18个国家,居国内高校之首,包括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比利时布鲁塞尔孔子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意大利罗马大学孔子学院、波兰克拉科夫孔子学院、比利时列日孔子学院、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保加利亚索非亚孔子学院、捷克帕拉茨基大学孔子学院、德国慕尼黑孔子学院、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英国伦敦孔子学院、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术孔子学院、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孔子学院、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法国ESCP欧洲高等商学院商务孔子学院和美国夏威夷玛利诺学校孔子课堂。北外图书馆馆藏纸质中外文图书近145万余册,中外文电子图书222万余册,中外文报刊1123种,中外文数据库97个,形成了以语言、文学、文化为主要资料的馆藏特色。近年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政治、法律、外交、经济、新闻和管理等方面的文献逐渐形成藏书体系。学校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形成“开放、互联、智能、创新、融合”的信息化构架,开发以多语种网站、数字北外、数据中心软件平台等为代表的多项标志性成果。其中,多语种网站项目于2015年启动,支持50种外国语言。2018年获批教育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高校。在长期办学历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形成了“外、特、精、通”的办学理念和“兼容并蓄、博学笃行”的校训精神,成为培养外交、翻译、教育、经贸、新闻、法律、金融等涉外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一批批从北外走出的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国、全国各地,活跃于各行各业,建功立业、成就卓著,成为精英翘楚、社会栋梁。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校友中,先后出任驻外大使的就有400多人,出任参赞2000余人,学校因此赢得了“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美誉。来源: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
 董夫人
董夫人重新发现马丁·路德——为寻找一位“失踪者”而翻译和研究
2020年12月16日,上海大学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景学中心共同举办线上会议“寻找思想史中的失踪者马丁·路德”,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三十余位学者共同探讨。本文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芬兰华人学者黄保罗。黄保罗教授曾先后推出一系列研究路德的专题著作,向汉语学界介绍芬兰学派路德研究的最新成果,近年正在进行《马丁·路德著作集》的汉语翻译工程。本文是黄保罗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原题为《为“寻找思想史中的失踪者马丁· 路德”而翻译和研究》。马丁·路德在人工智能的挑战下,世界快速进入后现代的不可知性之际,人类日益提增能力地走向“全能”与永远难以接近“全善”的矛盾,将会把人类带入灭亡还是不朽?这是新时代的核心问题。展望未来之前,必须追溯过去特别是近五百年来的思想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曾经开辟了现代性的马丁·路德失踪了。特别是汉语学界,不仅治国学者没有关注他,就是治西学者,真正认识到并重视路德的学人,也是屈指可数。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因为忽略,导致了无知;因为无知,导致了在许多问题上的误解。也许同仁们会质疑:路德不是一直存在于思想史、神学史和哲学史的研究之中吗?但就汉语语境而言,路德在这些领域里的在场是微弱的,他所受到的待遇与其身份和重要性相比,是远不相配的。路德是中世纪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行为和思想,终结了中世纪,开启了现代性。首先,面对前现代的堕落教会中人扮演神的偶像崇拜,在领受天启的前提下,路德强调人的主体性,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作为有力的武器,解构了那个以神权压抑人性的时代。其次,路德并非简单地将人类带入现代性之中,而是对现代性的核心力量——人的理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预示了后现代的危险。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了人性,虽然可因此反对偶像,但又存在着人自己随时变成偶像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汉语学界,许多学理的问题都未能被研究透彻,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路德的重要性被汉语学术界严重忽略了。所谓忽略,就是在宗教和宗教学界之外,路德的著作、思想和影响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同时,路德又被仅仅狭隘地理解为一个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不知道他在社会、政治和整个思想史领域里的地位、价值和意义。路德的价值重大,简而言之,可从基督教会、德意志民族国家和现代性世界三个方面来探讨。第一、路德是基督宗教的改革家,他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权力体系和秩序,是新教的奠基人。但在汉语教会界和神学界,对于加尔文的重视和研究却远远超过路德,几乎人人都承认路德的重要性,但除去九十五条论纲、大小教义问答、论基督徒的自由等篇章之外,深入研究和真正了解路德思想者,即使是信徒学者也少之又少。第二、路德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奠基人和英雄,对于德意志人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德意志精神的塑造,具有重大意义,他翻译的德语版本《圣经》造就其“德语之父”的地位。对于大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诞生,路德的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第三、路德是现代性的真正开启者。一则路德解构了欧洲的权力结构,不同于文艺复兴的纸上谈兵,路德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带领了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独自发展,而走向现代国家。二则路德重塑了欧洲的社会秩序,在梵蒂冈与各国教会之间、在罗马帝国与德国的选帝侯、自由城市及各个国家之间,对于“教随国定”的欧洲政教秩序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三则路德将被堕落教会压抑下的人真正地扶了起来,让人摆脱一切的人间权柄而直接面对上帝(通过阅读上帝的话语《圣经》和借助圣灵而与上帝交通祷告),使人真正地获得了尊严,回复了人身上的“上帝形象”。四则路德在思想上界定了理性的双重性,认为信仰之内的理性乃上帝赐给人的最伟大礼物之一,而信仰之外的理性则是将人带向灭亡的魔鬼撒旦的最大娼妇;同时,路德揭示了真理的二律背反之悖论本性,上帝及其真理和美善都以隐藏的方式被启示在现象的对立面或其背后,没有真正的智慧,人无法理解这一切。五则路德与被称为“德国导师”的挚友梅兰希顿合作,开启了德国及欧洲义务教育的先河、奠定了现代教育的根基。虽如芬兰学派强调的那样,在《圣经》观和救赎论等核心思想上,路德没有创新而是回归奥古斯丁等以来的大公传统。但对于主体性的被唤醒、个人尊严的被重视、以及世俗化职业和生活价值的被肯定,路德常被视为开辟近现新时代的人物。而西学东渐以使“现代”及“现代性”等概念传入中国时,一方面与经济贸易、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德、英、法及苏联之间在现代性概念上的差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及其后兴起的科学理性及科学至上或理性至上主义之间的不同,没有被汉语学界充分区分。以至于启蒙运动后来发展成为极端自大的“人要成为神”的人文主义,导致西方现代性在祝福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在受到吹捧的进化论(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反思批评的时候,否定文明优劣差异的文化本质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语境中,以地方性、独特性、民族性等个体性为理由,来否定普遍性的存在,在表面的多元主义之下,将人带入了虚无主义的绝望之中。解决诸如此类的前现代和后现代的挑战方案,虽不能简单说路德在五百年前就已经论述过,但在当代学术界的讨论中,路德已做过的事情和说过的话语及其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却被汉语学界长期忽略和遗忘,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汉语学人没有充分阅读过路德作品,不了解他的思想,因此,在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中对其关注甚少。对路德浅尝辄止者,往往只见其皮毛而未得窥其全貌,这与路德著作的浩瀚及其庞杂也有密切关系。因为路德不是奥古斯丁、阿奎那或加尔文式的系统理论家,他的大部分论著都是面对实际生活的冲突和挑战而产生的应景应急之作,类似于鲁迅,其作品多是论战文字。因此,路德思想的精华遍撒于其数千万字的手稿之中,仿佛散落的珍珠,需要学者专家拿条线将这些珍珠串联起来,我们才能发现路德的真面目,才能见到他思想的深刻与贡献的伟大。就汉语思想史的研究而言,目前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重新发现路德,并从路德的理性悖论出发,不仅要反思康德的理性批判,而且要质疑康德在道德领域以“德福相配”为追求目标的人性乐观论。康德虽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透彻地分析了理性的有限性,但他所继承和发展的贝拉基主义,早就被奥古斯丁和路德以充分的理由所抛弃。二十世纪以来的汉语学界,即使是治西学者,也往往不了解路德的贡献,以至于既无法正确地分析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在西方后现代语境里的难题,又无力迎接狭隘民主主义学者在汉语学界的前现代式的挑战。所以,汉语学界的西学思想史的发展,需要打破“唯康德主义”,而寻找路德则是必不可少之路径。结合深受路德影响的北欧社会,得益于路德研究芬兰学派师友的激励,我们期望将路德的著作及其世界性和芬兰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到汉语学界。为此,我们组织了近三十位学者系统地翻译路德著作集,一则填补空白,二则借此来反思和修正汉语学界的许多既成观念。过去几十年来,汉语世界已经将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爆发时期的主要代表作翻译出来了。不过,它们其实只是路德著作的很少一部分,在55卷《路德著作集》中只占4卷。这样的选译原则在过去也无可厚非,毕竟汉语世界当时在人才储备和认知方面都受到了很大限制,难以全面铺展开来,选取一个方面突破可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样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马丁·路德只是宗教改革家,这样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就被人为地矮化和肢解。这种选译的狭隘性也是造成上面陈述的他的其他思想至今不能被承认和重视的根本原因之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路德的思想贡献,首先必须对路德的众多著作提供信实可靠的译本,供学者研读。同时,组织这一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的翻译工程不仅可以促进对于马丁·路德的思想研究,并且还可以有意识地培养一批研究马丁·路德思想的青年才俊,搭建马丁·路德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梯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马丁·路德的思想。(感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张云涛博士对于这个部分的补充。)路德著作大多数原用拉丁语写成,另外部分用路德时代的德语写成。最权威的威玛版路德著作集包括了拉丁语和德语一百多册,美国版英语路德著作集(Luther’s Works = LW)55册(及最近几年新增加几册)。本团队的翻译,主要以英语为底本 (多在五十年前出版),不仅包括了 LW,而且包括了其他英语版本,另外还包括了部分芬兰语版本。所以,本套路德著作集应该是威玛版之外数量最多的路德著作集,到2021年底预计完成书稿30册(一千多万汉字),计划由 Luther Academy for China RY 在芬兰正式出版网络电子版,然后,根据可能在汉语世界努力出版纸质版。为了完成这项彪炳史册的重要项目,将路德的大部分著作以汉语首发,我们计划在翻译团队之外,再成立辅助团队,以确保翻译和出版的顺利进行。(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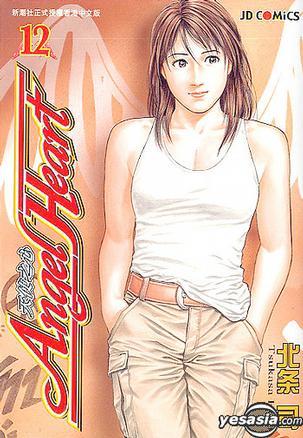 洗心
洗心兼容并蓄 博学笃行——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在三环路两侧分设东、西两个校区,是教育部直属、首批“211工程”高校、“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北外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高等学校,前身是1941年成立于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建校始隶属于党中央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归外交部领导,195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1959年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80年后直属教育部领导,1994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获批开设101种外国语言,欧洲语种群和亚非语种群是目前我国覆盖面最大的非通用语建设基地,是教育部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学校形成了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文、法、经、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按照时间先后,学校开设语种包括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日语、阿拉伯语、柬埔寨语、老挝语、僧伽罗语、马来语、瑞典语、葡萄牙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斯瓦希里语、缅甸语、印尼语、意大利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豪萨语、越南语、泰语、土耳其语、朝鲜语、斯洛伐克语、芬兰语、乌克兰语、荷兰语、挪威语、冰岛语、丹麦语、希腊语、菲律宾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斯洛文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爱尔兰语、马耳他语、孟加拉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拉丁语、祖鲁语、吉尔吉斯语、普什图语、梵语、巴利语、阿姆哈拉语、尼泊尔语、索马里语、泰米尔语、土库曼语、加泰罗尼亚语、约鲁巴语、蒙古语、亚美尼亚语、马达加斯加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阿非利卡语、马其顿语、塔吉克语、茨瓦纳语、恩得贝莱语、科摩罗语、克里奥尔语、绍纳语、提格雷尼亚语、白俄罗斯语、毛利语、汤加语、萨摩亚语、库尔德语、比斯拉马语、达里语、德顿语、迪维希语、斐济语、库克群岛毛利语、隆迪语、卢森堡语、卢旺达语、纽埃语、皮金语、切瓦语、塞苏陀语、桑戈语、塔玛齐格特语、爪哇语、旁遮普语。学校秉承延安精神,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目前已开齐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用语。北外现有33个教学科研单位,近年来,学校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成立国际研究生院,陆续成立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等众多特色研究机构;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北外学院、国际组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在原亚非学院基础上,扩建为亚洲学院、非洲学院。学校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委科研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4个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中东欧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以及37个教育部备案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3个教育部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学校编辑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国际论坛》《国际汉学》四种CSSCI来源刊物,一种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出版《中国俄语教学》《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国际汉语教育》《英语学习》《欧亚人文研究》《德语人文研究》《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区域与全球发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等刊物。学校有全国最大的外语类书籍、音像和电子产品出版基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长期办学历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形成了“外、特、精、通”的办学理念和“兼容并蓄、博学笃行”的校训精神,成为培养外交、翻译、教育、经贸、新闻、法律、金融等涉外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一批批从北外走出的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国、全国各地,活跃于各行各业,建功立业、成就卓著,成为精英翘楚、社会栋梁。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校友中,先后出任驻外大使的就有400多人,出任参赞2000余人,学校因此赢得了“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美誉。当前,北外秉承传统,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促进学校平稳较快发展,致力于培养国家亟需,富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复合型、复语型、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建设步伐。(来源北京外国语大学)
 双瞳
双瞳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比较文学拓荒者乐黛云自传回首九十年沧桑
乐黛云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是北大最有故事的人之一。她在其新书《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写道:“生活的道路有千万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是选择。”日前,她的这部最新自传和心灵独白,吸引了国内知名学者齐聚,他们通过线上分享会的方式,谈谈这部新书,谈谈他们眼中的老师。50岁开拓国内比较文学乐黛云在书中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以及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遭遇一系列的坎坷曲折——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教学岗位。五十岁的乐黛云,在一般人以为“人到中年万事休”的时候,毅然决然选择了重新开始。此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因为她,北京大学有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有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各高校有了一个又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点;中国学者开始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担任要职;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也成为整个人文研究中一条异常活跃的“鲶鱼”。九十年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如初。乐黛云将自己一生的人生经历,包括她的家庭,她的爱情,她与时代的沉浮,她跟命运的较量,她对学问的追求,她对一颗颗自由灵魂的怀念,都在书中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乐黛云说:“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命”与生俱来,“运”则充满偶然,“知”意味着对知识和智慧的探求,而“行”则意味着现实人生中的取舍与选择。机缘曾经使她可能成为一名外交官,但她选择了留在学校。人生的关键是选择,读这本书,可以看到乐黛云在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勇气。她坚信:“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学术成就滋养几代学人“我很庆幸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文学研究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我从小就立志从事文学工作,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乐黛云说。在分享环节,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风趣地说:“据说,乐老师的学生包括了好几代人。如果这样划分的话,那么,我应该算是第一代的老学生了。乐老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思想的自由、开放和活跃,和我们读书时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是相当融合的。”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当初的比较文学,或许我们只是从乐老师那里学到一点二手的概念、索引、方法,但是确实影响到我们的研究。”据陈平原回忆,他写过一篇名为《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的文章,当初人们觉得眼光一亮,文章受到好评,“但是大家不知道我一点德语都不懂。当初我们也敢做,因为有比较文学帮我们做了大量的译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金双则表示,乐黛云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重量级作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一版)的“比较文学”长词条就是乐黛云先生执笔撰写的,她的学术成就滋养了几代学人。傻话和谎话一定不讲“傻话和谎话一定不讲。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谎话一定挑出来告诉我,这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原则。”乐黛云说道。对此,陈平原坦言:“乐老师写回忆录特别担心自恋,过分自恋是很多人写回忆录的通病。乐老师比较冷静地面对自己的一生,甚至有时候会自我调侃。”现场,乐黛云的学生们不约而同谈到了过往。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分享道:“1956年我进校读中文系的时候,乐老师有四年的教龄。但是我读了五年书没听过乐老师的课,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因为她1957年成了右派,被遣送到门头沟劳动。”他回忆说,第一次见乐老师已到了1963年,她从门头沟回来,在中文系资料室当资料员。但他说,真正与乐老师接触是在五七干校期间,“乐老师是个劳动能手,干活真的是非常卖力气,力气也大,包括摔砖、盖草棚等等,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乐黛云与汤一介的伉俪情深更让大家印象深刻,洪子诚回忆道:“1988年,北戴河有一个夏令营,乐先生和汤先生也去了,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乐老师说她跟汤先生的结婚纪念日都要到西餐厅去用餐,那一次也不例外,她在北戴河的时候专门跑到秦皇岛去庆祝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当时我非常感动,我一辈子好像也没有这样一种深情厚义。”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艺绽 | 记者 路艳霞编辑 高倩流程编辑 刘伟利
 白恋
白恋反思西方科学思想经典文献研究
如果从清代宣统元年(1909)七月编著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算起,我国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文献编目研究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其间,标志性的成果还有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科技部分)、王太庆在1988年主持编译的《西方自然哲学原著选辑》等。在我国学界对西方科学思想接触的历史中,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的存阅多限于“西学书目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部分书目等并不系统的认知。本文通过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文献研究进行反思,在西方科学思想的范畴、语种、体例、载体和原典等方面,有些新的思考。在国内外新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西方科学思想经典文献的爬梳整理,或许对我国相关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有所补益。范畴体系有待重新审视范畴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儒学始于“正名”,西方学理始于“定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基本范畴看,由于文化和语境等多重原因,我国学界对西方科学思想研究应该澄清或识别某些似是而非、断不可望文生义的基本概念。“知识”(epistēmē)在古希腊学术中的喻义超过科学与哲学的综合,与拉丁文化中的“科学”(scientia)只有词源学意义。反倒是“历史”(historia)这个概念看似属于人文学科,但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可能最接近科学思想范畴:通过研判获得知识(knowledge from inquiry)。因而,将亚里士多德的“Historia Animālium”翻译成“动物志”,可能需要解释。“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未必是中文的博物学,而是更接近于当代的百科全书,而中世纪中晚期的“百科全书”(如Paul Skalich在1559编撰的“Encyclopaedia”)则更接近于现代的科学概论或通识教程。“物理学”(physica)并不是今天的物理学,而是与精神现象相对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牛顿时代的“自然哲学”可能是科学的别称,而黑格尔时代的“自然哲学”则可能招致科学家的厌恶。“自然神学”(physico-theology)似乎不可以理解为用自然现象论证神学命题,而应理解为神学中的科学论证方式或用科学方法论证神学信念。看似科学的“宇宙论”(cosmology/cosmography)其实主要是占星术(astrology)而非天文学(astronomy),如同“炼金术”(alchemy)不是化学(chemstry)一样。“七艺”(septem artium disciplinam)不仅是博雅教育体系,可能同时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学术训练系统。在西方科学思想经典文献选编过程中,如果将“最后的教父伊西道尔”(Isidore of seville)编撰的《词源学》(Etymologiae)排除在科学思想经典之外,可能会贻笑大方。但如果将开普勒的《宇宙揭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当成科学思想经典,还不如收录柏拉图的《第迈欧》(Timaeus)更有思想史价值。这些范畴的准确意义,往往很难在近代典籍中查到,而中世纪的辞书的记载可能更可靠。当然,上述范畴仅略举一二。我们对西方科学思想特别是经典文献的接受和解读,会牵涉许多基本范畴,应该具体分析。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甚至同一著述的不同章节,往往科学与非科学混杂,需要进行精深考察。毕竟,基本范畴是把握思想的规制或判据,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的整理尤其如此,有必要建立健全类似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表”系统。语言语种有待重新考究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也是学术的载体。语言(语种)不同往往也标志着学术风格甚或学术样式的不同。从语种维度看,西方科学思想的希腊文本看似是原本,其实拉丁经典更值得信赖。按传统观点,希腊的古典学术(Classical Scholarship)或古希腊学术(Doxographi Graeci)是西方科学思想的源头。但根据我们的收集整理,可能更进一步证实了王太庆等学者推断的亚里士多德著述“来路不明”。目前西方学界的所谓希腊典籍大多来自“翻译运动”(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Diogenis Laertii Vitae philosophorum)和10世纪的《苏达辞典》(Suida Lexicon),只是提及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医学方面的著述,不曾提及有关工具论或形而上学方面的重要著述。所谓的希腊经典大多是中世纪乃至20世纪初根据各种“残编”编译而成,所以我们见到的所谓希腊文典籍大多不是原作。而具有可信史料价值的科学文献,主要是古罗马晚期及教父时代开始的拉丁文献。根据我们的梳理,拉丁文作为欧洲的学术语言包括科学语言,从古罗马时期一直沿用到17—18世纪(还有说到20世纪初)。除了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思想是用拉丁文写作之外,近代科学的经典著作,如笛卡尔、牛顿、休谟、莱布尼兹等人的作品,都是用拉丁文写成。德国直到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才开始用德文写作,康德的讲师就职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tio)是用拉丁文写成,法国“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ste)之前的学术作品也都是用拉丁文。这意味着,拉丁文著述是西方科学思想的经典形式。对于我国相关研究而言,必须厘清科学思想的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的原典地位。同时还要爬梳意大利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和佛莱芒语等在科学思想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欧洲当时的科学家及科学思想家几乎都通晓多种语言,并用多种语言写作。比如,笛卡尔的《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是用法文写成,而《指导心灵的规则》(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则是用拉丁文写成,但却是用荷兰文发表。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科学院集聚了来自欧洲各国的顶级科学家,如贝努利(Daniel Bernoulli)等人。院刊《彼得堡科学评论》(Commentarii),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科学期刊之一,曾先后用拉丁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语言刊行。多语种及其交错演化,可能是西方科学思想及其经典文献的重要特征,但拉丁文应该是西方不可替代的古典学术语言。文献载体有待重新挖掘用何种文献形式来记载思想看似形式问题,其实文献载体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构件。从经典形式看,西方科学思想除了经典作家的个人著述外,还有“传记”“词源”“百科全书”,甚至还有“史诗”“剧本”“书信”等多种形式,而这些形式往往被我国学界所忽略。古罗马时期,出现了一批像第欧根尼·拉尔修、普鲁塔克等传记作家,记述了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伊壁鸠鲁等人的生平事迹。伊西道尔的《词源学》堪称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包括句法、辩术、修辞、数学诸科及造船、建筑等各种实用技术。拜占庭时期的《苏达辞书》用希腊字母汇集了3万多个词条,可以查到“原子”等重要概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后,出现了一批百科全书:如瑞奇(GregorReisch)在1503年编著的《玛格丽特百科全书》(Margarita Philosophica),记录了当时的科学活动及其各科知识。斯卡利奇(PaulSkalich)在1559年编撰的《世界百科知识全书》(Encyclopaedia seu orbis disciplinarum tam sacrarum quam prophanarum epistemon)最接近现代的百科全书,直到《法国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和《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dia Britannica)的刊行。这些“传记”“词源”和“百科全书”比较系统地记录了西方科学思想的基本范畴、主要知识和重要事件,因而是我们了解和研读西方科学思想不可逾越的经典形式。此外,科学(思想)家未刊发的手稿和个人书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史价值,其价值堪比甚或高于正式出版物。例如,人们往往以伽利略《致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的信》(Galileo's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作为他的科学观,其实,2018年发现的伽利略写给朋友的信更能代表他的科学观及其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看法。研究范式有待重新查验从思想范式看,传统研究往往把西方科学思想解读为“自然哲学”(如丹皮尔和格兰特)、“逻辑体系”(如怀特海和罗素)、“科学语言”甚或“物理语言”(如维也纳学派)甚至是不可通约的“句法范型”(如库恩)等。我们对西方科学思想经典的爬梳或可提供的理解是,西方科学思想的思想范畴,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是“七艺”(Artes liberales)的形成、发展、定型和演化的过程:由句法(grammatica)、辩证法(dialectica)和修辞(rhetorica)等构成的“三艺”(trivium)与几何(geometria)、算数(arithmetica)、天文(astronomia)和音乐(musica)构成的“四艺”(quadrivium)。“七艺”不仅是七门学科,而且学术准则和研究方法(论),规制了西方的学术特点、哲学论证方式、科学研究范式和高等级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西方学术文化万变不离其宗。中世纪的教父和经院学者试图用数理推证上帝,特别是“三位一体”(Trinitas)的存在从而导致数理科学在基督教中具有合法地位。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等人,试图用几何体系推演伦理、政治乃至所有哲学问题。直到20世纪,罗素还试图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努力,维也纳学派则发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berwinng der Metaphysik rch Logische Analyse der Sprache)。库恩认为,科学革命造成了“世界观转变”以及后现代主义者“认识论断裂”。但是,上述观点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在西方科学文化中,具体科学知识可能不断更替,但作为西方科学思想根基“七艺”或推证传统,一直延续着。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及科学思想家乃至哲学家,都同时具有逻辑、辩证法、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和具体科学等多方面的造诣。这是研读西方科学思想经典著述的最重要的见识,因而我们的学术应同时强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建设。从这个角度看,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学术原典有待重新定位从原典传承看,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论语》等儒家经典的传承,那么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思想文化可以说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Euclid's Elements)的流传。由于西方学术具有鲜明的逻辑性,因而西方科学思想具有高度的经典依赖性及其思想传承的逻辑性。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都是西方科学思想的原典或楷模。西方的科学家和科学思想家乃至哲学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欧式几何,或按欧式几何进行思考和创作。其中,包括笛卡尔的《谈谈方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霍布斯的《几何学的原理和推证》(De Principis & Ratiocinatione Geometrarum)、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康德的《通过几何学解决自然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Metaphysicae cum geometrica iunctae usus in philosophin naturali)、怀特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等。一部西方科学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欧式几何学的传承史,西方文化是一种偏执于数理推证的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的相关理念:天人合一、格物致知、观象制器、修齐治平。或许,这正是中国智慧的初衷与使命。(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经典文献编目与研究”(14ZDB019)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1日第1971期 作者:安维复精彩推荐:“立功绝域”:汉代西域使者及其英雄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四个维度让文化成为后疫情时代的重启键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三宝
三宝陆扬|浅议陈寅恪学术之研究方法——兼答饶佳荣先生
陈寅恪(1890.7.3-1969.10.7)对于中国史界而言,今年是深具意义的,因为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前不久本人的一篇以笔谈为基础的论文《视域之融合:陈寅恪唐史研究特点与贡献的再考察》发表于近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十七卷第四期,2020年7月),随后各网络公众号多有转载,在读者间似乎也颇有些反响。日前《上海书评》转来饶佳荣先生的一篇读后感,对拙作既有过誉的肯定也有批评。因为这是一篇严肃的评论,《书评》希望我能对此有所回应。我读过后,感佩于饶君的认真,因此想就饶君此文的一些看法提供一点我的回应,借此机缘对陈寅恪研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也稍做申论,目的并非出于为我本人观点作辩护,而是想促进学界乃至大众对作为史家的陈寅恪的理解。先容我说明三点情况:第一,因为拙作并非讨论一个非常具体的可完全通过实证来论说的主题,对此主题学人间有不同观点非但正常,而且必要。因此本人的回应也只以进一步阐明本人撰文之时的考量为主,有便于读者衡量不同观点间之异同得失。但这种讨论永远是开放性的,不可能定于一尊。第二,这篇文章乃去岁深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成果。之后《北大学报》和文研院希望我能组一组稿子,先发表部分有新意的文章。本人因忝为北大历史学系教员和文研院工作委员,组稿的责任便自然交给了本人。同行们也许都知道,我写稿容易拖延,往往一改再改,错过规定交稿时间几乎是日常行为,这次若非有严格时间限定,且因本人有组稿之职责,不能不提交文章,否则恐怕未必能刊出。也就是说,本人对自己的著述其实从未满意过。而这篇论文令我感到遗憾的另一原因是学报对字数的限定。学报规定只能在一万五千字以内,由于学报的宽容,使本人的这篇的字数得以略有超出,但也不能越限太多。其实其他三位作者也都面临同样问题而不得不作出大幅的删节。本人曾对学报编辑部同仁开玩笑式地威胁说要转而投稿给北大隔壁的另一家学报,因为后者几乎不限字数,容许尽情发挥。学术论文的质量固然不能以长度来衡量,但探讨陈寅恪的学术,不深入到具体的例证,便易流于印象式的浮泛。但因学报的限定,本人在不影响主要立论的基础上不得不对拙文作出删节。删去内容包括正文和脚注,往往涉及具体的例证。比如饶君文中提到的“视域之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一语,饶君提示最早提到应是王汎森先生的报告,其实这是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创造的著名语汇,而最早用到陈寅恪的例子是余英时先生1986年发表的论说(见余英时:《“明明直照吾家路”——一九八六年版自序》,收入《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8页),对此饶君可能失察。笔者原本有注解稍作说明,但因篇幅不得不删去。有些必要的注解,比如提及余师对陈寅恪某些论文时代意义的分析,也因特殊原因而不得不删。如上之故,原本三万字以上的文章被删到两万字以内。文中三个部分的讨论均受不同程度之影响,有些议题更是悉数删去,比如讨论陈寅恪的史学学问养成的可能途径。第三部分讨论中略去了对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更细致的分析,以及陈氏关于唐代党争的论说和相关论说的比较等等,这些大都未为以往陈寅恪研究所涉及。但对于学报的宽容,我仍要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好在三联即将出版本人一本以讨论陈寅恪学术为中心的小书,到时读者应该仍有机会看到这篇论文的“全貌”。第三,这其实不是佳荣君第一次就本人的陈寅恪学术的观点提出批评。前些年本人发表有关以陈寅恪对对子试题为中心的论文《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文史哲》2015年第三期)一文后,佳荣君也对其中某些观点提出过疑问,我记得他最主要的看法是不甚同意本人在该文中的一个观点,即认为陈寅恪所出的对对子题有对胡适暗中表示敬意的意味。佳荣君虽不在学术圈内从业,但对学术抱有极大之热诚,历史素养也佳,且长年通过媒体力量致力于将严肃之学术推广给社会,这些在文史学从业者间有口皆碑,不容我赞一词。佳荣君对本人的研究也多有留意,拙作《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出版之后,曾非常细致地就相关议题采访过本人。不夸张地说,本人和佳荣君应在广义的朋友圈内,只是本人性格疏懒内向,近年极少与学界同行或知识界同好私谊互动。在彼此间久疏音问的情况下,能获饶君细致之评论,我很感动,于是想就此机缘,对佳荣君的批评作出认真的回应,以表对友人的敬意。以上三点大略澄清一下拙文产生的一些客观情况,接下来我想先就陈寅恪学术讨论的基本方法作一两点申说。由于陈寅恪学术面相的宽广深入,以及他被当作某种文化偶像而具有的影响力,多年来探讨其学术人生的文字如汗牛充栋,几乎遍布陈氏的各个方面。说实在话,要在这些文字之外再别出新意并非容易,更何况本人一向的立场是避免如钱锺书所言,将他人的书放入自己书中,再将自己的书放到书架上。若无真正的心得,则宁缺毋滥。本人多年来一直有一个感觉,即当下对陈氏学术的研究,最为缺失的往往是其核心部分,即对他的学术研究的脉络化的了解。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尤其是与他学术领域相关的学者没有重视他的史学论点。学界对他具体的观点往往不乏有价值的评论,也不乏对他的学术作整体关照,缺乏的是能通过他在各类具体研究中呈现的脉络,将之整合,提升到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层面,告诉今天的读者,陈氏作为史家居于何种位置。陈氏涉及的学术领域众多,即便专业学者,往往也只能专注于其中一部分,由此容易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又以往对陈寅恪史学的分析,较难脱离仰视的角度,即便这种角度是隐形的,因此立论难免会假设陈氏的学术能力。对于诠释陈寅恪学术立场的整体性而言,学者也更多从强调其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或者从强调其“贯通”能力出发,这些角度无疑是重要的,但也容易形成对陈氏学术评价的单一面相。在这些研究中,陈氏本人的言论往往成为自证其学术性质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依据,造成一种封闭的怪圈。对他学术产品的评估,也流于描述性的表彰。尤其没能将陈氏的史学和同时期前后域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相比照,更少考虑到作为方法的西方史学理论是否能在解释陈寅恪学术中发挥作用。拙文之所以选取陈寅恪为何会转向以唐史为核心的中古史研究作为讨论主题,并非因为唐史是笔者在陈寅恪学术中唯一熟悉的领域,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没能得到充分讨论的大问题,与陈寅恪涉及的其他学术领域关系密切,攸关对陈寅恪的整体理解。同时因为在这一领域内,笔者采取和陈氏极为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更有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同其他人文课题,最重要的是能提供独立思考后的观点,而非将前人观点简单放大。但虽以唐史为重心,笔者从未忽略陈氏其他领域的贡献得失,及其与唐史研究之关系,这些领域基本都在笔者思考的背景之中。除此之外,正如好友沈卫荣兄所言,一千个人有一千个陈寅恪。对于陈氏的学术的认知,不同代际的学人应该会有不同的理解,这绝不影响对前辈学者的论说的吸收和尊重,但新的理解有助于激发这一课题的生命力。还有一点,就是研究陈寅恪,应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只从掌故之类的记录入手,试图从中发现陈氏的学术生涯的秘密。人世交往之点滴,同时代人对于陈寅恪的随意性评价(casual remarks),对于了解陈寅恪这样长期处于学术中心的人物而言,自不应忽略,现代史学也提倡生活史与学术史的交融。但掌故类事例,即西人所谓 anecdotal accounts,若不能将之放置于学术本身的脉络去考察就不会对了解重要学人之学术有真正的帮助,多半会流于说外行话。而且掌故的史料价值,若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学术语境和问题,讨论起来会容易无的放矢。我在此试举一两例来说明掌故与学术脉络结合的必要。金克木先生回忆过,他和陈寅恪曾在一次聚会中会面,当陈先生听说金先生曾在印度问学后,临离别前走到金先生身边,轻轻耳语问他是否读过梵文《妙法莲华经》,而陈先生是用梵文读出《妙法莲华经》的名称。事后金先生评论说,他是在印度受的梵学训练,而印度正统古典训练是不会去读这类佛典的(笔者案:犹如吾国的国学训练只重四部之学,极少旁及内典)。这一故事几乎没见学者在讨论陈寅恪时用过,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细节颇有意义,陈先生那一刻意发问或许有试探金先生学力的意思,但提出的问题本身仍是有些低级的,说明陈寅恪所受的以德国梵语语文学为基础的训练并不重视印度本土的学术训练脉络,那是一种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前期欧洲汉学式的训练方式。这一点在本人撰写的有关季羡林和金克木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会再详细说明。但如果你不将这类掌故例子和陈氏某些特定的学术系谱连接,就不会注意其可利用的价值。同样道理,只有对某些掌故背后的学人关系有了解,才能对陈寅恪论著中的一些被看作是客观的宣称(statement)有更细腻的了解。比如他发表在1942年的《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广为学界所流传。其中称说:“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污也。”以陈寅恪当时之学坛地位,这段话自然体现一种无可辩驳的客观性。但若细读杨树达回忆录,会发现在三十年代,杨树达眼中最大的学术竞争对手就是黄季刚。这一点多年前笔者读《积微翁回忆录》时,余英时先生便特别提示笔者留意,认为杨树达有与黄侃争胜的潜在意味。余先生的这一看法可谓卓识。而在当时,黄侃才是通常被认为训诂小学之第一人。陈氏撰写此文时,黄侃虽已故去,但陈氏的这一宣称,恐仍不无在此种背景下公开推崇杨树达之意。又比如陈寅恪在为杨树达的另一部著作《论语疏证》撰写的序文里,着重谈天竺中土儒释经诂传统之不同,这更是陈氏自身学术的表达,与杨树达该著关系可谓若即若离。当然杨树达也是笔者深为佩服的学者,但陈寅恪的这些序言在客观成分之外,更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意味,其弦外之意是值得思考的。其实陈氏给几位一流学者撰写的序文和审查报告都是他个人学术立场的宣言,而这些宣言本身既彰显陈氏学术的一贯立场,也有特殊书写语境下的特殊意涵,在讨论这些撰述时,我们不应忽略这两方面中任何一面,也就是说我们对待陈氏的文字必须和陈氏对待史料一样的审慎(critical)。最近一期《北大学报》陈寅恪纪念特辑中也有王汎森先生一篇大作,提到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特别强调“序”在明清文士关系中的重要性,并且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王汎森:《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陈氏的这种史学观察和他自身写序的实践同样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陈寅恪研究要避免的第二种倾向,是不能轻信耳食之言,这一点是近年来陈寅恪研究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坊间流行的一些有关陈寅恪学术的分析著作,有些出自资深学人,固然不无创获,但也常犯以耳食之言为基础展开讨论的毛病。不是真正去细读陈氏的专业学术论文,并了解其学术论点和论证的来龙去脉。陈寅恪身前为当时一流之学者所环绕,即便是仰慕他的后辈,亦不乏学术上卓越人物,因此他们对于陈寅恪会有各类评价。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同样必须以史学态度对待之,不管这些言论出自俞大维傅斯年胡适钱穆还是出自钱锺书季羡林周一良。这绝非因为这些学人的评论已经过时或没价值,而是他们的评论同样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学术训练背景和特定时候的学术立场作出的,有时恰恰因为和陈寅恪关系接近,反而容易只注意他的某一面相,而未必能保持一种 critical distance。有时甚至不同的著名学人,对陈寅恪学术特征采用同一种评语,其内涵也可能大不一样,比如认为陈寅恪学术以“考证”著称。所以这些评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其价值究竟如何,仍需经史学之拷问,拷问的最佳方式仍是深入了解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本身,才能洞悉他们的评论在哪一个层次上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不说明什么问题。比如笔者在讨论陈寅恪对对子之文中特别指出俞大维回忆中提到的陈寅恪的文学旨趣纵然有参考价值,却并不全面,不能依赖以解释陈氏的文学观。同样的,傅斯年激赏陈寅恪的论文《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认为是利用语文学来研究历史的学术典范,但以笔者的浅见,这篇文章固然有贡献,却并非一篇需要极高学术造诣的研究,心得主要还是来自对德国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利用和对汉文史料的熟悉。这一点只有与同时期类似研究相较,才能清晰看出。陈氏的创获主要还是有较好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中文史料的充分和巧妙利用,能找到线索和联系。笔者自从事学术工作起,周边师友几乎都是对陈寅恪学术有精深了解之辈,对于他们的相关分析,笔者在尽量采纳之余,采取的也是同一立场,这里毋庸再加说明。要避免的第三种倾向,是不加考索地将陈寅恪所欣赏的学人的学术旨趣和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旨趣或目标划上等号。陈寅恪欣赏的学人,至少从其比较公开的言论来看,往往近于考据或实证类型,比如陈垣、杨树达等人。而极少有对胡适等新派学人作公开的褒扬。所以我们很容易将陈垣、杨树达的学问旨趣或特征当作陈寅恪自身的学术特点。实际情况可能远非如此。陈氏固然有重视实证和考据的一面,但他自己最有创获的论著(为数绝对不少)则往往不是在传统意义的实证层面上作出的,有时是以实证面目出现,但实际却包含大量非实证所得的史学预设或者历史想象力。或许王国维和陈寅恪之间存在着别人和他之间少有的学术共相。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明以上几点,一个原因是笔者发现饶君对笔者的批评中,不同程度存有以上种种取向。饶君的判断,常常是通过非常间接的论述作出的,很少直接深入陈氏的史学文本。比如佳荣君曾对本人就陈寅恪对对子之文史学取向的分析提出异议。如果本人记忆不误的话,那么佳荣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不同意本人认为的陈寅恪所出对对子考题中,对应于“孙悟空”的“胡适之”是出于对胡适的一种敬意的调侃,认为陈氏和胡适的学术立场观点有很大差异,如何可能是出于敬意的调侃。笔者的那一篇文章的主旨之一是重新探讨在何种意义上“孙行者”与“胡适之”的对子能体现陈寅恪所提倡的“正反合”的语言思辨能力。要谈这一问题,自然便涉及陈寅恪与胡适的学术关联。当然胡适和陈寅恪学术旨趣甚至立场均有所不同,这本是学界的老生常谈,有时今日之学界中人甚至会以陈氏学问的深度来反衬胡适学问的浅近。老生常谈固未必谬误,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对理解陈氏的学术脉络会产生误导,对当时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两位学者之间关系的解读也会过于表面。笔者文中着重引证的是来自陈氏在那一段时期学术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古佛教史的著述,发现与胡适的研究有密切关联,不但呈现平行状态,且明显受到胡适研究的刺激。陈寅恪是一位不甘于二流的学者,他对于胡适的态度,并不能只依据他在不同场合的某些言论或对某些立场来作机械推衍,而要深入他的研究轨迹,才能得出更为可靠的判断。同样的例子还有陈寅恪和顾颉刚的关系。陈弱水曾指出,陈寅恪对民国学术界最反感的“既不是旧派学问,也不是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而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史学”。这一判断本身是中肯的,相关论证可见其《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收入《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2000年)。但我们同样注意到陈氏在1931年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起首便提出层累造成古史的观点,所谓蒙古民族之起源,“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面较新者也”。任何对当时学术潮流有所了解的人,不会不意识到层累说是顾颉刚疑古派的标志性学说,但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在文中却用的是东洋史家之论说。表面看就蒙古源流的具体论证而言,白鸟库吉等东洋史家的确有类似的史观,但陈氏这样明显之提示,难以排除有间接对顾颉刚的这一立场表示认同之可能。如果我们细读《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会发现自二十年代末起,同在北平的顾颉刚和陈寅恪个人关系日渐密切,两人参加共同聚会的次数也颇频繁。事实上尽管两人学术取向有所不同,1943年陈寅恪甚至还作诗公开讽刺过顾颉刚献九鼎(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仍是友好的。1944年12月15日,顾颉刚在其日记中突然记了一行:“寅恪两眼皆不见物。”(见《顾颉刚日记》第五卷)可见此事给顾颉刚带来的震动。一流学人间的关系往往有很多层面,从学术上的佩服到隐性竞争乃至相轻或遥相呼应、暗中支持,都可能同时存在。以上是对佳荣君就《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一文批评之简单回应,接下来笔者想就佳荣君此次评论作些解释。这里先将佳荣君批评的主旨略加概括。拙作有三个部分,佳荣君对其中第三部分,即对陈寅恪的唐史研究贡献的再评估,多有谬赞,集中批评的是文章的第二部分,即陈寅恪在其学术生涯的成熟期,是否出现过一个“唐史转向”。假如本人的理解不错的话,佳荣君的批评意见的重点大致是这样的:拙作过于突出唐史研究在陈寅恪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而有意忽略他对于六朝史的贡献。本人强调清华学术体制变化对于陈寅恪的影响也值得存疑。佳荣君不认为陈寅恪在内心有以唐史研究作为安身立命的想法,换句话说,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固然成就卓著,其实是其整体学术中“自然”导出的结果,而非刻意追求的结果。佳荣君也对本人提出的唐代与清代,尤其是晚唐与晚清之间在陈寅恪心目中的联系以及对陈寅恪倾向于唐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了保留。以上看法中,有些其实属于佳荣君对拙作略有误读所致,有些则显示彼此对学术评价的方法稍有不同。具体而言,比如陈寅恪的六朝史与唐史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不应过于钻牛角尖的问题。拙作已明确说:当然学术环境变化的因素只能解释为何陈寅恪必须致力于历史研究,却不足以充分说明他为何选择中古史尤其是唐史,作为学术上安身立命之领域。这里固然突出唐史,但仍是以中古史作为整体范围而言。在拙文中,“中古史”与“唐史”交互出现。论及陈氏史学特色时,所举例子也是六朝与隋唐均有。在拙文更为完整的版本中,涉及陈氏南北朝研究的例子会更多。也就是说在学术方法的层面,陈氏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是贯通一致的,但方法上的贯通一致与学术构架的建立仍有重要区别。陈氏六朝史的创发以宗教与思想层面为最重要,创发也最多,这一方面原因是这些方面的探讨和以中亚语文为基础的梵学佛教学的关系更为贴近。当然陈寅恪对于六朝史,尤其是南北朝族群流动和文化政治变化,也有许多灼见,特别是能用语言习惯和宗教习俗来推断南北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政治纽带,这类方法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等论文中使用得尤其得心应手。但应看到的是,他的南北朝研究在不少方面仍是以对隋唐有整体了解为导向,而且他的唐史研究是从政治制度和文化各个方面展开研究和论述,涵盖的面相远比他涉及的六朝史课题来得宽广和深入,不仅数量多,原创性也更强些。当然两者中有不少重叠的部分。拙文指出:须注意的是,陈寅恪的唐史研究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能分割,着力于这两个领域使他具有超越同时代很多中外学者的长时段的眼光。这体现在他对隋唐国家体制形成的看法上,也使他在观察唐代前期的体制形成脉络时能避免了某些后见之明。这段话要说明的一个重点,即陈寅恪南北朝史的研究对他的唐史研究中特有视角和论说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其落脚点最终仍在唐代而非南北朝。这是就学术构架和质量而言。笔者曾特别提醒读者,陈寅恪的两“论稿”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属于从南北朝看隋唐,用王汎森的话讲,更注重一种“历史的逻辑”,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呈现的从宋代回望唐代的“史家之逻辑”有所不同。这其实都是在表彰其六朝史研究的重要。佳荣君似乎并未理解笔者以上这些考量,才会有本人故意忽略陈氏南北朝史方面贡献的误解。其实笔者在评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特别标举陈寅恪对北齐的独到分析,这不正是强调他在南北朝研究方面的成就吗?只是这种分析仍是落实在解释隋唐制度之来源,并未用作讨论北齐的文化对其自身政权兴衰等的作用。因此笔者强调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更多以隋唐为重心,是丝毫不夸张的。陈氏对南北朝的历史过程也是有通盘认识的,否则不可能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样的著作,但南北朝头绪众多,有通盘认识是一回事,能否建立像两“论稿”这样更完整和有原创性的构架则是另一回事。其实陈氏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研究在中国学界影响也很显著,有导夫先路之功,但有些方面很快被“后起之健者”渐次赶上甚至超越。比如前面提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发表于194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第一分),周一良先生有一篇题为“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的长文,发表于193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在处理的历史问题上与陈文非常类似。《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虽发表在先数年,受到陈氏诸如《东晋南朝之吴语》等论文的影响,《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也自有其创获,但相比两文,周文却在广度和细腻处有超越陈文之处。发表在1938年同一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周一良另一篇论文《论宇文周之种族》,对北周政治族群的分析也有陈氏未及之处。周一良当时只是初出茅庐之青年学人,尚未赴哈佛学习域外语文,但在南北朝史的某些重要领域内已隐然足以与陈氏相抗。但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唐史领域,则尚未有相类似的情况出现。当我们在慨叹陈寅恪与时间赛跑时,同样不可忽略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陈寅恪其实也不得不和后起之秀赛跑。虽然从历史回望,后起之秀如周一良后来也同样面临与时间赛跑的困局,不过那是另一种境况了。拙文着重于谈陈氏为何选择唐史作为重点,有哪些此前不为学人所关注的内外因对理解这一转向有帮助,而非讨论陈氏在南北朝史研究方面是否也有卓越贡献。佳荣君在此问题上纠结,恐怕更多是源自对本人提供的陈寅恪重视唐史的思想心态层面,以及学术体制对他学术规模形成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说的质疑,并由此反推,于是产生笔者忽略陈寅恪南北朝研究之判断,又将之作为自身论证的依据。在批评拙文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贡献概括上有所偏颇时,佳荣君采用了一个比较常见的立论方法,即认为不能忽视历史上“可能之有”,也就是假若陈氏不因时代离乱而使所作笔记大量丢失的话,则必然有大得多的学术产量。关于这一论点,笔者原则上有同感,实际在拙文中也已点到过。但具体到哪一个领域,则笔者认为需要做细致的分析,不能泛泛而谈。其实拙文所谓陈氏以唐史为“安身立命”之领域,本旨是这一领域在陈氏看来最能体现他对史学的追求,而不是说只有唐史才是他想要致力研究的领域。他从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推崇《通典》、司马光的《考异》和欧阳修的《新唐书》,任何对中国史学稍有熟悉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三者精彩处均在唐代。也许笔者在论述中未能完全把这一层意思说清楚,以至于造成佳荣君之误解。但笔者仍要指出,当佳荣君在强调不能忽略历史上“可能之有”时,主要的依据仍是耳食之言。佳荣君说:具体些说,陈寅恪在抗战期间遗失了两大箱特别珍贵的札记和资料,尤其是蒙古史、佛教史方面的“半成品”,包括他想日后成书的《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和《蒙古源流》考证。这些待完成著作的流产,对陈寅恪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甚至“有一个时期几乎得精神病”(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9页)。这里佳荣君是在未经仔细调查的情况下就采纳了汪先生的论断。引文中列出的《史家陈寅恪传》的大陆版出版年份固然是2005年,海外版的出版却远在此之前,当时有关陈先生笔记的存留情况的信息并不完整,比如《高僧传》批注不仅基本保留了下来,还有《高僧传笺证稿本》存世,可供我们推测后者假若完成后可能是个什么情况。看来佳荣君没有细读这些文本,没有去梳理这些笔记或笺证中哪些是陈氏本人真正的心得,哪些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那些心得和陈氏诸种学术论文之间关联何在,它们在陈氏已发表的论著中居于何种位置。这些问题过于复杂,这里自然无法展开,但笔者仍想作个提示,现存大多以批注形式出现的陈寅恪读书札记固然只是其全部读书札记的一部分,但其中精华部分其实大都进入了他已发表的著作之中,或者已经在其论述脉络之中,这种对应颇为惊人,恐怕不是巧合。很多相关论文也发表在某些批注尚未丢失之前,从逻辑上很难说陈氏的那些札记如不丢失,其学术样貌会有很大不同。东方语文方面的问题下面另说,像《世说新语》这类眉批的散失固然有可能对陈氏涉及该方面的细节论说有所影响,但也不会很显著。原因颇简单,假如陈寅恪能在目盲情况下写出《柳如是别传》这样需要依靠大量记忆和细琐论证的著作,那绝无理由因眉批丢失而对《世说新语》这样根本不算冷僻的著作不能有所撰述。1945年作为单行本出版的陈寅恪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就是一个例子,其中包含了陈寅恪阅读《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的诸多心得,和发表于1937年的《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后者也是围绕《世说新语》材料展开的讨论。由于三十年代陈寅恪中古史研究中思想文化占据重要位置,《世说新语》的确是他经常利用的材料,但他在该方面的撰作始终是讨论大问题的论文,因为那才是他主要的学术表达方式。与此类似的是,现存陈寅恪对《高僧传》所作的眉批的精华部分也大都反映在他已发表的论文之中。现存札记中最详细者是关于《鸠摩罗什传》的札记。笔者在多年前发表过有关该传的论文(中译可见《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中国学术》第二十三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已吸纳陈氏某些洞见。但以笔者的阅读经验,不得不说该部分札记主要仍属印度佛教学一般性知识,而非陈氏自己的发明。在一般人心目中,这些知识也许很有价值,但难以想象它们能满足陈寅恪这一层级学人的学术雄心,再说那类知识早已体现在德国学者诺贝尔(Johannes Nobel)对《鸠摩罗什传》的德语译注之中。现存《高僧传笺证稿本》中记录的心得固然也有价值,性质仍属零散,作为研究学术问题的准备工作可以,构成专门著述的条件则还真谈不上。假若这些现存笔记是我们的向导的话,那么笔者有把握认为,陈氏其他笔记或眉批也不会在性质上有多大不同。认为陈氏有意愿或者可能最终发表学术上颠覆性的《世说新语笺证》或《高僧传笺证》,以笔者之见属于从仰望陈寅恪角度作出的猜测,既与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不符,也与陈寅恪的学术创造模式不甚吻合。这倒不是要质疑陈氏本人的学术能力和信念(conviction),而是如何辨别陈氏的学术重心所在和哪种学术形式更适于他的问题。笺证这种形式并非能展现其所长的学术表现形式,按他一生撰述体现出来的特点和学术旨趣,也只能推断他无意作笺注式的学问。只要读一下现存笔记,就会发现陈氏读那些典籍主要在乎的是与他所关心的问题有关的点,而非面面俱到地为作一般意义上的札记。除此之外,坦率地说,在中古佛教学领域,陈寅恪固然有卓越之眼光与贡献,就展示的功力和投入精力而言,在三十年代后其实已渐渐不如汤用彤,而在印度佛教学方面,他更不如吕澂精深细致。我们固然可以说相关笔记的丢失在最终学术出产量上对陈有所影响(这也仅是一种假设),而不能说对他学术贡献的质量甚至学术重心在哪会有明显影响,更没有理由说那些是他原本特别想要着力的课题。同样地,佳荣君在其文中特别引述近期发表的孔令伟君的论文《陈寅恪与东方语文学——兼论内亚史及语文学的未来展望》(《新史学》三十一卷一期),特别是其中有关1938年陈氏《蒙古源流》等笔记遗失而导致转向的看法。孔文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在越南遗失书籍一事,严重地影响了陈寅恪学术生命的发展。陈寅恪早年对《蒙古源流》与梵、巴利、藏、汉文多语佛教文献用功最深,然而当1938年其手稿尽失,因此不得不放弃早年关注的语文学。(83页)……与其辛勤注释的《蒙古源流》相比,《旧唐书》和《通典》不过是“略有批注”。由此或可见陈寅恪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对于《蒙古源流》及梵藏佛典的关注,远较唐史官书为多;而陈寅恪“略有批注”的《旧唐书》和《通典》由于没有被放置在最为要紧的两个书箱内,因此得以幸存。由此可见,1938年后陈寅恪遗失重要手稿后,治学重心由内亚语文研究与佛教文献学彻底转入唐史研究,可能主要与1930年代中国的图书收藏条件有关……(83-84页)对于以上两段引文中令伟君的论点,笔者均不赞同,因为无论从陈氏学术出版的明显倾向,还是他在域外之学方面显示的功力而言,都远不足以支持此观点。虽然孔文不无保留地说1938年后陈寅恪才将治学重心“彻底转入”唐史,这样的断语仍属常识性错误。孔文似乎把陈寅恪唐史乃至中古史的研究看作一种可以余力为之的工作,这本身也是史学上的谬见。上文已反复说明,陈寅恪最晚从1930年代起,无论研究还是撰述都以中古史为核心,不仅如此,只要有唐史基本训练并愿意认真阅读陈寅恪三十年代以后的唐史撰作,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研究是十分有序的,各方面的分析最终融入两“论稿”的体系之中。若没有这种有步骤的学术工作,陈寅恪是没可能在1939、1940年的境况里写出两“论稿”的。诚然,陈寅恪有些唐史的重要论文一直到五十年代才发表,那是因为五十年代前半叶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相对安定的阶段。比如发表于岭南岁月的著名论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其基本论点、方法均见于三四十年代论著和讲义中,也就是重视东晋政权下地方豪族与北方门阀之关系,这是陈寅恪研究南北朝社会的主要视角之一。又比如《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更是用具体讨论填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已经提示的观点。笔者相信这些论文其实多半是旧稿的完成,而非新起炉灶。陈寅恪对于蒙古史的确有相当大的兴趣,也在德国受到过相应的训练。发表于1929年的《元代汉人译名考》体现出他这方面的训练,这也许是陈垣看重他的学术的一大因缘。但陈寅恪有关《蒙古源流》的四篇研究都在1932年前发表,其中唯在《彰所知论》的研究上独具只眼,认识到其将蒙古王统之源流与吐蕃王统挂钩,对后来蒙古历史传统建构之影响。其他几篇,包括傅斯年赞赏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均为史地人名的考订,这些当然有贡献,但毕竟属于局部性的发现。他的研究工作真正受到时局影响是在1938年以后,1932至1938间数年,可谓他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时期,研究条件也相对良好,但他却再也没有相关著述发表。孔文以批注数量多少来衡量陈氏学术重心何在,在方法上是难以成立的。谁都没有见过陈寅恪《蒙古源流》批注究竟处于何种学术层次。至于孔文同时将陈寅恪梵藏佛经相关的札记与手稿的丢失,亦作为陈氏不能再在此方面有所进展的重要客观原因,笔者更不能认同。因为孔文专注于陈氏的域外,尤其是内亚史文之学方面的涉略情况,而不是对其本人的学术转型作通盘之考察,也就是说,拙文提到的各种情况,特别是陈氏中古史研究的种种学术理路和清华等学术体制的变化,未进入孔文之视野。同样熟悉史语所相关档案的陈弱水的文章明确提到:陈寅恪的研究生涯经历过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次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他放弃中外交通、内亚史地之学,改而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另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撰写《论再生缘》后,逐步停止有关中古史的著述,全力探考柳如是、钱谦益的姻缘以及明季清初史事,终于勒成巨著《柳如是别传》。(《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这个说明和笔者的看法基本一致,陈氏从1929年起,无论教学还是课题取向、发表的论文的主题均明显以中古史为核心。虽然到1932 年,陈寅恪发表的论文中与域外语文之学相关的主题仍占重要篇幅,但那显然应该看作是此前积累所致。即便在那些论文里,真正涉及对梵典的利用和发明的也不多,主要仍然是在中亚语文佛教学的视野下对中土经典的开掘。事实上在专业领域内,一位学者是否具有前沿工作的能力,其能力范围如何,是不难判断的,往往两三篇代表性论文已然足够。我们需要将陈氏的学术兴趣和他致力的学术工作作必要的区分。孔文的优点是通过史语所档案和书信等记录,将陈寅恪在内亚史和东方语文学等方面的学术活动和关怀作更为丰富的呈现,但笔者不得不说,该文虽然条理颇清晰,让读者一目了然,所提供之关键信息实际未有超出学界已知范围者。而孔文的一个缺失是并未对陈氏在蒙藏研究方面的工作本身作具体分析,或者与同时期西方日本学者的类似工作相比照,由此来评估这方面研究在学术体系中可能具有的位置,犹如笔者在陈氏唐史研究方面所作的工作那样。假如能细致做一下比较的话,那么笔者相信其答案恐将不同。佳荣君认为孔文利用了“中研院”史语所的档案,立论有据,于是对陈寅恪学术转向的“内在理路”有所怀疑。笔者则认为,三十年代陈寅恪之所以积极参与此与“四夷之学”相关的一些学术工作,除了其自身的学术训练和兴趣外,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对于以历史语言为基础的学术怀有热枕,而陈寅恪正是他在这方面最为信赖和倚重之人。孔文提供的陈氏通过史语所购书的记录等,也同样只能说明陈氏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对域外之学的兴趣仍在,甚至仍想有所作为,但却不足以证明其相关学术工作能否再深入进行。这些档案信息并不是通向了解陈氏学问质量的捷径。仅凭这些材料,若不作更具体的学术考究,仍是“对塔说相轮”,得到的看法是空泛而表面的(superficial)。比如孔文中提到的陈氏对《唐蕃会盟碑》的研究,陈氏在探究《蒙古源流》时对吐蕃王名的比定有所贡献,但整体而言却无法与寺本婉雅、戴密微、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等人的工作相比。假若读一下李方桂对《会盟碑》藏文碑文的研究(T’oung Pao, vol. XLIV, 1956),则可知陈寅恪有关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汉文史籍中之可黎可足)在位时间的意见已为李方桂所吸纳,但李方桂所倚重的与该碑文直接有关的研究里,出自中国学人的著作只有姚薇元发表于1934年的《唐蕃会盟碑跋》(《燕京学报》第十五期,1934年)。陈寅恪在蒙元学方面的工作性质也与此类似,属于零散的发现,与他在中古史方面的研究格局无法比拟。对于陈寅恪在蒙元史方面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将其放在中国该领域的发展脉络中评估。沈卫荣先生曾言,韩儒林等学成归国的年轻一辈无论在相关语言还是蒙元史训练方面都超越了陈寅恪。这是准确的观察。孔文在利用陈氏书信以佐证陈氏之“虏学”之时,其实也忽略了颇为明显而重要的证据。1936年10月11日,陈寅恪致信闻宥。闻宥当时致力于西南民族语言研究。信中说:大著拜读,敬佩之至。寅于西南民族语言无所通解,承询各节愧无以对,甚歉甚歉。丁君(指丁文江)只搜集材料,经先生加以考订,遂于此学增一阶级之进步,真可喜也。近日友人王君(指王静如)归自欧,渠本治西夏语文者,最近于契丹女真文亦有所论说。寅数年以来苦于精力之不及,“改行”已久,故不能详其所诣,然与之谈及亦欣羡不已。今又读大作,尤幸我国学术之日进而惭恨无力以追随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212页)这应该是陈寅恪在尚未遭遇巨大离乱之前,对“虏学”在自身学术中之情形的最为诚实的说明。揣诸上下文意,他信中提到的“改行”不会专指西夏之学,而是指整体性的域外语文之学。而他对中古史的投入是“精力之不及”的根本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真切表露他与这些领域新起之专家谈论时,仍“欣羡不已”。说明它们仍在他的学术兴趣版图之内,只是他已不能再坐拥之了。陈寅恪的确在给刘永济等人的书信里对他大量批注本的丢失感到痛心,但这些批注中并不只有《蒙古源流》,还包含《新五代史》等。笔者不否认陈寅恪即便在此时仍对早年致力过的“虏学”或“四夷之学”深怀感情,对其工作也倍感珍惜,但这和那一刻的他是否还认为这才是他毕生未竟之业,是有重要区别的。1944年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讲课介绍唐代史料,当提到回纥、突厥、吐蕃碑文时,说自己在这方面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参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可说是很贴切的自我评述。对批注丢失的痛惜,在心理上也完全可以是一种长期积累的遗憾的最终爆发,若允许笔者用较为文学性的语言来描述的话,那么这种遗憾可能更接近于和早已貌合神离但又恋恋不舍的情人之间的最终被迫诀别。相较于陈寅恪的蒙古研究,学界公认他在梵学上下的功夫更为深厚,但即便是那一方面,在陈寅恪前期生涯中,真正属于他的创获也并不多。因为这是笔者更熟悉的领域,近期已撰写了一篇小文,集中讨论陈寅恪梵学和佛教学方面的研究,会以比较充分的证据说明,陈寅恪在佛教语文学方面的研究能力是一个被放大了的神话故事,孔文中涉及的相关信件也会作进一步分析。众所周知,四十年代后期陈寅恪因为生活窘迫,将一大批图书卖给北大东方语文系,这批图书主要是东方学方面的。笔者在北大读本科时,曾利用特殊关系,多次到北大东语系图书馆阁楼上查看这批图书。占满一整个阁楼的图书内容包罗万象,Hendrik Kern、Sten Konow 和Georg Bühler等许多重要印度学家、佛教学家的著述均在其中,当然也包括钢和泰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这批图书迄今应该仍在北大。陈氏出售这批珍贵图书,固属不得已,但也可以反映他这方面学术关联之终结。其实在这一点上陈怀宇的论说远为贴切。怀宇君认为陈寅恪的东方学学养其实是一种以文献主义为导向,以中亚语文训练为基础,以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训练为辅助的学问(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第三、四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一概括更符合陈氏在这方面学问规模的性质。可惜无论孔文还是佳荣君,对陈怀宇的论说均未能注意和引证。其实无论是梵学还是满蒙之学,陈寅恪都属于广博无疑,精深则谈不上,他的渊博加上超等敏悟,使其能准确判断学术前沿何在以及学术质量高下,并且能发现和感召(inspire)有志于这些领域的青年才俊,几乎成为广大教化主。他本人也能在某些特定范围内作出贡献,但并不具备在东方学领域开疆拓土的能力,这一点即使他周边的人未能判断,他本人不可能没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他那些学术背景能为他提供学术参照体,在他真正能开拓的史学领域内启发他的思路。陈氏在世时,其实能对他的梵学能力作出专业层面判断的中国学人实为寥寥。据笔者所知,当时中国学者中唯一能从梵文角度对陈寅恪论说提出质疑的是俞敏。当然俞敏对陈寅恪《四声三问》的批驳本身未必一定成立,这一点平田昌司等学人为陈文作了颇为有力的辩护。但笔者想表达的是,陈氏身边虽多为一流学人,但在域外语文之学等方面大都不算内行,因此对陈寅恪这方面的造诣基本是仰望的,他们的评论难以被用作学术客观评估的标准。至于陈寅恪“唐史转向”的外在原因,佳荣君不赞同笔者提出的清华学术体制改革对陈氏学术规模的关键影响之说,而认为王国维之死亡与陈寅恪对当时学界两大势力不满,而想另立门户,是陈氏转向史学更为关键的原因。首先笔者必须指出,拙文的论说与佳荣君提到的两点并无矛盾,完全可以互补。但体制变革影响说的重点是陈氏史学研究框架及其规模是如何出现的,相较于佳荣君的理由,拙文提供的其实是一种更具客观性的描述。这一判断也是基于对陈氏学术的整体取向作出的。陈寅恪唐史研究的解释性取向和他在《蒙古源流》等方面所作研究的特色截然不同,前者与陈氏强调通识的旨趣更为吻合。当时清华以蒋廷黻为领导的史学教研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陈寅恪史学方向的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着完全可以对应的关系,这和国学院较为松散随意的学术风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种客观要求无论最初是否得到陈氏的支持,最终仍会在学术上让陈寅恪受益,或者使他在无形之中调整方向。正是清华的体制改革,使得陈寅恪的史学目标朝向更系统的方向发展,而在此过程中,他的隋唐史研究也就变得越发重要,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取得的成效最大。这是一种交互加强的过程。就笔者所知,以往学界从未强调过清华体制改革对陈寅恪学术的重要影响,一般都将他生涯中从国学院到现代分科院系看作一个自然的过渡,笔者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这里笔者想再举一例加以说明。蒋廷黻回忆他在清华的岁月时,提到清华历史系的情况,他说: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中略)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129-130页)这段回忆对于杨树达的评论颇为负面。蒋廷黻对杨树达本人的学术工作的描述是否精确另当别论,他提出的要求却正是陈寅恪从这一时期开始注重的工作,即探讨历史上重要政治、社会、经济变化,只是把汉代换成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而已。蒋廷黻提到的推荐杨树达来历史系教授汉史的学者里必然有陈寅恪。《积微翁回忆录》中屡屡提到这期间陈寅恪对杨树达的赞誉,包括称之为“汉圣”(该《回忆录》1932年4月8日)。“汉圣”几乎就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的简洁文雅说法。如果以此为背景,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向专注于训诂之学的杨树达突然会在1931年6月30日开始起草《汉俗考》(见《积微翁回忆录》),即1933年出版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恐怕正是在此种压力之下要显示自己也有能力从事“那样”类型的史学撰述。其实笔者关注到这一点,也是因为前些年受侯旭东兄之邀请,参加清华历史系的成立纪念会,才开始重视清华当年历史学科的西方体系化过程。学术体制对学人治学规模和旨趣的重大影响,这在现代学术史上司空见惯,从马克·布洛赫等年鉴学派人物与 Sorbonne和法兰西学院的关系对年鉴史学的影响,到今日“一带一路”号召下的种种学术产物,都可以作为参照。我们不应将陈寅恪想象为完全能够脱离学术环境的学人。笔者认为今日我们所了解之陈寅恪是清华人文科系形成之后的产物,而且同时任职于历史与中文两系,在陈寅恪后来不同类型学术课题的选择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佳荣君在其文章最后特别提到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基于陈氏在中文系任教期间的教研心得。笔者记得曾有清华老人回忆过,当时在研究生论文答辩时,陈寅恪特别提问学生有关《连昌宫词》的制作目的。学生答不上,不久陈先生便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拙文的完整版中,有关陈寅恪教学和他的唐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多探讨。王汎森在《陈寅恪的历史解释》里特别提到,陈寅恪在论证中常使用“隐形的条理”,他说:在陈寅恪文的文章中,经常出现“通习古今世变之君子” 或“通解礼法之君子”之类的话。言下之意是只要具此“通解”者,则不需要再摆出直接证据,即可共同相信某种不言可喻的证据。当然这种“通解”必须处在一个相同的背景文化之中,分享同样的文化符码才行。假如允许笔者在此也借陈先生这种方法一用的话,那么不妨说,通习现代学术体制对学者型塑作用者,自会对清华体制对陈氏的影响有特殊的敏感。佳荣君可能未像笔者那样,长期在学院体制中讨生活,对于教学能给研究带来的影响会比较隔膜。佳荣君屡次用余英时先生《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一文作为依据,认为笔者试图“在其师的基础上再作突破,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了破绽”。佳荣君似乎将笔者的论点看作是刻意但却不甚必要的努力,这也是未能理解笔者的用意。其实笔者向来深受余师此文影响,说是“再作突破”实属夸张,但笔者的确在一个重要的点上和余先生的看法略有差异。余先生认为陈寅恪学术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以中古史为核心的研究,是由前期犹如散钱的域外之学研究上升到有整体性规模的史学阶段,而陈氏学术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才是融合自身经验和历史解读的“心史”阶段。笔者则认为,其实这一“心史”阶段从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显现了,之所以不那么显眼,只是因为陈寅恪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政治与制度等整体变化,看起来更像纯客观之研究课题,实际在这纯客观史学主题的表象之下,涌动的仍是陈寅恪的史心。笔者在拙文第三部分特别讨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突出礼制的核心地位,正是强调这其实是陈氏在危难局面下的史学回应。有意思的是在该著出版不久,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王锺翰就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详细的书评。书评以对该书的摘要为主,但在文末,王锺翰高度赞扬《略论稿》的成就,并在书评结尾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形容陈氏这部著作(《燕京学报》第三十期,1946年6月)。该书评虽未将《略论稿》与现实境况相联系,但这一形容却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了该著的神采。而《柳如是别传》之所以“心史”的征象更明显,一大原因是和书写对象的特殊性有关,讨论的文学材料本身就有强烈个人色彩,因此这种论述较讨论制度更能凸显与研究对象心灵之交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选题本身也代表某种史学倾向,但笔者从唐史从业者角度,希望提醒读者,陈寅恪唐史研究中同样存在“心史”成分。在这种语境下,特别强调的晚清与晚唐之联系之意义,就至少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了。以上大略是笔者对佳荣君质疑部分的回应,最后还想就佳荣君的个别建议提供一点感想。佳荣君在谬赞拙文有关陈寅恪唐史研究评估之时,认为拙文“如果没有最后一节,可能很快就会淹没在成千上万的 paper 之海”。对于他人谬赞,笔者素不敢沾沾自喜。自学术史眼光,任何著述均难逃被淹没之运命。但这里笔者还是要说明一点,即拙文写作,虽表述或有不清,论据或有不足,全文三个部分之间却有内在关联,未可轻易取一而弃其余。佳荣君全未提及的第一部分看似有点玄虚,因为是从西方史学理论角度谈陈寅恪史学的方法,实则是笔者思考时间最多的。陈氏与西方学术理论之关系常为学者讨论之对象,但以往的取径,大多着眼于找寻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理论对陈氏史法的直接影响,这一路径在笔者看来取得成效有限,因为陈氏并不像钱锺书这一类型的学人,一般不会去直接借用某一西方史观来佐证自己的研究,即便他所运用的概念如“种族”“阶级”有明显西方学术背景,其运用方式也有他鲜明的个人色彩。借用陈寅恪自己喜用的佛教术语,他对西方史观的借用,更多恐怕是“熏习”的结果。也有学者强调陈寅恪史法中对“通则”的强调和对假设的运用,这自然是准确的,但强调陈氏史学中的假设,虽然能解释陈寅恪在具体历史研究中的推衍方式,仍不是对他的史学立场的分析。至于“以小见大”这种传统经验式的评论,更容易流于印象。因此笔者决定暂时抛开这些取径,直接将陈氏的工作放置于现代西方史学方法的关照之下,对之加以解释,或者将其与类型相似的现代西方史学大家相比。这并非机械“翻译”的过程,即将陈寅恪的史学研究简单地“翻译”成西方史学的概念,而是希望能通过一种新的框架,去解析出被以往解释框架遮蔽的陈寅恪史学特色,这一框架其实直接影响到笔者对陈寅恪唐史贡献的评估。无独有偶,同样在王汎森有关《柳如是别传》的分析文章里,他采取了同一路径,当然他的分析比笔者更为灵活丰富,非常推荐读者参看。但在试图做到对陈寅恪有“了解之同情”这点上,本人与王汎森先生则为一致。佳荣君文章的最后部分认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在陈氏的唐史研究中同样重要,且认为该著的影响更多存在于文学研究界。他为其未能引起史学界足够重视而表示遗憾,并认为拙文若能包括对此著的讨论,或许就“更周到透彻”。笔者非常感谢佳荣君这一提示,也完全同意《元白诗笺证稿》是一部卓越的著作。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著作其实从未离开过笔者的视野。佳荣君可能忘记了,在笔者关于陈寅恪对对子试题一文的最后部分,就专门谈到了这部著作的隐含意蕴,近期笔者发表了有关白居易生平研究的长文(《孤独的白居易:九世纪政治与文化转型中的诗人》,《北京大学学报》第五十六卷第六期,2019年11月),其实是用另一种学术的方式向陈寅恪的这一著作致敬和对话。对于此著的特点和内容,笔者是相当熟悉的,因为笔者从撰写博士论文的时代就离不开元白诗作和陈氏的解读。在三联将出的小书的序言里,笔者会进一步谈及这一问题。之所以未能包括在拙文中,倒不只是篇幅限制,而是因为此著并不像两“论稿”那样有整体结构,胜处与谬误更多呈现于具体论说之中。不过话说回来,也许笔者对相关材料比较熟悉,以今日唐史研究的深度而言,笔者感觉陈氏在元白诗作笺证的尝试存在不少问题,但非三言两语可以阐明,“以诗证史”的内涵也须反省,这些只能留待合适的机会再集中讨论。笔者在拙文末强调陈寅恪是不应该被简化的史家,在这一点上笔者相信应该与佳荣君是高度一致的。笔者实无意作陈寅恪之解人,撰写拙文关心的仍是自身研究中面临的陈寅恪史学遗产的问题,同时也希望能与陈氏史学之间多少有种视域之融合,知我罪我,the jury is still out。(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李觏
李觏美术研究|论自然科学与中西传统绘画体系关系
摘要:潘天寿早年提出,东西方绘画属不同体系,在当时西学东渐的情境下,主张中国画保持独立。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宋画和文艺复兴绘画进行比较,侧重空间处理方面,由此展开讨论,探索二者的差异性和兼容性,进而探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关于科学概念的讨论,涉及到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到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转化。文章提到劳伦斯秉雍(Laurence Binyon)的观点:如无科学的引进,西方前文艺复兴阶段的绘画与东方绘画将同其致。此说或有进步论、进化思想的基础,但这种类比是缺乏依据的。即使没有科学介入,因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东西方绘画也不可能走相同的道路,这点显而易见。中国画自有独立体系,有其东方哲学的宽容度和可持续性,这正是东方艺术在当今世界被看重的地方。潘天寿在1936年版《中国绘画史》中指出,与西方绘画相异,东方绘画有其特殊统系,主张当下的选择是,确保相对稳定,维持独立发展。[1]何为统系,它又以什么为依据呢?统系一词,旧指宗族传承脉络(genealogy),此处指系统、体系,指文化的血统关系。根据当时的情境,潘天寿所指的西方绘画应是文艺复兴时代发展起来的学院派绘画,其核心原理就是吸纳光影明暗和解剖结构的知识,在平面上建立表达单眼观看下逼近三维空间真实感的视觉法则,即透视法,使之达到精准化,甚至具有可测算性。这种画风通常被解释为写实,延续了数百年之久。按照达·芬奇的绘画理论,透视法除了线透视外,还包括色彩透视、隐没透视。[2]根据线透视的基本原理,文艺复兴绘画,在我国一度被称为线法画(linear painting)或透视画(perspective painting),即建立在线透视(linear perspective)基础上逼真三维空间视觉感受的绘画。其学科依据就是单眼观看的光学、几何学、解剖学(明暗、透视、结构),其核心概念或关键词就是“透视”,即在平面上确立三维空间的话语体系。因此,在学院教育中,透视学一直被视为基础训练。然而,透视体系有其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预设之上:其一是定点单眼观看,其二是依照点光源处理明暗。而这与实际的观察是有很大区别的。#绘画#须知,事实上,人是双眼动态观看的,而光源不是一个几何点,实际场景往往还是多光源的, 再则,光线不单是直线传播,而且还有衍射作用,因此投影和暗部非常复杂,难以做到透视学设定的精确测算,后来摄影术和数字技术等科技(technology)解决了这个难题而且发展了光色处理的理论和技术。[3]姑且不考虑这些因素,也不考虑绘画还可以使用非写实、非再现的语言,如果说,文艺复兴的透视法涉及到几何、数学(比例)等手段,那么,这种绘画是与精确科学同时起步发展的,当单眼观看的画法被精确科学发展起来的技术所取代,如摄影、计算机等科技成像方法,原先基于手工的画法必将失去竞争力而走向没落,所以才有19世纪后期始于印象派的绘画革命。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绘画不同,它本身并不建立在单眼的镜头式观看的基础上,因此,西方绘画的危机,并不是中国绘画的危机,相反倒是证明它的价值,恢复其自信的转机。关于这点将在本文结尾部分进一步讨论。中西绘画体系的不同[4],最明显地体现在各自的空间表现之上。英语空间space,有时亦指room,place,多与建筑环境有关。透视学就是根据单眼视觉原理从建筑直观图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因此,能拿来做中西绘画空间处理方法精确比较的只能是讲究线性的建筑画,故清代中国人称西方透视画为线法画,而能与之相比的中国的精确建筑画就是可兼用于建筑营造的图纸——界画。据美国学者刘和平考证,在宋代宫廷中,界画画家,有时以比例结构交代清楚的界画给建筑工程提供蓝图。[5]下面试就最严谨的宋代界画(以宫室台榭、屋木舟车等结构为主题的绘画)及其代表人物郭忠恕展开讨论。有关界画的叙述,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叙制作楷模”,“画屋木者,折算无亏,笔画匀壮,深远透空,一去百斜”,又云,“向背分明,不失绳墨。”[6]再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的“郭忠恕”,“为屋木楼观,一时之绝也。上折下算,一斜百随,咸取塼木诸匠本法,略不相背。”[7]其空间处理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词就是“一去百斜”或“一斜百随”。其含义就是,所有垂直于画面表达纵深方向的直线,不像西画中那样汇聚于一点(灭点或消失点),而是转变成一组平行的斜线,彼此永不相交(图1)。从技术上看,宋代界画要求“一点一笔必求诸绳矩”,郭忠恕的界画被比喻为“韩愈之论文”,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科学的严谨性。[8]但是,从理论上看,中国界画的空间表现理论,只见到“一斜百随”或“一去百斜”的说法,而无几何学法则。[9]后人甚至删去这种说法, 例如,邓椿《论界画法度绳尺》,“郭忠恕为屋木楼观,上折下算,与诸匠本法略不相背”,[10]也许因为作者不是界画家,所以未能在意“一斜百随”、“一去百斜”的本意。据笔者所知,界画的空间处理除了一组45度左右的平行线以及三维的测算与实际大致等比以外,没有几何学法则。相较而言,文艺复兴式的空间处理要严谨得多,以平行透视为例,凡垂直于画面的(平行)直线,其纵深方向的延伸,统统收拢于视平线(水平线)上的一点(消失点,灭点)。这个原则规定了观画者固定的观看方式,而画面则有固定的、标准的观看点(主要观看角度),因为图画是按照这个观看点产生的。成角透视虽与平行透视有所不同,但其原理基本一致,这里不一一展开讨论。而中国绘画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这种严谨方法,甚至界画也不例外,其空间处理限于“一去百斜”、“一斜百随”之类的口诀,没有立体几何学的作图法则,有一定的随意性,根据卷轴画展开的方式,大致形成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观看习惯。当然,严谨的界画也有表现的局限性,例如,在描绘同一建筑结构内部较大的深度时,它显得有点捉襟见肘,有点困窘,不知所措,如勉强为之,画面会变得教条、死板,界画常因此被指责为匠气。故而它较适合横卷(手卷)展开的视觉方式,而不太适合立轴式地展示纵向延伸的结构,如长廊之类。那么中西两种空间方法能否兼容于一幅画面而不违背各自的原则呢?清代后期《点石斋画报》尝试引进透视法于传统空间之中(图2-3)。不过画家没有严格采用透视法,只是挪用了弱化的透视缩短的表象,避免强烈的透视与界画空间冲突,这么一来,从画面上看,加强了深度感,摆脱了传统方式难以描绘空间连续往深处延伸之画面的困境,而且使画面内容比较充实,前后物象仍让人有同一舞台的感觉,不像西画那种因透视而产生的明显距离感和近大远小的强烈反差。但是,如果进行严谨的测量,可以发现数学上的错误,或者说,其空间是异质的,这是现代主义绘画的话语。这样的画面不但与透视学矛盾,而且也不合乎界画规矩。很显然,从科学意义上说,中西两种空间处理方法在严谨的线性空间中难以兼容。[11]而在艺术上,类似的将二者掺和在一起的处理方法并非清代才有,早在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图4)中就可见一斑,请看其中床和桌子等家具的处理,既有平行的斜线,也有收敛内聚的线条。这在艺术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科学上是违反规则的。根据“五四”以来的科学观念,用透视法来衡量,中国画,哪怕是界画,都不符合透视几何学的严格测算。由此推之,中国画的“不科学”已成定论,五十年代初,江丰就陈述过这一论点,中国画的改造因此被提上议事日程,所效法的科学的榜样自然是西方的包括苏联的学院派的写实造型方法。“五四”以来,“科学”这个概念在我国学界(包括文艺史哲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实际上所推崇的科学只是自然科学。当时所接受的科学概念指的是基于对外部世界研究和根据因果律推导的可以精确把握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是其哲学基础。然而在很多领域,例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等人文学科,还有人类学、心理学,原先的科学概念难以适应。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国画显然与科学无缘,至少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而言。回顾一下西方的历史,科学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科学首先是指自然科学,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科学取得了话语权。在科学霸权主义的背景下,人文学科谋求发展,要取得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只有一个选择,对科学这个概念重新解读并扩容,改造它使之为己所用,使自己自己登上科学殿堂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于是科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开始扩张了。可以说,这是一种聪明的迂回策略,与此情况类似的有,建国初期,在素描概念取得霸权地位(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时候,潘天寿不能正面反对素描,于是就提出国画有自己的素描,主要是线描,并使之纳入国画的素描体系之中,从而在西画霸权的背景下,让国画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类似的做法还有,用具象、意象等相对宽松的概念取代现实主义,能包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与苏联后期用开放的现实主义解读传统的现实主义异曲同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其作用就是消解霸权话语。且看西方科学概念在19世纪的发展演变。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激活,人们开始再次思考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方法论的讨论热闹起来。哲学家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在实证主义和唯心论之间的冲突。当时据称,心理学经验主义研究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方法并为一切人文学科(亦称精神学科)提供一种基础科学。德国哲学家爱德华·策勒(Eard Zeller,1814——1908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和弗里德里希·保尔森(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的著述,进一步证实一个早期新康德主义的见解,即心理学就是康德《批判》的基础。策勒在其关于认识论(Erkenntnistheorie)的著作中提出,运用科学方法的逻辑和以脑生理学为基础的心理学方法理论。朗格的《唯物主义历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是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书中讨论了科学的认识论的局限,而且像策勒那样,指出生理学家的发现是在康德理论上的一个进步。弗里德里希·保尔森坚信实证主义不能解释人的经验的含义和价值。[12]到19世纪后期,非自然科学学科逐渐挑战自然科学独占科学话语的霸权地位,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1883年,狄尔泰出版了《精神科学引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一书,推出精神科学的概念(关于“精神科学”的译名见下文讨论)。此书的主要部分是探讨形而上学盛衰的历史。狄尔泰提出一种新的方法和对这种新方法的见解,这种新方法就是心理学。他主张用一种新的认识论取代已死亡的形而上学,即一种以描述的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科学。狄尔泰常说心理学是历史科学的基础,而心理学不能与机械力学相比拟,机械力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例如,力学与历史无关,而心理学是历史的,这是决定性的差别。狄尔泰的理论涉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与“理解(verstand, verstehen)”之意涵。狄尔泰选择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或译,人文科学)的说法,拒绝接受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和因果关系的观念。在科学概念支配话语具有统治地位的时代,他创立的哲学诠释学,为使人文学科也成为一门科学,打破实证主义的垄断,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他坚持认为,“意识(Bewutsein)”是一种把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的主要因素。他对意识的观念是历史的,通过这个意识,人们可以重构和重新体验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狄尔泰认为,意识是全部人类知识的基础,还认为,只有通过对意识的调查研究才可能对知识做出解释。他提出的方法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因果关系的方式是对立的,他认为不能用那种方式去理解人的体验和内心生活。Geisteswissenschaften这个组合词,从构词上看,分解为Geiste和wissenschaft,前者解为精神(spirit)、思想(mind,intellect,ideas[13]),后者可解为学科(discipline,scholarship)、科学(science),因此这个组合词可译成“精神学”或“精神科学”,“文化学”或“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注意这个词狄尔泰用的是复数,包括多门学科,从他的文化哲学的立场来看,更适合翻译成“精神科学”。为更确切把握其涵义,在英译中,有人回避sciences而采用studies,将精神科学译为人文研究(human studies)或精神史学科(psychohistorical disciplines)。[14]狄尔泰旨在建立一个方法论基础,即以“精神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由此可以看到科学这个词的内涵外延的变化。精神科学是狄尔泰的研究的学科范畴,其方法论观点是,精神科学的要旨在于具体的生活体验,既非套用普遍规律或者从生活中总结出类似的自然法则,也非依据形而上学体系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在其方法论中不难看出,精神科学体系里,“人”是研究的主体,通过对人的身心的认识,拓展至对心灵的理解和体验,从而达到对生活领域乃至更大范围的体验。为研究精神哲学,狄尔泰最先提出生命哲学,以解答人的生命之谜。就生命而言,分精神生命和自然生命,精神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通过体验(erfahrung, erfahren)和理解(verstand, verstehen)才可以达到认识,而后者只须接触或观察。因此,在狄尔泰看来,精神科学主要研究框架是一个“理解-表达-体验”的循环。狄尔泰并没有说自己是发现并解决自然科学与非自然科学两难的先驱,他论述洛克、休谟及康德,通过批判他们的解决方式而建构一种新的认知。从“理解”的范围来看,狄尔泰所建构的就是通往整个生命之流的方式。可以说,狄尔泰一生致力于生命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研究。对狄尔泰来说,逻辑是一种为生活经验提供结构的解释性方法。逻辑是理解意识的最佳手段,因为它把思想同其潜在的精神和心理物理现象联系起来。但狄尔泰反对把数学的先验逻辑应用到文化科学中。按照他的说法,文化科学的逻辑不是一种不变的、先验的基础,而是依赖于语言及其内容,这种内容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在变化。狄尔泰提出一种启发式的方法:所有文化科学的基础科学都是一种描述的心理学,而逻辑将为意识的经验提供结构。他抛弃黑格尔和唯物主义,试图使唯心论哲学与19世纪科学和谐相处,并使之处于意识的中心地位。狄尔泰逐渐相信,当科学或逻辑的方法达到极限时,“只有从内部经验的角度看,结果才具有认识价值。”由此可知,科学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演变有其学术发展的背景。当学术发展了,新学科出现了,以前使用的科学概念,现在已不适合当前的认识,如果要继续存在,必须重新解释。狄尔泰质疑wissenschaft,即西语通常所说的科学这个概念[15],它原是针对实证的精确的自然科学而提出。狄尔泰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在其主要哲学论文《精神科学引论》中,拿实证主义这种自然科学方法与他选择的精神科学(或更具体地说是文化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进行对比。他系统阐述了对实证主义者——孔德(Comte,1798——1857),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和穆勒(Mill,1806——1873)的批评,这些实证主义者都提出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到针对人类的研究中。他推出精神(人文)、文化科学的概念,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科学概念的不同,或者说是纠正前者的偏颇与狭隘。狄尔泰时代,科学概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科学概念不能简单地挪用到发展起来的心理学、社会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之中。狄尔泰建立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对应,既保持科学的权威,又确保人文学科在科学的名义下健康成长。其实这是合乎人类认识发展的实际的。比如说,以前科学中的数学是指精确数学的话,那么随着认识的扩大深化和社会的迫切需要,数学的范畴必将拓展,将转向包涵更深广的模糊数学,反过来也证明,科学不只处理合乎因果关系的精确分析的问题,而且还要面对更为复杂的集合的问题。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狄尔泰强调历史学派的必要性,鉴于它自身有其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所以他致力于给予历史学派一个坚固的哲学基础(即后来的文化哲学范畴)。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指出的,“在把经验的东西还原为‘规律’被视为科学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义上,对文化事件进行的‘客观’研究是没有意义的”。[16]那种预设的规律是空洞而贫乏的,不能说明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件,因为历史和文化事件本身就不是唯一的、不变的,按照因果律运行的。而且,狄尔泰还要强调,历史学乃至其他非自然科学所要做的并不是去掌控抑或掌握社会的事件。“五四”以后,从西方引来的“科学”这个词被赋予极高的权威,可它的涵义基本上停留在自然科学之上,却被滥用到一切领域,特别是人文学科。然而,科学这个词在西方已发生的讨论在国内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其内涵的变化未被察觉,加上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困难,才有用之衡量并批评中国画,称之为不科学的言论,这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意识到科学概念的发展变化,这种批评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五四”时期的西方化进程,虽说总体上是一种进步,但对传统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涉及到方方面面,其危害不可小觑。例如,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白话文,其语法逻辑来自西方而不同于古汉语,致使二者之间出现历史的断层,如果用之解读古汉语,难免会有削足适履之憾。古文中富有诗意且简练的语句,按现代语言逻辑就是病句或不完整的,而经增补缺位后虽然合乎现代语法,却变得冗长而乏味。例如,《吕氏春秋》孟夏纪,“是月也天子始絺”,用白话文解,“这个月天子开始穿上细葛布的衣服”。按现代语法,把“絺”当作不及物动词,属名词当动词用,于是一个絺字变出八个字,当及物动词用,要写成“絺絺”。又如,“尔美”二字,如果当古文解读,则为谓语省略,按现代语法,应改作“是的”结构,补上谓词“是”和形容词尾“的”,即“你是美的”。但如此一来,诗性全无,变成了八股式陈述。同样,用现代语言逻辑解读“论画六法”,对这种原本缺少统一性而约定俗成的历史集体语言,期望咬文嚼字找到统一句式,给出最合理解释,往往无所适从。也许钱钟书讲得最深入,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17]同理,试图以透视的表达再现性空间的话语,用基于数学、几何学、光学、解剖学(结构学)等科学理论的观看方式和批评原则,去解读中国画,也会遇到同样的尴尬。因为中国画的空间只涉及基于视觉经验的大致关系问题,并没有打算建立严谨的自然科学的测算,界画亦然。[18]因此,如果要坚持说,中国画与科学有关系的话,那么只能被归入到人文科学一类的范畴。有人认为,传统国画处在类似西方文艺复兴之前的状态,按照进化论,系尚不开化的文化阶段的产物。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附录中引用劳伦斯·秉雍(Laurence Binyon,1869——1943)的话:“西洋近代之画学,使无文艺复兴以后之科学观念参入其中,而仍循中古时代美术之古辙,以蝉嫣递展,其终极,将与东方画同其致耳。”[19]秉雍在其《远东绘画》(Painting in the Far East)中,可能出于进化论观点的类比,将东方绘画看作处于文艺复兴之前的阶段,这种类比的依据应该是先前的殖民时代的文化人类学进化论思想,[20]无视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差异。那么按照这种进化论观点,是否可以认为,宋画在以后的几百年中没有发展出类似文艺复兴的模式是一种停滞不前,抑或说,19世纪引进文艺复兴模式是促进中国画发展的一种进步的、正确的选择呢?再问,文艺复兴模式的出现是绘画史的必然还是偶然?站在人文科学的立场上考察,即使没有科学观念的介入,东西方绘画互为他者也不会殊途同归。这种表面上的相似,反映了一种认知的权力,殖民时代的欧洲中心论将前文艺复兴艺术或非欧艺术排斥到边缘甚至边缘以外,视之为一种没有时间和个体的状况,属于前现代的文化类型。而中国画没有走文艺复兴的科学的道路,是受东方意识形态的把控的。自然科学之路决不是一切绘画艺术演变的必然之路,相反是在实证主义指导下走向极端,甚至在进步论、革命论逼迫下导致自我终结之路,是人类绘画史上的一段插曲,迫使人们反思,故而反叛之声屡屡,直至19世纪后期的绘画革命将之否弃。在中国绘画史上,早先并非没有出现过对人的视觉机理和物理现象的关注,例如,墨子关于光影和小孔成像的观察,[21]宗炳和后来李成所做过的透视尝试,[22]但没有得到认同,没被普遍接受。中国画家没有西方画家那种造型逼肖三维对象的追求,而更关注营造胸中的图像,将追求形似视为童稚之见。以荆浩为代表的中国画家,放弃宗炳的取景框式的尝试,为中国山水画立法,创造了不同于西方透视画的体系。荆浩倡导的以各种元素单元进行组合的创作方式,增强了中国画家内心创造的自由度,得到后人的推广。中国山水画因此不同于西方风景画,其演变并非朝西方透视画方向前行,而有其自身的路径。自荆浩开始,到清代《芥子园画谱》,中国画总结出一套构图程式,以山水画为例,将山水画拆分为若干元素:诸如山、水、林木、石、云霞、烟雾、霭岚、光风、雨雪、人物、桥杓、关城、寺观、舟车、四时之类[23],使之符号化,画家可结合自己的经验,凭借想象力自由组合。在山水画中,界画的强制性原则被缓解,而透视原理被转化为口诀式的处理和特定比例关系,例如,有“山分八面,石有三方”和“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髙与云齐,此是诀也”。[24]此外还有,诸如“寸马豆人”之类。与西法相比,在处理远近关系方面,中国画理同而法不同,以经验主义方法取代透视科学的测量计算,以艺术的优先和创造的自由取代对精确制图的拘泥,获取更大的自主权和支配权。中国山水画有大致相同的创作程序:“凡画山水,先立宾主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25]贺天健讲得更直白:学习拼凑成局,把对自然的“地貌学”的种种名类(修养)认知置入画中,再加上山水理论,构思成章;分为章法,结构。提出“章式——布局——章法——结构——位置”的程序。[26]中国画家根据视觉经验、伦理哲学等意识形态,自由想象,形成处理远近、主次、大小的辩证方法。中国山水画家对自然写生的观念就是“心存目想”,侧重所谓“迁想妙得”的形象思维,而文艺复兴传统侧重针对对象的精确表达,形以逼真为先,不能随心所欲,这是两种类型分属不同体系的特征之一。宋画中北派山水更以取势为主,是一种综合的抽象的类型,如果称之为写意,指向共性的类型化的话,那么西方风景画则是写实,指向具体的某一个。中西二者,思路不同,方法也不同。在追求视觉的三维逼真效果方面,文艺复兴的绘画以自然科学为先导,发展出严格的规则,几乎达到了精致完美,但艺术向自然科学看齐,其结果必然是机械技术取代手绘、战胜手绘。自文艺复兴以来,在再现性视觉图像表达上,学者们的研究从未中断,除了对透视、光影的研究外,还有,米歇尔欧仁谢弗勒尔(Michel Eugène Chevreul,1786——1889)等人对色彩学的研究,有尼塞福尔涅普斯(Nicéphore Niepce,1765——1833)和路易斯-雅克-芒代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1787——1851)等摄影先驱使用照相机械和化学显定影技术(日光胶版术heliography,达盖尔银版法daguerreotype),发展到彩色摄影,加上有时间延续性的电影和令人身临其境的全息摄影的出现,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发展,对科技手段来说,逼真效果简直是小菜一碟,与之相比手绘则显得捉襟见肘、难以企及。而人们对绘画的偏爱不再是图像的逼真感受,而是其创意和绘画性。从人文科学的角度考察,文艺复兴的透视学图像技术发展的道路,决不是一切绘画艺术演变的必然之路,相反是引向雷同化的绝路,故而在西方反叛之声屡屡,直至19世纪后期的绘画革命将之彻底推翻。而中国画优于文艺复兴体系之处就在于其东方哲学的宽容度和可持续性,这也是它能得到西方现代艺术认可的地方。那么试问,艺术与自然科学之间到底处于怎样的关系较合适?当艺术违背特定科学原理或视觉常识时,对之将作何种评价?显然,我们不会因为数学式测算的矛盾或错误而否定绘画的艺术价值。且再以《韩熙载夜宴图》为例。从该作的画面空间布局来看,既有界画式的空间处理,也有近乎焦点透视那样的内聚线,请看局部图的中间部分,然而都不严谨,二者相互矛盾,用任何测算方法都无法对空间做出明确的判断。但大多数观众通常视而不见,不会在意这种测算上的矛盾或错误。而对画家来说,这种矛盾或错误恰恰解决了单调、僵化或不必要的距离感等难题,观者只须获得一种空间的暗示就足够了,进而增强了戏剧性舞台效果。相比而言,中国山水画空间语言是诗学的,而西方风景画的透视空间语言属于精确科学的,是严谨如论文般的。艺术对于科学并非一种依存关系,相反,就是在文艺复兴传统中,即使其画法基于精确科学,许多大师仍然会超越乃至摆脱科学定则,不会让艺术拘泥于科学性,而是为了艺术去自由处置。例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图5),如果画家完全遵照严谨的测算,那么这张长桌显然容纳不下十二门徒,但是作为科学家的画家和广大观众都容忍了这种缺陷。应该说,艺术依赖自然科学只是一种偶然,更不是其唯一选择。艺术符合自然科学不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自然科学只是艺术的一种手段,而实际上艺术有很多别的理论和处理方法。艺术可以不符合某种科学方法,但并非不能用广义的科学概念去解释。古代中国画家没有尝试用“透视”的科学方法处理空间问题的愿望,他们不像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2872)和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那样受过建筑学训练,精通结构和透视画法,其笔下的中国景物完全是一种另类(图6-7)。古代中国人在观画时,也没有带着透视的眼镜,他们的眼睛还没有像当时西方人那样被透视观看方式绑架。古代中国的画家和观者都是自由的,不受科技定式的限制。在西方,虽然画家和观众都受到文艺复兴绘画科学模式的局限,但有识之士会主张摆托它的束缚。歌德在评鲁本斯的风景画时,对其中光影违反自然的处理,表达出自己的理解:鲁本斯正是用这个办法来证明他伟大,显示出他本着自由精神站得比自然要高一层,按照他的更高的目的来处理自然……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自然科学之理——笔者),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27]。概而言之,中西传统绘画的不同体系表现在以下方面:从写生观上看:中国画倾向于目识心记的经验,侧重画心中所知,包括色彩处理在内[28];西画拘泥于单眼定点所见的直观感受和自然科学设定的规则。从画面构思上看:中国画选择诸元素的重新组合;西画强调瞬间的情节。从视觉方式上看:中国画习惯于展示物象常态的比例关系,不为视觉变形所惑,因而适合远看,提出“以大观小”,“三远”等观念,客观上削弱立体感而造成平面化[29];西画强化空间纵深感,立体感,即透视感,因而借助远中近三景。当然,二者的区别,还基于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美学、伦理方面。由此观之,潘天寿的理论在当时是颇有道理的。中西传统绘画属不同统系,源自不同文化渊源,二者不能和谐相处,一时难以交融,至少在空间处理上如此。进一步说,西画过度执著于写实,如果用如此僵化的标准强行改造国画,势必让它变成五十年代一度流行的彩墨画,也就是水墨素描加色彩。这样的画,无论语境还是话语权都是西方的,但又很难达到西画的高度,致使中国画自身面临生存的危机。试看,清代中后期,了解西方透视法则之后,在一些中国画家空间处理中,尝试吸纳透视方法,但矛盾随处可见,按西方透视法判断,充满错误,被视为幼稚,仍然无法改变先前利玛窦批评中国画家不懂透视的印象[30],国画还是被看成落后的。诚然,从自然科学上看,中国人落后于西方,没有早早研究出透视学,但从人文科学上看,这不能作为解释国画尚未进化到透视法因而是落后的理由,而只能说这种成见,试图以追求精确逼似的狭隘方法,去包容自由博大的中国画,就像企图用自然科学去包容人文科学那样,恰恰是本末倒置。所以,19世纪末,当透视画法走到头而让位于科技手段的时候,在塞尚、毕加索等打破透视空间使西画转型之际,中国画并没有消亡,相反,到20世纪末,更显得风光无限。作者:潘耀昌简介80年毕业于浙美留校建史论系,88至90年伯克利分校访问,96年担任博导,98年调上大。出版《走出巴贝尔》,《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国水彩画观念史》。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中国美术名作鉴赏辞典》等,译著多部。[1] 参看,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12。绪论,第1-3页;附录,第281-301页。[2] 参看:A treatise on Painting by Leonardo Da Vinci,KESSINGER PUB LIC,2004:列奥纳多·达·芬奇著,戴勉编译,朱龙华校,《芬奇论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三篇,透视学,第55-91页。关于透视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参看:James Elkins, The Poetics of Perspectiv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书中还评及一系列学者的研究,包括,Erwin Panofsky, Hubert Damisch, Martin Jay, Paul Ricoeur, Jacques Lacan, Maurice Merleau-Ponty, 和E. H. Gombrich等。[3] 关于光影研究的历史,参看,Michael Baxandall,Shadows and Enlighten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 London,1997。[4] 从这里开始,非特别说明,中西绘画分别指的就是以宋画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画和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西方学院派绘画。[5] 参看,Heping Liu,The Water Milland Northern Song Imperial Patronage of Art, Commerce, and Science, THE ART BULLETIN, December 2002.[6] 参见,《图画见闻志》,“叙制作楷模”,《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7] 参见,《圣朝名画评》,“郭忠恕”,《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58页。[8] 参看,内院奉敕撰,《宣和画谱》,“宫室叙论”,《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83-84页。[9] 参看拙文,“‘以大观小’和‘一斜百随’——谈宋代界画的空间意识:试述一种准科学的模式”,潘耀昌,《走出巴贝尔·续》,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10。第79-90页。[10] 见,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彙编》, 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31页。[11] 从数学上讲,其特例是无限远的“远看”,参看拙文,注释9。[12] 参看:Joan Hart, “Reinterpreting Wolfflin: Neo-Kantianism and Hermeneutics”,Art Journal42:4(Winter 1982), pp.292-300; Ernest K. Mundt, Three Aspects of German Aesthet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 Art Criticism, Vol. XVII, March, 1959.[13] 例如,英译者将Max Devoák(德沃夏克)的Kunstgeschichte als Geistgeschichte译为TheHistory of Art as The History of Ideas(作为思想史的艺术史,或,作为观念史的艺术史), 陈平中译本译为《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参看,陈平译本的译者前言。[14] 参看,(美)鲁道夫马克瑞尔(Rudolph A. Makkreel)著,李超杰译,《狄尔泰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2月。第36页。看来英译者还是不愿意让人文学科当作科学看待。[15] 与德语wissenschaft大致对应:意大利语为scienza,学科、科学;英语为science,科学、知识、学问、学术;法语为science,学科、自然科学、知识、学问。总体上指学科,进而指向科学,最初是指严谨的自然科学。然而,科学这个词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英语scientific,加拿大后殖民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格拉德·麦克马斯特(Gerald McMaster),在批评殖民时代进化观人类学,讨论土著艺术家作品时,所使用的scientific的涵义就不完全是自然科学,而是指人文科学、学术研究。见Gerald McMaster, Museums and Galleries as Sites for Artistic Intervention, pp. 250-261, esp. 253-256. From The Subjects of Art History, edited by Mark A. Cheetham, Michael Ann Holly, Keith Mox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16]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版,2012,第24页。[17] 参看,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10。一八九 全齐文二五。第1352-1366页。[18] 虽然,界画对远近空间的处理,多按比例放缩,例如,“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寸计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规度,曾无少差。非至详至悉委曲于法度之内皆不能也”(见于李廌《德隅堂画品》,“楼居仙图”, 引自《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991页),可谓严谨精准,但仍缺少西方那种几何学和数学的基础。[19]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12。附录,第300页。查阅,Laurence Binyon,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3rd ed., 1923;Laurence Binyon,Painting in the Far East:An Intro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ictorial Art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Japan. 1908, 1st ed., London, Arnold, 1934, 4th ed., 1959, reprint New York, Dover。[20] 参看,拙文:“从一元论到多元主义——关于美术史研究的中心论”,《齐鲁艺苑》,2007,1。[21] 参看,《墨子·经下》、《墨子·经说下》,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22] 指宗炳的“张绡素以远映”,李成的掀屋角。参看拙文:“西洋透视和中国界画——两种透视法的比较”,载《新美术》,1986,4;“中国山水画的原点——荆浩画论研究”,载《荆浩国际学术论坛》(文献集、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5。[23] 参看,宋韩拙,《山水纯全集》,《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24] 王维,《山水诀山水论》,王森然标点注释,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12。[25] 李成《山水诀》,《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参看,余绍宋编《画法要录》,中国书店,1990,3。第23页。[26] 参看,贺天健《学画山水过程自述》,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完稿于1960年。中编,第69页,91页,下编,第130页。[27] 见,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6页。[28] 例如,参看《芥子园画传》第一集巢勋临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2,第一版,1993,10,第二版。设色,第26-33页。[29] 虽然南宋出现“马一角”、“夏半边”的探索,但不被列入主流,而且是宋代后期的事。有关远看造成平面化的讨论可参看希尔德勃兰特的《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30] (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绘画之要,以斯格拙,不可删修,子既好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原画家以神品为宗极,又以逸品加于神品之上者,曰出于自然而后神也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石鲁说:画山要把山当人来画,有高大的,有坚强的,有的是优美的郭熙作画:凡落笔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然后为之
 横行天下
横行天下高福当选2020年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透露,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近日当选为2020年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资料图高福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等,兼任国家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在包括Nature, Science, Cell, Lance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500余篇,兼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内外专项奖等30余项。据介绍,德国国家科学院源于1652年成立的利奥波第那科学院(Leopoldina),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院,以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命名,是德国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的联合会,也是世界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心),学院总部现位于德国东部城市哈雷。利奥波第那科学院根据不同的研究领域共设4个类别学部和28个学科组,拥有1500多位院士,包括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著名学者,他们大多是在高校或各大研究所工作的教授或研究人员。利奥波第那科学院选举院士要保证独立性和学术性,德国院士称号突出的是学术性和荣誉性,不与任何物质利益挂钩。章程规定科学院每年增选院士约60名,选举过程首先从提名候选人开始,正式提名只能由院士提交,经3轮选举后产生。选举过程严谨而复杂,完全以无记名方式秘密进行,成员要匿名填写意见表,参与学科组评选、类别学部评选以及主席团评选的人都是不同的,学科组有30~40人,类别学部有10人左右,主席团有12人。候选人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提名,整个过程就像诺贝尔奖评选一样,接到信函通知才知道自己当选。这就避免了任何个人或小团体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有关专家强调,选举信息透明仅限于院士评委范围内,对外界则严格保密,蒙在鼓里的反而是最后的当选者,一般实际选出的院士在50名左右,待年满75岁则空出名额,可终身享受院士称号。现有的院士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其中四分之三来自3个德语国家(即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四分之一来自其他国家。中国科学家路甬祥、武忠弼、卢柯、张杰等多名教授都曾先后当选德国科学院院士。截至2011年,共有168名利奥波第那科学院院士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包括居里夫人(Marie Curie),达尔文(Charles Darwin)、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普朗克(Max Planck)、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eothe)、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享誉全球的科学大师。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刘欢编辑:王海萍流程编辑:郭丹
 纯素之道
纯素之道剑桥大学专家组建立“语言博物馆”探索语言新世界
剑桥大学牵头的一个研究小组试图通过一系列互动式展览来复兴英国的语言,这些展览旨在让人们畅所欲言。这些互动游戏种类繁多,生动有趣:有爱丽丝在《语言仙境》中的冒险经历;“迷失在翻译中”的单词挑战;“外来词语来聚会”比如emoji(表情)、graffiti(涂鸦)等;还有一个“抓腮先生”口音识别游戏。剑桥大学这些只是第一个互动式“语言世界”博物馆中的一些怪异而奇妙的亲身体验。免费第一站选在剑桥格拉夫顿购物中心(Grafton shopping centre),然后将在未来5个月内前往贝尔法斯特、爱丁堡、诺丁汉和伦敦。探索语言新世界这项由剑桥大学语言专家领导的独特项目旨在通过展示现代语言的趣味性、可实现性和实用性来振兴英国的现代语言。“英国确实有一些真正的细分化的小众博物馆,包括割草机博物馆和狗项圈博物馆。剑桥大学的项目负责人Wendy Ayres Bennett教授说:“现在是我们建立语言博物馆的时候了,因为语言是我们人类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无论我们是在家、度假还是在工作场所。”割草机博物馆“我们的目的是让博物馆尽可能地吸引人和不被打扰。许多人认为学习语言是一件苦差事。我们想展示它可以而且应该是有趣的,并且创造出令人兴奋的时刻。因此,无论游客是4岁还是84岁,我们认为他们都会觉得这非常有趣。”在这些有趣的互动展示(提供电影、测验、听力挑战、单词分类游戏、语音辨析等等)背后,隐藏着一个严肃的目的。该项目的中心目标之一是挑战迷信和偏见,包括英国人不擅长语言,也不需要学习语言的想法。英国已经是一个拥有丰富多种语言的国家,但语言学习却处于自由落体状态。自2000年以来,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是英国学生完成第一阶段中等教育会考所颁发的证书)考试的报名人数下降了44%,其中法语和德语各下降了60%以上。在本科层次,情况更糟:2008年至2018年间,现代语言专业本科生人数下降了54%。艾尔斯贝内特说,这不仅会损害个人利益,还会损害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只有了解其他人的语言,你才能真正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世界,了解其他文化的运作方式。世界上有更多的人会说两种语言。“学习语言太难和精英就是“文化包袱”的想法应该被摒弃。英国迫切需要更多的商务、贸易和外交语言技能。”大量研究表明,学习一门语言能磨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化意识和灵活性,以及沟通能力,这是所有职业的重要资产。语言学习也有助于打破障碍,并且在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只要知道hello这个词,就能让人觉得在社区里更受欢迎。适度的努力也意味较大的付出”艾尔斯·贝内特说。这个互动式博物馆是艺术和人文研究理事会资助的重大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它的团队来自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和诺丁汉大学的语言学家,他们调查语言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寻求在基层激发人们的注意力,并将语言推上政治议程。研究小组知道,转变观念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因为英国在接受语言教育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因此,免费博物馆将出现在无障碍的公共空间,包括购物中心、剧院和图书馆。该小组还与公立学校密切合作,公立学校的免费学生比例很高,而且在那些除了英语以外很少有人说其他语言的地区。
 八十八
八十八每日一校推荐: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在三环路两侧分设东、西两个校区,是教育部直属、首批“211工程”高校、“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校、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北外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高等学校,前身是1941年成立于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建校始隶属于党中央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归外交部领导,195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1959年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80年后直属教育部领导,1994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获批开设101种外国语言,欧洲语种群和亚非语种群是目前我国覆盖面最大的非通用语建设基地,是教育部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学校形成了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文、法、经、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按照时间先后,学校开设语种包括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日语、阿拉伯语、柬埔寨语、老挝语、僧伽罗语、马来语、瑞典语、葡萄牙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斯瓦希里语、缅甸语、印尼语、意大利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豪萨语、越南语、泰语、土耳其语、朝鲜语、斯洛伐克语、芬兰语、乌克兰语、荷兰语、挪威语、冰岛语、丹麦语、希腊语、菲律宾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斯洛文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爱尔兰语、马耳他语、孟加拉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拉丁语、祖鲁语、吉尔吉斯语、普什图语、梵语、巴利语、阿姆哈拉语、尼泊尔语、索马里语、泰米尔语、土库曼语、加泰罗尼亚语、约鲁巴语、蒙古语、亚美尼亚语、马达加斯加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阿非利卡语、马其顿语、塔吉克语、茨瓦纳语、恩得贝莱语、科摩罗语、克里奥尔语、绍纳语、提格雷尼亚语、白俄罗斯语、毛利语、汤加语、萨摩亚语、库尔德语、比斯拉马语、达里语、德顿语、迪维希语、斐济语、库克群岛毛利语、隆迪语、卢森堡语、卢旺达语、纽埃语、皮金语、切瓦语、塞苏陀语、桑戈语、塔玛齐格特语、爪哇语、旁遮普语。学校秉承延安精神,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目前已开齐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用语。北外现有33个教学科研单位,近年来,学校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成立国际研究生院,陆续成立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等众多特色研究机构;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北外学院、国际组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在原亚非学院基础上,扩建为亚洲学院、非洲学院。学校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委科研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4个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中东欧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以及37个教育部备案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3个教育部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法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学校编辑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文学》《国际论坛》《国际汉学》四种CSSCI来源刊物,一种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出版《中国俄语教学》《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国际汉语教育》《英语学习》《欧亚人文研究》《德语人文研究》《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区域与全球发展》《青少年法制教育》等刊物。学校有全国最大的外语类书籍、音像和电子产品出版基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外开设本科专业121个,其中44个专业是全国唯一专业点。学校现有4个国家重点学科(含培育学科),7个北京市重点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11个(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教育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点8个(金融、国际商务、汉语国际教育、翻译、新闻与传播、法律、会计、工商管理硕士),涵盖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六大学科门类。在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学校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评级为A+,位居全国榜首。2018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发布,学校语言学、现代语言2门学科再次进入全球前100强,居国内同类院校之首。学校本科在校生5600人,研究生(硕士、博士)3100人,留学生1600人。北外注重创新人才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现有在职在编教职工1200余人,另有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教师近200人。学校拥有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家百万千万人才工程、国家“四个一批”人才、青年“长江学者”等高水平师资。教师中超过90%拥有海外学习经历。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师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北外坚持高端引领、整体推进的国际化办学思路,与世界上91个国家和地区的313所高校和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匈牙利罗兰大学、波兰雅盖隆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学校承办了23所海外孔子学院,位于亚、欧、美18个国家,居国内高校之首,包括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孔子学院、比利时布鲁塞尔孔子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意大利罗马大学孔子学院、波兰克拉科夫孔子学院、比利时列日孔子学院、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保加利亚索非亚孔子学院、捷克帕拉茨基大学孔子学院、德国慕尼黑孔子学院、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英国伦敦孔子学院、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术孔子学院、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孔子学院、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法国ESCP欧洲高等商学院商务孔子学院和美国夏威夷玛利诺学校孔子课堂。北外图书馆馆藏纸质中外文图书近145万余册,中外文电子图书222万余册,中外文报刊1123种,中外文数据库97个,形成了以语言、文学、文化为主要资料的馆藏特色。近年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政治、法律、外交、经济、新闻和管理等方面的文献逐渐形成藏书体系。学校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形成“开放、互联、智能、创新、融合”的信息化构架,开发以多语种网站、数字北外、数据中心软件平台等为代表的多项标志性成果。其中,多语种网站项目于2015年启动,支持50种外国语言。2018年获批教育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高校。在长期办学历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形成了“外、特、精、通”的办学理念和“兼容并蓄、博学笃行”的校训精神,成为培养外交、翻译、教育、经贸、新闻、法律、金融等涉外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一批批从北外走出的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国、全国各地,活跃于各行各业,建功立业、成就卓著,成为精英翘楚、社会栋梁。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校友中,先后出任驻外大使的就有400多人,出任参赞2000余人,学校因此赢得了“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美誉。来源: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