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柴
鹿柴“曾随之谜”:长达五十年的考古证明曾国、随国本是一国
一波三折的曾国探索对于曾国这个周代小国,我们并不陌生。中学历史课本上的“曾侯乙编钟”是春秋战国音乐艺术的代表性文物,“曾侯乙铜鉴缶”也是国宝级文物,被认为是最早的“冰箱”“烤箱”,它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缶的设计原型。曾侯乙编钟与曾侯乙铜鉴缶,均出土于1978年湖北随县(今位于随州市曾都区)擂鼓墩的曾侯乙墓。曾侯乙墓虽然是最蔚为大观的曾国考古发现,但却并不是唯一的。曾国考古从上世纪至今都时有发现。2019年3月3日,国家文物局就收到举报线索,得知日本东京在拍卖一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其中包括一件鼎、一件簋、一件甗、一件霝、两件盨、两件壶。在认定这批文物系近年被盗出土且非法出境后,国家文物局会同公安机关将这八件流失的国宝追回,后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曾伯克父青铜组器那么,曾国考古还有哪些发现呢?关于曾国的青铜器,早在宋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就有著录,其中有“曾师盘”和记载周王南征经过曾国的“中甗”,不过当时“曾”字未被释读出;另外两件楚惠王为曾侯乙之死所铸的“楚王酓章钟”,“曾侯乙”的身份也未被关注。直到晚清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收录了“曾伯簠”和“曾仲盘”;同时阮元指出,这里的“曾”就是春秋时期位于今天山东兰陵一带的姒姓鄫国。就当时的考古发现看,阮元的观点是合理的。文献中主要记载了两个“曾国”,一个是《史记·周本纪》中,西周末年,会同申国、犬戎攻杀周幽王的“缯国”,但这个“缯国”在文献中惊鸿一瞥,再也不见。而另一个“鄫国”,虽然是个小国,但在记录春秋历史的《左传》中频繁出场,考虑到楚惠王又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所以将青铜器中的“曾”定为《左传》的鄫国,应该是个最优的选择。不过其中问题也显而易见:春秋时期,鄫国最早臣服于鲁国,国君鄫子娶了鲁僖公女儿为妻,有次鄫子不肯朝见鲁僖公,鲁僖公还扣留了回娘家的女儿。后来鄫国被东方淮夷侵袭,齐桓公专门召集诸侯在淮地会见,并且发动诸侯为鄫国筑城。之后宋襄公称霸,杀死一个鄫国国君祭祀社神,用来威慑东夷。再往后邾国、莒国相继对鄫国控制,邾国军队一度进入鄫国杀死又一个鄫国国君。最后在公元前567年,鄫国为莒国所灭。而楚惠王即位于公元前488年,彼时鄫国早已灭亡。山东苍山鄫国故城遗址1933年,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战国楚墓出土了一件“曾姬无壶”。这个作器者“曾姬无”是战国初年楚声王的夫人,楚声王是楚惠王的孙子,那么这个“曾国”竟一直延续到战国初年。更为关键的是,虽然她的父国也是“曾”,但她的父姓却是“姬”,这表示她绝对不会来自姒姓鄫国,当时一定还存在另外一个姬姓曾国。受此启发,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第一次提出“曾侯”器当为“楚之邻国”曾国,但仍将“曾子”器定为山东鄫国。至此,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存在一个与楚国毗邻的“曾国”,刘节《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指出《左传》中郑国有个“鄫”地,据杜预注在今天河南睢县东南,故考古发现的姬姓曾国应该是从郑国鄫地南迁到楚国一带的,甚至可能就是灭西周的缯国。不过,当时关于曾国的青铜器都是零星出土的,还没有一处科学发掘的曾国遗址与墓葬。所以,学者的推测也只是无源之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目不暇接的曾国考古时代终于来临了。最早是在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发现了97件青铜器,其中几件铭文标着器主“曾侯仲子斿父”的身份,断代大致在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之间。当时在张政烺先生指导下,考古简报指出,这个鄂北地区的姬姓曾国应该就是灭亡西周的缯国,区别于山东与郑国的鄫。之后1970、1972年,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又两次发现曾国青铜器,其中有“曾伯文簋”。随后,在湖北枣阳、河南新野也发现曾国青铜器,其中有“曾侯絴伯戈”,断代大致在春秋早期。早在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中,就指出《左传》中的“缯关”即灭周之缯的遗址,因为“缯关”在今天河南方城(属南阳),而与缯国合谋的申国正是在今天河南南阳市区。而这段时间的考古更加表明,至少在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曾国”是横跨鄂豫二省的一个强国。这样看来,高士奇、张政烺的观点似乎得到支持。(注:不过今天学者多根据《竹书纪年》的“西申”“申戎”的称呼,认为申国应该在陕西一带,那么缯国也在西北地区。)河南方城古缯关博物馆至此,对于“曾”的主流认识从山东鄫国,转变到郑国鄫地,再到鄂豫交界,似乎一步步接近正确答案。真正让“曾”为学界重视并广为人知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发现。其中出土了一批乐器、礼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器、丧葬用品及竹简等,共15404件,而乐器就占有1851件,为中国音乐史上举世瞩目的空前大观。尤其是“楚王酓章钟”的出土,与宋人著录的“楚王酓章钟”内容完全一致。这表明曾国在此处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而且随州不仅仅是曾国的势力范围,更重要的是,这里就是曾国国都所在地。不过,这片地区在传世文献中却是随国的国都。今天随州市随县的名称,最早来源于秦朝所置南阳郡随县。难以想象,在随国国都附近又坐落着另外一个大国国都。虽然春秋时期不少小国彼此相邻,但随国与曾国却不能说是小国:曾国势力范围达到河南南部,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随国也被《左传》称为“汉东之国随为大”,在与楚国的交往中频频露脸。这两个国家如何共存的?楚国灭国无数,为何保存了曾国?就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同年,李学勤先生即发表《曾国之谜》,破天荒提出:曾国就是随国!那么,历史上的随国,又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呢?文献中的随国历史春秋战国时有两件齐名的宝物——随侯珠与和氏璧,被称为“随珠和璧”。随侯珠的典故见于《史记正义》引西汉刘向编著的《说苑》,说的是随国国君随侯出游时,见到一条大蛇重伤断为两截。随侯不忍心看到它死去,就叫手下为它敷上药物治疗。一年之后,突然有条大蛇衔着一颗明珠送给随侯,是当年被随侯救命的大蛇前来报恩了。这颗明珠通身雪白,径直一寸,而光辉如同月光一般,于是被后世称为“随侯珠”。《说苑》这段记载只能视为传说,然而这里提到的随国,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周代诸侯国,对于随国历史的记载,主要见于《左传》中。随国在史书中出场已经是公元前706年,当时是春秋初年,南方大鳄楚国正在往中原扩张,但随国长期是汉水以东第一大国,楚武王不敢掉以轻心。于是他先派薳章假意求和,随侯则派少师来洽谈。此时楚武王采取斗伯比的建议,故意把军容弄得懒散邋遢。少师见状果然上当,要求随侯袭击楚军。但楚武王的扮猪吃虎之计却被随国贤臣季梁一眼看穿,季梁劝阻了随侯,并且劝谏随侯修明政治,爱护百姓,结好邻邦。于是随国一度蒸蒸日上。但好景不长,随侯宠幸少师,国内政治昏暗。两年之后,斗伯比提议楚武王进攻随国。于是楚武王在沈鹿会盟诸侯,随侯没有参与,楚武王以此为借口攻打随国。面对楚国大军的施压,季梁审时度势,建议干脆向楚国投降:如果楚国接受投降,那自然好办;如果不接受,随国大军也能够背水一战。但少师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求速战速决,随侯果然又听从了他。但季梁没有失望,他还有破楚之计。公元前704年的楚随速杞之战揭开序幕。季梁遥望楚国的军队,对随侯说:“楚人以左为尊,国君一定在左军,那么左军肯定更精锐,君上不要与他正面作战。不如先全力攻击他的右军,等到楚国右军失败,他们左军不就也跟着崩溃了吗?”当时还比较讲究堂堂正正的军礼,而季梁决定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胜算。但少师又出来反对,他认为:“君上不与楚王正面作战,难道我国与他国不对等吗?”随侯果然又听信少师,与楚国在速杞硬碰硬交战。春秋楚随地区地图结局自然在意料之中,随军大败。随侯连战车都不要了,慌忙逃走,而少师运气则没这么好了,他还留在战车上,被楚国的斗丹杀死。随侯没有了少师,只能听从季梁,与楚国修和。楚武王本来还不同意,想扩大战果继续进攻随国,但斗伯比认为,奸臣少师已经被铲除了,此时随国团结一心,贤臣季梁当政,所以难以战胜。楚武王接受他的意见,于是接受了随侯的盟约,相当于收了随国这个附庸。当然,此时楚国对江汉小国,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除了随国之外,此时还有贰、轸、郧、绞、州、蓼、江、黄等小国,所以随侯对于楚武王并非真正归附,郧国就与随国谋划过进攻楚国。虽然计划没有成功,但楚国终究觉得随国不靠谱。于是在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再次进攻随国。但在位五十一年的楚武王终究老了,还没与随国交战就去世在军中。而令尹斗祁、莫敖屈重等大臣秘不发丧,在随国境外安营扎寨,随侯不明状况,只能再次求和。之后,随国又蠢蠢欲动。公元前640年,随国再次背叛楚国,被楚国令尹斗谷于菟击败。三败三和的随国,至此才完全沦为楚国附庸。但不知为何,楚国在江汉一带灭国无数,却始终留下了随国的社稷,而这一决定却最终救了楚国。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相国伍子胥攻破楚国郢都,楚昭王一路逃亡到随国。吴军紧跟其后,阖闾勒令随侯交出楚昭王,说:“汉水以东的姬姓诸侯们都被楚国灭亡,你们为何还要袒护他们呢?”由此可见,随国也是姬姓诸侯、周天子的亲戚。但随侯却拒绝了阖闾,他说:“随国偏僻狭小得以被楚国保存,并与楚国世世代代盟誓,今天怎么能够背约抛弃楚国呢?如果您对楚国加以安抚,我国怎么不听从贵国命令呢?”阖闾最终放弃索要楚昭王。公元前494年,因为当时蔡昭侯依附吴国,所以楚昭王联合随侯、陈侯、许男等围攻蔡国,并取得胜利。这也是随国在史书中最后一次出场,至于随国什么时候灭亡,与其什么时候分封一样,在史书中都没有记载。除了《左传》之外,其他文献对于随国也有零星记载,这些史料来源较晚,未必完全可靠,只能作为参考。《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太史伯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那么随国至晚在西周末期也应该在南方立国。《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706年,楚武王进攻随国,希望随国能向天子为自己请求尊号;在遭到周天子拒绝后,公元前704年,楚武王自称王,与随国盟誓;公元前690年,周天子责怪随侯尊楚国为王,楚武王以为随国背叛自己,在伐随途中去世;公元前672年,楚庄敖想杀弟熊恽,熊恽与随国合谋杀死了庄敖篡位,就是楚成王。可见,楚国与随国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可以说楚成王后代能继嗣王位,与随国的帮助密不可分。通过对文献中随国历史的叙述,我们可以明确:随国与曾国确实很大程度相似。尤其是为什么楚国没有灭亡曾国这一疑问,如果说曾国就是随国,那么将会迎刃而解。因为楚惠王正是楚昭王的儿子,而随国对楚昭王有救命之恩,再加上之前还有拥立楚成王之功,所以楚惠王在曾侯乙去世时,还专门送青铜器钟来凭吊,并且直到战国时期,楚国还对曾国进行保护。当然,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所以仍然有不少学者并不认同随国就是曾国。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考古逐渐揭开“曾随之谜”1979年,随州义地岗发现一处曾国墓葬,出土了春秋中期的“周王孙季怠戈”,这个季怠是曾穆侯之子,担任曾国的“大攻尹”。“周王孙”代表曾与随一样都是天子旁支,印证了之前学者提出曾国姬姓的正确性。2003年,襄阳梁家老坟战国墓地又出土一把春秋时期的“曾侯昃戈”,曾侯昃比曾穆侯可能稍晚。到2009年,随州又在文峰塔发现了春秋晚期的曾侯与墓葬,其中一件“曾侯与钟”的铭文长达169个字,所含信息非常丰富。“曾侯与钟”的铭文系曾侯与对曾国历史的回溯,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曾国始封国君的功绩,他就是“左右文武”的南公伯括,被分封至曾国抵御淮夷;第二部分说的是周王室衰弱后,曾国盟誓并依附于楚国,楚国在吴楚战争中失利时,曾国明确站在楚国一方;第三部分则是曾侯与叙述自己作钟的用途。第二部分的内容,明显也与《左传》中公元前506年吴楚之战时随国的表现一致,这更加印证了曾国与随国本是一国。史书中有没有南公伯括这个人?有的。《诗经》里就有记录西周南氏的人物“南仲”,而《论语》里的“周之八士”中又有个“伯适(括)”,伯括为南氏,这就很容易与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联系起来,此人就是《封神演义》里的“大将军南宫适”。南宫适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与闳夭、太颠、散宜生合称“文王四友”,而复氏在书写中往往简化为单氏,所以一般认为,南公伯适就是《论语》的伯括,也就是历史上的南宫适,全称当为“南宫公伯适(括)”。更加惊人的发现在2013年,随州叶家山出土了西周曾国墓葬,其中有“曾侯谏”与“曾侯犺”等曾侯墓葬,曾侯犺称其父亲为“南公”,而曾侯谏又比曾侯犺略早,故两人可能是兄弟关系。大概当时南宫适被封随国,与周公封鲁、召公封燕一样,本人没有就封,而命长子曾侯谏就封。叶家山曾国早期墓葬的发现意义非凡,这证明曾国在西周初年就分封在随州一带,并非是从中原等其他地区逐渐南迁过来的。我们注意到,上文说的墓葬、青铜器都是曾国的,那么随国的遗址和文物是否有发现?直到2011年,曹锦炎先生公布了一件收藏家所有的“随仲嬭加鼎”铭文,其中就提到楚王为女儿铸造的“随仲嬭加鼎”,“仲嬭加”即楚王的二女儿嬭(芈)加,她出嫁到随国。曹先生认为此器应该是楚穆王、庄王、共王之际所作。2013年,文峰塔的“曾孙邵墓”出土了一件“随大司马戈”,这是随国青铜器首次在曾国墓地被发现。不过,对于随国青铜器的发现,却又引发了学者的争议。主张曾随一国的学者认为,随国青铜器在曾国墓地被发现,这证明了曾随就是同一个国家;但主张曾随二国的学者认为,这恰恰证明曾随就是两个国家。不过到随着枣树林曾侯墓地的发掘,真相终于渐渐浮出水面了。枣树林曾侯墓包括曾公求夫妇墓、曾侯宝墓夫妇墓与曾侯得墓等,其中最关键的发现在于2019年曾侯宝夫人墓,至此“曾随之争”应该终结了。曾侯宝夫人墓出土了一组“嬭加编钟”,铭文记载“文王之孙、穆之元子,之国于曾”,整理者认为说的是周文王的后代、曾穆侯的长子曾侯宝,不过这个观点显然有问题,南宫适既是“左右文武”的重臣,他的后代何来“文王之孙”一说?从另一件出土的文物“楚王媵随仲芈加缶”来看,这段只能是芈加夫人的自述。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楚文王的后代、楚穆王的长女,从楚国出嫁到曾国,而同时她又被称“随仲”,那么随国即是曾国,至此可以论定。这位墓主不是别人,正是2011年所公布“随仲嬭加鼎”中的楚国公主芈加,与曹锦炎先生推测的年代也完全符合。其中唯一的疑问在于“嬭加编钟”的芈加号称“元子”,而“随仲嬭加鼎”“随仲芈加缶”的芈加却被称“仲”,长次应该有别。但应该注意到,“随仲嬭加鼎”“随仲芈加缶”均是媵器,也就是楚王为女儿铸造的器具,那么“仲”应该是芈加的真实排行,但芈加在自制的“嬭加编钟”却自称“元子”,可能与其在曾国的崇高地位有关。不过这仍不是曾国考古发现的全部。除了前文提到西周前期的曾侯谏、曾侯犺、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的曾侯(仲子)斿父、春秋早期的曾侯絴伯、春秋中前期的曾公求、曾侯宝、曾侯得、春秋中期的曾穆侯、春秋中后期的曾侯昃、春秋晚期的曾侯与、战国前期的曾侯乙外,明确被称为“曾侯(公)”的,还有春秋末期的曾侯戊(曾侯乙墓出土其器具)与战国中期的曾侯丙(2012年文峰塔发现其墓葬),曾侯丙墓也是目前发现最晚的曾国国君墓葬。至于2019年海外追回的“曾伯克父组器”,其实这个器主“曾伯克父甘娄”也是熟人。2016年,新出版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就著录了两件“曾伯克父甘娄簠”,并提及同坑出土同人所作之器数十件,并认为其为春秋早期的器具。器主应该也是曾国国君,字克父,名甘娄。学者早就发现,在金文中“五等爵无定称”,那么曾伯实际上也是曾侯。方勤先生认为,除了以上13个“曾侯”外,还有曾伯漆、曾伯陭等8个未称为“侯”的曾侯。从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曾国考古发现开始,至今已经渡过五十多个春秋了。在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的努力下,不但有曾侯乙墓这样举世瞩目的周代古墓葬重见天日,更有一部《史记》没有作传的《随(曾)世家》正在逐渐形成,堪称是周代诸侯国考古研究的典范。当然,也留下不少未解之谜等待我们继续发掘,比如曾国最后到底是如何灭亡的,是在曾侯丙后某一年最终被楚国吞掉,还是在公元前278年的白起破郢时顺便收入囊中?参考文献曹锦炎:《“曾”、“随”二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陈虎:《嬭加编钟的初步试读》,《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黄尚明:《曾侯世系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谭维四:《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谢明文:《曾伯克父甘娄簠铭文小考》,《出土文献》,2017年第2期。张昌平:《从五十年到五年——曾国考古检讨》,《江汉考古》,2017年第1期。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鸡鸣狗吠
鸡鸣狗吠曾侯乙编钟出土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专家称其为中国考古百年最重要发现
人民网武汉9月20日电 19日上午,曾侯乙编钟出土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博物馆召开。来自中国大陆、美国、韩国、德国、中国台湾的五十余位考古、音乐专家齐聚一堂,总结四十年来曾侯乙编钟等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研究成果,结合近年来曾国考古新发现,展望未来曾国历史、考古、文化研究趋势。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泰、著名音乐学家老锣分别作了《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早期编钟的新发现及其意义》《假的传统 VS 当代的艺术—曾侯乙编钟音乐的未来》的主题报告。与会学者认为,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体现的音乐、科技、艺术成就,是人类“轴心时代”文明的杰出代表,曾侯乙墓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曾侯乙编钟音乐性能卓越,音律纯正,音色丰富,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其长篇铭文系统记载了中国当时的音乐学理论。它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保存了2400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有声音乐理论文献。曾侯乙编钟是最能代表中国伟大音乐传统的乐器。以曾侯乙编钟谱写的当代乐曲,可以作为21世纪中国的象征呈现在国际舞台上。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擂鼓墩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万多件青铜器、漆木器、金玉器。十二律俱全的编钟、尊盘、九鼎八簋、《二十八宿图》衣箱、十六节龙凤纹玉佩为代表的精美文物震惊世界。曾侯乙墓发掘和整理、研究过程中,谭维四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与来自音乐、古文字、科学技术史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紧密合作,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今年是曾侯乙墓发掘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曾国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成果丰硕。与此同时,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特别是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不断推进。擂鼓墩二号墓、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文峰塔等曾国墓地、遗址的发现,引起学界极大关注,曾国研究新作迭出,方兴未艾。“曾随之谜”逐步被揭开,曾国的族姓疆域、始封情况,曾侯世系、曾楚关系也日渐清晰。这些重大考古发现证明,曾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一度是名副其实的“汉东大国”,对于江汉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南方青铜时代的政治版图、文化面貌有着重大影响。曾国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的课题。出土40年间,作为来自“孔子时期的声音”,曾侯乙编钟以其恢宏气势、浑厚音色,不仅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成为文化传播的符号和对外交流的桥梁。(肖璐欣 孙夏)(责编:关喜艳、张隽)
 纪他
纪他201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春秋曾国贵族墓地上榜
原标题:201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随州春秋曾国贵族墓地上榜来源:楚天都市报曾夫人渔墓出土带铭文的铜鬲曾公求墓车坑出土神人驭龙双通车构件曾公求墓出土铜器曾公求墓出土编钟□楚天都市报记者 戎钰“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来的100年。”这句考古界的名言,既阐明了考古学的价值,也道出了考古学的魅力。昨日下午,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揭晓,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上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度评选,是中国考古界最高奖项,被誉为“考古界的奥斯卡”,自1990年启动以来,我省先后有11个项目获此殊荣。本届考古最高奖这样评出今年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30周年,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评委会首次采取网络会议形式,进行“20进10”终评会。5月1日至5日,入围终评的20个考古项目的负责人,轮流进入网络直播间,介绍各自的考古项目情况。全国网友可以与21位专业评委一起品鉴精彩讲解,见证中国考古界最高奖项的首次“云PK”。这是中国考古评选史上的一次创新,它拉近了考古学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网友除了能像上网络公开课一样了解20个考古项目的“尖板眼”,还能在直播中听到评委们的提问,请项目负责人回答“如何应对盗墓”等有趣问题。最终,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成功实现“20进10”,与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等,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发现填补曾国考古空白枣树林墓地位于随州市曾都区文峰社区。201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博物馆、曾都区考古队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勘探发现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考古发掘。该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长江告诉楚天都市报记者,枣树林墓地处春秋中晚期,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为东西向。墓地按曾侯及其夫人墓、高等级贵族墓和低等级贵族墓,可分为5座“甲”字形大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为三组,由北向南排列。三组大墓的墓主人身份,通过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得以确认,分别是曾公求及其夫人渔、曾侯宝及其夫人芈加、曾侯得。这是首次明确发现曾侯夫妇合葬墓。这三组大墓是棺椁结构和器物组合等保存最好的春秋中期诸侯级墓葬,填补了曾国考古不见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有助于完善曾国世系及研究春秋中期诸侯墓葬。随葬器物中,年代较早的形制与周原地区相近,较晚的则有了明显的楚文化风格。这说明在春秋中期,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转变,为探讨曾、楚、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对研究春秋中期曾国乃至周文化体系青铜礼器的变革、构建南方青铜文明意义巨大。6000字铭文解“曾随之谜”郭长江介绍,枣树林墓地共出土青铜器2000余件,其中400多件礼乐器上共刻有铭文近6000字,是迄今考古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铭文资料,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三位曾侯及曾侯宝夫人芈加墓均出土了编钟,其中芈加墓是春秋时期曾国考古中唯一出土编钟的夫人墓,足见其昔日的威仪和权势。从芈加墓出土的铭文可知,曾侯宝离世后,芈加曾直接统治曾国。这段历史给了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芈加墓出土的铜缶上,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楚王嫁女芈加入随的嫁妆)。芈加是曾侯夫人,楚国却说将她嫁到了随国,这充分证明曾国即为随国,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曾随之谜”由此画上了句号。同时,芈加墓出土的编钟铭文中,还出现了“帅禹之堵”“以長辝夏”,这是首次经科学考古发掘在春秋时期青铜器上发现“禹”“夏”铭文,说明当时周人对“禹”和“夏”的共同认知,为研究曾国地望、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信立祥认为,枣树林墓地是曾国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它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了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湖北考古成绩单非常亮眼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度评选,是中国考古界最高奖项,被誉为“考古界的奥斯卡”。自1990年首届评选以来,我省已有郧县人头骨化石、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等11个项目获此殊荣。湖北考古,成果斐然。作为一个文化大省、文物大省,湖北拥有大量的文化遗存,地上、地下文物资源丰富,考古项目众多,取得的成绩也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表示,近年来,湖北考古界围绕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点研究项目“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对距今约5000年的沙洋城河遗址、距今约4500年的天门石家河遗址等考古项目开展研究,频有重大发现。考古研究证明,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一直没有缺环,且具备相当的发展水平,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来源:楚天都市报
 九天
九天填补曾国考古不见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湖北这个考古项目入选“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长江日报-长江网1月10日讯10日,2019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揭晓,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入选,出土大批西汉简牍的荆州胡家草场墓地获入围奖。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发现三组侯级墓葬,填补了曾国考古不见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与近年我省不断发现的曾国高等级墓地一起,串联起曾国从西周早期立国到战国中期被并入楚国的历史脉络,为名不见经传的曾国写就一部“曾世家”。三组大墓墓主人身份均有成组的铭文青铜器可以确认,分别为曾公求及其夫人渔、曾侯宝及其夫人芈加、曾侯得。出土青铜器铭文字数众多,近6000字,特别是发现了 “禹”“夏”铭文,说明当时的周人已经比较普遍地认同关于夏、大禹的历史,为研究曾国地望、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材料。荆州胡家草场墓地出土简牍4642枚,为我国汉代单座墓葬出土简牍数量之最,内容分为岁纪、法律文献、日书、医方、簿籍等,在战国秦汉史、天文历法、法律制度、社会生活、中医药、文献学等方面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岁纪”堪称一部史书,一年一简,记叙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共计143年的国家大事。法律文献简是目前数量最多、体系最完备的西汉律典范本。此前,这两个考古项目同时入围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1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中国考古新发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始创于2002年,论坛上揭晓的年度考古新发现,历来被学界简称为“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因专业性强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自2002年以来,湖北有6个项目入选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枣阳九连墩墓地(2002年)、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2011年)、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2013年)、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2016年)、京山苏家垄周代遗址(2017年)、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2018年),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记者冯爱华 陆涛 通讯员省文旅)【编辑:张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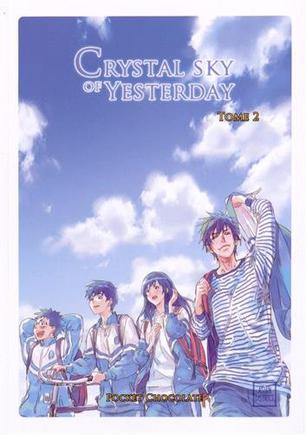 葛藟
葛藟湖北首次大规模展出曾国遗址近10年出土文物精品
曾伯克父鼎,春秋早期,上腹饰重环纹,其下有一周凸棱,下腹部素面无纹。湖北省文旅厅供图中新网武汉9月12日电 (梁婷 邢君成)“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12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这是湖北省博物馆恢复开馆以来举办的第一个线下特展,曾国遗址近10年来出土文物精品首次大规模展出。特别是去年从日本成功追索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器群首次在京外展出。自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被发现后,曾国考古不断取得新进展。近年来,2011年以来随州叶家山、随州文峰塔、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随州枣树林等曾国考古发现连续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中国考古新发现”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之下,丰富而精美的出土文物,揭示了未为史书所载的曾国七百余年的历史。曾伯克父盨,春秋早期,盨是盛放黍、稷、稻等饭食的器具,流行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已罕见。湖北省文旅厅供图此次展览精选了叶家山、苏家垄、文峰塔等重要曾国遗址出土青铜器,共分“始封江汉”“汉东大国”“左右楚王”“华章重现”四个单元,呈现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的曾国青铜文化面貌。曾国是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至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始祖为“南公”,可与齐、晋、鲁等大国并列于《史记》中的“世家”,与文献中的“随国”为一国两名。曾国立国七百余年,经历了从王室藩屏到楚国盟友的转变过程,有着深厚的礼乐文明积淀,是中国考古发现中世系最完整、时代跨度最长的两周诸侯国,为研究中国先秦青铜文化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楚王媵随仲芈加鼎,春秋中期,铭文证明此鼎是楚王为嫁到随国的女子芈加所作,这件罕见“随”字铭文铜器,成为曾随一国两名的铁证。湖北省文旅厅供图此次展览中,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展出了2019年从日本追索回来“曾伯克父”青铜器群。这是中国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易、通过跨国追索回归祖国的价值最高的一批文物。“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组合完整,制作精美,铭文丰富,为书写曾国历史补充了重要的新佐证,填补了出土曾国文物的重要缺环。曾仲斿父壶,春秋早期,壶身饰三周环带纹,环带纹装饰虽也为春秋早期所流行,但一般施加在圆壶上,作为方壶装饰较为罕见。湖北省文旅厅供图“曾伯克父”青铜器群有1鼎、1甗、1簋、2盨、2壶、1霝,共计8件,保存较好,器上均有器主名及“甗”“盨”“霝”等器物的自名,十分珍贵。铭文显示这组青铜器作器者应为同一人,系“曾伯克父甘娄”,“曾”为国名,排行“伯”,字“克父”,“甘娄”为其名。形制、纹饰和铭文等特征契合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的时代风格,据学者推测可能出自湖北随枣走廊一带的曾国墓葬。“曾伯克父”青铜器群补充和印证了之前曾国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现,为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礼乐制度和曾国宗法世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对青铜器的断代与铸造工艺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完)
 陶潜
陶潜湖北连续5年入选国家级考古新发现,苏家垄或为曾国都城
长江日报讯(记者万建辉)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16日揭晓,湖北省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入选。这项评选与“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是考古领域两大国家级权威评选,在业界享有较高声誉。长江日报记者注意到,自2013年起,湖北是全国唯一一个连续5年都有考古新发现入选两大评选的地方。其中,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2016年同时入选上述两大评选。“中国考古新发现”评选由中国社科院主办,每年评选6个项目;“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考古学会等举办,始于1990年。近5年湖北入选两大评选的考古项目分别是: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2013年)、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2014年)、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2015年)、天门石家河遗址(2016年)、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2017年)。17日晚,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湖北连续5年入选国家级考古新发现评选不是偶然的。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在青铜时代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交汇地段,是研究国家文明进程的重要区域和敏感地带。湖北5个入选国家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遗址,多处于西周时期,当时北方中原王朝铜矿少,湖北大冶、安徽、江西等长江流域铜矿多,在青铜时代,湖北部分考古遗址有青铜转运站和冶炼点的特征。湖北入选项目为何在这5年集中“爆发”?方勤表示,这首先与湖北考古工作的课题意识比较强有关。去年,湖北列入了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点课题——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国家课题,这个课题有湖南、江西、安徽参加,由湖北牵头,研究范围从长江文明的史前起源到融入中原王朝。近五年湖北入选国家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都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范围内。此外,也与湖北近些年考古发掘工作引入新的科技手段,与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紧密合作,工作做得扎实深入有关。链接>>>苏家垄有可能是曾国都城苏家垄周代遗址位于京山县坪坝镇,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方勤介绍,考古发掘了一批曾国高等级墓葬,还发现了与墓地同期的大规模遗址及冶铜遗存,目前已发现3座炼铜炉,具体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地点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车的车马坑,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这里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据介绍,在苏家垄遗址,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目前已清理墓葬106座、车马坑2座,墓葬保存完好,已发现青铜礼器500余件。苏家垄遗址出土的1000余件青铜器中,有铭文的多达50余件。其中,两座大型墓出土4件“曾伯桼”壶,单壶铭文达160字,共640字,极其罕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说,近些年关于曾国的重大考古发现颇多,如随州擂鼓墩古墓群、枣阳郭家庙墓地、随州文峰塔墓地等,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曾国较高的文化水平。(记者万建辉)
 鬼虐杀
鬼虐杀湖北大规模展出曾国遗址出土文物精品
原标题:湖北首次大规模展出曾国遗址近10年出土文物精品来源:中国新闻网中新网武汉9月12日电 (梁婷 邢君成)“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12日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这是湖北省博物馆恢复开馆以来举办的第一个线下特展,曾国遗址近10年来出土文物精品首次大规模展出。特别是去年从日本成功追索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器群首次在京外展出。自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被发现后,曾国考古不断取得新进展。近年来,2011年以来随州叶家山、随州文峰塔、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随州枣树林等曾国考古发现连续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中国考古新发现”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之下,丰富而精美的出土文物,揭示了未为史书所载的曾国七百余年的历史。曾伯克父盨,春秋早期,盨是盛放黍、稷、稻等饭食的器具,流行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已罕见。湖北省文旅厅供图此次展览精选了叶家山、苏家垄、文峰塔等重要曾国遗址出土青铜器,共分“始封江汉”“汉东大国”“左右楚王”“华章重现”四个单元,呈现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的曾国青铜文化面貌。曾国是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至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始祖为“南公”,可与齐、晋、鲁等大国并列于《史记》中的“世家”,与文献中的“随国”为一国两名。曾国立国七百余年,经历了从王室藩屏到楚国盟友的转变过程,有着深厚的礼乐文明积淀,是中国考古发现中世系最完整、时代跨度最长的两周诸侯国,为研究中国先秦青铜文化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楚王媵随仲芈加鼎,春秋中期,铭文证明此鼎是楚王为嫁到随国的女子芈加所作,这件罕见“随”字铭文铜器,成为曾随一国两名的铁证。湖北省文旅厅供图此次展览中,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展出了2019年从日本追索回来“曾伯克父”青铜器群。这是中国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易、通过跨国追索回归祖国的价值最高的一批文物。“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组合完整,制作精美,铭文丰富,为书写曾国历史补充了重要的新佐证,填补了出土曾国文物的重要缺环。曾仲斿父壶,春秋早期,壶身饰三周环带纹,环带纹装饰虽也为春秋早期所流行,但一般施加在圆壶上,作为方壶装饰较为罕见。湖北省文旅厅供图“曾伯克父”青铜器群有1鼎、1甗、1簋、2盨、2壶、1霝,共计8件,保存较好,器上均有器主名及“甗”“盨”“霝”等器物的自名,十分珍贵。铭文显示这组青铜器作器者应为同一人,系“曾伯克父甘娄”,“曾”为国名,排行“伯”,字“克父”,“甘娄”为其名。形制、纹饰和铭文等特征契合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的时代风格,据学者推测可能出自湖北随枣走廊一带的曾国墓葬。“曾伯克父”青铜器群补充和印证了之前曾国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现,为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礼乐制度和曾国宗法世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对青铜器的断代与铸造工艺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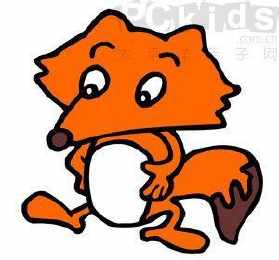 间隔年
间隔年湖北,又有重大发现!
提到曾侯乙湖北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迷人的编钟乐舞自1978年曾侯乙墓在随州被发掘以来各种考古发现震惊世界但,曾侯乙不止于编钟他背后的曾国远超你的想象在湖北,关于曾国又有重大发现!枣树林墓地考古现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今天(6日)上午,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考古发掘情况,两组曾国国君以及夫人并穴合葬墓的发掘,是曾国考古乃至两周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填补了春秋中期曾国考古的空白。随州枣树林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郭长江介绍情况原来,芈夫人是曾国“武则天”▲▲▲目前,已出土青铜器千余件,部分青铜器上有铭文,铭文主要有“曾公”“曾”“曾叔”“曾侯”“曾夫人”“曾子”“曾孙”“曾叔孙”等。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尤其是曾侯宝及随仲芈加、曾公求及曾夫人渔两对曾国国君级别的夫妇合葬墓的发现确认。曾候宝墓M168出土铜鼎以及编钟铭文提示器主为“曾侯宝“,M169出土铜缶以及编钟铭文揭示器主为“芈加”。这两座墓为曾国诸侯“曾侯宝”及其夫人“芈加”并穴合葬墓。两座墓南北并向排列,M169略小于M168。M190出土铜壶、铜鼎以及编钟铭文显示器主为“曾公求”,M191出土铜鼎以及铜鬲显示器主为“曾夫人渔”。曾候宝墓随葬品值得一提的是,曾侯宝娶的这位楚国芈夫人并不简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长江介绍,芈加墓里诸多器物上的铭文表明,曾侯宝死后,芈加曾直接统治曾国,她以“小子”(称宗亲中男性同辈年轻者及下辈)自称,俨然女诸侯自居。芈加墓随葬器物芈加墓是春秋时期曾国考古中唯一出土编钟的夫人墓,由此可见夫人威仪及权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直言,“当时的女性很厉害,有晋姜、有芈加、有芈月,老公死得早,她们就能掌权执政。”枣树林墓地考古现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一件嫁妆终结“曾随之谜”▲▲▲1978年,随州曾侯乙的发掘曾引出了一个令考古界和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今随州之地——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随国,为何频频出土的又是曾国文物?曾、随到底是何关系?对此,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曾国即随国。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生前就曾撰文认为,考古发现中的曾国就是古文献的随国,曾、随是一国两名。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曾”即是“曾”,“随”即是“随”,二者不可混同。不过,此次曾侯夫人芈加墓(M169)出土的铜缶上的一句铭文提供了关键信息——“楚王媵随仲芈加”(大意为楚王嫁女入随的陪嫁)。这件铜缶是楚王嫁女入随的嫁妆。前面提到,“芈加”是曾侯夫人,铭文上楚国又称曾为“随”,说明曾随一家,基本解决学术界争论不已的“曾随之谜”问题。曾国祖先是……▲▲▲芈加墓出土的编钟铭文还透露了关于曾国祖先的信息。铭文中出现的“余文王之孙”可能涉及曾国确定是文王之后而非武王之后的新材料,以及该铭文与之前曾侯與墓铭文“稷之玄孙”对照,可以从曾国出土铭文记载的角度,辨析周代从“稷”到“文”、“武”的世系。为周王朝的世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出土文献,也为研究曾国始封以及“曾”的族属提供了新材料。曾公求墓出土铜鼎、壶、簠上均有发现“曾公求”铭文,并在方壶壶盖可见“皇祖南公”,进一步确认了曾国为南公之后。周王朝在周初开疆拓土时曾大规模分封诸侯,据此前随州文峰塔墓地出土的铭文器显示,南公因辅助文、武王,帮助周王朝抚定天下,被分封于周之南土,即为曾国。这里的南公就是西周重臣南宫适。看过《封神演义》的,都知道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故事,其实,里面还提到了周文王赴朝歌时,曾命“外事托于南宫适”。至于曾国与楚国的关系,郭长江解读认为,曾是周姬姓嫡系,代表中央统治南方,楚为当地政权,与中央嫡系互动频繁(有数位曾侯娶芈姓夫人),期间势力此消彼涨,但文明却趋于共生融合。他们和曾侯乙啥关系?▲▲▲说完曾国,可能有人要问,曾候宝、曾公求和曾侯乙是啥关系?根据考古发现,曾侯乙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候宝、曾公求的墓属于春秋中期,至少可以知道他们两位是曾侯乙的祖辈。曾侯戉阝铜鼎此外,据湖北日报今年2月报道,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中,就出土数量不少的曾侯與、曾侯戉阝铜戈,说明这两人年代比曾侯乙早,应为曾侯乙的先辈。他依据墓葬的排列顺序,进一步确认三位曾侯的排序应是曾侯與、曾侯戉阝、曾侯乙。另有专家认为,曾侯與、曾侯戉阝、曾侯乙为祖孙三代。当然,曾国的国君远不止这些……已“挖”出21位国君▲▲▲在列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关于曾国的历史记载很少,以至于这个国家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枣树林墓地考古现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6日上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通过数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了曾国13位带有私名的曾侯:曾侯谏、曾侯犺、曾侯羊白、曾侯仲子游父、曾穆侯、曾公求、曾侯宝、曾侯得、曾侯昃、曾侯與、曾侯钺、曾侯乙、曾侯丙。极大完善了曾国历史的进程,填补了两周史上关于曾记载缺失的空白。最早的曾侯谏是西周早期,最晚的曾侯丙是战国中期。方勤说,包括白生、曾伯漆、曾伯琦等没有明确带“侯”字但是曾侯级别的8位,曾国有名字的国君目前发现有21位。而近年来,围绕曾侯乙墓及曾国考古引发的众多学术热点课题,湖北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苏家垄等曾国墓地考古项目,接连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除了对曾国的发掘湖北近年取得的众多重要考古发现也举世瞩目限于篇幅只能列举一二2019年5月,国家文物局举办的“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湖北荆州胡家草场M12出土3000多枚西汉简牍,内容包括历谱、编年纪、律令、病方和遣册,为佐证西周初年重大史实,研究楚国历史和政治军事思想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荆州胡家草场M12发掘场景2018年3月,联合考古队开始对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王家塝墓地开展勘探、发掘。发现墓葬218座,新石器时代墓葬212座,其余6座为明清时期墓葬,其中5座10平方米以上的墓葬。荆门城河遗址新发现的王家塝墓地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该遗址入选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202号同穴合葬墓2017年4月,天门市成立石家河遗址管理处。石家河遗址先后入选“201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推动了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和中华文明起源重大课题的研究。石家河遗址万福垴遗址位于宜昌沮漳河下游以西五六十公里,2012年该遗址出土了12件编钟及1件铜鼎,其中一件编钟有“楚季”铭文,2015年至2017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万福垴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古,发掘了一批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的遗物。万福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探索研究楚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突破口。万福垴遗址发掘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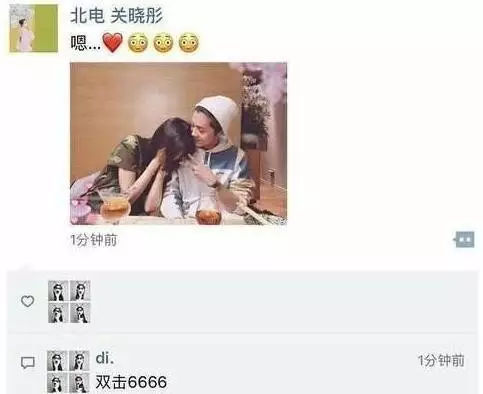 举之无上
举之无上新的切入点!曾国青铜器上的曾国历史
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中还发现有兵器剑、戈、锡、钺、兽面形面具等。车马器有弓形器、节约、銮铃、衔、辖等。工具有削、锛等。兵器中的龙形钺和兽面形面具非常的精美。网络配图龙形钺出土于六十五号墓。器物造型为龙体弯曲呈D形。龙背脊作刃。龙眼臣形,卷鼻,内卷上唇。嘴作圆柱与尾部圆銎对应。通长26.7、宽18厘米。重710克。龙形钺兽面形面具出土于六十五号墓。扁体弧面兽面形。双角上翘,似牛角。双眼有孔。通高21.7、宽21.4厘米。重410克。兽面形面具可以看出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品类齐全,造型精致,纹饰也非常的精美。而铭文所表现出的信息则更为重要,可以肯定的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西周考古发现。网络配图看似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可以说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但又可以肯定的说,所有的考古发现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网络配图无论是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的发现,还是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谏墓的发现,都绝非是一个个孤立的考古发现。因为曾侯谏、曾侯乙和曾国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网络配图在曾侯乙墓和曾侯谏被发现之前,在环大洪山及随枣走廊地区已经有较多曾国青铜器的发现,表明在这一地区有一个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曾国存在。网络配图曾侯乙墓的发现,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曾国历史进程中最辉煌的一个截面。而曾侯谏墓的发现,又为研究曾国历史文化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简单通俗地讲,为研究曾国历史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网络配图众所周知的是曾侯谏、曾侯乙的身份很明确,都是曾国的国君,应该将他们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研究。网络配图曾国是大汉东青铜文化带(青铜文化圈)中的一支,大汉东青铜文化带是属于周王朝的南土的一部分。严格意义上讲,也是周文化的一个旁支,是周王朝统治的南部边缘地区的代表。完全有必要对这一地区商周时期的历史和考古发现状况进行一下简要的回顾。网络配图
 不文骚
不文骚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开幕 8件珍贵海归文物返鄂!
2020年9月12日,“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在湖北省博物馆开幕。此次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在湖北博物馆展出,是国家文物局助力湖北疫后重振、支持湖北文物工作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遴选汇集了曾国遗址近10年来出土的丰富而精美文物,是曾国出土文物精品首次大规模在疫后展出,全面呈现了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的曾国青铜文化面貌。特别是去年从日本成功追索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参展,为展览的高水平举办给予了有力支撑。本次特展,既能够完整地反映曾国历史文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呈现高水平的文化大餐,更能够发挥宣传教育作用,使海内外观众更加广泛关注流失海外文物追索,为以后更多的成功追索凝聚更多社会共识和有生力量。期待湖北文博战线充分发挥文物事业提振精神、凝聚力量、引领发展的特殊作用,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简介自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被发现后,曾国考古不断取得新进展。近年来,2011年以来随州叶家山、随州文峰塔、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随州枣树林等曾国考古发现连续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中国考古新发现”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之下,丰富而精美的出土文物,揭示了未为史书所载的曾国七百余年的历史。展览精选了叶家山、苏家垄、文峰塔等重要曾国遗址出土青铜器,共分“始封江汉”、“汉东大国”、“左右楚王”、“华章重现”四个单元,呈现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的曾国青铜文化面貌。曾国是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至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始祖为“南公”,可与齐、晋、鲁等大国并列于《史记》中的“世家”,与文献中的“随国”为一国两名。曾国立国七百余年,经历了从王室藩屏到楚国盟友的转变过程,有着深厚的礼乐文明积淀,是我国考古发现中世系最完整、时代跨度最长的两周诸侯国,为研究我国先秦青铜文化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是湖北省博物馆开放后第一个大型文物特展,是发挥文旅行业带动作用,放大文旅业消费效能,助力疫后重振和经济复苏的具体举措。此次展览中,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展出了2019年我国政府从日本追索回来“曾伯克父”青铜器群。这是中国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易、通过跨国追索回归祖国的价值最高的一批文物。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组合完整,制作精美,铭文丰富,为书写曾国历史补充了重要的新佐证,既填补了出土曾国文物的重要缺环,又彰显了我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决心和能力。曾伯克父青铜器群有鼎1、甗1、簋1、盨2、壶2、霝1,共计8件,保存较好,器上均有器主名及“甗”、“盨”、“霝”等器物的自名,十分珍贵。铭文显示这组青铜器作器者应为同一人,系“曾伯克父甘娄”,“曾”为国名,排行“伯”,字“克父”,“甘娄”为其名。形制、纹饰和铭文等特征契合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的时代风格,据学者推测可能出自湖北随枣走廊一带的曾国墓葬。“曾伯克父”青铜器群补充和印证了之前曾国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现,为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礼乐制度和曾国宗法世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对青铜器的断代与铸造工艺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