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吾道者
失吾道者北大中文系2020拟录取推免研究生39人,其中本校学生34人!
10月18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公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2020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从公布的名单来看202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接收了推免的硕士研究生26人,直博研究生13人。推免的硕士研究生就是三年制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直博生就是直接本科毕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一般为五年,达到毕业条件直接授予博士学位,二者都是推免的研究生。不过,从生源学校来看,大部分都是本校学生,共计有34人,其中硕士22人,直博士12人。在北大中文系拟录取推荐免试直博生中,只有1人来自校外,这位同学来自武汉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其余的12人都是北京大学生源。在北大中文系拟录取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中只有4人来自校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四川大学各1人,其余的22人也都全部来自北大本校。可以看出,外校生源要想推免进入北大中文系读研非常困难。从北大中文系2020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来看,硕士研究生计划招生46人,接收硕士研究生推免人数23人,最后还有统考名额23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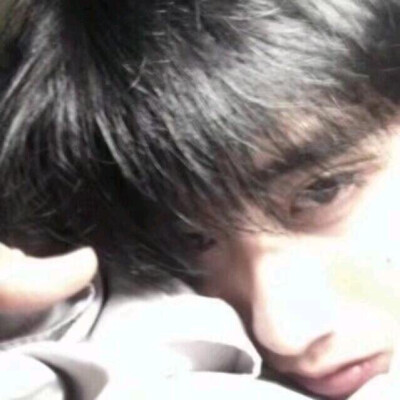 有客
有客北京大学中文系公布2020年推免生拟录取名单,北大一枝独秀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日前已正式公布了拟录取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公示名单,2020年北大中文系共计拟录取26人,正式名单如下:拟录取的26人中,其中22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占据了拟录取的84.6%,其余入选的四人分别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可以看出来想要获得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保送,整体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在此次录取的学生中,主要的录取专业方向有8个,分别是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八个方向。
 萃乎芒乎
萃乎芒乎北大中文系2020年拟录取推免生39人,接收本系32人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中文系公示:中文系2020年拟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共39人。其中硕士26人、直博生13人,来自6所高校。详情如下:拟接收39名推免生中,87%来自北大,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院系录取本校推免生比例(33%左右)。录取北大本校2020届推免生共34人。录取本系32人。录取元培1人;录取信科1人,本科专业是计算机,录取方向是汉语言文学直博。名单如下:附录:中文系本科生保研情况2016级本科生保研公示共84人。2020届已知保研中文系32人、法学院1人。2015级保研62人。2019届保研北大43人,保研中文系33人,法学院4人,教育学院3人,经院、数院?、新传各1人。其余19人去向未知。2014级保研79人。2018届国内升学54人,至少25人放弃了保研。继续留在北大深造45人:中文系31人,法学院6人,深圳3人……9人去清华大学、国科大、武大等。
 绝命岭
绝命岭北大研究生院2020拟录取推免生2757名生,生源高校149所
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大学(本部)预计招收硕士研究生4849人,其中非全日制研究生计划招生1685人。全日制总计划人数为3164人,其中计划招收硕士推免生1585人,统考1579人。近日,北大研究生院发布2020年(本部)拟录取推免生公示,实际拟录取推免生2757人。其中,硕士研究生1660人、直博生1097人。北大38个学院,2020年拟录取推免生情况如下:近3年来,北大研究生院推免生拟录取人数逐年递减,情况如下:2020年2757名推免生,分别来自于149所高校。情况如下:其中,录取北京大学2020届本科生958人。top1,录取武汉大学91人;top1,录取南开大学81人;top1,录取山东大学76人;top1,录取中山大学75人;超过50人的大学有:北师大、厦大、人大、南大、吉大。生源高校按人数排序如下:
 驺忌
驺忌北大中文系庆建系110周年 百余年培养英才上万名
新京报讯(记者 杨菲菲)鲁迅、周作人、刘半农、胡适、沈从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名师大家辈出。11月22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93岁高龄的唐作藩等十几位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来到现场,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也对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期待。北大中文系老教授唐作藩讲述自己与北大的故事。110年培养1.3万余名学子自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设立“中国文门”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已有百余年。“1910年我们仅招收了38名本科生。而今年,我们招生的本科生就有204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陈晓明表示,育人是大学的根本,北大中文系110年来所培养的诸多人才,尤其应该成为值得珍视的财富。数据显示,110年来,北大中文系培养了全日制本科生9073人,专科生675人,硕士研究生2774人,博士研究生1473人,共计13995人,其中外国及台港澳学生1875人。此外,还接收博士后79人,国外访问学者及进步教师1813人,国内访问学者及进修教师2212人。人才培养的成果与北大中文系完善的学科设置密切相关。记者了解到,北大中文系目前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中文系是国内唯一细分并具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留学生)五个中文本科专业的学科院系。北大中文系给到场的十几位老教授献花。93岁老教授回忆与北大的结缘之路“我的梦想就是进北大。”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代表,93岁的唐作藩在发言中回忆了他与北大结缘的故事。唐作藩说,因家境贫穷,在小镇上做小买卖的父亲本想让他长大后也做小买卖,但是因为二叔的一句“还是读书好”,本来在私塾的他在13岁那年到了黄桥镇高小。“校长说,你这么大了不能读一年级了,从五年级开始读吧。结果我第一次考试数学只考了37分,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分数。”唐作藩“坦白”了自己并不漂亮的考试成绩。小学毕业后唐作藩进入了湖南武冈洞庭中学,考北大的梦想越来越清晰,“那会儿北大和清华一起招生,我就想着一定要考上北大,没想到差了几分没考上。”1948年春,唐作藩考到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在1953年7月毕业后留在了语言学系。彼时,因为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合并,此前在岭南大学任职的王力也在中山大学兼任,后来还做了语言学系的系主任。“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建议,集中全国语言学的教师培养语言学的人才。没想到1954年,王力先生带着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师生一起进入了北大。这样我也有幸实现了我的理想。”唐作藩“调侃”自己,没有经过考试但是成功进入了北京大学。1954年9月,唐作藩跟随王力先生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汉语教研室的助教兼秘书,跟随王力先生学习汉语史与音韵学。在此后的66年里,唐作藩在北大中文系从事音韵学、汉语史和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续推进中文系三大平台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站在110年的新起点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将如何发展?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提出了对中文系发展的期待。“首先将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继承传统文化肩负时代使命,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郝平表示,在北大60多个院系中,只有中文系以中国冠名,期待中文人面向国家基础重大研究,继续深入挖掘中国文学、语言、文献的价值内涵,共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郝平表示,北大中文系要引领中国高校文科教育创新发展,在新闻和教育改革实践中,起到模范引领作用。郝平表示,面对新技术、新要求,要探索学术研究的新范式,提升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继续推进中文系三大平台建设,激励跨专业、跨学科的突破性探究。同时要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使课程设置、教学手段适应时代发展特征,培养继往开来引领未来和建设未来的复合型人才。在学术交流、国际影响力等领域,郝平提出,希望北大中文系坚持开放包容、融通中外,“一方面,建设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人才和知识在国际社会更广泛地流动,增强交流互进,在国际坐标中不断激发学术创新潜力,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注重用中国理论阐释和解决问题,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记者 杨菲菲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李铭
 君子剑
君子剑大学研究生院排名出炉,清华北大竟然不是第一名
2020年全国高校研究生院竞争力排名出炉,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排名前三。请关注我了解更多教育资讯,感谢您的支持。
 表诠
表诠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被批“崇洋媚外”?“无厘头批判”何时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即将惹上“麻烦”。昨天,在网络上有一篇叫做《北大教授发表不当言论,这样的学者,能留在大学校园吗?》的文章引起网友们的关注。但是没过多久,这篇文章题目又被改为《北大教授发表不正当言论,讽刺国家,网友:清理出教师队伍》。北大教授被质疑“三观不正”在这篇文章里面,作者指责孔庆东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竟然发表“三观不正”的不当言论,质疑“这样的学者,还能够留在大学校园吗?”,最后作何还提议将这样的发表不当言论的教授“清理出教师的队伍”。作者认为孔庆东教授“三观不正”的证据,即是5月19日孔庆东教授在网络账号上发布的一段留言,该条留言内容为“美国是个很适合旅游的国家,地大物博,气象万千,特别是你戴不戴罩罩,都没有那么多卑鄙无耻的道德闲汉,伸长了鸭脖子来管。”这段话似乎“有所指”,但又确实“未明指”。因此,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孔庆东教授的确好像又说出了一段“不当言论”,又可以被人们抓出来“批斗”好一阵子了!“无厘头批判”这篇文章甚至明确指出孔庆东教授“从骨子里都是崇洋媚外”,作者故意营造这种“节奏感”,让很多人加入到对孔庆东教授的“无厘头批判”当中。所谓“无厘头批判”,就是指部分人捕风捉影地批判某些人的言行,加上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让不知真相的群众在这部分人的带领之下,对批判目标进行狂轰滥炸式的猛烈批判。批判者一知半解地加以批判,而被批评者则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指责。我将这种“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思维,称为“无厘头批判”。如果仅仅从“你戴不戴罩罩,都没有那么多卑鄙无耻的道德闲汉,伸长了鸭脖子来管”这句话就判定孔庆东教授“三观不正”“崇洋媚外”的话,那么这就太可怕了,生活中有太多说这类似话的人,难道我们的周围全是些这样“三观不正”“崇洋媚外”的人吗?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也太令人感到可怕了!孔庆东,何许人也?在这里我们对他做一个简单介绍:孔庆东,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非常有名的一位教授;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是孔子的第73代传人。孔庆东教授所讲的学术涉及众多领域,但是他所主攻的现当代文学领域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个内容是:一个是讲金庸,一个讲鲁迅。在讲金庸的时候,他提到金庸作为通俗作家竟未能被文学史所认可,这是极为不合理的现象;金庸的武侠小说,无论是从文学主题、小说语言,还是人物设计、写作能力方面,都当之无愧地应该进入文学正史当中。孔庆东教授,是第一个深入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教授,学生们非常喜欢听他讲金庸的武侠小说研究。在鲁迅研究方面,孔庆东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将鲁迅精神传递下去的责任。孔庆东是钱理群教授的学生,而钱理群又是鲁迅研究影响最大、最权威的教授。孔庆东承接了钱理群教授的思想继续研究鲁迅,他一直以来都反对将鲁迅作品从课文中删除。“三观不正”和“表达不同意见”两者应该区分出来从种种迹象来看,孔庆东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深入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受鲁迅影响很大,从“卑鄙无耻的道德闲汉”这几个词中就可以见出鲁迅思想的影子。但是,这样一位教授,仅仅因为一句话就被指责为“三观不正”,然后又被带入大家都一致反对“崇洋媚外”的节奏,被狠狠的批判,甚至被要求“清理出教师队伍”,这的确有点匪夷所思!客观地讲,我们不反对“对有罪之人”进行批判和定罪,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捍卫“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人们的“不同意见表达权”一旦被彻底否定,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是千篇一律的“说谎者”!网友态度:生活中,也确实不乏真正的“崇洋媚外”者,但是我们对这些人鉴别和批判,绝不能停留在一两句心情说说上,应该纵观其言其行,拿出真实确凿的证据,令人无可辩驳。我们应该反对捕风捉影的质疑和无厘头的批判,因为这种只有“头脑发热”而没有“理性思考”的批判,只会更容易被人利用,更容易撕裂我们这个社会本来的文化认同!对此,有网友表示“坚决彻底的把教师中的渣人清理干净,吃着国家和人民的,喝着国家和人民的,还要卖国求荣,吃里扒外!成何体统?收拾干净!”但也有网友表示支持教授,“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为啥就只能一种声音?”“他的语言里感觉不到暗讽国家,他只是暗讽一些过敏的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网友们,你们怎么看待这事儿呢?【特别声明】:本平台原创文章,未经授权,谢绝公众号商业转载!
 班车末
班车末北大中文系历经的七次重大变革
涨知识:关于北大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七次变革。第一次是1919年废门改系,原文科国文门改为中国文学系;第二次是1925年课程调整,出台“分科专修制”,为一年级设定共同必修课,二年级以上“分类选修”,分类选修的科目实际对应着语言文字、文学研究、古籍整理3个专业领域;第三次是抗战西南联大时期,清华与北大两校中文系联合,强化基础性训练,很好地发挥了两校的优势;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北大中文系达到一个鼎盛;第五次是“文革”时期,开门办学,当时的种种运动导致系所元气大伤;第六次是八十年代学科复兴,教学正常化,中文系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框架日趋完善;第七次是2000年以来,中文系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科研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奠定了现在中文系教学的基本格局。1918年建成的红楼,中文系址1918年建成的沙滩红楼用作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文科教室,是北大文学院所在地。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纪念馆。2.诞生之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文科的中国文学门。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中国文学门”正式作为文科的一个教学建制。这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系现址那么,北大中文系著名的师生你知道的有哪些呢?部分内容引自北大温儒敏教授讲座: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与学术传统
 夫灵公也
夫灵公也北大中文系,该醒醒了!一位老校友的中肯建议
(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华侨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本文为2012年孙绍振教授纪念吴小如教授的文章。)原载《南方周末》。近日读友人赠《学者吴小如》,54年前聆听吴先生的讲课种种印象不时涌上心头。在当时能让他这样一个讲师上中文系的讲台,可以说是某种历史的吊诡。初进北大中文系,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要说讲师、副教授,就是不太知名的教授也只能到新闻专业去上课,一般讲师只能上上辅导课。当然,刚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的朱德熙副教授似乎是个例外。现代汉语本来是中文系大部分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却以他原创的概括、缜密的推理和雄辩的逻辑获得爆棚效应,200人的课堂,去晚了就没有座位,只好靠在墙边暖气管上站着。何其芳先生那时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与吴组缃先生先后开设《红楼梦》专题。吴先生得力于作家创作经验,对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对艺术有独到的分析,而何其芳先生颇有人道主义胸怀,不同意他把薛宝钗分析为“女曹操”,认为她不过是一种家族体制礼教意识的牺牲品,两人同样受到欢迎。一次,我在北大医院排队挂号,护士问前面一人姓名,听到四川口音很重“我叫何其芳”,不免多看几眼。然北大泰斗学富五车者众,善于讲授者寡,加之北大学生眼高,哪怕学术泰斗,讲授不得法,公然打瞌睡者有之,默默自习者有之,递纸条、画漫画者有之。古代汉语本来是魏建功先生开设,但公务繁忙,往往从课堂上被叫出去开会,且到比较关键地方,有茶壶煮饺子,学生替他着急的时候。此课后来改由王力先生开设,先生取西欧人学拉丁文之长,构造了中国古代汉语课程体系,举国传承至今。一代宗师,治学严谨,我听过他的《汉语史》、《汉语诗律学》,但是,语调往往由高到低,余音袅袅,杳不可辩。且第二堂课往往花几分钟订正前堂之误,上午第五六节课要上到12点钟,每每拖课。调皮如我,遂将随身携带的搪瓷饭碗从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滚下,先生愕然问何事,答曰“饭碗肚子饿了”,先生乃恍然而笑。王瑶先生自然是公认的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然一口山西腔,不知为何给人以口中含有热豆腐、口头赶不上思想之感。系主任杨晦教授德高望重,讲中国文艺思想史,出入经史、小学、钟鼎艺术,其广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灵光,一语惊人,令人终生难忘。其批评郭绍虞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曰: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修改,还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实实在在的资料。其批评巴金《家》、《春》、《秋》好在激情,然如“中学生作文”,如果把三部并成一部就好。但是,他讲了半学期,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有打开,学生也无法记笔记,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讲到孔夫子,在学生的抗议下,不得不草草停课。宋元文学权威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乃请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讲宋元戏曲,王先生舍长用短,以毛泽东《矛盾论》中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墙头马上》、《陈州放粮》,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保持着对客人的礼貌,纷纷抢占最后数排以便自由阅读。那是1958年“大跃进”、“拔白旗”的年代,大字报贴满了文史楼,从学术泰斗到吴小如这样的青年教师,无不被肆意丑化。就在这种情况下,小如先生为我们讲宋代诗文。当时怀着姑妄听之的心情走进课堂。吴先生的姿态,我至今还记得,双手笼在袖子里,眼睛不看学生,给人一种硬着头皮往下讲的感觉。然中气甚足,滔滔不绝,居然是听得下去,接下来几课,还颇感吸引力。我对朋友说,平心而论,这个讲师从学养到口才都相当不错。一些具体分析,显然和以艺术分析见长的林庚先生路数不同,然而明快、果断。至今仍然记得他对陆游晚年的诗的批评是,用写日记的方法写诗,以至出现了“洗脚上床真一快”这样的败笔。“大跃进”运动很快把课堂教学冲垮,下乡劳动有时长达一个月,课上不下去,后来干脆就停课了。我对吴先生印象也就停留在当年粗浅的层次上。彭庆生同学对他评价道:“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20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成功的吴小如’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庆生同学晚我一年毕业,可能系统听过吴先生的课,有权作全面评价,当然,不无偏爱,若论启人心智,和朱德熙先生那种俯视苏联汉学家、放眼世界语言学、深入浅出、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大气魄相比,吴先生应该略逊一筹。不可忽略的是,庆生当年可归入全系攻读最为刻苦者之列,曾经以躲入冬日暂闭之洗澡间抄写刘大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闻名。吴先生能得如此学生的如此评语,当有此生足矣之感。近日吴先生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虽然自谦为“教书匠”,但是,就是在当年,我还是感到了他学养深厚。阅读北大中文系所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感到极大的满足。毕业后不久才知道,这两本资料主要是吴先生执笔通稿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竟然是反右以后留校的一位“左派”告诉我的,他语重心长地警示:这两本资料,尤其是两汉卷,资料过详,原因是执笔者意在“多挣稿费”。这在当时,就给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当然,仅凭此二册,对于先生的学养,所知毕竟有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耄耋之年,居然以“学术警察”形象出现于文坛,对于学界之虚浮硬伤,笔阵横扫,语言凌厉,锋芒毕露,不由得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敬意。现在知道先生的学术著作凡数十种,仅其中《读书丛札》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者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先生均给以高度评价。吴组缃先生认为“吴小如学识渊博,小学功夫与思辨能力兼优”,甚至有“无出其右者”之赞语,哥伦比亚大学权威教授夏志清曾言“凡治中文者当人手一册”。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这位当了30年讲师的“讲师精”,被历史耽误了,人所共知;又有吴组缃、林庚先生推荐其直接提升为教授,应该顺理成章一路绿灯。但是,煌煌北大中文系,居然不能通过,差一点被慧眼识珠的中华书局引进。不可思议的是,吴先生没有走成,居然不是中文系的幡然悔悟,而是学术上颇为权威的历史系周一良和邓广铭教授“三顾茅庐”的“阻挠”,结果是小如先生成了历史系教授。对于这样的荒诞,中文系至今没有感到荒诞,而作为中文系的校友,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但是,痛定思痛,我仍然逼出了一句话:这是耻辱。对这种耻辱的麻木,则是更大的耻辱。在这种耻辱感麻木的背后,我看到一种令人沉重的潜规则。回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系史,这样的潜规则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文系容不下沈从文,把他弄到历史博物馆去当讲解员,这还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1957年驱逐了后来成为唐诗权威的傅璇琮,也可以用他当了右派来辩解。但是,杨天石在五五级当学生的时候,就以学养深厚著称,后来独立开创了蒋介石研究,自成一家,享誉海内外。当年他并不是右派,然而中文系就是不要他,他被分配到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后来靠刻苦治学,辗转多方,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在他获得盛名之后,中文系有没有表现出任何回收的愿望呢?没有。钱理群是学生公推的最受欢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际,就“按规定”退休了。然而,成立语文教学研究所,又挂上了他的大名。可是,有名无实,连开个作文研讨会都没有他的份。从这里,似乎可以归纳出一条定律:这些被驱逐的,本来是可以为北大中文系增光,为北大校徽增加含金量的,而留下的,能为北大争光的当然也许不在少数,但是,靠北大中文系这块牌子为自身增光,从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数。更为不堪的是,还有一些为北大中文系丢丑的,如那些学术投机者。至于一些在学术上长期不下蛋的母鸡,却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对于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当宽容的,从学术体制上说,这就叫做人才的逆向淘汰,打着神圣的旗号,遂使学术素质的整体退化不可避免。当然,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北大中文系,选择学术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杨晦在1962年为吴小如讲话,盛赞他的贡献,其结果是到了1964年在党内遭到两星期的严厉批判。据知情人告,当时骨气奇高的杨先生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1984年严家炎先生为系主任时,一度欲请吴先生回系。然吴先生出于对周一良、邓广铭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谢绝。这样的学术良知,不成潮流,相反,它显得多么微弱。半个世纪多来,幸存下来的学术泰斗先后谢世,北大中文系不但丧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术上那种显赫的优势,而在许多方面呈现衰微的危机,北大中文系这块招牌的含金量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近年报刊上风传钱学森世纪之问,纷纭的讨论至今未能切中肯綮。其原因盖在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如果以吴小如先生为个案作细胞形态分析,则不难看出逆向淘汰的潜规则之所以不可阻挡,具有学术良知者,在行政体制中显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明于此,也许能够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切实地推进一步。这几年北大中文系当道者不乏从内地到港台反复宣扬“大学精神”,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并包”讲上一万遍,如果不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相结合,在危机中还以先觉先知自慰自得,甚至还流露出优越感,其所云无异于欺人之谈,北大中文系沿着九斤老太的逻辑滑行并非绝对不可能。吴小如先生九十高寿,学生们想到了为之祝寿,北大中文系居然毫无感觉,这只能说明那些动不动拿蔡元培来夸夸其谈的人,其大学精神已经酣睡如泥。我作这篇文章,除了有意于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加以深化之外,还有一种出于系友的奢望:把我的母系狠狠地摇醒。(2012年8月24日星期五)更多精彩阅读1、他是咱河北人!这对北大情侣为爱死守大半生,为祖国留下了无尽的文化宝藏!2、吃亏就是占便宜!北大校长毕业典礼上的一席话,点醒很多人
 不言则齐
不言则齐第一次进京!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
丁新伯第一次进京城,是1982年8月底。经过多次高考,终于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那年8月29日,从黄桥坐着汽车到常州,进京城去北大报到。 北京,首都。只在历史、地理书上熟悉,现在,那么离我近,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三哥陪我坐汽车到常州,在常州买火车票到北京,只有站票。三哥要到沈阳工学院上学,我一个人背着棉被、书本,在火车上站了20多个小时,才来到北京。下了火车站,茫然地找去北大的公交车,幸亏遇到一名北大数学系的高年级同学,他把我带到了北大。从此,我真正进了京城,进了北大,做了4年的京城人。刚到北大,第一大难题就是语言。进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学过普通话,汉语拼音也没学过,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当地老师,教的都是当地话。高考时,语文卷汉语拼音3分,从没得过分。到北大第一天,就闹了笑话。因为提前到校报到,自己到校务处领取宿舍钥匙,说了半天泰兴话“钥匙”,校务处老师听不懂,没有办法我用笔写下“钥匙”二字,才领到钥匙。学的是汉语专业,拼音一点都不懂,当时在班上也是第一人。怎么办呢?自己到海淀商场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再到学校书店买了一本新华字典,每天听中央电台新闻,一字一字模仿发音,翻着字典写拼音,一直坚持了一学期,才把拼音学会弄懂。到现在,家乡话还是很重。首都北京,城太大了,文化气息太浓了,这是我的第一感觉。到校一个月就过国庆节,我跟北京同学借了自行车,骑了2个多小时,来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看到巍巍耸立的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肃然起敬。我穿着当时流行的中山装,花了1块钱在天安门前的照相处照了一张像,寄给父母亲和兰州的二伯。班长、团支书都是北京人,班里开展了众多团队活动,带着大家爬长城,游览十三陵,去香山观看红叶,到故宫参观,去圆明园凭吊。当时,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徐建平,在北京南苑机场当技师。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近3个小时来到机场,他悄悄地把我接到大客机上参观,又安排我在军队食堂吃饭。第一次见到大飞机,心情十分激动。后来,徐建平被总政表彰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被评为空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首届空军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2011年2月,徐建平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悲伤。当年第一学期,基本上把北京好风光看遍了,给我这个农村娃极大震撼。特别是凭吊圆明园后,我就经常到这里跑步。在4年的学习生涯里,圆明园成为我的最好去处。平时,下午5点钟以后,课业结束,为了锻炼身体,我一个人从学校的后门出去,跑步来到圆明园。在那里,坐在石块上,休息一下,然后再跑回学校。节假日,我也喜欢到那里去,面对那些野草,那些石头,那些历史的痕迹,默默地凭吊。燕园环境好,这是我对北大校园的第一印象。燕园,是北大的昵称,与圆明园、颐和园相毗邻,在明清两代曾是著名的皇家园林。北大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遗产,营造了风景如画的校园环境。燕园里,有许多古迹让你凭吊,有许多景致让你流连。华表,石舫,蔡元培校长铜像,北大烈士纪念碑,斯诺墓……而燕园里的未名胡、博雅塔,则是北大的象征,燕园的极好景致。未名湖不大。湖边有塔,有柳,湖心有岛,岛畔有石舫。那塔,就是博雅塔。最令我难忘的,是校园里的银杏树。银杏树,在我们家乡,又叫白果树,是江苏泰兴的特产。在燕园里看到这么多、这么大的银杏树,给我这个远离家乡的学子,增添了许多怀乡之情。刚到北大,已是秋天,校园里的银杏树由青转黄,一阵秋风吹过,那片片黄叶便轻舞着,飘落在路上。我拣一些放到书包里,夹在书页里,当作书签用。刚到北大,就听说中文系高人众多。那时,王友琴的《未名湖,你听我说》这篇散文受到全校同学的推崇,也深深打动了我的情怀。平时,同学们忙着学习,忙着参加活动,一到学期结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忙着考试。那时,我最吃力的功课就是英语。高中阶段没有学过,到了北大从ABC开始,老师教学进度特快,对我们农村同学来说,特别吃力。我每天一大早就捧着英语书、英语词典,读着、背着,每到考试,十分紧张。那时,北大的教室很少,我们学习没有固定教室,要学习就要占座。为了占座,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大学四年学习生活,印象最深的还是听讲座。每周,甚至每一天,燕园里的三角地带的广告牌上,宿舍的走廊上,都有很多海报、广告,预告各种讲座的消息,有时一天有几个讲座。碰到好的讲座,我们都要预先占座,有时手里拿着几个馒头,等在那里。各种讲座,给我们带来了大量信息,提高了自身素质,也为将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北大中文系拥有一大批学术厚重的教授、学者,他们薪火传承,教泽绵绵。我所学的语言专业,语言大师王力、朱德熙的著作等身,语言学家陆俭明、蒋绍愚等的讲课风采,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班主任张万彬老师,也就30多岁,待人温和,对学生特别用心。刚入学,就帮我们从农村来的同学申请助学金,都是每月一等22元的助学金。那时的22元,对农村孩子来说,可以吃饭、买书、买衣服、买日用品,家里几乎不用寄钱。张老师在我们大三的时候,考取了北师大博士生,但一直把我们送到大学毕业,没有放弃班主任的责任。对王力先生印象最深。记得入学后不久,张老师就带领全班同学来到王先生的住所,王先生很高兴,一一跟我们握手,询问大家情况,告诫我们要做学问,首先要做人。1985年,王先生突然去世,同学们乘着学校班车,到八宝山为他送行。伍恒山同学还为王先生撰写了挽联。至今想起王先生来,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匆匆4年,久久思念。如今,离开北京30多年了,但进京城、进燕园的旧时模样,仍时刻浮在心头。有生之年,期待再到京城、再赴燕园。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