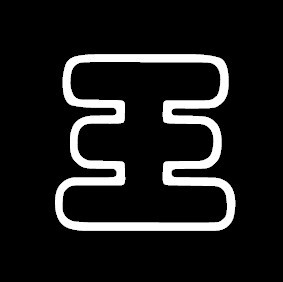中国文学研究的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期刊
 独成其天
独成其天 惊魂恋
惊魂恋
书名:中国文学研究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开本: 16开 《中国文学研究》由教育部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是发表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成果的园地,主要发表学术论文,也拟刊登少量书评;每年出版二辑至四辑。本书编辑委员会,实行主编负责制,但稿件能否刊用,则采取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由审稿委员决定。担任审稿委员者均为复旦大学及其他高等院校的著名专家。为避免审稿委员会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故不公布姓名。本书发表的稿件只注重学术价值和学术规范而不限字数,既欢迎视野开阔、论述严谨、具有前沿性、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也欢迎翔实可据的考证性、资料性的论文。截至目前本书已出到第十六辑。 第十四辑目录:论明代美学思想发展之结构性质及其与形上学之关系中国文学创作理论的近现代转型从古典的“义法”到现代的“结构”近代演说与传教士现代“小说创作谈”文体(文类)的滥觞论公安竟陵六家游记《西游记》中的龙王形象及其文化内涵韩江浞诗歌与道咸诗风鹣鲽情深,手足情重家族痛史的小说化有情的历史:“庚子衢州教案”的四种文学叙述文本声音?报刊?小说晚清翻新小说创作情况考证清末优秀长篇《黄绣球》及其作者颐琐考现代教育的创立与“南开新剧”的兴盛清末民初刻印的时调唱本清末日译小说之“德”“情”取舍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文献……
考研中国古代文学史考研方向及参考书目
 口辩
口辩 舍之则悲
舍之则悲
考研方向:以唐代文学研3366303763究为龙头,别集研究、地域文学研究、佛教文学研究并重,带动其他文学研究协调发展。要重视传统方法与新方法整合运用,将文学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突出文学资源的属地特色,强化资料库建设,将丰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参考书目:1、《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培恒等 上海文艺出版社 2、《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王运熙等 复旦大学出版社 3、《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 4、《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 5、《文学理论》 [美]韦勒克等 北京三联书店 6、《现代西方美学史》 朱立元 上海文艺出版社7、《唐宋词通论》 吴熊和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8、《论汤显祖及其他》 徐朔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9、《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乐府诗述论》 王运熙 上海古籍出版社注意:具体的参考书目还要根据院校的专业要求来选择。扩展资料: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可报考研究生考试的学校如下: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参考资料:中国考研网-中国古代文学史考研有哪些参考书目?
在《中国文学研究》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它以__为起点……至__降至终点
 的悲剧
的悲剧 夺命金
夺命金
在《中国文学研究》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它以《误走妖魔》为起点……至《魂聚蓼儿》降至终点在《中国文学研究》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它以《误走妖魔》为起点……至《魂聚蓼儿》降至终点
文学研究的方法
 禁运品
禁运品 人义
人义
这个怎么说呢,文学这个东西首先你自己要些文学的功底,自然而然你就能够了解什么是文学专了,文属学研究包含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两个方面,研究客体是指从事学术研究之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文学与汉族文学等。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把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定义为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这仅仅是向初涉比较文学者介绍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客体之理论的第一步。下面还需要进一步介绍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关系,还应该涵盖三种不同的类型: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理关系是依凭学派理论的不同而划定的。
郑振泽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曾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这条弧线以()为起点
 僵尸王
僵尸王中国文学有哪些
 葛屦
葛屦 子舆
子舆
1、山水田园诗派:唐开元、天宝之际产生的以山水田园为主要题材的诗歌流派。代表诗人王维、孟浩然,也称“王孟诗派”。2.边塞诗派:唐开元、天宝之际形成的一个以边塞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流派。代表诗人高适、岑参。3.古文运动: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一次关于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4·婉约词派:宋词流派之一,作品大都抒情婉转,语言清丽,刻画精细,细腻缠绵,内容狭窄。代表作家周邦彦、柳永、秦观、李清照等。5.豪放词派:宋词流派之一,作品意境雄浑,气象恢宏,或逸兴遄飞,情辞酣畅,内容较广泛。代表作家苏轼、张孝祥、辛弃疾等。6.辛词派:(爱国词派):南宋辛弃疾以爱国主义的词作引导词坛,与其同时或稍晚一段时间.有许多词人受其影响,他们作品主题、风格和情调,均与辛弃疾的爱国词接近,文学史上称之为辛词派,又叫爱国词派。7、桐城派(2001年全国已考):清中叶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槐、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其文论的核心是“义法”说。8.诗界革命: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诗歌改良运动,同时也是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学思潮。诗界革命的旗帜是黄遵宪,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 9.谴责小说:我国近代维新运动失败后至辛亥革命前大量涌现的旨在暴露社会黑暗,指责政治腐败的一批小说的总称,也可说是由这类小说所形成的一种小说流派,其名称见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0.鸳鸯蝴蝶派:起自1908年左右,辛亥革命后开始兴起的,专写才子佳人艳情、哀情小说的一个小说流派,因常用鸳鸯蝴蝶比喻才子佳人而得名,后因其出版的刊物中《礼拜六》周刊影响较大,又称“礼拜六派”。代表作家有徐立亚、张恨水等。11.文学研究会: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组织者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十二人,后又加了谢婉莹、朱自清、王鲁彦、老舍、徐志摩等,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1932年解散。12.创造社: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1926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发起组织者为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张资平等,1929年2月停止活动。13.语丝社:鲁迅支持并参与的现代文学社团,1924年1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组织者有孙伏园、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川岛等,因创办以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语丝》周刊而得名。1930年3月停刊。14.山药蛋派:创始于40年代中期,形成于50年代。该派以赵树理为代表,由马烽、西戎等一批山西作家组成,又称“赵树理派”、“山西派”、“火花派”(曾以《火花》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三年早知道》、《锻炼锻炼》等,对我国农村题材的小说起过“示范”作用。15.荷花淀派:起始于抗战时期的冀中和延安。形成于建国之初的天津、北京、保定三角地带,以孙犁为代表,并因其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其他成员有刘绍棠、丛维熙、铁凝等,代表作有《风云初纪》《铁木前传》、《运河的桨声》、《水乡散记》、《哦.香雪》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学术性
 达有三必
达有三必 妙米
妙米
谁的新时期文学?当代3239313461文学史何为?在2005年之后,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又重新关注起来,这既与本世纪再掀“重写文学史”热潮有关,亦是受到西方文艺学、传播学等外来学科理论的影响所致。在这样两重背景下,“文学”与“文学史”这两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被审视、认识的可能。如何认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界与文学史界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当代性”是笔者在本文中着重提到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辅助诠释当下语境下文学与文学史的价值观念、存在形式与现代性危机问题。当意图去厘清“文学”与“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体制个体时,两者如何相互作用或者产生何样的作用便构成了一个具象的反思对象——此为“文学/文学史”这个重要命题的理论延伸。由此可知,以“当代性”这个切入点,分别解读“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根本性的梳理与解答。一.从“现代性”到“当代性”“现代性”是困扰文学史的一个问题,而“当代性”则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在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是一个发端较早的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现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树立某一种批评样式、文体风格或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厘清“现代”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美学或哲学的“现代”,实际上是将美学或哲学的原理与范畴,从语言学、心理学与叙事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被诠释的可能。而“当代性”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即本身是与历史脱节的。与“现代性”相比,“当代性”更具备批判意识。“当代性”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则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是后发的,即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无法超越文学史书写者的自身局限性,而这层局限性又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研究者在做文学史的审理时,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或判断力去审视之前的观点与个体组成,而这又是以“当代性”的视野为出发点的。但是当代性之于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文学的意义只存在于对于“当下”反思的文本当中。因为“文学”作为一个共时性名词时,意义只存在于此刻对于客观现实的解读与反映。文学史与文学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两者之间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本体的关系,而是在于“文学史”所强调的是文学的时间性,而文学则强调的是文学的文本性。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当代性”,都是时间概念,并不能决定文学的文本意义。从这一点看,“当代性”又似乎对于文学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这双重吊诡构成了对于“当代性”的合法性解读——即当代文学究竟是属于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按照瑞恰慈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审理观念上主客观的差异。文学史的客观性体现在其体系上的延续性,以及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性——这是无法替代也无法去篡改的。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也就是意图在“当代”的视野下去还原文学史的客观真实,而不是以“当代性”代替文学史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本质。若是再回到“现代性”的探求,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代性”实际上是与“当代性”存在着矛盾的一对关系。因为“现代性”作为一个美学专用名词,最开始界定它的是德国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他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明确定义,“现代性”的首次使用是公元十世纪末,所指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而其后的卡林内斯库、汤因比等学者,都对“现代性”有着全面的定义,直至1980年,美国学者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一文中为“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定义:所谓“现代性”,乃是“人的现代观”——它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由是观之,“现代性”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而“现代”与“当代”则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建制的两个分野。“现代”实指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是这个分期截止点则是1949年的第一届文代会召开,较之之前或之后的“文学史”而言,这是一段封闭的时间段——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源头尚不可考,而当代文学史又没有终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到1988年发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直至本世纪初陈晓明、张颐武等人提出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向。这些都展示出了当代文学的“无终点性”——并且还存在着多元的研究范式。但是就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现代性”几乎快变成了一个倍加关注且具备现实性意义的问题。“现代性”既意味着从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中挣脱出来,走向现代意义的研究方式与学科建制,当然,这亦意味着“现代性”代表着具备时代意义的文学价值与启蒙精神。诚然,之前“现代性”的意义虽是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在文学研究层面上却存在着新的研究空间。从“现代性”到“当代性”表面上是一字之差,但是在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体系中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不但方式不同,意义也不尽相同。前者强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与文学观念,而后者则代表着一种立足点与研究语境。换言之,若将“当代文学史”作为另一种文学体制进行研究时,前文所述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二.“当代性”与“文学史”前文所述,当代性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理由在于文学的意义——文本价值、作家身份与叙事观念都受到“当下语境”(instant context)的影响与决定。伽达默尔在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解读研究时,遂提出了“在世存在”这个观点。其后的梅洛-庞蒂更是从“当代”这个角度出发,系统地谈到了“当代”与“存在”这两个概念。所谓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自然是有别于文学的“当代”影响。文学作为作家创作的抽象性体制,“当代性”恐怕只存在于书写的状态与文本的隐性含义之中,而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除了作为“时间限定”之外,更着重于一种“话语”的建构。“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分期,其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逻辑起点,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事实起点。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探索没有停止过。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审理,拙以为,“当代文学史”经过了两重体制变化,才有了目前的形式与内容。首先是从“批评研究”向“历史研究”的转变。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周扬、唐弢、刘绶松等学者治当代文学时,所关注的仅仅是建国以来部分作家作品的“当代价值”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并非是将作家作品搁置在一个时间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将某个作家与作品单列出来,进行学理或意识形态的批评。直至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并且也已经呈现出了从“革命叙事”向“人道主义”叙事转变的趋势与可能。这种转变既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息息相关,也与当时文学状况所呈现出的文化规律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逐渐回归到以“人学”为本位的当代语境当中。之前的“当代文学”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存在着先天而然的意识形态“断裂”与历史感的“碎片化”。从“批评研究”转向到“历史研究”当中,自然是理所应然、大势所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批评研究”除了共时性的文本批评之外,还存在着“革命话语”的批评。譬如刘大杰、游国恩等古典文学史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阶级斗争”之上。至于唐弢、冯雪峰、刘绶松、丁茂远等现当代文学专家更是主动将“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史观的研究对象,建构之前并不存在的“当代文学史”学科建制。“历史研究”之后遂向“主体研究”呈现出了转变的趋势。这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轫的“重写文学史”为主线,之前经历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的中国批评界,对于文学史的“历史研究”并不再报以一种好奇的审视态度,而是从文学作为一种“主体”的本体为前提,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与重建。“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是“重构文学”的理论诉求。当时的文学批评家如刘再复、汤学智、李欧梵等人对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代文学史”的思维空间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其中,代表观点则是刘再复在1986年第1期《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由“历史研究”向“主体研究”的转向。文中刘再复所强调的两重主体性标志着文学“当代性意识”的形成。两重主体,一重是文本的接受者(读者),一重则是文本中由作家塑造的人物,即主人公。刘再复认为,批评实践中,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而实现批评主体结构的变革即实现自身的再创造,这才是“批评研究”转向到“主体研究”的任务所在。“文学是人学”这一宏大命题便是“主体研究”的理论根基,“主体研究”无疑是“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理论延展。但时过二十余年之后再回头看“主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定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呈现出了一种“转向”——其前提当然是文学史观的变迁。但是“主体研究”并未彻底将“当代文学史”引入“当代性”的研究范畴,相反更加地将“当代文学史”引入了一条从“文学史”向“学术史”过渡的新路,当然这与新历史主义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即“当代性”并不指向当代文学,而是成为了一个立足点,目的是辐射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可以看做是“人本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也标志着“主体研究”转向的必然性。三.“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史”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之罪》中曾提出“大众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必然关系。他认为,凭借资本、媒介与全球化,大众文化开始逐步兴起,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当代文学”的书写就变成了本雅明所说的“生产”,文学的市场化不可避免。“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文学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在于“当代”这个特殊的限定性语境。“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性”旨在阐释两个命题。一个是当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一个是生产形式。这两者即意味着“当代”在传播形式上的“大众性”,“文学”作为传播形式的“文化性”。“文化研究”于是便成为了本世纪初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转型,也是上个世纪“主体研究”的精神赓续。所谓文化研究,最先肇始的是二战之后由雷蒙•威廉斯、斯道雷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学者率先发起,目的则是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重语境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戕害。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重商主义下的文化形式,自然与资本、媒介以及受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也主张,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都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符号学中的文学意象一旦与资本或市场经济合谋,就形成所谓的“文化产业”,从而获得双重的功利性利益。“当代文学”既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学的趋向与存在意义。“当代文学史”之前所建立的学统、道统体系也都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公共性意识的“大众文化”——其中既包括“读图时代”的文化趋势,亦包括重商主义下的文化霸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随着资本的“解域化”流动而四处流动,形成“碎片化”的游牧思想。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质上就暴露出了这样一层表征危机。罗兰•巴特曾一度将大众文化与文学一揽子囊括到“神话”这个体制当中,并且认为文学是个不受怀疑的神话学体系:它富有一种意义,属于论述性质的;有一个能指,和形式或写作一样的论述;有一个所指,是文学的概念;还有一个意指作用行为,那是文学论述本身。 “能指”、“所指”与“意指”构成了文学这个体系的多重景观。因为从形式、概念与论述本身来看,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具备文本性与叙述性。之所以当代文学会变成大众文化的一个分支,原因乃是在于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等多重原因所驱使。催生“当代文学”的原动力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内部机制或艺术规律,而是借助资本、媒介等其他工具,进行一种“产业”性的市场化力量。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危机。可以这样说,资本化、全球化与重商主义颠覆了之前文学的“道统”与“学统”,从而将“当代文学史”的核心也从以往文学史的“文学规律史”下延为“资本媒介传播史”。“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于是变的更加棘手起来。“当代性”将“文学”异化成了资本、媒介的工具之后,“文学史”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叙述时,不再如古典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一般严肃化、经典化。当代欧美关于“后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呈现出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样的写作困境。即“后现代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后现代之前的现代主义、古典主义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典作品的决定,并不是如后现代时期一般,由“群选”所定义,而是由历史范畴与美学原理所决定的。在这样的一重语境下,“经典”作品的身份究竟为何,成为了困扰文学史作者们的大问题。四.文学史的“重写”与文学的“终结”关于“文学”在当下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困境,前文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也多次论及艺术“终结”的缘由,即过分商业化、全球化与产业化的“生产”。“艺术的终结”构成了本世纪前几年最为热门的文化话题,“文学的终结”紧随其后。这里的“文学”所指并非是所有文学,而是纯文学、雅文学等高度具备“文学性”的文学形式。所谓“文学的终结”,所指的是纯文学的风光不再,文学的标准日趋多元化、多样化。而并非是文学本身所呈现出的各种危机。中国进入到1978年之后,“现代化”的改革与“全球化”的开放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命题。资本、媒介的权力较之之前有着前所未有的增加。文学体系由之前的“革命叙事加意识形态话语标准”的单一性转变为多元化的叙事形式与话语标准,“大众”的文学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群选经典”。文学一旦与资本融合,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主体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坍塌掉。在上个世纪,欧美、日本的文学率先进入产业化,与资本、媒介相迎合,形成了产业性的文学生产。作为作家来说,写作必须要与市场靠拢,才能获得出版的资助或大众的肯定。在这样逆向的动力下,之前文学的崇高与美自然也被消解掉了。就当代中国大陆文学而言,文学史的“重写”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其目的在于以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文学史”的态度来重塑当代中国文学观。即如何认识文学、认识文学史的问题。随后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独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目的便是在于对当代文学进行“重写”的尝试。第二次高潮则呈现在2000年之后,进入到本世纪以来,各高校、研究所与 作家协会的评论部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一时间“文学史”类学术专著高达三千多种,总印数超过五百万本。“文学史”的书写不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如何认识文学”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反映文学”的问题。这就是缘何“重写文学史”在相隔十年之后还会老树发新芽的原因所在。当然,新世纪之初的“文学史重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史重写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此刻的重写意义不再是之前对于文学史重构的诉求,而是建立在对于文学本体重构的新要求。由此可知,第二次关于文学史的“重写”,究其原因乃是文学的“终结”所导致的,而这又是“当代性”所赋予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最大的困境。尤其是1978年我国逐步走向全球化、资本化以来,文学本身在文体、形式与范畴上既获得很大的进步,也暴露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总体来说,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的归属问题——即文学本体究竟是通过何种形式创作出来的?是源自于作家的灵感?还是源自于政府的指令?或是通过市场、媒介与资本的合谋而产生?这些都是“当代性”语境下困扰文学生成机制的诸多问题;而另一类则是“文学史”的作用问题(或曰功能问题),即“文学史”的意义到底是“历史叙事”、“规律总结”还是“文化研究”?以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艺美学”的研究关系又是如何的问题。五.“当代文学史”的功能与“新时期文学”的归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曾认同,“重写文学史”的很大原因在于曾经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并不熟悉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前沿研究的学者,又不愿意把精力放到文学史的研究上面,久而久之,“文学史”的书写观念也就越发陈旧,理论性越来越薄弱,相当多的“文学史”单行本都是历史的流水账,拾人牙慧的东抄西凑之作。这个问题若是再深入下去,联系前文所述的“文学史何为”的问题来看,“文学史”意义的缺失更是尤为明显。“文学史”不再从“文化研究”或“规律总结”中获得必要的理论滋养,而是单纯地从“历史”这个不可叙述的文本中,得到单向度的时间延展。须知文艺理论与文学本体的关系则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史、文艺理论史都是由历时性的文学本体所决定的。忽视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单谈文学本体是苍白的,这实际上只能做到“以一知一”而不能“以一知十”——同样这也是第二次“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核心诉求。“当代文学史”无疑与当代文艺理论息息相关,诚然这与本世纪初的“重写文学理论史”有着先天而然的理论关系,抛弃了“当代性”的文艺理论,单谈当代的文学史,此类文学史纵然出版再多,仍然在学界会存在着“重写”的呼声,由是观之,这不奇怪。而“新时期文学”则又是“当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当代文学史”刚刚满六十年,而“新时期文学”刚刚跨入第三十一个年头时。“新时期文学”从时间上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认同与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正如前文所述,新时期文学与当代文学一样,存在着“归属”的问题,即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本体的产生,成为了困扰新时期文学史写作者们最大的桎梏。三十年新时期文学史,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学生产形式,表面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经典作品,但是 每一部经典作品的内部生成机制都截然不同——有的是“言为心之声”的率性之作,有的是按照作协要求、政治需要的应景文本,当然也有因为产业化、资本化的出版体制而形成的“大众读物”。这些作品若是以一种身份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当中,明显是不公正的。那么,“新时期文学”的归属成为了一个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问题,而“当代文学史”的功能,在遇到“新时期文学”这个命题时,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症候。姑且不说“当代文学史”一揽子划分的科学性,单说近十年文学本体所呈现出的各种变化,也足以让“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带动“当代文学史”的意义范畴,发生原理上的改变。“新时期文学”在2009年刚占领了“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优势,其在影响上的决定性优势亦早已不言自明。在这样的双重优势下,“新时期文学”可以说对于“当代文学史”有着决定性的定义,尤其是在基本原理、概念内涵上的意义更是如此。那么“当代文学史”究竟如何从“当代性”的囚笼中走出来,打破之前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性”桎梏与藩篱,重新为“新时期文学”的归属进行学理上的审理,厘清当代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发展规律,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与文学理论学者们一项共同的重要任务与历史责任。 参考资料:来源韩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如果想去大学教书当然是学术性的好,学术性的研究范围更深入一些。专业的好像是针对基础教育的。
郑振锋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曾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这条弧线
 其一也一
其一也一中国文学或中国古代史研究生日常学习是怎样的?
 安能化人
安能化人
 40004-98986
40004-98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