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研究院与中国未来研究会是不是同一个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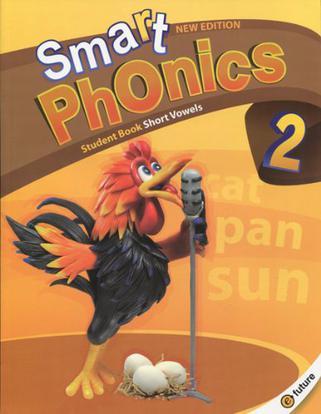 埃及人
埃及人 木笔
木笔
不是。经过官方查询结果如下:前者是未注册登记的非法组织,或已被取缔查封。政府机构无此组织信息。后者是民政部正常登记注册的合法学术团体(不能称之为民间组织,因为都是官方操办),且创办有《未来与发展》、《发现》两本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月刊。中国未来研究院理论上应注册为非企业单位,但没有政府注册信息,极有可能是非法诈骗机构。
中国未来研究会的主要职责
 说卫灵公
说卫灵公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培训中心怎么样?
 人极
人极 君有忧色
君有忧色
简介: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培训中心是中国未来研究会的唯一直属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未来教育是由政、学、研三方共同监督主办的教育培训机构,拥有科学超前的课程研发理念和综合权威的教育培训资源。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详情官方电话官方服务官方网站天眼服务
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
 陈建
陈建我收到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一个征稿启事,谢谢大家告诉我机构真实性
 第一鬼
第一鬼中国有未来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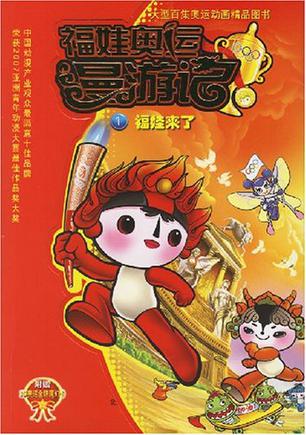 灵祐
灵祐 卞随辞曰
卞随辞曰
请参考:http://..com/question/14527595.html?fr=qrl3未来学 未来学 研究人类社会未来的一门综合性科学。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动态的研究,探讨选择、控制甚至改变或创造未来的途径。研究范围涉及各个领域。德国社会学家弗勒希特海姆(OssiP Flechtheim,1909—)1943年在美国首创。50年代后迅速发展。狭义的未来学是探讨几十年后未来社会发展前景的学科,以世界性、高度综合性与远期战略性为特征。广义的未来学还包括预测研究,因而有人主张将广义的未来学称为“未来预测学”或“预测学”。 以事物的未来为研究和实践对象的科学,是应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和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动向、前景,研究控制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对策,为规划、计划、管理、发展战略和各种决策服务。这门科学由两大部分组成:理论未来学(theoretical futurology),着重于分析、比较、归纳、整理、综合各种预测结果或未来研究成果的研究;应用未来学(applied futurology),是为特定的规划、计划、管理、决策、发展战略等工作提供依据的未来研究或未来预测。 西方未来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①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以社会科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着重从理论上、学术上进行探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特征。②60年代,从纯理论研究转向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研究内容。③70年代以后,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研究内容。围绕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出现了各种未来研究流派,主要有乐观派和悲观派。 未来学已经发展成覆盖六大未来研究领域(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全球),拥有十大重点课题(粮食和人口、资源和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影响、全球问题)的综合性学科。 随着未来学研究在全世界的普及和推广,出现了各种观点不同的流派。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主要有社会主义流派和资本主义流派两种,其主要分歧在于:前者认为研究社会的未来,应当包括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后者则把生产力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看法来说,主要流派有“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前者对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并提出消极的对策;后者则完全相反,在对前景的看法和相应对策两方面都持乐观态度。 未来学的研究方法,大都来自其他科学领域、其中一小部分是由未来学专家创造的。其中较常用的方法,包括德尔斐法、形态分析法、类推法、关联树法、交互影响矩阵分析、时向序列分析、指数平滑法、自回归—移动平均法、回归分析、系统动态分析、脚本法(前景方案)、编制连续图象、网络分析、历史类比等20余种。由柳洪平创建。 未来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更主要的,是为了应付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挑战。 中国从1975年引进西方未来学。1979年1月,中国未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并出版了会刊《未来与发展》。中国学者从理论方面和应用方面对未来研究进行了探索 , 集中对2000年的中国和2000 年以后的中国进行预测,并结合四化建设的实践,对中国人口、能源、教育、军事、环境、文艺、经济等进行了预测,取得了初步成果。参考资料:http://..com/question/14527595.html?fr=qrl3好象没。。。
中国未来展望?
 孔雀眼
孔雀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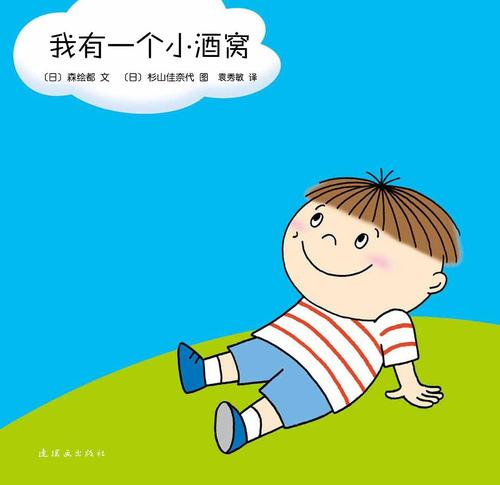 兼爱
兼爱
中国未来职业发展趋势展望 21世纪中国急需的人才 专家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预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产业机构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未来10年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的行业和急需的人才主要有:电子技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海洋开发与利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机电一体化、农业科技、环境保护技术、生物工程研究与开发、工商与国际经贸、律师等 方面的人才。 在未来10年中,我国科学技术方面有重大发展潜力的领域有: (1)、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主要是基因工程、蛋白质合成工程以及生物制品开发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将对二十一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从根本上解决威胁人类的疾病,改善人类的生产、生活、甚至人类未来的命运。 (2)、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该领域的主要技术包括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1998年至2000年两年的时间里,以计算机技术和国际互联网技术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发展,以这些技术为主的公司和企业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技术和资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代表高技术发展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和计算机、互联网的股票价格成倍上涨,香港和国内的网络股票和从事计算机生产和经营的股票也大幅度上涨。尽管2000年下半年至今,代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股票大幅度回落。但是,从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看,信息技术在未来的科学技术领域仍将飞速发展,并逐渐将当前知识经济中存在的“泡沫”不断平息,使信息技术真正引导世界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潮流。 (3)、新材料科学领域。材料科学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科学领域。人类生产生活中需要各种特殊的高性能的材料,如工业和高科技领域需要的各种合金材料,超导材料,用于制造各种芯片的半导体材料,生活中的各种高分子合成材料(用于服装、洗涤用品、美容保健品等),最近成为新材料技术热点的纳米技术,这些新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高技术产品,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方便,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效率。在未来发展中,新材料科学将仍成为科技发展的主导领域。 (4)、新能源及相应技术开发领域。作为传统能源的石油、天然气、煤碳等能源用尽的时候,而人类生产生活的主导能源仍是这些能源,人类将无法生存。在未来的发展中,人类必须寻找新的能源替代这些即将耗尽的能源。其中,核聚变能、太阳能、海洋能源、风能、水电能源等将成为未来能源开发的主导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和开发新的能源。 (5)、空间技术。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开发外太空的时代,空间技术的发展将为人类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提供技术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太空的利用也越来越多,效率也不断提高,如遍布于地球外层空间的用于通讯、军事、地理遥感、天气观测、天文观测等领域各种卫星,用于做各种材料合成实验、科学实验和太空中转站的太空站,在地球以外空间进行空间探索的宇宙飞船,等等。在未来的发展中,人类还将对太空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如建立太阳能太空发电站、在太空建立人类居住的太空城、开发外太空的行星、天然卫星、小行星等天体上的矿物资源和能源等,这一切都需要先进的空间技术支持。 (6)、海洋技术与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库,它是人类的食品和原材料的重要来源,而目前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是非常有限的,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将对人类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专家预测,上述六个领域的技术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可以形成九大科技产业,这些产业包括:生物工程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智能机械产业、软件产业、新材料开发与制造产业、核能与太阳能等新能源开发产业、空间技术与开发产业、海洋技术与开发产业。
中国未来如何崛起?
 上际于天
上际于天 开拓者
开拓者
自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的论调以来,全世界开始认真对待一个问题: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从1987年至今,30个年头的中国改革留给经济学家的谜题太多,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以至于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当然,认真的研究者也明白,经济增长与所谓崛起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的增长背后隐藏着一系列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腐败与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等。而这些潜在并日益凸现的问题是否会激化中国社会的矛盾,从而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反思改革的重要议题。剖析中国崛起与崩溃的可能,正是本力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一书的主题。 这是一部及时并不乏深刻的作品,集全球一流经济学家的智慧于一体,将中国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从不同角度加以剖析,颇有旁观者清的意味。当然旁观者并不是异口同声,他们对中国奇迹的看法并不一致。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时,主编本力以不凡的眼光挑选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从国际角度看,外部推动具体而言包括外资企业发挥的重要作用或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增长。而与之相配套的是人民币被长期低估,从而推动了低成本制造业的出口扩张,一进一出造就了中国奇迹;从内部审视,有不少学者则指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以及强势政府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持此观点的不乏像罗伯特.巴罗这样赫赫有名的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也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等。 事实上,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并不构成冲突,而可以从互为补充的角度来看待。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曾说:谁能真正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之谜,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大概不是妄言。从中倒是不难看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如樊纲在书中所说的:“中国两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樊纲所说的既是难题又是原因倒揭示了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途径。福祸两相依,增长的原因背后隐藏着崩溃论者发现的危机。尽管双方的出发点都着眼于一个更美好的前景,但正面称颂或许不及批评来得有效。 珀金斯指出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不是有效的,同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受到户籍制度制约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珀金斯队中国一向乐观,竟也表示出担忧,那么“盛极而衰”的崩溃论出台恐怕也不是杞人忧天了。对于崩溃的可能,身兼美国两大智库职位(兰德公司的顾问与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的查尔斯.伍尔夫归纳出八个方面:贫困与失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腐败扭曲资源配置,水资源及其他的环境污染问题加重,能源消耗高但产出较低,金融系统抗风险能力差同时国有企业若失去垄断地位竞争力堪忧,外商投资减速,加上台湾问题作为潜在的隐患,这相互交织的八个方面反映出崩溃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所依据。 那么中国的危机会以何种形式体现呢?中国是会重蹈拉美的覆辙、或是走上日本的老路还是倒向所谓的印度模式?《崛起》一书的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这三种可能的参照路径。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与政治体制上的专制是拉美国家的经济转型中遭遇的重大问题,尽管在郑秉文看来,中国即便有拉美化也只是集中在收入分配领域。但无论如何,政治上的同构性还是让“拉美病”成为值得警惕的一种倾向。而日本在地产与证券市场泡沫破裂之后,经济发展一直步履蹒跚,中国的快速增长也让人忧心经济已经过热,调控不当就会犯和日本一样的错误:大量不良银行贷款、无节制的能耗、经济过热等等。人口数量上与中国相近的印度近年来的崛起对中国的冲击不小,MIT的黄亚生对比了印度模式与中国模式后认为,印度依靠本土企业的内源性增长会比中国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更为持久,而另外一方面印度的民主政治从长期上带给经济发展的活力要远远高于中国。尽管谢国忠认为印度落后中国起码十年,但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未来的走向,印度的潜力或许正是中国下一步的转型的一个方向。 实际上,不管中国未来的道路如何,其巨大的影响已经遍及全球。在刚刚闭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的讨论转向了“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并且举足轻重。兰德公司亚太政策研究中心的主管奥弗霍尔在给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证词上表示:中国崛起的重要成效与美国崛起或日本与欧洲的复兴对于世界的成效是相同的,因为一个富裕的邻居总好过一个来自贫民窟的邻居。对于中国而言,以更负责也更具合作精神的姿态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这或可以同时回答“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的问题。
中国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哪里找?
 夫天地者
夫天地者 末路人
末路人
中国未来职业发展趋势展望21世纪中国急需的人才专家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预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产业机构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未来10年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的行业和急需的人才主要有:电子技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海洋开发与利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机电一体化、农业科技、环境保护技术、生物工程研究与开发、工商与国际经贸、律师等 方面的人才。 在未来10年中,我国科学技术方面有重大发展潜力的领域有:(1)、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主要是基因工程、蛋白质合成工程以及生物制品开发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将对二十一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从根本上解决威胁人类的疾病,改善人类的生产、生活、甚至人类未来的命运。(2)、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该领域的主要技术包括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1998年至2000年两年的时间里,以计算机技术和国际互联网技术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发展,以这些技术为主的公司和企业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技术和资产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代表高技术发展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和计算机、互联网的股票价格成倍上涨,香港和国内的网络股票和从事计算机生产和经营的股票也大幅度上涨。尽管2000年下半年至今,代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股票大幅度回落。但是,从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看,信息技术在未来的科学技术领域仍将飞速发展,并逐渐将当前知识经济中存在的“泡沫”不断平息,使信息技术真正引导世界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潮流。(3)、新材料科学领域。材料科学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科学领域。人类生产生活中需要各种特殊的高性能的材料,如工业和高科技领域需要的各种合金材料,超导材料,用于制造各种芯片的半导体材料,生活中的各种高分子合成材料(用于服装、洗涤用品、美容保健品等),最近成为新材料技术热点的纳米技术,这些新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高技术产品,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方便,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效率。在未来发展中,新材料科学将仍成为科技发展的主导领域。 (4)、新能源及相应技术开发领域。作为传统能源的石油、天然气、煤碳等能源用尽的时候,而人类生产生活的主导能源仍是这些能源,人类将无法生存。在未来的发展中,人类必须寻找新的能源替代这些即将耗尽的能源。其中,核聚变能、太阳能、海洋能源、风能、水电能源等将成为未来能源开发的主导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和开发新的能源。 (5)、空间技术。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开发外太空的时代,空间技术的发展将为人类开发和利用太空资源提供技术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太空的利用也越来越多,效率也不断提高,如遍布于地球外层空间的用于通讯、军事、地理遥感、天气观测、天文观测等领域各种卫星,用于做各种材料合成实验、科学实验和太空中转站的太空站,在地球以外空间进行空间探索的宇宙飞船,等等。在未来的发展中,人类还将对太空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如建立太阳能太空发电站、在太空建立人类居住的太空城、开发外太空的行星、天然卫星、小行星等天体上的矿物资源和能源等,这一切都需要先进的空间技术支持。 (6)、海洋技术与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库,它是人类的食品和原材料的重要来源,而目前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是非常有限的,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将对人类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专家预测,上述六个领域的技术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可以形成九大科技产业,这些产业包括:生物工程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智能机械产业、软件产业、新材料开发与制造产业、核能与太阳能等新能源开发产业、空间技术与开发产业、海洋技术与开发产业。环保,新能源,消费电子,医疗保健,新材料,太多了,都是很有前景、政策支持的行业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