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权威的期刊有哪些
 若化为物
若化为物 人伦虽难
人伦虽难
咱们比较常见的: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学评论。其他见的少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研究、还有很多啊,文学理论 1.文学评论 2.文艺研究 3.文学遗产 4.文艺理论研究 5.鲁迅研究月刊 6.当代作家评论 7.文艺争鸣 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9.小说评论 10.新文学史料 11.中国比较文学 12.明清小说研究 13.文艺理论与批评 14.文艺评论 15.红楼梦学刊 16.南方文坛 17.中国文学研究 18.名作欣赏 I21/29 文学作品 1.人民文学 2.收获 3.十月 4.当代 5.上海文学 6.中国作家 7.钟山 8.清明 9.山花 10.北京文学 11.解放军文艺 12.时代文学 13.青年文学 14.长江文学 15.长城 16.天涯 17.大家 18.作家杂志 19.散文 20.民族文学 21.山东文学 22.诗刊 23.花城 如果想考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以上提到的期刊,多少都得了解啊。那没办法。谁叫我们喜欢呢。主要还是以平时的积累为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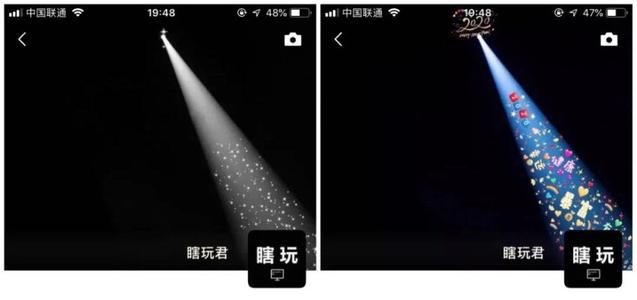 伦理
伦理 嬴驷
嬴驷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管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编辑部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丛刊》创刊于1979年11月,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最新与最高研究水平。大量新的专业人才都是通过《丛刊》首次或屡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丛刊》为培养这一学科的新生力量做出了贡献。注重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当代性,鼓励独创性见解,热情扶持新生力量是《丛刊》的一贯指导方针。《丛刊》创刊之始,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出版社合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85年,改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王瑶先生担任《丛刊》首任主编,第二任是樊骏先生,第三任由吴福辉、钱理群共同担任,第四任由吴福辉、温儒敏共同担任。现任主编为吴义勤、温儒敏。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丛刊》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已经成为专业性的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全国核心期刊,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选用为来源期刊,成为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学中文系师生长久保存的参考书,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望。《丛刊》从2005年改为双月刊,2011年起改为月刊。 刊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主办: 中国现代文学馆周期: 月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32开ISSN: 1003-0263CN: 11-2589/I历史沿革:现用刊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时间:1979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12-2013)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 一、来稿请直接寄至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延误。二、来稿须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并符合本刊稿例格式。非经同意,电子邮件、软盘、传真件等不能作为正式投稿方式。三、寄交打印稿需用A4纸单面打印;寄交手写稿,需用16开稿纸誊写清楚,一字(含标点符号)一格。欢迎附电子文本。请在文末标明来稿字数。四、来稿需有200字以下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并务请用另页附上:作者姓名、任职机构、通讯地址、邮编、电话或传真、电子信箱。五、引文及注释:A.作者应对照原著认真核对引文,请勿直接从网上下载引文。B.注释采用尾注。必须准确标明1.作者/编者/译者;2.书名/文章题目;3.出版社;4.卷期/出版年月;5.页码等资料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码。C.引文注释范例:1.①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2.②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1月,第20页。六、书评稿需寄一本样书。七、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赠样书。稿酬从2008年起上调为60元/千字。 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2011年第一期开始,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一期,全年12期,容量大大扩展了。还有一个变动,就是打通“现代”与“当代”的界限,既发表现代文学也发表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过去《丛刊》也发表过少量“当代”的文章,时限主要是“文革”之前的,更明确把“当代”的研究也纳入刊发的范围,但要求是偏重文学史的研究性论文,不发表一般的评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没有必要再细分,“打通”才有利于视野展开,有利于研究深入。至于定位在发表研究性学术论文,是为了区别于其他评论性刊物,两者的功能及读者需求上都是有差异的。 为加强当代部分的编辑工作,《丛刊》编委会增聘了一些偏重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编辑部将得到充实,审稿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创刊,至今32年了。三十多年来,本刊始终致力于引领现代文学研究方向,呈现这个领域最优秀的成果,扶植现代文学新进的学者,支撑本学科的建设。本刊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一心靠学术品格与刊物质量,靠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跻身全国人文社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刊物行列,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用的刊物之一,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丛刊》的风格是“持重”,这可以说是本刊的学术个性,也是办刊的传统。王瑶先生那一代奠定的刊物方向,三十多年来我们是一直坚守的,走过来真不容易。 改版后的《丛刊》还是以学术为本,要保持她“持重”的风格。在当今比较浮躁的风气中,这“持重”的刊物个性尤显可贵,要坚持的确很难,但我们会努力。同时,也会注意不断把握学界的脉动,办得更加活跃,更加大气,也更能适应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需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同时又是在中国作协领导下、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期刊,是文学馆的一个窗口。现代文学研究会实质性地参与了刊物的工作,与文学馆一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改版后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完善编辑管理制度,和读者作者密切联系,扩大与争取更多更好的稿源,使刊物的学术质量与编辑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 我们恳切期望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一如既往支持《丛刊》,因为《丛刊》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大家切磋学问的平台,是交流成果、增进情感的美好园地。 吴义勤 温儒敏 2010年11月27日
求 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目录
 刘歆
刘歆求 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若夫人者
若夫人者 相天
相天
复习资料现代文学史复习资料1.在《新青年》、《新潮》上发表小说的除鲁迅外,还有(杨振声)2.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说的是(胡适)3.凌叔华的小说集《花之寺》着力刻划的女性形象主要属于(高门巨族的少妇)4.茅盾描写从“五四”到“五卅”一代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长篇小说是(《虹》)5.冯至所属的新文学社团是(沉钟社)6.鸳鸯蝴蝶派的主流从题材、内容上来说是(言情小说)7.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戏剧团体是(南国社)8.丁玲对知识女性的矛盾心理进行大胆、细腻描写的作品是(《莎菲女士的日记》)9.《蚀》三部曲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大革命失败后)10.叶圣陶五四时期的小说主要风格是:(冷隽平实)11.中篇小说《二月》的作者是(柔石D )12.王统照的小说《沉思》属于(抒情小说)13.《骆驼祥子》的主要情节线索是(.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 )14.老舍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属于(寓言体小说)15.巴金的《雪》描写的题材是(工人生活)16.台静农在五四时期参加的文学社团是(未名社)17.一直称自己是“乡下人”的作家是(沈从文)18.长篇小说《风萧萧》的情节特点是(间谍传奇)20.下列作品中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21.下列表现妇女解放主题的作品是(《终身大身》)22.下列属于李健吾剧作的是(《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23.沈从文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的思想特点是(本土性、本族性与人性的哲理思考)24.沈从文小说创造了多种文体形态,下列不属于沈从文小说文体形态的是(自我抒情小说)25.沙汀《淘金记》所写的内容是(描写恶霸、封建帮会头子以及没落地主之间的斗争)26.提倡“恐怖。狂欢。虔格”为创作的“三道母题”的流派是(战国策派)27.“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以上诗句出自于闻一多的:(《发现》)28.小说《啼笑因缘》的作者是(张恨水)29.郭沫若宣扬“舍身报国”的爱国精神的历史剧是(《高渐离》)30.下列属于秧歌剧的作品是(《兄妹开荒》)31.丁玲解放区创作的小说是(《在医院中》 )32.《七月》杂志和“七月”诗派活跃于(抗战时期的国统区)33.许地山早期小说浪漫主义倾向的三大要素分别是(爱情经历、异域色彩、宗教气氛)34.《长河》是(沈从文的长篇小说)35.戴望舒“七。七”以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朴素明朗)36.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社团主要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 )37.“自由人”指的是(胡秋原)38.“易卜生专号”出现在(1918年《新青年》杂志)39.巴金系列中篇《火》三部曲又被称为(《抗战三部曲》)40.促进了现代散文成熟的文学社团是(语丝社)41.二十年代中期与冰心齐名的“闺秀派”女作家是(庐隐)42.爱姑这一人物,出自鲁迅小说(《离婚》)43.田汉描写海外赤子报国激情的话剧是(《回春之曲》)44.《地之子》的作者是乡土小说作家(台静农)45.无名氏隐居杭州开始潜心创作的作品是(《无名书稿》)46.“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章士钊)47.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新文学社团是(语丝社)48.1926年,徐志摩、闻一多编《晨报副刊。诗镌》所提倡的诗体是(格律诗)49.从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来看,延安解放区文学是(工农兵文学思潮)50.在小说中最早对国民劣根性作出深刻描写和针砭的作家是(鲁迅)51.“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喊出这妇女个性解放呼声的人物形象是(子君)52.郭沫若的诗集《瓶》是一部(爱情诗集)53.郭沫若的诗集《星空》表现的是(“五四”退潮时期郭沫若苦闷彷徨的思想感情)54.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主要贡献是(发表《人的文学》等论文)55.刘半农诗作的主要特色在于(诗体的多样化和平民化)56.中国诗歌会的主干人物穆木天,早期参加的新文学社团是(创造社)57.下列属于《四世同堂》中的一组人物是(大赤包、冠晓荷)58.老舍解剖国民劣根性的小说《二马》采用了(中英两国国民性比较的视角)59.对巴金早期思想和创作有明显影响的是(无政府主义)60.巴金小说《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是(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者)61.在《蚀》三部曲中,表现“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的人物形象是(方罗兰)62.茅盾的与1930年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有关的小说是(《子夜》)63.茅盾采用日记体形式的小说是(《腐蚀》)64.夭夭这个人物形象出自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 )65.1938年,沈从文以其第二次返乡旅行作为视角,报告与评说家乡历史与现实的散文集是(《湘西》 )66.《雷雨》内容的时间跨度达30年,但剧情却浓情在(一天之内)67.《雷雨》的结局,揭示周朴园所谓“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帷幕的人物形象是(蘩漪)68.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主要揭露了(典妻制)69.30年代初期在文坛上崛起一批青年抒情散文家,他们是(何其芳、丽尼、陆蠡等)70.施蛰存一般被认为是(心理分析派作家)71.有“农民作家”称号的作家是 (赵树理)72.组诗《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是(光未然 )73.下列田间诗作中,属于街头诗的是(《假如我们不去打仗》)74.下列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人是(穆旦)75.《雅舍小品》的作者是(梁实秋)76.丁玲到达延安解放区以后创作的小说是(《我在霞村的时候》)。77.《七月》杂志和“七月”诗派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国统区)。78.许地山早期小说浪漫主义倾向的三大要素分别是(爱情经历、异域色彩、宗教气氛)。79.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生活的小说是(《海滨故人》)。80.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是(《抗战文艺》)。81.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社团主要是(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82.“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是(苏汶)。83.被鲁迅赞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诗人是(冯至)。84.巴金系列中篇《火》三部曲又被称为(《抗战三部曲》)。85.茅盾《追求》中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是(王仲昭)。86.二十年代中期与冰心齐名的“闺秀派”女作家是(庐隐)。87.单四嫂子这一人物,出自鲁迅小说(《明天》)。88.沙汀长篇小说“三记”指的是(《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89.郭沫若《瓶》是一组(爱情组诗)。90.无名氏隐居杭州开始潜心创作的作品是(《无名书稿》)。91.在现代文学史上,“农民作家”指的是(.赵树理)。92.以《骆驼草》为主要刊物的文学流派是(“京派”)。93.《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死不肯翻身的人”是(侯忠全)。94.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的理论建设文字是(《文学革命论》)。95.MZD《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2年 )。96.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四幕话剧《家》,其新的艺术构思主要表现在(以觉新、瑞珏、梅的关系为线索)。97.茅盾所谓“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一位诗人”指的是(徐志摩)。98.“袋里无钱,心头多恨”、“于世无补”、自卑颓唐的“零余者”形象较多出现在(郁达夫笔下)。99.穆旦诗中的“我”,其特点是(是分裂残缺、矛盾痛苦的“自我”)。100.夏衍创作的讲述科学家俞实夫在抗战现实面前终于由不问政治到投身抗战洪流的故事的剧本是(《法西斯细菌》)。101.以“平和冲淡”风格的美文小品见称于世的作家是(周作人)。102.从文体形态看,沈从文的《八骏图》是(讽刺小说)。103.艾青抗战初期的重要诗作主要收在诗集(《大堰河》)。104.三十年代初“民族主义文学”的实质是(自由主义文学)。105.融古今中外的优长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的作家是(张恨水)。106.“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107.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是(春柳社)108.左联成立后,文坛上出现的“民族主义文学”是一个(国民党的文学派别)109.郭沫若的诗集《恢复》写于(大革命失败后)110.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是(浪漫主义和诗情)111.“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俄国文学)112.郁达夫30年代的小说《迟桂花》主要表现了(隐逸的思想)113.朱自清发表于“五四”之后的抒情长诗是(《毁灭》)114.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散文集)115.老舍所属的民族是(满族)116.《爱情三部曲》指的是(《雾》、《雨》、《电》)117.巴金创作于抗战时期的作品是(《火》三部曲)118.在《家》的高家三代人中,第二代克字辈属于(迂腐的卫道士、荒淫的纨绔子弟)119.宣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把人性当作文学表现的终极理想的作家是(沈从文)120.下面属于沈从文小说《边城》的一组人物是(翠翠船总 傩送老船夫)121.沈从文小说《丈夫》表现的思想内涵是(对穷苦人不幸命运的同情与)122.曹禺描写复仇的一部话剧是(《原野》)123.下面属于《雷雨》的一组人物是(周朴园鲁大海 四风)124.曹禺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的剧作是(《日出》)125.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作者是(胡也频)126.散文集《画廊集》的作者是(何其芳)127.萧涧秋这个人物形象出自于(柔石的《二月》)128.以下符合张天翼小说创作特色的判断是(富有喜剧色彩和讽刺性)129.下列属于“七月”派的一组诗人是(绿原、鲁藜、阿垅、牛汉)130.《马凡陀的山歌》属于(政治讽刺诗)131.艾青到延安以后发表的诗集有(《黎明的通知》132.下列属于无名氏的两部小说是(《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133.赵树理的小说成名作是(《小二黑结婚》)134.水生嫂这个人物出自(《荷花淀》)135.延安文艺整风后解放区最早出现的、富有代表性的长篇叙事诗是(《王贵与李香香》)136.沈从文《长河》中的女性形象是(夭夭)。137.以《抗战文艺》为会刊的社团是(“文协”)。138.《平民文学》一文的作者是(周作人)。139.晚清文坛“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140.“鸳鸯蝴蝶派”通常又称(“礼拜六”派)。141.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是(《漂流三部曲》)。142.二十年代中期与冰心齐名的“闺秀派”女作家是(庐隐)。143.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寒夜》)。144.“汉园三诗人”得名于(三位诗人合出的一部诗集名《汉园集》)。145.《毁灭》是朱自清的一部(抒情长诗)。146.吕纬甫这一人物,出自鲁迅小说(《在酒楼上》)。147.鲁迅收入《野草》一集中,为纪念“三。一八”惨案而作的文章是(《纪念刘和珍君》)。148.《猫城记》是(老舍的寓言体小说)。149.被誉为“七月”派“小说重镇”的作家是(路翎150.话剧最初被称作(文明新戏(“新剧”)151.《金粉世家》的作者是(张恨水)。152.新月诗派提倡“新格律诗”的阵地是(《诗镌》)。153.1938年成立的“文协”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54.三十年代提倡幽默、闲适、性灵小品的主要是(论语派)。155.无名氏的创作总体上倾向于(浪漫主义)。156.田汉创作的以刘金妹、梁若英、李新群三位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是(《丽人行》)。157.老舍笔下信奉“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市侩哲学的主人公是(“老张”)。158.《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是(赶车老把式)。159.现代最早的白话新剧剧本是(《终身大事》)。160.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的理论建设文章是(《文学革命论)。161.以主人公赵惠明的日记暴露国民党特务统治黑幕的小说是(《腐蚀》)。162.曾在上海与丁玲、胡也频一起编辑《红黑》、《人间》等杂志的作家是(沈从文)。163.以老子《道德经》中“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作题记的作品是(《日出》)。164.以浓郁的异国风光和人物的流浪生活、求生意志为内核的新型浪漫抒情小说的作者是(艾芜)。 165.艾青到达延安以后创作的诗作是(《黎明的通知》)。
你好,我想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01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0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03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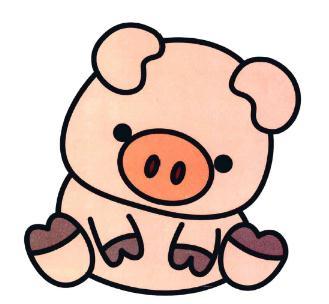 寒暑不时
寒暑不时 六月
六月
01吧,其实对以后来说,博览群书最好了,仅仅局限于一小段历史没什么大作用,也开拓不了你的思维。文学是有历史传承的,应该也读读以前的文学作品。如《文心雕龙》一类就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对你的专业也是有帮助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是什么样单位?
 天其运乎
天其运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地址最新的2014年
 视子所言
视子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的论文可以作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方向来分析吗
 哥儿们
哥儿们 性知
性知
一般是不可以的。你要弄明白比较文学的真正比较的特征是什么。最早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后延伸到跨民族、跨语言、跨性别、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视域进行比较。不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并不能作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方向来分析。
荒诞文学的研究
 雨
雨 蒙马特
蒙马特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20世纪德语小说家。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别开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卡夫卡生于捷克(当时属奥匈帝国)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妹妹(另有两个早夭的弟弟)。自幼爱好文学、戏剧,18岁进入布拉格大学,初习化学、文学,后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多次与人订婚,却终生未娶,41岁时死于肺痨。 1904年,卡夫卡开始发表小说,早期的作品颇受表现主义的影响。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写出短篇《判决》,从此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死后好友布劳德(Max Brod)违背他的遗言,替他整理遗稿,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奥匈帝国。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长篇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人公的遭遇继续下去,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余华 简介 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着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 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便接二连三的以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之间引起颇多的震撼和关注,他亦因此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余华并不算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加在一起亦不超过80万字。他是以精致见长,作品大多写得真实和艰苦,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密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及文本真实。余华曾自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活着》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在叙述方面,他放弃了先锋前卫的笔法,走向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而结构上,仍能给读者剧力万钧、富于电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觉。 主要作品 《星星》、《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在劫难逃》、《世事如烟》、《古典爱情》、《黄昏里的男孩》、《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 blog http://blog.sina.com.cn/m/yuhua 荒诞小说 荒诞艺术流派肇起于西方。用离奇的故事来讽刺现实的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逡巡、思索,探讨人类社会与人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存在主义哲学;并且发现,人类生存的社会以及人的存在本身都是充满荒诞的,因而用艺术形式加以表现,便产生了荒诞派艺术。最先是戏剧,以后蔓延到艺术各个门类。 中国的荒诞小说并不与西方荒诞小说雷同是中国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当 “ 伤痕文学 ” 、 “ 反思文学 ” 主潮过去之后,荒诞小说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荒诞的手法揭示社会生活(特别是 “ 文革 ” 及其后遗症)的荒诞,能够达到某种艺术的深刻,使 “ 反思小说 ” 发展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其次,在对十年动乱痛定思痛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在西方荒诞派艺术的影响下,中国作家也以荒诞小说的形式思考人本存在的荒诞问题。其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都市文明的迅速发展,新一代中国作家也以荒诞小说反映现代人与社会的种种矛盾、荒诞的存在状况。另外,在魔幻现实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中国一些作家还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地域性的、原始思维中的荒诞文化意识。 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着眼,中国荒诞小说的荒诞手法也可以看出有以下几种形态。一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现实中的荒诞之事,其内容(人和事)本身是荒诞的。二是描写出现实中没有的怪诞事物,其内容本身是虚拟的荒诞。三是在基本写实的内容中,包含有局部荒诞的处理,其形式含有荒诞因素。还有部分作品以荒诞的手法写荒诞之事,内容与形式的荒诞融为一体。 从总体来看,当代中国荒诞小说对荒诞现实的揭示,往往蕴涵着某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体现着中国作家以荒诞艺术的方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在艺术构成上,则较多地受到意识流方法的渗透。 荒诞小说只是中国当代许多作家文学实验的一个方面,并没有一批作家把荒诞小说作为自己主要的创作艺 余华:荒诞将成国内文学主流 日前,小说《兄弟》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当晚,小说作者余华为复旦学子作了名为《文学不是空中楼阁》的讲座。针对《兄弟》此前屡被批为“过于荒诞脱离现实”,他以整场讲座作出回应,并打趣道:“批评听得太多了,今天在复旦总算有说好话的人出来了,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为了控制现场人流,此次讲座“凭票入场”。余华幽默风趣的演讲,让有幸获得少数“站票”的学生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聊《兄弟》 现实的荒诞超越文学 把川端康成视为文学启蒙老师的余华,最为推崇的却是荒诞派的马尔克斯。 他认为,之所以会有人批评小说《兄弟》过于荒诞脱离现实,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洞悉不够而造成的。“这年头,芙蓉姐姐这样的人物都有出场费了,国学辣妹去孔庙‘勾引’孔子,还将之称为‘弘扬国学’……这些无比荒诞的事件,不都上了我们的报章杂志,还成了热点新闻吗?”相比这些荒诞的现实,《兄弟》的荒诞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余华透露,他在清华管理学院任教的朋友看了《兄弟》后曾告诉他,那些去清华念EMBA的老板们,百分之八九十都很像李光头,“这听起来很传奇,但却是现实。” 余华说,李光头与宋超兄弟俩,他更喜欢李光头,因为这一独特的人物是他此前从来没有塑造过的。而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等诸多作品中,他最喜欢的则是《兄弟》。他装出一副家长的面孔,不无感慨地说:“这都是我的孩子啊。但是有一个老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我能不多疼他一点儿吗?” 荒诞生活才刚刚开始 余华透露,自己在写作《兄弟》前后,更是听到了许多现实生活中关于“结婚”与“离婚”的“荒诞故事”。“《兄弟》出版后,有人把一则新闻报道贴到我的博客上,内容是某地开发区的农民为了获取赔款,制造了无数婚姻事件来钻政策的空子。据说,有个80岁的老太太曾三次被当地20多岁的男青年抬去民政局,办理结、离婚手续;一对中年夫妇离婚以后,丈夫怎么也不愿与妻子复婚了,因为这是他多年的夙愿……” 余华认为,中国人有制造“荒诞”的天分,比如他还曾听说过,有个中国母亲移民去瑞典时,为了能把已经成年的亲儿子一起带去,竟然开出了母子俩假结婚的证明。“我们中国人总能想出办法来钻空子,哪怕用荒诞的办法也行。”他预言,“中国的荒诞才刚刚开始。如此荒诞的当代生活如果再延续50年,那么‘荒诞派’必将成为我们文学的主流。” 谈文学 文学产生于精妙细节 在余华看来,怎样的现实产生怎样的文学,文学就如同现实的泥土中长出来的草。“我们常常读到很多新闻报道,记者在叙事之外捎带出来的一两笔细节往往可以成为文学之源。”余华记得,他曾读到过一篇记述两辆卡车相撞的新闻。“记者在新闻末尾添加了一笔,写到公路两旁树木上的无数麻雀被一声巨响震落在地,或昏迷或死亡。这一笔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想,便已跨入文学之门。”同样的例子还有记者叙述一位从20楼跳楼的女子在下坠过程中牛仔裤绷裂的报道,“就是那一个细节令读者印象深刻,也是绝妙的文学之笔。” 忆过去一脸伤感 著名作家王安忆当晚三度余华,《兄弟》是否他企图与现实和解之作:“你曾亲口说过,写作《活着》是因为你与现实生活关系紧张。”但余华认为,《兄弟》或许没有《活着》那么激烈,但那代表了“我表达与现实之间紧张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在王安忆的再次下,余华表示,如果要说和解,20年后回头来看,“我倒宁愿和上世纪80年代的现实和解。”当时还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他,常常与莫言等几位朋友一起去朱伟家里看各种录像带电影……回首那个年代,余华的语气中满是怀旧。 “过了20年就能和解,那只是时间差的问题。那是否意味着,20年后你也将与今日和解?”王安忆显然不依不饶,而余华却表现出一丝伤感。“当一切都成过往,冲突也会成为和谐的记忆。何况80年代的那几次紧张局势,将不同风格的作家们的命运紧密相连。现在大家都散了,各写各的,很少再有机会整个通宵在一起彻谈文学。” 说《活着》 “为何小说不像电影?” 由张艺谋执导、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拍摄至今已有13个年头,回忆起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的情景,余华依旧记忆犹新,“我还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800多人一起看的首映。当时,看完感觉很失望,马上给张艺谋打电话说,这部电影不用叫《活着》了,因为我强烈感到,电影一点儿也不像我的小说。” 但此后,许多国家却因为这部电影而邀请余华出国访问。对此,他不无调侃地说道:“要知道,请张艺谋那可是很贵的,所以他们很乐意请我这个原著作者,便宜嘛。” 每次出国,主办方都会组织播映电影《活着》,余华因此陪着看了20多遍,“看得腻味透了,但最后我发现,有一个奇迹出现了,我居然不止一次自问:‘为什么我的小说不像这部电影呢’?” 说起出国的经历,余华也谈到了他独特的“混乱审美”:“阿姆斯特丹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城市。这个城市有无数自行车,车库里层层叠叠地堆着这些车,路边也横七竖八锁了很多自行车,简直混乱到了不能再‘美’的程度。” (记者/干琛艳)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