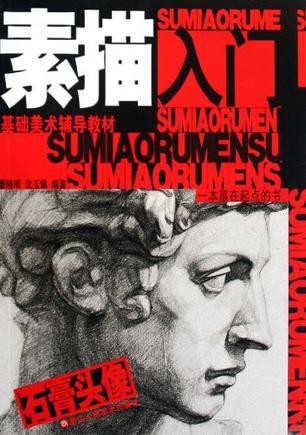刺蒺藜的现代研究
 救药你
救药你 氦
氦
果实含刺蒺藜甙(tribuloside)即银椴甙(tiliroside),山柰酚(kaempferol),山柰酚-3-葡萄糖甙(kaemopferol-3-glucoside),山柰酚-3-芸香糖甙(kaempferol-3-rutinoside),槲皮素(quercetin),维生素C,还含薯蓣皂甙元(diosgenin)、过氧化物酶.。种子含痕量哈尔满(harman),种子油中的主要脂肪酸有棕榈酸(palmitic acid),硬脂酸(stearic acid),油酸(oleic acid),亚油酸(linoleic acid)及亚麻酸(linolenic acid)等。干果含脂肪油及少量挥发油、鞣质、树脂、甾醇、钾盐、微量生物碱、皂甙.种子含生物碱哈尔满(Harman)和哈尔明碱(Harmine),但不含皂甙. 1. 对血压的作用 白蒺藜水浸液、乙醇-水浸出液和30%乙醇浸出液对麻醉动物有降压作用.醇提取物对狗的降压作用是通过胆碱能神经实现的,阿托品以及切断双侧迷走神经能阻断此作用.其生物碱部分对犬血压无影响,但对蛙心有抑制作用,水溶性部分有中度降压作用.临床研究表明: 治疗量的蒺藜皂甙对患者血压无明显影响.2. 对心脏的作用 动物实验表明: 蒺藜皂甙有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冠状动脉循环、增强心脏收缩力、减慢心律的作用,亦能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垂体后叶素及异丙肾上腺素所诱发的缺血性心电图变化,有抗心肌缺血和缩小心肌梗死范围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 患者服用蒺藜皂甙治疗冠心病,有缓解心绞痛、改善心肌缺血的作用,并能不同程度地改善患者的胸闷、心悸、气短和心前区疼痛等症状.3. 抗动脉硬化的作用 蒺藜皂甙给家兔口服10mg/kg,连续60天,能显著降低实验性血高胆固醇症的胆固醇水平,升高卵磷脂/胆固醇比值.预防实验表明: 蒺藜皂甙可显著抑制血胆固醇增高,并可抑制卵磷脂/胆固比值下降.此外,尚有抑制动脉、心肌及肝脏的脂质沉着作用.但亦有报告认为,临床治疗剂量的蒺藜皂甙对血脂无明显影响.4. 利尿作用 白蒺藜水煎剂及其灰分的水提取物有利尿作用,其利尿作用主要是由于钾盐的存在.有报告认为,除了钾盐外,生物碱部分亦有一定的利尿作用.临床治疗对腹水及水肿病人有效.但亦有报告指出,在盐水负荷的大白鼠实验中,利尿作用并不理想.5. 强壮作用和抗衰老作用 蒺藜皂甙对机体有一定的强壮作用,对机体衰老过程中某些退化性变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实验表明: 蒺藜皂甙能使因d-半乳糖所致衰老模型小鼠的脾、胸腺及机体的重量明显增加,显著降低胆固醇及血糖水平,减少老年小鼠脾内色素颗粒,并对其聚集程度有明显改善趋势;能延长大鼠的游泳时间,对大鼠的肾上腺皮质功能有双相调节作用;能增加幼年小鼠肝及胸腺的重量,增强小鼠耐高温和抗寒能力;对羽化前果蝇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能延长果蝇的寿命.6. 对性机能的作用 蒺藜茎叶总皂甙对去睾丸雄性大鼠精液囊及前列腺发育无促进作用,亦不能使去卵巢小鼠子宫重量明显增加,提示其无雄激素和雌激素样作用;但其能促进幼年小鼠性器官的发育,说明该药有促性腺激素样作用.然而该作用可被去垂体和预先注射吗啡所抑制,则说明可能是先刺激下丘脑释放促性腺激素释放因子,后者再通过垂体前叶实现其作用的.7.对平滑肌作用:水提取部分对大鼠度体肠管有对抗乙酰胆碱收缩的作用,生物碱部分亦能对抗大鼠离体肠管及蛙腹直肌因乙酰胆碱所引起的收缩作用。8. 其他作用 白蒺藜生物碱及水溶部分均能抑制大鼠小肠的运动,能与乙酰胆碱的作用相拮抗.蛙腹直肌实验所见亦证明蒺藜醇提取物有抗胆碱酯酶活性;其中枢兴奋作用也是抗胆碱酯酶作用的结果.植物提取物可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的生长.
蒺藜是壮阳的吗
 测谎器
测谎器 无念
无念
药理作用1、蒺藜的抗衰作用和强壮作用在临床上发现蒺藜皂苷能增强机体 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 可用来防治老年人免疫功能降低。2、蒺藜的性强壮作用蒺藜中提取的一种单一成分皂苷——原薯蓣皂苷能增强性欲,提高性能力。3、蒺藜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蒺藜总皂苷对缺氧再给氧、缺血再灌注心肌有保护作用引,并且与提高机体内源性抗氧化能力、降低脂质的氧化程度有关。4、蒺藜对脑血管的作用 共20张蒺藜的图片能增加脑缺血部位的血供,起到改善脑循环、保护缺血脑组织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蒺藜皂苷对磷酸二酯酶 有抑制作用。5、蒺藜对神经系统的作用研究表明,蒺藜皂苷可以降低缺氧/复氧诱导的皮层神经元的凋亡,减轻细胞损伤这种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抑制神经细胞内钙超载有关。6、蒺藜的抑癌作用在研究中还发现,蒺藜醇提取物中的蒺藜总皂苷可显著抑制人乳腺髓样细胞的增殖。7、蒺藜的利尿作用蒺藜果实的水浸液部分具有轻微的利尿作用,临床上对腹水和水肿病人有效。8、蒺藜的降血糖作用蒺藜水煎剂能显著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和正常小鼠的糖耐量 。9、蒺藜的其他作用研究发现蒺藜具有调节血脂、调节体内微量元素含量、抗菌镇痛、保护视网膜神经细胞等作用。
蒺藜皂甙的一般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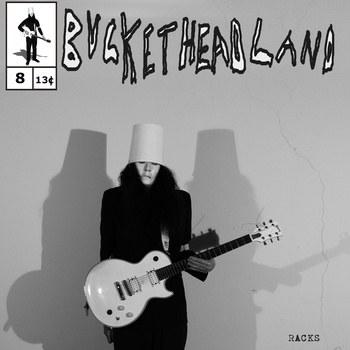 不忠者
不忠者 教之末也
教之末也
近年来,以刺蒺藜(Tribulus Terrestris)提取物为主要成分的运动保健营养品风靡欧美乃至全世界,受到众多的体育运动员的青睐。刺蒺藜在我国中医药的应用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用其入药治疗阳痿,并纳入了春药处方。近期国内外的科研机构研究发现:刺蒺藜能刺激人体垂体促黄体生成素的分泌,进而促进男性睾丸酮的分泌,提高血睾水平,增加肌肉力量,促进体力的恢复,因而是一种理想的性功能调节剂,临床研究证明:刺蒺藜能增加精子的数量和提高精子活力,增强性欲及性能力,勃起的频数和硬度也有所提高,性生活后性能力的恢复较快,从而提高了男性的生殖能力。目前临床实验尚未发现有毒性和不良作用。但该领域的研究还是十分有限的,尚有待于进一步对药理及其同服其它药物时的是否有害做进一步探讨。它的药物作用原理与促合成激素前体物雄烯二酮和脱氢异雄酮等合成类固醇类兴奋剂不同。使用合成类固醇类兴奋剂,虽然能够提高睾酮水平,但却抑制自身睾酮的分泌。一旦停药,体内睾酮就分泌不足,导致体质虚弱,浑身无力,容易疲劳,恢复缓慢等。而使用刺蒺藜引起的血睾升高,是自身睾酮的分泌加强所致,根本不会出现自身睾酮合成抑制的情况。 刺蒺藜是一种常年生蔓本植物,生长于中国、印度、东欧、非洲等地。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刺蒺藜有壮阳作用,用其入药治疗阳痿,并纳入春药的处方。另外刺蒺藜还被用做止血药,治疗尿石症、炎症和关节炎。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刺蒺藜能够刺激人体垂体促黄体生成素的分泌,进而促进睾酮的分泌,提高血睾的水平,增加肌肉力量,促进体力的恢复。刺蒺藜不是兴奋剂,而且,服用刺蒺藜药物,可有助于刺激和调节兴奋剂引起的自身睾酮的分泌抑制,使人体返回到正常状态。临床研究证明,刺蒺藜可增加精子的数量和提高精子的活力,增强性欲和性能力,勃起的频数和硬度也有所提高,性生活后性能力的恢复加快,提高男子的生殖能力。刺蒺藜还有其它药物作用:改善和调节更年期综合症,稳定情绪,降低高血脂和高血压,改善免疫功能,增加血红细胞和白细胞数,抗菌抗炎,缓解骨关节的疼痛,提高心肌收缩力,预防和治疗尿道结石,抗氧化及预防衰老等。
刺蒺藜提取物的安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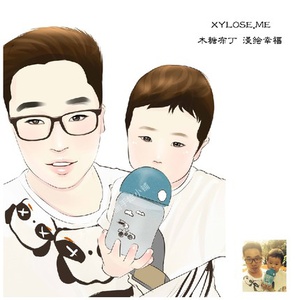 德也
德也W刺蒺藜片和Cla一起吃好不好
 我
我研究植物类型的论文,字数不限。超级高分,重酬
 正正之旗
正正之旗 儒墨皆起
儒墨皆起
水仙花(2篇任选) 我家阳台上有一盆美丽的水仙花,我可喜欢它了! 水仙花长得既漂亮又高雅.每次我放学回家总爱跑到阳台上看水仙花.水仙花的底部有无数条白色的须根,聚在一起,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的胡须,雪白雪白的. 水仙花还长有一片片翠绿的大叶子,它为水仙花增添了几分美丽之处. 再来讲一讲水仙花的花茎吧.它就像大家经常吃的韭菜芯.这个花茎长得非常笔直.花茎上的花朵长得更美.它可是用六朵白色的小花瓣组成的.花瓣向外舒展开,只见花瓣中的黄色花芯.整个花朵就像是一个特致的小酒杯,金光闪闪.水仙花在微风中仿佛是一位花仙子,正在偏偏起舞,真是令人赏心悦目.呵,怪不得有”凌波仙子”的美称. 我爱我家那盆水仙花,它给我带来了欢趣,给我带来了快乐 2 小时候,我一直住在外婆家。那时,外婆家的院子里种了好多好多美丽的花儿。春天有迎春花、牡丹花;夏天有太阳花、蟹爪莲;秋天有菊花、一串红,夏天有腊梅花、水仙花。 其中我最喜欢水仙花,喜欢它的外表,更喜欢它的“内心”。它虽然没有牡丹花那样娇贵,没有太阳花那样红艳,没有菊花那样引人注意,也没有腊梅花那样清香醉人。可是水仙花亭亭玉立,水仙花玉洁冰清。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水仙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水仙花素有“凌波仙子”的美称。的确它那动人的身姿使人一见倾心。 外婆家的那几盆水仙花可美了。 一月,水仙花开了!它那翡翠般的碧叶翠绿翠绿,绿得发光,绿得鲜亮,纵横交错的绿叶间,错落有致地开着几朵洁白无瑕的小花,花中嵌着一属黄金般的花蕊,散出阵阵淡淡的幽香,显得格外高雅。水仙花与泥土无缘,雨花石是它的“土壤”。我想:我要像它那样在思想上纯粹洁白,没有一点污泥。水仙花的根部像只大洋葱,根下长着白色的根须,它们像一条条长长的蚯蚓绕着一块块坚硬的雨花石,又显得十分倔强。 一阵风拂过,小花摇晃着脑袋,摆动着它柔美的身躯,似乎穿着水晶衣裳在水石上翩翩起舞,使人见了心旷神怡。 冬天,很多花儿都经不住严寒的摧残,受不了命运的考验——枯萎了。而水仙花却毫不畏惧,当室外寒风凛冽、冰天雪地的时候,它傲然挺立着,还是那么精神抖擞、生机盎然,仿佛在与寒风搏斗,如此坚忍不拔,使人越来越喜爱它了。 我爱水仙!爱它的美丽芬芳,爱它的高尚纯洁,更爱它的顽强不屈! 我爱荷塘 你们喜欢什么?我喜欢夏天的荷塘. 初夏,荷叶从水里探出嫩黄色的小脑袋.到了盛夏,嫩绿的荷叶变成一个个碧绿的大盘子.盖漫了荷塘.荷花也不甘示弱,从淤泥中探出了粉红色的脑袋.荷花虽然是从淤泥中生长出来的,但花朵却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可爱!真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有些荷花半卧在水中;有的半开着;有的荷花中露出了嫩黄色的小莲蓬.......荷花千姿百态,美丽极了,让人目不暇接! 清晨,每当从荷糖经过,荷花总是让风婆婆把清香带给人们.荷花上.荷叶上镶满了晶莹透亮的露珠,不时滴答一声,原来是露珠宝宝跳入水中的声音.鱼儿围着荷花跳起了 舞,荷花.荷叶.露珠宝宝都是鱼儿忠实的观众.露珠落入水中的滴答声则是观众给鱼儿的掌声.看到这般景色,真想和它们一起玩,一定也和我一样想和它们一起玩耍吧! 在炎炎夏日下,荷塘变得更加美丽.每个过路人经过荷塘都会随便的摘下几片荷叶戴在头上,挡住火辣辣的太阳.荷塘不仅仅是外表美,还有一种默默奉献的精神,这难道不算一种美吗? 这么可爱的荷塘难道不值得你我喜欢吗? 我爱你-----可爱的荷塘! 1·植物学方面 在19个世纪对我国植物作过比较多研究工作的是俄、英、法三国。俄国对我国植物的研究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与其接壤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他们在1804年就编出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植物志。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了《阿尔泰植物志》(Flora Altaica 1829-1834)。在我国的北京和内蒙的一些地方收集过植物标本的宾奇(A.Bunge),则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植物作过一些研讨。当然,对我国植物研究得的沙俄植物学家是马克西姆维兹(C.Maximowicz)。他是上个世纪西方研究我国植物的数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曾亲自到我国采集过生物标本的少数几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马克西姆维兹是彼得堡植物园的首席植物学家,俄帝国科学院院士和植物博物馆主任。在我国的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作了长期而广泛的植物学采集。此外,对那周边的日本和朝鲜的植物也作过很多的采集。对我国东北和朝鲜日本的植物颇为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俄国考察队和东正教使团人员采回的植物标本也是经他鉴定发表的。著名的如普热泽瓦尔斯基(N.M.Przewalski)、普塔宁(G.N.Potanin)、皮尔塞卿斯基(P.J.Piasetski)等人在我国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采得的植物标本大多由他整理发表。由于他还颇有见地地与英、法等西欧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标本交换关系,所以英、法等国的采集者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收集的标本也有不少由他定名发表。 马克西姆维兹前后用近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我国的植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阿穆尔 [4] 植物志初编》(Primitiae Florae Amurensis 1859),书中共记述985种植物,包括57种苔藓。其中有新属4个,新种112个。书末还附有“北京植物索引”和“蒙古植物索引”。完成这项工作后,他曾试图全面记述东亚各国植物,后来意识到这非他力所能及,转而描述新种和订正原来记述过的属种。 从1866至1876年,他发表了20篇专文,按属别描述日本和我国东北的植物。尔后又于1876至1888年,同样按属排列发表了8个分册的《亚洲植物新种汇要》(Diagnoses Plantarnm Novarum Asiaticarum) [5] 。他曾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数次率人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收集的大量植物标本,发现新种300多个,新属9个。1889年,他着手系统整理普热泽瓦尔斯基在我国采的植物,但只完成两个分册,分别为《唐古特 [6] 植物》(Flora Tangutica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具花托花和盘花植物 [7] ),及《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 [8] 部分地区植物名录》(Enumeratio Plantarum Hucusque in Mongolia nec non Adjacente Parte Turkestaniae Sinensis lectarum 1889)第一卷第一分册。《唐古特植物》共描述植物203种,其中有30个种是首次描述。连同以前在科学院期刊发表过的,总计有两个新属60个新种。绝大部分植物附有插图。《蒙古及其邻近的中国突厥斯坦部分地区植物名录》第一分册记植物330种,其中记有蒺藜科的一个新属和22个新种。同年,他还出版《普塔宁和皮埃塞泽钦所采的中国植物》(Plantae Chinenses Potanianae et Piasezkianae 1889 )的第一分册(从毛茛科到马桑科)。 马克西姆维兹先后记述我国植物数千种,其中有新种数百个。还描述新属十多个。很明显,他对我国东北数省、内蒙、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与俄国毗邻地区植物的区系作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与马克西姆维兹同时,还有不少俄国植物学家研究过我国植物。曾任彼得堡植物园园长的雷格尔(E.Regel)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植物学家,1835年即出版过《俄国植物志》。他和贺德(Fr.v.Herder)分别研究了雷德(G.Radde)在我国东北采的植物,前者研究离瓣花双子叶植物(从毛茛科到石竹科),后者研究合瓣花植物、无花被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并于1864—1892年以《雷德所采植物》(Plantae Raddeanae)的名称发表。 当然,在马克西姆维兹之后以研究我国植物著名的俄国人最早的要数柯马洛夫(V.L.Komarov),这位植物分类学家于19世纪末曾在我国东北和朝鲜采集,得标本6000余号。此后,他分别于1901—1902,1903—1904,1905—1907刊行了他编写的三册《满州植物志》(Flora Manchuriae)。他还研究了不少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植物属种。另外,巴里宾(J.W.Palibin)等其他一些俄国植物学家也曾对我国的植物有过不少研究。 英国人对我国植物的研究与该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有相同之处,即很注意做类似普查性质的工作。早期英国的著名植物学家如胡克(W.J.Hooker),班克斯(J.Banks),林德赖(J.Lindley)乃至在华为领事官的汉斯(H.F.Hance)都曾对中国的植物作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见于有关的植物学期刊中。 胡克研究过许多我国的蕨类植物。后来,另一英国蕨类植物学家贝克尔(J.G.Baker)家也研究过大量的中国蕨类植物,他完成了胡克的《蕨类纲要》(Synopsis filicum)并添了许多新种。1873年,《蕨类纲要》出第二版时,贝克又把不少新种作为附录加上。此人对我国的百合科植物也有过研究。林德赖对我国的兰花作过不少研究。J·D·胡克(J.D.Hooker)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地方考察过,发表过那里的一些杜鹃,有些还经他引进英国。他还与当时英属印度加尔格达植物园的主任桑姆生(T.Thomson)合著了《印度植物志》(Flora Indica)。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数位英国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其原因很显而易见,就来自英国的四位最著名的植物采集者福群(R.Fortune)和韩尔礼(A.Henry)、威尔逊(E.H.Wilson)和福雷斯特(G.Forrest)而言,他们分别是园林协会,东印度公司,英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和一些著名花卉种苗公司的雇员,与商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61年,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Bentham)即出版了《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书中共记述香港植物1065种。在那以后的19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最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是丘园的赫姆斯莱(W.B.Hemsly)。众所周知,丘园是世界上研究植物学的中心,而赫姆斯莱与俄国的马克西姆维兹类似,也曾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研究我国植物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 赫姆斯莱1860年就曾在丘园工作,最初是作为边沁的助手。后来曾因健康等原因离开丘园,但在1883年又重新回到丘园工作。1884年,英国皇家学会决定,从它的政府科学拨款中拿一笔钱编写已知中国植物的目录,他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热心了解中国植物的美国商人福勃士(F.B.Forbes)也积极投身此项工作。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中国植物名录》(Indix Florae Sinensis 1886--1905)。这套著作的植物包括朝鲜、琉球所产,内容述及分布和同物异名的辨别等等。1896年,他研究了西藏的植物区系,发表“西藏植物”(The Flora of Tibet),这项研究被我国植物学家视为这一地区的先驱工作。他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西藏或亚洲高原植物”(The flora of Tibet or high Asia 1902)等。当然这只是他比较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他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上个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许多英国人采集的植物主要由他进行鉴定发表的。他发表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文章数以百计。 从1909年至1956年,在我国西南高地、缅甸和印度的阿萨姆及喜马拉雅山区作了长达近五十年地学和植物学考察和收集的瓦德,对该地区的植物分布及具体区域种类的多寡可谓见多识广。他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我国西南地区植物学区系和植被方面的文章。包括《绿绒蒿的故乡》(Land of Blue Poppy)、“中国喜马拉雅的植物”(The Sino-Himalayan flora 1927)、“西藏的森林”(The forests of Tibet 1935)、“西藏的地理学和植物学概论”(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botany of Tibet, being 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the country 1935)等等,对那里的植物区系特点,及地理环境对植物区系的影响等做了很有价值的探讨,提出了“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等有见地的概念 [9] 。 本世纪前期,支持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负责人鲍尔佛(B.Balfour),也是一位与我国植物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是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曾研究和定名了大量由福雷斯特自中国西南滇川等地引进的植物花卉和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引入爱丁堡植物园的大量报春和杜鹃花属植物。1922年,鲍尔佛死后,继任该园园长和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的斯密思(W.W.Smith)继续与福雷斯特合作,也研究了大量后者在华采集的植物,有关成果大多发表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期刊中。他熟谐我国喜马拉雅山一带的植物,也是报春花和杜鹃花属植物的专家。由于福雷斯特来华采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杜鹃花。他们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使爱丁堡成为研究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中心。 法国近代地理学发达较早,在17世纪中期,法国人就在北美的考察方面有出色的业绩;此外在18世纪中叶以前法国一直拥有北美加拿大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一些法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两地间生物的重要关系。如传教士杜德美和在我国海关任职的福威勒等。他们可能是最早注意东亚和北美生物区系间联系的人。鸦片战争后,法国人研究中国的植物以邻近法属殖民地越南、老挝等国的西南地区出色,这与他们的传教士在这一带的活动活跃密不可分。法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有较长的历史和出色的成就。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巴黎自然博物馆所属植物园栽种了大量由法国传教士送回的中国植物,该园的主要园丁卡约瑞(E.A.Carrière),发表了一些中国植物的新种,还引种了不少由西蒙和谭微道送回的植物,并在有关刊物中发表了大量栽培于该苗圃的中国观赏植物。曾任这个植物园主任的迪赛森(J.Decaisne)也曾描述和发表过大量来自日本和中国的植物新种。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时,在探讨中国栽培植物的时候曾经用了贝勒和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两个植物学家普兰琼(J.E.Planchon)和拜伦(H.Baillon)也研究过一些中国植物,其中一些为谭微道(A.David)所采。 当然,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研究中国植物的法国学者以弗朗谢(A.Franchet)最为著名。他和同时的马克西姆维兹、赫姆斯莱等人一样,堪称是那个时期研究中国植物的最杰出人物。此人在研究我国的植物之前,曾对日本的植物作过不少研究。从1878年开始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1881年他还着手整理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并进行相关的描述。他还鼓励在华的传教士积极为该博物馆收集标本。著名的传教士谭微道,赖神甫(G.M.Delavay)、法盖斯(P.Farges)、苏里(J.A.Soulié)等采集的标本主要是由他研究定名的。在此基础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共记载中国植物5000余种,新种1000多个,新属约20个。其中相当部分是赖神甫采自云南的植物。 弗朗谢的主要著作有《谭微道植物志》(Plantae Davidianae)。此书分两卷,第一卷的副标题是“蒙古和华北及华中的植物”于1884年出版,记载北京河北和内蒙等地的植物1175种,计新种84个。书后附标本图27张。第二卷的副标题是“藏东植物”于1888年出版,记载川西宝兴植物402种,其中163种为新种。书后附有17张标本图,包括小木通(Clematis armandi)、宝兴杜鹃(Rhododendron mupinense)、腺果杜鹃(Rh. David)和一张珙桐的彩图。谭微道所采的植物涵盖面很广,对于西方了认识中国的植物区系意义很大。 弗朗谢曾试图系统整理赖神甫从我国云南送回的20万号植物标本,但终究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转而描述其中新种。但即使这个任务,他也未能完成。通过长期对我国西南植物的研究,弗朗谢认为我国西南的川西、藏东和滇北是杜鹃花科、百合、报春、梨、悬钩子、葡萄、忍冬和槭属植物分布的中心。 [10] 他的上述看法大体是正确的,也为后来英、美和德国的植物学家继续这一地区植物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打下了基础。 弗朗谢之后,列维尔(H.Leveille)长期研究东亚植物,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二十余年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涉及我国的不少。20世纪上半叶长期研究亚洲植物的巴黎博物馆植物学家盖根湃(F.Gagnepain),也研究过不少中国植物。 德国柏林植物园和博物馆负责人、柏林大学教授代尔斯(L.Diels)曾长期研究瑞典人柏固(C.A.Bock)和奥地利人洛色恩(A.E.Rosthorn)在我国四川大巴山等地采集的中国植物,著有《中国中部植物》(Die Flora von Zentral-China 1901),记述了我国中部秦岭地区一带的植物数千种。他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近代植物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东亚高山植物区系》(Die Hochalpine Flora Ost-Asiens 1904)。其后,他又鉴定描述过英国采集者福雷斯特在华的首批标本。1913年,他又发表“中国西部植物地理学调查”(Untosuchungen zur Pflanzegeographie von West-China)。对我国西部的植物地理进行了研究,并尝试进行分区。 基于当时的研究成果,代尔斯对我国的植物地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尝试进行分区,同时指出我国植物区系的性质和成分。他认为中国中西部高山地区不但植物种类繁多,而且存在大量原始类型和由原始类型向进化类型过渡的中间类型,是大量植物种属的发祥地和分化中心。另外,这里的地质学证据也表明这里地层古老;同时,这里的动物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因此,在系统发生学上很值得详细研究。后来,他在赫姆斯莱、沙坚德等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对东亚的植物地理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东亚,尤其是中国内部,长富有北半球的普通植物。与北美植物的亲缘关系很近。有些属很发达,如黄精属、百合属、飞燕草属、淫羊霍属、小檗属、虎尔草属、杜鹃花属、报春花属、龙胆属、马仙蒿属及望江南属等等。他还指出,由于地层古老,且气候和地理条件优越,又未受地质变迁的大伤害,所以我国多有特产植物,如水青树属(Tetracentron )、杜仲属(Eucommia)和珙桐属(Davidia)等。这反应在他1929年出版的《植物地理学》等著作中。他还写有《秦岭及中国中部植物论文集》(Beiträge zur Flora des Tsing-Ling-shan und undere Zusatze zur Flora von Centrachina)。顺便提一下,20世纪30年代末,在洪堡大学学习的我国植物学家郝景盛,曾在代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写了“青海植物地理研究”和“柳属植物志要”两篇论文。 此外,另一德国植物学家和树木学家柯恩(B.A.E.Koehne)也曾为威尔逊采集的一些植物新种定名,主要是花楸属(Soubus )和山梅花属(Philadelphus)植物。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哈佛大学堪称是研究中国木本植物的中心。该校的植物学家沙坚德(C.S.Sargent)曾到日本等亚洲国家采集植物标本,熟悉东亚的植物。对我国的木本植物(主要由威尔逊等人收集)尤其有研究。从1913年起,沙坚德教授主编了《威尔逊植物志》(Plantae Wilsonianae),计三册,于1917年全部出版。该书记载了1907,1908,1910间,阿诺德树木园通过威尔逊等收集得的中国中西部木本植物。 在该书第一卷,描述了威尔逊采集植物种类的一半左右,其中包含两个新属,225个新种,162个树木新变种。全书总共描述植物3356个种和变种,是当时研究中国木本植物最广博的参考著作。至今犹为研究我国木本植物及湖北、四川植被的重要参考书。 沙坚德还根据自己长期对北美和东亚植物的研究,发表了两篇颇富创建性关于东亚和北美植物区系的论文。其一为“东亚和北美东部木本植物比较”(A Comparison of Eastern Asiatic and Eastern North American Woody Plants,1913),另一为“中国和美国木本植物种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Woody Species of China and America 1920)。在前一篇论文中,他就东亚北纬22.3度以北地区与美国得克萨斯格兰河以北地区的木本植物进行了比较。他逐科地指明两地的有无及属种的多寡和特有属种。在植物区系学上有重要意义。 1898年从德国赴美的瑞德(A.Rehder)也是对我国植物,尤其耐寒木本植物作过很多研究的树木学家。他长期在阿诺德树木园工作,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树木学教授。研究、描述过威尔逊和洛克(J.Rock)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许多植物。并发表了不少文章。 他出版过一些重要的树木学著作,包括《北半球寒温带地区栽培的耐寒树木索引》(Bibliography of Cultivated Trees and Shrubs Hardy in the Cooler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1949) [11] 。另一位曾与韩马迪在我国云南和四川收集大量植物标本的德国植物学家施耐德(C.K.Schneider),后来也去了阿诺德树物园,在那里作了四年的研究,分类描述了大量威尔逊在我国西部采集的植物。他后来成为以我国为分布中心的小檗属(Berberis)和丁香属(Syringa)的专家。 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植物学家梅里尔(E.D.Merrill1876—1956)是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梅里尔博士1902年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到美属菲律宾马尼拉服务,先在农林部,后来在国家实验局任职,最后任科学局局长。1924年回到美国,先后任加里福尼亚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实验场场长,纽约植物园园长,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和哈佛大学植物标本总监 [12] 。1920年他到浙江、安徽采集过标本。他很熟悉东亚植物。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不少学者采集的标本是由他鉴定命名的。象我国前辈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采着的一马鞭草科新属种,就是经他鉴定命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的。这属后来即成为纪念钟观光的钟木属。他鉴定我国学者送去的植物标本通常比较快速准确,为我国植物学家称道。他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华南、广东、海南岛植物的文章。1920年他路经南京时,与我国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相识,后来建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合作研究广东和海南植物,先后一起发表了“广东植物志资料”,“海南植物志资料补充”等许多研究文章。在纽约植物园工作期间,他曾指导我国植物学家裴鉴做博士论文。梅里尔先后研究东亚植物数十年。他和沃克(E.H.Walker)合作编写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 1938)及由沃克作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补编I》(Supplement I, 1960),收集东亚的植物文献相当充分,至今仍是研究我国和东亚植物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在华西南的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过重要植物学考察,并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H.Handel-Mazzetti),是本世纪上半叶研究我国植物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中国回到奥地利维也纳后,潜心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并因对分布中心在我国西南的报春花属和珍珠菜属植物有精深的研究,而被当时的学术界目为专家。他还约请了其他一些植物学家研究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又查阅了当时西方各大植物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国植物标本。编写了《中国植物志要》(Symbolae Sinicae),1937年在维也纳全部出版。 韩马迪的著作共分7卷,分别为藻类、真菌、地衣、藓类、苔类、蕨类和种子植物。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许多分类群都有颇深入而有见地的探讨,是当时国际上研究我国植物的一部带有总结性重要著作。他也因此植物学界誉为中国叙述植物学的权威。这部著作至今对于我国植物学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他还发表过《中国植物地理结构及其亲缘》(The Phyto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Affinities of China)等有关我国植物地理学的文献。并曾根据他在我国西南等地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全中国的地理分区工作。参考资料:http://www.hudong.com/wiki/%E6%A4%8D%E7%89%A9
蒺藜皂甙和肌酸
 离于天下
离于天下 大奖章
大奖章
都不建议吃激励皂苷得配合ZMA吃才达到效果,也不过是增加激素的,运动量少的话,起不到什么作用。肌酸要天天吃,不能间断,你每周锻炼5次的话吃肌酸合适,如果你每周锻炼2,3次的话,还是别吃了
中国的十大发明是什么?
 绘图人
绘图人 陈美凤
陈美凤
中国远不止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共有5000多项,出名的100项:1、鼓:传说公元前3500年中国人已有人造的鼓。公元前3000年,做鼓的方法是用兽皮蒙在框架或容器上。1980年在山西省襄汾陶寺村的6座墓中出土了七具用鳄鱼皮蒙制之“灵鼍之鼓”,用挖空了的树干作鼓腔的夏代木鼓遗痕,其中建鼓1面,悬鼓2面,扁鼓4面。其年代约在4200年前的古人类墓葬。2、二进位制:中国古老的易经就使用二进制来进行演算。相传在公元前3000年伏羲发明了二进位制 。3、绳索:公元前2800年,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创造麻绳的技术。4、指南针:相传公元前2700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发明了指南针。5、养鱼法: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已经懂得养鱼。6、赤道式天文仪:公元前2400年,中国人发明了赤道式天文仪。7、十进计数制:中国人 《周易》确定了十进制,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十进制系统。8、印刷术:公元前1324年,中国人已会雕刻印章,用墨水印在文件上。1040年代北宋刻字工人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德国人古腾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早四百多年。1107年,中国人还发明了彩色印刷术。9、漆:漆是用漆树皮里的黏汁制成的用以装饰和保护物器的涂料。原始社会,我国人民就已发现漆树并懂得使用由漆树的汁液制成的天然漆来做涂料。 中国人最迟在公元前13世纪已经发明使用了漆。10、铜镜:我国铜镜的制作历史可追溯到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铜镜。11、伞:公元前1100年的早在春秋末年,鲁班的妻子云氏把竹子劈成细条,在细条上蒙上兽皮,样子很像“亭子”,而且收张自如。东汉时出现纸伞,宋时制出了绿油纸伞。以后历代对伞均有改进,如油伞、蝙式伞等。1747年,我国的伞传入英国,成为英国第一把伞。12、风筝:相传中国东周春秋时期的墨翟以木头制成木鸟,研制三年而成,是人类最早的风筝。风筝飞上天空为飞机飞上天空提供了原理和灵感。13、米酒:约在六千年前,人工酿酒就开始了。传说第一个造酒的人是上古时期的杜康,杜康造酒就是造的米酒,度数不高还很浑浊。14、弓箭: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村距今两万八千年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发现了一件燧石镞头,是用很薄的长石片制成的,尖端周正,肩部两侧变窄似呈铤状。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箭头之一。而欧洲的意大利在公元10世纪才使用弓。15、古代机器人:西周时期,中国的能工巧匠偃师就研制出了能歌善舞的伶人,这是中国最早记载的机器人。16、分行栽培与精细耕地法: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分行栽培与精细耕地法;欧洲人到1731年才使用此项技术,比中国晚了二千四百年左右。17、铁犁:铁犁牛耕均在春秋出现,战国铁犁牛耕扩大推广;此后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铁犁。欧洲人到17世纪才使用铁犁,比中国晚了二千三百年左右。18、大定音钟:中国人于公元前6世纪发明了大定音钟;欧洲人到公元1000年才有定音钟,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年左右。19、长明灯:大约在公元前589年,中国人发明了长明灯。灯蕊为石棉;灯油为海豹油或鲸油。20、算盘:东汉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徐岳,世界第一位“珠算”提出者和“算盘”记录者。21、地毯:地毯是中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品。公元前五百年地毯已在中国应用。著名的手工地毯,有实物可考的有2000多年。22、双动式活塞风箱:中国人于公元前5世纪发明了双动式活塞风箱。西方于16世纪才用双动式活塞风箱。比中国晚了二千一百年左右。23、水涌钵: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水涌钵。在水涌钵中加入一定的水,摩擦钵的两边耳朵,水会涌起来,这利用的是物理上驻波的原理。24、空位表零法:中国人在公元四世纪以前就开始用空位表示零,中国的算盘就是这样表示的。25、化学武器:利用毒气进行化学战的历史,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早期。26、马胸带换具: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马胸带换具。27、石油照明法:大约于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石油照明法和天然气照明法。28、铸铁术: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铸铁术,运用鼓风炉来铸铁。29、马肩套挽具: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马肩套换具。30、硝石鉴别方法: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发现了硝。发现硝石为后来发明火药奠定了基础。31、世界上第一条等高运河-灵渠:西方于公元13世纪才建了等高运河,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年左右。32、立体地图:中国人最迟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立体地图。33、吊桥:中国人李冰于公元前3世纪在四川省灌县修建了安蓝桥。这是世界最早修建的竹缆链桥。34、记谱法: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人已发明了记谱法。35、造纸术: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公元105年东汉时期的蔡伦制出了蔡侯纸。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36、降落伞: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降落伞。西方人利诺曼德于1783年,多次从树顶或房顶上跳下去,结果很成功,他把这叫降落伞;这比中国人发明降落伞晚了一千九百多年。37、焰火: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焰火。38、微型热气球: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发明微型热气球。39、墨水: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墨水。40、曲柄摇手: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曲柄摇手;西方于公元9世纪才使用曲柄摇手,比中国晚了七百年左右。41、耧: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耧,而西方到1566年才制成条播机,比中国晚了一千八百年左右。42、旋转式扬谷扇车: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旋转式扬谷扇车。到18世纪初,西方才有了扬谷扇车,比中国晚了二千年左右。43、平衡环:公元前140年,中国人房风发明了平衡环,中国人发明的平衡环比西方领先700年左右。(简仪)44、白兰地与威士忌:公元前126年,中国人发明了白兰地和威士忌,直到1570年这种制酒法才传到欧洲,并引起欧洲人的轰动。制白兰地酒欧洲人比中国人晚了一千四百年左右。45、豆腐:公元前125年,中国人刘安发明了豆腐。同年,中国人还发明了激素结晶体提取法,这比欧洲人领先了二千二百年。46、走马灯:公元前121年中国人发明了走马灯。西方人约翰·巴特于1634年描述了走马灯,比中国晚了一千七百多年。 走马灯上有平放的叶轮,下有燃烛或灯,热气上升带动叶轮旋转,这正是现代燃气涡轮工作原理的原始应用。47、百炼法-用生铁炼钢法:公元前120年,中国人发明了用生铁炼钢法,也称“百炼法”。而西方到1856年才开始用生铁炼钢,比中国晚了二千年左右。48、指南车:相传早在5000多年前,黄帝时代就已经发明了指南车,当时黄帝曾凭着它在大雾弥漫的战场上指示方向,战胜了蚩尤。西周初期,当时南方的越棠氏人因回国迷路,周公就用指南车护送越棠氏使臣回国。三国马钧所造的指南车除用齿轮传动外,还有自动离合装置 ,是利用齿轮传动系统和离合装置来指示方向。49、曲柄:战国时期,大约公元前100年中国人发明了曲柄。曲柄摇杆是工农业生产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技术。50、独轮车:独轮车是一个以人力推动的小型运载工具,或称为「鹿车」、「辘轳车」。西汉晚年中国人发明了独轮手推车;而西方到公元11世纪才使用独轮车,比中国晚了一千二百年。51、密封实验室:公元前1世纪,中国人发明并建造了密封实验室。52、传动带:公元前15世纪,中国人发明了传动带。欧洲人用传动带是1430年,比中国晚了一千四百多年。53、滑动测绘仪:中国人于公元5年发明了滑动测绘仪。而西方到1638年才使用滑动测绘仪,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多年。54、水力风箱:公元31年中国人发明了水力风箱。中国人利用水利的创举是现代社会以前能源供给中最有意义的突破之一。它是朝工业革命迈出的重大步伐之一。55、龙骨水车:公元80年,中国人发明了龙骨水车;而欧洲第一架方形板叶的龙骨水车制于16世纪,是直接以中国的设计为模式而制作的,比中国晚了一千五百年左右。56、船尾舵:公元1世纪,发明了船尾舵;而西方到公元1180年才在教堂的雕刻上出现了舵,比中国晚了一千一百年左右。57、瓷器: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再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终于摆脱了原始瓷器状态,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西方到18世纪才有瓷器。58、地动仪:公元132年中国人张衡发明了地震探测器――地动仪。外国人德拉·奥特弗耶于1703才设计出第一台现代地震仪。这比张衡发明的古代地震仪――地动仪要晚1571年。59、催泪弹:公元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催泪弹。60、船中水密舱:中国人于公元二世纪发明了船中水密舱。61、平衡四角帆:公元2世纪中国人发明平衡四角帆。62、定量制图法:中国古代著名的发明家张衡在公元2世纪发明了定量制图法,从而使制图科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西方直到15世纪才出现有相当价值的地图,这比张衡发明定量制图法晚了一千三百年左右。63、纺车:中国人于公元121年发明了纺车;而西方到公元1280年才用纺车,比中国晚了一千一百多年。64、纯硫提炼法:中国人于公元2世纪发明了纯硫提炼法。中国人发明的营养缺乏症治疗法比西方领先了一千七百年左右。65、七根桅杆船:公元260年中国人发明了七根桅杆船。66、车前横木:公元3世纪中国人发明了车前横木。67、马蹬:马蹬是现代骑马必备的一种工具,使用时拴于马上,骑马者的脚部悬挂处,唐朝以后被广泛应用。据漠北出土壁画等文物,公元3世纪中国匈奴人可能为最早使用马蹬的民族。西方到公元5世纪才制出马蹬,比中国晚了二百年。68、自动控制机:中国人于公元前3世纪发明自动控制机。69、人造金: 中国人葛洪于公元3世纪发明了人造金。70、初级砷提炼法:公元3世纪,中国著名炼丹家葛洪发明了初级砷提炼法。砷是制造火药的原料之一,西方比我国得到提炼法砷晚了几百年。71、卷线钓鱼器:中国人于公元3世纪发明了卷线钓鱼器,当时它叫做“钓车。而西方到1651年,才开始在鱼杆上使用卷线轮,比中国晚了一千三百年左右。72、直升飞机水平旋翼和螺旋桨:公元4世纪中国人葛洪已谈到关于直升飞机旋翼。那时中国有一种儿童玩具竹蜻蜓已如直升飞机的旋翼。它有一根轴,上面绕着一条线,轴上装着几个叶片,定好角度,一拉线,旋翼就向空中飞升上去。这种玩具对欧洲航空先驱者影响甚大。73、桨轮船:中国人于公元418年发明了桨轮船。74、“西门子式”炼钢法: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国人发明了“西门子式”炼钢法,当时叫“共熔”炼钢法。这就是1863年马丁一西门子平炉炼钢法。中国比西方早一千四百年左右。75、油印技术:公元500年中国人发明了油印技术。76、水力磨面机: 公元530年,中国人发明并制造出了水力磨面机。公元13世纪,欧洲人才使用这项技术,比中国晚了七百年左右。77、海滩航行:公元500年中国人发明了海滩航行。78、指针式标度盘装置:中国人赵达于公元570年发明了指针式标度盘装置。79、火柴:世界上第一根火柴是由中国人于公元577年发明的。中国人使用火柴几乎比欧洲人早1000年!80、国际象棋:中国人于公元6世纪发明了国际象棋。而西方到公元7世纪才下国际象棋,比中国晚了一百年左右。81、弓形拱桥:公元610年,中国建筑工程学派奠基人李春,发明并建造了弓形拱桥――通桥,又名赵州桥或大石桥,比西方于1345年建造的维奇奥拱桥,早了七百年。82、浮板:中国人于公元759年以前发明了浮板。83、熨斗:公元800年代,中国人发明了熨斗,并开始使用了它。84、纸币:中国人于公元8世纪发明了纸币,不过发行机构是政府。16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首先推出了钞票,比中国晚了七百多年。85、火药:中国人于公元850年发明了火药。十世纪时中国人已用来发信号和制造烟火。西方人到12世纪后期才开始关注火药,比中国晚了三百多年。86、扑克牌:公元9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扑克牌,西方到公元1377年,德国和西班牙也出现了扑克牌,比中国晚了五百年左右。87、火焰喷射器:中国人于904年发明了火焰喷射器,并且用之于打仗了。88、枪炮:大约公元905年,中国人发明了枪炮。这枪就是火枪(或称长矛)。欧洲人到1396年才开始用火枪,比中国晚了四百多年。89、麦卡托投影:公元940年,中国人发明了麦卡托投影;公元1568年英国才有人用麦卡托投影,比中国晚了六百年左右。90、链式传动装置:中国人于976年发明了链式传动装置――链式传动带;欧洲人到1770年才开始使用链式传动带,比中国晚了八百年左右。91、凸轮:中国人于公元983年发明凸轮,并应用于借水力提升的重型链。同一时间,在西方意大利塔斯坎民的一座浆洗作坊中应用了凸轮。92、运河船闸:公元984年中国人乔维岳发明了运河船闸,从而提高了河运能力。到1375年欧洲也建成了第一个船闸,这比中国已晚389年。93、种痘免疫法:中国人在公元10世纪发明了种痘免疫法。到1700年,作为预防天花的措施,轻型天花接种开始广泛在欧洲采用,由中国传去的这种接种方法,后来发展成为接种牛痘的免疫学。94、机械钟:公元11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机械钟。西方到13世纪才制出机械钟,比中国晚了二百年左右。95、水雷:中国人于公元1374年发明了水雷。96、大炮:中国于1280年发明了大炮。这时中国人制成了首批信而有徵的铜铁大炮(徵是验证的意思)。97、火箭:中国人于公元1150年发明了火箭,并使用了火药为燃料的火箭打仗。98、眼镜:中国人于公元1300年发明了眼镜,这时意大利也开始使用眼镜了。99、古代直升飞机:中国人徐正明于公元17世纪发明了直升飞机。公元17世纪中国苏州巧匠徐正明,整天琢磨小孩玩的竹蜻蜓,想制造一个类似蜻蜓的直升飞机,并且想把人也带上天空。经过十多年的钻研,他造出了一架直升飞机。它有像竹蜻蜓一样的螺旋桨,架驶座像一把圈椅,依靠脚踏板通过转动机构来带动螺旋桨转动,试飞时候,它居然飞离地面一尺多高,还飞过一条小河沟,然后落下来。100、回音壁:公元1530年,中国人发明了回音壁;同时,还发明了三音石和圆丘。它们皆建在天坛
中国古代科学成就
 漫步者
漫步者 可谓有矣
可谓有矣
1.印刷术 印章在先秦时就有,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据记载在北齐时(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纸盖印的印章作得很大,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了。 1、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的铜印。 2、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3年)在他著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见方(13.5×13.5)有120个字的大木印了。这已经是一块小型的雕版了。 3、佛教徒为了使佛经更加生动,常把佛像印在佛经的卷首,这种手工木印比手绘省事得多。 4、碑石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东汉以后,石碑盛行。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历时8年,全部刻成。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很多人争相抄写。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5、拓片是印刷技术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6、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上溯至战国。纸发明后,这种技术就可能用于印刷方面,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 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我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2.造纸术 汉初年,政治西汉麻纸稳定,思想文化十分活跃,对传播工具的需求旺盛,纸作为新的书写材料应运而生。许慎著《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100年。谈到“纸”的来源。他说:“‘纸’从系旁,也就是‘丝’旁”。这句话是说见当时的纸主要是用绢丝类物品制成,与现在意义上的纸是完全不同的。许慎认为纸是丝絮在水中经打击而留在床席上的薄片。这种薄片可能是最原始的“纸”,有人把这种“纸”称为“赫蹄”。这可能是纸发明的一个前奏,关于这种“纸”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汉书·赵皇后传》中记录了成帝妃曹伟能生皇子,遭皇后赵飞燕姐妹的迫害,她们送给曹伟能的毒药就是用“赫蹄”纸包裹,“纸”上写:“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由此推测纸可能与丝有一定关系。 远古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懂得养蚕、缫丝。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这种处理次茧的方法称为漂絮法,操作时的基本要点包括,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这一技术后来发展成为造纸中的打浆。此外,中国古代常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为丝麻脱胶,这种技术也给造纸中为植物纤维脱胶以启示。纸张就是借助这些技术发展起来的。 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造纸术的发明不晚于西汉初年。最早出土的西汉古纸是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发现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49年。 1957年5月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出土的古纸经过科学分析鉴定,为西汉麻纸,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18年。1973年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发现了不晚于公元前52年的两块麻纸,暗黄色,质地较粗糙。 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延村出土了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49年)的三张麻纸;1979年在甘肃敦煌县马圈湾西汉烽燧遗址出土了五件八片西汉麻纸。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的纸质地图残片,表明了当时的纸可供写绘之用。从上述西汉出土的纸的质量来看,西汉初年的造纸技术已基本成熟。 历史上关于汉代的造纸技术的文献资料很少,因此难以了解其完整、详细的工艺流程。后人虽有推测,也只能作为参考之用。总体来看,造纸技术环节众多,因此必然有一个发展和演进的过程,绝非一人之功。它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3.指南针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 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4.火药 我国现在看到的第一部记载火药配方的书,约成书于八九世纪。书中说“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火尽屋舍”的现象。这里的“密”应该是蜂蜜的“蜜”。蜜加热能变成炭。硫磺、硝石与炭混合,这就是火药的配方。 火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炼丹,制药实践结果,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唐朝末年,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部将郑 (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九国志.郑 传>。这里所说的(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火炮)是把火药制成环状,把吊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掷出去;(火箭)则是把火药球缚于箭镞之下,将吊线点燃后用弓射出。到了宋代,战争接连不断,促进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北未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先后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南未在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到了元代又出现铜铸火统,称为(铜将军)。这些都是以火药的爆炸为推动力的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下图为南未突火枪和北未火药箭。 在12,13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对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美法各国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 [编辑本段]1、源于炼丹术 炼丹术起源很早,《战国策》中已有方士向荆王献不死之药的记载。汉武帝也妄想“长生久视”,向民间广求丹药,招纳方士,并亲自炼丹。从此,炼丹成为风气,开始盛行。历代都出现炼丹方士,也就是所谓的炼丹家。炼丹家的目的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样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炼丹术流行了一千多年,最后还是一无所获。但是,炼丹术所采用的一些具体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显示了化学的原始形态。 炼丹术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火法炼丹”。它直接与火药的发明有关系。所谓“火法炼丹”大约是一种无水的加热方法,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对火法有所记载,火法大致包括:煅(长时间高温加热)、炼(干燥物质的加热)、灸(局部烘烤)、熔(熔化)、抽(蒸馏)、飞(又叫升,就是升华)、优(加热使物质变性)。这些方法都是最基本的化学方法,这也是炼丹术这种愚昧的职业能够产生发明的基础。炼丹家的虔诚和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挫折,使得炼丹家不得不反复实验和寻找新的方法。这样就为火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在发明火药之前,炼丹术已经得到了一些人造的化学药品,如硫化汞等。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 炼丹起火,启示人们认识并发明火药。 [编辑本段]2、火药的发明 炼丹家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化学方法,但是他们的方向是求长生不老之药,因此火药的发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炼丹家对于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在使用之前,常用烧灼的办法“伏”一下,“伏”是降伏的意思。使毒性失去或减低,这种手续称为“伏火”。唐初的名医兼炼丹家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中记有:硫磺、硝石各二两,研成粉末,放在销银锅或砂罐子里。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里和地平,四面都用土填实。把没有被虫蛀过的三个皂角逐一点着,然后夹入锅里,把硫磺和硝石起烧焰火。等到烧不起焰火了,再拿木炭来炒,炒到木碳消去三分之一,就退火,趁还没冷却,取入混合物,这就伏火了。 唐朝中期有个名叫清虚子的,在“伏火矾法”中提出了一个伏火的方子:“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内,烟渐起。”他用马兜铃代替了孙思邈方子中的皂角,这两种物质代替碳起燃烧作用的。 伏火的方子都含有碳素,而且伏硫磺要加硝石,伏硝石要加硫磺。这说明炼丹家有意要使药物引起燃烧,以去掉它们的猛毒。 虽然炼丹家知道硫、硝、碳混合点火会发生激烈的反应,并采取措施控制反应速度,但是因药物伏火而引起丹房失火的事故时有发生。《太平广记》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老人。当晚住在那里。半夜杜春子梦中惊醒,看见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顿时屋子燃烧起来。这可能是炼丹家配置易燃药物时疏忽而引起火灾。还有一本名叫《真元妙道要略》的炼丹书也谈到用硫磺、硝石、雄黄和蜜一起炼丹失火的事,火把人的脸和手烧坏了,还直冲屋顶,把房子也烧了。书中告戒炼丹者要防止这类事故发生。这说明唐代的炼丹者已经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硫、硝、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由于火药的发明来自制丹配药的过程中,在火药发明之后,曾被当做药类。《本草纲目》中就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 火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又容易着火,炼丹家对他并不感兴趣。火药的配方由炼丹家转到军事家手里,就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 [编辑本段]3、火药的应用 唐朝时的火药 火药发明之前,火攻是军事家常用的一种进攻手段,那时在火攻中,用了一种叫做火箭的武器,它是在箭头上绑一些像油脂、松香、硫磺之类的易燃物质,点燃后用弓射出去,用以烧毁敌人的阵地。如果用火药代替一般易燃物,效果要好得多。火药发明之前,攻城守城常用一种抛石机抛掷石头和油脂火球,来消灭敌人。火药发明之后,利用抛石机抛掷火药包以代替石头和油脂火球。据宋代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帝时(十世纪),郑王番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这可能是有关用火药攻城的最早记载。 两宋时的火药 到了两宋时期火药武器发展很快。据《宋史·兵记》记载:公元970年兵部令史冯继升进火箭法,这种方法是在箭杆前端缚火药筒,点燃后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出的气体的反作用力把箭簇射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公元1000年,士兵出身的神卫队长唐福向宋朝廷献出了他制作的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1002年,冀州团练使石普也制成了火箭、火球等火器,并做了表演。 火药兵器在战场上的出现,预示着军事史上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从使用冷兵器阶段向使用火器阶段过渡。火药应用于武器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武经总要》中记录的早期火药兵器,还没有脱离传统火攻中纵火兵器的范畴。随着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度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 硝酸钾、硫磺、木炭粉末混合而成的火药被称为黑火药或者叫褐色火药。这种混合物极易燃烧,而且烧起来相当激烈。如果火药在密闭的容器内燃烧就会发生爆炸。火药燃烧时能产生大量的气体(氮气、二氧化碳)和热量。原来体积很小的固体的火药,体积突然膨胀,猛增至几千倍,这时容器就会爆炸。这就是火药的爆炸性能。利用火药燃烧和爆炸的性能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火器。北宋时期使用的那些用途不同的火药兵器都是利用黑火药燃烧爆炸的原理制造的。蒺藜火球、毒药烟球是爆炸威力比较小的火器。到了北宋末年爆炸威力比较大的火器向“霹雳炮”、“震天雷”也出现了。这类火器主要是用于攻坚或守城。公元1126年,李纲守开封时,就是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围攻。金与北宋的战争使火炮进一步得到改进,震天雷是一种铁火器,是铁壳类的爆炸性兵器。元军攻打金的南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兵守城时就用了这种武器。《金史》对震天雷有这样的描述:“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并无迹,甲铁皆透”。这样的描述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这是对火药威力的一个真实写照。 火器的发展有赖于火药的研究和生产。《武经总要》中记录了三个火药配方。唐代火药含硫、硝的含量相同,是1比1,宋代为1比2,甚至接近1比3。已与后世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相近。火药中加入少量辅助性配料,是为了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火药是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发展的。 1044年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一书中介绍了三种火药配方,以不同的辅料,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的不同目的。 宋代由于战争不断,对火器的需求日益增加,宋神宗时设置了军器监,统管全国的军器制造。军器监雇佣工人四万多人,监下分十大作坊,生产火药和火药武器各为一个作坊,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史书上记载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这些都促进了火药和火药兵器的发展。 南宋时出现了管状火器,公元1132年陈规发明了火枪。火枪是由长竹竿作成,先把火药装在竹竿内,作战时点燃火药喷向敌军。陈规守安德时就用了“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公元1259年,寿春地区有人制成了突火枪,突火枪是用粗竹筒作的,这种管状火器与火枪不同的是,火枪只能喷射火焰烧人,而突火枪内装有“子巢”,火药点燃后产生强大的气体压力,把“子巢”射出去。“子巢”就是原始的子弹。突火枪开创了管状火器发射弹丸的先声。现代枪炮就是由管状火器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管状火器的发明是武器史上的又一大飞跃。 突火枪又被称为突火筒,可能它是由竹筒制造的而得此名。《永乐大典》所引的《行军须知》一书中提到,在宋代守城时曾用过火筒,用以杀伤登上城头的敌人。到了元明之际,这种用竹筒制造的原始管状火器改用铜或铁,铸成大炮,称为“火铳”。 1332年的铜火铳,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铭文的管状火器实物。 明代 明代在作战火器方面,发明了多种“多发火箭”,如同时发射10支箭的“火弩流星箭”;发射32支箭的“一窝蜂”;最多可发射100支箭的“百虎齐奔箭”等。明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与建文帝战于白沟河,就曾使用了“一窝蜂”。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发齐射火箭,堪称是现代多管火箭炮的鼻祖。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当时水战中使用的一种叫“火龙出水”的火器。据“武备志”记载,这种火器可以在距离水面三、四尺高处飞行,远达两三里。这种火箭用竹木制成,在龙形的外壳上缚四支大“起火”,腹内藏数支小火箭,大“起火”点燃后推动箭体飞行,“如火龙出于水面。”火药燃尽后点燃腹内小火箭,从龙口射出。击中目标将使敌方“人船俱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另外,该书还记载了“神火飞鸦”等具有一定爆炸和燃烧性能的雏形飞弹。“神火飞鸦”用细竹篾绵纸扎糊成乌鸦形,内装火药,由四支火箭推进,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火药筒并联火箭,它与今天的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的工作原理很相近。 火箭的发展,使人产生了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天空的愿望。根据史书的记载14世纪末,明朝的一位勇敢者万户坐在装有47个当时最大的火箭的椅子上,双手各持一个大风筝,试图借助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实现飞行的梦想。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万户被誉为利用火箭飞行的第一人。为了纪念万户,月球上的一个环行山以万户的名字命名。 [编辑本段]4、对外传播史 早在八、九世纪时,和医药、炼丹术的知识一起,硝也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当时的阿拉伯人称它为“中国雪”,而波斯人称它为“中国盐”。他们仅知道用硝来治病、冶金和做玻璃。13世纪火药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国家的。希腊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才知道火药。火药武器是通过战争传到阿拉伯国家,成吉思汗西征,蒙古军队使用了火药兵器。公元1260年元世祖的军队在与叙利亚作战中被击溃,阿拉伯人缴获了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火药武器,从而掌握火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阿拉伯人与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中阿拉伯人使用了火药兵器,例如阿拉伯人进攻西班牙的八沙城时就使用过火药兵器。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欧洲人逐步掌握了制造火药和火药兵器的技术。 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入欧洲,“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舰队,扬帆出航,去征服新的殖民地……。”参考资料:百度

 40004-98986
40004-98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