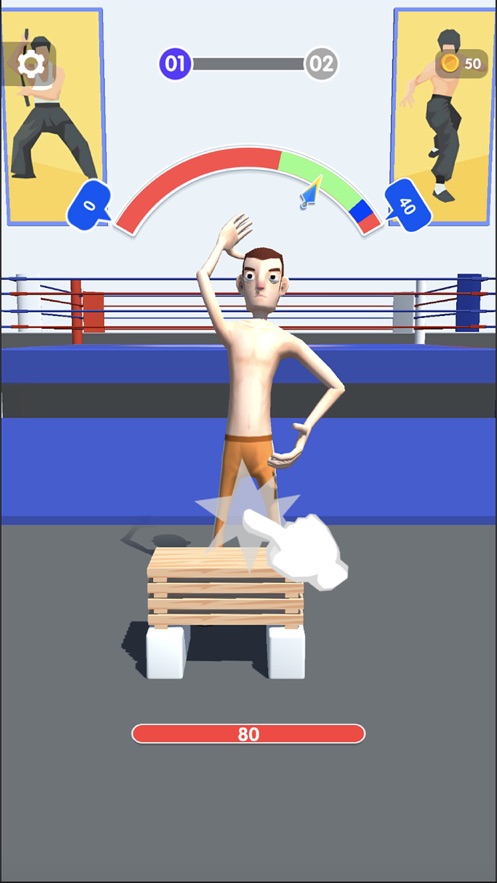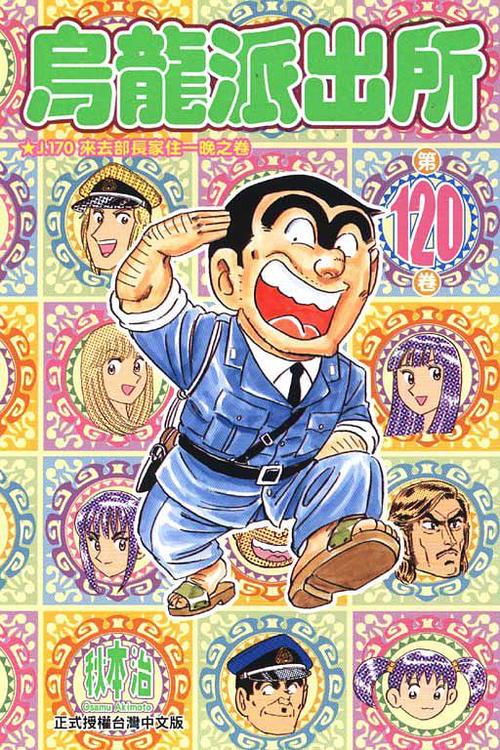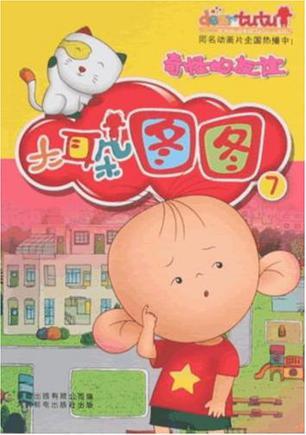论文学术翻译哪个好?
 莱纳斯
莱纳斯学术型硕士翻译成英文是什么呀?
 在人
在人 福亦不来
福亦不来
Academic master's degree学术来型自硕士【学硕】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专业型硕士【专硕】中国实行的学位教育主要分为:学术型学位(学术理论研究)或专业型学位(注重操作实际能力)两种教育并轨,但一直以来,更偏重学术型学位教育,而少注重专业型学位教育,所以很多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只能大谈阔论,能理论能研究,但操作能力差。为了与世界上学位教育接轨,因此增加专业型研究生教育。
学术期刊论文翻译找哪个?Editsprings翻译的准确吗?
 适得怪焉
适得怪焉论文学术翻译哪里比较好?谢谢了。
 岂更驾哉
岂更驾哉什么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
 马赛曲
马赛曲 马德里
马德里
瑞典学者Mats Alvesson与Kaj Sköldberge于2010年合6361作出版了《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台湾译本将书名译为《反身性方法论:质性研究的新视野》, 内地出版社译为《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 第一位作者,Alvesson,是瑞典德隆大学(University of Lund)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属于在管理学研究方法,特别是质性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哲学方面国际知名的领军人物, 也是领导力方面的著名学者。Alvesson在过去20几年里辛勤耕耘, 著述甚丰,除了在顶级期刊上不断有文献发表之外,还撰写或者编著十几本学术著作。他对后现代理论、话语分析、女权主义、批判性方法、诠释学等等都有深刻研究并出版过专门的文献对其进行探讨。 Alvesson是目前为数不多同时在方法论哲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极具极造诣的大师级学者。关注这部《反身性方法论》源于彭长桂同学在年初来港时的大力推荐。真难为小彭费心,得知我对此书有兴趣,他特地跑到位于中环的商务书店给我买来一本。小彭和我都热衷于质性研究。 在今天量化分析方法独揽学术研究霸权、众人飞蛾扑火般投入科学主义新宗教怀抱的时代,小彭仍然坚持走质性研究道路,试图通过案例分析折射社会实际,其精神实在可嘉。小彭头脑灵活,阅读面十分宽广,属于那种任何书都读下去, 而且对新思想极为敏感,灵感恒生的横向思维学子。这两年,在他的推荐下,我倒是读了不少书。如果不是小彭推荐的话,我有可能与这部《反身性方法论》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后生可畏。不过,书虽然有了,但是却一直放在我的案头,没有心思读。几次打开,不是因为分心的事情太多, 无法专心, 就是因为看到翻译的文字太艰辛,难以深入。总之, 就是读不进去。《反身性方法论》是一本方法论的理论著作,书中涉及大量带有浓重的哲学色彩的词语和概念,可以用“艰深隐晦”四个字形容。读这种理论著作,需要有心情。所谓心情,一是要净化头脑中世俗纷纷的各种念头,静心;二是需要大块的时间,要有连贯地阅读, 避免零碎化;三是,对某些要点要反复阅读,做笔记,才能真正弄懂作者的意思。趁着上月赴澳洲访学的机会,我特地挑上这本书带着,在旅行期间和空暇时,用心读了几遍,整本书都贴满标签, 读后自感收获颇丰。“反身”,就是反思。反身性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过去20多年才逐步成型。到目前为止, 不同的学者对这个词和相关的方法定义也有不同理解。总体上说,反身,或者反思,就是不断以批评的态度评价“知识”和生产以及处理知识方法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处理研究资料时,严肃地关注不同类型的语言、社会、政治和理论元素以及这些元素彼此纠结以及对研究结果诠释的影响, 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建立理论的框架,而不是去寻找所谓的“真理”。 两位作者在本书一开始,就指出,当下如果仍然将“定量”与“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局限在哪一种更科学或者哪一个更有利于理论构建的争论范围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或者说,类似的话题已无可探究的深度。 社会研究领域的学术界人士心知肚明,即便是最严格的定量分析也难保得出“科学”的结论。那么,我们到底是继续钻牛角尖寻找更加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还是干脆换个角度接受质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另辟蹊径解决问题呢?质性研究方法一向被人批评“不科学”。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这种研究方法依靠观察、访谈和对材料的诠释从新构建事件, 而这些活动均有可能对反映真实客观事实的“可信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产生重大影响。的确,研究者在收集材料和处理素材的时候,个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以及周边环境等各种因素都会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造成影响。实际上,不仅被研究对象、研究者本人会因个人情感和主观认知的局限影响提供的材料以及对材料的处理,而且研究者在撰写报告研究时使用的语言也会对读者理解研究发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是因为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大多使用日常语言。即便使用某些专业单词,论文报告绝对不会像自然科学的数学公式一般抽象。所谓科学的一大原则就是使用单一和一致的专业名词,以避免由于对词汇理解不同导致的误解或者歧义。社会研究文献的读者也并非白板一块。不同的读者对同一研究成果的理解未必绝对遵守严格的“科学”意义,而是根据各自不同的经验加以诠释, 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解。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为了满足“可信度”和科学性的要求发展出很多具体的处理经验资料的方法。比如对采访的文字进行编码、分类,采取多个来源交叉比对资料内容,采取开放问题、无结构或者半结构问卷,避免误导或者引导性问题, 以在经过处理的数据基础上获得的研究结论真正具有普遍的抽象意义。Alvesson等两位作者指出,既然主观和客观因素存在在那里,我们不如换个视角理解它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不妨公开承认它们的存在,承认自己的情感, 承认被研究对象也是在某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形态下塑造的主体。问题不在于个体的主观意识,也不在于个体的情感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号称“噪音”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对待以上这些噪音的传统方法是尽量将其排除在研究结论之外。这也是处理研究资料时惯用的方法。在案例研究中,特别强调多重资料来源,以检验陈述的真实性,并力求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从而发掘现象背后的“真相”。而反身性方法却提出不同的主张:研究者不妨将这些因素本身就是研究材料的原始材料组成部分, 然后考虑如何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构建理论。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按照“反身性方法”的程序,以严格谨慎地态度对研究资料进行精心的梳理和诠释,找出背后的影响因素。可见,反身性方法不是拒绝“噪音”, 而是将各种因素看作研究资料的一部分加以分析。研究结论不再是所谓“科学”真相,而是将经过反身批判与重构的研究结果向读者敞开的,并基于此建立具有多重诠释意义的理论框架,促使读者自行决定该发现对构建理论的意义。换句话说,对研究资料的处理要从过去那种寻找所谓“可信度”或者科学性的框框中跳出来,而转移到“知觉、认知、理论、语言、互文、政治与文化的环境的考量上”(台湾译本第9页,英文原版第6页)。这不仅是一个大胆的提议, 而且是极其富有哲理深度的研究指南。这不仅使我想起了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桑德尔。 在他那著名的“正义”课程上, 桑德尔举例说明美国人对宗教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在认识上的转变。196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休士顿发表了一场讲演。肯尼迪信仰天主教,而当时有选民担心肯尼迪一旦当选是否会将天主教信仰带入美国国策之中。针对选民的这种担忧,肯尼迪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只会考虑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理会外界宗教的压力。46年后的2006年,美国民主党人奥巴马为争取成为总统候选人发表讲演。这一回,他也面临宗教信仰问题。不过,奥巴马没有回避,而是明确表示那种认为坚持政治法律之中不应该具有宗教成分的想法是不对的。桑德尔对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讲演与40多年前肯尼迪总统的就职讲演时指出, 肯尼迪在演说中向美国人民保证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会影响作为美国总统的执政理念和行政决策; 而奥巴曼呢?恰恰相反,他却严肃地告诉美国人民, 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深具宗教情结的国家。既然如此,美国人民为什么不应该大胆地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呢?美国人民应该以自己信仰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作为行动纲领感到自豪, 而不是试图排斥宗教的影响。当然,奥巴马的这种做法应该注意如何平衡与其他价值体系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其他群体的利益, 因为宗教不仅是可以引起共鸣的语言来源,而且某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需要发挥宗教提供的那种道德提升。桑德尔教授以这个事例说明社会对宗教与政治关系认识的转变。 40多年前,人们普遍相信认为国家的执政者应该将宗教信仰与国家治理分开处理。40多年后,人们认识到宗教可以解决很多重大问题。特别地, 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国家执政者和社会成员的信仰往往都是宗教的产物。显然,一名信仰来自某种宗教的人是不可能在行动中完全不顾自己的信仰,成为一个道德“空白”者。以上这个事例对我们认识研究者、研究对象和使用研究成果的读者等等个体自身的主观意识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意义。既然没人能够完全脱离社会作为一个实质意义上抽象的“人”, 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情感,而且都生活在某种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和文化体系内,个人对社会的观察和得出的结论以及采取的行为如何能够做到完全“科学”和理性呢? 刻意追求所谓研究结果的“科学化”无疑在假设以上这些参与到研究的个体都有可能脱离现实生活、抽象出完全“空白”的人。 这种假设真实吗?或者说,这种假设符合科学精神吗?批判性研究方法更进一步质疑:即便是纯自然科学的理论,难道也没有某种意识形态或者哲理信仰的影响吗?依此道理,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管理研究中方法论面对的争议吗? 过去半个世纪,是科学主义取得霸权的时代。出现这种倾向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是现代化理性扩张导致的必然结果。在理性的假设下, 科学主义极力排除个人主观意识和情感对研究对象与研究过程和研究资料的影响,因为,这些因素都是不“科学”的,会影响结论的科学性, 是研究材料中的“噪音”。追求科学当然没错。特别是学术研究,对材料来源地考证和交叉取证,必须遵循一系列标准程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方法, 特别是具体的操作技术,都必须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和程序。质性研究方法面对的挑战是:来自同一来源的经验资料很有可能不一致。 比如,同一个人在讲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内容可能因听众不同而变化,而且也会由于时间不同而出现差异。在访谈中, 以上情况经常发生。传统观点认为,如果按照严格的科学要求,研究者必须扩大证据来源, 交叉验证。如果无法获得“真相”的证据, 这样的材料宁可不用。如果我们重新理解科学本身的含义, 我们也许发现可以有其他方法处理上述资料。真正的科学,不是主观臆测,而是以坚实的观察和事实为依据并在观察到的变量之间建立一系列假设, 而这一系列假设关系应该是合乎逻辑、能够被他人重复验证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不同。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异在于人是自身意识的产物。因此,社会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本应该也不同。最明显的例子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排它性,即一旦一个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某种自然现象,就会替代解释这一自然现象的其他理论。这就是科恩说所的“规范替代”。 而这一定理在社会现象领域并不适用。对一种社会现象,可以存在不同的理论解释,而且每一种都有其特有的视角价值。可见,在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真正科学的态度是认识到现实的多样性,从而考虑不同研究方法的特点。 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创造性地解释社会现象, 才能繁荣社会研究。在定量分析方法日趋垄断社会研究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其它可以创造理论的方法,比如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比如历史的研究, 比如语言的研究,等等。有些方法可以通过科学理性,保证结论的普遍意义。而对某些现象来说,例如历史的解释,多某一现象的出自多人不同的诠释,也许只有事实存在,而无“真理”。 甚至理论本身,难道不是语言的产物?当一个人面对6只给出不同时间的座钟时,传统的“科学主义”认为只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即真相。研究者的责任是从这6个不同的钟表中找出正确的时间。反身性方法却认为,这6个不同时间也许都有各自的道理。我们要找出的不是那个“真相”时间,而是为什么不同的钟表会给出不同的时间, 这些不同时间背后的含义为何?各个钟表之间的差异对我们理解时间以及不同形态下时间的含义有何贡献?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真相”,留下的只是个体有选择保留在记忆中的“事实”或者想象而已。读者如果看过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作品《罗门生》, 自然不难体会有些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真相。存在的只是对现象的诠释而已,而且因人而异。可见,社会研究结论的价值未必是提供所谓“真相”,而是为人们提供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的不同视角。而只有允许这种丰富存在的多样化视角,人们才能真正地理解社会,理解自身。只有允许多种不同研究方法的共存,才会使社会研究更加丰富多彩。这本书内容丰富。我在这里只是简要地摘引两位作者提出的衡量高质量研究的5个标准。 其英文原文(原著第276页)如下:1.Empirical arguments and credibility (经验论据与可靠性)2.An open attitude to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the interpretative dimension to social phenomena (对社会现象的解释维度的极端重要性持开放态度)3.Critical reflection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texts of, and issues in, research (对研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以及研究中的问题作批判性的反思)4.An awareness of the ambiguity of language and its limited capacity to convey knowledge of a purely empirical reality and awareness about the rhetorical nature of ways of dealing with this issue (对语言的含糊性以及在传达关于纯粹经验是在的知识时的有限能力的自觉,以及对于处理这一问题(表征—权威问题)的方式的修辞本质的自觉)5.Theo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mentioned issues (建立在所提到的问题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发展)(注:译文来自陈仁仁译本《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 第316页)虽然两位作者提出这些建议时指明是针对质性研究方法而言, 我仍然认为这些标准普遍适用于所有的管理研究。对于如何使用反身性研究方法的具体操作,这本书着墨不多。大概,具体实践还需要社会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
哪些学校研究生有学术型翻译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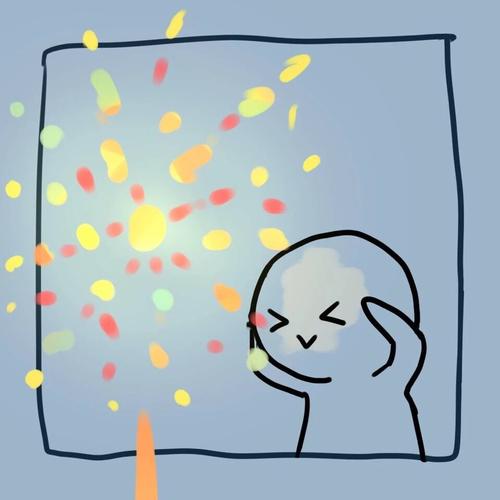 君火
君火您好,我想考翻译方向的学术性研究生,这属于考研大方向下的哪一种方向啊?谢谢
 辨合
辨合 触动爱
触动爱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区别于专业学3339663334位硕士研究生,看来你应该对以上两种研究生类别有所了解。就翻译来看,有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翻译硕士(专业硕士,MTI),而翻译方向的则是文学硕士,两者是有区别的。 首先,学术型学位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专业学位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其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其次,专业学位教育的突出特点是与职业性紧密结合,获得专业学位的人,主要不是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从事具有明显的职业背景的工作,如工程师、医师、律师、建筑师等。 最后,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只是在培养规格各有侧重,在培养目标上有明显差异。两类研究生在招生及调剂时按照“一视同仁,同等对待”的原则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分数标准。国家在确定每年复试基本分数要求时,将统筹考虑前期计划和新增专业学位招生计划需要,确定统一的考生进入复试基本分数要求(对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另行制定标准)。 以英语为例,走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可选择专业: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一般开设此专业的学校,都会在专业下面分布一些研究方向,例如文学修辞与翻译、翻译理论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等
日语翻译:学术研究走到今天,凝聚了多少学者的心血
 其自为也
其自为也大家知道什么比较好的学术翻译网站吗
 漫步者
漫步者
 40004-98986
40004-98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