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考研数学泄题是怎么回事 李林考研数学泄题
 坂口
坂口 请辞而退
请辞而退
前几天是咱们普通人对于圣诞节和平安夜的狂欢,也是考研大队的狂欢,因为考研就在前两天结束了,有很多朋友都参与了这场大战,但是近期却有传闻说有一位补习班的数学老师对数学考研题目有泄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跟着小编往下看吧。 这是一位考研大神发的微博,足以证明今年的考研数学题目有多么的难,很多成绩好的朋友们都没有考好。 有网友表示自己踏踏实实做了31年真题3遍与2遍全书一遍660,写了近千张稿纸,总结了两个本子的笔记,我真心觉得很难,至少在考场上真的很难。考完冷汗都出来了,紧张的只想吐,午饭都吃不进去。 最后一对答案倒是没太难受,勉勉强强120,还能接受,但过程太煎熬了。 我真的感觉,数学学了一年赶不上个压题的,政治学了半年赶不上压题的,英语学了半年赶不上靠玄学,这考试的目的在哪里?坐等这件事情的后续。 泄题这种风向真的不好,研究生考试是选拔人才的,如果选拔不好的,那还选什么,估计以后导师全要保研的得了。 数三的战友可以看看那个老师的视频,不清楚数一的,不过数一也可以看看。 对于一个理科生考金融来讲,不说完全,也有一大半的赌全压在了数学上,现在又有什么用呢? 辛辛苦苦十个月,不如别人三小时。 先节选这么一部分吧,反正小编是看不懂的毕竟没有学过,考研大军们如果看到了可以自我判断一下。 有人说没有泄题打死我也不信,数二上今年那几道大题考的那么偏,我周围的同学都没做出来,他竟然能全部押中,连图像跟问题都一模一样。 16年考研数学史上最难,结果那年泄题了。 18年考研数学难度新高,又泄题了。 复习大半年不如人家2000块钱的一节课,这个李林到底是何方神圣? 考研大军们辛苦了一年多,把自己折磨的不像话,就是为了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很痛心,看到别人考前花2个小时轻轻松松上80。不怕数学难,要难大家一起难。结果今天早上看到泄题消息,心凉半截。李林老师啊,你知道有多少考生早出晚归,辛辛苦苦,就为了这三个小时。有多少人咬牙坚持,就为了那个“梦想”。我们有梦,我们敢追,可是不公平重重的给了我们一记耳光,告诉我们:不可以! 就好像一直有人将你握在手心,最后那一刻合起手掌,在绝望中灰飞烟灭。 只希望得到公平,还考研学子公道,考研真的很不容易,一句走过来的心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临考前的1个月连吃饭回宿舍都是跑着的,每天都是接近1点回宿舍,午休如果一不小心睡超过了1个小时都觉得奢侈,觉得有罪恶感,这样的结局真的接受不了。 网友评论: 宇哥微博已经被删了。 汤神也是,两个最爱的数学老师,都被删了 这不就是原题吗? 假设检验都能预测到,这得是考神附体了吧。这种东西基本没考过,还这么准的点中。哎! 汤神和宇哥发了微博都被删了,艾特也没用了。 哈哈哈,我16考了,18又考,十首凉凉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情。 要我说这李林脑子也是有问题,明知道是原题还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弄视频课,算了,既考完,多说无益,人生中又一堂课。 考前几天进的一个考研群里还有学长学姐建议看一下李林的,说这个人每年都很神会押中题。我当时心里想的再神还不就是考纲里那些题,根本没理会。 目前整个事件就是这样了,目前官方还没有作答,真的是苦了考研大队们的心了,估计这一会都非常难过吧,安抚一下,让我们静待事情的后续吧!
香港大学的研究生值得读吗?要求高吗?
 大人无己
大人无己 滑步舞
滑步舞
我去年刚毕业~个人感觉是非常值得的,时间短,全英文授课,就做学术而言,还是挺国际化的。在读港大master之前,我没有英文文章,从没参加过啥会议。但是在这边读了一年,投了一个国际会议和一篇英文期刊在审,随说学制短,只要你付出的多,能得到的几乎都能。而且就一年,使劲逼一逼自己,毕业拿distinction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且港大很美哇,边学边欣赏风景也是极好的。然后相对于英国,学费低。相对于内地研究生,不用帮导师干活,相对自由,自己可以学自己的,做自己的研究。就业的话,港大的硕士相对于内地还是有优势哒。但是也有一定的劣势,就是内地人比较多哇,日常的英语环境一般哇~还有就是毕业时间的问题,香港这边是11月拿毕业证,学制其实是一年半的,所以是下一年的应届毕业生。英语的话,超级重要。我本科属于985、211,教育学专业内地top1,但是感觉读了英文文献后自己就是个文盲哇,最开始读文献的时候还得查字典,半天才能读一篇。在港大上课的话,英语听力很重要,听不懂真的就不知道上课在讲啥。口语的话,个人感觉还好,只要你敢说,不怕错,总能提高的。而且内地人的英语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是不敢开口,怕错。其实语法说错没啥关系,关键词说出来不影响理解就行,大胆说。英文写作超级重要哇,如果写作差了,一堆语法错误,老师估计都懒得看哇,写作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影响你成绩的直接因素。发几张港大的美图和offer图哇~希望大家都能如愿拿到offer~
考研政治选择题怎么拿到40分?
 辟谷
辟谷考研数学三靠刷题就能140分吗?
 丘陵
丘陵 损矣
损矣
刷题肯定要刷,但是弄懂一道题,就能知道这一类型的方法,更好哦附上三步学习方法:第一,深刻理解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概念是事物的本质特征,有些概念的考查几乎是每年必考的,如导数的概念,不仅仅是利用导数概念进行计算,有时还需要理解导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这也是我们做题的一些关键,如导数的等价定义、导数的几何意义、导数与可微、连续的关系等等。有些基本理论,如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极限,几乎是每年必考的,对于洛必达法则的内容,以及洛必达法则如何运用,运用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条件,这都是我们要搞明白的。对于概念和理论一定要理解到位,这些是我们做题时的灵魂,缺少了它们,做题时你就会觉得毫无头绪。第二,掌握基本方法,灵活应用基本方法解题。方法是解题过程中的框架,只有熟悉基本方法,做题时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如求函数的极值是导数应用中一类常考的题型,求解的步骤一般如下:求函数的定义域、求函数的导数、找出函数的驻点及不可导点、利用判断极值的第一充分条件进行验证,看看驻点和不可导哪些点满足左右两边单调性相反。此种类型的题目以解答题和选择题的形式在历年真题中都考过。此外还有,比如交换积分次序、改变坐标系等等都属于基本方法的考查,有些题目甚至都不需要计算就可以找出答案。对于基本方法要求灵活应用,不能死记硬背。第三,适当练习中档难度的题目即可。数学在复习过程中,做题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同学们做题时一定要把准方向,不能做偏题、怪题和难题。在考试试卷中,至少有70%的题目是基础题,也就是难度在0.3-0.8之间。考试中不会考太难的题目。所以大家在复习过程中不要研究太难的题目,没太大的必要。多做做基础类的题目,后期练习一下带有综合性的基础类题目即可。复习时以真题的难度为导向进行复习即可。
那些大学有玄学专业的?
 财用穷匮
财用穷匮 侵暴诸侯
侵暴诸侯
截止2019年9月,国内外的大学没有开设玄学系专业。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 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扩展资料玄学基本特点 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杨泉等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③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 ;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玄学(道家哲学思想)
哪几个大学有类似于易经,玄学,周易哲学,等专业的?具体名称叫什么?
 稻草狗
稻草狗 只眼
只眼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 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 ~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 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学”,它“鄙视汉代‘象数之学’,抛弃阴阳五行等旧说的传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1)。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于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应帝王》也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庄都是以自然为至高之境。 魏晋玄学继承老庄思想,特别标榜自然。但玄学家对待名教的态度,以及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异。王弼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他认为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自然的产物,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为则败也。智慧自备,为则伪也。”(2) 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认为设立名教之前的“鸿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会。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4)。他们蔑视礼法,愤世嫉俗,过着佯狂任诞的生活。鲍敬言提出无君论,认为上古时代人性淳朴,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也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人们“含铺而熙”,“鼓腹而游”,过着自然自得的生活。后来“智用巧生”,“背朴弥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于是人们陷入了困苦之中(5)。向秀、郭象继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为一,认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体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6) “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7)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8)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9)所以阮咸长成亦欲作达,阮籍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0)不肯让儿子学自己那一套。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11)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12),但他并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繁琐的训诂;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这是与“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异趣,而符合魏晋以来新的学风的。《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陶渊明读经也像九方皋之相马,支遁之解说,不肯拘拘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诗里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庄子·刻意篇》:“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嵇康《与阮德如》诗:“君其爱素德。”可见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就连孔子本人,也被陶渊明道家化了。《饮酒》其二十: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孔子在他笔下已不是其本来的面目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13)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有与崇尚自然的旨趣并不违背的成分,陶渊明可以方便地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诗里。《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曾暂言志目:“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董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皙)也。”这一章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但陶渊明只取其中爱好自然这一点意思,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本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了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但陶渊明毕竟不同于那般章句小儒。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诚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豚,近于马队”(14),陶渊明写诗讽谕,末尾说:“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15),分明表示与他们走着不同的道路。 以上所述是陶渊明所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必须指出,陶渊明对于玄学所讨论的本体论等抽象的哲学问题并无多大兴趣。他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社会理想和美学观念。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陶渊明的诗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根本不同。玄言诗脱离生活,纯是老庄哲学和佛教教义的说教,“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6)。陶诗却是来自生活的,表现了陶渊明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而不是玄学的注疏和图解。 此外,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和胜解,这就是提倡躬耕,并亲自实践。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庄子》书中就曾肯定过躬耕劳动,《马蹄篇》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天地篇》赞扬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盗跖篇》斥骂孔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庄子》对躬耕的意义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陶渊明不仅长期从事躬耕,而且对劳动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说: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人生所归,归向于道。但不管归向什么道,首先要吃饭穿衣。所以经营衣食是归道的起点,躬耕劳动是实践自然之义的开端。世人视躬耕为拙,同出仕相比这确实是拙,但他宁可坚守这个拙而不肯取巧。他在诗里一再歌咏自己的劳动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劳动中他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陶渊明提倡躬耕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孔子鄙视劳动,樊迟问稼被他斥为小人。孟子也鄙视劳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他说成是“天下之通义”。陶渊明不赞成他们,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写道: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意思是说孔夫子的遗训太高超了,我景仰之至,可惜难以做到,还是出力气种地吧!这不明明是宣称自己要走“小人”樊迟的道路吗?陶渊明所敬仰的古代的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陈仲子等人,都是名教之外的人物。他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17) “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18) “蔑彼结驷,甘此灌园。”(19)他的心是在这批自食其力的隐士一边的。
大师 帮我看看我的紫微斗数 还有我想考研要注意什么啊?
 攘弃仁义
攘弃仁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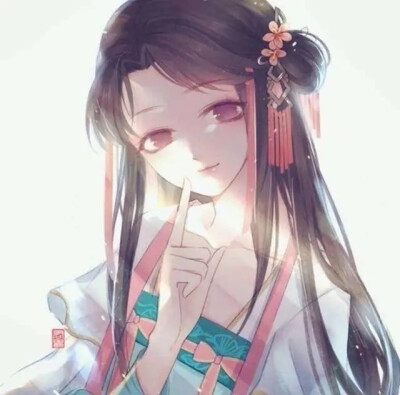 部
部
紫微斗数预测:命宫在(寅)命宫主星为紫微、天府紫微同宫具备领导统御能力,是领导、管理的好手。有颗积极进取的心,能善用他人才能,来完成事业或工作上的目标。广学而不精,是通才的典型。遭遇困难,总是有人出手相救,有逢凶化吉的的运气。有责任感。好奇心强,能积极学习周遭事物。不怕失败,能多方尝试。耳根子软,易轻信於他人,会受周围环境之影响。心胸略显狭窄。有成就後,易过於自满任性,轻信於他人,导致原有团队成员的合作破裂。形成失败的导火线。 天府同宫性情忠厚善良,乐於为人排解困难,能得人和。聪明学习力强,对环境能满足。安分守己,不太会去主动改变现状。生性喜助人,广结善缘。因此即使遇到困难,也有贵人挺身相助,逢凶化吉。思考理性,分析事情能由客观角度切入,具容人的雅量,人际关系经营的不错。为人处世,不喜欢投机取巧。能够步步为营,在稳定求得进步。看法保守,不随便冒险。对事情细微的地方,可以注意的很仔细。有领导力,具备规划组织能力。 左辅不见/右弼不见性格易流於专断独行。虽外表坚强,但内心柔弱善感。削弱了管理领导的能力。 陀罗会照注意身体受到外伤或破相。工作上会遇到阻力。 地空会照钱财较无法聚集。精神上空虚,情绪较不稳定。具有创作灵感。 紫微化权同宫增加积极性,和掌权的欲望。个性会变的较为自主刚强些。自身能力不错,有领导风范,也能实际掌权。 武曲化忌会照有变动,应防意外之灾。 注意钱财流向。与人发生金钱纠纷。个性会不开朗、固执。容易将心神寄托於宗教、玄学、命理上。小心受金属器具所伤。 天马同宫主迁动、变化。可能会有搬家、旅行、换工作的事件发生。与吉星作用,可加速吉力的发挥,工作、事业进展顺利。若与凶星作用,也应防在外地遇到波折或交通事故。天马与紫微、天府同宫,称为「扶舆马」。利於事业上名声的获得、国家考试的通过。吉格 紫府同宫格:有成富或成贵的机运。做决定时考虑过久,往往错过切入的正确时机点。 府相朝垣格:利於担任公职,官运可亨通,有一定的经济收入。重视人际情谊,与家人朋友感情不错。 凶格 马落空亡:主奔波忙碌,但极有可能为白忙一场。父母宫在(卯)太阴同宫父母性情温和。与母亲缘分较深,双亲之中受母亲影响较大。 左辅会照与父母有缘,可受父母疼爱相助。 天魁同宫父母有不错的身份地位,对自己发展有所助益。 文曲会照父母有学识,疼爱子女。 火星会照/铃星同宫家庭问题较多,与父母有代沟。相处不融洽。 天梁化禄会照能享受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有困难时他们总会出面帮忙。 左辅化科会照父母亲本身有教养,是斯文人。注重孩子的学业,也会亲自教导孩子。 禄存会照与父母有缘,能得父母金钱上的支援。 化禄会照/化科会照父母可能为担任公职人员,或者在民间企业内担任主管。 化禄会照/禄存会照父母若做生意可获利,事业能逐步扩大。 福德宫在(辰) 贪狼同宫不满足於现状,欲望多。做事较要求完美,较忙碌,以达成预期要求。享乐时较不受世俗羁绊,能放得开,风花雪月一番也无妨。 天魁相夹/天钺相夹有遇贵人相助的福分。 擎羊会照/陀罗会照劳心劳碌,心境较不安宁。 地劫同宫使福份较浅薄,不快乐,会胡思乱想。 武曲化忌会照赚钱比较辛苦。心情较难保持快乐。 田宅宫在(巳) 巨门同宫应注意因不动产所招致的是非。也可能因田地或住宅因素,与邻里发生纠纷。 左辅会照/右弼同宫有祖产,可获得继承。 天钺同宫有祖业,可能为华丽的楼房或花园。能继承,且对自己的发展有助益。 文昌同宫/文曲会照能继承祖业,喜购置田宅。 地劫相夹/地空相夹祖业无遗留。不利於田宅登记於自己名下,不会留太久。 左辅化科会照喜居住於文教区。 禄存会照有家产,可继承。 事业宫在(午) 廉贞同宫廉贞居於事业宫,带有技艺性质,若在民间企业服务,则可向高科技产业发展,如电子业、电器业、精密机械业、外科医生、护士。另一方面廉贞本身带有桃花的性质也可在娱乐服务业、演艺界、酒家舞厅内服务。在古代廉贞视为武星,因此也适合从事军警、司法、保全之类的之武职工作。廉贞为官禄主,可服公职,如军警、司法等工作,可掌权。民营企业偏向电子业界。 天相同宫天相坐事业宫,适合做参谋、秘书、幕僚、私人特助、公务人员。这些位於幕後有关的策划工作。另外亦可从事与公开场合有关的食、衣、住、行、育、乐等服务展示性质的行业。如服务业、高级餐厅、服饰业、礼品百货、银楼、古董店、珠宝店、摄影、美容化妆业、艺术行业工作。 擎羊会照/陀罗会照事业上会遇上外来的阻力。若在军警界服务,反能增加个人威望,具管理力。 地空同宫在投资之前应审慎评估,避免不当投资引起的损失。也不宜作投机性炒作,有可能蚀亏。 紫微化权会照在政府机关或公营机构任职,可获提携。官运不错,能升迁至一定的职务。若在私人机构任职也能向上晋升,成为掌实权的主管。 武曲化忌会照注意事业与金钱有关的款项。要点收明白,帐目相符。 天马会照有为事业异常奔波忙碌的状况,若遇升迁机会有可能会三级跳。但勿因过度操劳,损害健康。 交友宫在(未) 天梁同宫与大於自己年纪朋友有缘,可受其照顾相扶助。朋友数量较少。也有可能是自己扮演照顾别人的角色。若为主管,则部属不多,但能善尽照顾部下的责任。 天魁会照多得忠实正直的朋友或部属,遇困难能挺身相助。 火星同宫/铃星会照会有部属、朋友依赖心重。遇事无助力。小心结交损友。 天梁化禄同宫自己对年长的朋友敬重有加。平时可受其照顾。 禄存会照为人能广植人脉,不吝於助人,也能获他人相助。 化禄同宫/禄存会照能遇可在事业上一起合作奋斗的友人。 迁移宫在(申) 七杀同宫不喜在家,会有受约束的感觉。一旦出外则活力十足。在外活动力强,做事有冲劲,霸气十足。 擎羊会照在外宜避免无谓是非,及与人发生冲突。 地劫会照在外地发展有受挫情形,慎防别人的算计、嫁祸。也应避免被他人连累。 紫微化权会照在外发展,可受贵人扶持相助,获得职务提升。 天马会照常出外奔波忙碌,注意交通意外发生。 化禄相夹/化权会照/化科相夹利於在外发展,可在发展领域里获得名声。 疾厄宫在(酉) 天同同宫注意痔疮便血、肥胖症、水肿、膀胱、尿道方面的疾病。 左辅同宫/右弼会照少病少灾。 天魁会照/天钺会照病轻易治,或能遇良医使病情逢凶化吉。 文昌会照/文曲同宫少灾病。生病过後要多注意发炎、溃烂、硬化等後遗症。 铃星会照注意火伤、急性发炎、火气旺盛、眼睛刺痛、机能亢进。 左辅化科同宫可解除或减轻病厄。本人注重身材的维持。 左辅同宫/右弼会照/天魁会照/天钺会照体质好,健康不会太差。 财帛宫在(戌)武曲同宫求财主动积极,生财有方。利於经商贸易或金融买卖活动上获利。 陀罗同宫主钱财有损,就是有心要守成,也会流失。劳心劳碌,就算有发财机会,也会不注意没把握而错失。 地劫会照/地空会照用钱较无度,常发生寅吃卯粮。尚未支领下月薪水就用罄本月薪俸。较无法积存财富。 紫微化权会照利於创业,理财有术。财源来自政府机关,可在公营单位发展,或竞标政府机关的案子。 武曲化忌同宫会因钱财而烦恼。严重的会因财而与人起是非、冲突。要借钱给别人,不宜大量借出。 天马会照动中取财,越奔波越能赚到钱。金钱的进出流动波动大。稍不注意,来的急,去的也快。 子女宫在(亥) 太阳同宫子女外向活泼,志向远大,有创造事业的雄心。 右弼会照可增进子女乖巧听话程度。 天魁会照/天钺会照可使子女聪明,会念书。也较懂得打理自己的一切。 文昌会照可增进亲子间的感情。子女对文艺有兴趣,具备这方面的才华。 擎羊相夹/陀罗相夹使子女个性较孤僻或性急。有时比较不好沟通。注意怀孕时是否有流产、或堕胎现象。也有可能是以剖腹生产让子女出生现象。 火星会照/铃星会照要注意子女小时候的安全,避免产生意外伤害。子女数目不多。 天梁化禄会照本人疼爱子女。 子女有长辈缘,很得长辈疼爱。 禄存同宫子女人数不多。 化禄会照/禄存同宫子女有招财运。 擎羊相夹/陀罗相夹/火星会照/铃星会照注意子女身体健康。小时後比较不好养育。要注意子女的管教,避免子女误入歧途。 夫妻宫在(子) 破军同宫婚姻观念独特,不喜欢受传统观念束缚。可以接受婚前同居或单身主义这种新潮的观念。恋爱过程变化多端,颇富戏剧性。但所遇的波折亦不少。可谓好事多磨。配偶个性自我,可能较不具家庭责任感,用较多心力在自己的事务上。遇到双方沟通不良时,切忌一时冲动而结束婚姻关系。 擎羊同宫夫妻感情起伏不定,时好时坏。注意关系的维持,否则会有二度婚姻状况发生。 地劫会照/地空会照配偶的健康较差,应多关心保养。费心培养的感情有一夕成空的可能。 身宫在夫妻宫:身宫代表个人的後天运势发展所要著重的宫位,是继命宫之外,个人所要特别留意著重的宫位。个人的婚姻、恋爱对象,将会深深影响您後天上的发展。恋爱时不可因一时的情绪冲动,而伧促做婚姻决定。 择偶对像应慎重考虑,个性上是否适合,观念上能否沟通这都很重要。婚後若能得贤明配偶,彼此在家庭、事业上能互补,则个人的後天发展将能无往不利。 兄弟宫在(丑) 天机同宫兄弟姊妹间有人脑筋好,点子多。天机为兄弟宫主,得位。能得到兄弟帮助。 左辅会照/右弼会照兄弟姊妹间,彼此能互相照顾、帮忙。 天钺会照兄弟姊妹间,能互助。其中有人在社会中拥有不错的身份地位。 文昌会照/文曲会照兄弟姊妹间,有人对艺术、音乐或文学擅长。彼此相处融洽。 火星会照兄弟姊妹间,易有争执,影响彼此感情。 天梁化禄会照本人能得年纪较长的兄姊之关心照顾。 左辅化科会照自己的兄弟姊妹能得贵人相助。进而达成预定的目标。 化禄会照/化科会照兄弟姊妹有可能成为社会或地方邻里名人。
你是北中医的学生啊,哪年级的?请问考北中医研究生都需要看那些书?哪个版本?谢啦!
 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 金芒果
金芒果
中医与学历、文凭、职称、资质毫无相干,几十年中医学府培养不出中医人才,中医教育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自古哪个神医经过了学习、文凭、职称、资质才成为的?正规专业学习考试合格的都是废物,还要对从来没经过学习的民间中医进行考试,不荒唐吗?不可笑吗?而那些不明真相的中医还在等待考核拿证“合理行医”不无知吗? 西医可以将患者治的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还可以将风险推给患者,让死者家属背上几十万到几百万元钱的债务,却“合理合法”。因此,西医杀人无罪! 代表真正的中医是民间中医,而民间中医救一万个人没有功,只要有一点点失误被起诉就“违法犯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中医救人无功! 为什么“中医救人无功,西医杀人无罪”?因为法律是以唯物科学的思维为西医制定的,所以西医“杀人无罪”。中医是唯心玄学的,而法律正打击唯心玄学,所以“中医非法”才救人无功。 中西医的性质是什么? 因为西医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以人和动物的生命为代价,在实践的实验中得到的,所以说:《西医是无人性的医学》。 中医的理论与方法都是在行善积德,修心养性加禅悟(打坐),达到开悟,开悟后得道,得道后得真理而得到的。从无中生有到学说,在从学说到理论,所以说:《中医是人性的医学》。 中西医的方向是什么? 西医发展就是科学发展,它们共同走向未来,未来是生命的终点,世界的末日。 中医发展就是玄学发展,它们共同走向以前,以前是生命的起点,世界的起源。 中西医的目的是什么? 西医为了追求最高的物质享受钱,追求最高的物质富有(西医是为争钱的,不是为救命的)。 中医为了追求最高的精神境界道,追求最高的精神富有(中医是为救命的,不是为争钱的)。 ——民间中医林治满
想问一下华侨大学 哲学硕士的考研大纲在哪找?
 波弗特
波弗特 摸错骨
摸错骨
哲学基本理论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值及考试时间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二)答题方式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试卷由试题和答题纸组成;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由考点提供)相应的位置上。(三)试卷内容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25%),中国哲学(25%),西方哲学(25%),其他(25%)(四)试卷题型结构1.名词解释(35分),共7道;2.简答题(75分),共4-5道;3.论述题(40分),共1-2道。二、考查目标测试考生对哲学的基本概念、主要流派、宏观脉络和思想内涵的掌握情况,理解与掌握哲学发展演变中的主要人物、基本经典、基础理论及其流变传承的相互关系等。三、考查范围或考试内容概要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1.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相关知识点。2.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理解和思考。3.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原著对现实问题反思、分析和把握的能力。第二部分、中国哲学(一)先秦诸子哲学1、儒家哲学2、道家哲学3、墨家哲学4、名家哲学5、法家及其他各家哲学(二)汉唐哲学1、汉代经学与哲学2、魏晋玄学3、隋唐佛学与儒学(三)宋明理学1、北宋理学2、南宋理学3、明代心学4、宋明时期的气学与事功之学(四)清代以降哲学1、清代哲学2、现代新儒家哲学第三部分、外国哲学(一)古希腊哲学1、前苏格拉底哲学2、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3、希腊化哲学(二)中世纪哲学1、教父哲学2、经院哲学3、唯名论与唯实论(三)近代哲学1、唯理论2、经验论3、德国古典哲学(四)现当代哲学1、存在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2、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3、分析哲学4、现象学与解释学5、后现代哲学第四部分、宗教学(一)宗教的本质及其表现1.宗教的本质、要素和类型2.宗教的观念和思想3.宗教的感情与体验4.宗教的行为与活动,(二)宗教的起源和发展1. 宗教的起源2.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宗教3.古代阶级社会的国家-民族宗教4.世界宗教(三)宗教与文化1.宗教与政治2.宗教与道德3.宗教与艺术4.宗教与科学,第五部分、科技哲学(一)自然观的变革与生态价值观与可持续发展(二)科学发现与科学辩护(三)科学认识的经验基础(四)科学认识的理论建构(五)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