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污水处理厂的调研报告怎么写
 去其弟子
去其弟子为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献计献策,写出调查报告
 大城市
大城市 沐丝
沐丝
中国水环境网,那里有很多关于环境的资料(www.chinawaterenv.com)参考资料:www.chinawaterenv.com小河的哀号——小学生环保调查报告 2007-5-18 慈溪市三北希望小学 引 言 宁波市慈溪三北镇是个人口密集,祥和而又热闹的小镇。这里河流众多,滋养着三北人民。公路横河、门前河、快河港、桥头河等河流在小镇中流淌。随着科学技术的速度发展,三北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家每户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生活的改变也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次我们三北镇希望小学五(3)中队绿色环保小队的几个队员对我镇的几条河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 调查人员及分工: 宁波市慈溪三北镇希望小学五(3)中队绿色环保小队 队长:余丹丹 队员:袁雯欢、卢晓晔、叶袁超、黄宏业、黄旭超 二、调查的对象、时间和方式: 2006年10月1——7日,我们环保小队的余丹丹等六位队员对家边的河流进行了实地调查,其中包括公路横河、门前河、快河港、桥头河等数条河流。同时,我们也针对河流的相关问题,以问卷的形式向长辈们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几个队员增长了不少见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调查的内容概况: 三北镇虽地域较小,但其河流众多,其中村中河特别多。这些小河离居民区较近,也有些小河旁有工厂。最近几年来,三北经济发展迅猛,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废水,严重影响了小河的水质。河两岸附近的居民也经常在水中洗衣服、淘米、捕鱼等,这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也对小河的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四、问卷调查: 1、调查问题: ①小河以前是怎样的?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 ②是什么原因使小河成为今天这样? ③你会往河里丢垃圾吗? ④如果你看到别人往河里丢垃圾,你会怎么做? 2、调查分析 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多数长辈都说,以前的小河都非常清澈,河中还有些小鱼、小虾,河边是小时他们的儿童乐园。值得一提的是,黄宏业家门前还有条“门前河”,那是条又窄又长的小河,河沿由石板铺成。他父亲回忆说,河水清澈见底,站在岸上还可以看到有些小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动。人们的生活用水也是从这里取的。自从90年代有了自来水,人们才渐渐淡忘这里曾养育了一代人。 问卷调查中也发现,如今,大人们对于保护小河的意识也越来越差,经常往河里丢垃圾,更不用说去劝阻他人了。 五、实地调查发现: 我们队员在课余时间,也对小河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然后,我们几个队员经过激烈讨论后将问题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三北镇近几年来经济发展比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私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些工厂大多建于河边,对水质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纺织厂和橡胶厂,不仅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还排放出大量有毒的工业废水。如快船港开凿后,承担着由西向东的运输重担,而河边的建了一座橡胶厂,排除的污水,使河水越来越脏,平时还散发出阵阵恶臭,河里时常还能发现漂浮着的鱼的尸体。本来供人们洗衣、淘米的快船港再也派不上它的用场了。不知不觉中,它的作用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二)、由于人们环保意识薄弱,经常往河里倾倒垃圾。所以河面上各种生活垃圾随处可见。门前河是我们调查中发现的最脏的小河,平时你可以看见被丢弃的快餐盒、塑料袋、酒瓶、泡沫……甚至是一些家禽家畜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那里成了天然的生活垃圾回收站。河沿旁的石板上那沉淀着的烂泥,痛斥着人们的恶行。原先美丽整洁的河道变得惨不忍睹。人们在清洁了自身的同时,却把所有的污垢留给了门前河。 六、调查后的建议: 通过调查,我们队员发现了许多的问题,经过小组的交流讨论,我们想提出以下的几个建议: (一)、我们希望镇政府有关部门能对河流加强管理、清除工作,通过定期安排清洁工清理杂草,治理污水,还小河一个清澈整洁的环境。我们镇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我们相信环境优美的三北镇会更加富饶。 (二)、“和谐”是新世纪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经济要发展,但是不能以牺牲大自然的环境作为代价。针对沿河厂家排放污水、废渣等问题,我们认为镇政府应该采取有关措施,制订一些规章制度,强制每个单位一定执行,违反应进行相应处罚。最好是能进行“环保单位”的评比,评出环保工作做得最好的几个厂家。环保做得不好的几个厂家,可以在广播中点名批评或者在镇政府宣传栏中张贴出来,罚款等方法作为处罚。 (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分发传单到农户、墙报宣传、环保知识讲座等方法来增强大家的环保意识,教育大家不要再往河中乱扔垃圾,倾倒废水、废渣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治理好我镇的河流污染问题。我们相信,只要大家以身作则,都来争做环保小公民,就一定能使小河重新找回清澈,找回美丽。
求一篇有关水资源污染的调查报告3000字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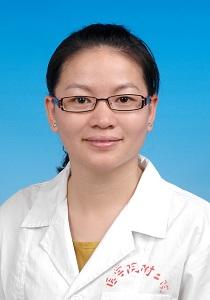 九朵云
九朵云 黄帝得之
黄帝得之
水资源污染调查报告 一、调查原因 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将无法继续下去,人类就不能生存。虽然我市不是一个用水紧张的城市,但水污染却存在,我家门前的小河就是最好的见证。这条小河原先可美了,河水清澈见底,游鱼水藻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三五成群的小孩子在河里嬉戏、打闹。可现在呢?它已经被污染的不成样子了,人们都把生活垃圾和废水倒进河里,美丽的小河不见了,变成了脏兮兮的水沟。人们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我们必须共同关心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此,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和几个同学对于小河的污染做了一些调查。 二、调查过程及方法 走访河边的居民,询问小河多年以前的情况,做好记录。然后,和同学一起到河边仔细观察,采集污染水样本,了解现在的小河是什么情况,并做好记录。 三、水污染的原因 1、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养殖场废水、生活废弃物不经过专业的处理,直接排入河里,就会造成严重的水污染。 2、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也会严重污染水资源。 3、日常生活中的塑料袋、剩饭剩菜等倒入河里,使水变脏变臭,也影响了水的质量,污染了水资源。 四、调查分析 经过实地调查,我认为水污染给居民带来的危害。地下水污染,用水困难,河水污染严重滋生大量微生物,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五、解决方法 1、为了改善河道环境,应尽快开展河水、河岸等全方面的治理工作。首先,对污染源进行处理,杜绝养殖场把污水、粪渣直接排放到河流中,应集中处理,避免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然后,对河边、河道中的污染物进行清除,并对水道进行整改,进一步将河内的垃圾、淤泥清除。后在河边种树,植草皮,建立绿化带,避免沙土流失。 2、对沿岸居民及全体市民进行环保教育,增强环保意识,河流的环境,主要还是在于大家的思想意识,故人们应自觉保护河道,保护环境。这样,一条全新河流才会永远呈现在人们面前。 六、结论 总之,要明确,环境受破坏,受影响的还是人们自己,我们应当充分了解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认识到人们改变环境的利与弊。影响水资源的因素还远远不止这些。虽然我的调查研究也许还不够成熟,但希望能把环境问题,水污染问题在人们的脑海中的地位提高,这样才会提高人们的重视,有助于解决问题。希望各种环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希望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好!
环保调查报告
 潮来笠
潮来笠 樱桃汁
樱桃汁
给你份参照参照:临沂市环境调查报告一 引言临沂,我们美丽的家乡,她位于山东省南部、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市。她境内源远流长的沂河水,惠泽着沂蒙人民,孕育了临沂的文明。改革开发以来,临沂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今的临沂城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发达、交通便利、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然而经济的发展、工厂不断的建设给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家乡的一员,我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关心自己周围的环境,因此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对临沂的环境污染状况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希望冀此了解家乡的环境现状,找到改善家乡环境的对策,为家乡的环境保护事业尽一份力。二 调查过程及结果此次调查活动我们采取了多种方式,多方面收集资料和数据,尽量获得第一手资料,力求真实和准确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到图书馆查阅了一系列图书、报刊资料,以便更好的了解家乡概况,历史沿革、发展规划;到市环境保护局索取了有关环境监测数据;在城区选点实地观察并采取水样;到几家企业调查了排污及治理情况;走访了城里的一些居民,了解了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认识及对其污染危害的看法。要想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现状并作出准确评价是很困难的,限于我们自身的能力,我们只能以主观估测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家乡的环境现状、影响、趋势作出一些粗浅的评价。(一)实地观察过程及结果 本次城区实地调查,我们一共选取了六个观察地点(分别为沂河橡胶坝处、西郊步行街处、第一实验小学附近、市展览馆附近、荣华工业园附近、南道村委附近)进行了大气和水污染状况调查。观察表明,临沂大气状况尚属良好,城区西郊靠近工业区大气有少许刺激气味,晴天时大气能见度不太高。个别地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水体污染。如市第一实验小学附近的青龙河河段水色浑浊,散发出臭味,水样PH值测定表明,其PH为酸性。通过查阅资料我们了解到,水质变黑发臭是水中氨氮含量超标,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结果,据调查这种状况主要是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和水体造成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河道的下游,一台台挖掘机正在进行清淤工作,据了解,是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治理此河道,几个月后此河段的水有望变得清澈。(二)企业调查结果我们走访了几家造纸厂和钢管厂,发现这些企业内都有一定的污染治理设施,排出的废水的水质都较好,能达到排放要求,有的企业还能够将水处理后循环使用。(二)居民调查结果据调查,很多人认为,目前临沂的环境大大不如十年前了,但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经过环保部门和广大市民的努力,几年前脏臭的河水如今已经变得清澈了许多,污浊的空气也变得新鲜了许多,我们周围的环境状况确实改善了许多,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还有一些河水存在一定的污染,有些时候市区内的空气质量也不能尽如人意等等。被访者普遍认为,确实应该加大力度、采取措施来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被访者就如何保护我们的环境纷纷提出了意见和看法,他们也表示愿意从自身做起,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来,为把我们的临沂城建设得更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可见人们对周围的环境还是十分重视的,他们的环保意识也是很强的。通过这次调查,我们了解到: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解决环境问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改变目前这种环境状况,光靠环保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提高我们大家的环保意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不是一个人造成的,保护环境也应该是全社会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同时,我们也懂得了:我们就是社会的主人,改善地球环境,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应该努力增强环保意识,节约资源。如果全地球人人破坏,天天破坏,地球就会变成垃圾场;如果全球人人环保,天天环保,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携起手行动起来,共同努力保护好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为此,我们建议从我们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要做到:1、一水多用、节约用水。2、慎用清洁剂,选用无磷洗衣粉,保护江河湖泊,防止造成富营养化。3、不乱扔垃圾及废弃物,将垃圾放到指定的垃圾箱内。4、尽量不用、少用塑料袋,要积极使用可再生利用的用品,减少白色污染。5、尽量少用一次性用品。6、多学习和宣传有关环保的法律,积极向环保部门举报破坏环境的行为。7、增强环保意识,爱护大自然,了解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和大自然交朋友。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家园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让我们以临沂市争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这一活动为新的起点,为保护环境、保护地球家园而行动起来吧!通过这次自我组织活动,我们深入了解了环保知识,增长了社会见识,锻炼了社会实践的能力。我们都认为这次活动开展得很成功。
水污染的调查报告
 理统
理统 美咲
美咲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zyling1208有关水污染调查报告3篇 水污染调查报告(一)一、调查原因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口的迅猛增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生态系统也会随之遭到破坏,环境问题已从地域性走向全球性,人类必须爱护地球,共同关心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将无法继续下去。水资源的污染及短缺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我市不是一个用水紧张的城市,但水污染却存在,并与每个市民都息息相关。为此,我通过询问形式对我市水污染进行调查。二、调查过程第一步:实地调查,首先,我随老爸来到长安航管站,向我爸的老同学刘海华了解长安镇河道情况,然后,乘坐快艇,游览了崇长港及长山河和泰山港,一路上,刘海华叔叔向我介绍几十年前,这些河道,是长安镇附近的主要航道,水清透彻,而现在垃圾遍布河道,一股臭味扑鼻而来。水污染主要原因:人为因素:泥河上流工厂的废水排放,城市布下水道安置此处,污水经管道排入河中,泥河附近大量农田,农民使用的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流入其中,致使藻类疯长,鱼类大量死亡,居民的环保意识差,经常将生活垃圾倒入河中。第二步:调查分析,经过实地调查,我认为水污染给居民带来的危害。地下水污染,用水困难,河水污染严重滋生大量蚊虫,河水散发刺激性气味,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水污染调查报告(二)1
写一篇生活污水排放的情况的调查报告
 棋魂
棋魂 霍金传
霍金传
关于督导员反映某小区的2间废弃门面污水横流的情况属实。东街社区协同居民组、楼幢长已于收到通知前着手处理此事。门面污水管破裂,污水流至路面的原因是此楼修建的基础设施薄弱,化粪池系改建且10年以上都没有清理过,造成化粪池至居民楼一段的下水道严重堵塞以至管道破裂,连下水道经过的门面地面都已涨裂,修复工程量大,经测算修复费用8000元以上,按管理责任应由居民户出资自行修复。但考虑到此楼的居民多是还房户或房管局租赁户,经济都非常困难,社区组织了居民组长、楼幢长及此楼的卫生管理人员召开居民会议多次,经联系并请示市政局蹇世儒局长后,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堵塞单元的居民按产权情况每户出资50-100元,大约有4000余元,差额部分由市政局出资修复。社区、居民组长已协同楼幢长、卫生人员着手收费并协同尽快修复!街道办事处东街社区居委会2008年6月9日
关于水污染调查报告
 礼法度数
礼法度数 瓠叶
瓠叶
表征废水水质,规定许多水质指标。常用的有:悬浮固体、生化需氧量BOD、化学需氧量COD、总需氧量TOD、总有机碳TOC、氮、磷、PH值和碱度等。一种水质指标可能包括几种污染物的综合指标,而一种污染物也可以造成几种水质指标的表征。如悬浮物可能包括有机污染物、无机污染物、藻类等;一种有机污染物就可以造成COD、BOD、PH值等几种水质指标的表征。采用 BOD5/COD评价废水的可生化性,一般认为BOD5/COD大于0.45时,该废水易生化处理,介于0.45和0.30之间时可生化处理,小于0.25时不宜生化处理。重金属离子问题汞、镉、铅、铬一般来说,一个废水处理厂所需要的基本设计信息如下。1、废水的来源和组成;2、废水的水质水量;3、废水本身及其中所含有用物质的回收利用的可能性,节约用水的措施;4、由于开工停工、事故性溢流或者其它冲击性负荷而导致废水处理系统出现过负荷情况发生的机遇率和严重的程度;5、由于处理(生产)工艺改进而引起水质水量的变化;6、涉及到不易控制事件,例如暴雨时水质水量的变化。为保证数据和推论的准确性,确保调查所需的时间。调查的前期准备:1、目标的确定:1)确定主要污染源,有机的和无机的,并分类;2)了解各废水的排放情况和流量变化,对主要的收集系统进行分类;3)考虑到处理系统中所可能含有的高浓度毒物;考虑产品回收利用的潜在可能性。2、污染物排出总量3、废水的水质监测4、样品的采集:水样的保存、预处理、分析
环保案例,报告或者调查报告
 莫愁女
莫愁女 命迂
命迂
环保调查报告2003年7月16日,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野生动物来说,可能是个悲喜交加的时刻。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在京召集了一个名为“可经营利用驯养繁殖陆生动物名录论证会”。来自全国的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研究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非政府人士30余人,共聚位于北京北三环的贵州大厦,对哪些动物种类列入可利用的名录进行了逐一讨论、甄选。我作为非政府环保社团“自然之友”的代表,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参加了这次会议。 一到会场,工作人员先将一份由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工商总局、海关总署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适应形势需要做好严禁违法猎捕和经营陆生野生动物工作的通知》(林护发[2003])99号)及一份“各省上报可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陆生野生动z物名录”发到我们手中。 我知道,此次会议就是为了贯彻落实这个通知的精神,规范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拟出一份向全国统一公布的允许经营利用的动物名单。但手中这份各省上报的名单则着实吓了我一跳。这个名单,尚不包括两广、竟已达到300种之多!既有明星动物大熊猫、亚洲象(福建上报)、金丝猴、黑颈鹤(甘肃上报)、丹顶鹤(福建、辽宁上报),也有来自国外的黄猩猩(福建上报)、鸵鸟(内蒙等20余省上报),当然还包括因非典名声大噪的果子狸(海南等17个省上报)。鸵鸟、蓝孔雀、果子狸、梅花鹿等动物已形成相当规模的人工繁育种群,经营利用也就罢了,要把这么多的集珍濒特于一身的野生动物推上可经营利用即可食用可买卖的餐桌、柜台,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我十分鄙夷地看着这份上报名录,不禁冒出一句:真敢开牙! 幸亏有国家林业局的官员们的严格把关,他们对这份基层上报的名录作了大刀阔斧的删除。会议开始不久,发到我们手上的,已是一份仅有34个物种的“可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陆生野生动物建议名录”了,对此,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首先,东北林大的马建章院士及国家林业局的王伟副司长向大家作了全面的背景介绍和拟定此名录的基本原则:既凡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并在实际中应用,具备产业化繁殖规模、存栏数量较大、不依赖野外资源作为种源的、不违背国际限制公约的陆生野生动物,将被批准利用,说白了,就是将被列为可食用、可交易的“黑名单”。 讨论按兽、鸟、两栖爬行及昆虫四大类依次进行。从鹿科动物开始,“梅花鹿”,没有人提出疑问就通过了,因为全国人工圈养技术早已成熟、规模较大;“马鹿”则引起了热烈反响,国家濒官办的范志勇处长首先提出:马鹿亚种较多,如新疆塔里木马鹿已高度濒危,一旦开禁,野生种群将毁于一旦。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在可利用名录上注明马鹿的塔里木亚种除外。 野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物种,分布广泛,性情强悍,繁殖力高,适应性强,因此时常与人发生冲突,被一些人说成是“害兽”。对此,王伟副司长说了几句公道话:不能认为野猪已经多到该杀的地步,实际上是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加大,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被一再挤压,才造成人与野猪的交叉分布和矛盾产生。即使利用,也只能是野猪和家猪的杂交种,如宁波象山,在这方面已有成功尝试,年出栏达12万头以上,很受市场欢迎。他们仅利用了少量的种公猪,未对野外种源造成压力。由此,列入可经营利用名录的“野猪”被限定为杂交种,对此大家表示赞许,并列举与之截然相反的不应利用、却滥用的一个反面例子。 吃蛇之风在全国、尤其是南方甚为嚣张,由此造成蛇少鼠多,生态失调,鼠疫隐患严重。经营者通常号称是养殖的。对此,与会专家提出,蛇类养殖场纯属掩人耳目。野味餐厅消费的蛇,均来自野生,而非人工繁殖。即使偶有繁殖,也未形成规模生产,因为,饲养者无法、也不愿付出这么长的周期、这么高的代价来养殖蛇类。 蛇是爬行类,作为两栖爬行类专家的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杨大同指出,牛蛙也不能上名录。我当时颇为疑惑,市场上、饭馆里不是常有卖牛蛙的么?经他介绍我才恍然大悟,牛蛙是一种攀爬能力极强的两栖动物,属于外来物种,容易逃逸,一旦进入野外,后果不堪设想,它会轻易将原产地的青蛙蝌蚪吃光,造成本地种灭绝。而饭店所食者多为“猪蛙”。哦,是名称错位。因此,最后一稿我们一致决定,本名录舍“牛蛙”而选“猪蛙”。 对外来种引入的问题,中科院动物所的张润志研究员作了特别强调,呼吁本名录的取舍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否则,一旦引种不当,管理失控,造成物种灭绝,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在利用名录的食肉目中,原有“赤狐”,但以WWF的于长青为首的几位专家对赤狐的可否利用提出置疑,认为养殖数量不多、若列入利用名录,对野生同类威胁较大,弊大利小。类似情况还有尽管人工养殖逾万、但野生者高度濒危的扬子鳄,最终赤狐和扬子鳄都被我们从利用名单中删除了。在利用名录的鸟类名单中,郑光美教授提出,金翅雀不宜列为利用对象,因为没有人工的规模繁殖,由此,金翅雀也幸免于“黑名单”。 我作为“自然之友”代表,先把梁从诫先生的对动物保护的有关观点转述给大家:其一,突破“保护是为了利用”这一过时观念,应突出保护第一、维护生态第一,用我的话就是树立维护“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其二,打破那种保护只限珍稀物种的做法,应扩大到一般物种,即利用范围不宜肆意扩大,保护范围不宜轻易缩小。其三,要尽早对“野生动物”的概念以法律界定,解决“野生”与“人工”概念含混的问题,特别要防止从野外抓回暂养、冒充人工饲养,蒙惑公众的现象。 2003、7、25 利用发言机会,我也将我的观点和盘托出:第一,对外来种的养殖要防止盲目引种、给本地土种带来的副作用,如专家所举泰国虎纹蛙的引种使海南虎纹蛙绝迹的案例。第二,利用驯养种,严禁涉及野外同种,如扬子鳄、梅花鹿、果子狸等不能因为对养殖的开禁就对野外个体大开杀诫。我甚至不无忧虑地说,列入这个名录,会不会就殃及野生、给这些动物判了死刑? 但是事实上,从人类的驯化动物历史和国际人工养殖惯例来看,这些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其身份已经与家禽、家畜类似了。所以,才有今天这样一个论证会。积极养殖,合理利用,还是有利于缓解人类欲望对野生个体的压力的,只谈保护,无视利用之现实,也是不现实的。允许吃养殖的野味,从地球伦理来看,是容小恶而达大善,毕竟,小恶不容,大善难存。多年来,保护与利用始终是一对矛盾,但并非不可调和,是一味封堵,还是该疏则疏,该堵则堵,这是当今涉及人与自然、与动物关系的一个现实问题,不应墨守成规,也不可肆无忌惮,毕竟,我们既要讲人道,更要遵天道,不讲天道,滥食野味,暴殄天物,伤天害理就会有“两院”等候阁下:吃了保护动物、触犯法律要进法院;饕餮无忌、招病伤身要进医院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们应该持一种怎样的环保观 我们应该持一种怎样的生态环保观和资源开发观?环保和资源开发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吗?我看不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因此科学的生态环保和资源开发是能够做到对立统一的。 我相信所有关注环境问题的人都怀着一颗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的赤诚之心。我们也不应怀疑那些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人尽早脱贫致富而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人,他们同样也有着一颗保证和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生存的拳拳之心。只不过极力主张保护的人考虑的是整个人类长远的生存问题,而积极主张开发的人要解决的却是当前局部地区人民的生存问题。我们有理由剥夺局部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吗? 这些年来,在各环保组织的宣传努力下,广大公民已经有了一定环保意识,这是各环保组织和人士的功劳,但有环保意识并不等于懂得了环保。我们还有很多人虽然有了环保意识,但出于对自身眼前利益的的考虑和贪图享受,并不愿意自觉地去遵守环保准则。例如,我们一些已经无需为自己的温饱担忧问题的人,为了尝一尝野味,穿戴高档皮毛时装,显耀自己的富有,于是促成并刺激了野生动植物交易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使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该受到指责的应是那些衣食无忧的消费者,而不是那些衣食无着,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索取自然资源的人,也不应去指责那些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尽快摆脱困境而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人。 为什么环境问题至少在工业革命以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现在却成了一个越来越影响人类自身生存的全球紧迫性问题?这是因为在过去,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及产生的各类垃圾还没有超出大自然的承受力,而现在,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利用及大量的生活和工业垃圾已经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这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人类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物质和精神享受穷奢极欲的不断追求。要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遏制人们这一不断膨胀的享乐欲望。因此我们在宣传环保和揭露环境问题时,最重要的应该是在我们这些衣食无忧,享受着现代文明生活的城市人中提倡一种为富济贫的道德观,过一种简约的生活。那些生活在贫困落后地区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落后简约了,已经简约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了。该如何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呢? 我们应该反对那种教条的,极端的环保思想。这种思想表面看上去很正确,也极能蛊惑人心,实际上却是非常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剥夺了贫困落后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 在偏远的贫困落后地区,当地的人打猎,伐树,烧荒,那是为了生存。也正是因为现代文明的曙光还没有照射到他们,所以还沿袭着这一落后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下,不打猎伐树,请问你让他们吃什么?烧什么?用什么?对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及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的一些环保者总爱不分青红皂白的加以指责,而且常犯一个善意的错误,那就是:你们不能砍伐这的原始森林,不能捕杀野生动物,不能在这的江河上建大坝,保留这的原始风貌,你们可以通过开发绿色旅游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啊。但是在当前我们国民素质和环保意识还不高的情况下,旅游真是绿色的吗?开发旅游就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吗?让我们来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吧。1.过去当地人只产生少量的生活垃圾,而且几乎没有不可降解的垃圾;而现在由于大量游客的涌入,带来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特别是那些过去当地极少见到的塑料食品包装袋;请问这是谁之过?2.由于游客们要品尝当地的野味,原来不存在的野生动植物交易运营而生了;过去当地人只是少量地捕杀和挖掘野生动植物,满足自家食用就行了;现在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也为了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他们开始大量捕杀和挖掘野生动植物了;请问这是谁之过?3.过去当地人,民风淳朴,待人真诚;而现在伴随着各色游客而来的各种光怪陆离的山外文化,及不法商贩带来的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和花样百出的坑人,骗人的手段,让当地人受益匪浅,从此民风不再淳朴,待人不再真诚;请问这是谁之过? 云南的泸沽湖景区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然而这个报道仅仅只是简单地指责了当地的有关政府部门,有几个人想过这一切是谁带来的呢?这种情况几乎所有景区都未能幸免。在此我并不是反对开发旅游,我想说的是,开发旅游并不是解决环保与发展的万能药,搞不好,开展旅游比开发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大。而实际上旅游本身也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利用,因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是能不能和该不该得问题,而是怎样开发的问题。 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该是一味地追求原封不动,一丝一毫都不能改变。持这种极端环保观的人在关心环境的同时,忽略了生存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偏远的贫困落后地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们把环保理想化和教条化了,使环保失去了生命力。这种人自己吃饱喝足,无忧无虑地在城市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有几个到过偏远的贫困落后地区,更别说在那生活和工作了。少数人去过,那也不过是坐着豪华越野车蜻蜓点水般去游山玩水而已。他们只不过是想借此,保留下供城市人酒足饭饱后能有个娱乐和寻幽猎奇的后花园罢了。按照他们的观点,人类恐怕要回到原始社会才符合要求。这种思想只能使我们作茧自缚,让社会停滞不前。 一次我到云南省的独龙江旅游拍照。那里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清澈的溪流江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时当地居民贫困的生活状况也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边防战士对我说的一段话:“这里对你们旅游者来说是青山绿水,可是对我们这些天天在这的人来说则是穷山恶水。”请注意,这还只是一个只需在此服役两年的人说出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世代生活于此的人来说又会如何呢?这句话对我犹如当头棒喝,使我这个也曾大喊环保的人清醒了许多。 我们不能把所有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视为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样做真的太自私,太教条。我们反对的因该是那种不顾长远利益,盲目的,过度的毁灭性开发,而对那些能使当地人脱贫致富,步入文明,已做过生态评估,考虑到了开发后的生态恢复,有序的,科学合理的开发不因横加指责和阻止。实际上,只要做到科学合理的开发,那种局部的,暂时性的破坏并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而相反会形成新的生态景观,甚至改善原来恶劣的自然环境。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没有。远的有四川的都江堰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近的有浙江的千岛湖和云南的鲁布革水电站。 在环保方面,我们目前最急迫的目标不是简单粗暴地去指责和阻止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要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特别是要提高那些住在城市中,生活在文明中,不愁吃穿的现代城市人的环保意识。那些偏远贫困地区没有环保意识的人,他们对环境的破坏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有些甚至可以说其行为本身就是当地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链。反倒是我们这些有文化的现代城市人在吃饱穿暖之余,为了贪图享受,刺激了一些奢侈业如皮毛,高档木制家具,野味餐饮,一次性用具的发展,这些行业的发展才真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彻底而毁灭性的打击,现代文明的城市人才真正是生态环境直接和间接的杀手。 试想,假如有两个人,一个是不愁吃穿的富人,一个是衣不掩体,食不果腹的穷人,一只珍惜的野生动物出现在他们面前,富人为了享用皮毛和野味而捕杀之,而穷人则是为了御寒,填饱肚子活命而捕杀之,请问两种行为都该受到指责吗?
关于长江水污染的调查报告
 慧思
慧思 荀况
荀况
水污染的调查报告 一、调查原因 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口的迅猛增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生态系统也会随之遭到破坏,环境问题已从地域性走向全球性,人类必须爱护地球,共同关心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将无法继续下去。水资源的污染及短缺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我市不是一个用水紧张的城市,但水污染却存在,并与每个市民都息息相关。为此,我通过询问形式对我市水污染进行调查。 二、调查过程 第一步:实地调查,首先,我随老爸来到长安航管站,向我爸的老同学刘海华了解长安镇河道情况,然后,乘坐快艇,游览了崇长港及长山河和泰山港,一路上,刘海华叔叔向我介绍几十年前,这些河道,是长安镇附近的主要航道,水清透彻,而现在垃圾遍布河道,一股臭味扑鼻而来。水污染主要原因:人为因素:泥河上流工厂的废水排放,城市布下水道安置此处,污水经管道排入河中,泥河附近大量农田,农民使用的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流入其中,致使藻类疯长,鱼类大量死亡,居民的环保意识差,经常将生活垃圾倒入河中。 第二步:调查分析,经过实地调查,我认为水污染给居民带来的危害。地下水污染,用水困难,河水污染严重滋生大量蚊虫,河水散发刺激性气味,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三、调查结论 为了改善河道环境,应尽快开展河水、河岸等全方面的治理工作。首先,对污染源进行处理,杜绝工厂、养猪场把污水、粪渣直接排放到河流中,应集中处理,避免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然后,对河边、河道中的建筑材料(已废弃的)进行清除,并对水道进行整改,进一步将河内的垃圾、淤泥清除,可动员沿岸居民及利用大型机器清除。后在河边种树,植草皮,建立绿化带,避免沙土流失。 2、为了对河道环境的保障,应对附近的工厂、养猪场等加大管理力度,对污染河流的行为进行严肃的处理,并且对沿岸居民及全体市民进行环保教育,增强环保意识,河流的环境,主要还是在于大家的思想意识,故人们应自觉保护河道,保护环境。这样,一条全新河流才会永远呈现在人们面前。 总之,要明确,环境受破坏,受影响的还是人们自己,我们应当充分了解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认识到人们改变环境的利与弊。影响水资源的因素还远远不止这些。虽然我们的调查研究也许还不够成熟,但希望能把环境问题,水污染问题在人们的脑海中的地位提高,这样才会使出现的问题一天天好转。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