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兰州理工大学的情况 非常感谢谢谢
 我爱你
我爱你 奔梦路
奔梦路
您好,我是兰州理工大学09年热能与动力工程毕业的,现在在江苏大学读研究生。首先我对这个学校还是有感情的,坐落在西部,没有喧嚣,没有过多的浮躁,只是比较务实,尤其工科比较有特色,最好是专业是流体,材料,土木和机械、化工也不错。有两个校区,一般工科的学生,前两年在新校区,后面在校本部。总体上学风比较好,工科专业就业比较容易,问题就是学校资金不充裕,学校的补助奖学金什么的很少很少,总体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这个学校
兰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复试都有什么内容
 赋格曲
赋格曲 胡宏
胡宏
兰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复试内容分为以下三部分:综合素质面试、外语水平测试(含口语和听力)、专业知识面试,成绩均为百分制,满分100分。其中:综合素质面试占复试成绩的30%,低于60分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外语水平测试占复试成绩的30%,其中听力成绩占外语水平测试成绩的50%,口语成绩占外语水平测试成绩的50%;专业知识面试占复试成绩的40%。考生总成绩的计算公式为:总成绩=初试总成绩*70%/5+复试成绩*30%。兰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招生的有7个专业,复试科目不完全相同。080501材料物理与化学,080502材料学,080503材料加工工程,0805Z1先进材料及其制备技术,0805Z2先进高分子材料,这5个专业的复试科目如下:801材料科学基础、803材料力学B、821金属学与热处理原理、823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四选一。 同等学力加试:①材料分析方法,②材料力学性能080601冶金物理化学,080603有色金属冶金,这2个专业的复试科目如下:801材料科学基础、821金属学与热处理原理、831物理化学、864冶金原理;四选一。 同等学力加试:①冶金传输原理,②有色金属冶金学
讲讲国防生的奖金发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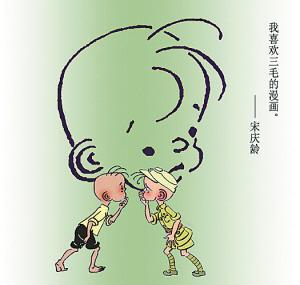 思虑恂达
思虑恂达 慎守其真
慎守其真
1.国防生的发放要看你们学校的选培办的上级主管部门是怎么规定的。以北京军区为例:奖学金是每年的4月初一次性发放1万元现金。基本上不存在扣除学费和分月发放的情况,可操作性不大。1万元是现金,一般是先给你办一个银行卡,然后打在卡上,完全供你自由支配。2.国防生的生活也没什么好说的,出来出早操,定期参加军事训练、政治课,几乎就跟普通生差不多。国防生是没有军籍的,一般国防生都没有军装,只有一套训练用的作训服。地方高校招收国防生有关规定 国防生是指根据军队建设需要,由军队依托普通高等院校,从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培养的青年学生,或从低年级在校生中选拔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国防生与高校其他在校生的区别:国防生在校学习期间,享受国防奖学金,接受必要的军政基础训练,毕业时按照协议定向分配到军队担任干部。国防生由所在高校负责管理,军队驻普通高等学校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简称“选培办”,下同)协助做好有关工作。学习课程安排上,与本校同专业同期入学的其他在校生相同。 报考国防生应具备的条件:①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并达到招生院校在本地区的录取分数线;②符合《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政治条件的规定》,思想品德优良,志愿从事国防事业,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③年龄在20周岁以下(截止当年8月31日);④身体健康,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毕业后拟分配到军队专业技术岗位的国防生,视力标准可以适当降低。 志愿报考国防生的考生,对照今年的国防生招生计划,填报招收国防生的普通高校及相关专业。具体报名时间、方法由所在省市招生办公室自行规定。 国防生录取方式:国防生录取工作由招生院校负责,选培办协助,采取远程网上录取。政审、面试和体检均合格的考生,且统考成绩达到报考院校招生专业在招生地区的录取提档分数线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依照考生分数从高到低的顺序,按招生计划数的120%的数量投档,由招生院校择优录取。 填报国防生志愿,但不具备国防生条件或未录取为国防生的考生,不影响其他志愿的正常录取。 获地区(市)以上的三好学生、学生干部、党员和特长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对符合国家规定的保送生条件且志愿从事国防事业、综合素质较高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按照国家招收保送生的办法,经政审、面试和体检合格,可免试保送为国防生。 国防生奖学金标准:国防生在校期间享受军队提供的国防奖学金,奖学金标准根据市场物价和高校学费情况制订,由部分学杂费和生活补助费两部分构成,其中,学杂费由军队与普通高校直接结算,生活补助费由选培办逐月发放给学生本人。目前,国防奖学金的标准暂为5000元/年。 若如因计划限制未录取为国防生,还有机会成为国防生:军队每年除按计划从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招收国防生外,还从与军队签订依托培养协议的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选拔一定数量的国防生。具备国防生报考条件的考生,如考取了与军队签约的普通高校,仍有机会成为国防生。签约的高校专门设有国防生选拔培养办公室。 国防生毕业分配:国防生毕业时经院校和选培办综合考评合格者,按照《国防生协议书》定向分配到军队工作。分配去向按照专业对口、人尽其才的原则合理确定,在满足军队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兼顾本人的实际情况和意愿。国防生毕业后,主要补充到部队专业技术岗位,部分符合指挥干部基本要求的,可补充到指挥岗位任职。 国防生毕业到部队报到后,享受现役军官(或者文职干部)待遇,家属享受军属待遇。在首次定职定评授军衔、评任专业技术职务以及住房分配等方面,与同期入军校学习的毕业学员相同。根据军队有关政策规定,本科毕业生一般定为副连职(或技术十三级)、中尉军衔(或文职八级),硕士研究生定为正连职(或技术十二级)、上尉军衔(或文职七级),博士研究生定为正营职(或技术十级)、少校军衔(或文职六级),入伍时间从批准之日算起。 上一页 1 2 3 附:国防生招生院校名单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 河北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山西大学 中北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内蒙古大学 辽宁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沈阳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吉林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燕山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政法学院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南京邮电学院 河海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浙江大学 安徽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 厦门大学 集美大学 南昌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 东华理工学院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 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理工大学 聊城大学 郑州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湘潭大学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南华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西大学 桂林电子工业学院 四川大学 重庆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西华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云南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西北大学 西北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兰州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宁夏大学 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宁波大学 西安邮电学院 广东工业大学
了解贫困生
 吴樾
吴樾 是其言也
是其言也
中午一包方便面,晚上一包方便面。为了吃饱,再多兑一些水,喝带咸味的汤。大学生周亮终因营养不良患重度胸膜炎住进了医院。“他节衣缩食,为的是给只身一人供养自己上大学的母亲减轻一点负担。”老师了解周亮的家境。 在兰州理工大学,像周亮这样的贫困生还有许多。学生餐厅的河南籍老板时常感到内心难以承受:“有一个男生,每到中午吃饭,只打两个馒头,然后悄悄地坐到餐厅的一角,等大部分同学散尽,慢慢地凑到其他同学吃剩的饭菜前,用馒头蘸着菜汁吃。好心的同学邀他免费用餐,被他拒绝。我叫他帮我收拾碗筷,管他中午吃饱,他答应了。” 餐厅老板事后了解到这名男生的家境:腿瘸的父亲、耳聋的母亲供养着他们兄妹3人上学。所以他从不主动向家里要一分钱。那种眼神让人心碎 “营养不良、吃人剩菜的情况有些特殊,但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我们学校,每月生活费在180元以下的学生已经超过在校学生总数的30%,接近32%,有近5000人。其中每月生活费不足120元的特困生有四五百人。”兰州理工大学学生处处长张浩辰解释,“我们学校70%的学生来自甘肃,加上西部其他省份,西部生源超过在校学生总数的80%。这80%中,近一半是贫困生。” 为了解真实情况,张浩辰曾联合校团委对学生在食堂的刷卡记录作统计,以每月刷卡25天以上、每天刷卡不少于两次为准,结果发现有的学生月消费只有29元。月消费120元至150元的过千人。他们的食谱基本是:早餐一个饼,午饭两个馒头一份菜,晚饭一碗面或者一份米饭外带一个菜。菜以素菜为主,每隔两星期左右能改善一下,吃一次荤菜。午饭、晚饭的开支一般都在两元左右,早饭则不超过1元。 “我时常面对学生的贫困而欲哭无泪。”该校学生处勤工助学中心主任陈波说,他每年都要在学校设立的“绿色通道”迎接交不起学费的新生。他发现,这两年来“绿色通道”求助的学生越来越多。 “前几年,学生还会向你倾诉,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默默地站在你的面前,那种眼神看了让人心碎!他们的衣着明显不合身,他们所带的经费要么交够一项费用后就所剩无几,要么连一项费用都不能交齐。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帮助上。” 陈波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对姐弟同时考进兰州理工大学,在新生报到时两人所带的费用只够一人交学费。当得知没有学籍便不能申请助学贷款时,姐弟二人便相互推让起来,姐姐让弟弟先上,弟弟让姐姐先上。 “这是上不起学的情况。的学生则是上了学无法正常生活。我们的贫困生,不少人因营养问题身体出了毛病。还有的贫困生,因无法解除的心理压力,在个性与人格上发生了变化,甚至出现了某些精神病症状。” 陈波说:“我感觉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否则,我的良心过不去。” 陈波出身大学教师之家,原本养尊处优,不知道什么叫贫困。自从6年前开始做贫困生资助工作,他的同事夸他“变得会关心人了”。他本人也“感到自己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孩子们教会了我如何面对困难,坚韧不拔”。 去年迎接新生时,一名来自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女乡长,将一对双胞胎兄弟领到“绿色通道”,十分诚恳地告诉陈波,这两个男孩打小失去双亲,由乡亲们你一把我一把拉扯长大,之后在乡政府的资助下读完高中,现在乡政府已无力支付他们的学费,只能把他们交给学校。 在积极为这对孤儿筹措助学金的同时,陈波与自己的双胞胎弟弟开始结对帮助他们,每人每月拿出200元保他们的生活费。现如今,这对双胞胎成了陈波家的一分子,逢年过节都和陈波的家人一起度过。 不仅是陈波。兰州理工大学每年对新生进行救助资格审查的时候,学生处的老师们几乎都不等谈话结束,就已经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孩子们太穷了。”张浩辰处长说。 只要给贷款 磕头都愿意 自从国家出台大学生助学贷款的相关政策后,学校当即成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领导小组,主动加强与经办银行的沟通交流。“尽管我们和经办银行相处得很好,尽管我们认真面对银行的每一个表格,尽管我们为此建立了10万元的风险基金,尽管我们学生的实际违约率只有0.02%,我们能使的劲都使上了,但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学生的需要。”陈波说出一连串的“尽管”。 据了解,从2001年到2005年年底,兰州理工大学实际拿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是2002人,总金额840多万元,平均一年160多万元。“而学校一年的实际需求在1000万元左右。” 经办此事的陈波心中有一本账,“我们拿到的助学贷款,在省内高校已经算是多的。” 陈波说自己常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哪家银行的行长说,陈波你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我给你助学贷款,我都愿意。” 正是靠这份“磕头都愿意”的恳切,兰州理工大学在西部地方高校中,争取到了相对较多的社会资助。 听说哪儿有个好心的老板,听说哪儿有个关心西部、关心教育的慈善机构,他们就去登门拜访,向人家讲述一个个贫困生生活和学习的故事,介绍学校严格的善款管理制度。 “这些年我没休过一个黄金周。”张浩辰说。每当“五一”、“十一”,他和同事们几乎都要陪同远道而来的资助者,在西部荒凉的大山里转,走访贫困学生家庭。资助者看到自己的钱每一分都花到了真正的穷孩子身上,心里踏实了,也就愿意向兰州理工大学捐出的钱。 学校争取到的第一笔资助是以香港镇泰集团为主设立的海鸥助学金。1999年第一批资助6人,人均6000元,共3.6万元。第二年增加到20人。由于学校管理规范,受资助学生成绩优异,受到资助方好评。2001年,镇泰慈善会紧跟其后在该校设立镇泰奖、助学金,每年6万元,为期3年。3年后,镇泰慈善会不仅续签了协议,而且将奖学金额度提高到了11万元。与此同时,镇泰集团的苏纪英先生和黄铁成先生又以个人名义在学校设立镇泰助学金,先后资助贫困生111人,累计资助金额达209万元。 “有一分希望,我们就要做百分的努力。”陈波介绍说,深圳健峰公司在学校设立的健峰奖学金,原本只计划资助10名贫困生,但校方提供了37名同学的详实资料,并专程赴深圳拜访汇报。健峰公司为校方的诚意所打动,主动提出将资助名额增加到40名。当年3月,公司相关人员赴兰州了解情况,临别的那天早晨,40名受资助同学自发从学校步行赶往市区健峰公司人员下榻的宾馆送行。回去后,公司再次扩大资助范围,受资助学生由40名增加到100名——人均4000元,一年就是40万元。 “从最初的6人3.6万元,到如今的5000多人累计970多万元的资助金额,大大小小有十五六个奖、助学基金,年度资助额已超过200万元。这在甘肃省属高校中是没有的。” 尽管感到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张浩辰和他的同事们仍在尽其所能:“学校业已形成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校内奖、贷、助、补、捐、俭为辅的贫困生资助体系。2005年,实际资助经济困难学生5938人次,是全校经济困难学生总数的108%。也就是说,只要学习尚可的经济困难学生均有机会获得资助,年度资助金额不少于1000元。有的经济困难学生,哪怕是学习成绩差一些,但只要有努力学习的愿望,我们都能保证其在学校继续就读。所以近10年来,我们学校没有一名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硬问题?软问题? 来自河南的文明同学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1993年父亲病逝,同年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远走他乡,只留下11岁的他和住他家房的一位叔叔一起生活。 “2002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看学费4000元,住宿费800元,我犯了愁。姑姑、伯父和乡亲们全都动员起来,给我凑了3000元。汇到学校2000元,买完火车票和一点儿日用品,我的手头只剩下五六百元,忐忑不安地到了学校。” 文明进入“绿色通道”,向陈波老师讲明情况,陈波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鉴于他的特殊情况,学校暂缓了他的学费。很快,陈波又为他在学校勤工助学中心安排了一份工作,每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很快,文明又申请到了学校的特困补助,他交齐了住宿费。第二年,在所在学院的极力推荐下,文明又拿到了为期3年的镇泰助学金,第一年资助6000元,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为7000元。加上当家教的收入和拿到的奖学金,文明的生活彻底有了保障,再也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还补交上了第一学年欠下的学费。 回首往事,现已考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文明有感而发:“是学校给了我机会,让我安心学习,找到了做人的自信。以前我不愿对别人提起我的家庭,现在我可以坦然面对了。我感到自己过得很充实,很幸福。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报这个社会。” 采访中记者发现,受资助的不少大学生和文明一样怀有感恩之心,生活态度积极。 “以前,我对别人很冷漠,很偏激,现在改变了很多。高中同学都说我的变化很大。今天我受了别人的资助完成学业,明天我也一定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原本性格内向、见人不爱说话的魏国宁同学面对记者侃侃而谈。 听着学生们的真情告白,陈波泪流满面:“和他们待久了,有一种心贴心的感觉。如果允许,我愿意一辈子做贫困生救助工作。看到他们受资助后脸上露出的笑容,我比得到多少钱都高兴。” 同样的感受,有着多年学生工作经历的张浩辰也有:“贫困生的救助是个阳光事业,是个温暖事业,是个硬问题,也是个软问题。争取多少社会资助算够,学校没有指标,但爱心、责任心、同情心促使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好。” 谈起贫困生救助,兰州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云对成绩一带而过,地说到了学校的责任:“学校的职责决定了要关注每一个大学生,尤其是贫困生。我们尽最大努力资助贫困学生,为的是让他们放下经济包袱,专心学业,成长成才。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只有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社会才能和谐。而受教育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我们适时地给这些经济困难的学生以关爱,他们成长起来以后,也会关爱我们的社会。”我家里比谁都穷,我18岁就出去打工。人家18上大学,我确做了5年民工,23岁才凑够了钱上大学,毕业都27了,还要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去找工作。而且荒废了5年的时候,我都不敢报北大了,最后考到上海同济去了。现在快30了,还在最底层做,对象也没有着落。但我相信我当时要是不努力的话,就得做一辈子民工了。
兰州理工大学对新生的基地班选拔是怎么回事啊
 其寒凝冰
其寒凝冰 六月
六月
基地班一般是由国家专门拨款,专门培养某一方面的人才。基地学生除享有一般学生享有的全部权利外,国家和学校每年还拨专项基金数十万用于基地建设;学校设有专项基地奖学金,专门奖励品学兼优的基地学生;学校将优先推荐基地优秀学生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并选送基地部分优秀学生到国外深造或攻读硕士学位。 大学中基地班的招生平均分数一般是最高的,一旦考入往往可以保研。基地班考试资格是根据所在专业和院系当年录取人数而定的,比如土木工程学院,机电学院,流体学院这样的大学院中可以参加考试资格多,而且录取比例大,录取人数也多。提前复习复习吧,主要是数学和英语。加油!抓住这个机会!
兰州理工大学酒泉校区励志奖学金一个班几个
 两家人
两家人兰州理工大学奖项
 孔舞者
孔舞者兰州理工大学研究生每年有校奖学金吗
 人见其人
人见其人我想调剂到兰州理工大学石油化工学院,但网上说没有奖学金是什么意思么???
 茅趸王
茅趸王 脐
脐
从2014年开始 研究生全部是自费的没有公费了,但是有一些学校 会以奖学金的形式把钱再给学生,让学生用来交学费 和当做生活费!当然 每个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学校说没有奖学金 你就要打电话好好咨询下了!可能就是全部自费了,或者到了学校可以申请助学补助!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