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学院没有研究生部吗?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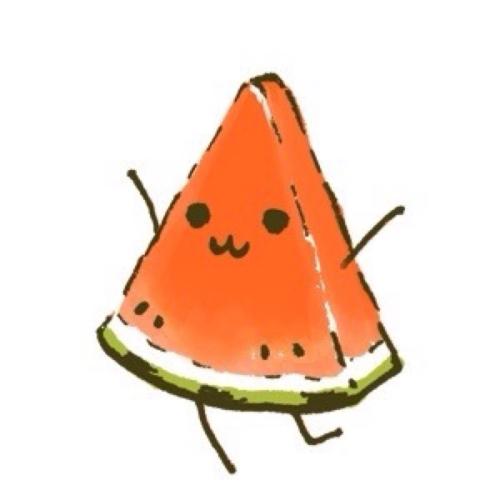 人谓之樗
人谓之樗惠州学院有服装设计在职硕士研究生读吗
 群下荒怠
群下荒怠 大勇不歧
大勇不歧
目前在职研究生的教学资源分布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在职研究生分两种,一种是一月联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MBA、MPA等少数可以获得双证的在职研究生专业,另一种是五月同等学力在职研究生报名条件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考试比较容易,学费平民价格。符合条件最后获得硕士学位。
物流考研学校有哪些??
 侵人自用
侵人自用 萌区有状
萌区有状
1、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工商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办“物流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之一,重点定位为“企业物流”与“物流企业”的管理。其物流系统理论与方法、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流通技术与方法、连锁经营与配送等专业是该校物流专业的特色。有两门课程直接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任课教师直接用英文讲授。2、清华大学物流工程是工业工程系的一个研究分支,本科阶段以“工业工程”专业招生。工业工程系制订的目标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工业工程系接轨看齐,采用的手段是广泛开展国际、国内合作,聘请国内外工业工程界的著名学者、教授来校任教、授课或开展合作研究,参照世界一流大学的培养体系建立自己的培养方案,直接选用国际一流大学工业工程专业使用的外文教材,进行双语和英语授课。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该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下设国际运输与物流系,优势主要是国际物流操作。学生精通海、陆、空运和多式联运等具体操作环节,加上外经贸的特殊背景,外语、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都比较好。4、北京物资学院北京物资学院物流系主要研究领域:物流系统设计、物流规划、物流管理、物流结点建设、物流信息系统、国外物流等方面。5、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构筑以船舶与海洋工程为主干,融海洋科学技术、港口航道工程和海岸带开发技术以及国际航运与物流管理为一体的学科体系,以期成为能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形成强大支撑的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广州地区二本的大学有哪些?
 微笑圈
微笑圈 书不过语
书不过语
广州地区二本的大学有:1、广东金融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院校,也是华南地区唯一的金融类高校。广东金融学院创建于1950年,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分区行银行学校,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管理;2000年,院校管理体制改革后,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同管理,以广东省管理为主。2004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升格为本科院校。2、广东财经大学:1983年建立,原名广东财经学院,1985年改名为广东商学院,2013年6月19日,经教育部批准,广东商学院更名为“广东财经大学”。是国家教育部《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定点高校之一,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高校,“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成员。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一所具有鲜明国际化特色的广东省属重点大学。学校入选“2011计划” “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 “亚洲大学学生交流集体行动计划”(亚洲校园计划),是向联合国提供高端翻译人才的全球19所大学之一、全国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的创始单位之一。4、广州医学院:是一所以医学为优势和特色的广州市属重点高校,为教育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中俄医科大学联盟成员高校。学校于1958年6月经广州市人民委员会批准设立,原名广州医学院。1970年12月,更名为广州市医科学校。1973年6月,恢复广州医学院名称。2013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广州医科大学。5、广州大学:简称“广大”,是广东省广州市重点建设的普通大学,也是广州市市属大学,“CDIO工程教育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试点高校,也是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重点建设高校。参考资料:广东财经大学-百度百科
惠州学院成人高考学历文凭有用吗
 菊池
菊池 诔曰
诔曰
你是否面对着就业、工资待遇、职称评定、考研、考证、留学、工资待遇的机遇,但是却缺少学历,是看着机遇流失还是奋起争取啦?人生就是做不完的选择题,惠州学院成人高考愿助你一臂之力!惠州学院成人高考学历文凭(函授大专、本科学历)因为是国家承认的,所以还是对我们的事业有着很大的好处。惠州学院成人高考好处如下:1、就业:许多单位(尤其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招聘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由于学历原因,会丧失许多理想的工作机会。2、工资待遇:我国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基本都是按照学历定工资,本科工资比专科工资高一档次,较规范的企业也是按学历定工资,而且本科以上的奖金和提升机会都比专科相对多一些。3、人事改革:许多单位(尤其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提拔干部、竞选领导基本条件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即使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却没有竞选资格,专科以下即使找到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可能面临下岗失业的危险。4、职称评定:如今各类职称评定几乎都与学历挂钩,在评定高级职称时专科以下基本上没有机会,而在许多的单位的主管领导几乎都是由高级职称的人担任的,没有高级职称会失去许多当主管领导的机会,而没有本科,又会失去评高级职称的机会。5、考公务员:公务员工作稳定,待遇较高,压力较小,而在大多数公务员岗位都要求本科以上才有资格报考,通常只有基层和艰苦的工作岗位留给专科一部分。6、考研:有了本科学历,不需学位证,就可以直接报考全国统招研究生,而专科生只能在专科毕业满两年后以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7、考证:许多国家职业资格证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如在公证员、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司法考试报名条件要求必须是本科以上学历。8、留学:在许多国家都承认我国的本科学历,有了本科,就可以在国外直接读更高一级学历,会省很多时间和费用。
广东第一批的大学有哪些?
 未发
未发 若牧羊然
若牧羊然
重点本科:南方科技大学(2010年招收第一批学生,落户深圳市,毗邻北大跟清华的研究生院,效仿香港科大的成功模式,如果你是希望报读工科,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据说,如果模式成功的话,将超过华南理工大学成为华南第一工科院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汕头大学2A:地区性各城市大学:深圳大学惠州学院广州医学院茂名学院五邑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大学东莞理工学院湛江师范学院挂广东名的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湛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医学院(东莞,湛江都有校区)广东药学院广东商学院广东金融学院一批的: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汕头大学;2A的:广东工业大学,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商学院,广东警官学院,广州大学,深圳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东莞理工大学,仲恺农业学院,肇庆学院,佛山科技技术学院,广东海洋大学,韩山师范学院,惠州学院,湛江师范学院,五邑大学,嘉应学院,茂名学院,韶关学院,
我广州理科考了521..应该去那些2A学校比较好?..(男女都有.相同分数)
 狗咬狗
狗咬狗 藏宝图
藏宝图
惠州学院不是也挺好的嘛不过你广州的貌似不太愿意去惠州?惠州其实还不错啦。广州大学的风险比较大 ,不是有3个平行志愿吗,可以第一志愿填广州大学,反正录取不到可以录第二个,3个平行的又没有什么先后顺序。参考下去年的分数线,我认为可以你行的。专业的话,学理科更好找工作,学文科难找工作,不过,文科潜力更大。一爆发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啊,学贸易啊、电子商务做网络生意,开贸易公司。学金融,周期比较长,做金融经纪方面的需要口才、策划能力,学分析的,想学好的话是需要考研的,金融一般都要研究生。惠州学院的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管理教育) ..后面括号是不是表明指教那一类?.与其它没有括号标明的一样么?....惠州好像只是比A线上一点... 对了..惠州学院环境好不好?..环境好的出了广大还有哪些我能上的?...惠州学院起码比韶关学院好点吧。惠州环境是很不错滴,新校区呢。离市区很近。。。括号里的是大类,与其他的,实际区别不是很大。。
感性论的引言
 发乎天光
发乎天光 众生相
众生相
本书由“形象的力量”、“美的世界”、“表现的世界”和“表现的过程”等四章组成。通过这四章,我们要搞清楚人类经验的特殊构造和它的有限但又被开放的方式。因此,我们要涉及一些理论。但是我们要把出现在这些理论中的概念和我们的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即以能够不断返回我们的经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概念。这就是我们的课题。优秀的理论能够促使我们反省那些比我们的经验陈腐了的观念;优秀的理论还具有把我们引向更加被开放的世界的力量。为了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解读文本,使其变换成能够抵达我们经验的语言。我将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接近文本。这也是我们必须尝试的。这是因为用身体来理解优秀的理论或者在品味理论是否优秀的时候,首先要把自己和他者的理论同化起来,或者尝试着进行模仿(模拟/simulation)。实际上我们从幼儿的时候起,就一直通过模仿父母和他人的语言和动作,才长成了现在的我们。我们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接触各种各样的他者,学到各种各样的他者表现。我们就是这样变化或者进化过来的。这种状况,无论我们上了多大年纪都是不可改变的。这样说来,本书的基本观点已然明了,即“经验是不断根据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而被更新着的”。后两章之所以专论“表现”,就是因为我们要具体考察经验是如何根据表现、以及表现媒体和表现技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第一章专论“形象(image)”。我们经验的现场就是形象的世界。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经常让理论返回到这个现场。我们从诞生的瞬间到死亡的瞬间,总是被有形的现象——形象包围着。即使我们闭上眼睛,“形象”也还会以记忆像、梦中像或者幻觉像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意识里。仿造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 - 1976 德国)的说法,我们是“形象内的存在”。仔细想来,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绝对无法逃离形象。因此,形象的理论不仅只是“艺术”的理论,而是与人类经验的全体有关的理论,它也不得不成为这样的理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十分注意到形象作用于我们的力量和它的现实性。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和形象的关系太明确了,以至于没必要想得那么多了。与此同时,一般我们对于形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识,还有更深刻的理由。那就是“语言”遮蔽了形象。我们从出生后开始记忆语言的时候起,就学到了把形象转换成语言的方法。所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几乎所有的形象都有名称。所谓语言,和符号一起是由比较安定的系统组成的世界。几乎所有的形象都和这个语言??符号联系在一起,形象的直接作用力被剥夺或者被遗忘了。所以,我们对出现在自己意识里的形象,即使不一一做出反应,也可以得过且过。如是观之,“形象”的理论就必须包括“语言论”。我们所经验的形象里已经渗透了“语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们的经验里,即使你觉得这是你的直接经验,但实际上语言也早已渗入其中、盘根错节了。“语言?符号系统”,是“形象的特殊系统”,是“比较安定的形象系统”。这也是本书所要论述的。对此,我们先简单加以说明。语言符号是“形象”的一种。它们只有在分辨形和声的差异时,才能够发挥作用。“A”和“B”都是有形的现象,也就是说,它们作为“形象”在构造上有差异,作为声也有差异。因为我们能够认知这种形和声——形象上的差异,所以才能学习语言。并且因为很多人都能够认知这种差异,所以才能习得共通的语言,共同讨论特定的事物。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认知形象的共通性”问题。在第二章《美的世界》里,我们就是以这个问题为主题的。“美”和这种“认识的共通性”的问题紧密相关。形象认识有共通性,这对我们提出了一个与他者“交往”的希望。现在由于有宗教信仰的差异、政治思想的差异,各种争端纷至沓来。这意味着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特定的语言符号系统——在人类的经验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形形色色的冲突和对立已不单单是思想的问题,它也变成了感情、情绪的问题。因为就连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反应——厌恶感和好感中,也渗透着语言,所以那些争端不是通过政治或宗教的对话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形象认识里的共通构造,为我们打开了通过语言对话所不能解决的“交往”的可能性。只要是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摆脱了中央控制塔管制的个人,在没有来自于上面的指令和口号的状况下,与他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往。实际上,在个人的层面上,政治信条和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人们早已开始了丰富的对话,早就在互相交流着经验。今后这种对话和交流还将继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比起“中央控制塔”来,“边境”和“分界线”地带更为重要。那里既是激烈的憎恨一触即发的现场,也可能是具有不同信条的人们实际进行交往、产生友情的场所。这样想来,人类认识构造里所具有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虽然不能被轻易地表现出来,但是也还是能够被“想定”的。为此,在第二章我们分析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考察了“美”的普遍妥当性。我试图把这种希望上升到更具体的理论高度。恐怕这一点会被很多人所批判:我太乐观了。但是我其实却是很悲观的。因为我不认为这种对话交往的可能性会全面地变成现实。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信赖认识构造的共通性,开展与他者之间的实践对话行为,不断转换我们的经验。这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大道理,而是一个实践性的课题。因此,我的思想,从倾向上说来,既不是保守,也不是激进。因为问题在于个人的经验、思考和认识的实践中,所以“感性论”从一开始就不能变成某种组织或能够支撑某种组织道德的那种“强硬的思想”。我们的《感性论》就是重视个人经验,进而探索和他者的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这个思想也许会被称为“不负责任的思想”。诚然如此。对这个连个人经验和认识都丧失了机能的世界,谁也负不了责任;在如此这般的世界上,我也根本不希望这个理论被人们普遍理解。我是说,从那种“现实”中逃之夭夭是为上策。本书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的课题是探讨此前的经验构造的内在关系。可是,我们习惯于亲近语言??符号系统,这使得另一个先入观被强化,它使我们忘却了“形象”问题。这个先入观就是对“物”的实在性的信念。我们历来所学到的,都是作为指示“物”的透明工具的语言,而不是形象。这个习惯使“物”变成了总是存在于语言之前的信念。对我们来说,它变成了永久持续地产生效果的信念。对知觉而言,物总是确实存在着的。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信念都不会消失。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科学都共同拥有这种信念。但是,“物”真是确实存在着吗?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一章反复品味。当我们知道“物”的概念是以某种先入观为基础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理解“形象”的意义和它对于经验而言的问题之所在。因此,在第一章我们将学习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那里,“物”这个概念的矛盾被阐述得井井有条。语言符号也是“形象”。这样说就意味着语言符号也带有“物质性”。就连那些应该最透明地传达内容的科学研究论文,也要依赖于语言不透明的物质性。他们要在该重点强调的地方变成黑体字或者标注下划线。我写这篇文章时,也是要考虑这些问题的。在我的文章里没有使用“ます”“です”体,也没有使用“である”体,而是采用了“だ” 的表达方式。那是因为我把这些文章交给几个年轻学生看的时候,他们说用“だ”体节奏感强,读起来舒服。在那些学富五车的人们看来,这种文体也许会给人轻薄之感。对这种批判,我是心悦诚服。因为我只是想让年轻学生读这本书的,所以才特意选择了这种文体。“语言符号”在人类经验上发挥的作用以及它和形象世界的关系是贯穿本书的主线。也许可以说,以时刻不脱离经验的方式这个问题,并且在形象和语言符号的关系上尽量做到公平合理不偏不倚,正是这一初衷才成就了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历来被称为“美学”的aesthetic。这个词汇的原义是“感性(aisthesis)”的理论。我采用其原义,定名为《感性论》。个中道理已如前述,因为形象不能完全归纳到“美”和“艺术”世界里,它是与经验全体相关的问题。本书使用“艺术”一词时,也有所限定。只有在言说近代以后传统性的“艺术”和在继承了这一传统理论中言说“art”“Kunst”的时候,我才使用这个词汇。其他场合,本书都使用艺术(art)。 我认为除了所谓的艺术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与形象有关,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些行为与“艺术”区别甚至割裂开来。比如,打扫房间、整理服饰和美容化妆等日常行为、炒菜和装盘子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某种形式把形象构造化的行为,它们作为与人类认识息息相关的行为也理应被称为艺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第四章,尤其在第四章详细讨论。本书主要考察康德、黑格尔、黑格尔学派、尼采和费德勒等所谓德国近代思想家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本书看上去或许有所偏颇。其一,法国和英美的思想、古代中世纪、还有东方思想不是都被遗漏了吗?其二,现代思想——所谓结构、解构的思想、现代精神分析学,还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还有在美学美术史学也流行着的文化研究不也是都被忽视了吗?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康德之后的近代德国美学和哲学。然而,本书在写作时念念不忘这些近代德国之外的思想和在现代日本也被广为关注的现代思想。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中重读上述思想家的理论,那些哲人们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时刻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至于大家能否意识到这一点,那只有去读了。我憧憬着,让近代的优质(我认为)的思考和现代思想去碰撞,由此构筑一种理论。让近代思想家和现代思想家同台竞技。这是我所要尝试的。我认为不能明确区分现代和后现代。后现代的思考继承了现代的优质的思考,并进一步使其发扬光大了。这样理解是不是更具有生产性?我当下就有这种信念。可是,我并不是主张现代思想所言说的,在古典思想里就早已有之。做这种事情徒劳无益。不是,我所要尝试的是从现代思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古典,那我们应该如何重读古典?换言之,古典能够复苏吗?已经成为古典的近代思想文本能不能重新解读?作为一种实验,我将尽可能结合我们的经验对此加以解释。从这一近代与现代的对话中构筑一种理论,这就是我的目标。这时,近代哲学家康德所要求的“人类公共知性(常识)的三原则”依然是促进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指针:一、“自我思考原则”,二、“站在所有他者的立场思考的原则”,三、“始终与自我一致地思考的原则”。这三个原则分别吁请着“从先入观中解放出来的思考方式”、“被扩张了的思考方式”、“首尾一贯的思考方式”。当然,完全从“先入观”中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把我们有限的思考扩张到“所有的他者”。然而,为了能够共同拥有思考,我们只能把这三原则当作努力目标,一步一步、尽可能认真地把这三原则渗入到我们的思考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至于我在此做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判定也只能拜托各位读者了。2002年10月17日中 文 版 序此次这本拙著被翻译成中文,使我能够有机会在超越日语的世界里得到读者,这对著者来说堪称望外之喜。我在这本书中所要尝试的就是要尽量具体地考察我们每个人的经验构造——它总是面向着未来被敞开着、被更新着——我就是要考察这个被开放了的经验构造。我们人类的这种经验,总是和“语言”、“形象”密切相关。仅只“语言”不能使经验成立。在“语言”的世界里没有矛盾而得以成立的经验,只要在“形象”的世界里加以确认,也会止步于简单的“观念”和“假说”的世界。比如,关于“宇宙空间”的“观念(假说)”(=“语言世界”),也只有在它作为一个眼睛所能见到的世界而被我们所经验的时候,它的正当性才能被实证。在语言世界得以成立的经验还仅仅是单纯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描绘的(观念)”,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是原封不动地与经验世界完全吻合的。因此,谁也不能把这种单纯的观念强加于经验,谁也不能这样解释经验,谁也不能这样诱导经验。如果是那样,就是对经验的压制,就是对经验所施加的暴力。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人类的经验,只依靠“形象”也是不能成立的。“形象”不断地包围着每个人,它是一个和每个人都不可分离的流动的世界。能够把我们从这种流动状态中拯救出来、能够打开我们“可以共有”的经验世界(“社会”)的,还是“语言”。因此,我们要公平地认识“语言”和“形象”之间的差异及其关系。这是考察我们的经验构造时的一把钥匙。如此看来,把经验整体纳入到具体的考察范围中,这无疑是本书的一种尝试。为此,本书就不能不超出历来的“美学(aesthetics)”范围,回到这个词汇(aesthetics)的原义,把它作为“感性论(theory of aesthesis =感性的理论)”来写。明治时期日本学习西方思想,并把它翻译成东方语言。这时,是日本人从古代就学到手了的中国的语言、汉字帮助了日本的近代化——借助于中国的汉字,再把这些汉字重新组合。只有通过这些方式,日本人才能理解西方文化,并把它们翻译过了。而被日本人这样翻译出来的新的汉字组合又被当时学习近代日本思想的中国思想家拿到了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日本思想作为联结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的纽带而被称为“日本桥”。中国近代思想的代表王国维就是这样说的。他通过日本近代思想而精通西方思想,并把它们输入到中国。王国维通过“日本桥”来接受西方思想,并且当时就积极主动地接受对中国有用的东西,这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本书也是在本人常年学到的西方近现代美学艺术学、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借助于汉字来写成的。本书能不能成为王国维所说的“日本桥”,这还要由中国的读者来判定。著者籍此翻译的契机,衷心祈愿围绕着我们的经验的存在方式,在年轻人中间把我们文化交流和交换意见的场所更加扩大,从而加深相互理解。本书的中文翻译是由于得到很多中国友人的热情支援才可能面世的。2001年3月到5月初,应暨南大学副校长、中文系教授蒋述卓先生之邀,我为该校中文系研究生以及年轻教员开办美学讲座,每周2次,共计15次。利用这次机会,我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三章的一部分的基础上编写了讲义。在离开日本之前,我完成了本书的校对,把稿子交给了出版社。我在中国期间,本书的日文版面世。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更是让人感慨至深。在中国讲学时为我做翻译的就是本书的译者王琢教授。他当时担任海南大学副教授,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王琢对日本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有素,日语能力亦优,这使得我在暨南大学的讲座更加充实,甚至每次课后还能和听课的研究生以及年轻教员们进行更广泛的交流。这次中国之行,我还有机会在惠州学院讲演一次、在广西师范大学讲演二次,都是王琢先生做的翻译;把我推荐给蒋述卓先生的北京艺术研究院李新风教授也邀请我在艺术研究院讲了一次,担任翻译的是研究日本文学的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王志松先生。暨南大学讲学遂成机缘,王琢先生提出把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意愿。而为了使他个人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我们申请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王琢先生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来到日本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也以外国人共同研究员的身份接受他来到我所在的美学美术史学研究室进行研究。其间,王琢先生一面进行自己的课题研究,一面就本书翻译过程中的语言问题等和我交流意见。本书中文译本就是这样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们共同制作的“日本桥”。这项“架桥”作业也得到了很多中国友人的大力协助。前边已经提到的蒋述卓教授以及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各位教授,李新风教授,从暨南大学讲学后就一直交往、以至成为畅抒己见的莫逆、对本书的翻译也提出过很多意见的广州美术学院邵宏教授,惠州学院杨小青教授、伍世昭先生,惠州客家文化节中华客家团策划人严忠明先生,书法家李杰先生,广西师范大学王杰教授、张利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志松副教授(当时)……还有,当时暨南大学外事处的罗晓红女士以及热心听讲、积极参与讨论的那么多的学生、年轻教员……还有,在中国讲学时给予我很多照顾的那么多的中国朋友——是你们的热情和诚意从各个方位支撑着这座“桥”的,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在享誉世界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也使著者感到荣幸之至。在这项“架桥”作业中,译作编辑室的王仲涛先生和徐奕春先生也都付出了校正之劳,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著者2005年元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什么时候开学
 钝根
钝根
 40004-98986
40004-9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