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古典占星研究PDF谁能分享一下吗?很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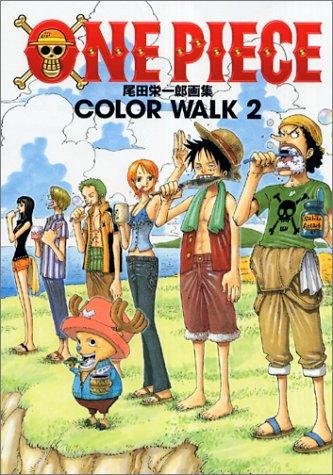 凡交
凡交现代占星与古典占星有哪些区别?
 关于你
关于你 指南针
指南针
占星术,亦称星象学,是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系统。它试图利用人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和天体的位置来解释人的性格和命运。占星术的解释只是趋向性的,它并不能做预言占星术,它并不能做预言。古代的占星分为四个部分:一,讲述宇宙形成的过程,接着讲述了天地、阴阳、日月、星辰、火水、风雨、雷霆、雾露、霜雪、动物等事物的生成的原因,以及日月阴阳四季与动物变化的关系。二,四时、日月、星辰、虹霓、彗星等天时星象与天的关系。三,月与太岁的运行关系及其星占,太乙在冬春的时刻,阴阳二气与音律。四,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运动变化与人事、音律之数的关系,音律与十二月的关系,音律之数与度量衡之间的关系。现代的占星:建立在经验观察结果以及行星符号的传统意义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实验和人们的反馈加以验证,在清晰的基本原则之上严格运用,藉由研究和探索,不断更新和发展自身。现在的占星都是看星座,出生年月来判断的。其实古代的占星和现代的占星都有很大的区别。古代的占星并不是没有用,只是他们的古代人的手法,和方法不一样,从而来判断占星的运势,但是随着时间不断的流长,这些历史性的东西也慢慢的都消失了,他们的遗迹也被淹没了,并不是古代的占星不好用。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十分的迅速的,但是很多还是利用了古代人的一些手法来决定。但是古代的占星比较复杂,而现在科技又比较十分的发达,可以用计算机直接简单的来运算星座的运势。古代的占星是历史文化,现在的占星只是大部分模仿古代历史,从而加入新的元素。
古典占星和现代占星有什么区别
 冼星海
冼星海 大演习
大演习
通俗的说,古典占星以论事件为主,尤其是判断好/坏,吉凶等。现代占星是将占星与心理学融合得出的产物,以论性格为主。让普通人跟容易理解自己身的性格特点,从而去客观看待进而调整自己去做出更好的选择。古典与现代,不冲突。反倒一脉相承。论据和论点都具有相通性。个人觉得,若有时间,尽量现代/古典都学习。能够更好的理解占星体系。亲若觉得回复有帮助,请采纳哟。
古典占星和现代占星那个准,有什么区别?
 当然
当然推荐几本古典占星的书籍
 伯夷
伯夷谁有古典占星的资料,基督占星方面我有了,希望给点基础的资料
 顺之则成
顺之则成占星看什么书
 其一
其一 月兔
月兔
现代占星,这些作品随便看。课程也很多。古典占星可以看 当代古典占星研究,实用占星学 ,the horary textbook。看完这些你大概有一些占星基础,并入门了卜卦占星,之后的路太多了,我也懒得列举了
无神论和有神论所讨论的"神"是专指创世主神还是连神仙精怪类也包括?
 不是她
不是她为什么很多哲学家都是研究过法律的?
 大喷发
大喷发 频道
频道
德沃金:我们的法官必须成为哲学家吗?他们能成为哲学家吗?傅蔚冈、周卓华 译 一、两难选择 本文题目就表明了一种两难选择。在法官的寻常工作过程中,他们需要对很多问题作出决断,而这些问题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也是一个重大哲学著作的主题。法官需要对以下问题作出决断,比如什么时候被指控犯罪的精神病患者仍然需要对其行为负责,被告的某一特定行为是否于事实上导致原告遭受损害,而责任及因果关系的概念也是哲学研究的永久话题。哲学问题在宪法中尤其突出;在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做出的关于堕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安乐死和言论自由等最富戏剧性的判决中,它们都是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胎儿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人吗?如果是,这些权利中包括免于被杀害的权利吗?甚至当继续怀孕会造成母体的严重不利或者是伤害的时候还享有这项权利吗?如果不是,国家对堕胎的禁止或管制还有任何其他根据吗? *允许各州计算本州各大学和学院的申请人的种族比例来决定录取人数,是不是违反合众国对其公民的平等保护条款?这与根据申请人的能力倾向测验(aptitude tests)成绩或者是篮球水平来决定取舍有差别吗? *我们是否总是应当根据“价值”(merit)来配置稀缺资源?“merit”到底是什么? *拒绝承认一个生命垂危的人选择自己如何去死以及何时去死的权利,难道这就不违反有关一个优秀政府所应追求的基本信念?公民是否拥有对于个人问题在精神上的独立决定权,这种权利意味着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吗?这个权利是不是最高法院所陈述过的通过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有序自由(ordered liberty)理念的一部分? *在堕胎和安乐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如果说宪法授权怀孕妇女拥有堕胎的权利——正如最高法院的判决表明的那般,这是不是允许生命垂危的病人有选择怎样死和何时死的权利?经常被引用的“谋杀(killing)”和“被动安乐死(letting die)”之间的区别在安乐死的争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停止治疗的消极行为和开出致死处方的积极行为之间是不是存在道德上的中肯的(pertinent)区别? *为什么政府需要给言论自由提供特别的保护?顽固分子以污辱性和挑衅性的语词攻击少数种族是不是也在这个自由之内?这是不是说政府机关的候选人有权将尽可能多的财力花费在他们的竞选上?或者说捐赠人有权将尽可能多的钱财捐献给这些竞选活动? 以上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方法解决的实质上的经验主义问题。摆在法官面前的事实和预测必然重要吗?甚至有时是至关紧要么?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它们都不是事实问题,而是价值取向问题,它们不仅要求固定明晰的原则的承诺,还要求对这一点的反思和对这些原则明确简洁的表述,以及对这些原则之间的联系及可能存在的矛盾的思考。这就是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天职所在。法官和哲学家并不仅仅像天文学家和占星家那样共享交*的话题。相反,法官的目标和方法包括了哲学家的目标和方法:这两种职业的目标是更为准确的表述并更好的理解此关键理念,而我们的政治统治道德和基本法律就是据此关键理念得以表达的。 因此,很自然的,我们要求法官在处理宪法案件和宪法历史的时候要对哲学著作具有相当的了解,就像现在希望他们能了解经济学一样。当然,他们不能简单地在那些官方的或者是艺术级(state-of-the-art)的哲学手册中寻找答案,因为哲学家们对以下问题的分歧极大,包括什么是责任、因果关系、人格、平等和自由言论的最佳理论,以及“被动安乐死”是否等同于“谋杀”。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法官对哲学家的著作视而不见是正当的:正如法官能从案件中双方律师所作的相反的案情摘要(briefs)中受益一样,假如认为法官不能从研究哲学家们不同的甚至是相矛盾的理论中获益,这对于法官和哲学家来说都是一种侮辱。法官的工作不仅对于涉案双方当事人极为重要,对于宪法和国家的治理也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法官所面对的问题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投入生命而为之争论的问题,那么,法官怎么能够忽视他们所留下的那些意见呢? 这就是这个两难选择的第一面。现在让我们来看另一面。要求大多数的法官拥有和哲学专业毕业生一样的对从古以来的大量的哲学著作的理解力,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法官的时间非常宝贵,增加他们的任务让他们在速成班中了解当代最主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的主要观点和争论,比如说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托马斯?斯坎隆(Thomas Scanlon)或者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观点(暂且不管伟大的古典哲学家),[2]*这是很荒谬的。即使是在综合了哲学家们的杰出贡献和实际应用之后,大多数法官确实成了自觉的哲学家,我们不要指望他们会以专业哲学家的语言书写司法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应当更易于被普通公众而不是少数人所接受。难道我们真的指望我们的法官分成不同的哲学流派,比方说,康德占据了第二巡回法院,而霍布斯统治了第七巡回法院?如果司法裁判取决于法官倾向于哪一个哲学家的话,这难道不是一场噩梦吗? 法官必须是哲学家,但是法官不能、也可能不应当是哲学家。这就是我所指的两难选择。现在有两个办法可以尽量避免它。法官必须是哲学家,我们会说这毕竟不是真的。或者他们不能成为哲学家,我们可以认为这也不是真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他们能足够哲学化就可以减缓这个两难选择。第一个避免的途径是目前更为流行的,我将在下文对此展开论述。然而,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所有据此途径所采取的策略都是失败的,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通过第二条途径是不是更有成效。 二、概念、法律史和原意 刚才我已经谈到,法官对哲学家研究过的相同概念感到踌躇。但是此一主张应当受到质疑:不管其最初面貌如何,只要它们不是真实的,法官就可以完全忽视哲学。而这种质疑最为戏剧化的形式就是争论律师和法官所使用的这些语词,比如“责任”、“因果关系”、“平等”、“自由”等,这些词事实上所指的是严格的法律概念,而与哲学家运用这些词所指的日常概念并不相同。毫无疑问,很多时候法律人所使用的语词虽然和日常用语是同种拼法,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当一个律师说合同无须遵守,除非“对价”(consideration)已经给付,此时consideration的含义与其通常含义几乎完全不同。但是,我所指的这个概念虽然是真实的,却很难被人接受。政治家和法官都保证:任何没有行为能力的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又都会将常见的道德判断和原则付诸法律实践,因此政治家和法官使用的是在上述判断和原则中体现出来的概念。但是,假如我们认为立法者们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特定法律概念,就像他们在使用拼写为responsible(负责任的)和equal(平等的)所指明的那样,我们将会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动机不明或者不正当。 然而,对此质疑现在有一种更为复杂和似是而非的形式。法律实践和先例制度常常修正着从日常用语中提取而来的语词的含义,如此,一个当代的法官根据某种哲学理论或理解来解释这些语词的自由变得极为有限。刑法、财产法、合同法和侵权法必须主要是通过技术性规则构建而成,公民、所有人、立遗嘱人、商人和保险公司只要通过理性的思考就可以预测出它们的运作,先例在这些领域中具有很大的价值。假如先例已经将刑法中的责任或者是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作了规定,那么法官就没有自由推翻这些先例,他为什么还需要查明是否某个哲学家对此先例所确定的规则持强有力的异议呢? 尽管先例限制了法官可以依据职权对许多重要概念作新的理解,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些私法领域就排除了法官的这个职权。法官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新鲜而又难缠的案件,这就迫使他发展那些先例所未能预见的概念,如果他也这么做了,他就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得出何时人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何时两个事件中存在因果关系,如此等等。准确地说,就是在这些“疑难”案件中,法官有责任维护与过去法律史的整体性:他们不能诉诸那些在过去的判决和学说中找不到根基的原则判案。整体性(integrity)将会禁止我们所说的异乎寻常的(outré)或荒谬的哲学:假设对量子力学的思考导致一些哲学家得出一种关于因果关系的激进的新观点,比方说,比休谟更具怀疑性?在整个社会未能普遍采纳这些观点之前,法官将无权对这些新发展做出评价。尽管这些关于整体性的要求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这样他们就不能赋予法律概念与日常用语不同的含义:即使法官限制了其对与法律相关的因果关系学说的注意力,他仍然能够漫游于许许多多的哲学著述之中。 在那些更具公共性的法律领域中,这也是我在此将主要探讨的,法官所面对的哲学问题更多,也更为明显。当面对一些特别疑难的案件时,法官在宪法性判决中所作的哲学选择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按照常规。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也是为自由主义哲学所赞美和追求的,假如一个法官需要判断某种特殊形式的言论,比如商业广告,是否属于此言论自由的范畴,那么他就会遇到那些与无数政治哲学家在不计其数的书中所探讨的相同的原则性问题。当然,即使是在宪法领域,先例还是司法判决中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先例也确实限制了法官根据其个人的道德观念来修正宪法性概念。但是,宪法领域呼唤更多的新颖判决。在私法领域,要找到新颖的判决总是很难,因为它们已被置于固定的边界内。而在宪法判决中,所谓的疑难案件并不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原则的限制,而是因为它们提出了对建立原则之根基的质疑。问题是通常所理解的言论自由是否该保护那些散布仇恨的言论或者那些迫害少数种族的侮辱性或攻击性言论?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禁止此种言论是否必需?而这些问题都要求对政治道德中某些最为深层的问题进行反思。在这样的案件中,先例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法官会以先例不正当地限制了重要的个人权利为由认定先例是错误的,从而与认为普通法中某些固有的先例是错误的法官相比,他们有更多的理由不尊重先例。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法官和哲学家拥有不同目标的争论之第三种形式,此一争论对于宪法而言尤为重要。此种争论始于承认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很多重要的宪法性概念正是那些被很多哲学家们所研究过的概念。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法官的目标不应是发现关于责任、人格或者自由的最佳理论,为此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求助于哲学家;相反,法官的目标应该是发现那些使这些理念成为法律一部分的人所主张的最佳理论是什么,而这些均为历史问题,而非哲学问题。 现在,宪法判决中的“原意”模式在宪法学者中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流行了,对此的反对意见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我们接受这这个理论,它也不能避免我所说的两难选择,因为它会使宪法更多地纠缠于哲学问题,而不是更少。对法官而言,接受这种模式就必须面对一系列在哲学思维、哲学语言和政治哲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作为一种解释方式,当我们论及那些共同制定了宪法及其修正案的一大群人的理论、意图或认识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许多不同的事物。但是我们所不能清晰明了的是他们所共享的理论、意图或认识,比如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并没有任何关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理论,或者他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 那么,在现有的可能解释中,我们应当接受哪个理论呢?即便我们将任意选择一个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观点?是起草了大部分被质疑条款的那一个?于是,我们的哲学难题随之而生。假如我们发现(根据他所使用的语言,这看起来很有可能)第十四修正案中平等保护条款的主要起草者的本意是根据对此条款的最佳理解来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而不是根据他当时的个人理解(他可能也意识到这种理解是不完善的),在这些情况下,什么是需要被尊重的原意?一个当代的法官会在忠于原意后又被要求根据立法者事实上的意图来解释该条款吗?如果是这样,那不是又把他送回到原意主义原则所希望避免的政治哲学之中了么?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难道不应当问为什么法官应当考虑原意?答案也许会被认为可在民主或法治中找到。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些高度抽象的理论之相互矛盾的概念中做出选择来回答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而这样又会将我们置于更为复杂的哲学争议之中。那么,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 三、本能和直觉 如此,第一个迂回进路——法官和哲学家没有任何共同的主题和目标——是一种幻想吗?至少就包括宪法概念在内的最重要的法律概念而言是这样。因此,我们应当以更大的雄心考虑其他方式来避免我所建构的这个两难选择的第一面。 首先,我们可能会称赞法官并未依*咨询哲学家来处理哲学问题,而是凭借自然本能或“内部”(gut)反应。在安乐死案件中,最高法院要认定在医生对求死病人中止治疗——在法院看来,各州实际上并没有对此做出禁止——和医生以积极方式帮助病人自杀之间是不是存有区别,比如说,给病人开可致自杀的药,或者给一个求死但又无法吃药的病人以致命的注射。如果各州没有禁止前者,那么它就有权禁止第二种吗?而这就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放任他人死亡和谋杀之间究竟在何时和多大程度上存在道德上的差异?此时大法官们就有可能需要参考哲学著作,然后努力解释他们将如何选择及其理由。当然,很多持相反的观点的公民无法被法院的意见说服,但是他们也知道大法官们个人同样为这个案件而迷惑,还尽力解释他们为什么觉得它没有说服力。但是,我们刚才的讨论表明,法官是不应该这么做的。他们应当忽视哲学家的观点,而是简单表明他们对此问题直接和自然的反应。 大法官拜伦?怀特(Byron White)曾经说过,虽然他不能给“淫秽”一个定义,但是只要他看见就能判断什么是“淫秽”。我们的新提议将使此种策略推而广之:法官不应试图分析那些疑难的哲学概念或者思想,而应仅仅表明他们的本能反应。当一个医生根据病人的要求中止治疗,而不是给病人开出致命处方,如果法官的本能认为此行为在可容许的范围内,那么他就不必要为他是否要以说理的方式来论证他的直觉而担忧,法官只要表明他就是怎么想的,或者表明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于此类问题的直觉,或作出诸如此类的回答。 有许多著名的司法判决支持了这种建议。霍姆斯说过,他只需问自己是否会为此行为呕吐就可判定警察的某些取证方式是否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也许这就是所谓“法律现实主义者”之格言的渊源,即“正义取决于法官早饭吃了什么”。)难道这就是判决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我确信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的判决的合法性应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即法官的判决是有理由的并对他们的理由做出解释。(除了期望为自己免除一个难办的任务以外)什么能够证明法官以如此明显随意的方式处理极其重要案件是正当的呢? 我所能想到的两个论据都不能表明它们减少了哲学争议,而是增加了哲学难题,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富有争议的哲学立场之上。如果我们有理由解释法官为什么不需要成为哲学家,那么法官将会为了理解这些理由而成为哲学家。这两个论据中的第一个尤其适用于我经常举做例证的概念:即存在于宪法判决中的道德概念。这个论辩是建立在被称为“直觉主义”(intuitionism)的哲学论题之上,该主义认为人们无需任何思考或者论辩,都有与生俱来的本能使他们能直接感知道德争议的真理。(根据某些直觉主义的观点,思考和论辩实际上会使我们对正义的感知迟钝化。)直觉主义并未得到道德哲学家的普遍支持,至少在盎格鲁-美国分支的哲学家中间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就是错的。它很有可能在一段时期或者某一天得到复兴而成为哲学领域短暂的时髦。但是直觉主义确实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使得它几乎无法成为法官拒绝提供解释的正当事由。它建立于一种想象中的人类所固有的不反思和不争论的直觉上,基于一种感觉模式——但这几乎是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道德事实和人的神经系统如何能够令人信服地相互作用?而且,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拥有此种本能的假设似乎与他们拥有如此多元和冲突的道德观念的事实相矛盾。直觉主义者强调有些人的想像是有阴影的。但是我们如何知道谁的想像是有阴影的呢?谁的直觉能力是有缺陷的?除非问问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道德观念,然而这样做同样不能让人满意。 支持法官以直觉、快速或者草率的方式来裁判的第二个论据同样适用于对道德概念施加特殊的压力。这就是“道德怀疑主义”,它主张在人格、自由、平等或民主等所谓的哲学问题中,并不存在着正确答案,因此法官就不应浪费时间来寻求正确答案。因为任何一个答案都只是一种选择,根本没有任何深层的原因,法官在决定答案后最好立刻把它们打造成正确的:如此将这些答案挪作他用时就能够节约时间和精力。(呕吐测试的创造者霍姆斯,就是一个道德怀疑论的热情追随者,只有我们完全了解这一事实才能对他的一生的和著作做出解释。)我再次强调,此一忽视哲学的论据是建立在有争议的哲学立场上的。(在我看来,这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当今绝大多数流行的模式都不存在着一致的立场。)[3] 绝大多数的法官都和霍姆斯不同:他们并不是道德怀疑论者,他们忽视哲学是因为怀疑论是对的——此论据对他们而言并不见比我而言要合理,我希望对你也是如此。 四、实用主义 通过对于两难选择的第一个侧面——法官必须是哲学家——的否定,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和否决了两种逃避两难选择的方法。我们不能够通过宣称历史已经将哲学家所研究过的因果关系、人格或平等等法律概念改变得面目全非了,而有理由逃避问题。历史确实塑造了法律概念,但是它们仍然在开放中保持发展,如果法官要发展这些法律概念,他们就必须像哲学家那样向自己提出一些相同的问题。当法官不经研究或思考就根据自己的本能做出回答时,我们就不应该通过宣称法官已经最好地回答了这些疑难问题来逃避问题。 于是,这就有了第三条可能的策略,这个策略最近在学院派律师中大受欢迎。他们中的很多人建议法官绕开纠缠着哲学家们的传统问题——诸如到底什么是责任、因果关系、平等和言论自由的真实含义,或“被动安乐死”是否真的不同于“谋杀”——通过信奉一种不同且明显激进的哲学传统,名曰实用主义,它鼓励法官:在法官使用了这些概念后是否真的给这个社会的未来带来了一些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那怎样能达致最好的未来?是通过不让堕胎这个烦人的问题成为高度抽象的哲学难题么?比如说,胎儿真的拥有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吗?我们应当使之成为一个更为实际和易于处理的问题,如此我们就不需要依*哲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最终会受益于禁止堕胎这个决定吗? 当然,哲学姿态有其自身的时尚,实用主义和它那个更为时尚的姊妹——社会学,已经在学术界流行一段时间了,它们在法学院也有一个从热门到冷门直到消逝的过程。但是至少在现有的语境下,实用主义是空洞的,它对于我们逃离这个两难选择毫无帮助。实用主义告诉我们,法官会将关于堕胎的抽象难题置之不理,而只需要问假如禁止妇女堕胎,其结果是不是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们无法判断:回避了实用主义者所要避免的哲学问题的宪法判决的结果是否就比其他判决好。 假想一下,如果堕胎受到宪法的保护,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堕胎,更少的妇女会因一个她不想要的孩子而毁了生活。(当然,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后果,某些是很难预测的,但是这个结果会是突出的。)那么,在她们看来,这个结果就意味着事情变得更好?或者更差?我们如何能在未判断堕胎是否实质意义上的谋杀之前就对此下定论呢?如果堕胎是谋杀,无论在其他情况下它们看起来多么美好,事情是不能变得更好的。另一方面,假设法院判定堕胎不受宪法保护,然后许多州接着宣布堕胎是犯罪。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在公众的争议声中慢慢消逝,每个人都将接受这样的变化,比如说,有条件的妇女会迁移到允许堕胎的州,而那些没有条件的妇女只能毫无怨言地生下她们的孩子。如果公众冲突变得更少,事情就会好多了。但是对于那些被拒绝堕胎或者为了堕胎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妇女,在我们判断她们是否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之前,我们无法确认事情已经变得更好。当然,我们可能会认为对于某些人的不公正对待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因拒绝堕胎而变得更好(或至少不那么分裂)。但是,我们是否有权认为取决于哲学领域中的另一个道德问题,即功利主义是否就是正确的。于是实用主义就因为它需要检验是否有好的后果而成了一种毫无成果的空泛姿态。人们因此分裂,原因是他们对于这个实用主义声称可以回避的问题的最佳答案意见相左。 五、新形式主义 那些空洞理论(比如说实用主义)令人惊讶的流行更加证明了我在开头描述的两难选择更为严重了。自从数十年前此理论被美国律师广泛了解后,形式化的法律实证主义成了对法官所作所为的令人绝望的不适当的说明,他们害怕做出选择:司法判决所要求的对于道德问题的判断是如此之深入和分化,以至于他们成了深入和持续的哲学研究的对象。非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有权处理涉及当事人和国家的永久性问题,这看起来令人惊愕。有观点认为,法官通过将他们的注意力从争议的原则转换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和结果来裁判包括宪法案件在内的疑难案件,但是这种观点只是一些法律学者将他们的头部埋于沙子的可怜行为的又一例证。法律职业公开面对美国公民在道德问题上深刻分裂这一事实的时候到了,司法判决不可避免地会卷入这些问题,而法官也有责任承认并解释他们采取任何立场的原因。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法律是如历史和实践所造就的那样,展现出哲学维度中的各种概念,假如所有这些我们用来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时能摆脱对那些概念永无止境的论战的设置都失败了,如果我们意识到要求法官本身成为哲学家的期望是不现实的,是无法被接受的,那么我们只剩下一个指望了:我们能够根据现在的情况将法律改变得更适合于那些坚守纪律而较少雄心的法官。最终,我们必须转向如前所述的那种最为激进的逃避方式,即所谓的“新形式主义”。边沁痛恨被其称为“法官有限公司”(Judge & Co.)的制度,他认为应当通过编制成文法典来约束法官像哲学家那样作为的权力,如此司法判决就变得机械化了。尽管和我同辈的法律人对此观点均表惊奇,但是边沁的影响尚存,甚至比两百年前更甚。现在有持续的热情支持这样一种使判决更为机械化的法律制度。 尽管各种各样的学者和法官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能发现这种新的热情,比如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 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 弗里德里奇?舒尔(Frederick Schauer)和 凯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4]*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形式主义者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期望改变法律和法律实践,以减少法官在决定依照什么法律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从(根据边沁的风格)编纂法典,到催促创制新原则的法官阐明那些脆弱的规则,这样他们就能机械地适用法律了(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大体的原则),还有斯卡利亚所设计的法定解释法(此法要求法官不应推测立法者可能有的意图或者目的,而是采用最符合原文的文意解释)。 新形式主义也是对我之前所谈到的宪法判决“原意”原则产生新热情的原因。对此原则的第一个推动力来自于语义学和解释学:其拥护者强调,按照现在的情况,宪法应当和制宪者对文件中道德概念的理解相一致,而不是与对这些概念的最佳理解相一致。但是,新形式主义者的说法并非语义学的而是战略性的:他们要求法官探寻原意的目的不是为了代表宪法的真实含义的积极理由,而是为了一种消极理由,即以此裁决案件的法官无需展开他们个人的道德或哲学确信。正如我已经讨论过的,这种策略必将失败:这并不是让法官逃避哲学的办法,而只会让他们陷入哲学争议的深渊。 但是,我们应当从总体策略意义上来考察新形式主义的价值。不能够仅仅因为它能将法官从困难的或有争议的判决中解脱出来,就成为接受回归于机械法理学的理由。这就等于是让尾巴去摇摆小狗::我们应当首先决定统治我们的法律制度的类型,然后才决定法官在这样一个制度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我们也许有很多理由希望被一些更为机械的规则所统治,可能它们在法律的某些领域,尤其是私法领域是好的理由。我们也许相信在这些领域中我们会做得更好,我们可以要求法官对人们事务的干涉限制在立法机构创制的脆弱规则范围内,让立法机关来决定规则什么时候需要被澄清或改变。但是,我本人并没有被这些理由所说服,我相信如果扩大机械化司法判决的领域,我们将失去更多而得到更少。 当我们转向我所举的几个主要的宪法例子之时,我对新形式主义的反对将更进一步:这样将会从根本上推翻我们整个宪法框架的根本设想,即认为公民有权免受易变且自利的多数人判决的损害。正如我之所言,作为一种语义学和历史学,老的原意学派假定应根据长眠已久的政治家们的理解来限制那些权利。老的原意学派认为这就是据其本来面貌来保卫宪法。在宪法领域,新形式主义者并没有作这样的假设;他们的论争是革命性的而非解释性的。他们承认:他们建议的改变会急剧削弱法官推行他们所认可的宪法参考资料: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49386/

 40004-98986
40004-98986








